在新作《那些少女沒有抵達》的寫作過程中,吳曉樂曾經擔心:會不會有人在讀了這本小說之後,跑出來質疑她厭女呢?
這樣的擔心,是基於她打造「母親」這個角色時的一個選擇。從小說的第三頁開始,讀者就能看到女主角承受著母親的高壓控管,之後更會發現主角因而深受創傷。但在此同時,吳曉樂卻選擇不將母親的作為歸因於任何「苦衷」──她選擇不讓母親出身貧窮,或者童年時曾被惡待,甚至還讓這個角色在事業上也相當成功。
這樣的設計,違背了近年來流行的某種套路:母親之所以會對自己的小孩殘忍,總是因為過去被壓迫的經驗,再不然也是因為某些長期以來的辛苦。更廣泛來說,造成傷害的女人,似乎總是要有自己的苦衷,即使她壓迫的是另一個女人。
依循這樣的套路也許是容易的事,但吳曉樂拒絕這麼做。
相反地,她批評這個套路:「這好像認為女人是完美的,總是只有被迫害之後才會迫害別人。」她認為,這樣的套路陷入了某種溫情主義,「而到了2023年,這種說法已經不再能說服我。」
➤告別溫情主義,承認女性不同的樣貌
吳曉樂的批評,其實源於她在創作過程中的自我反省。5年前,她出版小說 《上流兒童》,同樣關注強勢逼迫孩子前進的母親,但讀者不難看出,媽媽的執念源於她的家境、她的成長背景,而故事的結局則是母子之間的諒解與和解。
《上流兒童》,同樣關注強勢逼迫孩子前進的母親,但讀者不難看出,媽媽的執念源於她的家境、她的成長背景,而故事的結局則是母子之間的諒解與和解。
但後來,這本書被引進到法國,法方出版社卻表達無法認同這個結局,希望她能夠更改。吳曉樂回憶,當時聽到對方的說法,她非常震撼,也才突然意識到,她原以為合情合理的劇情設計,其實「也陷入亞洲的某種主義──我也不願意接受她是一個『人』」。
因為,如果我們接受媽媽們也都是人,就不再需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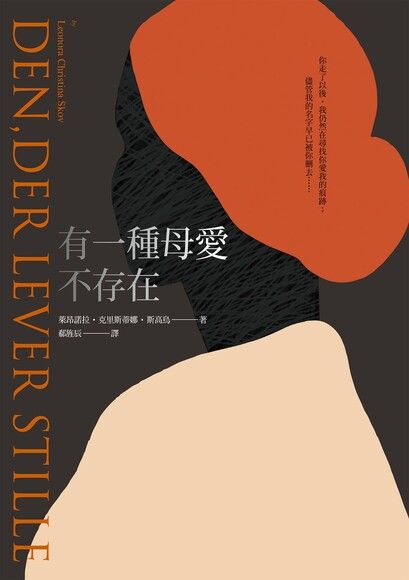 執著於一定要給她們好的、和解式的結局,彷彿女性總是苦情,而她們的苦衷又都終究要能夠被理解、被體諒。吳曉樂說,在讀了丹麥作家斯高烏( Leonora Christina Sko)的小說《有一種母愛不存在》之後,她的想法更為確定。
執著於一定要給她們好的、和解式的結局,彷彿女性總是苦情,而她們的苦衷又都終究要能夠被理解、被體諒。吳曉樂說,在讀了丹麥作家斯高烏( Leonora Christina Sko)的小說《有一種母愛不存在》之後,她的想法更為確定。
小說中的母親無法接受女兒是同志,甚至把自己罹癌怪罪到女兒頭上。女兒相當痛苦,而且,她最初的反應也是去尋找母親性格的成因,但找了許久,卻發現母親真的沒受過什麼創傷。說到這裡,吳曉樂語氣嚴肅:「當我們一直想證明某個人有創傷,這代表我們只願意看到一部分的人。」
換句話說,當我們安於「為母親找創傷」的套路,反而意味著我們還沒準備好看到女人的各種樣貌,只因為某些真實的樣貌將會讓我們感到不舒服。
唯有告別這種套路,我們才能好好體察社會上真實存在的性別不平等,以及性別的各種幽微影響力。就以《那些少女沒有抵達》為例子,吳曉樂說,與其認為主角吳依光的母親有任何創傷,更有力的觀察可能會注意到:身為事業有成的女性,母親在往上爬的過程中,很可能必須內化社會上「成功男性」的各種標準,因此「學會揚棄陰性的價值」。她甚至還要學會使用各種暴力──即使並非肢體的,是情感上、精神上的暴力。而在與女兒的關係中,母親正是不斷要求女兒壓抑感受,並且動用情感上的暴力強制執行。
不論如何,女人也可能施行暴力,也可能賤斥重要的陰性價值。這個念頭可能讓人不舒服,卻是現實。吳曉樂認為,書寫這個令人不舒服的現實並不是厭女──反而,各種套路對於母親、對於女性樣貌的扁平想像,「或許才是真正的厭女」。
「我認為這本小說,是我理解女性身分的莫大里程碑。」吳曉樂自信而且肯定。
➤接受那些不得而知,甚至享受沒有答案的狀態
是現實就應該當做現實處理,所以《那些少女沒有抵達》拒絕給出輕率的、斬釘截鐵的答案,即使那樣的答案可能看似合理,也令人感到安心──針對性別、針對母女關係如此,針對其他問題亦然。
小說裡許多地方沒有確切的答案。最明顯的莫過於,直到小說最後,吳依光還是無法清楚解釋母親為何那樣對待她。而在這個問題之外,故事中還有其他疑問,也是最終都沒有解答。
比如重要的支線劇情:發生在學校游泳池的不幸事件,只有兩位當事人在場,而這兩名少女各執一詞,講法並不一致。讀者或許會在情感上比較希望哪一方是對的,但文字本身確實無從推知孰是孰非。偏偏這個事件又後果嚴重,尤其對吳依光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談到這段情節,吳曉樂笑說:「身為作者我也不知道真相,而且是角色有意識地讓我不知道,他們把我這個作者也block(阻擋)在外面了。」不是作者偷懶不設計,而是作者筆下的角色自己就會去主動隱藏真相。畢竟,此事涉及兩個高中生心裡的祕密與糾結,不論哪個版本正確,都足以證實一名少女陰暗的念頭,而雙方又都有說謊的動機──角色自己不會讓旁人知道,於是作者和讀者就跟吳依光一樣,也不可能知道。面對這樣的不得而知,吳曉樂承認,「我如果是吳依光,也一定會陷入巨大的困惑」,但這也是必須接受的事。
而吳曉樂甚至不只接受而已。她說,面對不知道答案的事,她經常是享受的。「在小說裡,我們可以不要給出答案,這是我在寫作中最大的快樂。」
關於這點,吳曉樂分享了一個軼事。她的伴侶是律師,工作經常需要寫訴狀,而訴狀有制式的格式,寫作時又必須不時引用判例和法規,還得一字不漏、複製貼上。「寫1000個字,可能有600字在寫之前就已經決定好要長什麼樣子。」有一天吳曉樂在寫作時,伴侶經過她身旁,看了兩分鐘,問她怎麼知道等等要寫什麼,吳曉樂回答:「我不知道,而且你現在看我寫了這一頁500字,等等你一離開可能都會刪掉。」伴侶很驚訝地問:「這樣難道不恐怖嗎?」吳曉樂的回答是:「我覺得你們那樣才恐怖。」

Midjourney製圖
現實中本來就會有很多的不得而知,關於真相、關於原因、關於前進的目標與過程。既然如此,對吳曉樂而言,如果還被期待凡事要按照常軌、給出確切答案,反而才是真正的恐怖。
「我受夠了臺灣一定要有答案這件事情」,說到這裡,吳曉樂音量提高,語氣堅定。她說,大學就讀臺大法律系,最後卻拒絕從事法律工作,正是因為她對此感到厭倦。「法律系有個東西讓我很累,就是一定要有答案。畢竟花幾十萬塊、幾十個小時打了一場官司,法官不能說『我不知道』。」
「而我想要停留在那個『我不知道』的狀態久一點點。」吳曉樂這樣說。
➤一起練習,踩上佈滿灰塵的地板
發現自己不知道確切的答案,甚至可能永遠無法得到解答,是件令人感到困惑的事。但吳曉樂認為這並不恐怖,相反地,以為凡事必然能得到確切答案,對她而言才是真正的恐怖。這就如同,描繪女性的可能樣貌之一,書寫其恐怖與難以索解,這些並不是厭女的舉動;相反地,以為凡事都可以依照套路理解,而拒絕看到人們真實的樣貌,才是真正帶有偏見。
不符合套路的女性樣貌,以及不得而知所帶來的困惑,這些都是會讓人感到「不舒服」的課題。而《那些少女沒有抵達》當中,吳曉樂正在陪伴讀者一起面對這樣的課題。
不舒服,但是沒有關係──對此,小說中的隱喻,是踩在佈滿灰塵的地板上。
這個隱喻出現在小說接近結尾的地方。吳曉樂說,她猜想多數讀者可能不覺得這個場景特別重要,但這是她身為作者非常重視的段落。在這個段落裡,吳依光回憶起她小時候趁暑假拜訪住在美國的阿姨。阿姨不像媽媽那麼要求整潔,家裡的地板上因此積了不少灰塵。有一天,吳依光臨時起意,踢掉拖鞋,光著腳踩在階梯上。一開始,吳依光覺得好髒,好不舒服,但多走幾步,髒還是髒的,但她意識到「原來弄髒,不過就是這樣」。
歷經了故事中的許多波折之後,女主角回想起這個童年記憶。吳曉樂說,這是吳依光的「練習」──她是個敏感的人,但一直以來,不是被母親強迫壓抑自己的感受,就是被自己敏感的感官控制。直到這個場景裡,她才有機會練習面對「灰塵」,練習怎麼回應踩上灰塵時感官給她的訊號。
對此,吳曉樂用了一個精準的詞:吳依光在試著「馴服」她自己的感官。「馴服」意味著違背母親的教導,不再壓抑自己的感受,但另一方面,「馴服」也意味著,即使在踏出第一步時,感官不斷傳來「不舒服」的訊號,她仍不容許自己被這樣的感受壓倒,仍然要求自己往下走。
去練習馴服自己的感受。去允許世界可以不完美。去練習理解「這些灰塵並不會殺掉你」。
世界並不完美,總有難以理解的人,還有難以回答的問題──思考這些並不舒服,但不會殺掉我們。世界是髒的,而在我們自己多走幾步之後,或許也將意識到,「原來弄髒,不過就是這樣。」●
|
 那些少女沒有抵達 那些少女沒有抵達
作者:吳曉樂
出版:鏡文學
定價:450元
【內容簡介➤】
|
|
作者簡介:吳曉樂
居於臺中。喜歡鸚鵡。魂系遊戲玩家。
著有《致命登入》、《我們沒有祕密》、《上流兒童》、《可是我偏偏不喜歡》、《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
Tags:
在新作《那些少女沒有抵達》的寫作過程中,吳曉樂曾經擔心:會不會有人在讀了這本小說之後,跑出來質疑她厭女呢?
這樣的擔心,是基於她打造「母親」這個角色時的一個選擇。從小說的第三頁開始,讀者就能看到女主角承受著母親的高壓控管,之後更會發現主角因而深受創傷。但在此同時,吳曉樂卻選擇不將母親的作為歸因於任何「苦衷」──她選擇不讓母親出身貧窮,或者童年時曾被惡待,甚至還讓這個角色在事業上也相當成功。
這樣的設計,違背了近年來流行的某種套路:母親之所以會對自己的小孩殘忍,總是因為過去被壓迫的經驗,再不然也是因為某些長期以來的辛苦。更廣泛來說,造成傷害的女人,似乎總是要有自己的苦衷,即使她壓迫的是另一個女人。
依循這樣的套路也許是容易的事,但吳曉樂拒絕這麼做。
相反地,她批評這個套路:「這好像認為女人是完美的,總是只有被迫害之後才會迫害別人。」她認為,這樣的套路陷入了某種溫情主義,「而到了2023年,這種說法已經不再能說服我。」
➤告別溫情主義,承認女性不同的樣貌
吳曉樂的批評,其實源於她在創作過程中的自我反省。5年前,她出版小說 《上流兒童》,同樣關注強勢逼迫孩子前進的母親,但讀者不難看出,媽媽的執念源於她的家境、她的成長背景,而故事的結局則是母子之間的諒解與和解。
《上流兒童》,同樣關注強勢逼迫孩子前進的母親,但讀者不難看出,媽媽的執念源於她的家境、她的成長背景,而故事的結局則是母子之間的諒解與和解。
但後來,這本書被引進到法國,法方出版社卻表達無法認同這個結局,希望她能夠更改。吳曉樂回憶,當時聽到對方的說法,她非常震撼,也才突然意識到,她原以為合情合理的劇情設計,其實「也陷入亞洲的某種主義──我也不願意接受她是一個『人』」。
因為,如果我們接受媽媽們也都是人,就不再需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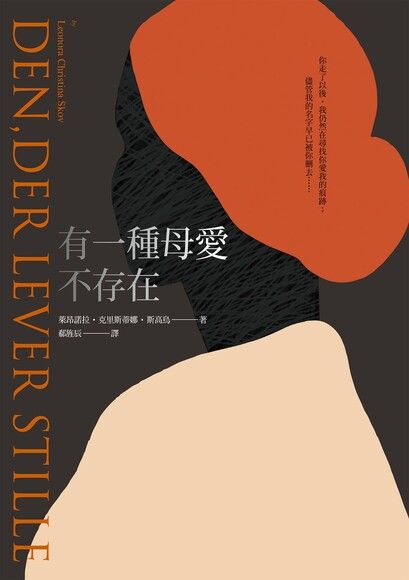 執著於一定要給她們好的、和解式的結局,彷彿女性總是苦情,而她們的苦衷又都終究要能夠被理解、被體諒。吳曉樂說,在讀了丹麥作家斯高烏( Leonora Christina Sko)的小說《有一種母愛不存在》之後,她的想法更為確定。
執著於一定要給她們好的、和解式的結局,彷彿女性總是苦情,而她們的苦衷又都終究要能夠被理解、被體諒。吳曉樂說,在讀了丹麥作家斯高烏( Leonora Christina Sko)的小說《有一種母愛不存在》之後,她的想法更為確定。
小說中的母親無法接受女兒是同志,甚至把自己罹癌怪罪到女兒頭上。女兒相當痛苦,而且,她最初的反應也是去尋找母親性格的成因,但找了許久,卻發現母親真的沒受過什麼創傷。說到這裡,吳曉樂語氣嚴肅:「當我們一直想證明某個人有創傷,這代表我們只願意看到一部分的人。」
換句話說,當我們安於「為母親找創傷」的套路,反而意味著我們還沒準備好看到女人的各種樣貌,只因為某些真實的樣貌將會讓我們感到不舒服。
唯有告別這種套路,我們才能好好體察社會上真實存在的性別不平等,以及性別的各種幽微影響力。就以《那些少女沒有抵達》為例子,吳曉樂說,與其認為主角吳依光的母親有任何創傷,更有力的觀察可能會注意到:身為事業有成的女性,母親在往上爬的過程中,很可能必須內化社會上「成功男性」的各種標準,因此「學會揚棄陰性的價值」。她甚至還要學會使用各種暴力──即使並非肢體的,是情感上、精神上的暴力。而在與女兒的關係中,母親正是不斷要求女兒壓抑感受,並且動用情感上的暴力強制執行。
不論如何,女人也可能施行暴力,也可能賤斥重要的陰性價值。這個念頭可能讓人不舒服,卻是現實。吳曉樂認為,書寫這個令人不舒服的現實並不是厭女──反而,各種套路對於母親、對於女性樣貌的扁平想像,「或許才是真正的厭女」。
「我認為這本小說,是我理解女性身分的莫大里程碑。」吳曉樂自信而且肯定。
➤接受那些不得而知,甚至享受沒有答案的狀態
是現實就應該當做現實處理,所以《那些少女沒有抵達》拒絕給出輕率的、斬釘截鐵的答案,即使那樣的答案可能看似合理,也令人感到安心──針對性別、針對母女關係如此,針對其他問題亦然。
小說裡許多地方沒有確切的答案。最明顯的莫過於,直到小說最後,吳依光還是無法清楚解釋母親為何那樣對待她。而在這個問題之外,故事中還有其他疑問,也是最終都沒有解答。
比如重要的支線劇情:發生在學校游泳池的不幸事件,只有兩位當事人在場,而這兩名少女各執一詞,講法並不一致。讀者或許會在情感上比較希望哪一方是對的,但文字本身確實無從推知孰是孰非。偏偏這個事件又後果嚴重,尤其對吳依光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談到這段情節,吳曉樂笑說:「身為作者我也不知道真相,而且是角色有意識地讓我不知道,他們把我這個作者也block(阻擋)在外面了。」不是作者偷懶不設計,而是作者筆下的角色自己就會去主動隱藏真相。畢竟,此事涉及兩個高中生心裡的祕密與糾結,不論哪個版本正確,都足以證實一名少女陰暗的念頭,而雙方又都有說謊的動機──角色自己不會讓旁人知道,於是作者和讀者就跟吳依光一樣,也不可能知道。面對這樣的不得而知,吳曉樂承認,「我如果是吳依光,也一定會陷入巨大的困惑」,但這也是必須接受的事。
而吳曉樂甚至不只接受而已。她說,面對不知道答案的事,她經常是享受的。「在小說裡,我們可以不要給出答案,這是我在寫作中最大的快樂。」
關於這點,吳曉樂分享了一個軼事。她的伴侶是律師,工作經常需要寫訴狀,而訴狀有制式的格式,寫作時又必須不時引用判例和法規,還得一字不漏、複製貼上。「寫1000個字,可能有600字在寫之前就已經決定好要長什麼樣子。」有一天吳曉樂在寫作時,伴侶經過她身旁,看了兩分鐘,問她怎麼知道等等要寫什麼,吳曉樂回答:「我不知道,而且你現在看我寫了這一頁500字,等等你一離開可能都會刪掉。」伴侶很驚訝地問:「這樣難道不恐怖嗎?」吳曉樂的回答是:「我覺得你們那樣才恐怖。」
現實中本來就會有很多的不得而知,關於真相、關於原因、關於前進的目標與過程。既然如此,對吳曉樂而言,如果還被期待凡事要按照常軌、給出確切答案,反而才是真正的恐怖。
「我受夠了臺灣一定要有答案這件事情」,說到這裡,吳曉樂音量提高,語氣堅定。她說,大學就讀臺大法律系,最後卻拒絕從事法律工作,正是因為她對此感到厭倦。「法律系有個東西讓我很累,就是一定要有答案。畢竟花幾十萬塊、幾十個小時打了一場官司,法官不能說『我不知道』。」
「而我想要停留在那個『我不知道』的狀態久一點點。」吳曉樂這樣說。
➤一起練習,踩上佈滿灰塵的地板
發現自己不知道確切的答案,甚至可能永遠無法得到解答,是件令人感到困惑的事。但吳曉樂認為這並不恐怖,相反地,以為凡事必然能得到確切答案,對她而言才是真正的恐怖。這就如同,描繪女性的可能樣貌之一,書寫其恐怖與難以索解,這些並不是厭女的舉動;相反地,以為凡事都可以依照套路理解,而拒絕看到人們真實的樣貌,才是真正帶有偏見。
不符合套路的女性樣貌,以及不得而知所帶來的困惑,這些都是會讓人感到「不舒服」的課題。而《那些少女沒有抵達》當中,吳曉樂正在陪伴讀者一起面對這樣的課題。
不舒服,但是沒有關係──對此,小說中的隱喻,是踩在佈滿灰塵的地板上。
這個隱喻出現在小說接近結尾的地方。吳曉樂說,她猜想多數讀者可能不覺得這個場景特別重要,但這是她身為作者非常重視的段落。在這個段落裡,吳依光回憶起她小時候趁暑假拜訪住在美國的阿姨。阿姨不像媽媽那麼要求整潔,家裡的地板上因此積了不少灰塵。有一天,吳依光臨時起意,踢掉拖鞋,光著腳踩在階梯上。一開始,吳依光覺得好髒,好不舒服,但多走幾步,髒還是髒的,但她意識到「原來弄髒,不過就是這樣」。
歷經了故事中的許多波折之後,女主角回想起這個童年記憶。吳曉樂說,這是吳依光的「練習」──她是個敏感的人,但一直以來,不是被母親強迫壓抑自己的感受,就是被自己敏感的感官控制。直到這個場景裡,她才有機會練習面對「灰塵」,練習怎麼回應踩上灰塵時感官給她的訊號。
對此,吳曉樂用了一個精準的詞:吳依光在試著「馴服」她自己的感官。「馴服」意味著違背母親的教導,不再壓抑自己的感受,但另一方面,「馴服」也意味著,即使在踏出第一步時,感官不斷傳來「不舒服」的訊號,她仍不容許自己被這樣的感受壓倒,仍然要求自己往下走。
去練習馴服自己的感受。去允許世界可以不完美。去練習理解「這些灰塵並不會殺掉你」。
世界並不完美,總有難以理解的人,還有難以回答的問題──思考這些並不舒服,但不會殺掉我們。世界是髒的,而在我們自己多走幾步之後,或許也將意識到,「原來弄髒,不過就是這樣。」●
作者:吳曉樂
出版:鏡文學
定價:45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吳曉樂
居於臺中。喜歡鸚鵡。魂系遊戲玩家。
著有《致命登入》、《我們沒有祕密》、《上流兒童》、《可是我偏偏不喜歡》、《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
閱讀通信 vol.370》當我在書裡讀到你的時候
延伸閱讀
書.人生.吳曉樂》文學從不擔保快樂
總有那麼一本或數本書,一位或多位文人作家,曾在我們的閱讀行旅中,留下難以遺忘的足跡。「書.人生」專欄邀請各界方家隨筆描摹,... 閱讀更多
現場》自己的書自己出?一想到庫存我險險焚書坑掉自己:潘柏霖、吳曉樂自費出版講座側記
由作家吳曉樂、獨立書店現流冊店、出版人A編工事中於今年4月共同成立的「台灣出版民間真相與正解促進會」,每月邀請出版人、作家、譯者、通路等出版產業從業人員擔任對談嘉賓... 閱讀更多
線上對談》拉開轉身的餘裕,我把「自己」還給母親:謝凱特、吳曉樂雲端暢聊
編按:繼與家庭斷裂切割的《我的蟻人父親》、重建關係的《普通的戀愛》後,謝凱特推出散文新作《我媽媽做小姐的時陣是文藝少女》,以坦誠、細膩的文字刻畫母親,並於書中自白,...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