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有段時間沉迷韓國電影。那陣子追看李滄東、金基德、朴贊郁、奉俊昊等導演的作品,一片接一片,各種無以名狀的黑暗、狂暴、不安洶湧而來,這是我不曾在其他電影感受過的猛烈情緒。但這樣的愛好卻沒有跨越到當時正在席捲電視頻道的韓劇,以及熱烈興起的K-POP風潮。我試著尋找韓國文學作品,發現沒幾本被翻譯,幾乎空白。況且台灣對於韓國總有著百感交集的情緒。從早年同以勞力密集出口導向產業拚經濟,到後來的科技製造產業的拚搏,乃至最民族主義的國際棒球賽事,處處都可看到台韓的交錯競逐。但其實兩國在20世紀的發展軌跡有著不少相似之處。
台灣在1895年後成為日本殖民地,韓半島在1910年被日本吞併。
二戰後,國共內戰,國民黨政府敗逃來台;韓半島形成美蘇對峙前線,韓戰爆發,捲入整個東亞局勢,最終以北緯38度線分斷南北韓。
台韓經濟起飛的年代,同處在威權政府統治下,一個號稱台灣奇蹟,一個則是漢江奇蹟,並列亞洲四小龍。
台韓都在1980年代前後展開民主化運動之路。先是韓國強人朴正熙遭暗殺,全斗煥政變掌權,接著台灣在1979年底發生美麗島事件,韓國則是在1980年爆發光州事件。
台灣在1987年解嚴,掙脫長達38年的戒嚴枷鎖;韓國在1987年6月出現全國規模的示威抗爭,要求修憲、直選總統。
此後兩國在各自的道路上深化民主,面對各自在全球化時代的種種危機和難題。這些簡短的台韓歷史對照,或許是我們在台灣閱讀金英夏的前提補充。
▉兩個村上的綜合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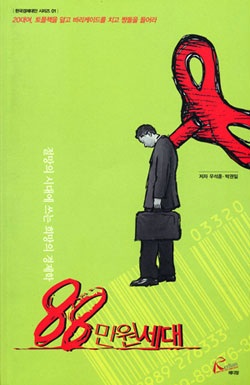
《88萬韓元世代》韓文版書封
韓半島的近代命運是徘徊在金英夏小說的幽靈。1968年生的金英夏,出生在南北韓非軍事區,父親是打過越戰的韓國軍人,因軍隊換防,金英夏的童年不停轉學,也沒交到朋友。他在18歲考入延世大學企管系,參加的社團是韓國傳統音樂社──起初只是想學吉他,發現韓國傳統音樂社什麼樂器都不用花錢買就決定加入了。當年跟他一起入社的同學,是日後寫出《88萬韓元世代》的經濟學者禹皙熏。他們企管系的同班同學李韓烈,則是加入卡通漫畫愛好社。
金英夏在長篇小說《光之帝國》虛構了一個與自己同樣在1986年進入延世大學的北韓間諜。透過間諜視角,呈現當年大學裡的知識、政治氛圍。在威壓政權下,學生們偷偷組織讀書會,熱切研讀馬克思、毛主義、北韓領袖金日成的主體思想,幻想發動革命,推翻政府。這些想法與行動,在潛伏的間諜看來有如兒戲,他根本不覺得這些涉世未深的大學生能成就什麼。
但時代轉變了。1987年初,發生首爾大學學生朴鍾哲被拷問致死事件,到了6月演變成全國抗爭紛起,延世大學的李韓烈在大學門口示威被催淚彈擊中頭部,昏迷一個月後死亡。他的犧牲激化了抗爭規模,也加速促成韓國邁向民主化之路。
還沒成為小說家的金英夏在歷史現場,目睹自己的同學出殯遠行之日,聚集了數不清的送行人潮。儘管韓國在該年底迅速修憲、實施總統直選,民主卻不是一碗三分鐘就可以吃的泡麵,它需要更長時間來厚植基礎。
金英夏讀大四的1989年,延世大學裡出現激進學生虐殺冒名學生的案件,就發生在李韓烈待過的卡漫愛好社。這個事件讓金英夏徹底看清暴力只會召喚暴力的本質,也使他重新思考人性,思索個體在群體中的壓迫和盲從。無論以如何堂皇的國家、社會、主義或正義為名施行暴力,都必然危及個體的獨立自主。他從此遠離政治運動,投身給予個人最大空間和自由的文學。
金英夏的作品和個人經歷,每每令我想起日本的兩個村上。以金英夏年輕時親歷學生運動,最終選擇離開、擁抱個人主義的形象,有點像49年生的村上春樹。村上春樹在《挪威的森林》嘲諷了60年代末搞學運的激進左翼毫無想像力,而1972年淺間山莊的私刑肅清,彷如預示了日後韓國的大學裡學生的過激暴力。村上春樹曾受邀至美國的大學客座數年,金英夏同樣也在紐約待過4年。他們都將費茲傑羅的《大亨小傳》翻譯到各自的語言裡,他們都愛貓,他們都不生孩子。

金英夏的Podcast節目《金英夏的讀書時間》
金英夏的另一面是前衛、新潮,總在嘗試各種事物。他在27歲出席文學獎頒獎典禮時,左耳戴著耳環,嚇壞一眾韓國媒體。他早年的小說譬如成名作《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充斥殺人、死亡氣息,也成為當代文學的異數。這簡直像是村上龍以高度爭議的《接近無限透明的藍》拿下1976年的芥川賞。當年留長髮的村上龍戴著蒼蠅大墨鏡呼菸的飄撇模樣,在在挑釁著日本文壇。村上龍出道後玩音樂、拍電影,寫大量雜文、小說,自修財經趨勢、發行電子報,主持電視節目等,一如金英夏這些年來活躍於新媒介平台。台灣讀者可能還沒讀過他的小說,就看過tvN熱門節目《懂也沒用的神祕雜學辭典》裡能言善道、幽默博學的小說家金英夏。此前他的小說有好幾部改編成電影,他親身參與改編工作,寫原創電影劇本,也錄製過一系列的Podcast節目,朗讀、分享他喜歡的世界文學作品。從事如此大量外務的同時,他依然維持寫作本業,彷彿兩個村上的綜合體。
金英夏擅長寫少年也有如兩個村上。他的《黑色花》寫20世紀初的少年金二正搭上前往墨西哥的朝鮮移工船,寫他在險惡航行的掙扎、受到初戀情慾的煎熬,又如何在殘酷的龍舌蘭莊園採收工作、移工抗爭和墨西哥內戰的混亂中勉力存活。在這本彷若出自墨西哥小說家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手筆的歷史卷軸,不難辨識出類似村上春樹《海邊的卡夫卡》或村上龍《希望之國》的執拗少年身影。而金英夏的《猜謎秀》寫沉迷於網路世界的青年,像是村上龍《共生蟲》中的繭居少年,他們都試著以小說理解年輕人的處境,用故事、幻想來化解以虛擬空間為隔閡的世代壕溝。

金英夏被改編為燒腦電影《殺人者的記憶法》的原作小說,不免也讓人聯想到村上龍的《老人恐怖分子》、《寂寞國的殺人》和《味噌湯裡》等書。金英夏巧妙設計了一個悖論:患了阿茲海默症的天才連續殺人犯,該怎麼應對新近出現在周圍的連續殺人者,才能保護自己的女兒?這個老去的殺人者並非為了快感而殺人,而是追求著執行完美無暇的殺人,一次次犯行,直到沒有地方可以改進為止。在這部以瘋癲尼采般口吻寫成的簡斷小說,金英夏試圖以有序的語言,述說一則逐漸失序崩塌、垮陷的殺人回憶。這個老人就跟村上龍筆下要炸毀日本社會的老人一樣,不是無害而遲鈍的長照等待者,而是充滿憤怒和殺意的猛獸。
▉幾種在地接引
韓國與日本皆是布滿層層禮教規範的社會,映照兩個村上,金英夏也以他的實踐衝決網羅。如今他的作品陸續譯介來台,我們該如何解讀?金英夏在訪談說,「被翻譯的作品終究是該語言的文化資產」,就這點而言,可從台灣當代文學觀察到在地例證。
抱歉又要把村上春樹拖出來當案例。根據張明敏《村上春樹文學在臺灣的翻譯與文化》專書研究,自從村上春樹在1980年代被翻譯到台灣後,台灣不僅成為世上翻譯村上作品最完整的地方,也形成獨特的村上接受現象。隨著村上銷量、傳播漸廣,各種文學獎競賽時常可看到模仿村上腔的稿件,村上寫到的爵士樂手、古典樂曲目成了讀者指引,村上翻譯成日文的外國文學也會出現台灣譯本。許多開始接觸文學的讀者是從村上讀起。村上幾乎成了台灣讀者、寫作者的基本養分。
但這樣的作者畢竟不多。隨著翻譯文學在台的紮根擴散,其實不太容易再出現這類具有統治力的文化翻譯現象。繼續引述金英夏的話:「我相信作家的真正成就並非被翻譯的語言數量,而是母語讀者們的深刻理解和熱愛。」因此我想從台灣的同代作者來接引金英夏。
綜觀金英夏現有的中文譯本,大概可與台灣的五年級作家互相參照。例如年紀相仿的何致和,在差不多的時間點寫出小說《白色城市的憂鬱》,同樣與《猜謎秀》出入網路上下兩端,探究虛實交纏的記憶。又或如同年的成英姝。他們的小說,特別是短篇,行文爽利直接,時常聚焦在城市生活的突變異想,充滿黑色幽默的趣味。在我看來,成英姝《無伴奏安魂曲》就是變奏版的《殺人者的記憶法》,既恐怖又極其日常。
然而我最想對照的是賴香吟。閱讀《光之帝國》,我對金英夏描述的韓國社會變遷有著滿滿既視感,似乎我讀的不是韓國,而是台灣。台韓相似的民主化時程,一同被綑綁在美國設置的第一島鏈防線,小心翼翼在美中兩強之間博奕求活。在這樣的地緣政治大局下,個人情感容易被淹沒忽略。

賴香吟一系列以年份為題的短篇,則是在時代變動裡,奮力保存個人的衰小。她的〈虛構一九八七〉開頭句:「我的1987年,開始於一個傳言中的喪禮。」小說寫一個同學的消逝,寫敘事者在1987年進大學,在社團接觸到228、黨外人士,參與示威遊行。多麼像是會在金英夏筆下出現的敘述。金英夏至今不曾寫過他的早逝同學李韓烈,卻可能以另一種輪廓浮現在賴香吟的小說。
在〈野地一九八九〉,賴香吟若有似無寫出隱隱的幻滅。上台北重考大學的敘事者,街頭撞見後解嚴的風起雲湧,旁觀他人之激情,但敘事者擺脫不了微弱的猶疑:「這些東牽西扯、連成一氣的事情就是所謂政治嗎?」、「民主、人權、自由,這些原本寫在紙上的硬名詞這幾年忽然變得立體起來,我還來不及搞清楚呢,它們已經運作得複雜。」這似乎也像金英夏小說的北韓間諜,冷眼看待彼時的民主運動。到了〈暮色將至〉,曾經燃燒的青春、理想都化成灰燼,有的只是老病,以及堅硬的政治現實。人到中年,被傷痛和回憶消磨,僅存餘力應付生活。即使你曾是間諜、天才殺人犯,都抵擋不了時間的刷洗。
如果我們無法以準確的在地語彙,適度接引翻譯作品,依舊不加思索套用宣傳用語,我們恐怕難以累積、磨礪自身眼光。當然,在對照本地作品之餘,我們仍該回到韓國文學自身的脈絡來理解金英夏和其他近年引介入台的作者。台灣讀者一向不缺見識世界各國的暢銷作品,缺的是如何在閱讀他人之時,盡可能照顧到對方的本源基礎,避免腦補誤讀,以形成自身評判、擇取的準則。如此一來,我們才算是真正妥善化用了翻譯而來的資產。
閱讀金英夏的小說,總讓我不時聯想台灣、韓國乃至東亞局勢七十多年的歷史。整排從東北亞至東南亞的弧線上的國家,有如一連串相同主題的變奏曲。主題由美蘇兩強給定,不同地區演奏出各自參差的變形版本。國共內戰可能演變至南北中國對立,一如兩韓分治的局面;韓戰可能是日後越戰翻版,最終由朝鮮人民共和國統一韓半島;越南或許也有機會形成如當前兩韓競爭的態勢。這些可能性並非存在於平行宇宙,而是扎實潛藏在周邊鄰國之中。只有深入理解我們的鄰人,我們才能更深入理解自己。文學總是最基礎的起點。●
Tags:
韓國作家金英夏(漫遊者文化提供)
十多年前,我有段時間沉迷韓國電影。那陣子追看李滄東、金基德、朴贊郁、奉俊昊等導演的作品,一片接一片,各種無以名狀的黑暗、狂暴、不安洶湧而來,這是我不曾在其他電影感受過的猛烈情緒。但這樣的愛好卻沒有跨越到當時正在席捲電視頻道的韓劇,以及熱烈興起的K-POP風潮。我試著尋找韓國文學作品,發現沒幾本被翻譯,幾乎空白。況且台灣對於韓國總有著百感交集的情緒。從早年同以勞力密集出口導向產業拚經濟,到後來的科技製造產業的拚搏,乃至最民族主義的國際棒球賽事,處處都可看到台韓的交錯競逐。但其實兩國在20世紀的發展軌跡有著不少相似之處。
台灣在1895年後成為日本殖民地,韓半島在1910年被日本吞併。
二戰後,國共內戰,國民黨政府敗逃來台;韓半島形成美蘇對峙前線,韓戰爆發,捲入整個東亞局勢,最終以北緯38度線分斷南北韓。
台韓經濟起飛的年代,同處在威權政府統治下,一個號稱台灣奇蹟,一個則是漢江奇蹟,並列亞洲四小龍。
台韓都在1980年代前後展開民主化運動之路。先是韓國強人朴正熙遭暗殺,全斗煥政變掌權,接著台灣在1979年底發生美麗島事件,韓國則是在1980年爆發光州事件。
韓國光州事件,市民及學生舉行大規模的遊行(取自518기념재단)
台灣在1987年解嚴,掙脫長達38年的戒嚴枷鎖;韓國在1987年6月出現全國規模的示威抗爭,要求修憲、直選總統。
此後兩國在各自的道路上深化民主,面對各自在全球化時代的種種危機和難題。這些簡短的台韓歷史對照,或許是我們在台灣閱讀金英夏的前提補充。
▉兩個村上的綜合體
《88萬韓元世代》韓文版書封
韓半島的近代命運是徘徊在金英夏小說的幽靈。1968年生的金英夏,出生在南北韓非軍事區,父親是打過越戰的韓國軍人,因軍隊換防,金英夏的童年不停轉學,也沒交到朋友。他在18歲考入延世大學企管系,參加的社團是韓國傳統音樂社──起初只是想學吉他,發現韓國傳統音樂社什麼樂器都不用花錢買就決定加入了。當年跟他一起入社的同學,是日後寫出《88萬韓元世代》的經濟學者禹皙熏。他們企管系的同班同學李韓烈,則是加入卡通漫畫愛好社。
金英夏在長篇小說《光之帝國》虛構了一個與自己同樣在1986年進入延世大學的北韓間諜。透過間諜視角,呈現當年大學裡的知識、政治氛圍。在威壓政權下,學生們偷偷組織讀書會,熱切研讀馬克思、毛主義、北韓領袖金日成的主體思想,幻想發動革命,推翻政府。這些想法與行動,在潛伏的間諜看來有如兒戲,他根本不覺得這些涉世未深的大學生能成就什麼。
但時代轉變了。1987年初,發生首爾大學學生朴鍾哲被拷問致死事件,到了6月演變成全國抗爭紛起,延世大學的李韓烈在大學門口示威被催淚彈擊中頭部,昏迷一個月後死亡。他的犧牲激化了抗爭規模,也加速促成韓國邁向民主化之路。
還沒成為小說家的金英夏在歷史現場,目睹自己的同學出殯遠行之日,聚集了數不清的送行人潮。儘管韓國在該年底迅速修憲、實施總統直選,民主卻不是一碗三分鐘就可以吃的泡麵,它需要更長時間來厚植基礎。
金英夏讀大四的1989年,延世大學裡出現激進學生虐殺冒名學生的案件,就發生在李韓烈待過的卡漫愛好社。這個事件讓金英夏徹底看清暴力只會召喚暴力的本質,也使他重新思考人性,思索個體在群體中的壓迫和盲從。無論以如何堂皇的國家、社會、主義或正義為名施行暴力,都必然危及個體的獨立自主。他從此遠離政治運動,投身給予個人最大空間和自由的文學。
金英夏的作品和個人經歷,每每令我想起日本的兩個村上。以金英夏年輕時親歷學生運動,最終選擇離開、擁抱個人主義的形象,有點像49年生的村上春樹。村上春樹在《挪威的森林》嘲諷了60年代末搞學運的激進左翼毫無想像力,而1972年淺間山莊的私刑肅清,彷如預示了日後韓國的大學裡學生的過激暴力。村上春樹曾受邀至美國的大學客座數年,金英夏同樣也在紐約待過4年。他們都將費茲傑羅的《大亨小傳》翻譯到各自的語言裡,他們都愛貓,他們都不生孩子。
金英夏的Podcast節目《金英夏的讀書時間》
金英夏的另一面是前衛、新潮,總在嘗試各種事物。他在27歲出席文學獎頒獎典禮時,左耳戴著耳環,嚇壞一眾韓國媒體。他早年的小說譬如成名作《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充斥殺人、死亡氣息,也成為當代文學的異數。這簡直像是村上龍以高度爭議的《接近無限透明的藍》拿下1976年的芥川賞。當年留長髮的村上龍戴著蒼蠅大墨鏡呼菸的飄撇模樣,在在挑釁著日本文壇。村上龍出道後玩音樂、拍電影,寫大量雜文、小說,自修財經趨勢、發行電子報,主持電視節目等,一如金英夏這些年來活躍於新媒介平台。台灣讀者可能還沒讀過他的小說,就看過tvN熱門節目《懂也沒用的神祕雜學辭典》裡能言善道、幽默博學的小說家金英夏。此前他的小說有好幾部改編成電影,他親身參與改編工作,寫原創電影劇本,也錄製過一系列的Podcast節目,朗讀、分享他喜歡的世界文學作品。從事如此大量外務的同時,他依然維持寫作本業,彷彿兩個村上的綜合體。
金英夏擅長寫少年也有如兩個村上。他的《黑色花》寫20世紀初的少年金二正搭上前往墨西哥的朝鮮移工船,寫他在險惡航行的掙扎、受到初戀情慾的煎熬,又如何在殘酷的龍舌蘭莊園採收工作、移工抗爭和墨西哥內戰的混亂中勉力存活。在這本彷若出自墨西哥小說家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手筆的歷史卷軸,不難辨識出類似村上春樹《海邊的卡夫卡》或村上龍《希望之國》的執拗少年身影。而金英夏的《猜謎秀》寫沉迷於網路世界的青年,像是村上龍《共生蟲》中的繭居少年,他們都試著以小說理解年輕人的處境,用故事、幻想來化解以虛擬空間為隔閡的世代壕溝。
金英夏被改編為燒腦電影《殺人者的記憶法》的原作小說,不免也讓人聯想到村上龍的《老人恐怖分子》、《寂寞國的殺人》和《味噌湯裡》等書。金英夏巧妙設計了一個悖論:患了阿茲海默症的天才連續殺人犯,該怎麼應對新近出現在周圍的連續殺人者,才能保護自己的女兒?這個老去的殺人者並非為了快感而殺人,而是追求著執行完美無暇的殺人,一次次犯行,直到沒有地方可以改進為止。在這部以瘋癲尼采般口吻寫成的簡斷小說,金英夏試圖以有序的語言,述說一則逐漸失序崩塌、垮陷的殺人回憶。這個老人就跟村上龍筆下要炸毀日本社會的老人一樣,不是無害而遲鈍的長照等待者,而是充滿憤怒和殺意的猛獸。
《殺人者的記憶法》電影海報(取自HANCINEMA)
▉幾種在地接引
韓國與日本皆是布滿層層禮教規範的社會,映照兩個村上,金英夏也以他的實踐衝決網羅。如今他的作品陸續譯介來台,我們該如何解讀?金英夏在訪談說,「被翻譯的作品終究是該語言的文化資產」,就這點而言,可從台灣當代文學觀察到在地例證。
抱歉又要把村上春樹拖出來當案例。根據張明敏《村上春樹文學在臺灣的翻譯與文化》專書研究,自從村上春樹在1980年代被翻譯到台灣後,台灣不僅成為世上翻譯村上作品最完整的地方,也形成獨特的村上接受現象。隨著村上銷量、傳播漸廣,各種文學獎競賽時常可看到模仿村上腔的稿件,村上寫到的爵士樂手、古典樂曲目成了讀者指引,村上翻譯成日文的外國文學也會出現台灣譯本。許多開始接觸文學的讀者是從村上讀起。村上幾乎成了台灣讀者、寫作者的基本養分。
但這樣的作者畢竟不多。隨著翻譯文學在台的紮根擴散,其實不太容易再出現這類具有統治力的文化翻譯現象。繼續引述金英夏的話:「我相信作家的真正成就並非被翻譯的語言數量,而是母語讀者們的深刻理解和熱愛。」因此我想從台灣的同代作者來接引金英夏。
綜觀金英夏現有的中文譯本,大概可與台灣的五年級作家互相參照。例如年紀相仿的何致和,在差不多的時間點寫出小說《白色城市的憂鬱》,同樣與《猜謎秀》出入網路上下兩端,探究虛實交纏的記憶。又或如同年的成英姝。他們的小說,特別是短篇,行文爽利直接,時常聚焦在城市生活的突變異想,充滿黑色幽默的趣味。在我看來,成英姝《無伴奏安魂曲》就是變奏版的《殺人者的記憶法》,既恐怖又極其日常。
然而我最想對照的是賴香吟。閱讀《光之帝國》,我對金英夏描述的韓國社會變遷有著滿滿既視感,似乎我讀的不是韓國,而是台灣。台韓相似的民主化時程,一同被綑綁在美國設置的第一島鏈防線,小心翼翼在美中兩強之間博奕求活。在這樣的地緣政治大局下,個人情感容易被淹沒忽略。
賴香吟一系列以年份為題的短篇,則是在時代變動裡,奮力保存個人的衰小。她的〈虛構一九八七〉開頭句:「我的1987年,開始於一個傳言中的喪禮。」小說寫一個同學的消逝,寫敘事者在1987年進大學,在社團接觸到228、黨外人士,參與示威遊行。多麼像是會在金英夏筆下出現的敘述。金英夏至今不曾寫過他的早逝同學李韓烈,卻可能以另一種輪廓浮現在賴香吟的小說。
在〈野地一九八九〉,賴香吟若有似無寫出隱隱的幻滅。上台北重考大學的敘事者,街頭撞見後解嚴的風起雲湧,旁觀他人之激情,但敘事者擺脫不了微弱的猶疑:「這些東牽西扯、連成一氣的事情就是所謂政治嗎?」、「民主、人權、自由,這些原本寫在紙上的硬名詞這幾年忽然變得立體起來,我還來不及搞清楚呢,它們已經運作得複雜。」這似乎也像金英夏小說的北韓間諜,冷眼看待彼時的民主運動。到了〈暮色將至〉,曾經燃燒的青春、理想都化成灰燼,有的只是老病,以及堅硬的政治現實。人到中年,被傷痛和回憶消磨,僅存餘力應付生活。即使你曾是間諜、天才殺人犯,都抵擋不了時間的刷洗。
如果我們無法以準確的在地語彙,適度接引翻譯作品,依舊不加思索套用宣傳用語,我們恐怕難以累積、磨礪自身眼光。當然,在對照本地作品之餘,我們仍該回到韓國文學自身的脈絡來理解金英夏和其他近年引介入台的作者。台灣讀者一向不缺見識世界各國的暢銷作品,缺的是如何在閱讀他人之時,盡可能照顧到對方的本源基礎,避免腦補誤讀,以形成自身評判、擇取的準則。如此一來,我們才算是真正妥善化用了翻譯而來的資產。
閱讀金英夏的小說,總讓我不時聯想台灣、韓國乃至東亞局勢七十多年的歷史。整排從東北亞至東南亞的弧線上的國家,有如一連串相同主題的變奏曲。主題由美蘇兩強給定,不同地區演奏出各自參差的變形版本。國共內戰可能演變至南北中國對立,一如兩韓分治的局面;韓戰可能是日後越戰翻版,最終由朝鮮人民共和國統一韓半島;越南或許也有機會形成如當前兩韓競爭的態勢。這些可能性並非存在於平行宇宙,而是扎實潛藏在周邊鄰國之中。只有深入理解我們的鄰人,我們才能更深入理解自己。文學總是最基礎的起點。●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
【閱讀韓國・以文學捕捉當代韓國社會縮影】完整專題
【閱讀韓國・再多一點】
【Openbook國際書展參戰(;・`д・´)】
2/6(五)歡迎加入玩耍!•̀.̫•́✧書寫、行動與反思:和島嶼互動的幾種方式
閱讀通信 vol.367》如果我在晚上九點敲響你的房門
延伸閱讀
閱讀韓國・首爾直送》孤兒般的存在,是當代人的寫照:金英夏專訪
閱讀更多
評論》新鮮的韓國風景與現代感覺:金英夏的「新世代文學」
閱讀更多
閱讀隨身聽EP8》漫遊者文化總編輯李亞南/總編選書術大公開 ft.韓國文學
你那一邊,現在是白天還是晚上?已回到家,或是在通勤的路上?無論什麼時間、地點,歡迎隨時打開「閱讀隨身聽」。在此Podcast節目中,...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