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專輯可以有很多種聽法。第一次播放《女兒的九十九種藍》,戴著耳機,邊做雜事漫不經心,沒有任何閱讀準備,樂音先一步抵達。忽遠忽近的手風琴像一波波潮汐,沖淡了世界。頃刻間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正中央,一個母體橫空出世,神聖,莊嚴,無垠。
那一刻,我連忙翻看歌詞:
波浪載著月亮般的女兒
載著太陽般的女兒
去到二十一世紀
去到更遠——
—〈發明波浪的女兒W〉
原來詩可以有這種讀法。先關閉眼睛和邏輯,用聽覺和直覺去讀。原來聲音也有情節、有光影、有氣候。
對於還不清楚《女兒的九十九種藍》來歷的閱聽者,最直白的介紹方式,是音樂人羅思容為零雨組詩〈女兒〉譜曲的專輯。但若只是單純譜曲,恐怕唱不出波浪和月光。或許更貼切的說法,是羅思容所形容的「以詩入歌」——不只是譜寫旋律,而是沉入〈女兒〉的子宮,在那裡潛伏、滋養,與詩同體呼吸,孕育出一片聲音的海洋。
如同封面深淺交疊的藍,這張專輯拍打出一片無邊的流域,女人、母親、女兒、創作者、閱聽者的角色彼此滲透、轉換、流動,生命在詩與聲音中不斷誕生,也不斷孕育他者,潮汐般循環往復。
➤被女兒召喚,十首詩一夜成曲
唱詩,尤其是唱零雨的詩,羅思容並不陌生。2015年羅思容與孤毛頭樂團專輯選擇 12 位台灣重要女性詩人,為其詩作譜曲歌詠,製作專輯《多一個》,其中一首即是零雨的〈關於故鄉的一些算計〉。
《女兒的九十九種藍》是兩人的再度交會,也是一次更浩大的挑戰。就零雨聽來,相較〈關於故鄉的一些算計〉民謠曲風,這回的編制與氣勢更爲宏闊,可能是羅思容創作的一大突破。她以原創者的視角坦言,創作〈女兒〉時沒想過要改編成歌,詩中大量口語、白話、生硬的醫療用詞,都讓她疑惑:「到底要怎麼唱?這真的好困難。」
零雨的困惑其來有自。《女兒的九十九種藍》如潮汐變化萬千,時而肅殺,時而瘋癲,時而莊嚴,時而低泣,卻都貼伏著文字的呼吸節奏。你想像不到這首詩能這樣唱,然而經由羅思容的聲音,那些字就像找到自己的喉嚨。

更意外的是,羅思容只用一夜時間,抱著一把吉他就為〈女兒〉10首詩譜好了曲。
那是怎麼樣的一個夜晚?詩如何啟動她的創作閥,讓樂音如海潮傾瀉?
羅思容說,第一次讀〈女兒〉組詩,被震撼得不由自主流淚。開篇的序詩宣告:「這些女兒 / 發明了二十世紀的波浪」,是一句神聖的宣示,也是聲聲召喚,讓她想用喉嚨與音樂唱和回應。「這10首詩像百年來全世界女性的生存樣貌與命運,是文學與詩史上獨一無二的作品。」羅思容說,〈女兒〉寫到歇斯底里、憂鬱等等那些女人被污名化的標籤,也寫到社會與醫療體制的隱性壓迫,但零雨沒有直接控訴,而是讓一切潛伏在看似平靜的海面之下。
你的婚姻令人羨慕
房子車子兒子一應俱全
但你為什麼憂鬱
醫生說(——他是個男的)
你晚上失眠耳朵暈眩間歇性的
頭痛不時來襲
——我也不知道原因就由醫生用藥
(——他是個男的)
醫生說
最重的藥都用了現在
你什麼也不需要只需要海
—〈閉緊嘴巴的女兒 H〉
歷經漂泊、掙扎、對抗之後,一切終將回到海洋。那裡是生命的根源,像母親的子宮,也像未來的搖籃,涵融一切的危險與不可預測性。
在〈女兒〉中,海洋反覆出現。它是誕生,是嚮往的歸途,也是女性之間不需言語就能心領神會的匯流處,同樣在羅思容的創作中潛伏已久。她沒有正式公開發表的詩作〈秘〉寫道:
從時間的背脊
翻落一座青春的海洋
藍色的深海
有女人
愛,徬徨
不絕的潮汐之歌
旋轉,旋轉
➤以詩入歌:就像附身,然後轉生
訪談中,羅思容言談方式極富詩意,總是意象先於論述,感受先於邏輯。她的話語不僅止於吐出語言,而是展開一幅圖像。她形容以詩入歌,也帶著強烈的身體感,「就像附身,然後轉生,孕育出另一個新生。我們相互邂逅,又相互成為彼此。」
改編零雨的詩,挑戰在於如何承接詩人思想裡的複雜與深度。詩或藝術作品,最觸動人心的,是隱藏其中作者的生命質地。身體、語言、文化、心靈都必須敞開,才能與詩相遇。
唱詩,先從念誦詩開始。詩如咒,引領身體與直覺深入文句間的流動,帶羅思容通天遁地,潛入海底三萬呎,讓自己的、零雨的、古老的原始的、現代的新穎的女性故事一一經過她。羅思容的身體變成記憶的載體,喉嚨變成產道,吟詠出一首首圖像各異卻氣息相連的生命之歌。
那個被召喚的夜晚,歌從詩的子宮破水而出,向世界發出第一道聲響。

➤瘋癲與甜美並存,憂鬱與神聖同在的女兒
這張專輯的誕生,起源於零雨的邀約。2020 年中研院中國文哲所研究員楊小濱舉辦現代詩座談會,以〈女兒〉為主題。零雨遂邀請羅思容以詩為基礎創作歌曲。本來以為只採一、兩首詩來應和座談會跨界元素,沒想到 5 年後在目宿媒體支持下,以完整的專輯型態面世。
零雨回憶,第一次聽到羅思容僅以一把吉他伴奏的錄音時,便深受觸動。尤其序詩〈發明波浪的女兒W〉聖詠般的低音共振出一種深沉的悲劇感,為整張專輯定下基調。隨著旋律起伏跌宕,她在〈黑色的女兒L〉聽見了轉折,「像在大海找到浮木,有人共同奮鬥的感覺。」當樂音流向第10首〈牙牙學語的女兒K〉,最後的大合唱收尾,更讓零雨感動莫名。
但其實,兩人對於〈牙牙學語的女兒K〉有著截然不同的詮釋。零雨說,可能多數讀者會將這首詩視為和解,然而她心底是悲觀的,「世人都喜歡甜甜的,我就有點反諷的意味去寫『聽海的搖籃曲/甜甜的/餵給你』」
莊嚴、神聖、不安、憂鬱、被污名、寬廣、瘋癲……這些情緒狀態在〈女兒〉中交織成一張大網,羅思容主張:「我們就承認吧,穿越吧,瘋就瘋到底。也像〈牙牙學語的女兒K〉的合唱,要甜就甜到底。」
甜,有何不可?甜,是女性集體的力量,也是高舉的武器。穿越過種種情狀後,羅思容蛻變為世界的女兒、女兒、母親,超越語言的女聲大合唱是一首安魂曲,讓生命靈魂在此安頓,再次啟程,繼續徜徉在世界的海洋中。
➤用身體保留聲音的本源
不同觀點的敘事,讓原作有了新的神情。零雨認為,經過改編的音樂作品,本質上便是一種嶄新的創作。她借用班雅明〈譯者的任務〉(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的觀點來比喻:翻譯並非僅是將原作的意思轉換成另一種語言,而是為作品注入第二次生命。
有趣的是,當天零雨突然想起朋友將她的詩作讓AI生成旋律,當場就播放出來。聽起來精準無瑕,甚至極具霸榜潛力。那麼,為什麼人類還要繼續歌唱?還要繼續發出聲音?稍早時羅思容的即興吟唱,也許早已透露了答案。
辨識不出是什麼語言,但不覺陌生。她彷彿化身一顆頌缽,嗡嗡震盪空氣一圈圈漣漪;又像一支槳,擺盪桌椅與書櫃之間划開一條淙淙小河,流經在場所有人。我們就像共鳴的音箱,互相牽引出身體與聲波的顫動。極其安靜,而且細微。
那是一種超越語言的交流,像回到語言尚未被發明的時代。古印度的想像裡,宇宙最初不是光,而是聲音,是那道被稱作「Om」的原初震動。羅思容的吟唱彷彿召回了開天闢地的古老力量,糅雜生命經驗去浸潤每一次創作。她信奉的「聲音詩學」就是如此,彷彿對著虛空也對著宇宙,對著歷史參與一場浩瀚的對話。
「聲音不只是媒介,而是本源。」為了保留詩與歌最原初的力量,羅思容刻意捨棄傳統編制及錄音流程,細選了鋼琴、手風琴、打擊樂器、單簧管等樂器來共同編織。她帶著樂手一起讀詩,一起進入詩的情緒流動,簡單定下Key 及和弦,「然後就直接進錄音室了!不管我們是三人、五人或者更大的編制,每次湧現出來的情感都有所不同,就像海洋也每天都有變化啊。」
接近即興的錄音方式,每個當下都是唯一且最好的一次。奇妙的是,很少需要重來。羅思容也說,除了一些音韻上的微幅調整,專輯成品與5年前錄製的粗胚,幾乎沒有差別,彷彿在那個被詩附體的夜晚,聲音已臻圓滿。

➤在流動中互為彼此,找到屬於自己的藍
〈女兒〉說的,本來就是眾人的故事,你我的故事。零雨自陳先從照顧母親的經驗出發,將自我生命與他人故事,以及虛構想像揉合成極複雜且多層次的女兒意象,看見她們在不同情境中轉換身分。
生命角色的流動,往往隱藏著不安。尤其當女兒要反過來照顧年邁母親的時刻,不得不成為自己的母親,也成為她的母親。這可能是許多女兒最深層的恐懼,最無能為力的時刻,羅思容刻意保留一種哀莫大於心死的平靜,不生不滅的唱念,聽者彷彿看見一個正在海邊誦念金剛經的女兒。而她的身影,正是我們自身的倒影。(零雨:「唸金剛經這種事情,好像多半是女人會做的吧。」)
然而,女性生命角色的流動,並不全是荒涼的風景,它同時也蘊藏著豐饒與生機。羅思容提起舊作〈跈等阿姆跳舞〉(跟隨媽媽跳舞),記錄了與母親、女兒一同在戶外起舞的片刻。月光灑落,蝴蝶與蜜蜂在身邊穿梭飛舞,超越了血緣與物種的疆界,當下就像五代同堂的生命情境,「我們可以互為母親,互為女兒,互為大地,也互為海洋。」
女性的海洋,是日常涓滴匯流而成的。採訪開始之前,有隻小蟲異常乖順地停留在零雨袖口,她推開窗將小蟲放走,邊說自己只打蚊子。那麼蟑螂呢?「蟑螂也不打。」零雨傳授用抹布網羅蟑螂的祕訣,跟羅思容討論起蟑螂尺寸與移動速度的關係,再聊到每次從超市買回任何物品,得用南僑水晶肥皂細細洗過外包裝才安心。
在日常點滴中建立起屬於自己的秩序,小小的宇宙也因此得以安定,面對流動與轉變便多了從容。歷經過「成為母親的母親」的階段,零雨的時間感卻還童了,「我有時感覺自己是自己的女兒。以前年紀小,遇到事情很容易緊張,現在比較能安撫自己了。」
羅思容忙不迭點頭,「現在可以跟自己玩得很開心,就算媽媽不在身邊,也能陪伴自己。」
「其實女人從來不會長大。」零雨用一種像在形容什麼可愛動物的語氣說道。無論是什麼樣態的女兒,本來就是可愛的,值得愛的。
拍照的碼頭邊,她們衣衫頭髮被風吹起,不會長大的女人笑得開懷。她們身後的天空是藍的,淡水河是藍的,世界的女兒們穿越了浮世藍悲喜藍,讓力量回流到自身,成為滋養的源頭。九十九是接近無限的大,也是接納與等待,包容專屬我們自己的一種藍,互相陪伴,彼此映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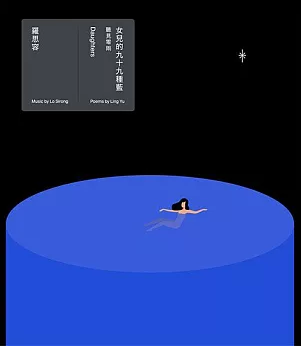 羅思容/女兒的九十九種藍——聽見零雨 羅思容/女兒的九十九種藍——聽見零雨
定價:690元
【內容簡介➤】
|
|
作者簡介:
歌手:羅思容
寫詩、畫畫、唱作歌詩。從獨特的語境尋找富於文學性與音樂性的創作語彙。她的音樂以詩為基調,並吸取北管、地方戲曲、原住民音樂等元素,植根傳統並吸納藍調、爵士、搖滾、古典樂等世界音樂的曲風,帶來多層次的交流對話和想像空間。
歌詩作品《每日》《攬花去》、《多一個》、《落腳》、《今本日係馬》並參與26張合輯,曾榮獲3座金曲獎、金音獎、華語音樂傳媒大獎等。詩文作品發表于《現代詩》、《臺灣文學季刊》、《笠詩刊》、香港《呼吸詩刊》、人間副刊等。中時晚報、幼獅文藝專欄寫作。十餘年來,持續譜唱台灣詩人作品,包含吳濁流、賴和、跨越語言一代詩人、周夢蝶、商禽、零雨…等五十餘家,並於日本、澳門、馬來西亞、香港、中國等地演出,也在流浪之歌音樂節、金鼎獎、總統文化獎頒獎典禮、台北詩歌節、台灣文學館、鍾肇政文學園區等重要典禮演出。版畫作品《愛情魚》、《自由落體》榮獲日本Awagumi版畫大賞的入選獎。
詩人:零雨
本名王美琴,台灣當代重要詩人。台灣大學中文系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亞語文碩士,哈佛大學訪問學者。自述30歲後開始寫詩,以第一本詩集《城的連作》踏入詩壇。2022年以詩集《女兒》獲頒台灣文學獎「金典獎」,2025年獲頒紐曼華語文學獎,是繼楊牧、朱天文、張貴興之後,第四位獲得此獎的台灣作家。該獎指出她的作品語言簡潔精煉,卻蘊含複雜意義,融會了古典與現代、東方和西方的文學、哲學、藝術等深厚底蘊,令人驚喜。
零雨寫詩主題多元、詩意浩瀚。生活素樸的她,詩眼透析事物本質,擅長捕捉日常場景的細膩氛圍,抑或是穿梭時空向經典致敬——她將對藝術的熱情,凝鍊成知性冷靜的筆調,創造出獨一無二的語言風格。曾任《國文天地》副總編輯、《現代詩》主編、《現在詩》創社發起人之一、宜蘭大學教師,現已退休專事寫作。她曾獲年度詩獎、吳濁流文學獎、太平洋國際詩歌獎。著有詩集《城的連作》、《消失在地圖上的名字》、《特技家族》、《木冬詠歌集》、《關於故鄉的一些計算》、《我正前往你》、《田園/下午五點四十九分》、《膚色的時光》等。
|
Tags:
編按:2022年詩人零雨出版詩集《女兒》,收錄10首描繪普世女性境遇的敘事詩,當年即獲得Openbook好書獎年度中文創作。今(2025)年零雨更榮獲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
長期關注女性議題的詩人暨音樂人羅思容,早在《多一個》專輯時即曾與零雨合作,當年她讀到〈女兒〉組詩時即深受感動,決定改編成歌。而長期致力於以影像保存文學的目宿媒體,也在拍攝「我們在島嶼朗讀」短片時,與詩人零雨結下緣分。
隨著詩人、音樂人及文化媒體的相遇,目宿首次製作發行詩歌跨域企劃「聽見零雨」音樂專輯與單曲。三方最終以4年時間,醞釀出華語詩歌新專輯《女兒的九十九種藍》。
羅思容以同為女性的心跳和文學之眼,將零雨〈女兒〉組詩譜曲成歌,唱出疼痛又療癒的生命樂章。《女兒的九十九種藍》近日在串流平台推出,實體專輯預計8/25上市。新專輯問世之際,零雨、羅思容共同接受Openbook專訪,透過女兒、孕育、創作等意象,暢談身為女人(兒)、同為創作者,在本次詩歌跨界計畫交流的心得。
一張專輯可以有很多種聽法。第一次播放《女兒的九十九種藍》,戴著耳機,邊做雜事漫不經心,沒有任何閱讀準備,樂音先一步抵達。忽遠忽近的手風琴像一波波潮汐,沖淡了世界。頃刻間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正中央,一個母體橫空出世,神聖,莊嚴,無垠。
那一刻,我連忙翻看歌詞:
原來詩可以有這種讀法。先關閉眼睛和邏輯,用聽覺和直覺去讀。原來聲音也有情節、有光影、有氣候。
對於還不清楚《女兒的九十九種藍》來歷的閱聽者,最直白的介紹方式,是音樂人羅思容為零雨組詩〈女兒〉譜曲的專輯。但若只是單純譜曲,恐怕唱不出波浪和月光。或許更貼切的說法,是羅思容所形容的「以詩入歌」——不只是譜寫旋律,而是沉入〈女兒〉的子宮,在那裡潛伏、滋養,與詩同體呼吸,孕育出一片聲音的海洋。
如同封面深淺交疊的藍,這張專輯拍打出一片無邊的流域,女人、母親、女兒、創作者、閱聽者的角色彼此滲透、轉換、流動,生命在詩與聲音中不斷誕生,也不斷孕育他者,潮汐般循環往復。
➤被女兒召喚,十首詩一夜成曲
唱詩,尤其是唱零雨的詩,羅思容並不陌生。2015年羅思容與孤毛頭樂團專輯選擇 12 位台灣重要女性詩人,為其詩作譜曲歌詠,製作專輯《多一個》,其中一首即是零雨的〈關於故鄉的一些算計〉。
《女兒的九十九種藍》是兩人的再度交會,也是一次更浩大的挑戰。就零雨聽來,相較〈關於故鄉的一些算計〉民謠曲風,這回的編制與氣勢更爲宏闊,可能是羅思容創作的一大突破。她以原創者的視角坦言,創作〈女兒〉時沒想過要改編成歌,詩中大量口語、白話、生硬的醫療用詞,都讓她疑惑:「到底要怎麼唱?這真的好困難。」
零雨的困惑其來有自。《女兒的九十九種藍》如潮汐變化萬千,時而肅殺,時而瘋癲,時而莊嚴,時而低泣,卻都貼伏著文字的呼吸節奏。你想像不到這首詩能這樣唱,然而經由羅思容的聲音,那些字就像找到自己的喉嚨。
更意外的是,羅思容只用一夜時間,抱著一把吉他就為〈女兒〉10首詩譜好了曲。
那是怎麼樣的一個夜晚?詩如何啟動她的創作閥,讓樂音如海潮傾瀉?
羅思容說,第一次讀〈女兒〉組詩,被震撼得不由自主流淚。開篇的序詩宣告:「這些女兒 / 發明了二十世紀的波浪」,是一句神聖的宣示,也是聲聲召喚,讓她想用喉嚨與音樂唱和回應。「這10首詩像百年來全世界女性的生存樣貌與命運,是文學與詩史上獨一無二的作品。」羅思容說,〈女兒〉寫到歇斯底里、憂鬱等等那些女人被污名化的標籤,也寫到社會與醫療體制的隱性壓迫,但零雨沒有直接控訴,而是讓一切潛伏在看似平靜的海面之下。
歷經漂泊、掙扎、對抗之後,一切終將回到海洋。那裡是生命的根源,像母親的子宮,也像未來的搖籃,涵融一切的危險與不可預測性。
在〈女兒〉中,海洋反覆出現。它是誕生,是嚮往的歸途,也是女性之間不需言語就能心領神會的匯流處,同樣在羅思容的創作中潛伏已久。她沒有正式公開發表的詩作〈秘〉寫道:
➤以詩入歌:就像附身,然後轉生
訪談中,羅思容言談方式極富詩意,總是意象先於論述,感受先於邏輯。她的話語不僅止於吐出語言,而是展開一幅圖像。她形容以詩入歌,也帶著強烈的身體感,「就像附身,然後轉生,孕育出另一個新生。我們相互邂逅,又相互成為彼此。」
改編零雨的詩,挑戰在於如何承接詩人思想裡的複雜與深度。詩或藝術作品,最觸動人心的,是隱藏其中作者的生命質地。身體、語言、文化、心靈都必須敞開,才能與詩相遇。
唱詩,先從念誦詩開始。詩如咒,引領身體與直覺深入文句間的流動,帶羅思容通天遁地,潛入海底三萬呎,讓自己的、零雨的、古老的原始的、現代的新穎的女性故事一一經過她。羅思容的身體變成記憶的載體,喉嚨變成產道,吟詠出一首首圖像各異卻氣息相連的生命之歌。
那個被召喚的夜晚,歌從詩的子宮破水而出,向世界發出第一道聲響。
➤瘋癲與甜美並存,憂鬱與神聖同在的女兒
這張專輯的誕生,起源於零雨的邀約。2020 年中研院中國文哲所研究員楊小濱舉辦現代詩座談會,以〈女兒〉為主題。零雨遂邀請羅思容以詩為基礎創作歌曲。本來以為只採一、兩首詩來應和座談會跨界元素,沒想到 5 年後在目宿媒體支持下,以完整的專輯型態面世。
零雨回憶,第一次聽到羅思容僅以一把吉他伴奏的錄音時,便深受觸動。尤其序詩〈發明波浪的女兒W〉聖詠般的低音共振出一種深沉的悲劇感,為整張專輯定下基調。隨著旋律起伏跌宕,她在〈黑色的女兒L〉聽見了轉折,「像在大海找到浮木,有人共同奮鬥的感覺。」當樂音流向第10首〈牙牙學語的女兒K〉,最後的大合唱收尾,更讓零雨感動莫名。
但其實,兩人對於〈牙牙學語的女兒K〉有著截然不同的詮釋。零雨說,可能多數讀者會將這首詩視為和解,然而她心底是悲觀的,「世人都喜歡甜甜的,我就有點反諷的意味去寫『聽海的搖籃曲/甜甜的/餵給你』」
莊嚴、神聖、不安、憂鬱、被污名、寬廣、瘋癲……這些情緒狀態在〈女兒〉中交織成一張大網,羅思容主張:「我們就承認吧,穿越吧,瘋就瘋到底。也像〈牙牙學語的女兒K〉的合唱,要甜就甜到底。」
甜,有何不可?甜,是女性集體的力量,也是高舉的武器。穿越過種種情狀後,羅思容蛻變為世界的女兒、女兒、母親,超越語言的女聲大合唱是一首安魂曲,讓生命靈魂在此安頓,再次啟程,繼續徜徉在世界的海洋中。
➤用身體保留聲音的本源
不同觀點的敘事,讓原作有了新的神情。零雨認為,經過改編的音樂作品,本質上便是一種嶄新的創作。她借用班雅明〈譯者的任務〉(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的觀點來比喻:翻譯並非僅是將原作的意思轉換成另一種語言,而是為作品注入第二次生命。
有趣的是,當天零雨突然想起朋友將她的詩作讓AI生成旋律,當場就播放出來。聽起來精準無瑕,甚至極具霸榜潛力。那麼,為什麼人類還要繼續歌唱?還要繼續發出聲音?稍早時羅思容的即興吟唱,也許早已透露了答案。
辨識不出是什麼語言,但不覺陌生。她彷彿化身一顆頌缽,嗡嗡震盪空氣一圈圈漣漪;又像一支槳,擺盪桌椅與書櫃之間划開一條淙淙小河,流經在場所有人。我們就像共鳴的音箱,互相牽引出身體與聲波的顫動。極其安靜,而且細微。
那是一種超越語言的交流,像回到語言尚未被發明的時代。古印度的想像裡,宇宙最初不是光,而是聲音,是那道被稱作「Om」的原初震動。羅思容的吟唱彷彿召回了開天闢地的古老力量,糅雜生命經驗去浸潤每一次創作。她信奉的「聲音詩學」就是如此,彷彿對著虛空也對著宇宙,對著歷史參與一場浩瀚的對話。
「聲音不只是媒介,而是本源。」為了保留詩與歌最原初的力量,羅思容刻意捨棄傳統編制及錄音流程,細選了鋼琴、手風琴、打擊樂器、單簧管等樂器來共同編織。她帶著樂手一起讀詩,一起進入詩的情緒流動,簡單定下Key 及和弦,「然後就直接進錄音室了!不管我們是三人、五人或者更大的編制,每次湧現出來的情感都有所不同,就像海洋也每天都有變化啊。」
接近即興的錄音方式,每個當下都是唯一且最好的一次。奇妙的是,很少需要重來。羅思容也說,除了一些音韻上的微幅調整,專輯成品與5年前錄製的粗胚,幾乎沒有差別,彷彿在那個被詩附體的夜晚,聲音已臻圓滿。
➤在流動中互為彼此,找到屬於自己的藍
〈女兒〉說的,本來就是眾人的故事,你我的故事。零雨自陳先從照顧母親的經驗出發,將自我生命與他人故事,以及虛構想像揉合成極複雜且多層次的女兒意象,看見她們在不同情境中轉換身分。
生命角色的流動,往往隱藏著不安。尤其當女兒要反過來照顧年邁母親的時刻,不得不成為自己的母親,也成為她的母親。這可能是許多女兒最深層的恐懼,最無能為力的時刻,羅思容刻意保留一種哀莫大於心死的平靜,不生不滅的唱念,聽者彷彿看見一個正在海邊誦念金剛經的女兒。而她的身影,正是我們自身的倒影。(零雨:「唸金剛經這種事情,好像多半是女人會做的吧。」)
然而,女性生命角色的流動,並不全是荒涼的風景,它同時也蘊藏著豐饒與生機。羅思容提起舊作〈跈等阿姆跳舞〉(跟隨媽媽跳舞),記錄了與母親、女兒一同在戶外起舞的片刻。月光灑落,蝴蝶與蜜蜂在身邊穿梭飛舞,超越了血緣與物種的疆界,當下就像五代同堂的生命情境,「我們可以互為母親,互為女兒,互為大地,也互為海洋。」
女性的海洋,是日常涓滴匯流而成的。採訪開始之前,有隻小蟲異常乖順地停留在零雨袖口,她推開窗將小蟲放走,邊說自己只打蚊子。那麼蟑螂呢?「蟑螂也不打。」零雨傳授用抹布網羅蟑螂的祕訣,跟羅思容討論起蟑螂尺寸與移動速度的關係,再聊到每次從超市買回任何物品,得用南僑水晶肥皂細細洗過外包裝才安心。
在日常點滴中建立起屬於自己的秩序,小小的宇宙也因此得以安定,面對流動與轉變便多了從容。歷經過「成為母親的母親」的階段,零雨的時間感卻還童了,「我有時感覺自己是自己的女兒。以前年紀小,遇到事情很容易緊張,現在比較能安撫自己了。」
羅思容忙不迭點頭,「現在可以跟自己玩得很開心,就算媽媽不在身邊,也能陪伴自己。」
「其實女人從來不會長大。」零雨用一種像在形容什麼可愛動物的語氣說道。無論是什麼樣態的女兒,本來就是可愛的,值得愛的。
拍照的碼頭邊,她們衣衫頭髮被風吹起,不會長大的女人笑得開懷。她們身後的天空是藍的,淡水河是藍的,世界的女兒們穿越了浮世藍悲喜藍,讓力量回流到自身,成為滋養的源頭。九十九是接近無限的大,也是接納與等待,包容專屬我們自己的一種藍,互相陪伴,彼此映照。●
定價:69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
歌手:羅思容
寫詩、畫畫、唱作歌詩。從獨特的語境尋找富於文學性與音樂性的創作語彙。她的音樂以詩為基調,並吸取北管、地方戲曲、原住民音樂等元素,植根傳統並吸納藍調、爵士、搖滾、古典樂等世界音樂的曲風,帶來多層次的交流對話和想像空間。
歌詩作品《每日》《攬花去》、《多一個》、《落腳》、《今本日係馬》並參與26張合輯,曾榮獲3座金曲獎、金音獎、華語音樂傳媒大獎等。詩文作品發表于《現代詩》、《臺灣文學季刊》、《笠詩刊》、香港《呼吸詩刊》、人間副刊等。中時晚報、幼獅文藝專欄寫作。十餘年來,持續譜唱台灣詩人作品,包含吳濁流、賴和、跨越語言一代詩人、周夢蝶、商禽、零雨…等五十餘家,並於日本、澳門、馬來西亞、香港、中國等地演出,也在流浪之歌音樂節、金鼎獎、總統文化獎頒獎典禮、台北詩歌節、台灣文學館、鍾肇政文學園區等重要典禮演出。版畫作品《愛情魚》、《自由落體》榮獲日本Awagumi版畫大賞的入選獎。
詩人:零雨
本名王美琴,台灣當代重要詩人。台灣大學中文系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亞語文碩士,哈佛大學訪問學者。自述30歲後開始寫詩,以第一本詩集《城的連作》踏入詩壇。2022年以詩集《女兒》獲頒台灣文學獎「金典獎」,2025年獲頒紐曼華語文學獎,是繼楊牧、朱天文、張貴興之後,第四位獲得此獎的台灣作家。該獎指出她的作品語言簡潔精煉,卻蘊含複雜意義,融會了古典與現代、東方和西方的文學、哲學、藝術等深厚底蘊,令人驚喜。
零雨寫詩主題多元、詩意浩瀚。生活素樸的她,詩眼透析事物本質,擅長捕捉日常場景的細膩氛圍,抑或是穿梭時空向經典致敬——她將對藝術的熱情,凝鍊成知性冷靜的筆調,創造出獨一無二的語言風格。曾任《國文天地》副總編輯、《現代詩》主編、《現在詩》創社發起人之一、宜蘭大學教師,現已退休專事寫作。她曾獲年度詩獎、吳濁流文學獎、太平洋國際詩歌獎。著有詩集《城的連作》、《消失在地圖上的名字》、《特技家族》、《木冬詠歌集》、《關於故鄉的一些計算》、《我正前往你》、《田園/下午五點四十九分》、《膚色的時光》等。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
閱讀通信 vol.364》星象顯示今年最亮眼的書是……
【徵才】Openbook閱讀誌誠徵夥伴 · 全職編輯 · 一名!
延伸閱讀
詩人計畫.零雨》深情而無窮大的浩瀚系詩人
「詩人計畫」希望透過專訪,探尋詩人廣袤的心靈,縱述創作與生命史,捕捉日常中詩意展現的瞬間。此計畫由詩評人沈眠與Openbook閱讀誌共同企劃,... 閱讀更多
2022Openbook好書獎.年度中文創作》女兒
閱讀更多
書.人生.羅思容》閱讀像愛情
總有那麼一本或數本書,一位或多位文人作家,曾在我們的閱讀行旅中,留下難以遺忘的足跡。「書.人生」專欄邀請各界方家隨筆描摹,記述一段未曾與外人道的書與人的故事。...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