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個世紀,我也寫過科幻小說。但我長期投身同志文學史,多年來擱置科幻。怎知道,2021年的奇妙因緣把我送回科幻世界:澳洲學者韓瑞(Ari Heinrich)在邱妙津《蒙馬特遺書》英文譯本之後,接著完成拙作《膜》的英文翻譯。不少英文媒體看了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英文版,便用書評或專訪的形式,探問為什麼《膜》會在1990年代台灣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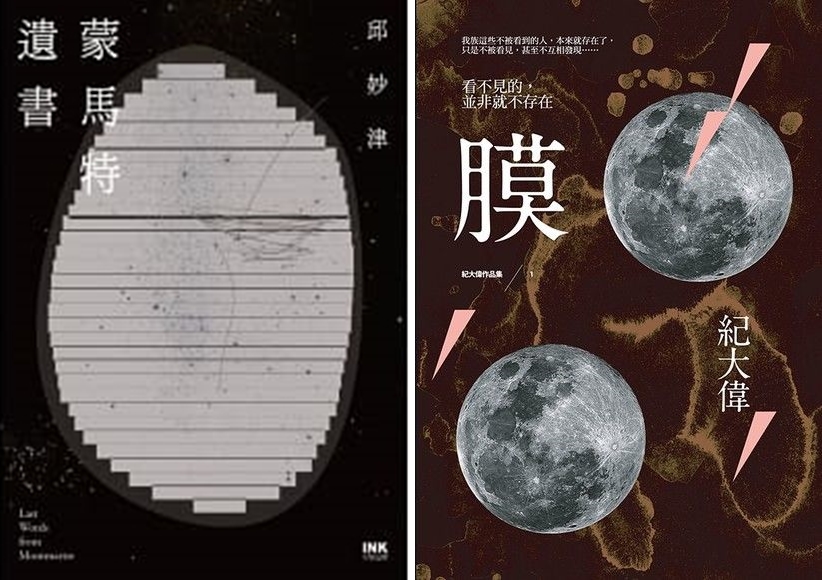
為了回應各界提問,也為了修補自己對於科幻的想法,我惡補多種英文科幻,其中包括三位英國重量級作家的近作:石黑一雄2021年的《克拉拉與太陽》,麥克尤恩的2019年小說《像我這樣的機器》,以及讀者眼前這本溫特森的2019年小說,《科學愛人》。
對台灣讀者來說,石黑早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前就廣受歡迎,麥克尤恩的歷史小說《贖罪》和改編電影為人津津樂道,溫特森的成名作《柳橙不是唯一的水果》,具有自傳色彩的女同性戀成長故事,網羅死忠粉絲。

上述三本小說不約而同聚焦在「人機一體」這種介於人類和機器之間的形體,例如生化人(android)、複製人(replica; clone)、賽伯格(cyborg)。這幾種形體各有千秋,不可一概而論,我在這篇短文為了方便,只好暫時統稱它們為人機一體角色。石黑早就寫過改編成影劇的科幻小說《別讓我走》,溫特森也寫過反烏托邦小說,但是這三位名家在短時間內密集推出形體類似的人機一體小說主人翁,畢竟讓人好奇:難不成他們同時遇到宇宙下訂單?
我臆測,這是因為時至2010年代,人們不得不承認人類的界線已經瓦解。人們在2010年代徹底捲入社群網站打造的「後真實」世界(美國總統大選、英國脫歐公投、台灣幾次大選,都顯然遭到各種社群網站操弄)——人類再也無法確認自己對於世界的認知,是否如同科幻片裡頭被植入人腦的假記憶。
再說,各家紛紛指認AI(人工智慧)即將帶來下一波挑戰(真人的現職都要被AI這種假人給搶走;大家的擇偶對象恐怕不再是真人而是AI人偶),那麼,真人和假人的界線,要如何維持?處於這種時代氛圍中,就算再嚴肅的小說家也想要利用科幻小說這種「不嚴肅」的通俗形式,點評人類的疆界要如何重畫。
科幻小說包含的類別繁多,宇宙探險故事是一類,在科幻電影常見,但畢竟遠在天邊。人機一體故事則是科幻體系中的另一類,看起來遠比宇宙探險逼近你我:玩手機(或者被手機玩)的低頭族被手機擺布,一個口令一個動作,通通變成複製人;從戴上紫色隱形眼鏡的學生、攜帶計步器計算運動量的上班族,到連結葉克膜續命的病患,都是科技跟人體結合的賽伯格。至於跟人同進同出的智慧型手機,根本就是生化人——「android」這個字本來是指《銀翼殺手》電影中的生化人(我在上一世紀常用的email ID,就是「android」),如今變成某種手機的名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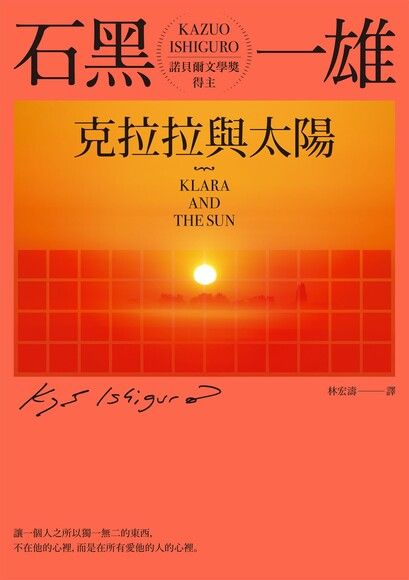 在各國熱賣的《克拉拉與太陽》中,主人翁克拉拉是個少女模樣的人型玩偶。她的任務就是要在人類越來越難以交朋友的新世紀,為孤僻的小朋友帶來友情。克拉拉一方面要忠於付錢買她的家長,另一方面也要滿足她服務的小朋友,結果三者之間出現三角關係的情感張力。克拉拉逾越的界線,包括她的職業倫理界線,也包括人類與非人類的界線:她這個非人類善解人意,比人類更具人性。
在各國熱賣的《克拉拉與太陽》中,主人翁克拉拉是個少女模樣的人型玩偶。她的任務就是要在人類越來越難以交朋友的新世紀,為孤僻的小朋友帶來友情。克拉拉一方面要忠於付錢買她的家長,另一方面也要滿足她服務的小朋友,結果三者之間出現三角關係的情感張力。克拉拉逾越的界線,包括她的職業倫理界線,也包括人類與非人類的界線:她這個非人類善解人意,比人類更具人性。
在《像我這樣的機器》中,一對男女買了一具生化人解悶,怎知道這位非人類壯漢跟女主人劈腿,卻又滿口道德,成為這對男女急於脫手的夢魘。《像我這樣的機器》書名至少對應兩種詮釋:一,生化人就像是人類男主人這樣——這種詮釋的「我」,是人類男性;二,眾多生化人就是生化人壯丁這樣——這種詮釋的「我」,反而是這位敢愛敢殺的生化人。這兩種並存的詮釋,對應書中競爭主導權的兩名男性,並且對應書中平行的兩條故事線:一條是三名主角的小天地,另一條是架空歷史的英國社會(在另類歷史中,同性戀解碼名家圖靈沒有早死,反而轉型成為人工智慧專家)。
上述兩部小說各自鋪陳少女版本、成年版本的三角戀愛:人機一體會介入(而且足以摧毀)既有的人倫關係。乍聽之下,石黑和麥克尤恩似乎是保守派,因為他們擔憂人機一體的角色破壞人倫,但是仔細一看,他們的立場不盡然如此:他們筆下的少女賽伯格和壯丁生化人都擇善固執,因而看破血肉人類的鄉愿偽善。非人類足以瓦解人類的倫理,是因為親子關係或男女關係早就千瘡百孔、不堪一擊。
我先介紹石黑和麥克尤恩的小說,再轉向溫特森的《科學愛人》,一方面是要為溫特森這位巨星暖場,另一方面是要把《科學怪人》放入當代英國文壇網絡。畢竟,這部小說並不是懸置在歷史真空中的孤例。《科學愛人》的中英文書名都向《科學怪人》這部號稱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說致敬,但致敬之中也含有惡搞:「怪人」變成「愛人」,「Frankenstein」變成「Frankissstein」。

《科學愛人》作者珍奈‧溫特森(Jeanette Winterson),照片:University of Salford Press Office
書名的中文翻譯是神來之筆:《科學怪人》述說19世紀瘋狂科學家打造人見人怕的怪物,重點的確在於怪物的「怪」。《科學愛人》則鋪陳21世紀新創企業量產性愛機器人,重點變成機器人誘發的「愛慾」。
英文書名「Frankenstein」原本是瘋狂科學家法蘭肯斯坦的名字——但各國流行文化通常誤以為法蘭肯斯坦是怪物的名字——這是誤會,因為《科學怪人》原作中的怪物並沒有名字。溫特森發明的「Frankissstein」這個新字,形同「法蘭肯斯坦」這個名字的扭曲變形,名字拉長的部分,多了幾個「s」,像是打結的手機充電線,新字裡頭還埋藏了「kiss接吻」這個愛慾行為。
《科學怪人》的怪物由死人屍體碎塊縫合而成,猶如今日廉價的組裝牛排。改寫《科學怪人》的《科學愛人》則將文本當作肉塊一樣切割,並且重新排列組合。《科學愛人》來回縫合兩條故事線:在第一條故事線,《科學怪人》的原作者瑪麗.雪萊活在19世紀初,跟著丈夫雪萊(英國浪漫主義大詩人之一)追求生命的出口,卻一再承受至親至愛的生命結束:親生子嗣一個接一個早夭,就連丈夫雪萊也意外早死。
目擊太多死亡之後,瑪麗.雪萊有感而發,在小說中將屍體轉化成新生命。在第二條故事線,「麗雪萊」(也就是「瑪麗.雪萊」這個名字的變形,中文版翻譯成「芮雪萊」)是活在今日的跨性別科學家,致力打造滿足世人的性愛機器人。第一條故事線的背景是歐洲各大古城,第二條故事線的背景則是美國內陸鳥不生蛋的科學園區——這個場景轉換,暗示科學研發的全球中心早就從歐洲轉移到美國。
石黑和麥克尤恩都把發言權交給人機一體的角色,故事線也就逾越了人類與非人的界線。溫特森的小說倒不一樣,沒有把發言權交給被製造出來的怪物或性愛機器人,而是讓19世紀的瑪麗.雪萊以及21世紀的「倫羅德」儘量吐露心聲。
「倫羅德」這個名字是「羅德拜倫」——亦即「拜倫勳爵」(Lord Byron,一般簡稱「拜倫」)的英譯——的變形。在19世紀,同樣身為浪漫主義大詩人的拜倫,是雪萊夫婦追隨的文壇大哥;在21世紀,倫羅德則是愛財好色的粗俗商人,開口閉口就譏諷中國市場對於性愛玩伴的飢渴。溫特森蜻蜓點水提及中國,自然反映了今日英國跟中國的緊張關係。溫特森筆下逾越人與非人界線的行為,並不是在人造人那邊,而是在人造人的產製者(瑪麗.雪萊和倫羅德)這邊的內心小劇場。
在《科學愛人》,19世紀的瑪麗.雪萊和21世紀的倫羅德儼然是全書兩大主角。這兩個角色性情差異極大,似乎搭不起來,但他們剛好同樣展現了當代人的極度孤獨:瑪麗.雪萊送走一具又一具屍體,倫羅德則在一具又一具玩具之間打滾。他們不敢指望活人陪伴,頂多寄望人造物。
值得留意的是,人造物並非只限於用肉塊重新排列組合的情趣機器人,也包括用文字段落重新組合而成的小說。瑪麗.雪萊和溫特森打造的活人愛侶替代品,不是人機一體生化人,而是科幻小說——或者該說,科幻小說就是當代人孤枕難眠之際,陪人入夢的生化人。只不過,這種生化人的形狀不像人體而像是書本,甚至像是電子書一樣沒有形體。在我們不斷被迫改用視訊調情取代實體親密的疫情時刻,《科學愛人》的寓言更是當頭棒喝。●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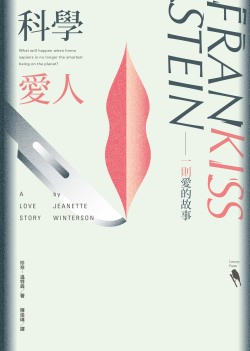 科學愛人:一則愛的故事 科學愛人:一則愛的故事
Frankissstein:A Love Story
作者:珍奈.溫特森(Jeanette Winterson)
譯者:陳佳琳
出版:新經典文化
定價:420元
【內容簡介➤】
|
|
作者簡介:珍奈.溫特森 (Jeanette Winterson)
英國當代小說家,1985年寫下自傳色彩的第一部作品《柳橙不是唯一的水果》,獲頒英國惠特布雷小說獎,授權BBC拍成影集,並親自改編,獲得許多國際大獎。2013年她再以成長題材寫出暢銷又獲獎的回憶錄《正常就好,何必快樂?》。2006年因其文學成就獲頒大英帝國勳章(OBE)。
溫特森童年遭親生父母棄養,由信仰虔誠的溫特森夫婦收養,在曼徹斯特受教育成長。然而她因為愛上女孩,不見容於養父母,也無法再從事家庭期待於她的傳教工作,16歲決定離家自立更生。艱難的年少生活,養成她獨立思考的特質,且言論大膽,對自己熱愛的文學勇敢發聲。如今她已是英國文壇公認代表性的聲音。BBC舉辦「女性分水嶺小說」票選中,她以三部作品同時獲得提名,成為入選作品最多的當代小說家。
目前為止她總共出版了10部小說,另外著有童書、非虛構作品和劇本,並長期為《衛報》撰稿。
|
Tags:
(圖片來源:Unsplash/Susan Wilkinson)
在上一個世紀,我也寫過科幻小說。但我長期投身同志文學史,多年來擱置科幻。怎知道,2021年的奇妙因緣把我送回科幻世界:澳洲學者韓瑞(Ari Heinrich)在邱妙津《蒙馬特遺書》英文譯本之後,接著完成拙作《膜》的英文翻譯。不少英文媒體看了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英文版,便用書評或專訪的形式,探問為什麼《膜》會在1990年代台灣出現。
為了回應各界提問,也為了修補自己對於科幻的想法,我惡補多種英文科幻,其中包括三位英國重量級作家的近作:石黑一雄2021年的《克拉拉與太陽》,麥克尤恩的2019年小說《像我這樣的機器》,以及讀者眼前這本溫特森的2019年小說,《科學愛人》。
對台灣讀者來說,石黑早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前就廣受歡迎,麥克尤恩的歷史小說《贖罪》和改編電影為人津津樂道,溫特森的成名作《柳橙不是唯一的水果》,具有自傳色彩的女同性戀成長故事,網羅死忠粉絲。
上述三本小說不約而同聚焦在「人機一體」這種介於人類和機器之間的形體,例如生化人(android)、複製人(replica; clone)、賽伯格(cyborg)。這幾種形體各有千秋,不可一概而論,我在這篇短文為了方便,只好暫時統稱它們為人機一體角色。石黑早就寫過改編成影劇的科幻小說《別讓我走》,溫特森也寫過反烏托邦小說,但是這三位名家在短時間內密集推出形體類似的人機一體小說主人翁,畢竟讓人好奇:難不成他們同時遇到宇宙下訂單?
我臆測,這是因為時至2010年代,人們不得不承認人類的界線已經瓦解。人們在2010年代徹底捲入社群網站打造的「後真實」世界(美國總統大選、英國脫歐公投、台灣幾次大選,都顯然遭到各種社群網站操弄)——人類再也無法確認自己對於世界的認知,是否如同科幻片裡頭被植入人腦的假記憶。
再說,各家紛紛指認AI(人工智慧)即將帶來下一波挑戰(真人的現職都要被AI這種假人給搶走;大家的擇偶對象恐怕不再是真人而是AI人偶),那麼,真人和假人的界線,要如何維持?處於這種時代氛圍中,就算再嚴肅的小說家也想要利用科幻小說這種「不嚴肅」的通俗形式,點評人類的疆界要如何重畫。
科幻小說包含的類別繁多,宇宙探險故事是一類,在科幻電影常見,但畢竟遠在天邊。人機一體故事則是科幻體系中的另一類,看起來遠比宇宙探險逼近你我:玩手機(或者被手機玩)的低頭族被手機擺布,一個口令一個動作,通通變成複製人;從戴上紫色隱形眼鏡的學生、攜帶計步器計算運動量的上班族,到連結葉克膜續命的病患,都是科技跟人體結合的賽伯格。至於跟人同進同出的智慧型手機,根本就是生化人——「android」這個字本來是指《銀翼殺手》電影中的生化人(我在上一世紀常用的email ID,就是「android」),如今變成某種手機的名號。
在《像我這樣的機器》中,一對男女買了一具生化人解悶,怎知道這位非人類壯漢跟女主人劈腿,卻又滿口道德,成為這對男女急於脫手的夢魘。《像我這樣的機器》書名至少對應兩種詮釋:一,生化人就像是人類男主人這樣——這種詮釋的「我」,是人類男性;二,眾多生化人就是生化人壯丁這樣——這種詮釋的「我」,反而是這位敢愛敢殺的生化人。這兩種並存的詮釋,對應書中競爭主導權的兩名男性,並且對應書中平行的兩條故事線:一條是三名主角的小天地,另一條是架空歷史的英國社會(在另類歷史中,同性戀解碼名家圖靈沒有早死,反而轉型成為人工智慧專家)。
上述兩部小說各自鋪陳少女版本、成年版本的三角戀愛:人機一體會介入(而且足以摧毀)既有的人倫關係。乍聽之下,石黑和麥克尤恩似乎是保守派,因為他們擔憂人機一體的角色破壞人倫,但是仔細一看,他們的立場不盡然如此:他們筆下的少女賽伯格和壯丁生化人都擇善固執,因而看破血肉人類的鄉愿偽善。非人類足以瓦解人類的倫理,是因為親子關係或男女關係早就千瘡百孔、不堪一擊。
我先介紹石黑和麥克尤恩的小說,再轉向溫特森的《科學愛人》,一方面是要為溫特森這位巨星暖場,另一方面是要把《科學怪人》放入當代英國文壇網絡。畢竟,這部小說並不是懸置在歷史真空中的孤例。《科學愛人》的中英文書名都向《科學怪人》這部號稱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說致敬,但致敬之中也含有惡搞:「怪人」變成「愛人」,「Frankenstein」變成「Frankissstein」。
書名的中文翻譯是神來之筆:《科學怪人》述說19世紀瘋狂科學家打造人見人怕的怪物,重點的確在於怪物的「怪」。《科學愛人》則鋪陳21世紀新創企業量產性愛機器人,重點變成機器人誘發的「愛慾」。
英文書名「Frankenstein」原本是瘋狂科學家法蘭肯斯坦的名字——但各國流行文化通常誤以為法蘭肯斯坦是怪物的名字——這是誤會,因為《科學怪人》原作中的怪物並沒有名字。溫特森發明的「Frankissstein」這個新字,形同「法蘭肯斯坦」這個名字的扭曲變形,名字拉長的部分,多了幾個「s」,像是打結的手機充電線,新字裡頭還埋藏了「kiss接吻」這個愛慾行為。
《科學怪人》的怪物由死人屍體碎塊縫合而成,猶如今日廉價的組裝牛排。改寫《科學怪人》的《科學愛人》則將文本當作肉塊一樣切割,並且重新排列組合。《科學愛人》來回縫合兩條故事線:在第一條故事線,《科學怪人》的原作者瑪麗.雪萊活在19世紀初,跟著丈夫雪萊(英國浪漫主義大詩人之一)追求生命的出口,卻一再承受至親至愛的生命結束:親生子嗣一個接一個早夭,就連丈夫雪萊也意外早死。
目擊太多死亡之後,瑪麗.雪萊有感而發,在小說中將屍體轉化成新生命。在第二條故事線,「麗雪萊」(也就是「瑪麗.雪萊」這個名字的變形,中文版翻譯成「芮雪萊」)是活在今日的跨性別科學家,致力打造滿足世人的性愛機器人。第一條故事線的背景是歐洲各大古城,第二條故事線的背景則是美國內陸鳥不生蛋的科學園區——這個場景轉換,暗示科學研發的全球中心早就從歐洲轉移到美國。
石黑和麥克尤恩都把發言權交給人機一體的角色,故事線也就逾越了人類與非人的界線。溫特森的小說倒不一樣,沒有把發言權交給被製造出來的怪物或性愛機器人,而是讓19世紀的瑪麗.雪萊以及21世紀的「倫羅德」儘量吐露心聲。
「倫羅德」這個名字是「羅德拜倫」——亦即「拜倫勳爵」(Lord Byron,一般簡稱「拜倫」)的英譯——的變形。在19世紀,同樣身為浪漫主義大詩人的拜倫,是雪萊夫婦追隨的文壇大哥;在21世紀,倫羅德則是愛財好色的粗俗商人,開口閉口就譏諷中國市場對於性愛玩伴的飢渴。溫特森蜻蜓點水提及中國,自然反映了今日英國跟中國的緊張關係。溫特森筆下逾越人與非人界線的行為,並不是在人造人那邊,而是在人造人的產製者(瑪麗.雪萊和倫羅德)這邊的內心小劇場。
在《科學愛人》,19世紀的瑪麗.雪萊和21世紀的倫羅德儼然是全書兩大主角。這兩個角色性情差異極大,似乎搭不起來,但他們剛好同樣展現了當代人的極度孤獨:瑪麗.雪萊送走一具又一具屍體,倫羅德則在一具又一具玩具之間打滾。他們不敢指望活人陪伴,頂多寄望人造物。
值得留意的是,人造物並非只限於用肉塊重新排列組合的情趣機器人,也包括用文字段落重新組合而成的小說。瑪麗.雪萊和溫特森打造的活人愛侶替代品,不是人機一體生化人,而是科幻小說——或者該說,科幻小說就是當代人孤枕難眠之際,陪人入夢的生化人。只不過,這種生化人的形狀不像人體而像是書本,甚至像是電子書一樣沒有形體。在我們不斷被迫改用視訊調情取代實體親密的疫情時刻,《科學愛人》的寓言更是當頭棒喝。●
Frankissstein:A Love Story
作者:珍奈.溫特森(Jeanette Winterson)
譯者:陳佳琳
出版:新經典文化
定價:42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珍奈.溫特森 (Jeanette Winterson)
英國當代小說家,1985年寫下自傳色彩的第一部作品《柳橙不是唯一的水果》,獲頒英國惠特布雷小說獎,授權BBC拍成影集,並親自改編,獲得許多國際大獎。2013年她再以成長題材寫出暢銷又獲獎的回憶錄《正常就好,何必快樂?》。2006年因其文學成就獲頒大英帝國勳章(OBE)。
溫特森童年遭親生父母棄養,由信仰虔誠的溫特森夫婦收養,在曼徹斯特受教育成長。然而她因為愛上女孩,不見容於養父母,也無法再從事家庭期待於她的傳教工作,16歲決定離家自立更生。艱難的年少生活,養成她獨立思考的特質,且言論大膽,對自己熱愛的文學勇敢發聲。如今她已是英國文壇公認代表性的聲音。BBC舉辦「女性分水嶺小說」票選中,她以三部作品同時獲得提名,成為入選作品最多的當代小說家。
目前為止她總共出版了10部小說,另外著有童書、非虛構作品和劇本,並長期為《衛報》撰稿。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
閱讀通信 vol.370》當我在書裡讀到你的時候
延伸閱讀
話題》不朽的科幻史詩:葉李華談艾西莫夫「基地三部曲」
科幻小說大師以撒.艾西莫夫(Isaac Asimov)一生創作不懈,曾多次榮獲科幻界最高榮譽雨果獎與星雲獎,作品浩如繁星。其中最知名的基地系列(The... 閱讀更多
書評》歷史科幻物語,那不曾存在又似乎具體存在的80年代:評賽門.史塔倫哈格「迴環記憶三部曲」
閱讀更多
漫射計畫》過去的未來就是現在:屬於台灣的科幻漫畫,常勝與鐵柱對談
漫畫是載體、是傳播媒介,也屬於時代的光,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國家漫畫博物館籌備小隊接收了一批臺灣漫畫,每雙月發行《漫射報》專刊,邀請不同專家一起閱讀館藏,...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