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行列車》整體讓我相當振奮與喜歡——有些讓我覺得張口結舌的好,我試說明如下。
有部我在電視台上看得沒頭沒尾的義大利片,其中一段是這樣:父親照顧殘疾的小兒子心力交瘁,預備或真的自殺。兒子不解,問道,你為什麼憂鬱,你還有我啊!——在我看來,小說家利文曄沿路尋回的,就是這種令理性或知性啞口無言的「誤會寫實」片刻——書寫,在於能夠「誤會」既存秩序與輕重緩急,換句話說,就是「誤會權力」。而妙的是,權力一旦被誤會,它就無法一如預謀的施展手腳。
➤半本死亡之書,重訪悼亡記憶
〈失語〉短,短到幾乎會以為沒結構——但跳接是「另類結構」——從貓頭鷹的生命白,掩飾暴行(對狗)的布簾白,街頭藝人的無差別白,到了「我想起一個朋友」的「慶仔」。如果要寫慶仔,內容未免單薄——不單薄,因為不是真寫慶仔。
慶仔段落是唯一沒點出白色的,但白很醒目。小混混紗布泛出血跡,紗布絕對是白的。關於失語,只寥寥數句。然而,最後的「家將白」翻出三個逆高潮——現身、認出(因為不可能而更加強烈)、止步,重組了小說。原來它既非「動保懷友」也非「憶兒時」。我把收束三疊讀作矛盾祈願:請你復活!請你死去!
這使慶仔類似「祖宗神」,慶仔的「台語身」也才有了更廣闊邈遠的無意識表徵。事實上,被與英語平起的台語,在小說的作用同於「屌」(樣)。從屌的效益(氣哭老師)、無傷(露鬼臉)到後來不斷消亡,合併了前面白色漸層,勾勒出對「台語身」又愛又怕的感情沈積,別具風格。
〈失語〉是全書少數不領屍身的。〈地震〉中,主角已然加入「一同怕死的生之慶典」。人稱牡丹的女性作為主角的〈圓柱體〉(諧音「援助體」)、〈魔法師〉以及〈香水〉,這5篇的基調較為不同,焦點較集中(後面合稱五焦)。其他7篇,即使我會將它們歸於「珠灰大漫步系列」,它們仍並非只互相重覆,而更似「卡農輪唱」,儘管「死得好看」這類描述,頻率就異常地高——《日行列車》可說是「半本死亡之書」。
我對民俗了解有限,但根據我淺陋的心得,小說裡的細節,都較一般民俗知識更為深入。可確定的是,作者與「對悼亡仍保有深情的族群或世代」,尙不疏離——儘管作者未必意識其是文化底蘊,但我以為,在更具專門的研究者手中,或將發掘更多意涵。
➤自主服喪:邊緣中心化與在前觀念處書寫
如果習俗是「文化服喪」的印記,《日行列車》更大的探索,是與「文化服喪」交互作用的「自主服喪」。〈妖怪村〉裡,8歲兒子的「認字」癡狂與母親的「擦字」儀式,都寫得令人萬分動容,尤以母親的「頂替不辯」,可說是寫到了語言所難以抵達之處。
人之喪命可源於猥褻噴字這類輕浮,足見生命多麼脆弱,而牽掛又是多麼濃烈。〈雨神〉裡的舅公令我想到阿爾欽博托以蔬果繪製的「隱藏的臉」,在超越視覺上,並非經由取消,而是引入「更肉體的肉體」。
無論舅公的外表或心智,一旦被標籤,都不會好聽,在小說裡,舅公與各式人物卻給人渾然天成的感覺。即便是「與雨執拗」的「荒誕」,作者寫起來都無一分「怪氣」——在曾被讚「最溫柔」的〈老菸〉,應不只是「溫柔」,還能「使溫柔」。詩歌裡有「憫」的傳統,《日行列車》應很容易被指為「憫派」,但小說最好的部分,都不只是道德或感情的在場。
電影史在論戰「邊緣/中心」時,有過一個論點:如果邊緣不能成為中心,邊緣/中心就等於「把邊緣再邊緣化」。因此,能在邊緣「坐地為中心」而解中心,更值借鏡。這也是《日行列車》的倫理敏感度。
〈日行列車〉一篇並非簡單二元對立的反啟蒙(啟蒙原詞即為「光」),儘管它與〈鎖〉同樣會提供反啟蒙豐富的話語資源。但兩者之所以有後勁,還因為利文曄把握了寫出「前觀念」的獨到技巧。如此不但擺脫了觀念的暴力與限制,還去到更模糊更禁忌之處。
久病的父親算哪一種男性?主角在CPR安妮的課堂上很投入,表現良好。父癱並沒有造成他的社會或生理退避,但病父的性與性別存在,確實構成混沌性。安妮成為同學猥褻的對象,明顯因為她被當作女性,但是不是也因為她是病人呢?跳接數事後,主角回去就問母親問題,母親答以父親病因,可此處主角的困惑,當然與性有關。
➤要屌不屌:無題性慾如無產階級
陰性化男性的成長組構,並不是粉紅通行就完結。在所有作品中,我注意到一個,我會稱為「要屌不屌」的隱伏線。理論上,陰莖當然可以不為父權共犯,可具體會發生什麼?將生殖力與豐收綁起來想像的,農業時代的陽具崇拜,與當前「成就取向人格與壯陽性」糾纏的型態,應該已有不同。像「草食男」的稱謂,不也暗示某單一「性表現」更合規格?可是利比多的內在多樣差異,應該原本就存在。
我前稱的「五焦」,有篇直接讓「性的主流預設前提」與「無題性別」 交錯,就「性預設出問題是問題」而言,寫得相當出色。但〈日行列車〉除了類似元素出場,還有均衡的好處。它讓我想到許多不用透視法的畫作,類似的「無題性慾」以「驚鴻一瞥」的方式浮現(列車上與沙發上)。
母親論及「發紅蛋」一段,或會被誤為「懲戒蕩婦」的言說,但這說不通她的哭泣。我以為,這段更適宜看作和所有與「無(或少)性階級者」(借用「無產階級者」)的同在有關——除非是宗教人,就像崇尚名牌般,社會也存在崇尚特定奢性(慾)。
在這脈絡中,〈圓柱體〉裡的牡丹,本身也更接近「無性階級」,她的「援助」包括了幫不想性交的少男騙同儕,此更似「弱弱相憐」而非風月。五焦都具較明顯的記憶點與手法,但「珠灰大漫步系列」發展了不少「插曲」即「正曲」的寫法,讀者如能留意,會發現許多別有洞天處。
「無賴派」的名言說:墮落到底才是人。閱讀《日行列車》,屢屢讓我心生「成為弱者才是人」之感。弱者就能穿牆而過,這就是文學。無論這堵牆是生死、貧富、語言或性別——文學即是在此護持了它本身——最隱密與不可侵犯的尊嚴與意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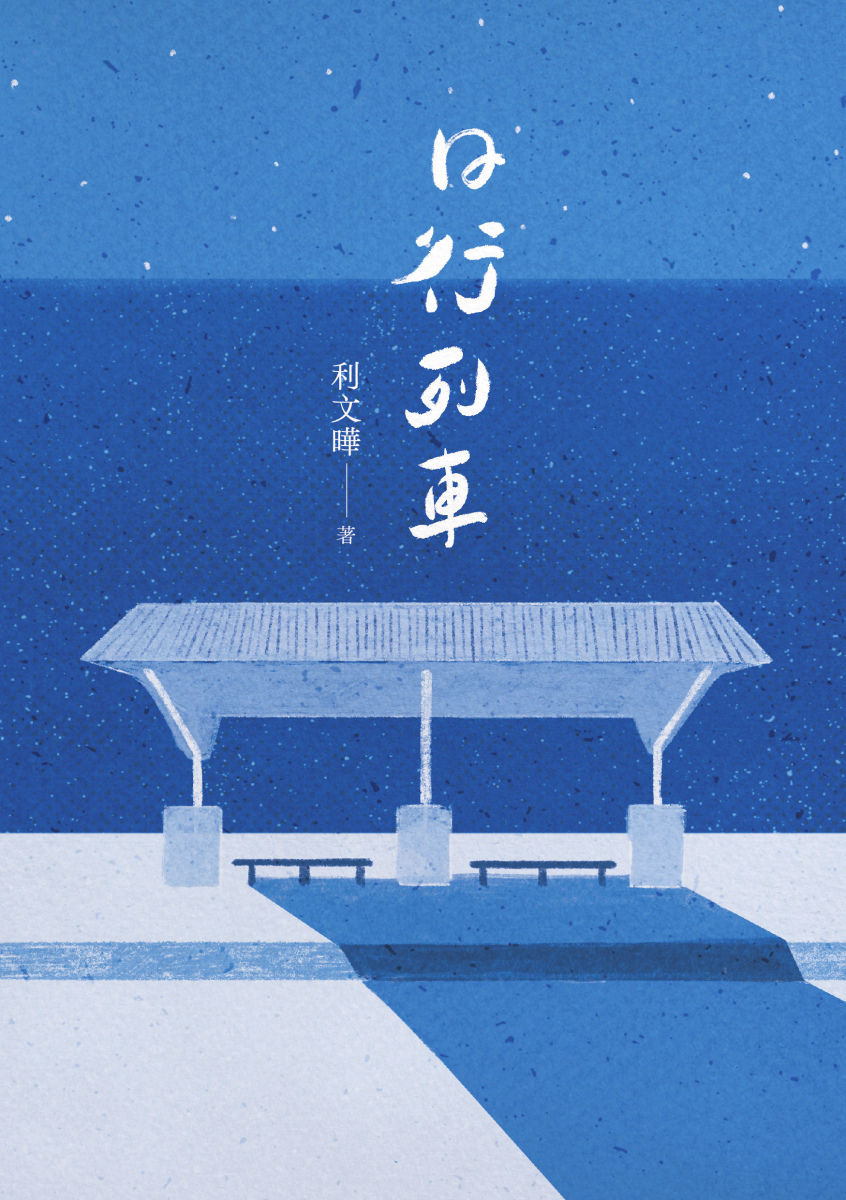 日行列車 日行列車
作者:利文曄
出版:九歌出版
定價:350元
【內容簡介➤】
|
|
作者簡介:利文曄
1994年生,高雄楠仔坑人,雄中/成大法律系/台文所畢業,現任職於科技業。曾獲國藝會補助、印刻超新星文學獎、成大鳳凰樹文學獎等。
喜歡閒晃,於是繞一大圈到了這裡,還不知道要往哪裡去。
|
Tags:
(底圖圖源:wikipedia)
《日行列車》透過十二篇短篇小說,
本書將於4/29上市,Openbook閱讀誌獨家優先刊登作家張亦絢為《日行列車》所寫之推薦序,以饗讀者。
《日行列車》整體讓我相當振奮與喜歡——有些讓我覺得張口結舌的好,我試說明如下。
有部我在電視台上看得沒頭沒尾的義大利片,其中一段是這樣:父親照顧殘疾的小兒子心力交瘁,預備或真的自殺。兒子不解,問道,你為什麼憂鬱,你還有我啊!——在我看來,小說家利文曄沿路尋回的,就是這種令理性或知性啞口無言的「誤會寫實」片刻——書寫,在於能夠「誤會」既存秩序與輕重緩急,換句話說,就是「誤會權力」。而妙的是,權力一旦被誤會,它就無法一如預謀的施展手腳。
➤半本死亡之書,重訪悼亡記憶
〈失語〉短,短到幾乎會以為沒結構——但跳接是「另類結構」——從貓頭鷹的生命白,掩飾暴行(對狗)的布簾白,街頭藝人的無差別白,到了「我想起一個朋友」的「慶仔」。如果要寫慶仔,內容未免單薄——不單薄,因為不是真寫慶仔。
慶仔段落是唯一沒點出白色的,但白很醒目。小混混紗布泛出血跡,紗布絕對是白的。關於失語,只寥寥數句。然而,最後的「家將白」翻出三個逆高潮——現身、認出(因為不可能而更加強烈)、止步,重組了小說。原來它既非「動保懷友」也非「憶兒時」。我把收束三疊讀作矛盾祈願:請你復活!請你死去!
這使慶仔類似「祖宗神」,慶仔的「台語身」也才有了更廣闊邈遠的無意識表徵。事實上,被與英語平起的台語,在小說的作用同於「屌」(樣)。從屌的效益(氣哭老師)、無傷(露鬼臉)到後來不斷消亡,合併了前面白色漸層,勾勒出對「台語身」又愛又怕的感情沈積,別具風格。
〈失語〉是全書少數不領屍身的。〈地震〉中,主角已然加入「一同怕死的生之慶典」。人稱牡丹的女性作為主角的〈圓柱體〉(諧音「援助體」)、〈魔法師〉以及〈香水〉,這5篇的基調較為不同,焦點較集中(後面合稱五焦)。其他7篇,即使我會將它們歸於「珠灰大漫步系列」,它們仍並非只互相重覆,而更似「卡農輪唱」,儘管「死得好看」這類描述,頻率就異常地高——《日行列車》可說是「半本死亡之書」。
我對民俗了解有限,但根據我淺陋的心得,小說裡的細節,都較一般民俗知識更為深入。可確定的是,作者與「對悼亡仍保有深情的族群或世代」,尙不疏離——儘管作者未必意識其是文化底蘊,但我以為,在更具專門的研究者手中,或將發掘更多意涵。
➤自主服喪:邊緣中心化與在前觀念處書寫
如果習俗是「文化服喪」的印記,《日行列車》更大的探索,是與「文化服喪」交互作用的「自主服喪」。〈妖怪村〉裡,8歲兒子的「認字」癡狂與母親的「擦字」儀式,都寫得令人萬分動容,尤以母親的「頂替不辯」,可說是寫到了語言所難以抵達之處。
人之喪命可源於猥褻噴字這類輕浮,足見生命多麼脆弱,而牽掛又是多麼濃烈。〈雨神〉裡的舅公令我想到阿爾欽博托以蔬果繪製的「隱藏的臉」,在超越視覺上,並非經由取消,而是引入「更肉體的肉體」。
無論舅公的外表或心智,一旦被標籤,都不會好聽,在小說裡,舅公與各式人物卻給人渾然天成的感覺。即便是「與雨執拗」的「荒誕」,作者寫起來都無一分「怪氣」——在曾被讚「最溫柔」的〈老菸〉,應不只是「溫柔」,還能「使溫柔」。詩歌裡有「憫」的傳統,《日行列車》應很容易被指為「憫派」,但小說最好的部分,都不只是道德或感情的在場。
電影史在論戰「邊緣/中心」時,有過一個論點:如果邊緣不能成為中心,邊緣/中心就等於「把邊緣再邊緣化」。因此,能在邊緣「坐地為中心」而解中心,更值借鏡。這也是《日行列車》的倫理敏感度。
〈日行列車〉一篇並非簡單二元對立的反啟蒙(啟蒙原詞即為「光」),儘管它與〈鎖〉同樣會提供反啟蒙豐富的話語資源。但兩者之所以有後勁,還因為利文曄把握了寫出「前觀念」的獨到技巧。如此不但擺脫了觀念的暴力與限制,還去到更模糊更禁忌之處。
久病的父親算哪一種男性?主角在CPR安妮的課堂上很投入,表現良好。父癱並沒有造成他的社會或生理退避,但病父的性與性別存在,確實構成混沌性。安妮成為同學猥褻的對象,明顯因為她被當作女性,但是不是也因為她是病人呢?跳接數事後,主角回去就問母親問題,母親答以父親病因,可此處主角的困惑,當然與性有關。
➤要屌不屌:無題性慾如無產階級
陰性化男性的成長組構,並不是粉紅通行就完結。在所有作品中,我注意到一個,我會稱為「要屌不屌」的隱伏線。理論上,陰莖當然可以不為父權共犯,可具體會發生什麼?將生殖力與豐收綁起來想像的,農業時代的陽具崇拜,與當前「成就取向人格與壯陽性」糾纏的型態,應該已有不同。像「草食男」的稱謂,不也暗示某單一「性表現」更合規格?可是利比多的內在多樣差異,應該原本就存在。
我前稱的「五焦」,有篇直接讓「性的主流預設前提」與「無題性別」 交錯,就「性預設出問題是問題」而言,寫得相當出色。但〈日行列車〉除了類似元素出場,還有均衡的好處。它讓我想到許多不用透視法的畫作,類似的「無題性慾」以「驚鴻一瞥」的方式浮現(列車上與沙發上)。
母親論及「發紅蛋」一段,或會被誤為「懲戒蕩婦」的言說,但這說不通她的哭泣。我以為,這段更適宜看作和所有與「無(或少)性階級者」(借用「無產階級者」)的同在有關——除非是宗教人,就像崇尚名牌般,社會也存在崇尚特定奢性(慾)。
在這脈絡中,〈圓柱體〉裡的牡丹,本身也更接近「無性階級」,她的「援助」包括了幫不想性交的少男騙同儕,此更似「弱弱相憐」而非風月。五焦都具較明顯的記憶點與手法,但「珠灰大漫步系列」發展了不少「插曲」即「正曲」的寫法,讀者如能留意,會發現許多別有洞天處。
「無賴派」的名言說:墮落到底才是人。閱讀《日行列車》,屢屢讓我心生「成為弱者才是人」之感。弱者就能穿牆而過,這就是文學。無論這堵牆是生死、貧富、語言或性別——文學即是在此護持了它本身——最隱密與不可侵犯的尊嚴與意義。●
作者:利文曄
出版:九歌出版
定價:35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利文曄
1994年生,高雄楠仔坑人,雄中/成大法律系/台文所畢業,現任職於科技業。曾獲國藝會補助、印刻超新星文學獎、成大鳳凰樹文學獎等。
喜歡閒晃,於是繞一大圈到了這裡,還不知道要往哪裡去。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
閱讀通信 vol.371》我有故事,你有真心嗎?
延伸閱讀
書評》還沒愛夠阿嘉莎:評《阿嘉莎.克莉絲蒂:謀殺天后與她的未解之謎》
閱讀更多
書評》用上最頂的技藝,只為與爛梗擦身而過:讀王仁劭《而獨角獸倒立在歧路》
閱讀更多
書評》天才物種的生態觀察紀錄:評寺尾哲也《子彈是餘生》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