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集是這次決選作品中,數量最多且引起較少爭議的。除有一本詩集引起現場詩人評審立即與強烈的對立之外,在競爭激烈的情況下,選擇的標準似乎自動從選出好詩集,自然調整為開創性足夠與否。也許是在這種情勢中,3本獲獎的詩集在會議中,評審的發言大半集中在肯定詩集深化的不同面向,而甚少得到負評。其中王天寬的《開房間》,另外得到深研劇場史的評審,從劇場的角度予以詮釋,令人感覺有如驚喜加映。
▉知性能有幾多種?
如果說,每次評審會議都有一個關鍵字,今年的關鍵字應該就是對散文討論而出現的「知性」一詞。不知道是否受到近年來,社會與學校對思辨力的探討影響,儘管「思辨力」三字從未出現在評審現場,這與「知性」之所以出現的原因,是一致的嗎?我不敢下斷語。但從被反覆以不同方式重新詮釋「知性」ㄧ詞的過程中,的確開啟值得進一步思索的現象。
無庸贅言,「知性」在評審口中,並非一般概念中的「軟性」,當然也不會只是某種姿態,而應該具有某種可檢驗的實質。智性或知性,本就不與文學分離,這並非全無前例的觀點。諾貝爾文學獎曾頒發給柏格森的哲學書寫,或許就可以說,正是這種意識強烈的表現。
然而,在文學獎項評判上以這個標準思考,卻難免某些困境。這在檢視散文與非虛構書寫作品的過程中,尤其明顯。第一個原因是,當我們將作品中的知識密度或嚴謹程度,與各學科的專門著作相比,若干散文作品原始企圖可能僅止於隨性發揮或「誨人不倦」,又令人感到某種不上不下的尷尬。在討論非虛構作品時,有評審以半認真半開玩笑的方式問道,難道我們竟是以討論一篇論文的標準在檢視這些作品嗎?然而,若是作品的層次或處理不若一篇論文,我想,這也是有點奇怪的。
 如果是以傾向與嘗試而言,非虛構書寫可以說是確為決審作品帶來一番新氣象,也是令人振奮的新局。然而,若是從作品的完整性或周密程度而言,獲獎的作品,在評審過程中,也並非受到毫無保留的支持。與大眾想像的可能略有出入,這些作品被討論時,難以迅速得到評審的肯定共識,只有很少的成份,是基於它們不是如小說散文等類別,是「正統」的文學。而是當它們被與其本身的書寫傳統相比之時,仍不夠成熟或完美。
如果是以傾向與嘗試而言,非虛構書寫可以說是確為決審作品帶來一番新氣象,也是令人振奮的新局。然而,若是從作品的完整性或周密程度而言,獲獎的作品,在評審過程中,也並非受到毫無保留的支持。與大眾想像的可能略有出入,這些作品被討論時,難以迅速得到評審的肯定共識,只有很少的成份,是基於它們不是如小說散文等類別,是「正統」的文學。而是當它們被與其本身的書寫傳統相比之時,仍不夠成熟或完美。
儘管認為「知識雖好,但非文學正途」的意見並非全然缺席,但那往往並非決斷性的評判之語,而較近於有待討論的感受——整體而言,在對非虛構書寫的討論中,較具決定性因素的,是對書中某些細節或若干手法,是否太過輕率或可更周延的反覆檢驗——這是否表示,我們用更苛刻的方式看待非虛構書寫?我想並不是。即使是我以「瑕不掩瑜」的「環境記憶政治」角度,一度為其辯護的《煙囪之島》,我也確實認為,儘管達成高難度與意義深遠的貢獻,從作為書寫範例的角度而言,還是有完善的空間。——雖然那也是極小的空間。在討論過程中,另有評審表示,其成績可說遠超過想像。雖然不能說這本著作的成就是有目共睹,但仍多少表示其價值匪薄。
延伸來說,我偏向相信,是因爲對知識與文學性兩者都「愛之深,責之切」,才無法簡單達成共識。在阻擋反智進球的守門員一事上,文學確實該有其角色,但知性很難單獨成行,隨之而來必有嚴謹度等標準。對於非虛構書寫,似乎也不應只有報導文學的傳統典範作為參考。曾經在其他文學獎中,出現過的評論獎以及論述的美學,是否在文類更加開放後,也會成為思考的方向,這很可能是未來的課題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明顯具有知性優點的《天亮之前的戀愛:日治時期台灣小說風景》,倒是因爲其史識與文采很快受到普遍肯定,而完全未進入上述針對散文與非虛構小說,關於知性判準的斟酌。此略同夏曼 · 藍波安的《大海之眼》,尖銳的言詞或者帶抗議性的表達,評審並無負評,反而有意見指出,此可破解社會強求弱勢者溫良的偏頗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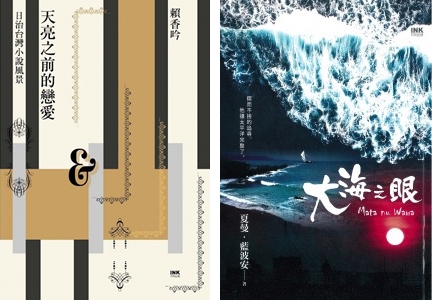
▉小說是否拉警報?
最後,只有4本小說作品進入決選,如果說是「小說拉警報」可能略略誇張。畢竟,張貴興的長篇小說《野豬渡河》幾無負評地掄得首獎。在評審過程中,更是只有閱讀角度的不同,但結論ㄧ律爲盛讚,另一本得到佳評如潮對待的作品,則是極爲年輕的小說家洪明道的首本短篇小說集《等路》。此書主要的使用文字雖是台語,但也深受台語非母語的評審青睞。這一方面顯示,文學已可以是保存母語的好夥伴:另方面,也讓我們感到「台語共讀」的氣氛,也到了令人更可親可感的階段了。
儘管如此,對照近年重要文學獎的得獎作以及小說書寫風氣,仍有必要指出,年輕一代小說創作力的強韌多元,與金典獎入選作品似乎出現了微妙,也值得注意的斷裂,這個斷裂很可能要追溯到出版環境——因爲金典獎是以出版品為評審與授獎的對象,已經創作出受到肯定作品的小說作者,若未將作品集結成書,自不可能列入觀察與獎勵之列。

若是有一批小說作者正處於集結成書的籌備期,那我們確實可視此沉潛期爲種子破土之前的寧靜。不過,若是在上述自然起伏的現象外,也存在其他現實的因素,那就值得嚴肅面對。若干年輕的小說者,曾詢問若本身不屬有經營社群意願的寫作者,是否在與出版社的初步接觸時就會有困難?認爲出版社尋求「自帶客群」的作者,這種焦慮在年輕作者群中似乎日漸普遍。
固然,文學界過去一直是孤僻者與外向者可以各分天下,但網路世代導致對曝光性更強的需求,是否壓抑了若干「作者成爲出書作者」的意願與可能性?我們不能斷言,自媒體趨勢與出版界對此的依賴,一定傷害了文學小說的出版,但若是「有創作,無出版」的現象,比我觀察到的更嚴重,那就代表可能需要尋求更積極的研究與改善。此次金典獎得獎作者中,即有兩位爲第一次出版作品的作者(也因此同獲蓓蕾獎),顯見新血確為文學生力軍。目前重翻譯輕自製的台灣出版風氣,是否對小說出版的負面影響更勝於其他文類?也值得注意。
另外兩本進入決選惜未獲獎的小說是洪茲盈的《墟行者》與林美冬的《流螢》。前者得到的支持不多但很強烈,正反意見都經表達;後者雖因未獲票數而未有深入討論,但在討論其他作品時,因為是以原住民族居地爲故事發生地的小說,也被比併提及。
這兩部作品都呈現了不完全是純文學小說的型態與觸角,也發展了純文學小說未必置於優位的能力:分別是科幻的想像與「環境謎題」——雖然後者未必很清楚是想成爲ㄧ部懸疑推理作,但謎的設計與解開,都有一定水準,頗見用心。螢火蟲的主題,扣緊不同意象,結尾也富哲理,指出了「架空生態概念未容當地知識」的毀滅性。兩本都挑戰了小說的邊緣地帶,儘管我本身更傾向不偏重情節的小說,但文學環境應當均衡,兩位擁有以「全面構思情節完成小說」誠意的作者,也值得我們以珍惜之心細讀。

作家顧德莎(攝影:王志元)
決選作品中,五年級世代以上的男女性別比,粗略估算約為九比二,其中包括甫過世的顧德莎。其作《說吧,記憶》,因在病重之中執筆,未能使全書的文學表現趨於ㄧ致,但其為台灣受薪階級女性以及早熟卻晚成的女性書寫者,留下珍貴證言,在評審之中,並非未有知音。文學不只是和自己賽跑,也是和病魔與死神賽跑。最後謹以短語感念所有未及完全開花的作者:他們也是春泥,我們總不忘記。 ●
Tags:
詩集是這次決選作品中,數量最多且引起較少爭議的。除有一本詩集引起現場詩人評審立即與強烈的對立之外,在競爭激烈的情況下,選擇的標準似乎自動從選出好詩集,自然調整為開創性足夠與否。也許是在這種情勢中,3本獲獎的詩集在會議中,評審的發言大半集中在肯定詩集深化的不同面向,而甚少得到負評。其中王天寬的《開房間》,另外得到深研劇場史的評審,從劇場的角度予以詮釋,令人感覺有如驚喜加映。
▉知性能有幾多種?
如果說,每次評審會議都有一個關鍵字,今年的關鍵字應該就是對散文討論而出現的「知性」一詞。不知道是否受到近年來,社會與學校對思辨力的探討影響,儘管「思辨力」三字從未出現在評審現場,這與「知性」之所以出現的原因,是一致的嗎?我不敢下斷語。但從被反覆以不同方式重新詮釋「知性」ㄧ詞的過程中,的確開啟值得進一步思索的現象。
無庸贅言,「知性」在評審口中,並非一般概念中的「軟性」,當然也不會只是某種姿態,而應該具有某種可檢驗的實質。智性或知性,本就不與文學分離,這並非全無前例的觀點。諾貝爾文學獎曾頒發給柏格森的哲學書寫,或許就可以說,正是這種意識強烈的表現。
然而,在文學獎項評判上以這個標準思考,卻難免某些困境。這在檢視散文與非虛構書寫作品的過程中,尤其明顯。第一個原因是,當我們將作品中的知識密度或嚴謹程度,與各學科的專門著作相比,若干散文作品原始企圖可能僅止於隨性發揮或「誨人不倦」,又令人感到某種不上不下的尷尬。在討論非虛構作品時,有評審以半認真半開玩笑的方式問道,難道我們竟是以討論一篇論文的標準在檢視這些作品嗎?然而,若是作品的層次或處理不若一篇論文,我想,這也是有點奇怪的。
儘管認為「知識雖好,但非文學正途」的意見並非全然缺席,但那往往並非決斷性的評判之語,而較近於有待討論的感受——整體而言,在對非虛構書寫的討論中,較具決定性因素的,是對書中某些細節或若干手法,是否太過輕率或可更周延的反覆檢驗——這是否表示,我們用更苛刻的方式看待非虛構書寫?我想並不是。即使是我以「瑕不掩瑜」的「環境記憶政治」角度,一度為其辯護的《煙囪之島》,我也確實認為,儘管達成高難度與意義深遠的貢獻,從作為書寫範例的角度而言,還是有完善的空間。——雖然那也是極小的空間。在討論過程中,另有評審表示,其成績可說遠超過想像。雖然不能說這本著作的成就是有目共睹,但仍多少表示其價值匪薄。
延伸來說,我偏向相信,是因爲對知識與文學性兩者都「愛之深,責之切」,才無法簡單達成共識。在阻擋反智進球的守門員一事上,文學確實該有其角色,但知性很難單獨成行,隨之而來必有嚴謹度等標準。對於非虛構書寫,似乎也不應只有報導文學的傳統典範作為參考。曾經在其他文學獎中,出現過的評論獎以及論述的美學,是否在文類更加開放後,也會成為思考的方向,這很可能是未來的課題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明顯具有知性優點的《天亮之前的戀愛:日治時期台灣小說風景》,倒是因爲其史識與文采很快受到普遍肯定,而完全未進入上述針對散文與非虛構小說,關於知性判準的斟酌。此略同夏曼 · 藍波安的《大海之眼》,尖銳的言詞或者帶抗議性的表達,評審並無負評,反而有意見指出,此可破解社會強求弱勢者溫良的偏頗態度。
▉小說是否拉警報?
最後,只有4本小說作品進入決選,如果說是「小說拉警報」可能略略誇張。畢竟,張貴興的長篇小說《野豬渡河》幾無負評地掄得首獎。在評審過程中,更是只有閱讀角度的不同,但結論ㄧ律爲盛讚,另一本得到佳評如潮對待的作品,則是極爲年輕的小說家洪明道的首本短篇小說集《等路》。此書主要的使用文字雖是台語,但也深受台語非母語的評審青睞。這一方面顯示,文學已可以是保存母語的好夥伴:另方面,也讓我們感到「台語共讀」的氣氛,也到了令人更可親可感的階段了。
儘管如此,對照近年重要文學獎的得獎作以及小說書寫風氣,仍有必要指出,年輕一代小說創作力的強韌多元,與金典獎入選作品似乎出現了微妙,也值得注意的斷裂,這個斷裂很可能要追溯到出版環境——因爲金典獎是以出版品為評審與授獎的對象,已經創作出受到肯定作品的小說作者,若未將作品集結成書,自不可能列入觀察與獎勵之列。
若是有一批小說作者正處於集結成書的籌備期,那我們確實可視此沉潛期爲種子破土之前的寧靜。不過,若是在上述自然起伏的現象外,也存在其他現實的因素,那就值得嚴肅面對。若干年輕的小說者,曾詢問若本身不屬有經營社群意願的寫作者,是否在與出版社的初步接觸時就會有困難?認爲出版社尋求「自帶客群」的作者,這種焦慮在年輕作者群中似乎日漸普遍。
固然,文學界過去一直是孤僻者與外向者可以各分天下,但網路世代導致對曝光性更強的需求,是否壓抑了若干「作者成爲出書作者」的意願與可能性?我們不能斷言,自媒體趨勢與出版界對此的依賴,一定傷害了文學小說的出版,但若是「有創作,無出版」的現象,比我觀察到的更嚴重,那就代表可能需要尋求更積極的研究與改善。此次金典獎得獎作者中,即有兩位爲第一次出版作品的作者(也因此同獲蓓蕾獎),顯見新血確為文學生力軍。目前重翻譯輕自製的台灣出版風氣,是否對小說出版的負面影響更勝於其他文類?也值得注意。
另外兩本進入決選惜未獲獎的小說是洪茲盈的《墟行者》與林美冬的《流螢》。前者得到的支持不多但很強烈,正反意見都經表達;後者雖因未獲票數而未有深入討論,但在討論其他作品時,因為是以原住民族居地爲故事發生地的小說,也被比併提及。
這兩部作品都呈現了不完全是純文學小說的型態與觸角,也發展了純文學小說未必置於優位的能力:分別是科幻的想像與「環境謎題」——雖然後者未必很清楚是想成爲ㄧ部懸疑推理作,但謎的設計與解開,都有一定水準,頗見用心。螢火蟲的主題,扣緊不同意象,結尾也富哲理,指出了「架空生態概念未容當地知識」的毀滅性。兩本都挑戰了小說的邊緣地帶,儘管我本身更傾向不偏重情節的小說,但文學環境應當均衡,兩位擁有以「全面構思情節完成小說」誠意的作者,也值得我們以珍惜之心細讀。
決選作品中,五年級世代以上的男女性別比,粗略估算約為九比二,其中包括甫過世的顧德莎。其作《說吧,記憶》,因在病重之中執筆,未能使全書的文學表現趨於ㄧ致,但其為台灣受薪階級女性以及早熟卻晚成的女性書寫者,留下珍貴證言,在評審之中,並非未有知音。文學不只是和自己賽跑,也是和病魔與死神賽跑。最後謹以短語感念所有未及完全開花的作者:他們也是春泥,我們總不忘記。 ●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
【2019臺灣文學金典獎】系列報導
閱讀通信 vol.372》蹲點是I人用的,社交恐怖分子請用「佔點」
延伸閱讀
2019臺灣文學金典獎.得獎評語》張貴興獲年度大獎,洪明道、王天寬、曹馭博獲蓓蕾獎
閱讀更多
2019臺灣文學金典獎.決審觀察》須文蔚:禮讚台灣文學創作的經典作品
閱讀更多
2019臺灣文學金典獎.決審觀察》石曉楓:文學邊界的想像與挑戰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