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米奇.艾爾邦(左,Jenny Risher攝)與大塊文化董事長郝明義(大塊提供)進行對談
郝明義(以下簡稱「郝」):看你這麼多年寫的書,有些始終貫穿的主題,譬如生死;另外,也有些前後很有意思的對應,譬如最新這本《遇見奇卡》,就是你在設法保護一個6、7歲小女孩生命的故事。17年前出版的《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故事的起始也是因為一個人要去救一名8歲小女孩的命。你覺得這其中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艾爾邦:2003年出版《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的時候,我沒有小孩。當時只是在寫故事的時候設定了一個概念:照顧孩子,是生命的重要意義。那本書的主角艾迪是個原來生命沒有意義的人,但是當他在緊要關頭拯救了8歲的小女孩時,他的生命就出現了意義。當年,我當然沒有預料到我自己會有類似的遭遇。這是頭一次有人問我這個問題,很有趣。
艾爾邦:2003年出版《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的時候,我沒有小孩。當時只是在寫故事的時候設定了一個概念:照顧孩子,是生命的重要意義。那本書的主角艾迪是個原來生命沒有意義的人,但是當他在緊要關頭拯救了8歲的小女孩時,他的生命就出現了意義。當年,我當然沒有預料到我自己會有類似的遭遇。這是頭一次有人問我這個問題,很有趣。
如果我沒有在海地經營那所孤兒院,就不會有機會救到一些孩子。有幾個孩子曾患重病,我們送去醫院救了回來,醫生說很不可思議。而奇卡,你知道,她得的是罕見癌症DIPG,我並沒能救回來。不過如果留在海地,她只能活3、4個月,我把她帶回來,我們又相處了兩年時光。這麼說,我和艾迪是有些相似之處。
但我今天比當時更確信的是:在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照顧孩子。如果你能救一個孩子的命,那不是救了她的將來,也可能是世界的未來。因為等那個孩子長大,她可能做的事很多。
郝:你的前一本書《在天堂裡遇見的下一個人》,一方面故事是接續《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講那個逃過一刧的小女孩後來的故事,另一方面書前也特別獻詞給奇卡,這本書的創作是否和奇卡有關?
艾爾邦:奇卡一死,我就想馬上寫一本她的書。但是美國的出版社不建議,說我應該讓時間沉澱一下再動筆。於是我先寫了《在天堂裡遇見的下一個人》,把對奇卡的許多感情都放進那本書。書裡有個女人,她在天堂裡抱到自己失去的孩子,但才那麼幾秒鐘的時間,孩子又不見了,她一下子大哭起來。我覺得那其實是在寫我自己。得到孩子,轉眼又失去,真是掏心裂肺。
我一直等到一年半之後,覺得自己比較有了出版社所說的沉澱後的角度,才真正動筆寫奇卡。其實如果當時我就動筆,那會是一本完全不同的書。也許會比較不好,也許會更好,不知道。
但不管怎麼說,現在我完成了《遇見奇卡》,我很滿意這本書,覺得是我所有書裡最棒的一本。當然《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極為成功,但當時我還沒有自己觀察生命的角度,書裡的角度主要是墨瑞的,是他的想法,我自己的很少。
但是在《遇見奇卡》,我寫的是我從一個孩子身上體會到的看待生命的角度,無與倫比。雖然奇卡年紀很小,但她教了我很多。希望台灣的讀者也會喜歡這本書。
郝:啊,那難怪。我在讀《尋找奇卡》的時候,有感覺到你的平靜。我隱約覺得寫這樣的故事,你的情緒應該會更洶湧一些,原來你激動的情緒已先有了紓發的管道。
艾爾邦:是的,也許我的憤恨、沮喪都經由先前的那本書渲洩很多了。在美國出版界,大家都說:不要寫一本講孩子死去、太感傷的書,沒有人想看。我知道要寫也不能寫一本只是讓人肝腸寸斷的書,必須更深入。

米奇.艾爾邦與奇卡(取自Mitch Albom官網)
所以我在書的第一頁就先告訴讀者她死了,你不用看了一百多頁才發現這件事。不過你也會知道:她雖然死了,但會再回來和我說話。此外為了不讓讀者覺得恐怖,我從第一頁開始就用幽默的筆觸來寫。
所以,聽你說我顯得很平靜,我很高興,那是我希望的。奇卡剛走的那一年半裡,我的狀況一塌糊塗。現在我平靜下來寫,希望讀者知道這雖然是寫一個孩子死去的書,但不是要你肝腸寸斷。
郝:奇卡會回來和你說話?她過世後真的曾經現身嗎?
艾爾邦:不是,也是。我現在坐的這裡是我的工作室,每天早上我起得早,奇卡在世時也都起得很早。我太太還在睡覺,所以我下來這裡,做早餐,然後坐到電腦前,奇卡就坐在我右手邊的地板上。我說我要開始寫東西了,妳不要出聲,奇卡說好。然後不到10秒鐘,她就又開始說話了。你知道,她就是愛說話。
兩年裡,我們大半情況都是如此。所以奇卡死後,我每天下來,一坐到椅子上,閉上眼睛,就能浮現她在我身邊的影像,也會出現許多對話。那到底是真有其事,還是我想像出來的?我也不知道。
書裡的許多對話,有些是我們曾經確實交談過的,有些是我坐在這裡想像的,但覺得她就坐在我身邊。我不會說那是我和鬼魂的對話,但也真的是我和她的對話。我閉著眼睛說一句,好像她也回一句。畢竟,我們在這個地方曾經交換過那麼多有趣的對話。
郝:你曾在書裡說過:「每一個家庭都是一個鬼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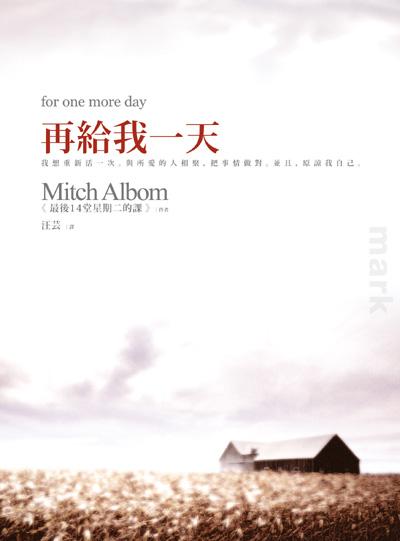 艾爾邦:你的記憶力真好。那是在《再給我一天》書裡。沒錯,現在我家也是,奇卡走了。
艾爾邦:你的記憶力真好。那是在《再給我一天》書裡。沒錯,現在我家也是,奇卡走了。
郝:前面提到的呼應還有個例子。你在《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裡還寫過一句話:「一個陌生人,造就一個家庭。」你收養奇卡,真的是讓你的家庭完整了。
艾爾邦:我的孤兒院有52個孩子,奇卡是其中之一。現在我們孤兒院有兩個孩子來美國讀大學,未來其他孩子也都會來讀。等他們讀完大學,就可以回海地,為他們國家貢獻心力。所以我的責任是要活得久一點,讓更多孩子有機會來美國接受大學教育。
郝:先為你鼓鼓掌。然後,你在《再給我一天》裡寫到:「一個孩子只能不是他父親,就是他母親的孩子。」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話,請你再多說一些。
艾爾邦:那是說孩子在成長過程裡,在父母之間難免有一邊是他更倚賴些,更親近些,可以多要一點通融。但不管怎麼說,孤兒院裡的孩子情況不同。他們已經失去了自己的父母,我們是永遠無法替代的。

米奇.艾爾邦經營海地有信孤兒院,並每個月親自訪視孩子們(取自Mitch Albom官網)
奇卡來我們家,雖然我們扮演的就是父母的角色,幫她洗澡、餵她吃東西、照顧她,和父母能照顧的沒有兩樣,但我們不會要孩子叫我們爸爸、媽媽,而是「米奇先生」、「潔寧小姐」。
奇卡的爸爸雖然從不在她的生命之中,但她還是會編故事,有時候會說她爸爸帶她去買過冰淇淋,我們就說那很好啊。
奇卡雖然知道她媽媽死了,基本上對她媽媽一無所知,但她有時候會說她媽媽這個,說她媽媽那個。有一次,奇卡說:「如果我去天堂,我媽媽會在那裡等我。」但接下來一句是:「但她怎麼認得出我是誰?」
我們說,當媽媽的都會認得出自己的小孩。她又問:「那我又怎麼認得出她呢?她會是像我這種古銅色的皮膚嗎?」不過再怎麼說,奇卡還是想到她有個媽媽會在天堂裡等她。所以每個孤兒都會有自己的鬼故事。你領養孤兒的時候,一定不能想自己要當他們的爸爸、媽媽。你只是個大人,是很愛她們,可以幫助、引導他們的大人。「爸爸」、「媽媽」是他們自己一生的課題。
郝:但我記得書裡有一段,奇卡雖然沒有對你叫出「爸爸」,但有說過很接近的一句話,你也很感動。
艾爾邦:那不是一句話。當時我在說我小時候,6歲時的一個故事。那天我爸爸帶我去湖邊遊泳,要我別游遠了。我游了一陣子,湖裡有一群孩子看到我,不知怎麼就指著我說:「我們去追他!」然後就過來了。我嚇得趕快朝我爸爸的方向游去。雖然只有10碼遠,我覺得像是游了一哩。等好不容易終於游到了,我抓住爸爸,抱住他的腰。他的腰圍、他皮膚的觸感,讓我感受到的那種踏實,即使現在和你說話時,都還在我眼前。
我覺得當爸爸的就是要給孩子這種安全感。所以我跟奇卡說:希望我也能給妳這種感覺,妳讓我有機會做這件事。奇卡跟我說:「你讓我有這種感覺。」
對我來說也是。即使我不是奇卡的爸爸,但她是我的女兒。她讓我覺得我像個父親,比任何小孩的爸爸都更像個父親。

(取自Mitch Albom官網)
郝:你們雖然有52個孩子,但奇卡還是有不同的特別吧?
艾爾邦:當然。尤其她是那麼需要我們。她來美國,這對她是一個陌生的國家。我們對她生活中每一分每一秒都有責任。
我們沒有和其他孩子度過那樣的兩年,我們也沒有帶過其他孩子奔波全世界,去尋找可以救她的醫生、藥物——從密西根到紐約,到德國,各種醫院。
這和你陪一個孩子住兩年,只是送她去學校、看她交朋友不同。這是我們需要全神貫注的兩年。奇卡在我們心中當然永遠占了一個特別的位置。
郝:書裡有個地方特別打動我。當時你和你太太有些情況,奇卡哭起來,因為她不知道可以怎麼幫助你們,讓你們不必那麼難過。
艾爾邦:對。那是我學到很重要的一課。那天在醫院裡,我和潔寧在房間另一頭,看報紙上的一個新聞,兩個人說話聲音就大了起來。那跟奇卡完全無關。
奇卡從床上喊:「你們在說什麼?」
我就跟她說沒事,叫她別擔心。
「可是你們聽起來很難過。」
我走過去跟她解釋。說人生有難過的時候,也有開心的時候。就像她經常開開心心的,也讓我們很快樂。
可是她卻哭了起來。說她不知道要怎麼幫忙。
我問她不知道要幫什麼?
「幫你們現在快樂起來。」
這是因為我們跟奇卡在一起總是非常快樂,即使她住進醫院,我們在她面前也總是強顏歡笑,所以她習以為常,就覺得讓我們開心成了她的責任。
我跟她學到的這一課就是,大人之間有什麼事,不論有什麼難題,都不要攤在孩子眼前。孩子會覺得那成了他們的事。
郝:奇卡帶給你最大的幸福是什麼?最難忘或最想念她的是?
艾爾邦:有一天我們在玩卡片,給卡片著色。當時奇卡已經不能走路。到哪裡都要我抱著,上車、去洗手間,去哪裡都是。
我和她玩到一個時間,說我要去工作了,要去電台。
「可是,米奇先生,我還要玩。」
我說我知道,可是現在不一樣,我要去工作了。
奇卡雙手環抱說:「不。那不是你的工作。你的工作是carry me(抱我、帶我)。」
那真是特別的時刻。我們每個人都要在人生的路途上承載什麼。你的雙手裡抱的是金錢,還是財富,還是什麼,都看你。我本來一生抱的都是書、公益,但突然間我發現我抱的是一個孩子,是不論字面上,還是真實的動作上都在抱。
我也忽然發現,這是我做過的,也是我將來會做的事情之中最重要的一件了。
我擁有奇卡的無數照片、無數回憶,但如果你問我最難忘的一刻,就是那一刻了。她自己不知道她的話對我有那麼大的啟發。
郝:所以你已經真正是父親了,而你對自己當父親的感觸?
艾爾邦:坦白說,我心底有一塊地方還是在告訴我:你失敗了。一個真正的父親,一個最好的父親,應該有法子救活的自己孩子。這可能會跟我一輩子。(哽咽)除此之外,我對身為一個父親的體會就是:愛你的孩子要遠比愛你自己還多。
郝:在書裡談過許多生死的主題之後,你最新的感觸是什麼?《遇見奇卡》中對生死的感觸,和寫《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時有什麼不同?
艾爾邦:在最近兩年半的時間裡,我先是失去我的母親,然後是奇卡,再來是我的父親。我自己也成了孤兒,那是很可怕的一段時間。我媽媽說過:「如果你活得久,那就得準備好夠多的眼淚,不然就得你先走。」
你提到的這兩本書,我的感觸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我很幸運,37歲時因為失去墨瑞,讓我對生死多少有了一些心理準備,後來也一直帶著當時的體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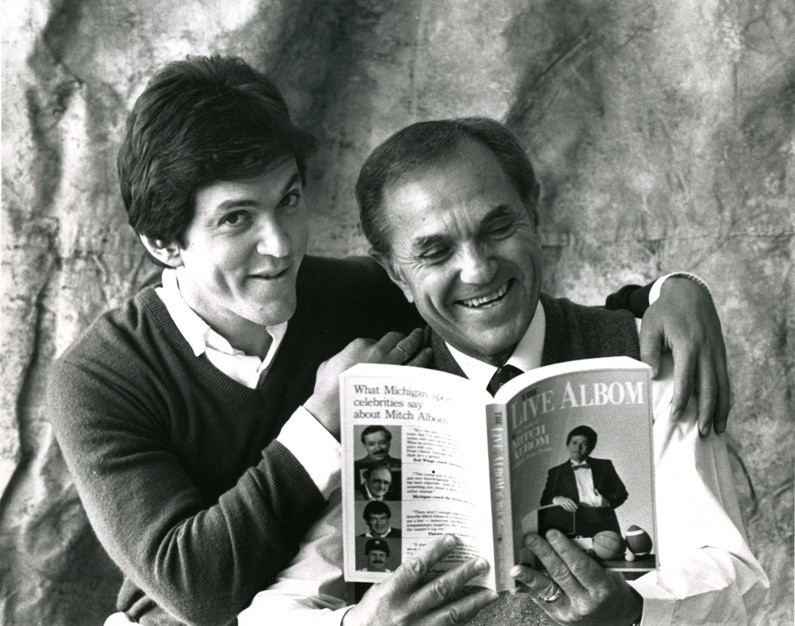
米奇.艾爾邦與父親的合照(取自Mitch Albom官網)
但是,失去老師,和失去你的父母、失去你的孩子畢竟是不同的。我跟墨瑞學到的課題,讓我在失去長輩,比如我父母的時候,有一定的心理準備。但是面對失去孩子這件事,就完全派不上用場。
我自己不時會回頭讀《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失去奇卡之後,我也找出來讀,看能不能有什麼啟發,找到安慰,但完全沒有。墨瑞沒有失去過孩子,所以我得自己來。
郝:其中最大的不同是?
艾爾邦:只有加入了「失去自己子女的社團」的人才明白。以這次疫情來說,我到許多地方辦活動,看到一些自己孩子死於這次疫情的父母。特別是4歲到9歲的孩子死了很多。這些父母都有些特別的神情,明白的人看了就知道。他們「破裂」(broken)了,看看他們的眼睛就知道,我們是處在同一個社團裡。
我不知要如何形容,就是你生命裡有些東西永遠不見了。你在背著哀傷行走,哀傷成為你的影子,成了你的鬼魅,去到哪裡都在。你也不是分分秒秒都意識得到,但它就是在那裡。
郝:你相信輪迴嗎?
艾爾邦:不相信。墨瑞相信,但我不相信。我相信人死後,靈魂就是要去某一個地方。我們死了之後都會去某個地方,但不會再回來。
郝:那就是天堂?
艾爾邦:對。
郝:不過你相信生命是交互影響的。
艾爾邦:對,這我相信。《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寫的就是這個。我自己的生命也是。多年前,我去見一位老教授,因為他缺乏醫療費用,我想提供他一些慰藉(comfort),寫了一本書幫他籌些錢,結果是他給了我更大的慰藉。
人生很多事情都像是朝湖裡丟一顆石頭,到底會激起什麼樣的漣漪?有多大?你不知道。你今天見了什麼人,說了什麼話,會怎麼影響你一輩子?不知道。若不是因為出版那本書,我也不會認識你,今天和你談這些。
海地地震發生後,如果不是有人打電話給我,如果我沒有去海地,我就不會遇見奇卡,也不會體會到有關父母、女兒的許多事。生命是相互關聯,而且彼此會產生漣漪。
郝:你是個宗教信仰很虔誠的人嗎?
艾爾邦:我是個有信仰的人,但不會很正經地遵行宗教儀式。星期天我不去教會,但每天早上我會禱告,相信宇宙裡有個更高的存在俯視著我。起床後,我拿著咖啡到電腦桌前禱告,先感謝上帝讓我這一天平安醒來,我的雙手、雙腳、身體都正常,活動自如。
看看窗外的花園,感謝我有如此平安的環境,沒有戰亂,在自己安全的家裡,上有結實的屋頂,不怕風雨。我每個月去一次海地,知道貧窮是怎麼回事,許多人沒地方住、沒東西吃的生活是怎麼回事。我每天起床後5分鐘裡所感受到的幸福,是多少人一天或多少天的時間都無法企及的。
再來我會為一些人祈禱,為一些我知道處境很辛苦的人祈禱,最後再為我自己禱告。全部時間大約10到15分鐘。然後,我就開始工作了。
郝:再次為你鼓掌。
艾爾邦:這是我自己的儀式。我相信上帝會接受各式各樣的儀式。我自己喜歡這種和上帝私密的對話,接著,我會開始和寫作的私密對話。我相信上帝給我獨特的才能,讓我進行一些有啟發、充滿希望的寫作。
郝:這次疫情如此嚴重,正是每個人都需要信仰的時候,你怎麼看?
艾爾邦:最近我收到世界各地許多讀者的來信。在太平日子裡,有些人會說我寫的東西太輕、太正面了,美好到不夠真實。但這次瘟疫對世界各地都造成重大傷害,很多人都在找我的書,讀了一本還要再讀一本,大家需要尋找希望。
最意外的是,我收到一位來自伊朗的讀者的信,伊朗和我們距離很遠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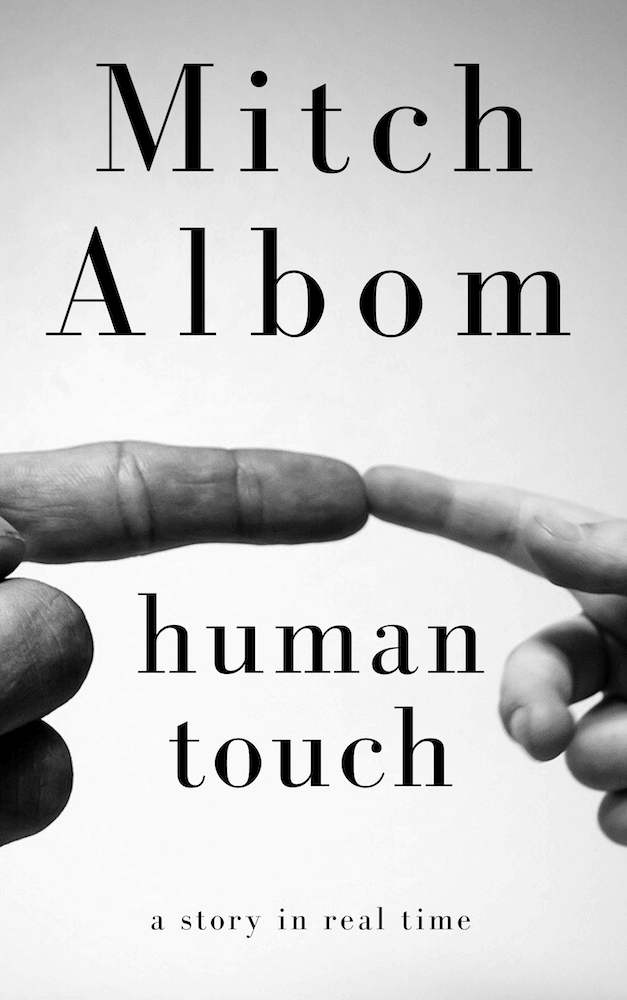
米奇.艾爾邦近期發表的小說《human touch》,供讀者於線上免費閱讀
你知道我在新寫一本免費讓大家讀的小書吧。我把時間設在今天,就在疫情肆虐的此刻,地點則是我居住的底特律市附近的一個小鎮。故事關於鎮上四口人家之間,因為疾病而發生的事情。其中有個8歲的小男孩,他很神祕,可能是個關鍵人物。
我在每個星期五發表一篇,現在已經發了兩篇,也自己錄成有聲書,都免費。看過的人如果想支持,也可以捐點錢給一個幫助底特律疫情的基金。我也參與管理這個基金,也很希望台灣可以做中文版。
郝:當然好。你每天忙這麼多事,都怎麼安排時間?
艾爾邦:我每天9點左右開始工作,就是寫作。不看新聞,不收電郵,全神貫注在寫作上。寫3個小時,到中午休息。然後就忙所有其他的事,很多很多。然後晚上大約12點入睡。
郝:謝謝你今天接受訪問。最後我想說,讀完《遇見奇卡》,今天又訪問你之後,我想到你在《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裡的一句話:「境界更高的忠誠,是人與人對彼此忠誠。」
艾爾邦:啊。對。我是說人的忠誠有很多形式,比如你對老闆的忠誠,你對政府、國家的忠誠。但境界更高的忠誠,是純粹人與人之間的忠誠。
郝:你遇見奇卡,陌生的兩個人之間發展出的這種關係,讓我想到這句話可以形容。
艾爾邦:奇卡後來已經不是陌生人了,她是我們的家人。●
|
 遇見奇卡 遇見奇卡
Finding Chika: A Little Girl, an Earthquake, and the Making of a Family
作者:米奇.艾爾邦( Mitch Albom)
譯者:吳品儒
出版:大塊文化
定價:380元
【內容簡介➤】
|
|
作者簡介:米奇.艾爾邦( Mitch Albom)
國際知名的暢銷作家,有7本著作榮獲紐時暢銷排行榜第一名,包括經典回憶錄《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連續4年維持聲勢不墜。他的虛構及非虛構出版作品,全球累積銷量超過四千萬冊,翻譯成47種語言,銷售49國。艾爾邦也創作了獲獎的電視影集、舞台劇及電影劇本、音樂劇,並撰寫全國性報紙專欄三十餘年,曾13度獲「體育新聞編輯聯合會」選為全美最佳運動專欄作家。2006年,他在家鄉底特律成立S.A.Y. Detroit這個傘形組織,統合管理九所慈善機構。自2010年起,他在海地太子港開設營運「海地有信孤兒院」(Have Faith Haiti Orphanage),每個月親自訪視。現與妻子潔寧住在密西根。
*本書所有的作者收益將捐贈給海地有信孤兒院
|
Tags:
作家米奇.艾爾邦(右)與來自海地的女孩奇卡(取自Mitch Albom官網)
編按:暢銷作家米奇.艾爾邦(Mitch Albom)睽違10年後再次回歸紀實寫作,推出新作《遇見奇卡》。艾爾邦曾出版《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再給我一天》等作品,其中7部皆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排行榜第一名,《時代雜誌》譽為「通俗文學界的貝比.魯斯」。
2010年海地大地震後,艾爾邦與妻子接手「海地有信孤兒院」(Have Faith Haiti Orphanage),將52位院童視為家人照顧,並因此而與小女孩奇卡相遇。奇卡到院時年僅3歲,5歲時診斷出罹患罕見癌症「瀰漫型內因性橋腦神經膠細胞瘤」(Diffuse Intrinsic Pontine Glioma,簡稱DIPG),米奇決定將她帶回美國接受更好的治療。長達兩年的求醫之旅,米奇夫婦體會到扶養孩子的喜悅,也深刻受到奇卡對抗病魔的樂觀與幽默影響,進而重新理解家庭的定義——不管是以何種方式形成的家庭,只要是基於愛的關係,就能緊密連結。
艾爾邦過去的作品皆由大塊文化譯介至台灣,《遇見奇卡》中文版上市之際,大塊董事長郝明義與作家進行對談。艾爾邦坦言這本新書是最深入剖析自我的作品,「雖然是寫一個孩子死去的書,但不是要你肝腸寸斷。」對談中貫串艾爾邦歷來的寫作脈絡,探觸幸福的奧義、生死的哀傷與超克,在面對疫情懷惴不安,眾人尋找信仰和希望之際,或可提供心靈的慰藉。以下是對談內容。
作家米奇.艾爾邦(左,Jenny Risher攝)與大塊文化董事長郝明義(大塊提供)進行對談
郝明義(以下簡稱「郝」):看你這麼多年寫的書,有些始終貫穿的主題,譬如生死;另外,也有些前後很有意思的對應,譬如最新這本《遇見奇卡》,就是你在設法保護一個6、7歲小女孩生命的故事。17年前出版的《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故事的起始也是因為一個人要去救一名8歲小女孩的命。你覺得這其中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如果我沒有在海地經營那所孤兒院,就不會有機會救到一些孩子。有幾個孩子曾患重病,我們送去醫院救了回來,醫生說很不可思議。而奇卡,你知道,她得的是罕見癌症DIPG,我並沒能救回來。不過如果留在海地,她只能活3、4個月,我把她帶回來,我們又相處了兩年時光。這麼說,我和艾迪是有些相似之處。
但我今天比當時更確信的是:在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照顧孩子。如果你能救一個孩子的命,那不是救了她的將來,也可能是世界的未來。因為等那個孩子長大,她可能做的事很多。
郝:你的前一本書《在天堂裡遇見的下一個人》,一方面故事是接續《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講那個逃過一刧的小女孩後來的故事,另一方面書前也特別獻詞給奇卡,這本書的創作是否和奇卡有關?
艾爾邦:奇卡一死,我就想馬上寫一本她的書。但是美國的出版社不建議,說我應該讓時間沉澱一下再動筆。於是我先寫了《在天堂裡遇見的下一個人》,把對奇卡的許多感情都放進那本書。書裡有個女人,她在天堂裡抱到自己失去的孩子,但才那麼幾秒鐘的時間,孩子又不見了,她一下子大哭起來。我覺得那其實是在寫我自己。得到孩子,轉眼又失去,真是掏心裂肺。
我一直等到一年半之後,覺得自己比較有了出版社所說的沉澱後的角度,才真正動筆寫奇卡。其實如果當時我就動筆,那會是一本完全不同的書。也許會比較不好,也許會更好,不知道。
但不管怎麼說,現在我完成了《遇見奇卡》,我很滿意這本書,覺得是我所有書裡最棒的一本。當然《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極為成功,但當時我還沒有自己觀察生命的角度,書裡的角度主要是墨瑞的,是他的想法,我自己的很少。
但是在《遇見奇卡》,我寫的是我從一個孩子身上體會到的看待生命的角度,無與倫比。雖然奇卡年紀很小,但她教了我很多。希望台灣的讀者也會喜歡這本書。
郝:啊,那難怪。我在讀《尋找奇卡》的時候,有感覺到你的平靜。我隱約覺得寫這樣的故事,你的情緒應該會更洶湧一些,原來你激動的情緒已先有了紓發的管道。
艾爾邦:是的,也許我的憤恨、沮喪都經由先前的那本書渲洩很多了。在美國出版界,大家都說:不要寫一本講孩子死去、太感傷的書,沒有人想看。我知道要寫也不能寫一本只是讓人肝腸寸斷的書,必須更深入。
米奇.艾爾邦與奇卡(取自Mitch Albom官網)
所以我在書的第一頁就先告訴讀者她死了,你不用看了一百多頁才發現這件事。不過你也會知道:她雖然死了,但會再回來和我說話。此外為了不讓讀者覺得恐怖,我從第一頁開始就用幽默的筆觸來寫。
所以,聽你說我顯得很平靜,我很高興,那是我希望的。奇卡剛走的那一年半裡,我的狀況一塌糊塗。現在我平靜下來寫,希望讀者知道這雖然是寫一個孩子死去的書,但不是要你肝腸寸斷。
郝:奇卡會回來和你說話?她過世後真的曾經現身嗎?
艾爾邦:不是,也是。我現在坐的這裡是我的工作室,每天早上我起得早,奇卡在世時也都起得很早。我太太還在睡覺,所以我下來這裡,做早餐,然後坐到電腦前,奇卡就坐在我右手邊的地板上。我說我要開始寫東西了,妳不要出聲,奇卡說好。然後不到10秒鐘,她就又開始說話了。你知道,她就是愛說話。
兩年裡,我們大半情況都是如此。所以奇卡死後,我每天下來,一坐到椅子上,閉上眼睛,就能浮現她在我身邊的影像,也會出現許多對話。那到底是真有其事,還是我想像出來的?我也不知道。
書裡的許多對話,有些是我們曾經確實交談過的,有些是我坐在這裡想像的,但覺得她就坐在我身邊。我不會說那是我和鬼魂的對話,但也真的是我和她的對話。我閉著眼睛說一句,好像她也回一句。畢竟,我們在這個地方曾經交換過那麼多有趣的對話。
郝:你曾在書裡說過:「每一個家庭都是一個鬼故事」。
郝:前面提到的呼應還有個例子。你在《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裡還寫過一句話:「一個陌生人,造就一個家庭。」你收養奇卡,真的是讓你的家庭完整了。
艾爾邦:我的孤兒院有52個孩子,奇卡是其中之一。現在我們孤兒院有兩個孩子來美國讀大學,未來其他孩子也都會來讀。等他們讀完大學,就可以回海地,為他們國家貢獻心力。所以我的責任是要活得久一點,讓更多孩子有機會來美國接受大學教育。
郝:先為你鼓鼓掌。然後,你在《再給我一天》裡寫到:「一個孩子只能不是他父親,就是他母親的孩子。」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話,請你再多說一些。
艾爾邦:那是說孩子在成長過程裡,在父母之間難免有一邊是他更倚賴些,更親近些,可以多要一點通融。但不管怎麼說,孤兒院裡的孩子情況不同。他們已經失去了自己的父母,我們是永遠無法替代的。
米奇.艾爾邦經營海地有信孤兒院,並每個月親自訪視孩子們(取自Mitch Albom官網)
奇卡來我們家,雖然我們扮演的就是父母的角色,幫她洗澡、餵她吃東西、照顧她,和父母能照顧的沒有兩樣,但我們不會要孩子叫我們爸爸、媽媽,而是「米奇先生」、「潔寧小姐」。
奇卡的爸爸雖然從不在她的生命之中,但她還是會編故事,有時候會說她爸爸帶她去買過冰淇淋,我們就說那很好啊。
奇卡雖然知道她媽媽死了,基本上對她媽媽一無所知,但她有時候會說她媽媽這個,說她媽媽那個。有一次,奇卡說:「如果我去天堂,我媽媽會在那裡等我。」但接下來一句是:「但她怎麼認得出我是誰?」
我們說,當媽媽的都會認得出自己的小孩。她又問:「那我又怎麼認得出她呢?她會是像我這種古銅色的皮膚嗎?」不過再怎麼說,奇卡還是想到她有個媽媽會在天堂裡等她。所以每個孤兒都會有自己的鬼故事。你領養孤兒的時候,一定不能想自己要當他們的爸爸、媽媽。你只是個大人,是很愛她們,可以幫助、引導他們的大人。「爸爸」、「媽媽」是他們自己一生的課題。
郝:但我記得書裡有一段,奇卡雖然沒有對你叫出「爸爸」,但有說過很接近的一句話,你也很感動。
艾爾邦:那不是一句話。當時我在說我小時候,6歲時的一個故事。那天我爸爸帶我去湖邊遊泳,要我別游遠了。我游了一陣子,湖裡有一群孩子看到我,不知怎麼就指著我說:「我們去追他!」然後就過來了。我嚇得趕快朝我爸爸的方向游去。雖然只有10碼遠,我覺得像是游了一哩。等好不容易終於游到了,我抓住爸爸,抱住他的腰。他的腰圍、他皮膚的觸感,讓我感受到的那種踏實,即使現在和你說話時,都還在我眼前。
我覺得當爸爸的就是要給孩子這種安全感。所以我跟奇卡說:希望我也能給妳這種感覺,妳讓我有機會做這件事。奇卡跟我說:「你讓我有這種感覺。」
對我來說也是。即使我不是奇卡的爸爸,但她是我的女兒。她讓我覺得我像個父親,比任何小孩的爸爸都更像個父親。
(取自Mitch Albom官網)
郝:你們雖然有52個孩子,但奇卡還是有不同的特別吧?
艾爾邦:當然。尤其她是那麼需要我們。她來美國,這對她是一個陌生的國家。我們對她生活中每一分每一秒都有責任。
我們沒有和其他孩子度過那樣的兩年,我們也沒有帶過其他孩子奔波全世界,去尋找可以救她的醫生、藥物——從密西根到紐約,到德國,各種醫院。
這和你陪一個孩子住兩年,只是送她去學校、看她交朋友不同。這是我們需要全神貫注的兩年。奇卡在我們心中當然永遠占了一個特別的位置。
郝:書裡有個地方特別打動我。當時你和你太太有些情況,奇卡哭起來,因為她不知道可以怎麼幫助你們,讓你們不必那麼難過。
艾爾邦:對。那是我學到很重要的一課。那天在醫院裡,我和潔寧在房間另一頭,看報紙上的一個新聞,兩個人說話聲音就大了起來。那跟奇卡完全無關。
這是因為我們跟奇卡在一起總是非常快樂,即使她住進醫院,我們在她面前也總是強顏歡笑,所以她習以為常,就覺得讓我們開心成了她的責任。
我跟她學到的這一課就是,大人之間有什麼事,不論有什麼難題,都不要攤在孩子眼前。孩子會覺得那成了他們的事。
郝:奇卡帶給你最大的幸福是什麼?最難忘或最想念她的是?
艾爾邦:有一天我們在玩卡片,給卡片著色。當時奇卡已經不能走路。到哪裡都要我抱著,上車、去洗手間,去哪裡都是。
我和她玩到一個時間,說我要去工作了,要去電台。
「可是,米奇先生,我還要玩。」
我說我知道,可是現在不一樣,我要去工作了。
奇卡雙手環抱說:「不。那不是你的工作。你的工作是carry me(抱我、帶我)。」
那真是特別的時刻。我們每個人都要在人生的路途上承載什麼。你的雙手裡抱的是金錢,還是財富,還是什麼,都看你。我本來一生抱的都是書、公益,但突然間我發現我抱的是一個孩子,是不論字面上,還是真實的動作上都在抱。
我也忽然發現,這是我做過的,也是我將來會做的事情之中最重要的一件了。
我擁有奇卡的無數照片、無數回憶,但如果你問我最難忘的一刻,就是那一刻了。她自己不知道她的話對我有那麼大的啟發。
郝:所以你已經真正是父親了,而你對自己當父親的感觸?
艾爾邦:坦白說,我心底有一塊地方還是在告訴我:你失敗了。一個真正的父親,一個最好的父親,應該有法子救活的自己孩子。這可能會跟我一輩子。(哽咽)除此之外,我對身為一個父親的體會就是:愛你的孩子要遠比愛你自己還多。
郝:在書裡談過許多生死的主題之後,你最新的感觸是什麼?《遇見奇卡》中對生死的感觸,和寫《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時有什麼不同?
艾爾邦:在最近兩年半的時間裡,我先是失去我的母親,然後是奇卡,再來是我的父親。我自己也成了孤兒,那是很可怕的一段時間。我媽媽說過:「如果你活得久,那就得準備好夠多的眼淚,不然就得你先走。」
你提到的這兩本書,我的感觸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我很幸運,37歲時因為失去墨瑞,讓我對生死多少有了一些心理準備,後來也一直帶著當時的體會。
米奇.艾爾邦與父親的合照(取自Mitch Albom官網)
但是,失去老師,和失去你的父母、失去你的孩子畢竟是不同的。我跟墨瑞學到的課題,讓我在失去長輩,比如我父母的時候,有一定的心理準備。但是面對失去孩子這件事,就完全派不上用場。
我自己不時會回頭讀《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失去奇卡之後,我也找出來讀,看能不能有什麼啟發,找到安慰,但完全沒有。墨瑞沒有失去過孩子,所以我得自己來。
郝:其中最大的不同是?
艾爾邦:只有加入了「失去自己子女的社團」的人才明白。以這次疫情來說,我到許多地方辦活動,看到一些自己孩子死於這次疫情的父母。特別是4歲到9歲的孩子死了很多。這些父母都有些特別的神情,明白的人看了就知道。他們「破裂」(broken)了,看看他們的眼睛就知道,我們是處在同一個社團裡。
我不知要如何形容,就是你生命裡有些東西永遠不見了。你在背著哀傷行走,哀傷成為你的影子,成了你的鬼魅,去到哪裡都在。你也不是分分秒秒都意識得到,但它就是在那裡。
郝:你相信輪迴嗎?
艾爾邦:不相信。墨瑞相信,但我不相信。我相信人死後,靈魂就是要去某一個地方。我們死了之後都會去某個地方,但不會再回來。
郝:那就是天堂?
艾爾邦:對。
郝:不過你相信生命是交互影響的。
艾爾邦:對,這我相信。《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寫的就是這個。我自己的生命也是。多年前,我去見一位老教授,因為他缺乏醫療費用,我想提供他一些慰藉(comfort),寫了一本書幫他籌些錢,結果是他給了我更大的慰藉。
人生很多事情都像是朝湖裡丟一顆石頭,到底會激起什麼樣的漣漪?有多大?你不知道。你今天見了什麼人,說了什麼話,會怎麼影響你一輩子?不知道。若不是因為出版那本書,我也不會認識你,今天和你談這些。
海地地震發生後,如果不是有人打電話給我,如果我沒有去海地,我就不會遇見奇卡,也不會體會到有關父母、女兒的許多事。生命是相互關聯,而且彼此會產生漣漪。
郝:你是個宗教信仰很虔誠的人嗎?
艾爾邦:我是個有信仰的人,但不會很正經地遵行宗教儀式。星期天我不去教會,但每天早上我會禱告,相信宇宙裡有個更高的存在俯視著我。起床後,我拿著咖啡到電腦桌前禱告,先感謝上帝讓我這一天平安醒來,我的雙手、雙腳、身體都正常,活動自如。
看看窗外的花園,感謝我有如此平安的環境,沒有戰亂,在自己安全的家裡,上有結實的屋頂,不怕風雨。我每個月去一次海地,知道貧窮是怎麼回事,許多人沒地方住、沒東西吃的生活是怎麼回事。我每天起床後5分鐘裡所感受到的幸福,是多少人一天或多少天的時間都無法企及的。
再來我會為一些人祈禱,為一些我知道處境很辛苦的人祈禱,最後再為我自己禱告。全部時間大約10到15分鐘。然後,我就開始工作了。
郝:再次為你鼓掌。
艾爾邦:這是我自己的儀式。我相信上帝會接受各式各樣的儀式。我自己喜歡這種和上帝私密的對話,接著,我會開始和寫作的私密對話。我相信上帝給我獨特的才能,讓我進行一些有啟發、充滿希望的寫作。
郝:這次疫情如此嚴重,正是每個人都需要信仰的時候,你怎麼看?
艾爾邦:最近我收到世界各地許多讀者的來信。在太平日子裡,有些人會說我寫的東西太輕、太正面了,美好到不夠真實。但這次瘟疫對世界各地都造成重大傷害,很多人都在找我的書,讀了一本還要再讀一本,大家需要尋找希望。
最意外的是,我收到一位來自伊朗的讀者的信,伊朗和我們距離很遠啊。
米奇.艾爾邦近期發表的小說《human touch》,供讀者於線上免費閱讀
你知道我在新寫一本免費讓大家讀的小書吧。我把時間設在今天,就在疫情肆虐的此刻,地點則是我居住的底特律市附近的一個小鎮。故事關於鎮上四口人家之間,因為疾病而發生的事情。其中有個8歲的小男孩,他很神祕,可能是個關鍵人物。
我在每個星期五發表一篇,現在已經發了兩篇,也自己錄成有聲書,都免費。看過的人如果想支持,也可以捐點錢給一個幫助底特律疫情的基金。我也參與管理這個基金,也很希望台灣可以做中文版。
郝:當然好。你每天忙這麼多事,都怎麼安排時間?
艾爾邦:我每天9點左右開始工作,就是寫作。不看新聞,不收電郵,全神貫注在寫作上。寫3個小時,到中午休息。然後就忙所有其他的事,很多很多。然後晚上大約12點入睡。
郝:謝謝你今天接受訪問。最後我想說,讀完《遇見奇卡》,今天又訪問你之後,我想到你在《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裡的一句話:「境界更高的忠誠,是人與人對彼此忠誠。」
艾爾邦:啊。對。我是說人的忠誠有很多形式,比如你對老闆的忠誠,你對政府、國家的忠誠。但境界更高的忠誠,是純粹人與人之間的忠誠。
郝:你遇見奇卡,陌生的兩個人之間發展出的這種關係,讓我想到這句話可以形容。
艾爾邦:奇卡後來已經不是陌生人了,她是我們的家人。●
Finding Chika: A Little Girl, an Earthquake, and the Making of a Family
作者:米奇.艾爾邦( Mitch Albom)
譯者:吳品儒
出版:大塊文化
定價:38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米奇.艾爾邦( Mitch Albom)
國際知名的暢銷作家,有7本著作榮獲紐時暢銷排行榜第一名,包括經典回憶錄《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連續4年維持聲勢不墜。他的虛構及非虛構出版作品,全球累積銷量超過四千萬冊,翻譯成47種語言,銷售49國。艾爾邦也創作了獲獎的電視影集、舞台劇及電影劇本、音樂劇,並撰寫全國性報紙專欄三十餘年,曾13度獲「體育新聞編輯聯合會」選為全美最佳運動專欄作家。2006年,他在家鄉底特律成立S.A.Y. Detroit這個傘形組織,統合管理九所慈善機構。自2010年起,他在海地太子港開設營運「海地有信孤兒院」(Have Faith Haiti Orphanage),每個月親自訪視。現與妻子潔寧住在密西根。
*本書所有的作者收益將捐贈給海地有信孤兒院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
【2/6國際書展講座】書寫、行動與反思:和島嶼互動的幾種方式
閱讀通信 vol.366》為什麼要叫勇者,不叫英雄?
延伸閱讀
對談》紀實漫畫(雜誌)的結束與開端,《熱帶季風》的浪潮:訪漫畫家高妍、阿多與慢工黃珮珊
閱讀更多
對談》她們所愛的(植物)世界:三浦紫苑 x 鄒欣寧談《沒有愛的世界》
日本直木獎&本屋大獎得主三浦紫苑近日推出全新長篇小說《沒有愛的世界》中譯本。繼《哪啊哪啊~神去村》之後,睽違10年,三浦再度以自然為題,... 閱讀更多
專訪》即使只是小人物,也能成為別人的英雄:訪《做工的人》導演鄭芬芬、編劇洪茲盈及作者林立青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