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安心,安心——這裡是美國牛津大學詩詞社本部 ft.《蟻王要的也不是這種蟻后》
:我台北人,29歲,本名湯博宇。
:等等,我們已經開始了嗎!?
我猜想我沒有很適應小我快10歲的年輕人節奏,比方說,一見面就衝著訪綱的問題,逕自進入輕微混合饒舌風的ChatGPT問答狀態。看著他兩手臂和耳朵下方布滿刺青,毛毛鬈鬈的頭,固然沒有一般刺龍紋鳳的大哥嚇唬人的意思,卻也意會到年輕人紋上一些骰子、鎖鏈、椅子、鏟子等不知所云,是另一種擺明了「你不要問,接受我的存在就好」、覆上「工業風遮罩」的另類武裝型態。
這位對坐的29歲台北人是IG詩人,網路帳號署名「美國牛津大學詩詞社」,常發些有諧音哏押韻的手寫詩自娛娛人。後來這些詩被眼尖的編輯在網海淘寶,打撈出版成冊,名為《蟻王要的也不是這種蟻后》。亮黃色書皮上,桃紅色文案下著「苦中作樂,葷腥不忌,真理與胡鬧,只在一句之隔。」
於是來之前,我便略知對坐者性格叛逆一二。見了面,看他亮出一身鬧鬧的刺青與醒目的鼻釘,更明白這類人對前輩雖不致失禮,也多少懷有些「建議」。我因此還是不免自我審查了起來,想說我應該要chill一點,或是稍微變奏以示即興的功力與真誠的來意。我說,等等,博宇等等,讓我先來上幾句。
:我是想說,我來之前就想說:為什麼會找我訪問你?是有誰發現我之前不太好的時候,會看查理.布考斯基的詩嗎?他的詩很下流,可是我正在腹黑(但又自認心懷陽光)的時候,看了覺得有爽度,莫名治癒。然後讀到你的詩,也是一樣的感覺,覺得你是台灣布考斯基嗎?
:我不知道布考斯基,但你說的我懂,我寫作時也往往有點痛苦,但寫這些時會有樂樂跑出來,就是一個由苦到樂的過渡。

我看著前面鬈鬈頭的湯博宇,問他為何說話有點ABC腔,原來是高中時去美國唸過書。我又再從繼續的身家調查中意會到,他身上紋的各種「東西」,是曝露他大學主修工藝設計的線索痕跡。我暗忖,這樣90後世代的大男孩心裡有什麼苦衷?然而,我們出身台灣,儒雅有禮,偏好先禮後兵,「挖苦」前先「挖苦挖苦」,從不知道是多巴胺、腦內啡、催產素,還是血清素催生的「樂樂」聊起。
:我以前很喜歡在開車的時候聽饒舌,也會在車上就開始即興創作。雖然這次你好像很想談「諧音哏」,其實我覺得就是某種節奏韻律,有這種律動感出來的時候,樂樂就會跑出來。我覺得喜歡詩,還有這些律動,那是人的天性。
:但就像饒舌歌手的歌詞,你也不只是「打油詩」那樣的追求而已?
:對,我喜歡的那些黑人饒舌歌手,像是Kendrick Lamar等,他們其實都有社會觀察與批判的部分。其實我沒有辦法接受「言之無物」,發文必然是有想要寫的東西。
湯博宇說起自己寫詩的訣竅,居然沒先跟知名線上課程平台簽約,就全然不藏私地公開方法絕學。不聽不知道,一聽我嚇到,原來美國牛津學院詩詞社的社辦深處,有一座Notion庫房,嚴密規劃三層結構:其一堆積著生活中乍現快閃過的靈感,其二是消化整理過後的思緒,再來才是最終結晶化成的作品。
乍看non-sense或是有點低級的紙面噴射,原來也有它生命的指涉,有它貌似中二,少說大二,甚至博二的反差萌。一個有潛力的「關鍵字」,歷經情緒性觸發,進入思辨運行軌道,跳脫框架,逆向破壞以詞語和句讀的失之毫釐。經過這番嚴正胡搞,那些糾纏自己的「字」竟然就輕鬆地滑離字根,脫隊字典。或也稱不上進入邪典,就只是讓世界稍微斜了那麼一點。就是在那個瞬間,牛津悄悄位移到美國,世界也就莫名插枝千里地,離苦得樂。
:你有注意到你的這些詩詞、諧音哏可以匯聚成什麼形狀樣態的「關鍵字雲」嗎?
:我沒有特別這樣分類,但確實發現我好像特別關注某些事,(他指著訪綱上「夢想/目標/志向」這串字詞),就是有「這樣」的壓力。

眼前的湯博宇忽然開始丟裝備,輕微繳械。他說自己青春期叛逆讓父母傷腦筋。怎樣叛逆?他說曾經環島全台,與朋友到處拾材,現場組裝成椅子拍照,是為一樁行動藝術。
眼看他丟在檯面上的叛逆,就像是把刺青上的傢私,那些迷你的鎖鏈、椅子、骰子、鏟子亮出來,我忽然秒懂,當自以為陰暗面或反骨,也是多半小二,至多中二等級的時候,是會怎麼讓其他人啼笑皆非。然而,這份無害也沒做派的單純可愛卻讓我想哭,因為緊接而來最大的揭露是:「我其實不是很有自信,一直都不是很有自信的人。」
:我不喜歡以往認為詩就是一種風雅的東西,我覺得創作應該沒有門檻。
:這很酷。
:我一直都不是那種很酷的創作者。我很知道我要服務觀眾跟讀者,我也喜歡這個互動,如果沒有放上IG我也不會有動力。
年輕孩子意圖做一些事引人注意,希望找到才華轉換、尊嚴永駐的成功模版,卻一個不小心就捲入演算法與點擊率構成的苦樂循環裡。湯博宇說他不算原生網路世代,但是成名、成功、被看見的壓力,每天都在社群裡挑起自己的敏感神經。
他說當很多周圍的人炫耀著自己已經賺到幾桶金,人生車尾燈已拋開自己幾萬公里,這使人緊張。而他選擇在自己的蟻窩裡建構小小的城國,一個寄生於Notion中,微型而有機的地下組織,時而投靠向蟻王,片刻效忠於蟻后,嘗試把創意搬來挪去,樂在蟻生的韻律感中,連帶地把膨脹的自己搞笑地洩氣消風。

湯博宇把自我表述與被看的苦樂寫得傳神,自嘲與揭露這些博取注意的行徑,比方這篇:「有人看/就開始有壓力/大器的人/承受大器壓力/普通的人/就還不想放棄」。又比方另一篇寫著:「在有限的土地上/每個人都想當王/在有線的主意上/每個人都想張狂/好房或好的乳房/上下滑東張西望」。
然而他卻是慷慨地攤開內心所有,一如普羅大眾或多或少有過的內心陰影面積,比方罪惡感、自卑自信、比較心、成名心、直男癌云云。藉由書寫,將這些世俗名利、慾望流行再淡薄仔看淡一點,看薄一點。與落入所謂世道、上道的爭逐遊戲規則,拉開一層笑玩與冷感的心理距離。略帶嫉俗憤世的時刻,只消再笑自己一輪,一輪又一輪地笑過,這些痛苦,也就過了。
重新再看湯博宇的渾身鏟子、骰子、椅子,是遊走江湖的明哲保身,是穿越無實質意義的所謂事實、信仰和觀念的新型法器。如此輕微逆天而行,在都市與社群叢林裡闖闢出一條險異折曲的行跡,也無怪刺青裡頭還混著松本大洋的《惡童當街》裡,小白對小黑講的那一句「安心,安心」。
:那你以往真的有想到出書的以後嗎?出書是蟻王要的蟻后嗎?
:出書畢竟還是很酷,你看這個黃色亮亮的皮,而且它就被封存在這裡了,蟻后還不知道會怎麼樣,但我也有把我的詩文試著弄在陶器上面。
:陶器?
:就是你知道要是有一天蟻后的人撿到這個陶器,他們可能會發現這個時代某些生活的痕跡跟意義……
:噢!我沒有想到你說的是這種程度的蟻后……
事實是,當小博宇開始邁入30年紀,並非住在寶町,而是住在曾經是台北某個町的他,也被迫漂流海外後,再重新審視與識別、被各種利益結構滲透而入的,自己的原鄉。為了守衛那個天真爛漫的夥伴與還懷有希望的自己,不得不拿出頑抗的姿態。然而守護者可能不是隻身擋之在前的小黑,卻是屁顛屁顛呼叫自己的小白。

:我的詩集裡,還有最近另一系列詩在開發中,是寫周圍的人,然後有點像分鏡,很像構成我的世界觀。
:哇,好酷的idea,那要不要試著連續發表某一個角色,然後讓這些角色慢慢發展成一座微型宇宙?
訪問到後來我也有點不知所云,但是湯博宇和編輯們好像都很可以的樣子,真是開心。
選擇戾氣,不免有點太耗力氣,最終只是被自己的黑暗所噬滅。不如找到孩子氣或傻裡傻氣,或遊走跑跳滑行於外環邊沿,像個人類學家般對這座又歡樂又病態的城市和自己考現,並試著將這些人類行跡,如蟻群經行的筆跡與劃痕歪歪斜斜地記錄下來。
這些圖文它乍看嘻嘻哈哈,其實內核嘻哈,熱心冷眼登上看台俯瞰人性有多奇葩,如此留下的世界或許近乎神諭,送到可堪參透且欲擘畫對人類集體更共生共榮圖景,而非互相虐殺的人手裡。●

|
|
|
作者簡介:美國牛津大學詩詞社 牛津津有味,組成是半筋半肉,字字鑽進你的腰間肉。 職業詩人,美國牛津大學詩詞社社長,幽默感是幫助消化的最佳解藥。有時燉得很爛,有時生硬難嚼。靈感總是把社辦當自己家一樣自由進出,不拿筆的時間比拿筆的時間還要長很多,因為生活需要抽絲剝繭,細嚼慢嚥。如果幽默能發電,我們也能叫牛津大學核能研究社。 創作就從碎碎唸開始,一旦你踏出第一口,the rest will follow. |


 蟻王要的也不是這種蟻后
蟻王要的也不是這種蟻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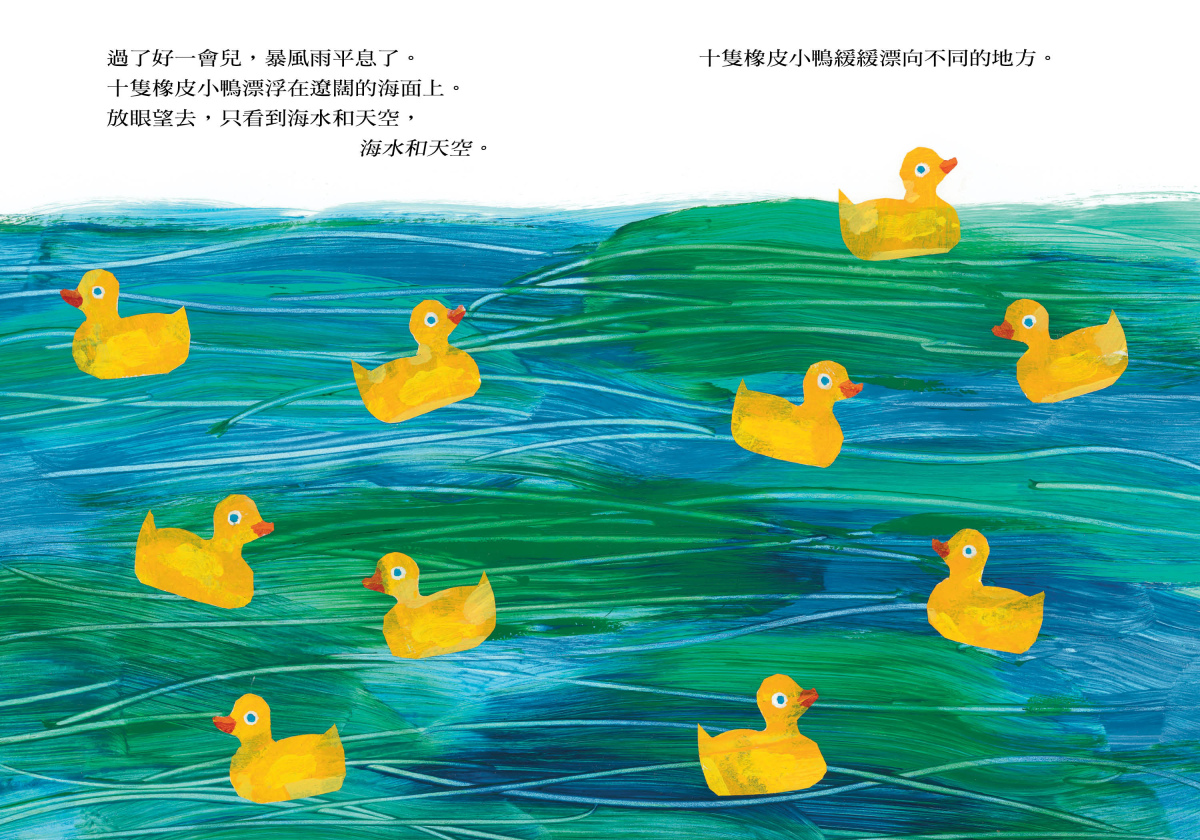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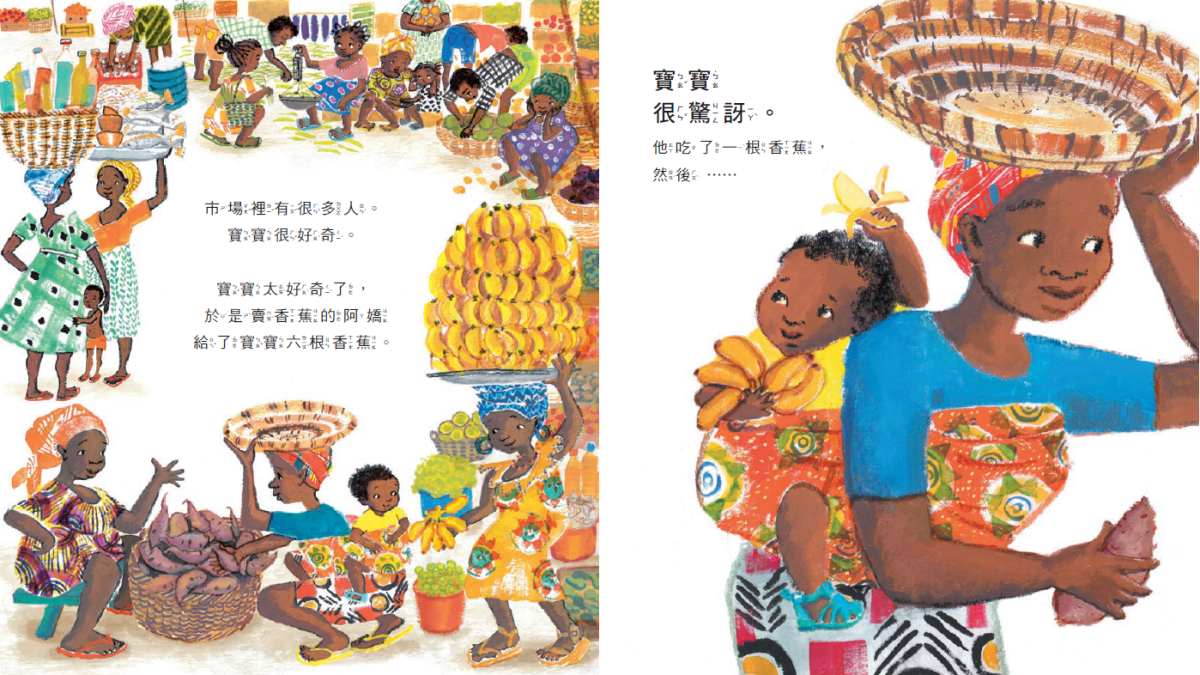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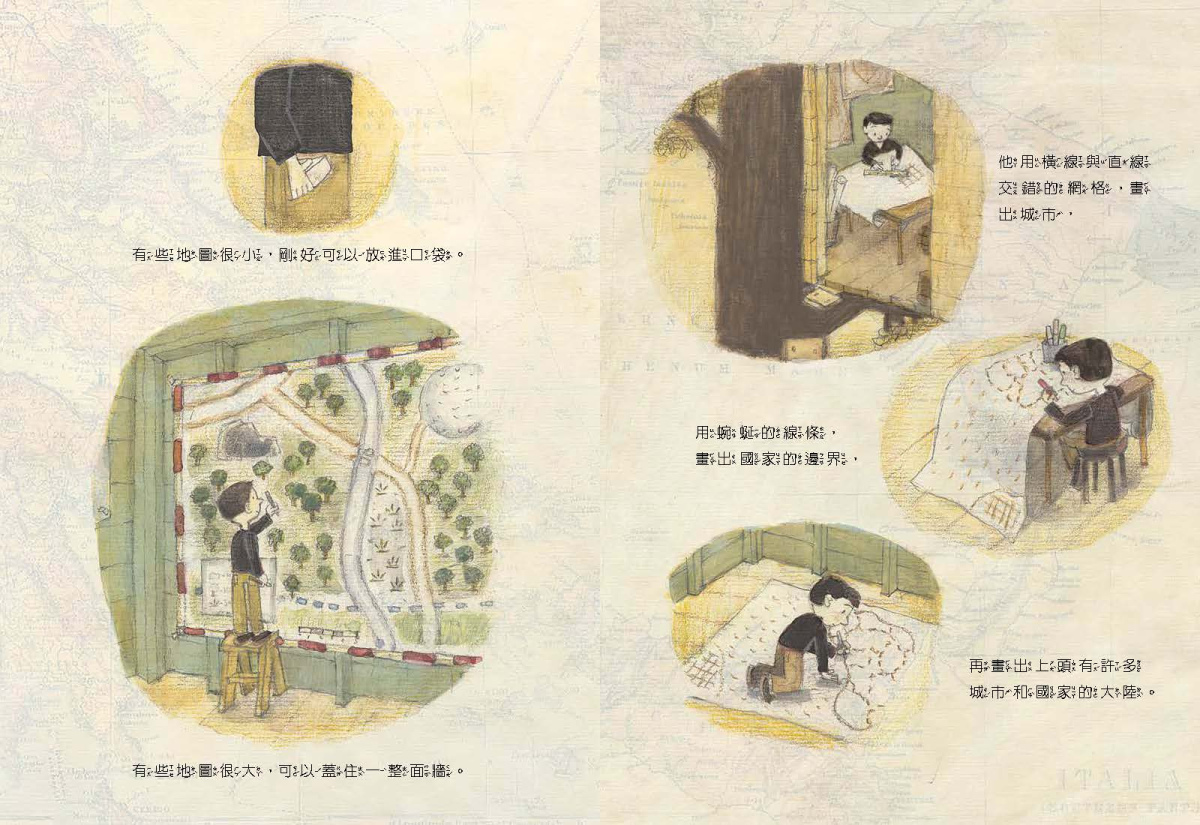





閱讀隨身聽S10EP8》法律白話文運動劉珞亦/看新聞氣噗噗嗎?法普書來幫你 ft.《童話陪審團》
本集節目中,法律白話文運動社群總監劉珞亦回顧了自己做法普的初衷,法白如何從出版、社群、媒體多面向地設計出法白的長久運營模式,台灣人買法普書嗎?該如何讓兒童與社會大眾對法律感興趣呢?法律的思辨性如何如何在童書中呈現?請聽劉珞亦娓娓道來。
Openbook閱讀誌成立迄今已屆7年,閱讀了超過兩萬本新書,其中有大半的作品, 圍繞著台灣這塊土地,映照不同面向的時代樣貌。我們特別精選推介過的年度好書,籌畫「島讀共同體」系列活動,將它們化為2場作家對談、2組共4場自然與生態走讀活動與3場人文議題Podcast節目。深入了解更多,請點擊:「島讀共同體」。
【精華摘要】
➤出版如何放到法白的內容生產中
主持人:法律白話文運動的內容包含Podcast、短影音、數位媒體、出版,這是跨領域的,相同內容在多種形式中應用。你認為這樣做有什麼優缺點呢?
劉珞亦:我們採取分散的方式,希望每個點都能達到不同的受眾。隨著數位發展,閱聽習慣越來越多元,有些人喜歡看短影片,有些人偏好社群圖文,有些人則只聽Podcast,還有些人喜歡看書。對我們來說,法律普及最重要的是讓大家更容易接觸法律,因此我們在每個平台上都打造屬於法白的產品,我認為這有助於傳播。
舉個例子,像奇異果,有些人覺得不好吃,但如果打成汁加點蜂蜜,可能就會變得更容易接受。我們嘗試改變傳達方式,讓法律知識更容易被接受。我們專注於如何讓這個過程變得更「美味」。
主持人:出版界瀰漫著紙本書越來越難推的氛圍,在這樣的情況下,法白為什麼還投入書籍出版?這對你們來說是支持還是負擔?
劉珞亦:其實是正面的。我們的出版有兩種模式。第一種是將已有的內容轉換成書籍,比如法白的第一本書《江湖在走法律要懂》,就是從網站文章收集並改編而成的。《法律歸法律》則是從IG文案擴寫而來。這些都是將我們既有的內容轉變為書籍,已經成為我們的標準操作流程。第二種模式是我們專門為一個主題撰寫書籍,比如《公民不盲從》,這是為了人權議題特別撰寫的。
我們之所以堅持出版,是因為書籍有一種特質,它比較容易長久流傳。一篇IG文案、短影片或Podcast可能隨著時間被遺忘,但一本書出版10年、20年後,仍然可能有讀者翻閱。
對我們而言,書籍很容易出現在教育現場或圖書館,或許某人無意中翻到,進而認識我們,了解法律。這種影響是數位產品比較難達到的,所以我們會繼續做下去。
➤童書很難做?《童話陪審團》的企劃
劉珞亦:如果社會對法律有越來越多的了解,法律水準提升,不僅對律師,對整個社會來說,都是好事。我也會因此感到快樂。
主持人:《童話陪審團》這本書你們做得快樂嗎?
劉珞亦:做書的過程一定不快樂。如果做一件事的過程中本身就超級快樂,那這件事可能並不那麼重要。黃仁勳曾說過,「很棒的工作,其實做起來並不容易」。撰寫書籍的過程需要不斷反覆修改,才能達到最好的結果,這個過程中難免感到痛苦,但當你看到它賣出去時,那份快樂就會隨之而來。
主持人:比起出庭,做書痛苦時,你會不會覺得出庭反而比較容易?
劉珞亦:這也不一定。所有來找律師的人,沒有一個是快樂的,他們一定是帶著憤怒、悲傷或困惑來,不管是離婚還是犯罪。從事律師工作,痛苦的部分在於承擔當事人的情緒,我個人其實不太喜歡,因為我容易受到他人情緒的影響。相較之下,我更喜歡做法治教育。
例如,離婚案件往往充滿情感拉扯,情緒張力最強且反覆無常。這種痛苦其實與法律無關,而是來自於當事人的情緒影響。
主持人:《童話陪審團》為什麼選擇以童話為主題?
劉珞亦:主要是企劃上的考量。如果我們寫一則法律文案,故事是大家不知道的,讀者為什麼會被吸引呢?可能是因為他們好奇故事內容或想了解法律。但童話的邏輯恰恰相反,大家都知道「國王的新衣」、「小紅帽」、「三隻小豬」這些故事。正因為大家都知道,反而不會去思考法律問題。
舉例來說,「三隻小豬」裡的豬大哥用茅草蓋屋,有沒有違反《建築法》或《水土保持計畫法》?從輕鬆的故事中切入嚴肅的法律問題,反而能引起讀者的興趣。再如「小紅帽」幾歲?讓她工作有沒有違反《勞動基準法》對童工的定義?從已知的故事中探討未知的法律知識,讀者其實會很感興趣。
➤ 減少廉價的批評,不了解,其實是了解的開始
劉珞亦:了解更多法律,我認為可以減少許多廉價的批評。許多知識了解得越多,反而會走向「不確定性」。人們常說:「真理越辯越明」,但實際上,有時候越辯越不明,不明反而是接近真理的路徑。法律充滿了不同情境下的詮釋角度,在不同案件中,解釋方式可能會有所不同,因此越來越不確定。
以2024年4月23日的大法官死刑言詞辯論為例,網路上充斥著情緒性的言論,但了解法律的人因為知道「不確定性」,反而不會急於發表憤怒的評論。我們需要減少不必要的新聞評論,讓大家更冷靜。提升媒體識讀和判斷社會案件的能力對我們來說很重要,而且我覺得這種改變正在發生。
主持人:像推「薛西弗斯的石頭」,一方面希望大家用比較理性的心智,但另一方面,會有一些新聞試圖將狀況搞得更模糊、更情緒化。
劉珞亦:用「薛西弗斯的石頭」來形容我們,是極大的稱讚。它看起來很愚蠢,但卻充滿毅力。有時候,毅力非常重要,因為效果往往不是立即可見的。就像我剛才分享的,我們討論議題,試圖翻轉一些思維,這過程就像推石頭。
在推石頭的過程中,以前會有很多人留謾罵性的評論,但聽了我們的節目、看了我們的書後,他們不再這樣留言。對我們來說,這已經足夠了。而且,這樣的情況確實發生在我們節目中的回饋裡。有聽眾分享說,聽了我們的節目後,他現在的答案變成了「不知道」。這個「不知道」對我來說,就像石頭向上推進了一點。
➤降低期待+不要看錯方向
主持人:法白已經運作了……
劉珞亦:10年。
主持人:10年了,那你如何保持適當的期望值?
劉珞亦:降低期待。大家常常高估自己,認為「我今天做了這件事,一定要立刻有反應,否則社會就是爛的,我不做了」。這可能是一種誤解。改變本來就是一點一滴、慢慢累積的。
舉個例子,法白的第一本書,當時我們在某地舉行了新書發表會,雖然有不少人參加,但和現在相比還是少了很多。當時有與會者和我們互動,但我們並沒有特別記住。五、六年後,他已經成為法律系的大學生,他邀請我回學校演講,並告訴我,他之所以選擇念法律,是因為參加了那場新書發表會,從那時起對法律產生了興趣。這對我來說,是一種極大的鼓舞。
我們總是關注那些似乎無法被我們改變的人,悲觀地認為他們無法被改變。但事實上,社會上多數人是有可能被改變的,或者他們正中立地觀望。因此,我們應該把更多心思花在那些已經被改變或可能被改變的人身上,這樣會讓自己更加鼓舞。每次發生這樣的事情,我都會感到非常感動,覺得自己對社會有一點點小小的幫助,這就足以讓我繼續堅持下去。
主持人:所以你的建議是:第一,不要抱太高的期望;第二,不要看錯方向。
劉珞亦:沒錯,不要一直關注那些總是在批評你的人,他們永遠都會存在。把心思放在那些支持你、喜歡你的人身上。●
主持人:吳家恆,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畢業,英國愛丁堡大學音樂碩士,遊走媒體、出版、表演藝術多年,曾任職天下雜誌、時報出版、音樂時代、遠流出版、雲門舞集、臺中國家歌劇院。除了在大學授課,在臺中古典音樂臺擔任主持人之外,也從事翻譯,譯有《心動之處》、《舒伯特的冬之旅》、《馬基維利》、《光影交舞石頭記》等書。
片頭、片尾音樂:微光古樂集The Gleam Ensemble Taiwan
【島讀共同體】完整專題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