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題》唯有直接地寫,才能展示承受的撕裂:蔣亞妮談諾貝爾文學得主安妮.艾諾(Annie Ernaux)
講題:時間,書寫者的手術刀—談安妮艾諾
主講:蔣亞妮(作家)
整理:梁嘉真、趙俐雯
散文作為一種文類,應奠基於非虛構的全然事實描述,抑或能有揮灑想像的虛構空間?這之間的界線與拿捏,近年來已有大量的交流討論。與此平行的另一個軸線上則是私書寫、私小說,以小說的敘事與樣態,交託寫作者的生命經驗。安妮・艾諾的作品袒露了她少時尋求願意協助她施行墮胎手術的曲折歷程、曾與已婚者偷情、父母的離世種種,引起讀者兩極評價。艾諾的私書寫手法如何有別於散文與回憶錄?為什麼她往往任由時間飛逝,直到事過境遷後再以回顧的姿態進行書寫,透過文字對話,讓當下的自己提筆回應留存於日記裡的狀態與心情?
長期投身於散文書寫的作家蔣亞妮,與讀者分享她對艾諾的評析與觀察,就從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致詞開始。
➤書寫,是為了復仇
蔣亞妮解釋,她熱愛閱讀不同作家獲頒諾貝爾文學獎的致詞:「那是世界上最精湛的、可以說是用一生完成最好的散文作品……你會被那些東西震撼。」致詞內容之所以打動蔣亞妮,或許正因為那是作家所能步入的最高文學殿堂,除了傳達感謝,更涉及面對書寫這樣的技藝,身為「工匠」的世界級寫作者,在發表感言的時間內,各自說明以如何的精神態度來琢磨與打造文學作品,以及面對國際關注時,無以迴避地捫心自問——闡述「為什麼要書寫」。
「我書寫,是為了替我的族類復仇(J’écrirai pour venger ma race.) 。」當安妮.艾諾試圖為自身的寫作生涯定下基調,偶然間翻到60年前的自己在日記寫下的這句話,遂放入致詞內容。

蔣亞妮認為,艾諾之所以寫作,是為了理解「為何她與自身之外的種種,會讓她遠離了她的出身?為什麼選擇走向寫作這條路,讓她離家人越來越遠,與他們越來越不一樣?」蔣亞妮描述,艾諾的父母只具備基本識字能力,平時說的法語是「帶有方言感、土話的」法語。可以想見,後來接受大學教育、從事教職的艾諾跟父母間逐漸出現階級與文化的隔閡。這樣的隔閡感,其實也顯見於她與法國文壇的齟齬間。
蔣亞妮表示,艾諾即便廣受讀者歡迎,卻在追求精緻的法國主流文壇飽受抨擊:「即使她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都沒有得到(法國主流文壇)肯定。」她解釋,當2022年諾獎頒發給艾諾後,引起法國《費加洛報》巨大的反彈,貶抑其書寫為「平凡、可悲、粗暴、骯髒,讓法國語言乾澀化,無益於人民真正自由跟水準提升。」蔣亞妮引述後隨即表達自己的不同立場:「這些巨大如浪潮般的批評,就是對艾諾最大的肯定。因為這就是她一生追求的寫作風格,也是她意欲顛覆的,來自於菁英右派、男性的聲音。」
蔣亞妮拋出情境:「試想,一個法國主流男性作家,若出生在安妮.艾諾這樣的階級,得到無數的大獎,龔固爾文學獎、諾貝爾文學獎後,會不會不斷書寫、回顧、探討跟責問自己階級的問題呢?還是他就一往無前的走,直直向右,走到《費加洛報》主編旁,跟他們一起喝酒、夜宴?這是有可能的啊。」
顛覆與反抗全然表現在艾諾刻意「反其道而行」的書寫風格,過去她在校教授學生詞藻華美的法國文學作品時,即決意摒棄優美,因為這幫助不了她想寫下的生命經驗。
蔣亞妮如此理解:「她必須把這些東西連根拔除。只有直接地寫、直接地說,她才能夠展示自身承受的撕裂(rift )。」艾諾這麼形容自己書寫的語言:「這樣喧囂的語言傳達了憤怒和嘲笑,甚至是粗魯,一種過度的、謀反滋事的語言。這樣的語言,往往是被羞辱冒犯者用以回擊記憶中他人的鄙視、侮辱,及被侮辱而感到的羞恥(of shame and shame at feeling shame)。」

蔣亞妮歸納,艾諾所遭受的撕裂,除了來自與原生家庭產生的階級落差,更和「她的歡愉、她的月經、她的墮胎」有關。艾諾在致詞提到:「我想要完整描述年輕時我的女性身體所遭遇的一切。」這包括她對於性的探索與快感,以及學生時期非預期懷孕,當時保守的法國政府仍禁止並譴責墮胎手術,使她不得不私下找密醫尋求妊娠中止的方法。她迫切需要將身體發生的一切,被壓抑的記憶、一度無法言說的事情書寫出來。
這股強烈且誠實的念頭一如她在《嫉妒所未知的空白》書中所道:「一直以來,我就渴望無所顧忌的書寫,彷彿預料作品出版的那個時候,我將已死去。如同告別人世前的絕筆,再也沒有外人的評判。」如此決絕的意念,似乎也對應到了她被形容為持手術刀自剖般、精準犀利的寫作筆法。
➤如刀割般精準自剖
值班醫生一現身,揭開這一夜的第二幕。從親眼見證生與死的第一幕,進展到祕密曝光與審判的階段。
他坐在我床上,抬起我的下巴:「妳為什麼幹出這種事?說!為什麼?」他冒著怒火的雙眼盯住我不放。我懇求他不要讓我死去。「看著我!跟我發誓,妳不會再幹這種事。永不再犯!」他狂亂的雙眼讓我以為,如果我不發誓,他會眼睜睜讓我死掉。他拿出處方箋,「妳得到天主醫院。」我說我寧可到診所。他又說了一次「天主醫院」,口氣堅決,像是在表示,像我這種女孩,唯一的去處就是醫院。他向我要診療費。我站不起身,他自行打開我的書桌抽屜,從皮夾裡拿了錢。
(這一幕,幾個月前我曾經書寫過,我剛在一堆文件裡發現那一篇文字。我發現自己使用了相同的字眼,像是「他會眼睜睜讓我死掉」等等。我在廁所流產的一幕,我也用了相同的比喻,比如炸彈或手榴彈爆炸,或是酒桶的木塞爆開。當你沒法子用其他的語彙去描述,某個畫面就確切代表了一切經過,沒有別的可能性,不啻證明,我確實經驗的過程,正是如此。)
——安妮.艾諾《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
諾獎評審對艾諾的評語是「手術刀式的精準筆法」,蔣亞妮認為艾諾像操刀的外科醫師,卻刀口朝內,將自己剖開,讓讀者清楚看見她的寫作與血肉之軀的關係。這不免帶有殘忍的意味:「安妮的作品讀起來很殘忍,那個殘忍,其實並非關於故事發生什麼——不是墮胎,不是失戀、不是崩潰、不是離婚,都不是。她在切割自己,她同時也在切割時間。」這份殘忍,正是蔣亞妮口中最迷人以及讚譽實至名歸之處。
「她非常有意識自己正在玩弄時間。」如何玩弄?「她隔著時空跟過往同樣是書寫者的安妮.艾諾對寫。」蔣亞妮說。

艾諾在《嫉妒所未知的空白》裡,描寫自己憑空想像47歲情敵的樣貌與姿態。她認為寫作就像「為了生命中的一段日子下標題,也許就是掌握這段時期的方式。」蔣亞妮評析,2000年前後,艾諾作品中最重要、最大的變革就是開始頻繁使用括號,用以區別過往(括號外的描述)與寫作當下(括號內的描述)。這就是她將自己剖開得更細緻、進行跨時空對寫的方法。此外,艾諾也往往使用第一人稱,達到讓讀者身歷其境的臨場感。「這是她報復性、挑戰性的寫作形式。她會直接地『霸凌』你的閱讀,但是非常痛快。 」蔣亞妮小結。
無論是面對父母的逝世、在愛戀中狂熱折磨、墮胎的痛苦與不安,艾諾願意在事件發生後的某一日,再度翻開日記,撬開記憶的門鎖。透過書寫,她得以讓私己的感受和記憶為人所知,一如《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結語所寫的:「將我的身體、感覺、想法轉化為文字,也就是某種清楚易懂、普遍性的東西,好讓我的生命完完全全融進其他人的腦海和生活。」這或許是她書寫時懷抱的另一目的,揭露與分享難以忘懷的衝擊記憶。
➤「滯後」的書寫
(我之所以寫下這些文字,似乎只為了最後要描述1964年1月,發生在巴黎17區的一切。就像15歲那年的我,不過是為了一、兩個未來的願景而活著;為了到遠方旅行,為了做愛。我還不曉得會用那些字眼。我還不曉得自己會寫下什麼。我想延緩自己動筆的時刻,繼續維持等待的狀態。也許,我懼怕書寫會讓所有景象崩解消逝,就像性慾在高潮後馬上蕩然無存。)
——安妮.艾諾《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
「在時間的糾結裡面,有些東西必須隔著很遠才能進行。」蔣亞妮以「滯後」一詞來形容艾諾書寫時機的選擇,並認為,這或許是她在迫切渴望書寫下,仍然選擇延緩和等待的原因。
透過「滯後」的寫作方式,反覆思索、確認自己該如何揀選漫長的記憶去構築當年的場景。由此,在艾諾的書寫中,讀者可窺見她整理思路的過程。事過境遷後,艾諾願意回到蔣亞妮稱之為「難纏」的時刻,提取與書寫:透過《嫉妒所未知的空白》坦白曾經對前愛人的新歡有過發狂的強烈嫉妒,在《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真實記下「女人所承受的暴力」、墮胎經驗刻骨銘心的過程。
蔣亞妮認為艾諾「用書寫讓自己意識」,而她試圖「操控時間」的方式,其實並非明確劃分出過去與未來的交界,「而是把時間消弭」。
活動最後,蔣亞妮引述了《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段落作結:
我從不覺得自己犯了罪。我唯一譴責自己的部分,是我竟然讓這種事發生,卻不曾回顧這段經歷,就像一份被白白糟蹋的禮物。藉著這本書,我消除了這僅有的罪惡感。我所經歷的一切,包含了社會與心理的起因,但是其中有個理由,我再確定不過:正是發生了這種事,我才能有所頓悟。
——安妮.艾諾《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
或許寫作之於艾諾,便是依據真實生命,打造「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多重宇宙的方式吧。●
|
2022諾貝爾文學桂冠 安妮.艾諾經典小說 (2冊合售) 作者簡介:安妮.艾諾 譯者簡介:張穎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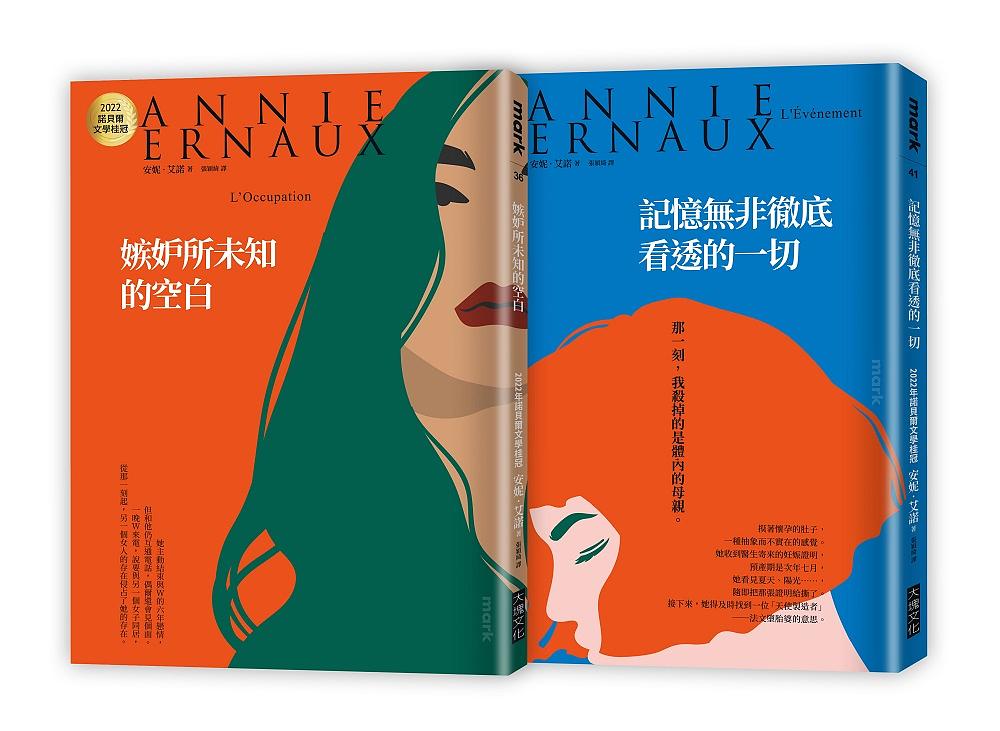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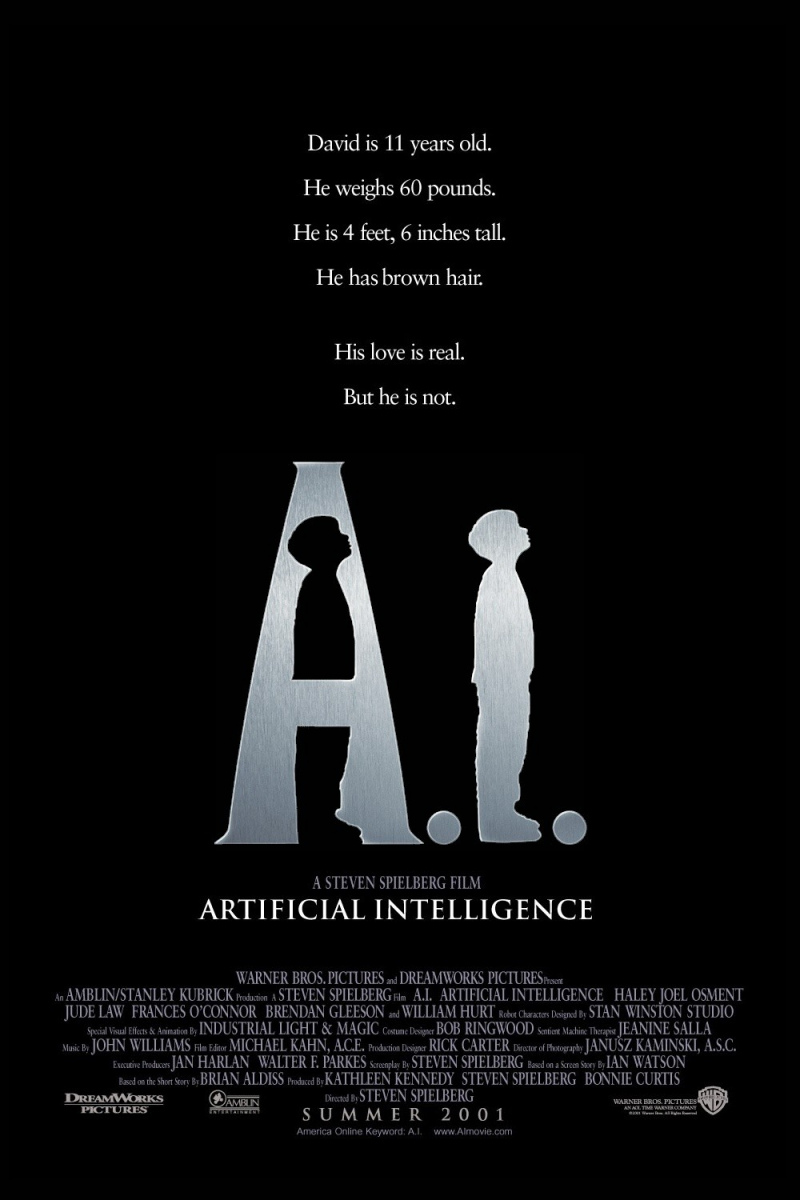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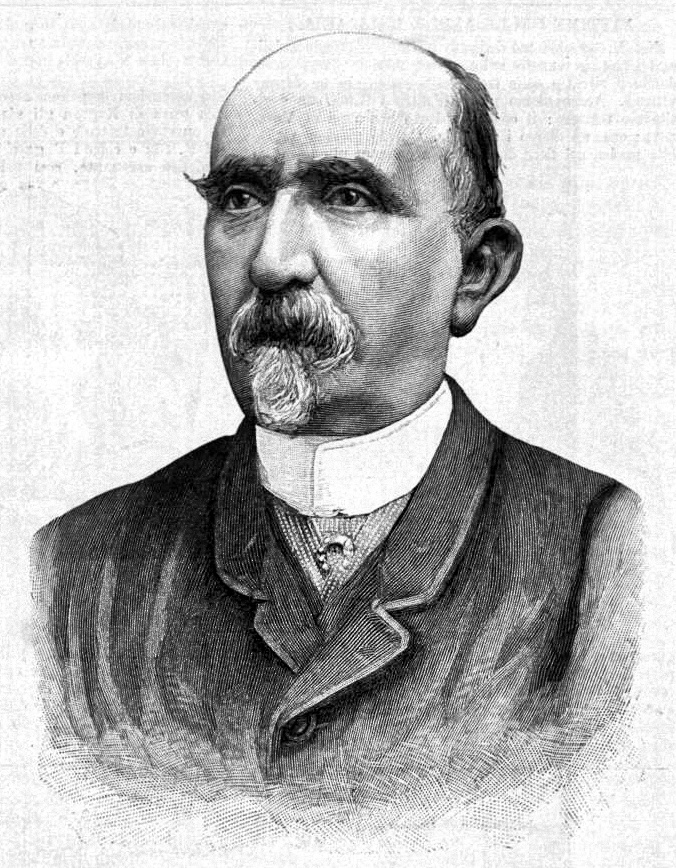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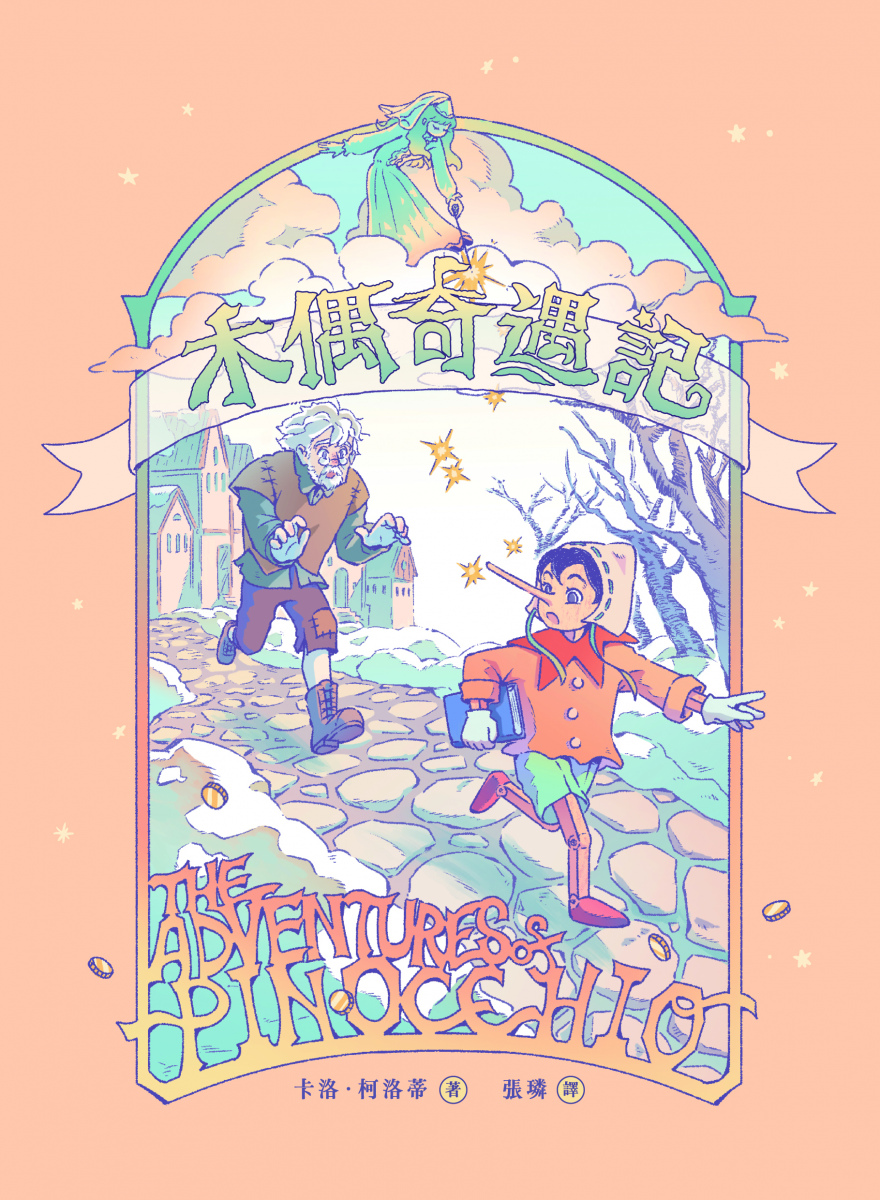
書評》話語的凝聚:讀《阿拉伯人三千年》
過去20年來,我們對於阿拉伯世界有許多刻板印象式的想像:從浮誇的海灣石油富豪到西方媒體中可怕的恐怖分子。從伊拉克到摩洛哥的數十個國家都被我們劃分為「阿拉伯國家」,彷彿他們在某種烏托邦狀態下應該統一成為一個國家。我們很少思考,到底什麼是阿拉伯人?放眼全球,很少有個民族像阿拉伯這樣用同一種語言卻又破碎成這麼多國家,而「阿拉伯民族」似乎又是一種共同體。
提姆.麥金塔-史密斯(Tim Mackintosh-Smith)這本《阿拉伯人三千年》,博學地探究了這個問題。這不是我們一般接觸到的通俗歷史,更像是一部帶著年份的探索之旅。打開厚重的700頁,彷彿拉開一張巨大而華麗的地毯,然而千萬別被厚重嚇壞,作者在書中提問的問題很直接簡單:究竟什麼是阿拉伯人?構成阿拉伯人的核心要素是什麼?而3000年以來,阿拉伯人這個身分/概念面臨什麼樣的挑戰與轉折?
要回答這樣的問題不容易,作者不是躲在西方學院的普通學究,而是長年在阿拉伯生活的學者,他在葉門旅居了將近40年時間,阿拉伯語好到足以「辨認當地硬幣上的拼寫錯誤」。而旅居葉門也讓他對阿拉伯有獨特的觀察視角——南葉門在伊斯蘭創教之前有自己的古代文明與身分,有種帶有距離又不會太遠的視角。而葉門就像是阿拉伯世界的迷你版:在歷史上大部分時間是分裂破碎的狀態。
➤話語凝聚出的認同體
一如「話語」將阿拉伯人給凝聚起來,本書不拘泥於歷史流水帳細節,而是直指問題核心的寫作方式,也「凝聚」了阿拉伯人豐富而複雜的3000年歷史。阿拉伯人的文化核心是阿拉伯語,而且必須要唸出來,話語(聲音)在阿拉伯語的重要性無可比擬。只消看看這些案例:阿拉伯這個字本身就是指「會說阿拉伯語的人」;而先知穆罕默德受到啟示的第一件事,就是安拉要求他「誦」;伊斯蘭召喚人們祈禱的方式是由專人爬到清真寺高處,高聲呼喚(現在當然有了擴音器);《古蘭經》最早還沒有集結成冊時也是採用口耳相傳。這裡的話語是指高級阿拉伯語,用作者的話說是:「豐富、奇異、幽微、催眠、困難到令人抓狂的」,是大阿拉伯認同最核心的催化劑。
這本書也是,短短700多頁是不可能講完這麼廣大土地與這麼多部落、國家、社群的歷史。但作者的敘述「凝聚」了這3000年來的重點與脈絡,並且加上深刻而旁徵博引的評論,使得這本書流暢又發人深省,就像是誦讀阿拉伯詩詞本身優美而精彩,沒有令人厭煩背誦的流水帳,而是專注著把阿拉伯人的故事娓娓道來。
阿拉伯人歷史上有三次最強大的「凝聚」,第一次是高級阿拉伯語在西元前5世紀有了雛形,第二次無疑是先知穆罕默德(PUBH)創立伊斯蘭教,第三次則是埃及總統納瑟(Gamal Abdel Nasser)透過無線電廣播向全阿拉伯世界放送阿拉伯民族主義。
穆罕默德創教的重要性毫無疑問,而話語力量在《古蘭經》中表現無遺,相比於他的兩個亞伯拉罕宗教前輩,《古蘭經》非常講究誦讀,更不要說先知本人其實是不識字的。伊斯蘭的「凝聚」力量讓阿拉伯人在7世紀橫掃了整個西亞地區,並建立起前所未有的大帝國。納瑟則是用迷人的語言掌握力:高級阿拉伯語與埃及方言雙聲道,搭配在1956年開始普及化的收音機,放送他的民族主義訊息,使得整個阿拉伯世界如癡如醉。但納瑟的政治成就跟先知完全無法相提並論,他在葉門、六日戰爭、敘利亞的各種失敗,透露了阿拉伯人難以統一的現實。
除了上述三個曇花一現的時間之外,阿拉伯人都是一盤散沙,而且阿拉伯帝國在創立200年後,半島上的阿拉伯人就逐漸退出歷史舞台,在宗教、政治上都越來越無足輕重。政治軍事上被引入的突厥奴隸喧賓奪主,真正在近代統一這片土地的是鄂圖曼人。而宗教上,伊斯蘭在10世紀之後晉身成為世界型宗教,脫離了阿拉伯人的掌控。
但阿拉伯人最偉大的成就大概在「擴散」,不僅是話語的擴散,還是移民的擴散。阿拉伯帝國在擴張期間,將從伊拉克到摩洛哥大片不同土地的人給「阿拉伯化」,作者這麼說道:「他們的源頭是一支島嶼種族,但現實……有趣多了;源頭紛繁眾多,種族不是一支種族,島嶼甚至不是一座島。」事實上,阿拉伯世界不同的人群儘管都認可高級阿拉伯語,但他們日常生活中都操著不同的方言,差異甚大。阿拉伯人既是統一的,又是分裂的。
➤阿拉伯的絕望與希望
語言的確讓阿拉伯人進入現代文明時遭遇了一些困境,作者很有見解地提到:從1455年古騰堡發行第一本印刷版聖經,到1822年埃及設立第一個官方印刷廠,整整350年,多數阿拉伯文使用者都跟印刷術完全隔絕。這其中有阿拉伯文本身的非戰之罪,因為阿拉伯字母有大量的音標,以當時的印刷術刻起來成本過高,而沒有這些音標會有大量的歧異。想像一下阿拉伯文使用者有350年無法使用網路,這會對一個文明造成多大的影響。作者並在最後諷刺阿拉伯人從沒有印刷術的「前真相」時代,直接跳到網際網路的「後真相」時代。
這裡要特別指出,了解阿拉伯人為何如此,也是這本書最重要的價值之一。本書花了整整4個章節的篇幅,探討伊斯蘭創教以前的阿拉伯世界。古老的習俗、族裔分野以及部落文化至今仍在幽微影響阿拉伯人,我們仍可以從今天的問題中找到原始的影子。
然而,作者在敘述完20世紀阿拉伯世界的戰爭、殘殺、獨裁統治等各種不幸的事件後不禁問道:600年難道不夠一個民族擺脫宿命?西元7世紀阿拉伯人被波斯與拜占庭帝國夾擊,在中世紀被突厥王朝,在冷戰則被美蘇。多數阿拉伯人仍活在一個又一個獨裁的統治者底下,即便2009年「阿拉伯之春」爆發後一度產生改變的可能,但阿拉伯世界後來又再度回到了往日絕望的軌跡。
作者在行文中也透露了一些希望:在最遠離故鄉的地方,阿拉伯人創造出驚人的文化奇蹟。例如一名移民到蘇門答臘的阿拔斯後裔阿布杜拉的阿拉伯文墓碑,這塊墓碑來自印度西北方的坎貝港,這裡盛產精緻大理石的墓碑,任何足夠負擔經費的人可以預訂墓碑上面刻上任何想要的《古蘭經》經文(偶爾加上波斯詩人的詩句),乘著每年的季風交替完成墓誌銘訂單與貨物交易,而買家則以此證明自己是一個富有的國際文化成員。又或者西班牙安達路西亞在伊斯蘭時期所產生的輝煌,讓今日西班牙語乃至於英語都有著可觀的阿拉伯語單字。
阿拉伯人也不至於妄自菲薄,作者在書末敏銳地說道:「(阿拉伯人)會在自身的歷史看到閃光……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世界主義兼容並蓄,公民社會不是西方的一部分,是他們自身歷史的一部分。」閱讀這本《阿拉伯人三千年》能讓讀者真正深入了解阿拉伯人,探索這個獨特、偉大、命運多舛與充滿挑戰,經由一個話語所凝聚的共同體。●
Arabs: A 3000-Year History of Peoples, Tribes and Empires
作者:提姆•麥金塔―史密斯(Tim Mackintosh-Smith)
譯者:吳莉君
出版:臉譜出版
定價:105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提姆•麥金塔―史密斯
英國阿拉伯語學者和譯者,阿拉伯文學文庫(Library of Arabic Literature)資深學者,英國《每日電訊報》譽為「沙那的智者」。著有多本關於中東的得獎著作,包括《與丹吉爾人同行--追尋中世紀旅行家伊本.巴圖塔的足跡》、《葉門:字典國度的奇幻之旅》。現居葉門,至今已旅居阿拉伯世界近四十年。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