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寫出一條大家都能戀愛的路:朴相映╳陳雪對談側記
韓國作家日前來到台灣舉辦分享會「當我們在創作的路上:戀愛,寫作,還有我自己」,台灣作家陳雪應邀同台對談。對談過程中,兩人相互分享了跨越性別身分、世代、國籍的小說家們,如何在各自的寫作崗位上持續嘗試開啟與社會的對話空間。
朴相映憶起2018年在韓國出版第一部小說集《無人知曉的藝術家之淚和宰桐義大利麵》,當時的相關報導並未刊登他本人的照片,反而選用了朴贊郁電影中女同性戀情慾場景的劇照。朴相映無奈笑談自己那張被缺席的臉與格格不入的配圖,彷彿這已是身為南韓酷兒小說家所面對的日常。
在長年守舊且恐同的南韓社會中,酷兒文化的呈現總是偏向悲傷、憤怒與沉重。朴相映對於這樣刻板而單一的框架感到不滿:「酷兒是特別、同時也是普通的存在。」因此,朴相映致力呈現更豐富多樣的酷兒情感面貌,也同時透過寫作面對自我的課題。
然而問題是,如何在如此保守的社會風氣下書寫同性戀主題呢?朴相映的寫作策略,是輕盈。如同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所謂文學的「輕」,其實是在外界與內在之中尋求和諧的方法。朴相映的小說擅長以幽默、犀利和輕快的筆調,捕捉當代酷兒群體在現實世界中生存的歡樂與哀愁。南韓國內主流媒體甚至以「新人類」的稱號來介紹朴相映,他笑道:「我感覺大家認為我的登場很突兀,連我自己都覺得有點好笑。」不過他也從此下定決心,希望找到更有趣的方式持續書寫。
在台灣書市,繼《在熙、燒酒,我,還有冰箱裡的藍莓與菸》(2019)、《想成為一次元》(2021)與《信任的模樣》(2022),今年朴相映的出道作《無人知曉的藝術家之淚和宰桐義大利麵》終於翻譯出版,與台灣讀者相遇。陳雪表示,閱完朴相映的作品後,最敬佩的便是他處理嚴肅議題時的輕盈:「就像用槓桿把沉重的石頭輕盈的翹起來。」在歡快的閱讀過程中,朴相映讓讀者卸下心防傾聽他說故事,也心甘情願為他筆下的人物流淚。

「會不會是因為我不會喝酒?沒有感受過喝醉的輕鬆感?」陳雪笑著反思自己一路以來的創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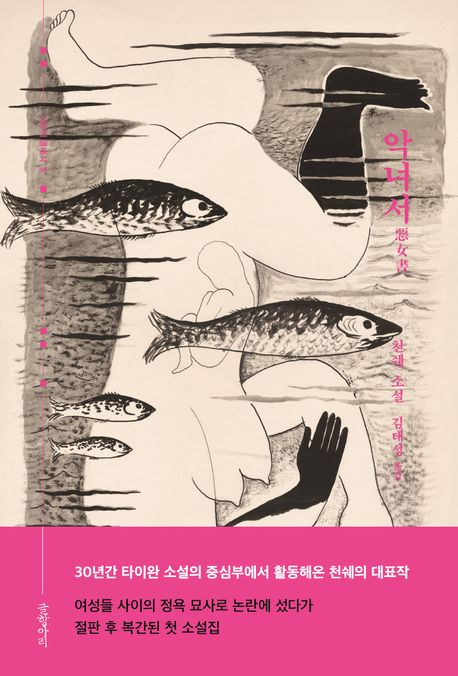
1994年,陳雪出版第一本作品《惡女書》,同樣以突破刻板的同性戀文學書寫方式震撼文壇。90年代的台灣同志文學,大部分偏向以痛苦的吶喊來迫使人們關注,而陳雪卻是赤裎揭露了女同性戀的情慾。
提起出道作,陳雪回想起當年出版時遭受過的令創作者感到悲憤的困境,例如編輯在閱讀中感受到不適,作品差點無法順利出版;小說販售時被要求封膜,並貼上十八禁貼紙等等。如今30年過去,《惡女書》也在今年於南韓翻譯出版。聽完後,朴相映深有所感的說:「我經常在想,是因為有陳雪這樣的前輩作家站在前頭,我才能夠站在這裡如此自由的書寫。」
社會風氣的轉變需要眾人的努力,而作家所擁有的寫作力量,即是藉由文學持續和人們互動對話。2019年台灣正式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然而陳雪認為作家們的使命尚未完結。朴相映問及台灣後同婚時代的酷兒文學,陳雪分享自己在台灣文學獎場域中的觀察。她注意到,這類創作目前似乎仍以約砲、一夜情、網路交友等情慾書寫為大宗,另一方面她也留意到,女同志書寫數量有下降的現象。

同婚通過之後,同性戀主題還能夠書寫什麼呢?在朴相映的小說裡,充滿著在現實中力求生存或迷惘的生活難題,諸如:成為反同母親長照者的gay,如何在居家照護、工作與愛情中取得平衡;COVID疫情下經濟受創的同志酒吧,連帶影響的是同志族群平時重要的生活圈;男同志情侶如何在首爾買房,又避免讓人起疑⋯⋯
陳雪因此發現了台灣酷兒文學各種發展的可能:「沿著同志(婚姻)這條主軸向外擴展的議題」,例如婚姻內部的問題、同性與異性戀在婚姻中的視角差異、同志伴侶生育求子等等。「我也很期待看到(同志)離婚文學啊!」陳雪語畢,全場一陣爆笑。

講座尾聲,朴相映表示自己在閱讀陳雪不同時期的作品後,對於她在創作歷程中豐富的變化感到驚艷。陳雪笑著回應:「我是雙子座AB型,我喜歡改變自己。」身為作家,她期望作品能與當代不同年齡層、領域的讀者互動。因此即便面對改變可能造成讀者的流失,陳雪依然會努力的嘗試不同的寫作主題、風格和方法。
得到前輩作家的啟發和鼓勵,朴相映彷彿鬆了一口氣,他透露自己目前正在撰寫的新作是一本關於1940年代女性財閥的懸疑小說:「一開始想成為作家是因為阿嘉莎・克莉絲蒂,一直想嘗試推理小說。」
從首爾到台北,從《惡女書》到《無人知曉的藝術家之淚和宰桐義大利麵》,朴相映與陳雪兩人都仍持續在寫作中,證明各種(性)少數的存在是如此特別又普通。或許文學不僅提供了作者與讀者在紛亂的世界中面對自身課題的力量,也同時為人們開啟了相互理解和對話的可能。●

|
|
|
作者簡介:朴相映 1988年出生於韓國大邱。在成均館大學(Sungkyunkwan University)主修法語文學和新聞傳播學,在東國大學研究所學習文藝創作。26歲時進入第一家公司工作,後來在雜誌社、廣告代理公司、諮詢公司等多種業界,以正式員工和非正式員工之間的身分工作了7年,但從未確信那是他所應存在的地方;經歷上班族的生涯後,領悟到工作不過是一種社畜生活,開始夢想著辭職。2016年憑藉短篇小說〈尋找芭黎絲.希爾頓〉獲得文學村新人獎及文學村青年作家獎,2018年推出首部小說集《無人知曉的藝術家之淚和宰桐義大利麵》更同時奪得第9屆文學村青年作家獎及許筠文學作家獎,一躍成為韓國同志文學代表作家。2019年再以〈一片石斑,宇宙的味道〉獲得第10屆青年作家獎首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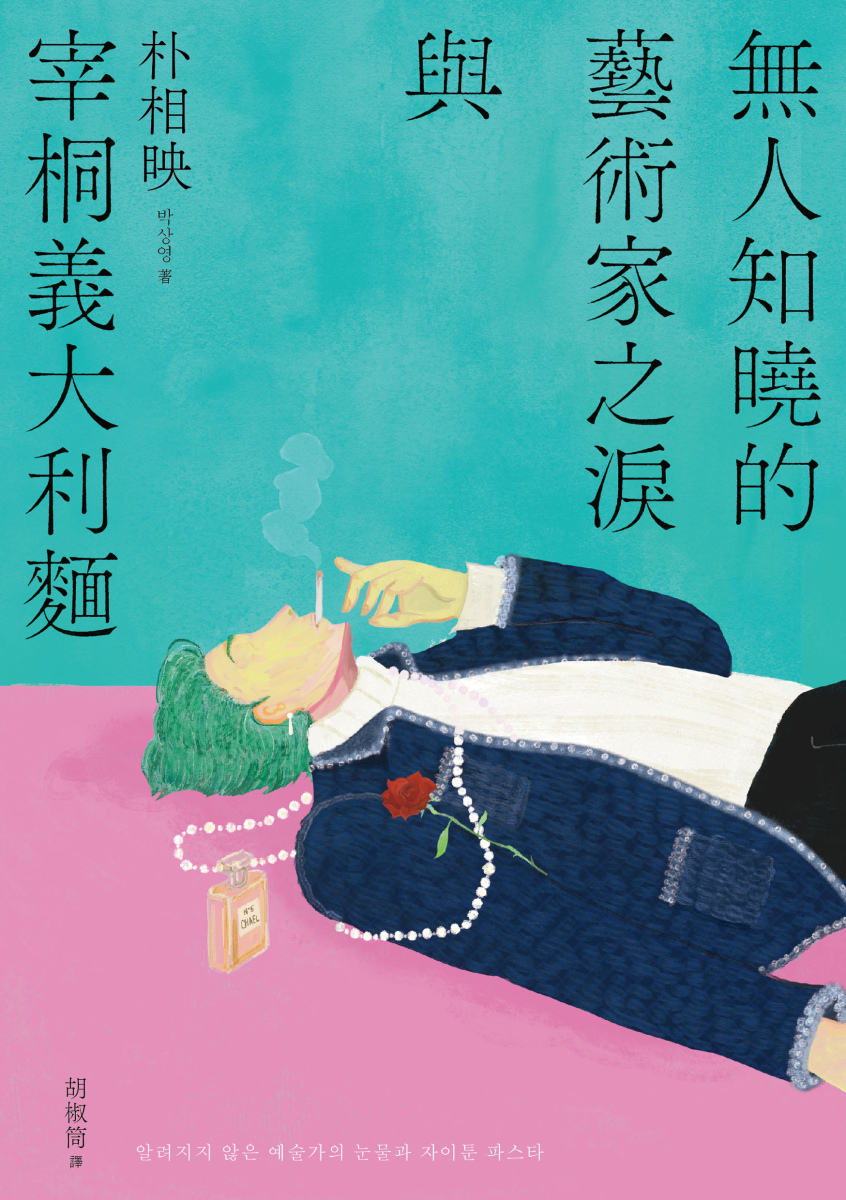 無人知曉的藝術家之淚和宰桐義大利麵
無人知曉的藝術家之淚和宰桐義大利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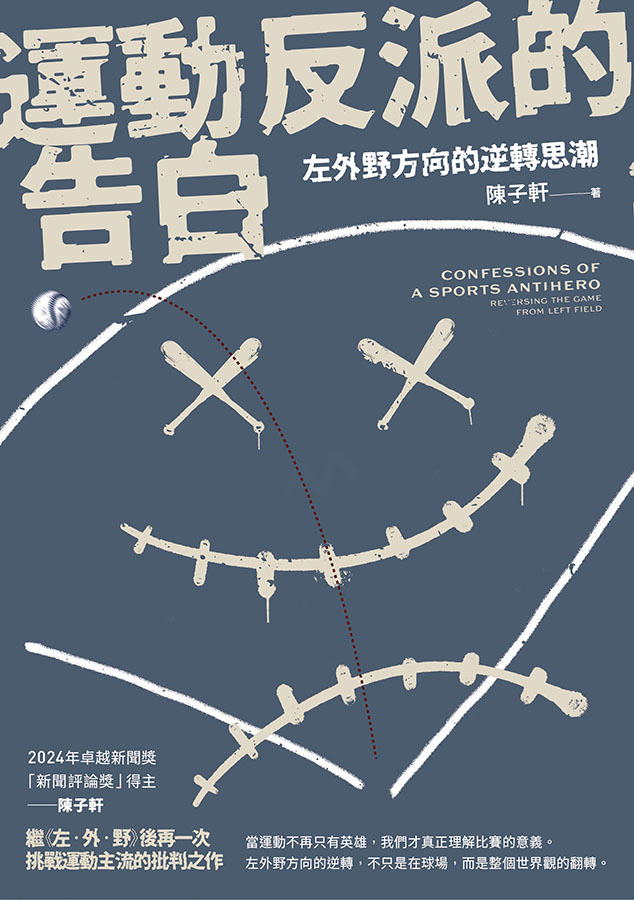 運動反派的告白 :左外野方向的逆轉思潮
運動反派的告白 :左外野方向的逆轉思潮
報導》首屆臺灣國際兒少書展開幕!義大利主題國、臺中主題城市,邀請民眾跨越城市邊界,感受閱讀盛宴
2025第1屆臺灣國際兒少書展於今(18)日至21日於臺中國際展覽館展開,以「跨越城市.閱讀無界(Crossing Cities, Reading without Borders)」為主題,由臺中市擔任首屆書展主題城市,並以義大利為主題國。書展期間將有來自14個國家的作家、插畫家、版權人、出版專業人士來台,共127家參展單位,預計舉辦超過200場講座、手作活動、工作坊等,邀請民眾一起感受閱讀無限延伸的可能。
文化部長李遠說,一個國家如何對待、教育兒童、青少年,就可以知道這個國家文化及文明的進步。所以,兒少政策是他加速推動進行的工作之一,例如「繪本新秀獎勵」、「繪本學校」、「金繪獎」等培育、獎勵繪本創作者的政策,到推出鼓勵高中生創作的「青漫獎」、成立「公共電視兒少台」,以及目前正在規劃設計的「國家兒童未來館」等,希望讓現在的孩子能及早享受所有的文化政策、活動及設施。
李遠分享自己寫作與陪伴孩子閱讀的經驗,相信跟他的孩子差不多年紀的父母,因為閱讀而有了不同的教養觀念,也讓他興起舉辦兒少書展的想法。而首屆國際兒少書展選擇在臺中舉辦,除了南來北往的地利之便,臺中還擁有包括國家漫畫博物館籌備處、國立臺灣美術館、國立臺灣交響樂團等文化場所資源,期待能吸引更多人潮,讓國際兒少書展成為台北國際書展後的第2大書展。
➤九大主題展區,繽紛繪本、童書、漫畫、文學、影像,還有旋轉木馬!
此次書展主題展區有:義大利主題國館、繪本故事館、童書主題館、台灣漫畫館、文學書區、公民書區、主題城市館、文化部附屬館所、得獎作品館等九大主題展區。
義大利主題國館帶來義大利優質的童書、插畫與民眾分享,並舉辦6場以義大利為主題的文化活動,民眾可以近距離體驗義大利的美麗與魅力。繪本故事館結合沉浸式影像展、圖繪互動活動,展示以夢想為主題的100本臺灣原創繪本及16場說故事活動,由紙本書出發加入時間的流轉與空間的漸變,開啟不同繪本的體驗。
一向在台北國際書展相當受注目及歡迎的「公民書區」,由獨立出版聯盟、台灣勞工陣線協會、台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攜手合作,推出「獨字樂園PLUS」,與15家獨立書店合作,精選百種以上書目,更將充氣溜滑梯、旋轉木馬、海盜船等都搬進書展會場。
得獎作品館則展示2025年第49屆金鼎獎得獎作品、第16屆金漫獎入圍作品、2024Openbook好書獎得獎作品、文化部文學創作獎勵作品等重要獎項的得獎與入圍作品。讀者可以享受到不同類別書籍的精選好書。同時,也特別介紹兩位在各自領域具有重要貢獻的老師—鄭明進老師與黃健和老師,讓民眾能更深入了解創作、出版產業的脈絡與發展。
由文策院策劃的「臺漫大發現 勇闖故事島」展區,規劃《海巫事務所》、《台灣特有種》、《Vtuber孔子》、《引路人》主題展區,結合展示與互動設計,再現經典場景與角色,讓讀者在趣味互動中感受臺漫的魅力。文學書區以「文學與未來的距離」為題,推出至少40本以上的臺灣兒少文學原創書單,呼應聯合國SDGs的未來願景,展現臺灣的全球公民意識。
「臺中主題城市館」以「從林開始:書頁裡的奇幻旅程」為題,呼應即將陸續開館的臺中綠美圖與童書之森,也融入「從0開始閱讀」意象。以「臺中大百科」為選書主軸,從信仰文化、人文故事、水文與生態、時光風景等精選好書,邀請讀者透過閱讀看見臺中的故事。
集結國家人權博物館、國家漫畫博物館籌備處、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歷史博物館、臺南生活美學館、臺東生活美學館等7個館所的文化部附屬館所聯合展區,展場以「書籍堆疊意象」貫穿全區,青春舞台、筆型不倒翁構成書寫叢林,現場參加活動就有機會扭蛋換禮物,是專屬兒少的多元文化閱讀派對,更是一段充滿探索與能量的青春文化冒險。
文化部政務次長李靜慧於開幕記者會表示,書展是促進出版產業蓬勃及民眾閱讀習慣提升,兩者間良性循環的一個重要平台,因此文化部長期在台北辦理國際書展,至今已具相當規模,也是亞洲數一數二的大型國際書展。基於過去良好的根基,文化部與出版界、各縣市經過長達1年的討論後,推出第2個以兒童、青少年為主題的國際書展,並以文化平權為概念,選擇每一年與不同的城市合作辦理,讓具國際規模的書展能夠輪流到臺灣各個城市旅行。「文化部會全力辦好每一屆臺灣國際兒少書展,繼續推廣閱讀、照顧出版產業,持續讓良性循環產生」,邀請全國觀眾在接下來4天,盡情享受出版界為大家準備好的心靈饗宴。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長曾能汀說,展會期間為響應文化平權,邀請偏鄉學校800人次的孩子們來到書展;同時,許多公共圖書館館員也會來到書展進行選書。「臺中一定會以熱情及旺盛的購買力作為最好的回應,不會讓大家失望」。
➤六大節目區,豐富講座、工作坊、直播,以及知名國際作家分享對話
書展開始前,自6月中至今已舉辦一連串講座、創作分享會等系列暖身活動,書展期間節目更加豐富,包括:銀河主舞台、星語沙龍、童夢沙龍、雲朵沙龍、直播室及跨域媒合等六個節目區。特別是以下幾場講座邀請到資歷豐厚、享譽國際的作家、畫家、策展人、評論者等,令人期待。以下為Openbook閱讀誌為讀者精選的國際作家活動:
時間:9/18(四)14:15–15:15
地點:銀河主舞台
主講:寶拉・米里亞姆・維斯康蒂(Paola Miryam Visconti)。
講者介紹:義大利作家、《Dynowish》奇幻系列的作者,並將作品拓展至動畫與跨媒體項目,目前正開發一部國際動畫影集。
時間:9/18(四)15:30-16:30
地點:銀河主舞台
主講:埃馬努埃拉・納瓦(Emanuela Nava)
講者介紹:義大利著名兒童作家,納瓦出版了一百多本兒童與青少年讀物。透過寓言與以動物為主角的故事,以細膩的方式探討如疾病、家庭暴力等困難議題。曾獲得包括葛林薩納・卡武爾獎(Grinzane Cavour Prize)在內的多項文學獎項。也曾擔任知名兒童電視節目《藍樹》(L'Albero Azzurro)的編劇與撰稿人,並為成人開設朗讀課程,參與教師培訓活動。
時間:9/18(四)16:45-17:45
地點:銀河主舞台
主講:菲利浦 ・佐丹諾(Philip Giordano)。
講者介紹:義大利自由插畫家,設計書籍封面、兒童玩具與圖書,並涉獵動畫領域。佐丹諾以簡練風格、色彩鮮明的造型見長,配合標誌性人物與圖形化背景,作品具即視辨識度與視覺吸引力。
時間:9/19(五)13:00-14:00
地點:童夢沙龍
主講:思琪・漢歐爾 (Ziggy Hanaor)。
講者介紹:英國作家、編輯與倫敦獨立童書出版社Cicada Books的創辦人。歐漢爾在 2009 年因女兒出生後,從編輯職轉向創立自己的出版社,起初以設計/贈禮書為主,逐步擴展為以圖畫書與非虛構童書為主的出版品類。
時間:9/19(五)15:30-16:30
地點:童夢沙龍
主講:莉迪亞·布蘭科維琪(Lidia Branković)。
講者介紹:出生成長於德國柏林,自幼深受都市多元文化啟發。布蘭科維琪不僅是一位作家,還擔任圖畫書插畫家,擅長結合類比與數位技術,風格溫暖而略帶超現實感,擁有清晰的概念性。
時間:9/20(六)13:00-14:00
地點:童夢沙龍
主講:莉迪亞·布蘭科維琪(Lidia Branković)&思琪・漢歐爾 (Ziggy Hanaor)
時間:9/21(日)15:30-16:30
地點:銀河主舞台
主講:廣松由希子。
講者介紹:出生於1963年,童年在美國洛杉磯,後隨家移居東京成長。曾任兒童家用圖書館(BUNKO)編輯、及千尋美術館(Chihiro Art Museum)策展人與首席編輯,後轉任自由作家、評論家與獨立策展人。
為鼓勵民眾參與兒少書展,文化部推出門票全額抵用金,凡購票入場者,門票金額可全額折抵現場消費,購票入場當日不限金額消費、購買品項,均可抵用;文化幣在兒少書展現場消費亦可點數放大,2點送1點。此外,桃園以北、高雄以南、東部地區民眾,憑參觀當日前後3日,赴臺中市區或自臺中市區出發的大眾運輸乘車證明;離島居民憑赴臺機票、船票;身障人士及陪同者1名;18歲以下、19至22歲憑文化幣者均可免費入場。
現場消費滿1,500元可兌換書展專屬帆布袋1只,每日數量有限,換完為止。歡迎民眾踴躍前往臺中國際展覽館參加首屆臺灣國際兒少書展,詳細活動訊息請參閱「臺灣國際兒少書展」官方網站。●
➤完整系列活動,點擊以下圖片↓↓↓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