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短評》#359 踏上詩意旅程的極品好書懶人包
●偽魚販指南
林楷倫著,寶瓶文化,350元
推薦原因: 文 樂 獨 益
時而素人,時而文青,這些文章的風格像在刮魚鱗,不規則飛噴。作者的確像在cos魚販又cos作家,重點是人生經驗強大,不論胡思亂想還是打嘴炮,都能奇趣橫生。不過光是一本還不知道賣什麼藥,敲碗等待續集先。強烈建議魚攤就是書攤,打卡75折。【內容簡介➤】
●行走的人
獲致幸福的恬靜藝術
Marcher la vie : Un art tranquille du bonheur
大衛.勒.布雷頓(David le Breton)著,粘耿嘉譯,大田出版,380元
推薦原因: 議 樂 益
行走是人類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點都不特別。但是在作者筆下,我們將發現行走的意義是多元的,是深刻的,是發人省思且充滿詩意的。在閱讀的過程中,讀者彷彿與作者一同在各處走著。除了聆聽他對沿途風景的描述外,我們也一同感受他對於個人與外在世界獨到且相當深刻的體悟。【內容簡介➤】
●入境大廳
陳偉棻著,時報出版,330元
推薦原因: 文 樂
《入境大廳》是一本令人讀來清新且愉悅的旅外文學作品。在外國求學、求職與任職的經驗,成為作者最佳的取材對象與養分,透過書寫散文,帶領讀者來到求學的英國、任職的香港與家鄉臺灣。「機場大廳」成為上述各地的中介站,也是觸發你我感知內心與外國經驗的生命作品。【內容簡介➤】
●不在場證明
Travel as an Alibi
李桐豪著,新經典文化,340元
推薦原因: 樂
職業旅行家用自己的愛憎情愁灌注成一趟趟的旅行,拓展世界的邊界。筆下的旅行又以它們的結構、主題、擬寫凝塑出旅人的身影。行程經過別緻打理,穿梭於異域、故事、案件、人物之間,流線迤邐。經過精心整理的舊文,讓留下的旅行收束在旅人與陌生空間和移動感之間,那種觀望又親密的關係上。一種旅人與旅行互相嗅聞的狀態。【內容簡介➤】
●疫年記西藏
當我們談論天花時我們在談論什麼
唯色著,大塊文化,580元
推薦原因: 知 批 議 樂 獨 益
這是唯色記錄西藏歷史文化與記憶的傑作,也是她對於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下的發想與省思。疫情之下閱讀此書,窺見此時與昔日藏地僧人和民眾的生命點滴。在作者筆下,疫情中的西藏風土更加鮮明,昔日的歷史不只是回憶,也能啟發與撫慰我們的心靈。【內容簡介➤】
●蝴蝶的重量
奈莉.沙克絲詩選
奈莉.沙克絲(Nelly Sachs)著,陳黎、張芬齡譯,寶瓶文化,380元
推薦原因: 文 獨 益
簡單的文字,直接的譬喻,緊湊的節奏,略帶神祕的轉折,這本沙克絲的詩選有如暗夜潛逃,人奔影喘,清醒得透不過氣來。作者與集中營擦肩而過,劫餘而不作控訴,顯然經驗到了某種超驗。遣詞煉句不重而威,隱隱傳來猶太的共振,格外有股洪荒之感。【內容簡介➤】
●改變世界的紀錄片工作者們
ゲームチェンジング.ドキュメンタリズム: 世界を変えるドキュメンタリー作家たち
Someone's Garden著,雷鎮興譯,行人文化實驗室,680元
推薦原因: 議 樂 益
一本紀錄片工作者的訪談集,有著各自獨特的影像創作觀與思想魅力。因紀錄片屬性特定,書中的討論對話更輻射出全球連動的社會問題,記錄了少為人知或亟待關注的議題。書名上的「改變世界」或許太過雄心,但這些創作者都強帶game changer氣勢,選擇直面資源與注目度都十分邊緣、或者處理起來極度困難的議題,以此重新定義影像、改變社會僵化的規則。【內容簡介➤】
●湧與浪
自由中國號
漫畫:狼七,編劇:食夢蟹,蓋亞文化,240元
推薦原因: 知 樂 益
這部漫畫依然是政府的推動案之一,但與先前所見充滿大內宣氣氛的台漫相較,1950年代的冒險題材確實較為特別。數位青年以一艘造於清末的中式無動力帆船穿越太平洋的旅程,加上這艘船50年後的重生,真人真事組成了穿越未知、尋回失落英雄的兩個命題。事件及其所帶來的傳奇感,具足了轉換成漫畫的條件。時代的動蕩與完成夢想的熱情,兩相激盪,帶我們走出了1950年代臺海的既定印象。【內容簡介➤】
●百年情書
文協時代的啟蒙告白
國立臺灣文學館、林佩蓉、黃小蛋、蔡明諺、黃信彰、邱函妮、陳淑容、陳婉菱、石婉舜、張晏菖、陳佳琦、李家驊、鄭有傑、王嘉玲、黃子恩著,前衛出版,450元
推薦原因: 知 議 樂 益
臺灣文化協會是日治時期臺灣人民建立文化主體性的重要團體,扮演著中介新的外來與現代化知識至臺灣社會的重要橋樑。閱讀本書,就彷彿置身於「百年情書.文協百年特展」的展場中,書中的舊照片、檔案文件、圖畫再次帶領讀者回到1920年代的臺灣社會,一窺當時文協如何使用各種媒體來宣揚新知識,以及藝文活動者如何藉由創作與書寫,一同啟蒙臺灣,建立臺灣在地文化的主體性。【內容簡介➤】
●數位監控
我們如何拿回均衡的科技生活
Slow Computing:Why We Need Balanced Digital Lives
羅布.基欽(Rob Kitchin)、阿里斯泰爾.弗瑞瑟(Alistair Fraser)著,黃開譯,時報出版,480元
推薦原因: 思 議 益
原書名「慢運算」其實才是本書兩位作者的核心論點。他們視「慢運算」為數位時代下的社會運動,以奪回「時間主權」和「數據主權」為目標。書中的論述可說是這場運動的宣言,在不否定數位優點的前提下,指出全然順從數位生活,將對個人、社會帶來的蛀蝕崩毁。本書同時也是運動的指導方針,提供人們重新調整人與數位疆界的策略。那些調整使用數位裝置的方法,或許並不新穎;但若能將作者社運式的言下之意放入心中,轉換核心動能,應該更有可能從過度倚賴數位帶來的不適中逐步解放。【內容簡介➤】
知識性.設計感.批判性.思想性.議題性.實用性.文學性. 閱讀樂趣.獨特性.公益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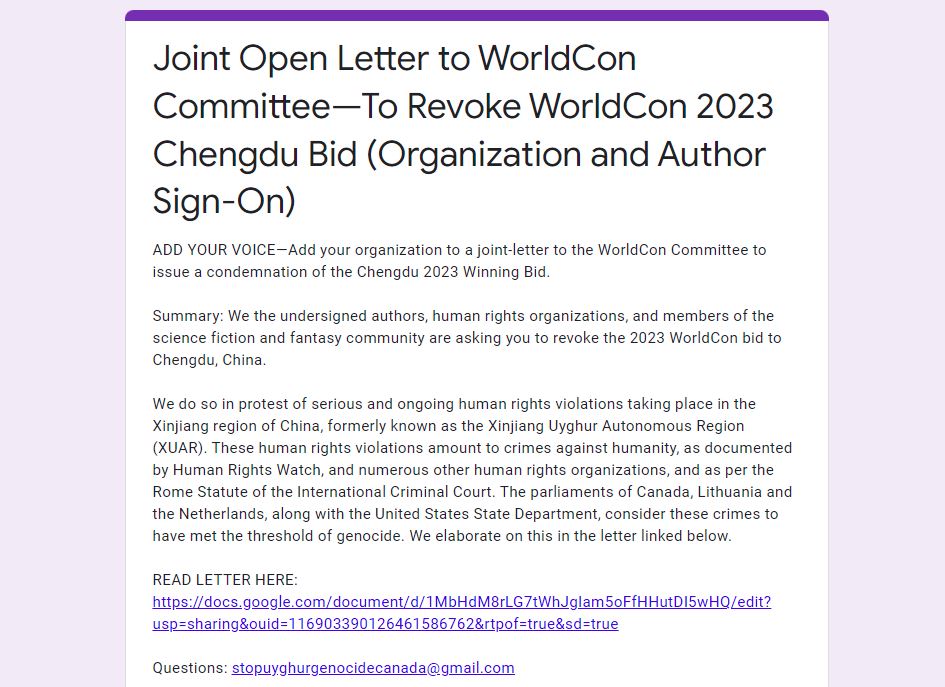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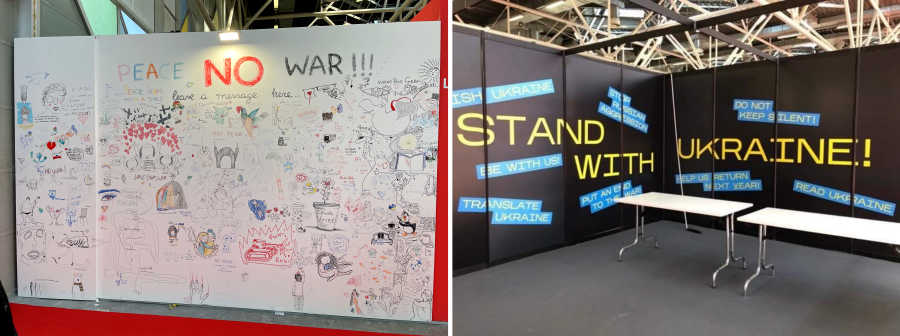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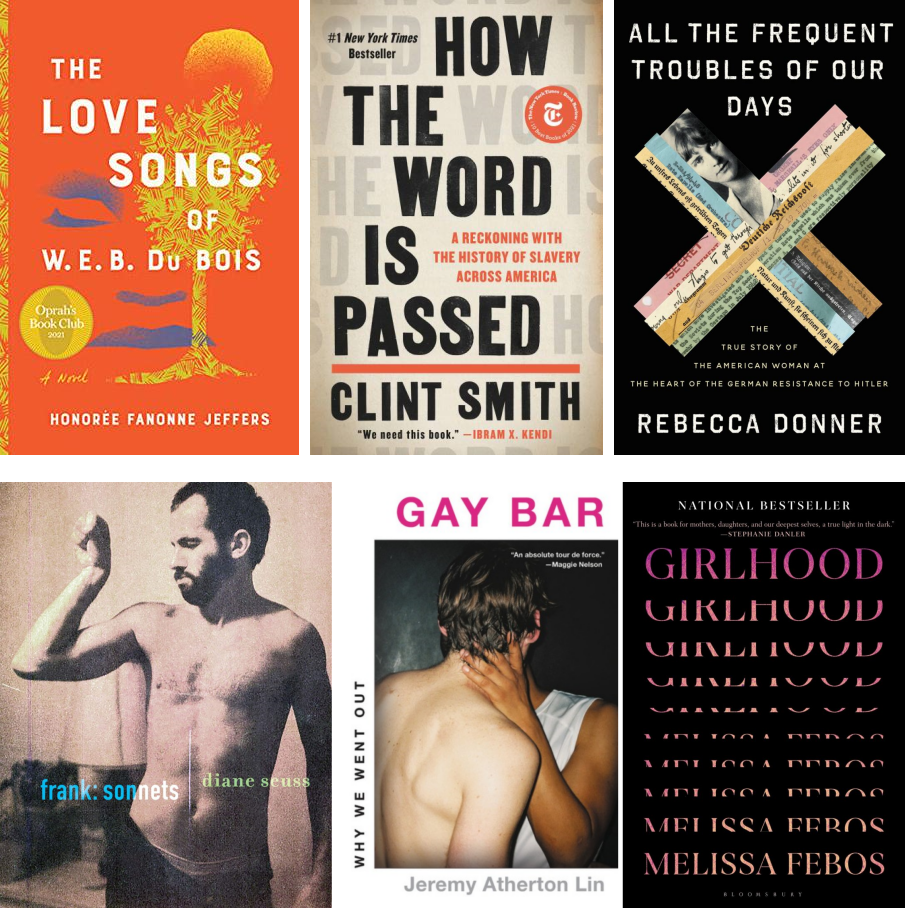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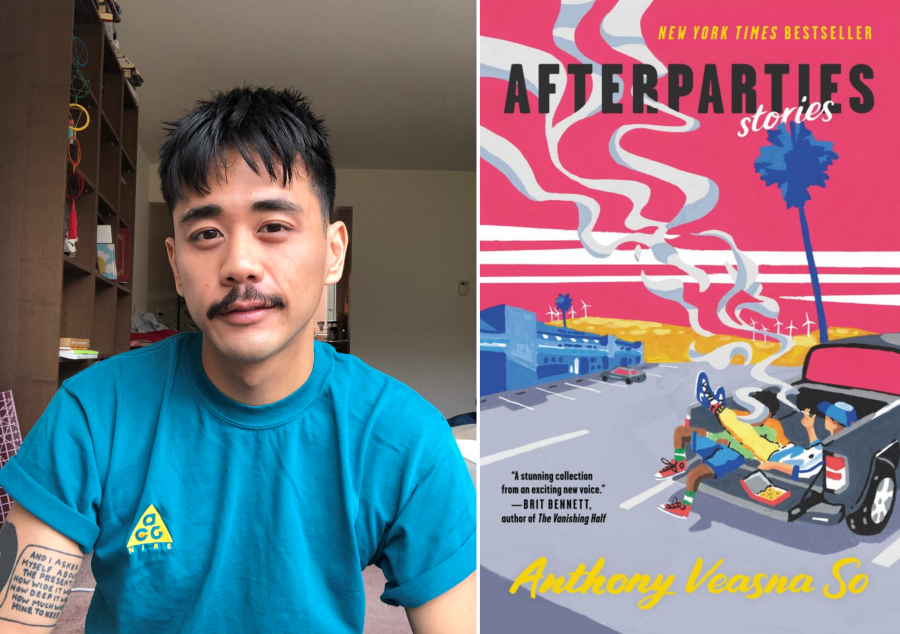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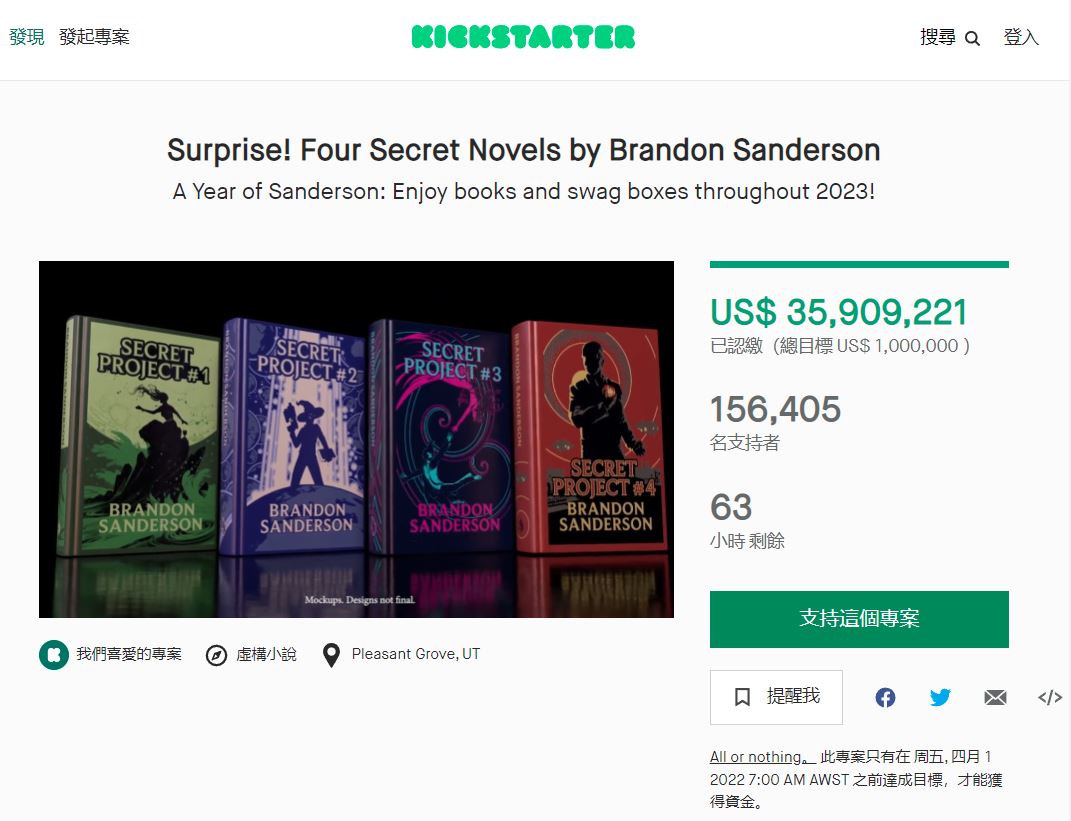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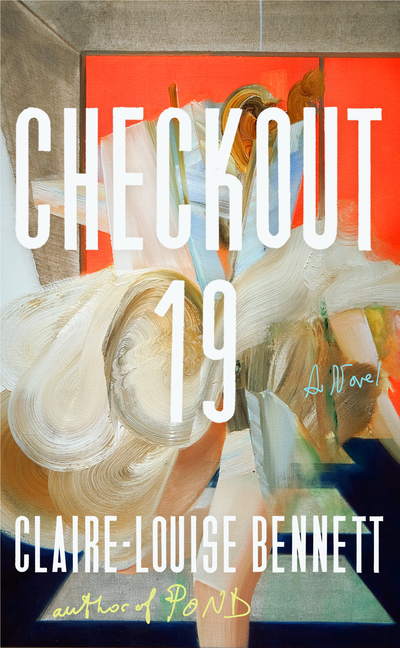 ■2015年以出道作《
■2015年以出道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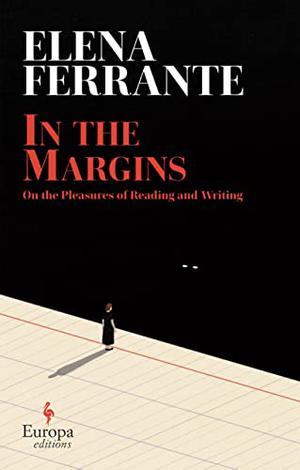 ■以
■以
書.人生.何敬堯》推開恐懼之門:我與人魚、鬼、貓妖
我怕鬼。
我懼怕任何有關恐怖之物。
鬼魂、妖怪、邪魔、異形、貞子、鬼小丑……等等怪物,總讓我毛骨悚然,驚駭萬分。
猶記得童年時,大約五、六歲,常去一家位於溪岸邊的理髮店,店內陰暗角落有一個櫥櫃,櫃內擺放許多漫畫,讓顧客等待時可以自由瀏覽。我很喜歡閱讀櫃內的格鬥漫畫,也在當時喜歡上《城市獵人》漫畫,總是看得不亦樂乎。直到有一天,我拿取櫃內最底層的一本漫畫書,讀到人魚故事。我嚇到寒毛直豎,冷汗直流。
漫畫描述人類吃人肉,劇情鋪陳人肉其實是「人魚之肉」,並畫出某種人魚的外貌如同夜叉惡鬼,雙眼瞪大,滿嘴尖牙,逢人就咬。幼年的我,目睹人魚張牙舞爪的駭人面貌,當下心驚膽跳,連忙將漫畫書放回櫃子。等待理髮的時間,我如坐針氈,一顆心撲通撲通狂跳,凶狠人魚不斷迴游腦海,揮之不去。
「人魚好可怕!」
相較於其他孩童與人魚的第一次接觸是迪士尼的美人魚公主,我與人魚的初次邂逅竟如此提心吊膽。從此,我去理髮店時,再也不敢翻閱櫃內漫畫。我心中浮現黑色幻想,那個書櫃彷彿棲息不祥之物,四周籠罩詭異氣息,只要一靠近就讓我喘不過氣。我總覺得……人魚正躲在書櫃中。
那時,年紀尚幼的我,意識到一件事情:「原來,我很害怕怪物。」隨著年齡增長,我的生活經驗不斷印證此事。
從小到大,只要看到電視上播放的恐怖靈異節目,讀到書中的怪誕情節,或者瀏覽漫畫中的妖怪圖畫,總讓我不寒而慄,甚至晚上還會做噩夢。如果朋友與我一同觀看鬼片,朋友通常不會被戲裡可怕情節嚇到,而是先被我誇張驚嚇的叫聲與動作嚇到,導致朋友觀賞恐怖片的興致全無。
雖然我很害怕鬼,害怕妖怪,害怕任何有關恐怖之物,但是我人生旅途的方向,卻越來越接近鬼怪、妖精、怪物……這類黑色存在。近年來,我在文學創作與研究的道路上,主要以「妖怪、怪異」文化為主軸。
為何我害怕恐怖之物,卻每天鑽研怪物傳說,甚至還寫妖怪小說呢?
就讀清大臺灣文學研究所時,是我開始研究妖怪的起點。當時,我想研究妖怪的其中一個理由,是因為我很好奇,難道恐怖之物存在的意義只是為了嚇人?如果妖怪只是為了嚇人而存在,那麼也許可以針對這點找尋一種對策,讓我不再被妖怪嚇到。於是,我戰戰兢兢推開了恐懼的門扉,踏進黑暗中,期望能找到對抗怪物的法寶。
時至今日,我一步一步學習辨識妖怪的臉龐。雖然我尚未找到「不被怪物嚇到」的妙方,但已經不像從前那樣畏縮面對恐怖之物。
後來得知,童年時閱讀的人魚漫畫,是高橋留美子老師的作品《人魚之森》。故事描述一位漁夫吃人魚肉而永生,他孤單活了數百年,唯一願望是變回普通人類。但是,並非任何人吃了人魚肉都可以永生,如果體質無法適應,就會變成模樣可怕的「半魚人」,兩眼圓凸,尖牙利齒,會瘋狂攻擊他人。我小時候看漫畫,就是被這種半魚人嚇到。
漫畫創作的妖怪,真實存在嗎?我逐漸理解,妖怪的真面目,很多時候來自於人類的創造與想像。妖怪的誕生,呈現了人類對於世間道理、森羅萬物的觀察、期望、恐懼……等等反應。如同高橋留美子漫畫中,追逐人魚肉想獲得永生的人,被慾望驅使,結果卻淪落為醜陋的半魚人。
人們將心中幻影投射於妖怪之身,才創造出千奇百怪的怪物形態。妖怪是「真實的幻想」,蘊含著人類文明的黑暗面向。既然妖怪形體十之八九由人們賦予,那麼不同文化的人們,對於妖怪形象就會有不同想像。
例如,明代畫家蔣應鎬描繪《山海經》的「陵魚」,人面魚身,兩手雙足,正在手舞足蹈,一旁雲朵隱藏著蓬萊山,暗示此境神祕魔幻。
江戶時代古書《和漢三才圖會》十四卷「外夷人物」篇章,描繪「氐人」這種人面魚身的怪異種族,則是有手無足的形象。
文學家西川滿出版的詩畫集《人魚燦爛》,書中附上人魚藏書票,由峯梨花刻製,西川滿手彩,則是西洋人魚曼妙姿態,金色長髮垂肩,看似慵懶愜意。
爬梳各國各處、不同社群所流傳的妖怪紀錄與圖像,我認為怪物的型態與內涵,會受到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空間、相異的人類社群文化所影響。就算是同一種妖怪,也會擁有五花八門的形象。因為,每隻妖怪都是由人類餵養而成,最後妖怪會長成何種樣貌,端看人類投餵何種食物。
例如人魚,可以像是迪士尼的可愛美人魚,也能展現出高橋留美子漫畫中「半魚人」邪惡外型。我漸漸明白,也許並不是人魚很恐怖,而是人魚背後隱藏的人類意念太過黑暗恐怖,才會讓怪物擁有驚嚇的面貌。
講到驚嚇,另一種讓我很害怕的存在是「鬼」。我與「鬼」的初次邂逅,大約也是五、六歲。
那時候,我住在三合院,鄰居叔公過世,三合院搭起棚子舉行喪禮,棚子側邊懸掛「十殿圖」,描繪凡人進入地獄十殿接受審判的場景。鬼差鬼卒懲罰惡人有各種方式,例如拔舌、油鍋、刀山、勾腸……等等讓人目瞪口呆的刑罰。我目睹紅鬼綠鬼懲罰人們的殘酷行為,嚇得魂飛魄散,回家後連續做了好幾天的噩夢。
因為童年經驗的影響,我一直以為,鬼怪只會嚇人。鬼怪嚇人,是為了教導人們要行善積德。不過,我這幾年也逐漸意識到,「嚇人」只是妖怪的其中一項能力而已。有時候,妖怪、鬼怪存在的目的,並非嚇人。
日治時期,臺灣人會製作一些關於鬼怪的趣味童玩,這些鬼怪玩具的存在意義,是為了娛樂人們。例如有一種「吐舌鬼」玩具偶頭,內部有竹串機關,只要扯動竹串,鬼怪玩具的舌頭與眼球就會作出相應動作,妙趣橫生。1936年出版的《版藝術:台灣土俗玩具集》書中,就有版畫作品記錄了這種奇異玩具。
1942年9月號《民俗臺灣》,封面是「鬼玩具」,立石鐵臣繪製。這項鬼怪玩具由木頭製成,鬼怪握住鐵棒的地方,有一個手把,旋轉手把,就能讓杵上下移動。立石鐵臣不太清楚這是鬼怪正在搗糕,或者是仿造地獄場景。不過立石鐵臣認為這項玩具:「構思也好,美感也好,可說傑作。」
雖然日治時期的鬼怪玩具很難流傳至今,但是藉由書冊記錄的圖像,今人也可以得知曩昔臺灣創作者就會以鬼怪作為玩具題材。鬼怪不只是嚇人而已,實際應用於玩具、娛樂領域,鬼怪也能具備挑動人們童趣心情的特殊能力。
妖鬼的存在,其實很有潛力多方面發展。我強烈意識到這一件事情,是在清大臺文所讀書的時候,我在課堂上讀到臺灣文學家西川滿的作品。
當時的閱讀文本,是西川滿的《華麗島民話集》與《華麗島顯風錄》。走入西川滿字裡行間,天女散花般的景致讓人目不轉睛,臺灣神奇民俗故事交織成華麗迷宮。
民俗故事經常與妖鬼相關,所以西川滿也有相關創作。例如〈過火——宜蘭新興天神宮祭〉,描述宜蘭天神宮過火儀式,西川滿註解這間宮廟的守護神是由山貓妖怪變成。
貓妖竟能成為廟宇神明?此事讓我很訝異。藉由西川滿的作品啟發,我一路調查臺灣民俗文化,赫然得知此事是常見鄉土故事。例如高雄民譚,昔日紅毛港周圍樹林常有「死貓吊樹頭」的習俗,導致貓鬼顯靈,於是人們認為樹林附近小廟的神明是「貓仔公」。除此之外,金門也有「貓仔宮」,民間傳言曾有貓被殺而作祟,於是人們建立小廟祭祀。
西川滿應用妖鬼文化,不只是文學創作,連美術設計也顧及。例如,他經常在書本版權頁附上黑色老虎圖畫,黑虎造型來自「外方紙」的黑虎紙錢。黑虎是一種恐怖妖怪,法師道士會使用這種外方紙驅逐黑虎妖怪。
西川滿的創作,刺激人們對於妖鬼文化的另類想像,也讓人們得知「妖怪、怪異」在文學藝術等等領域有著極大的發展空間。
雖然這幾年來不斷研究妖鬼故事,但我也沒有完全克服對於怪物的恐懼之心。事實上,我仍然像小時候那樣,害怕齜牙咧嘴的怪物突然撲過來,與朋友一同看恐怖片時,我仍會被厲聲警告不准突然發出尖叫聲。
儘管如此,在妖鬼創作與研究的旅程中,我也逐漸發覺妖鬼故事的不同面向。雖然妖怪真的很嚇人,但是妖怪也非常有趣,因為妖怪千變萬化,擁有各種形貌,象徵「未知的世界」。未知,雖然是恐懼的來源,但是它也讓人著迷,因為它代表著無限的探索空間。
我怕鬼,我怕妖怪。但我也同時認為,妖怪很有趣。●
何敬堯
臺中人,定居大肚山。臺大外文系、清大臺文所畢業。寫作主題包含奇幻、歷史、推理、妖怪。榮獲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臺大文學獎、臺北縣文學獎。中正大學駐校作家。作品被改編為漫畫、手機遊戲、桌遊、音樂劇。
歷年出版書籍:《妖怪臺灣》獲金石堂年度十大影響力好書、《妖怪臺灣地圖》獲文化部中小學生讀物選介、《妖怪鳴歌錄》獲臺灣文學館好書推廣、《華麗島軼聞》(合著)獲博客來OKAPI年度選書、《都市傳說事典:臺灣百怪談》。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