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人生.張郅忻》風鈴碎
在我成長的小鎮裡,很少出現「書店」,大多是以販賣文具為主的「書局」,就算有書,也是跟學校相關的參考書。
第一次在書店買書,是一間在大水溝對岸新開的小書店。我已經不記得書店的名字了,只記得那間書店是我低年級的導師陳老師開的。那次月考考得不錯,我拿獎狀回家向阿公討賞。
「妳要什麼?阿公買給妳。」阿公看著獎狀喜孜孜地問。
「我想要吃豆花、香蕉和買書。」阿公立刻發動摩托車,帶我去大水溝上的豆花攤吃豆花,再去一旁的水果攤買了一串香蕉,接著過了馬路到對岸的書店,讓我挑選一本喜歡的書。
書店大約只有4、5坪的大小,入門左側有一個小小的收銀台,四周全是米白色訂製書架。雖然樸素,卻是小鎮中書籍最多的書店。陳老師見我來,很開心的招呼我們。她指著自己的兒子說,這間書店是為了他開的。陳老師當時已近退休的年紀,她曾教過我的大叔叔,算是教了兩代孩子。她的兒子差不多三十來歲,人長得十分高大,坐在小小收銀台裡,有點怯生生看著我們。我後來才知道,老師的兒子有智力發展的問題,雖然外表像一個成人,但眼神動作都如孩子。
書架上有兒童版的世界名著,我一本一本拿下來翻看,終於挑了一本名叫《簡愛》的書。也許是父母在我很小的時候離異的關係,我一直對於孤女的故事情有獨鍾。我把書拿到櫃台交給老闆,阿公掏錢,只見老闆慢慢按著計算機、找零。陳老師一臉笑意看著她的孩子,送我們到店門口才轉身進去。
可能是小鎮裡買書的人太少,小書店經營沒多久就關門了。沒過多久,柏油馬路取代大水溝,大水溝邊的小攤販一一遷離。每次回家路過偌大的十字路口,我想起的是豆花攤、水果攤和對岸的小書店。
兒時見過最富麗堂皇的書店,莫過於位於新竹市區金石堂。金石堂所在的位置就在新竹火車站斜對面,當時最熱鬧繁華的三角地段,一共有四層樓高。一間金石堂比小鎮所有書局加起來都還要大。第一次看見金石堂時,確實感受到「黃金屋」的態勢,一進門就可以看見暢銷排行榜上的書陳列在門口,侯文詠、吳淡如、張曼娟⋯⋯,他們的照片伴隨書籍一起迎接我們。
對孩子來說,最吸引人的不是一、二樓堆疊的書籍,而是三、四樓的文具層。玻璃圍牆邊的櫃子上,擺著各種動物裝飾的陶瓷杯盤。架子上有各種功能、顏色的筆,還有卡片、書籤和漂亮的筆記本。我們總是在文具架間流連忘返,總覺得這裡的文具比起小鎮更新更好。
雖然我很喜歡逛金石堂,但當時年紀還小,沒辦法獨自搭火車過去。還好,阿婆也愛到處走逛。如果家裡的煎餃攤提早賣完,下午有空,口袋又有錢,她會帶我們姊妹搭半小時火車到新竹。第一站通常就是距離最近的金石堂。阿婆不進書店,讓我們自己進去玩耍,並交代半小時後到金石堂旁的玻璃攤找她。
金石堂和隔壁店鋪的中間有一條狹窄的防火通道,玻璃攤就在通道入口處。原來陰暗狹小的甬道,因為玻璃攤而顯得奇異,就像進入《哈利波特》的斜角巷,令人忍不住駐足觀看。賣玻璃的阿姨有小兒麻痺,她坐在輪椅上,各式可愛精緻的玻璃就擺放在她腿上的木箱裡。阿婆會跑去坐在金石堂的階梯上,和賣玻璃的阿姨閒聊,有時還幫忙推銷玻璃。阿姨的臉圓圓的,一頭梳理得熨貼的短髮,厚厚嘴唇抹上鮮紅唇彩。每次逛完金石堂,阿婆就會讓我們在阿姨的攤子上挑選一個喜歡的玻璃。有小雞、小熊這類小動物,也有杯盤等迷你餐具,我把這些可愛的玻璃放在書櫃上,紀念每一趟新竹行。
唯獨一次什麼也沒帶回。那時,我約莫三、四年級,爸爸沒有工作,長時間待在家。我拜託爸爸帶我們姊妹去新竹玩,爸爸苦笑回答我,他沒錢,連坐火車的錢都沒有。爸爸的理由不足以打發我,我拿出自己存的零用錢,告訴爸爸,我有錢。雖說有錢,但也不過是一百多塊,只夠我們往返新竹的車錢,沒有辦法買別的東西,也不能吃吃點心。
「我只是想逛一下書店,不會亂買東西的。」我信誓旦旦向爸爸保證。爸爸有點無奈苦笑。他比誰都知道女兒的個性。我是想要做什麼就會想方設法達成的人,大叔叔曾這樣說我:「做毋得的硬硬要。」雖然我不喜歡這個評價,但也不能否認他的說法。爸爸即使不想出門,仍是穿上外套,帶我們去搭火車。
他帶著我們走進金石堂,到達三樓,琳琅滿目的文具叫人迷眩。妹妹拉著我走到文具櫃側邊,只見一排以延伸掛鉤吊掛的各種各樣玻璃風鈴,有鈴蘭花造型,也有長得像水母般的。冷氣房裡沒有風,想聽一聽風鈴聲的我們,動手輕輕搖晃風鈴。正當我們比較哪個風鈴最好聽時,匡啷!大妹竟一不小心摔碎其中一個風鈴。爸爸和我面面相覷,想著同一件事,我們沒有多餘的錢可以買下那破碎的風鈴。
更戲劇的事發生了,就在風鈴掉落後的幾秒鐘,忽然間,整棟大樓暗了下來。「停電了!」在伸手不見五指又堆滿文具書局的大樓裡,大家慌張叫喊。還好,備用照明燈很快亮起,我們跟著人群慢慢往樓梯的方向移動。正當要下樓時,電力恢復,大廳再次燈火通明。這時,爸爸看了我一眼,我馬上明白他的意思。快走!我們像逃犯般匆匆離開金石堂,搭上回家的火車。
過了些年,我考上新竹女中,日日在新竹城中晃蕩。阿姨的玻璃攤已不在。同學之間常相約金石堂,一來地點明顯,二來等人時可以隨手在暢銷書區翻看新書。很長一段時間,朱少麟《傷心咖啡店之歌》占據大半個櫃子。我翻看並買下,後來還跟好友造訪陸弈靜開的咖啡館。走進風格沉鬱的咖啡館,沒有喝咖啡習慣的我們就像毛頭小子闖入大人世界般,點了一杯加糖加奶的甜膩冰咖啡,坐在小桌椅上想像朱少麟倚頭寫稿的模樣。
高二時,距金石堂不到一百公尺的地方又開了一間誠品書店。和金石堂明亮富麗的情景不同,誠品的墨綠色予人一種寧靜的感覺。誠品的書主要在地下一樓,需要走下旋轉梯才能到達。旋轉梯旁有個圓形咖啡座,用來辦講座、音樂演出,平日則可以點杯咖啡坐在那裡看書。咖啡對於當時還是學生的我來說價格太過昂貴,所以一次也沒買過。倒是因為國文老師的推薦,我們曾在那裡聽過幾場方瑜老師談宋詞的講座,三、四十張椅子一下就滿了,我和同學便坐在旋轉梯上聽講。
誠品的書架擺放較為開闊,多了許多看書的空間,除了圍著咖啡廣場擺放的長凳外,地板上、旋轉梯上,四處可見有人坐在那手捧一本書專心讀著。我也是其中一員,國文課本以外的文學書籍,很多都是在這裡看完的。文學類的書架依出版社分類,幾乎每個出版社都有屬於自己的顏色,橘色的是聯合文學,綠色的是九歌⋯⋯。
升上高三,我和好友被選上籌辦畢業旅行的任務,連續無數個放學後的晚上,我們窩在旅遊類的書牆下,翻閱一本又一本的旅遊書籍,拿著筆記本抄寫圖片上看起來不錯的景點和旅館。在網路尚未如現在普及的年代,好不容易憑藉抄下的筆記,訂下三天兩夜的住宿,其中一晚住在淡水,書中看來是間簡單樸實,價格還算合理的旅館。
到了實地才發現,這間旅店比想像中小且舊,房間更是奇怪,牆面四周和天花板全是鏡子。我們幾個女生,一見旅館的裝潢就嚇了一跳,一度考慮要換一間住。然時間已晚,我們只好用報紙把牆面鏡子遮住,才勉強入睡。我心裡頗自責,好好一趟畢業旅行,真不該讓我這粗心人負責。我不由得責怪起放在書店裡的旅遊書,怎麼會放上這樣的資訊?盡信書不如無書,我倒是得到最好的教訓了。好在同學們沒有因此而掃興,依舊開開心心走完這趟旅行。
儘管發生這件事,我還是很喜歡新竹誠品。後來在外縣市讀大學,只要回新竹,一定會去誠品走走。研究所考上清大,發現新竹誠品徵人,興高采烈寫了自傳投遞過去,沒想到真收到第二階段面試的電話。面試主管一見我,就先自我介紹說她是我竹女的學姊,並坦白說因為我還在讀書,並不打算錄用我。
「那為什麼還要叫我來?」我難掩失望的問。
「我想看看寫這自傳的人。」學姊一臉笑意,理所當然的回答。一場面試變成學姊妹的見面會。
雖然沒有應徵上誠品,但偶而我還是會來這裡走逛,直到畢業後到高雄工作為止。許多年後,等到自己有機會在九歌出書時,不禁想起曾坐在九歌書牆下,那一片綠油油的光景。
曾經最熱鬧的火車站前,隨著金石堂、誠品和SOGO百貨搬遷,顯得蕭條許多。某次偶然途經金石堂舊址,在金石堂搬遷後成為商場,商場正歇業待租。景物不依舊,人事也全非。這些年來,阿公、爸爸因病辭世,高中好友之一則因意外在年華正茂時驟然離世,看著拉下的鐵門與空蕩的走廊,腦海中忽然浮現那一地碎風鈴,以及曾經美妙動聽的風鈴聲。●
張郅忻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希望透過書寫,尋找生命中往返流動的軌跡。著有散文集:《我家是聯合國》、《我的肚腹裡有一片海洋》、《孩子的我》及長篇小說《織》、《海市》。曾於蘋果日報撰寫專欄「長大以後」,人間福報副刊專欄「安咕安咕」、「憶曲心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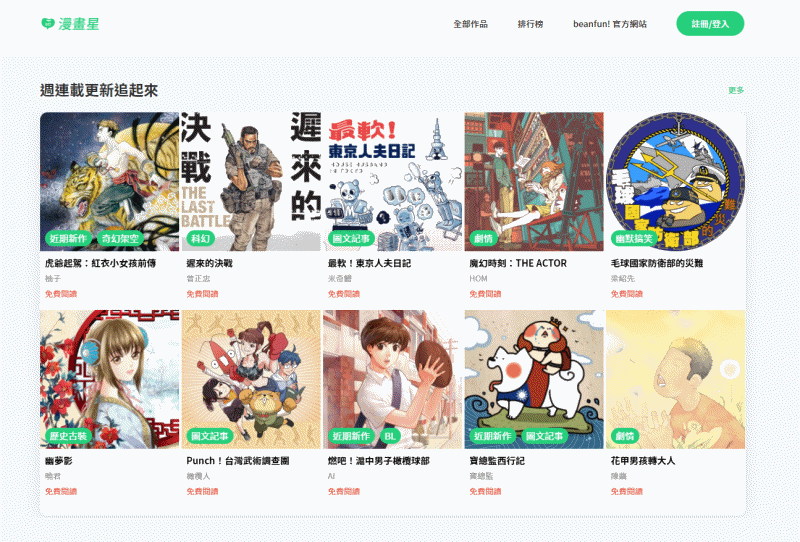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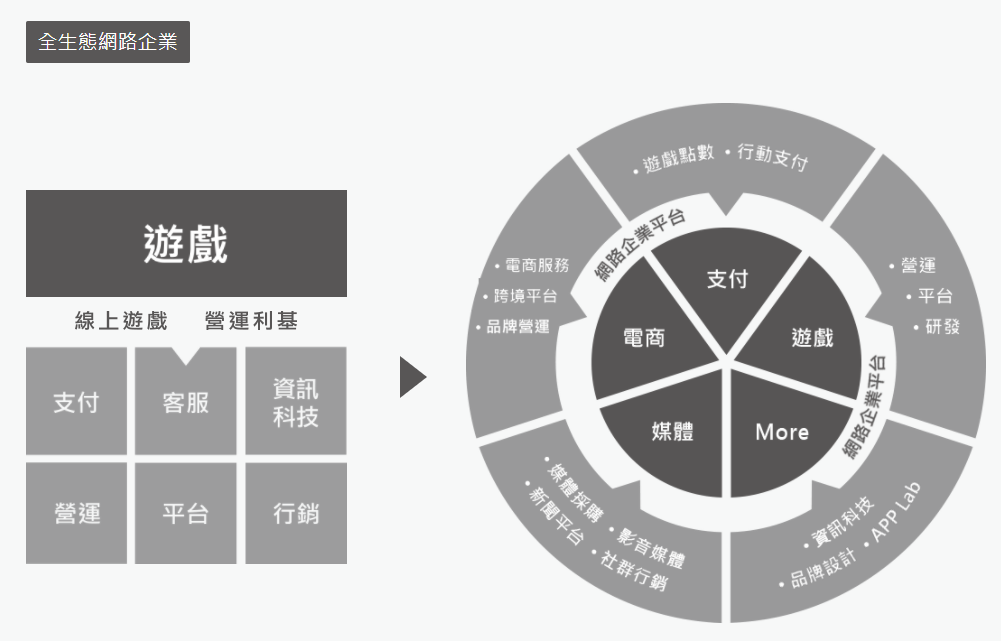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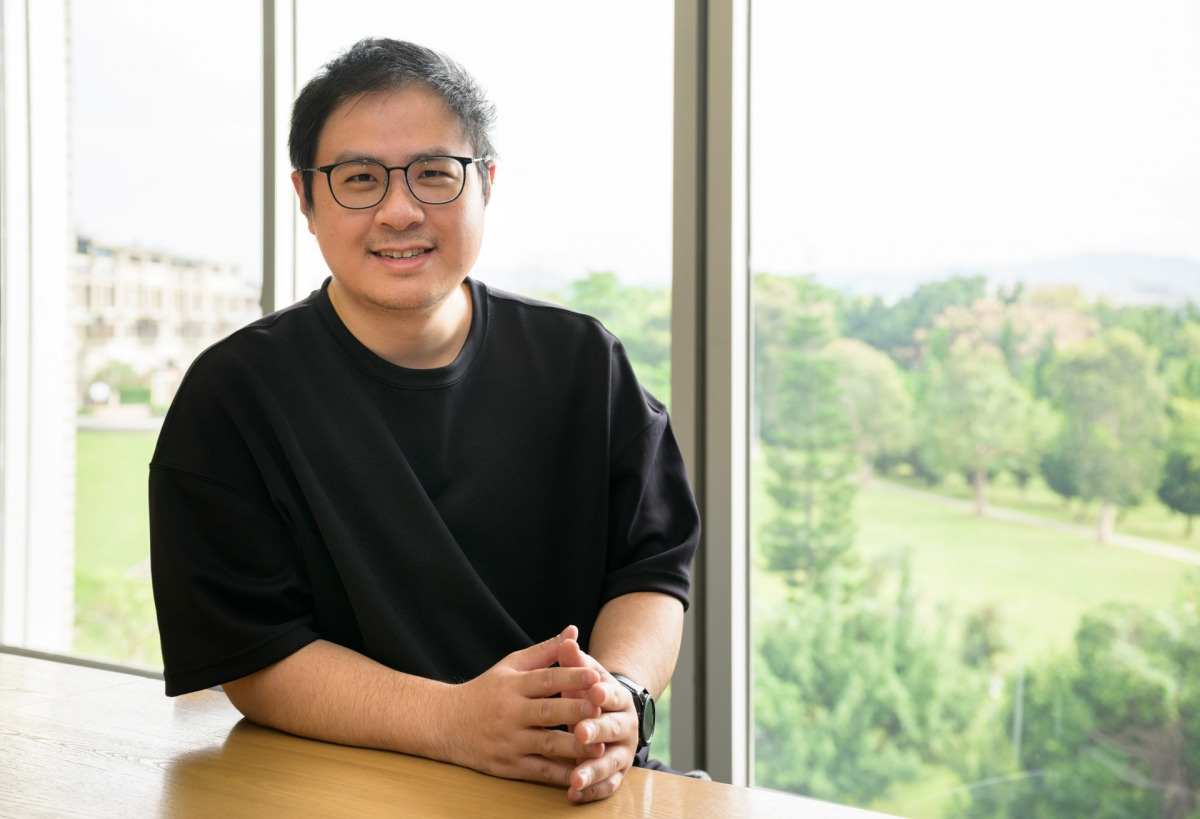




東亞書房》直木獎作家X音樂組合YOASOBI跨界合作,發行小說集及樂曲,及其他藝文短訊
【業界新聞】
■日本4位直木獎作家島本理生、辻村深月、宮部美幸與森繪都,上個月與雙人音樂組合YOASOBI跨界合作,發行小說集《第一次的》(水鈴社)。在這部合集中,4位小說家皆從「第一次做〇〇事時讀的故事」主題出發,分別書寫「第一次喜歡上一個人時讀的故事」、「第一次離家時讀的故事」、「第一次成為嫌疑犯時讀的故事」,以及「第一次告白時讀的故事」。YOASOBI以4篇小說為原型創作的音樂作品,將在今年內逐步推出。
■去(2021)年10月底公布的第25屆日本推理文學大獎,並列獲選新人獎的大谷睦《雲端之城》及麻加朋《藍色的雪》,上個月24日由光文社正式發行。
大谷的《雲端之城》在角色及場景設定上皆別出新意。曾在伊拉克擔任傭兵的主人公鹿島丈,歸國後成為資訊數據中心的警衛,並遭遇了數據中心的連續密室殺人案,讓他不得不在被封鎖的「雲端之城」與兇手對峙。大谷透過緊湊的步調、寫實的描繪,以及意外的情節展開,呈現科技時代實際支配著世界、宛如「巴別塔」的數據中心的內在樣貌。
《藍色的雪》則是以家族慘劇以及5歲女孩失蹤事件為開端的大河懸疑小說。一同度過炎夏數日的3個家族,突然間遭逢悲劇。事件雖疑點重重,但卻因為線索不足,而被埋藏在漫長的時光中。許久以後,一封告發信,重新在平靜的湖面激起水花。隨著謎團逐漸釐清,讓人不寒而慄的真相也浮上了檯面。有讀者在閱後心得中表示,理解到書名意思的瞬間,驚訝得雞皮疙瘩都冒出來了。
■日本作家、翻譯家暨福爾摩斯研究家北原尚彥,與日本一級建築師村山隆司,在上個月共同推出《夏洛克.福爾摩斯的建築》(X-Knowledge),呈現他們對於福爾摩斯系列作的場景考察。柯南.道爾筆下的福爾摩斯,幾乎已成偵探的代名詞。北原及村山搜羅並分析原作中的建築用語及相關描寫,根據有限的資訊,盡可能視覺化地還原福爾摩斯探案中的事件現場及建築設計,並邀請讀者從建築的觀點,一同體驗偵探解謎的樂趣。
【得獎消息】
■第56屆吉川英治文學獎評選結果出爐,本屆獎項由中島京子的《溫柔的貓》(中央公論新社)及京極夏彥的《遠巷說百物語》(角川出版)並列獲獎。
中島京子過去便曾以《東京小屋的回憶》、《羚羊角》、《漫長的告別》等作榮獲多項文學大獎。去年8月出版的《溫柔的貓》,從小人物之間的戀愛及家族羈絆為出發點,思考外來移民、種族偏見及在留政策。擔任幼保人員的單親媽媽美雪,愛上了比她小8歲的汽車維修員庫瑪。兩人相遇、相戀、並希望能一同共組家庭。然而,庫瑪身為斯里蘭卡人的外籍身分,卻成為兩人幸福之路的絆腳石。雖然故事本質上觸及沉重的移民難民問題及大環境中的個體困境,但中島以溫柔的筆法將美雪與庫瑪的故事娓娓道來,並透過兩人的遭遇,思索「國際化」底下的不平等、移民政策的缺漏,以及入國管理制度的黑暗面。
京極夏彥的《遠巷說百物語》,則是繼他的直木獎得獎作《後巷說百物語》及柴田錬三郎獎得獎作《西巷說百物語》後,第三部摘得文學獎殊榮的《巷説百物語》系列作品。《遠巷說百物語》相關資訊,詳見〈2021年7月東亞書房〉。
■第42屆日本科幻奇幻小說大獎於上個月底出爐,本屆由漫畫家吉永史的漫畫作品《大奧》摘得桂冠。大奧全系列共19冊,單行本自2005年開始發行,並於2021年完結,期間曾榮獲2009年第13屆手塚治虫文化獎漫畫大獎、2010年小學館漫畫獎少女部門獎,並被改編為多部影視作品。漫畫《大奧》的故事設定在第3代將軍家光在位時期,一種只有年輕男子會染上的怪病「赤面痘瘡」快速蔓延,讓男性人口銳減至女性的4分之1,政經大權也因而落入女性手中。德川家光的乳母春日局,將家光唯一的女兒千惠扮成男性,以取代其父職位。吉永以架空的歷史,顛覆男尊女卑的社會,並開展出與當代歷史詮釋完全不同的世界觀。
【作家動態】
就在此時,醫院的同僚向她介紹了一份「高收入的副業」。29歲、女性、單身、鄉下出身、非正職員工的她,最終將自己的子宮、自由與尊嚴全權交給了陌生人,在東京當起代理孕母。對生活陷入困頓的理樹來說,還有什麼可以再失去的呢?反烏托邦小說《燕不歸來》,圍繞著孩子的議題以及隨之而來的「生育產業鍊」,從而探討代理孕母是否最終成為對貧困女性的利用及榨取。
將有償陪飲當作志願的女子、深夜潛入學校的高中生、行將就木的年邁女性、私底下不斷背刺周遭親友的作家,他們所面對的,是一個即將發生改變的世界。《春天的可怕事物》設定在2020年新冠肺炎正將開始蔓延的春天。川上透過6個短篇連作,書寫糟糕狀況發生前夕的「當下」,以及個體在汪洋中浮沉的不安與茫然。
■《絕叫》、《繭》、《勁敵》作者葉真中顯,於本月出版全新作品《Long Afternoon》(中央公論新社)。在新央出版社擔任編輯的葛城梨帆,某天突然收到一份來自新人獎落選者志村多惠的原稿。故事從學生時代友人多年後的再會開場,立場不同的2個角色,在不愉快的對談後萌生了殺意。「不如最後索性殺了這個女人吧」,故事中的她這樣想著。梨帆在細細品味著女性角色的心境與困境的同時,自身無法忘懷的某個事件,也與原稿内容產生了微妙的呼應。葉真中在《Long Afternoon》中,以現實及文字的網絡,勾勒女性之間細緻的羈絆。
■曾出版《第二次滿月》、《月亮前方三公里》、《八月的銀之雪》的作家兼天文物理學者伊與原新,上個月推出新作《白腹琉璃流星群》(角川出版),呈現靜謐星空如何成為幸福的導航。高中最後的文化祭,彗子與好友久志等人用1萬個空罐,拼成一幅白腹琉璃的掛畫。此後的28年歲月,他們從耀眼的青年,成為泯滅於人群中的中年人。回到故鄉的彗子與舊友們重逢後,決定一同靠著自己的手,製作出可以觀測流星故鄉的天文台。
45歲的他們,能重新找到照亮自己人生的閃耀之星嗎?伊與原透過5人合力完成天文台的過程,描繪他們各自的家族以及高中夏天的回憶,呈現結合了科學與人生浪漫的溫柔故事。書評家石井千湖評述:「缺乏資金、也不再像十幾歲年輕人般體力充沛的40多歲男女們,利用知識與情報逐漸搭建起天文台的過程,讓人不禁也跟著心潮澎湃。」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