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擂台上使出一記漂亮的左勾拳,這值得喝采 ; 但左勾拳要是用在街上或其他地方,就叫「人身傷害」。如果不意圖傷害,也非愛好拳擊,目標是讓人們透過實際體驗,思索暴力、身體界線或其他尚無以名之的內容,那麼,我們可以選擇不使用擂台,但在同時,卻也不可能透過隨機打人,就達成目標——必須加入更多具備溝通可能性的元素,這就是創作。任何表現,如同「出拳」,根據它結合的手法與環境,是藝術還是侵犯,並不是誰說了都算,必需分析與檢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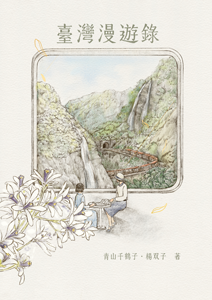 這個開場白,針對的是楊双子《臺灣漫遊錄》(2020年)4月出版時的風波事件。
這個開場白,針對的是楊双子《臺灣漫遊錄》(2020年)4月出版時的風波事件。
我認為,在第一時間裡,感到受騙或不受尊重的讀者完全有理。出版社只追加了說明與修正,並未真正致歉,恐怕也過於簡慢,輕忽了這可能對全體小說讀寫造成的傷害。然而,若把此事件等同於《灣生回家》的造假,其實也有不妥。一部將精神深深植基於平等問題的小說,未能在「側文本」中,共享同樣的品質,反映的是「包裝」的退化而非活化。
遊戲、文本滲透側文本或倒轉翻譯的位階——這些都兼有創造性與批判性,但除了意念,「側文本」並沒有動用足夠的技術輔助語言,完成邀請與暗示,可謂「弄巧成拙」。在第一個層次上,我將之歸因於實驗性出版的經驗不足,使得「小說文本與側文本的特殊連動」沒在成書階段完備。因為失落若干環節,導致「作戲」的戲感扁平——開玩笑一旦不夠「玩笑氣」,戲耍也會被感覺成搶劫。問題並不在不該戲耍,而在戲耍(策略)得不夠(完整)。
我們似乎沒有順利地繼承那個福樓拜寫《包法利夫人》,尤瑟娜直搗18個世紀前羅馬皇帝人生的小說遺產。這個症候或許並不完全來自文學的內部。挾帶新傳播技術的社會,以真人實事號召保證「可看性」,帶來了像「真人秀」這類形式,即便「假新聞」的泛濫,也與「沒有判斷力地嗜食真事」這種消費養成有關——貌似對真實興趣無比高漲的同時,一部分的文化,已進入「窮得只剩下真」的象徵能力弱化狀態。
也許我們處於比任何時候都該認真看待小說藝術的年代,不單單只因為作品的文學成就,而在於小說究其本質,並不馴服於「實事標本」的極權,並且在它的最佳狀態裡,提供了足以對抗「偽真實」不自由綑綁的路徑。這個小說力量,我建議以「假設能動」名之。小說固然可與「史實能力」競逐,但此競逐並非它的必然與義務。「假設能動」的最大化,已被許多理論家闡釋過,通常以「不可能的文學」稱之。「不可能」的另一面,就是「最大的可能」。而「可能」,就是「假設能力」。
《臺灣漫遊錄》在側文本上的失誤,根源於意欲將「假設能動」擴展至側文本,或說使用側文本以對照文本的「假設能動」時,沒有注意到側文本區有其一向預設功能,在擴展時,光是創意並不夠,必須調動更多技巧與預設功能周旋。曾有某地景藝術因位置與材料,導致駕駛眼花而車禍頻傳,藝術原不必負責交通安全,然而,作品一旦選擇著地於街道,當考慮用路者的文化(並非只能放棄),才算完整。儘管對側文本爭議感到遺憾,《臺灣漫遊錄》的書寫成績,仍令人難以忽略。
過去因為戒嚴體制,不只文學,包括學術研究,「時期」選擇都並不真正自由。迴避「敏感時間段」,可說是台灣「悲傷的特色」。自《花開時節》,楊双子就展現了她「重訪日治時間」的獨特能耐。當時,林芙美子與北川兼子等女作家來台演講旅遊,對稍涉文化史的讀者來說,並不陌生。「你仔」(小說寫作「哩呀」)也是彼時激起關心的「歧視乎?非歧視乎?」事件。〈冬瓜茶〉中,百合情是雙重的,除了雙女主的作者與譯者,又加入兩個女學生。但「同(志)性傾慕」並非楊双子唯一關心。小說如漫畫《美食偵探王》般,設有「貪吃」與「好(女)色」的循環。而「殖民是什麼?」及對其「愛與傷」的探討,是在「變奏」之外,還能層層遞增的表現景深。
同樣以「時間旅行」展開,尚有賴香吟的〈清治先生:一九五八病情〉與李昂的〈密室殺人 大祭拜〉。處理的仍是「台灣時間體」問題。戒嚴體制確立,勢必招募僱用維持其運作的人員。進入體制,也會在第一時間裡,顯得「再自然不過」——賴香吟的筆調溫和,留下的想像空間卻不只大且冷冽。在這個書寫中,寫「另眼看待」蘇清治易,寫「順理成章」的蘇清治就難——小說選擇了後者。寫人物但非以人物為中心,人物乃是令讀者得以循跡而上,遇見結構的線索繩頭。賴香吟的時間機器始於戰後,終於美麗島事件。至於李昂,則會從四面八方,包圍以「美麗島事件」為原點的時間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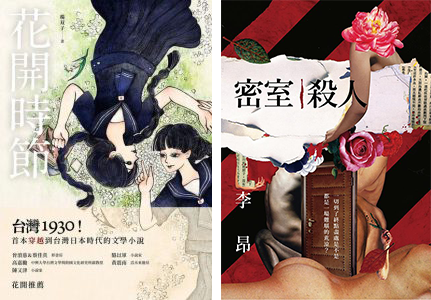 從〈密室殺人 大祭拜〉來看,成就非凡的小說家似乎打算將自己若干作品重新定位並「回收再利用」,這是大膽的「破壞性創造」。但重頭戲更在長篇小說《密室殺人》。是否可將整部《密室殺人》視為「反小說」?作品似又較此定義複雜。小說最厲害的是,儘管使用理性的語言(即便「神神鬼鬼」之時),李昂拼貼出的圖示,俱是令人心驚的無意識風暴。比如述及親異議份子的女作家,拒絕藏匿逃亡的男政治犯——理性來看,作家被監控,拒絕很實際,應該沒有良知困擾。
從〈密室殺人 大祭拜〉來看,成就非凡的小說家似乎打算將自己若干作品重新定位並「回收再利用」,這是大膽的「破壞性創造」。但重頭戲更在長篇小說《密室殺人》。是否可將整部《密室殺人》視為「反小說」?作品似又較此定義複雜。小說最厲害的是,儘管使用理性的語言(即便「神神鬼鬼」之時),李昂拼貼出的圖示,俱是令人心驚的無意識風暴。比如述及親異議份子的女作家,拒絕藏匿逃亡的男政治犯——理性來看,作家被監控,拒絕很實際,應該沒有良知困擾。
然而,那是多麼暴力的場景!彼此「並無殺意」的男女「互為死神」。體制性的殺戮沒有人臉(把行刑者的臉安上,也不是殺戮真正的臉),兇手無影無蹤又如影隨形。這種經驗不會改變人的性別,但足以「剝奪人對自我的所有預設」:女作家被迫進入「準虐待狂」位置,「被迫」是「受虐」,但「角色」又是「準虐待」。這是閹割的極致。在「關於閹割的大迷宮」中,戒嚴暴力與從性別而來的「典型與非典型的閹割慾望」交錯,呈現了令人震驚的激進觸角。
「一九九七年/或是九九七一年/與我/何干呢」,在〈礫石〉這首詩中,西西已然傳遞「認同石頭時間」的訊息,透過她對「更長時間」的情有獨鍾,來發揮她的「意在言外」。〈石頭述異〉中,遊記宛如兩隻腳的舞步,一隻在「可見可走的物理界」,一隻在「可思可記的想像界」。西西善於掌握形式的宗師風範由來已久,但這篇技巧的簡潔洗練,還是令我驚異如遭電擊。文學當出世或入世?兩者經常各執一詞。〈石頭述異〉卻達到令「出世入世」交鋒生輝的境界。自發的記憶與思索是澆不熄的。這篇「退萬步言」的小說,不能不說,也是給人們「行萬里路」的糧草。
「長時小說」傳統上被想像成「歷史的」,但小說能夠處理的,更加遼闊。以上我選了四篇向度殊異的,以俾交相觀摩。
回應時事或當下性的小說經常處境尷尬,因為它偶爾會「到不了明天」。然而,劉芷妤的〈追女仔〉跨過了這種難度,繪出宛如「ㄧ圖斃命」,既有代表性又有延展性的「那些年,我們一起看的新聞」。時事有感,感超時事。劉芷妤是會「作梗」的小說家,但並不「為梗而梗」。「梗」在她筆下的意義似正轉變:使梗如鯁,如鯁有喉。〈追女仔〉是第一篇我一讀就決定必須選入年度的作品。而想必會令人聯想到《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的〈鬼〉,也是「小鬼小說」——被棄孩童世界的小說。不同於若干評者,我認為,本篇非但前半部可圈可點,後半更是深刻沈穩。因為只有小孩才會以離奇(但主觀上合理)的方式尋求出路,也只有經歷同樣浩劫者如文中三兄妹,會如昆蟲的「共心現象」般,擁有外人不知的共同語言。作者陳靜排除掉如貧窮的因子,更凸顯出社會化匱缺傷害的「不可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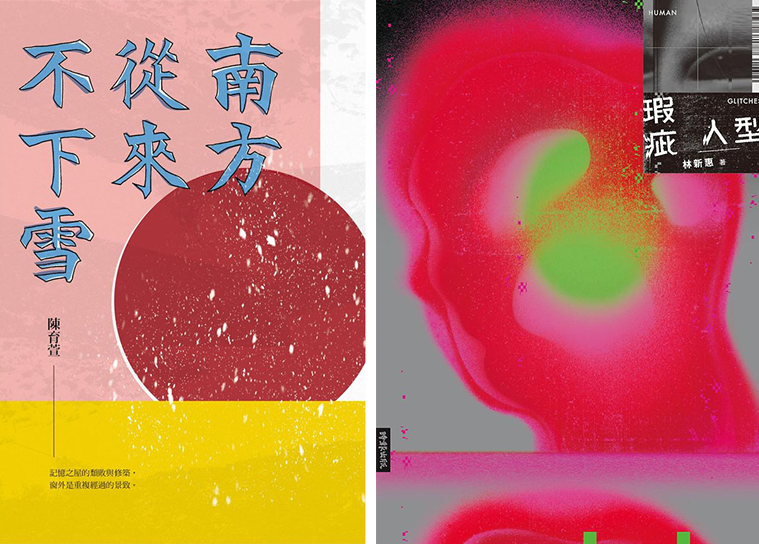
〈反光〉選自陳育萱的小說集《南方從來不下雪》,選入的原因不單單只因「高樓清潔工」是所有行業中,「最不願從事的高危職業第一名」——我想特別指出該篇收束上的啟發。小說以描寫公文型態收尾,公文的具體性與施作性,指涉的是事件與社會體系的關係。如果可以簽報救助的文件,是否也該有「避免清潔不友善之建物」的文件(難道「清潔/勞動不友善」的反省還未進入建築思想中?)?——〈反光〉給出了一個不將社會性書寫,封閉於悲嘆或憐憫主義的可能性。林新惠的《瑕疵人型》已受多項獎項肯定,〈California Hotel〉如同小說集中的多篇,不視傷害在秩序後,是能揭開「秩序即傷害」之作。
鄭守志的〈永夜〉驚悚,裴在美的〈命運之神〉平淡——無論驚悚或平淡,如果技巧充份,都是利器。自〈耶穌喜愛的小孩〉始,裴在美就是「性傷害」的先驅作者。〈命運之神〉令讀者不費吹灰之力地齊平於主角視角,為「如何避免剝削當事人」,立下標竿性的範例。形於無形的技巧,跨國婚姻與A片等元素,自待剖析,在此只先予簡單然鄭重的致敬。〈永夜〉同樣不易ㄧ筆帶過,但技巧上仍有小處可斟酌。不過,我在最後一刻,仍被本作的深刻與勇於開創打動。暴力開始處,即是語言終結時。
本作是否援引《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作為觸發,仍有模糊空間,畢竟,若只聚焦該事件,不至於將自殺方式弄錯。也因此,我傾向理解作者書寫的是更普遍的現象:每回「性暴力的揭發」,因社會未表足夠接納,既引發倖存眾焦慮,周遭偶對倖存者「倒打一耙」,也成倖存眾夢靨。——集中營倖存者的見證,也出現過類似效應。「不說是苦」,「說也苦」,就可能將倖存者從絕境逼向「最壞」:透過反轉角色,演示性暴力。專業者只要看到兒童對布偶做出某些行為,即能警覺性侵。但若布偶是真人,則成「受暴變加暴」的悲劇。即使是「最壞」,也去想像、去釐清,是令小說做布偶,也是〈永夜〉的文學承擔。
除了以上6篇,對「如何思考傷害」作出貢獻的作品,還有以不同筆法切入「日常」的各篇:林楷倫有望自成一家,或振起「漁界文學之文藝復興」。我在他的多篇傑作中抉擇,最後覺得馬祖與產銷兩元素,真的太少出現在文學之中了,我因此選了〈北疆沒有大紅色的魚〉。林銘亮的〈遠行者:五個聽來的故事〉,在並非對苦澀與恐怖ㄧ無所知的詼諧中,令小確幸與大荒謬並進。高于婷的〈六角恐龍〉,出色地寫出那些被當成不出色者的孩子(們),如何維護自我脆弱的感情。
另外,將日復一日造成的麻木、緊繃與內縮凋敝描寫入微的,是沈信宏以教員一日為摹本的〈定期保養〉。〈三溫暖〉則是一篇非常疼惜人的小說:簡媜筆下的女性身體相遇,仍有靦腆,但絕不虛浮,平實之中,也非不見曲折。在疫情籠罩的一年,照顧者的身體因被特殊化而受到側目。若干歧視浮出,照顧者的壓力,更以超乎尋常的強度成為「日常」。小說場景是在疫情之前,但在疫情中閱讀,喚起的省思,並不因此更少。
何玟珒以不太正經腔調起始的〈那一天 我們跟著雞屁股後面尋路〉,令人不無驚艷的,其實交融了哀歌。小說對照了不同起源的「變性」,他人祈願的與自我渴望的。台灣民俗性別觀的入鏡,也令思考細緻。配置不同風格語言時,對火候與過渡的掌握,也有近乎直覺的準確與自由。在書寫姿態上,熊一蘋的〈銀河飛梭〉,又更絕對與孤注一擲。強壯的虛無?冷漠的溫暖?小說人物無視大多數的法則,也可說有打破禁忌的品格。身體或時間都是身外物,但又非有惡意的殘酷。比如只是為了讓對方開心,也可以「吃對方割下自己的肉花」。
一般視為重心的事物,主角只是行禮如儀,遇到任何事,既不憂鬱,也不「不憂鬱」——這是少數會讓我覺得「極端有趣」的小說。作品非常美的部分,在於能將這種罕見色澤維持一致,且不淪為噱頭或誘餌式的事物。王定國的〈噎告〉也頗奇異——儘管他的人物初看好似與熊一蘋的大大相反,是被一切常識與義務緊緊裹住「正常過頭」的人——但裹粉不久就會掉落。無懼地迎向漫畫式的誇張與傳神,〈噎告〉是少數大膽利用戲劇性推動情節的「驚愕交響曲」。有點像「鴨兔錯視圖」,每個情節都提供了雙重意象。就以「怪嫖記」而言,一邊是「妓院解決一切」的古老幻想憧憬,一邊是「牛郎織女完全行不通」。此作不單手法有意思,透過手法呈現的嚴肅主題,也極為豐富。
在寺尾哲也的〈現在是彼一日〉中,三個在美國參加遊行的台灣男子,其中一個突然「脱序」,不但被制服還送了醫,什麼話都還沒說。其中一人評論同伴的「行為」謂「這不合理啊」。因「有諸事不明」,小說彷彿影像粒子仍在亂竄的畫面。我對這篇小說極高評價的原因如下:〈現在是彼一日〉完全可以讀作「對318的真正回返」——而回返318,意謂的並不是回到「318佔領立法院」,而是必須回返在「318與323」之間的「無以名狀」。323的佔領行政院非常慘烈,也有人可以說是「這不合理啊」——但不合理不等於沒有正當性或理性,「不合理」也意謂著「超出計算、預期與控制」——反抗與控制的關係是什麼?我們應該成為「可預測的」到什麼地步?
在當代,多重認同(族群、階級、性別等都包含在內)是一存在,但經常被簡化的處境。如果一個人的家庭或生命歷程,令其在同一項目上,擁有一個以上高低強弱不同的認同可能時,身份政治並非ㄧ般想像的,是個加減乘除即可運作的大熔爐。若干平衡,較易取得,有些傷痕,不該遺忘。邱常婷的〈斑雀雨〉中,反覆出現的「母親允諾變鳥」ㄧ節,意涵繁生。母親想要給予女兒文化的吸引力與光榮感(這裡透過的是原住民族的故事),恰恰暴露了所處的下風位置。
這正是弱勢者的兩難。女兒執著的「人不可能變成鳥」,除了最表面的知識體系對抗(所謂科學對抗神話),也暗示了兩件事,「人變鳥」可能是放棄(人的)現實原則的逃逸既定(社會)遊戲規則,「人變鳥」同時也是強勢擘畫弱勢要有可供滿足投射想像的「類別化特色」。而無論逃逸或臣服優勢者想像,都不足以拆解殖民性的陷阱。把高難度的思辨完全轉換成緻密清澈的小說語言,〈斑雀雨〉因此獲選為年度小說的得獎作,希望給予不盲目樂觀、戮力深化批判性的創作者,最大的感謝與祝福。●
|
 九歌109年小說選 九歌109年小說選
編者:張亦絢
出版:九歌文化
定價:420元
【內容簡介➤】
|
|
編者簡介:張亦絢
生於臺北木柵。巴黎第三大學電影及視聽研究所碩士。早期作品,曾入選同志文學選與臺灣文學選。另著有《我們沿河冒險》(國片優良劇本佳作)、《小道消息》、《晚間娛樂:推理不必入門書》、《看電影的慾望》、《我討厭過的大人們》,長篇小說《愛的不久時:南特 /巴黎回憶錄》 (臺北國際書展大賞入圍)、《永別書:在我不在的時代》(臺北國際書展大賞入圍),短篇小說集《性意思史》獲openbook年度好書獎。2019年起,在BIOS Monthly撰「麻煩電影一下」專欄。
張亦絢|個人網站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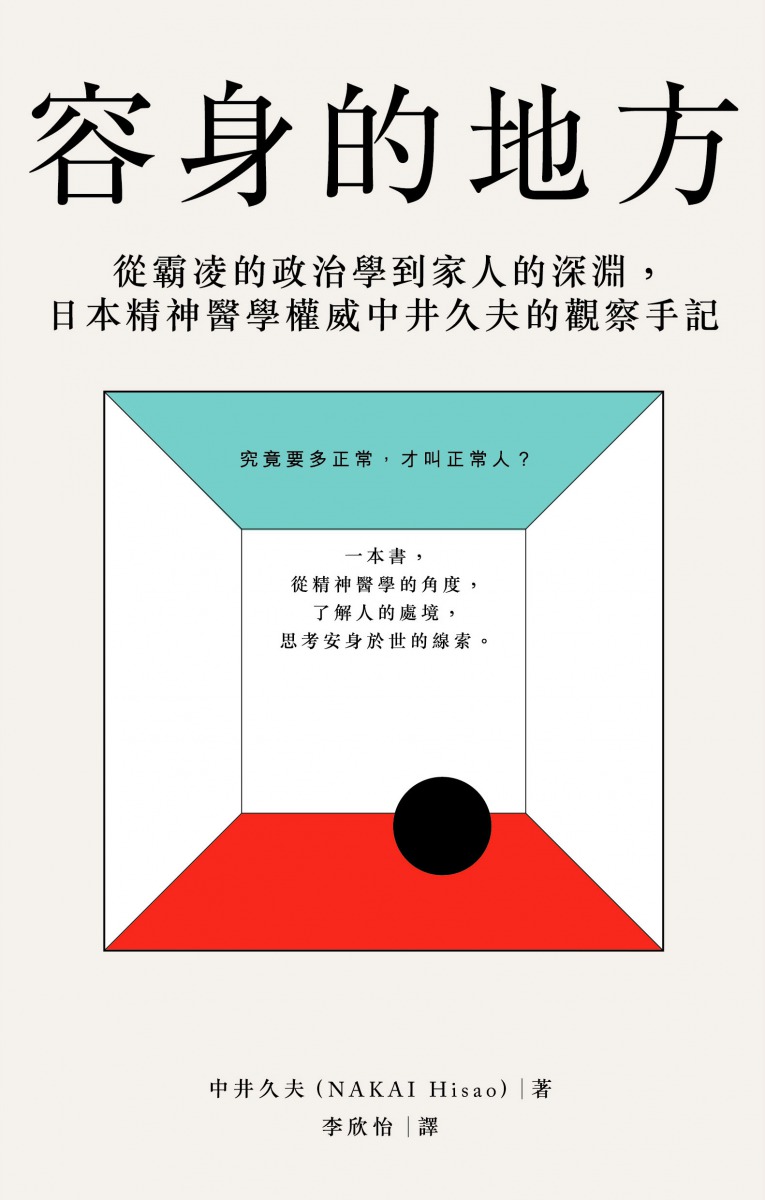


評論》張亦絢主編九歌109年小說選:這是因為我們還能夠假設
在擂台上使出一記漂亮的左勾拳,這值得喝采 ; 但左勾拳要是用在街上或其他地方,就叫「人身傷害」。如果不意圖傷害,也非愛好拳擊,目標是讓人們透過實際體驗,思索暴力、身體界線或其他尚無以名之的內容,那麼,我們可以選擇不使用擂台,但在同時,卻也不可能透過隨機打人,就達成目標——必須加入更多具備溝通可能性的元素,這就是創作。任何表現,如同「出拳」,根據它結合的手法與環境,是藝術還是侵犯,並不是誰說了都算,必需分析與檢驗。
我認為,在第一時間裡,感到受騙或不受尊重的讀者完全有理。出版社只追加了說明與修正,並未真正致歉,恐怕也過於簡慢,輕忽了這可能對全體小說讀寫造成的傷害。然而,若把此事件等同於《灣生回家》的造假,其實也有不妥。一部將精神深深植基於平等問題的小說,未能在「側文本」中,共享同樣的品質,反映的是「包裝」的退化而非活化。
遊戲、文本滲透側文本或倒轉翻譯的位階——這些都兼有創造性與批判性,但除了意念,「側文本」並沒有動用足夠的技術輔助語言,完成邀請與暗示,可謂「弄巧成拙」。在第一個層次上,我將之歸因於實驗性出版的經驗不足,使得「小說文本與側文本的特殊連動」沒在成書階段完備。因為失落若干環節,導致「作戲」的戲感扁平——開玩笑一旦不夠「玩笑氣」,戲耍也會被感覺成搶劫。問題並不在不該戲耍,而在戲耍(策略)得不夠(完整)。
我們似乎沒有順利地繼承那個福樓拜寫《包法利夫人》,尤瑟娜直搗18個世紀前羅馬皇帝人生的小說遺產。這個症候或許並不完全來自文學的內部。挾帶新傳播技術的社會,以真人實事號召保證「可看性」,帶來了像「真人秀」這類形式,即便「假新聞」的泛濫,也與「沒有判斷力地嗜食真事」這種消費養成有關——貌似對真實興趣無比高漲的同時,一部分的文化,已進入「窮得只剩下真」的象徵能力弱化狀態。
也許我們處於比任何時候都該認真看待小說藝術的年代,不單單只因為作品的文學成就,而在於小說究其本質,並不馴服於「實事標本」的極權,並且在它的最佳狀態裡,提供了足以對抗「偽真實」不自由綑綁的路徑。這個小說力量,我建議以「假設能動」名之。小說固然可與「史實能力」競逐,但此競逐並非它的必然與義務。「假設能動」的最大化,已被許多理論家闡釋過,通常以「不可能的文學」稱之。「不可能」的另一面,就是「最大的可能」。而「可能」,就是「假設能力」。
《臺灣漫遊錄》在側文本上的失誤,根源於意欲將「假設能動」擴展至側文本,或說使用側文本以對照文本的「假設能動」時,沒有注意到側文本區有其一向預設功能,在擴展時,光是創意並不夠,必須調動更多技巧與預設功能周旋。曾有某地景藝術因位置與材料,導致駕駛眼花而車禍頻傳,藝術原不必負責交通安全,然而,作品一旦選擇著地於街道,當考慮用路者的文化(並非只能放棄),才算完整。儘管對側文本爭議感到遺憾,《臺灣漫遊錄》的書寫成績,仍令人難以忽略。
過去因為戒嚴體制,不只文學,包括學術研究,「時期」選擇都並不真正自由。迴避「敏感時間段」,可說是台灣「悲傷的特色」。自《花開時節》,楊双子就展現了她「重訪日治時間」的獨特能耐。當時,林芙美子與北川兼子等女作家來台演講旅遊,對稍涉文化史的讀者來說,並不陌生。「你仔」(小說寫作「哩呀」)也是彼時激起關心的「歧視乎?非歧視乎?」事件。〈冬瓜茶〉中,百合情是雙重的,除了雙女主的作者與譯者,又加入兩個女學生。但「同(志)性傾慕」並非楊双子唯一關心。小說如漫畫《美食偵探王》般,設有「貪吃」與「好(女)色」的循環。而「殖民是什麼?」及對其「愛與傷」的探討,是在「變奏」之外,還能層層遞增的表現景深。
同樣以「時間旅行」展開,尚有賴香吟的〈清治先生:一九五八病情〉與李昂的〈密室殺人 大祭拜〉。處理的仍是「台灣時間體」問題。戒嚴體制確立,勢必招募僱用維持其運作的人員。進入體制,也會在第一時間裡,顯得「再自然不過」——賴香吟的筆調溫和,留下的想像空間卻不只大且冷冽。在這個書寫中,寫「另眼看待」蘇清治易,寫「順理成章」的蘇清治就難——小說選擇了後者。寫人物但非以人物為中心,人物乃是令讀者得以循跡而上,遇見結構的線索繩頭。賴香吟的時間機器始於戰後,終於美麗島事件。至於李昂,則會從四面八方,包圍以「美麗島事件」為原點的時間體。
然而,那是多麼暴力的場景!彼此「並無殺意」的男女「互為死神」。體制性的殺戮沒有人臉(把行刑者的臉安上,也不是殺戮真正的臉),兇手無影無蹤又如影隨形。這種經驗不會改變人的性別,但足以「剝奪人對自我的所有預設」:女作家被迫進入「準虐待狂」位置,「被迫」是「受虐」,但「角色」又是「準虐待」。這是閹割的極致。在「關於閹割的大迷宮」中,戒嚴暴力與從性別而來的「典型與非典型的閹割慾望」交錯,呈現了令人震驚的激進觸角。
「一九九七年/或是九九七一年/與我/何干呢」,在〈礫石〉這首詩中,西西已然傳遞「認同石頭時間」的訊息,透過她對「更長時間」的情有獨鍾,來發揮她的「意在言外」。〈石頭述異〉中,遊記宛如兩隻腳的舞步,一隻在「可見可走的物理界」,一隻在「可思可記的想像界」。西西善於掌握形式的宗師風範由來已久,但這篇技巧的簡潔洗練,還是令我驚異如遭電擊。文學當出世或入世?兩者經常各執一詞。〈石頭述異〉卻達到令「出世入世」交鋒生輝的境界。自發的記憶與思索是澆不熄的。這篇「退萬步言」的小說,不能不說,也是給人們「行萬里路」的糧草。
「長時小說」傳統上被想像成「歷史的」,但小說能夠處理的,更加遼闊。以上我選了四篇向度殊異的,以俾交相觀摩。
回應時事或當下性的小說經常處境尷尬,因為它偶爾會「到不了明天」。然而,劉芷妤的〈追女仔〉跨過了這種難度,繪出宛如「ㄧ圖斃命」,既有代表性又有延展性的「那些年,我們一起看的新聞」。時事有感,感超時事。劉芷妤是會「作梗」的小說家,但並不「為梗而梗」。「梗」在她筆下的意義似正轉變:使梗如鯁,如鯁有喉。〈追女仔〉是第一篇我一讀就決定必須選入年度的作品。而想必會令人聯想到《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的〈鬼〉,也是「小鬼小說」——被棄孩童世界的小說。不同於若干評者,我認為,本篇非但前半部可圈可點,後半更是深刻沈穩。因為只有小孩才會以離奇(但主觀上合理)的方式尋求出路,也只有經歷同樣浩劫者如文中三兄妹,會如昆蟲的「共心現象」般,擁有外人不知的共同語言。作者陳靜排除掉如貧窮的因子,更凸顯出社會化匱缺傷害的「不可逆」。
〈反光〉選自陳育萱的小說集《南方從來不下雪》,選入的原因不單單只因「高樓清潔工」是所有行業中,「最不願從事的高危職業第一名」——我想特別指出該篇收束上的啟發。小說以描寫公文型態收尾,公文的具體性與施作性,指涉的是事件與社會體系的關係。如果可以簽報救助的文件,是否也該有「避免清潔不友善之建物」的文件(難道「清潔/勞動不友善」的反省還未進入建築思想中?)?——〈反光〉給出了一個不將社會性書寫,封閉於悲嘆或憐憫主義的可能性。林新惠的《瑕疵人型》已受多項獎項肯定,〈California Hotel〉如同小說集中的多篇,不視傷害在秩序後,是能揭開「秩序即傷害」之作。
鄭守志的〈永夜〉驚悚,裴在美的〈命運之神〉平淡——無論驚悚或平淡,如果技巧充份,都是利器。自〈耶穌喜愛的小孩〉始,裴在美就是「性傷害」的先驅作者。〈命運之神〉令讀者不費吹灰之力地齊平於主角視角,為「如何避免剝削當事人」,立下標竿性的範例。形於無形的技巧,跨國婚姻與A片等元素,自待剖析,在此只先予簡單然鄭重的致敬。〈永夜〉同樣不易ㄧ筆帶過,但技巧上仍有小處可斟酌。不過,我在最後一刻,仍被本作的深刻與勇於開創打動。暴力開始處,即是語言終結時。
本作是否援引《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作為觸發,仍有模糊空間,畢竟,若只聚焦該事件,不至於將自殺方式弄錯。也因此,我傾向理解作者書寫的是更普遍的現象:每回「性暴力的揭發」,因社會未表足夠接納,既引發倖存眾焦慮,周遭偶對倖存者「倒打一耙」,也成倖存眾夢靨。——集中營倖存者的見證,也出現過類似效應。「不說是苦」,「說也苦」,就可能將倖存者從絕境逼向「最壞」:透過反轉角色,演示性暴力。專業者只要看到兒童對布偶做出某些行為,即能警覺性侵。但若布偶是真人,則成「受暴變加暴」的悲劇。即使是「最壞」,也去想像、去釐清,是令小說做布偶,也是〈永夜〉的文學承擔。
除了以上6篇,對「如何思考傷害」作出貢獻的作品,還有以不同筆法切入「日常」的各篇:林楷倫有望自成一家,或振起「漁界文學之文藝復興」。我在他的多篇傑作中抉擇,最後覺得馬祖與產銷兩元素,真的太少出現在文學之中了,我因此選了〈北疆沒有大紅色的魚〉。林銘亮的〈遠行者:五個聽來的故事〉,在並非對苦澀與恐怖ㄧ無所知的詼諧中,令小確幸與大荒謬並進。高于婷的〈六角恐龍〉,出色地寫出那些被當成不出色者的孩子(們),如何維護自我脆弱的感情。
另外,將日復一日造成的麻木、緊繃與內縮凋敝描寫入微的,是沈信宏以教員一日為摹本的〈定期保養〉。〈三溫暖〉則是一篇非常疼惜人的小說:簡媜筆下的女性身體相遇,仍有靦腆,但絕不虛浮,平實之中,也非不見曲折。在疫情籠罩的一年,照顧者的身體因被特殊化而受到側目。若干歧視浮出,照顧者的壓力,更以超乎尋常的強度成為「日常」。小說場景是在疫情之前,但在疫情中閱讀,喚起的省思,並不因此更少。
何玟珒以不太正經腔調起始的〈那一天 我們跟著雞屁股後面尋路〉,令人不無驚艷的,其實交融了哀歌。小說對照了不同起源的「變性」,他人祈願的與自我渴望的。台灣民俗性別觀的入鏡,也令思考細緻。配置不同風格語言時,對火候與過渡的掌握,也有近乎直覺的準確與自由。在書寫姿態上,熊一蘋的〈銀河飛梭〉,又更絕對與孤注一擲。強壯的虛無?冷漠的溫暖?小說人物無視大多數的法則,也可說有打破禁忌的品格。身體或時間都是身外物,但又非有惡意的殘酷。比如只是為了讓對方開心,也可以「吃對方割下自己的肉花」。
一般視為重心的事物,主角只是行禮如儀,遇到任何事,既不憂鬱,也不「不憂鬱」——這是少數會讓我覺得「極端有趣」的小說。作品非常美的部分,在於能將這種罕見色澤維持一致,且不淪為噱頭或誘餌式的事物。王定國的〈噎告〉也頗奇異——儘管他的人物初看好似與熊一蘋的大大相反,是被一切常識與義務緊緊裹住「正常過頭」的人——但裹粉不久就會掉落。無懼地迎向漫畫式的誇張與傳神,〈噎告〉是少數大膽利用戲劇性推動情節的「驚愕交響曲」。有點像「鴨兔錯視圖」,每個情節都提供了雙重意象。就以「怪嫖記」而言,一邊是「妓院解決一切」的古老幻想憧憬,一邊是「牛郎織女完全行不通」。此作不單手法有意思,透過手法呈現的嚴肅主題,也極為豐富。
在寺尾哲也的〈現在是彼一日〉中,三個在美國參加遊行的台灣男子,其中一個突然「脱序」,不但被制服還送了醫,什麼話都還沒說。其中一人評論同伴的「行為」謂「這不合理啊」。因「有諸事不明」,小說彷彿影像粒子仍在亂竄的畫面。我對這篇小說極高評價的原因如下:〈現在是彼一日〉完全可以讀作「對318的真正回返」——而回返318,意謂的並不是回到「318佔領立法院」,而是必須回返在「318與323」之間的「無以名狀」。323的佔領行政院非常慘烈,也有人可以說是「這不合理啊」——但不合理不等於沒有正當性或理性,「不合理」也意謂著「超出計算、預期與控制」——反抗與控制的關係是什麼?我們應該成為「可預測的」到什麼地步?
在當代,多重認同(族群、階級、性別等都包含在內)是一存在,但經常被簡化的處境。如果一個人的家庭或生命歷程,令其在同一項目上,擁有一個以上高低強弱不同的認同可能時,身份政治並非ㄧ般想像的,是個加減乘除即可運作的大熔爐。若干平衡,較易取得,有些傷痕,不該遺忘。邱常婷的〈斑雀雨〉中,反覆出現的「母親允諾變鳥」ㄧ節,意涵繁生。母親想要給予女兒文化的吸引力與光榮感(這裡透過的是原住民族的故事),恰恰暴露了所處的下風位置。
這正是弱勢者的兩難。女兒執著的「人不可能變成鳥」,除了最表面的知識體系對抗(所謂科學對抗神話),也暗示了兩件事,「人變鳥」可能是放棄(人的)現實原則的逃逸既定(社會)遊戲規則,「人變鳥」同時也是強勢擘畫弱勢要有可供滿足投射想像的「類別化特色」。而無論逃逸或臣服優勢者想像,都不足以拆解殖民性的陷阱。把高難度的思辨完全轉換成緻密清澈的小說語言,〈斑雀雨〉因此獲選為年度小說的得獎作,希望給予不盲目樂觀、戮力深化批判性的創作者,最大的感謝與祝福。●
編者:張亦絢
出版:九歌文化
定價:420元
【內容簡介➤】
編者簡介:張亦絢
生於臺北木柵。巴黎第三大學電影及視聽研究所碩士。早期作品,曾入選同志文學選與臺灣文學選。另著有《我們沿河冒險》(國片優良劇本佳作)、《小道消息》、《晚間娛樂:推理不必入門書》、《看電影的慾望》、《我討厭過的大人們》,長篇小說《愛的不久時:南特 /巴黎回憶錄》 (臺北國際書展大賞入圍)、《永別書:在我不在的時代》(臺北國際書展大賞入圍),短篇小說集《性意思史》獲openbook年度好書獎。2019年起,在BIOS Monthly撰「麻煩電影一下」專欄。
張亦絢|個人網站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