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人類都需要牽繫與愛,專訪《親愛的艾德華》作者Ann Napolitano
2010年,一架從紐約前往洛杉磯的班機失事墜毀,一百多人罹難,僅有一名9歲男童奇蹟生還。這場悲劇事件縈繞在小說家安.納波利塔諾(Ann Napolitano)心頭,她花費8年的時間完成《親愛的艾德華》,出版後即登上各國暢銷書榜,影視改編作品即將開拍。
本書以雙線交錯的敘事,呈現機上乘客的心路歷程,以及劫後餘生的艾德華內心掙扎和思念。對家人而言,他「只是艾迪」;但對媒體和世人來說,他卻是「艾德華」。一場空難後,他和世界看待他自己的視角已然不同。
空難的唯一倖存者為什麼是他?他是否就像鄰家女孩的簡單說法,「就像哈利.波特一樣」,難道他是冥冥之中「被選中的人」?透過這篇訪談,作者向我們闡述,她如何在這個以悲劇起始的情節中,為讀者送上一個如此悲傷、卻又能帶來希望及深意的成長小說。
▇這部小說的靈感來自於2010年的真實空難事件,請問你如何構思其中的情節與角色?動筆寫作之前,是否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準備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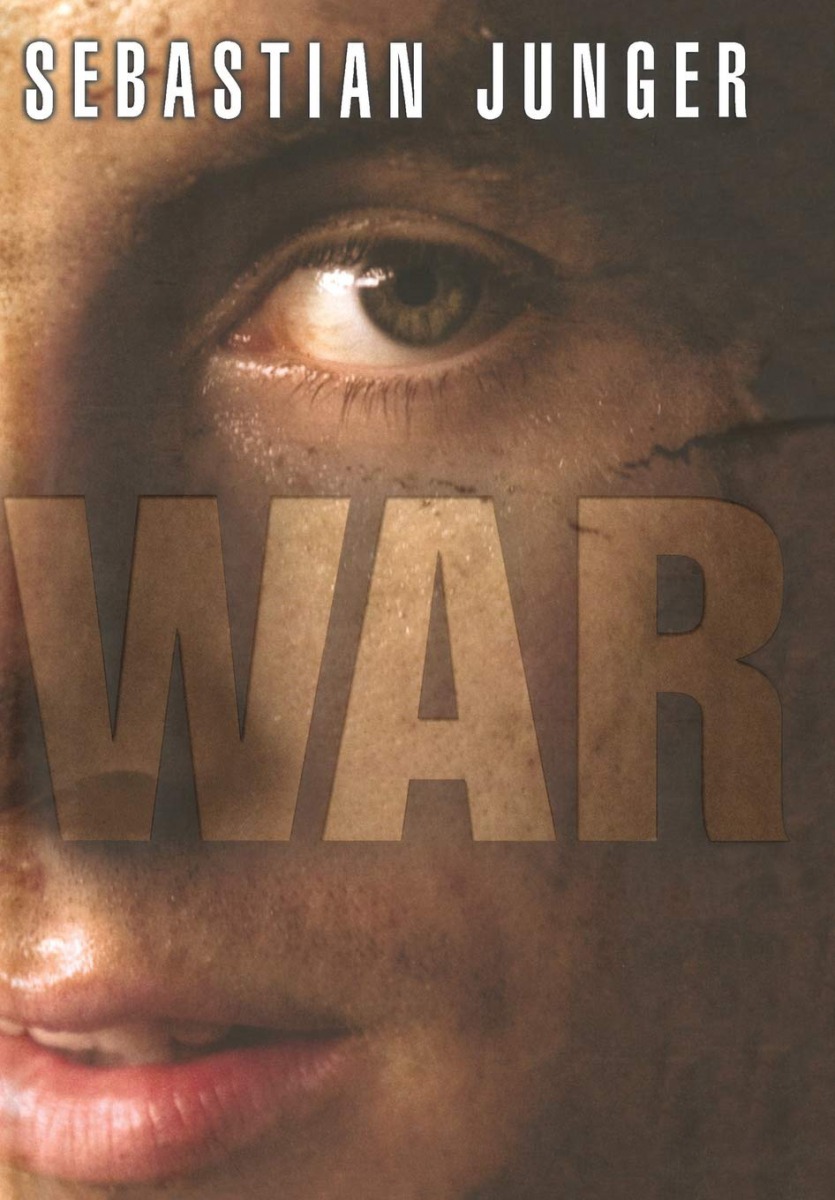 創作這本書的第一年,我的工作內容就是研究與規畫這本小說。我反覆思考飛機上要有哪些乘客、怎樣的乘客,然後閱讀與這些人相關的書籍作為研究。例如,構思克里斯賓.考克斯這個角色時,我讀了奇異電子公司執行長傑克.威爾許(Jack Welch)的自傳。為了描寫班傑明.斯提曼這個角色,我訪問一位從事軍職的朋友,並且閱讀賽巴斯提安.鍾格(Sebastian Junger)所寫的《戰爭》(War)一書。當然,我也做了許多關於墜機事件的相關研究。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來完成所有研究,才允許自己開始著手寫下這個故事。
創作這本書的第一年,我的工作內容就是研究與規畫這本小說。我反覆思考飛機上要有哪些乘客、怎樣的乘客,然後閱讀與這些人相關的書籍作為研究。例如,構思克里斯賓.考克斯這個角色時,我讀了奇異電子公司執行長傑克.威爾許(Jack Welch)的自傳。為了描寫班傑明.斯提曼這個角色,我訪問一位從事軍職的朋友,並且閱讀賽巴斯提安.鍾格(Sebastian Junger)所寫的《戰爭》(War)一書。當然,我也做了許多關於墜機事件的相關研究。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來完成所有研究,才允許自己開始著手寫下這個故事。
▇有沒有哪個角色讓你格外鍾愛,並占據你心中的特別地位?如果有,會是誰呢?讓這個角色如此特殊的原因為何?
我喜歡書中的所有角色,真的。不過有兩個人在我心中占據十分特別的位置:佛羅里達,以及阿倫迪校長。佛羅里達是一位非常獨特的女人,特別到遇見她的人應該都會覺得不知如何是好,她的經歷、個性等種種元素,讓我在描寫她時得到相當大的寫作樂趣。此外,我真的很愛阿倫迪校長這個角色,他對艾德華既和藹又善良,而且有一個全心全意熱愛蕨類的心。
某些方面,艾德華這個角色確實反映我的一些特質。青少年時期的我,個性安靜、害羞且乖巧,整體而言,艾德華也是這樣的個性。不過,我的閱讀量比艾德華大一些,這方面我就比較像鄰家女孩雪伊了。
▇寫作這本書時,遇到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描寫艾德華一路從墜機到故事結局的這段旅程,絕對是最艱難的部分。我不希望他的故事太濫情又感傷,希望他的成長與康復令人感到真實,我因此反覆修改並調整了許多小地方。相較之下,我認為書中在飛機上發生的對話與情節,相對較容易描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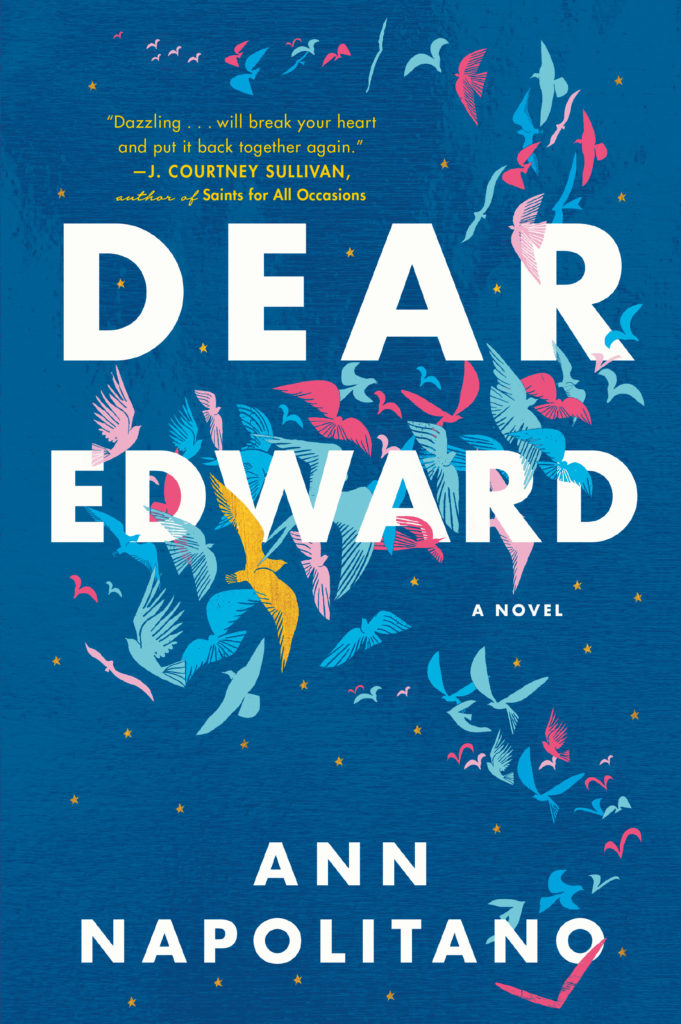
▇寫作本書的過程以及出版後,有什麼是讓你感到驚喜,或覺得辛苦也相當值得的?
寫作此書我最驚訝的一件事,是明明寫下的是一個悲傷的故事,過程中竟如此愉快。這種感覺確實不符合我的預期,會有這種愉快感受就好像是做錯了什麼。然而,我最終想通了,我之所以會有這種感覺,是因為書中的角色們,為我帶來許多善良及仁慈。發生空難之後,許多人對艾德華展現出慈愛及憐惜,身為作者的我也深刻感受到,這些善意帶給我非常大的滋養及安慰。琢磨了八年的時間,我才終於動筆寫這本書,我很喜愛身處在那個虛構世界的那種時間。
▇啟發你動筆寫作的人是誰?對於剛開始寫作的新手作家,你有何建議?
啟發我的人是9歲的我。我從9歲就開始寫作,當時有一個學校的字彙作業讓我寫到忘我,那時我就發現寫作顯然是我該選擇的那條路。我想提供給新手作家的建議,聽來好像會有點老套,不過,這確實是最有用的方法:「盡量多寫,然後再寫作、再修改。重要的是,就算你覺得寫出來的東西不算太好,也不要太灰心。」
只要持續練習,就會越寫越好。你可以找一、兩位值信賴的朋友,請他們閱讀你的作品,然後請他們誠實告訴你哪裡寫得好、哪裡又寫得差。多聽聽別人的觀點,而且是真實的參考意見,對於寫作這件事有極大的幫助。讀好書、讀好句子,每天堅持下去。
▇來到2021年,妳希望台灣的讀者在閱讀這本書時能夠得到什麼?
閱讀此書的過程中,我希望台灣的讀者們都能夠感受到故事中的種種仁慈及善意。這本書最大的意義,是為大家帶來人類都需要的牽繫與愛。
▇如果能任意邀請三位小說家或作家一起用餐,你會邀請誰?為什麼?他們如何影響了你的寫作之路?
我非常害羞,所以可以邀請仰慕的文學名人一起用餐的這件事,其實連想都不敢想,不過我就試著來想像一下。首先,我會邀請作家芙蘭納莉.歐康納(Flannery O’connor),她是一直長住在我心中的寫作者,我也因此將她寫進我的第二本小說《A Good Hard Look》。她非常機智、非常誠實,能和她一起吃飯,絕對會是很有趣的經驗。另外,我還要邀請愛爾蘭小說家大衛.米契爾(David Mitcehll),單純是希望親口讚美他的小說《雲圖》(Cloud Atlas)有多厲害。第三位人選,大概會是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因為在我二十出頭的那段時間,他的作品對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尤其是他的小說《奉使記》(The Ambassadors)。我想邀請的三位客人中,已有兩位不在人世了,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請問你手邊正在進行的寫作計畫是什麼呢?能和讀者分享嗎?
我正在準備寫另一本小說,但現在還無法以能夠讓他人能理解的方式來說明這部作品(笑)。●
|
|
|
作者簡介:安.納波利塔諾(Ann Napolitano)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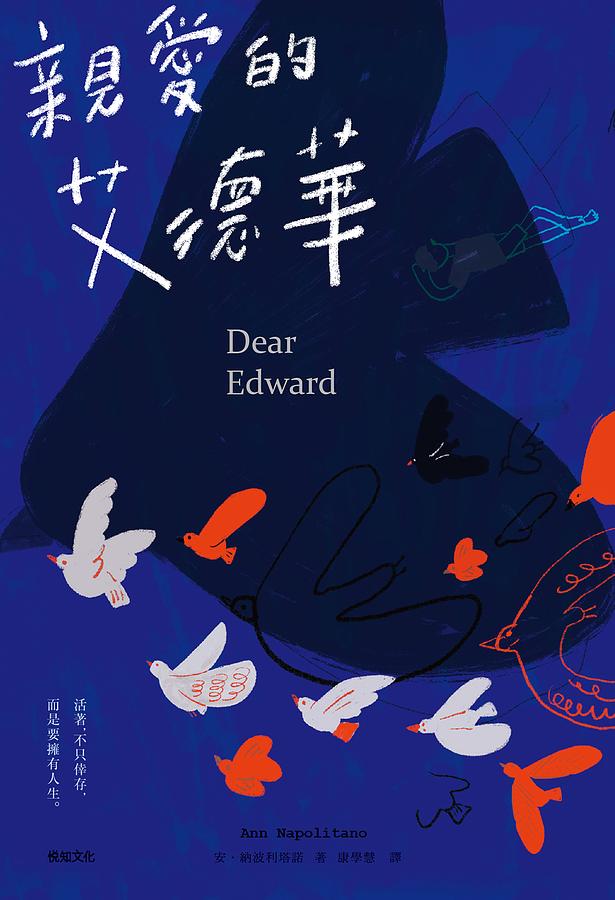


書.人生.東燁》我的大(ㄆㄧˋ)俠(ㄏㄞˊ)進化史
即使過了再多年,一句經典廣告台詞依然深烙我心,說是每個人心裡都有一位大俠。之於我,大俠的啟蒙是楚留香,但那是指膾炙人口的港劇,是鄭少秋飾演的楚留香,卻非古龍文本中的楚留香。儘管那當年還沒上小學,我卻記得香帥搓鼻子、後空翻,還有「我踏月色而來」的提扇,以及隨手一彈就撂倒強敵的翩翩風采。只是迄今始終沒能搞懂,究竟他彈出的那是一枚石子或琉璃珠,又甚者可能是枚銅錢──試想,一位能住在遊艇上且不務正業的美男,他拿銅錢出來亂扔砸人,好像也很符合邏輯?
若說我的「俠」之啟蒙是香帥,那麼俠客之路的具體實踐,大概就是《水滸傳》了。林教頭在山神廟前的滿腔憤恨,是充滿悲劇性格的一種抒發;魯智深倒拔垂楊柳,則意味著向「不可能」奮勇頑抗的膽壯。那年我國二,身材矮小,戴著看似愚蠢的黑框大眼鏡,還頂著呆瓜平頭跟幾顆青春痘,我不耐煩於潘金蓮的小曖昧,只反覆咀嚼一眾天罡星們的官逼民反,特別是當武二郎一口氣宰了張督監他家十幾口人,還在白壁上蘸血寫了「殺人者,打虎武松也」這幾大字時,我忽然就有了一種想去找國中那個籃球隊長單挑的衝動,儘管無冤無仇,但我就想找個能打的,也試試自己的拳頭。
不過當然我沒幹這蠢事,反而趁著數學課時拿出筆記本,一行行開始寫下故事。那些手稿至今猶在,收藏了將近卅年,幾萬字的水滸傳續集中,我當仁不讓成為新主角,算是第一百零九條好漢,班上同學無不叫好,紛紛報名成為配角,而數學老師理所當然是高俅之流的新反派,必然要成為我的劍下亡魂。
這麼說來,我原來其實可以算是武俠小說類型的作者?那些後來出版的愛情啊、教育啊、妖怪啊,都是我胡亂斜槓的結果。
我想像中的大俠是快意恩仇的,是在大碗酒、大塊肉中,能夠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的,更是在繁重且苦悶而又得不到宣洩的抑鬱國中小男生的想像世界中,閉上眼睛就能揮舞雙鞭、蛇矛、狼牙棒的。
好多年後,當從事教職了,我才從學生身上明白:叛逆原來區分隱性與顯性,有些人張牙舞爪如狂亂的小獸,有些人則內心醞釀光怪陸離的異想;如果國中時期的我是屬於後者,那顯然高中之後,我就演變成純粹的動物型態,那些年的抽菸、打架、飆車與翹課,十足十滿足成全了我的大俠夢,但差別是武二郎化妝成行者就輕易躲避追捕,我卻得拆了機車車牌,還得在台中雙十路上跑給警察追。
那時我開始喜歡上課偷看小說,也認識了幾個以後影響一生的朋友,當中有些人讓我白眼無數,例如憨頭蠢腦的郭靖,即使他排山倒海的掌法確實迷人,但那個性委實教人倒胃口;有些則豁達灑脫,其不馴性格簡直是我夢寐以求的楷模,就連一柄長劍信手揮灑,令狐沖也能演繹著天生就該他練的獨孤九劍──只是同樣秉持著過於無所謂的性格,人家令狐沖最後可抱得美人歸,我卻差點連高中都畢不了業。
所以在那個與寫作絲毫沒有牽扯的年月裡,我偶爾去上學,偶爾跟朋友鬼混,更多的時間裡,則跟玩樂團的同好們鎮日捧著樂器窮攪和。我深深覺得,玩團的人才是真正的放蕩不羈,也更加確信,其實我信奉的大俠之道,既不是俠之大者的郭先生,也不全然是笑傲江湖的令狐沖,當然更不是投機取巧卻總是狗屎運到家的韋小寶,而是一生坎坷流離,卻始終傲氣不減的楊過。
那些年除了音樂,我滿腦子只想遇見一位屬於我的姑姑,在那個帶著大半悲劇色彩的愛情典型中,無意間也奠定了我後來的寫作風格與人格,只是當時自己並不自知,原來無論水滸或金庸,我走的都只是一條自以為很酷的屁孩之路而已。
這些事我很少對別人提及,總感覺講了也未必誰有興趣,然而他們真實發生過也存在於我的生命中,甚至形塑成一個後來的我。後來的我的樣貌,朋友們是這樣說的,他們說無論穹風或東燁,這人所在的地方,必然有酒,必然有恩怨,必然有他任性胡鬧的樣子;但在更後來的後來,當了老師以後,我則說遇見那些比我當年更匪類的頑徒時,我才知道自己當老師,原來是一種對年輕時狂妄躁動的報應,活該我作惡多端,現在也只能一天到晚幫小孩擦屁股,一邊料理他們,還得偶爾望著編輯撥打的來電顯示,盤算著該如何瞎掰拖稿的理由。
寫過很多小說,儘管多是些類型故事,但起碼也塑造了上百計的主角們,可是我一直無法為所謂的「大俠」立下一個確切的定義。或許是因為在生命歷程中,有過多個截然不同的階段,而每個階段又變異太大所致;好像相去數年之間,想法就會一折又過一折,從浪子般的香帥開始,到青面獸、豹子頭、花和尚與黑旋風的江湖縱橫,再轉向令狐沖的笑容與楊過的孤傲,最後則融成了手拿粉筆,一邊聊著元稹如何愛過一個又一個,一邊又提醒學生要謹守分寸,別讓已經案牘勞形的我還要費心處理他們的性平案件的游老師──想到這裡,我忽然開始理解那個一直很北七的郭靖最後為什麼會戰死在襄陽了。
原來,大俠不見得都是男人,也未必非得武功高強──大俠如果活在一個不能說殺人就殺人的年代,武功再高也沒屁用──所以大俠也許可以亦正亦邪,任性描繪他的俠影,那可能是一段用刻骨銘心四字來形容都嫌淺淡的愛情故事,也許則奇想成雙掌翻飛出術法靈光的遊仙,在海平面上酣鬥一條紫電龍王,甚至我幻想每天遇見的那位開宮廟還撿回收垃圾的阿婆,就是隱姓埋名間,卻身懷絕技能通神驅鬼,一記靈符就打得你魂飛魄散的不世高人。
大俠會有諸般面貌,不同身分或職業,他們可能沒沒無聞,卻在心中貫徹自己的信念而無怨無悔。現在我是這樣以為的,就像這一陣子,我挺喜歡大陸的靈異故事《我當陰陽先生的那幾年》,每每開車無聊時、在浴室洗衣服時、拿著拖把清潔屋子時,手機打開還是崔作非手執「甲午玉卿破煞符」在力戰五通神或老殭屍的小說廣播劇。那個乍看之下毫不起眼小青年,彷彿只是個社會底層的打工族,卻遭逢無數危難,在搭救蒼生之餘,又困於修道人的五弊三缺而不能脫身的悲劇中還能自嘲自解的模樣,對不惑之年的我而言,想來這興許就是這階段的我的大俠了吧?我這樣想:不然還能怎麼辦?你已經知道自己沒有天賦異稟,既沒有撿到玄鐵重劍的巧合際遇,也沒有思過崖上遇見風清揚的狗運,你只能在生活的小小小細節中,去實踐一點點的大俠夢,你不這麼覺悟,不然還能怎麼辦?這年頭,連當一個屁孩都要這麼卑微,日子也真是苦難得很了。
於是當寒假終於又要到來,「讀書心得寫作單」發給學生後,我已經不復從前那麼期待,短暫的一個月裡,別去奢望孩子們碰觸什麼經典名著。他們也許會挑戰幾個困難的副本,或結隊共同經歷一段遊戲裡的冒險,甚至像我當年一樣,甩開離駕照還很遠的顧慮,一扭油門就奔向輕狂飛揚的大千世界,但我並不感到太過絕望,畢竟這也許是世代的不同,當年我們只能在筆畫點捺之中尋覓並勾勒自己的大俠形象,而現在他們則有自己的方式,如此而已。
反正每個人心裡都有一位大俠,隨著年齡增長,大俠的形象會一變再變,我有我的大俠演化史,我想孩子們應該也是吧?那些他們讓現在的我很看不慣的,不也正好是當年長輩們對我極不順眼的?大俠本來就是叛逆的,沒一點叛逆性格的話,還當什麼屁大俠呢?
所以我就繼續心安理得地,當一個學生眼中的老屁孩了。●
東燁
東燁,以前是穹風。
從電機到中文,從中文到視傳;曾經是作者,後來是酒吧老闆,不小心當過樂團主唱,現在變成國文老師;相信世上好玩的事情永無止盡,更堅信生命永遠都有值得探索的極限,這就是我。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