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部放送》2025Openbook好書獎怎麼選?選完之後呢?
強調公正、客觀的年度好書評選,希望藉此推廣閱讀,鼓勵優秀作家及出版社。得獎者獲贈獎座,無獎金。
➤評選對象
前一年度11/1之後,至當年度10/31期間,於台灣出版或代理銷售的繁體中文著作。
➤評選標準
【一般書籍】
- 為一般大眾挑選出一年內最不能錯過的好書。入選的書,須具相當可讀性,「是好書,也是好看的書」,可讓讀者享受閱讀的樂趣,亦能提升視野。學術用書及太過冷僻、專業的作品,不列入評選。
- 優先選出具有:啟發性、前瞻性,能帶動文化提昇的書。
- 考量重點:整體編製水準、文字表現(包括翻譯)、知識的正確性、題材開創性、架構完整等角度。並考量當前資訊呈現形式、閱讀環境及閱讀習慣的多樣性,選出能召喚當代讀者共鳴、吸引更多讀者加入閱讀行列的年度好書。
【兒童暨青少年圖書】
- 選出今年度內,最值得推薦給一般兒童(3到12歲)及青少年(13到17歲)閱讀的好書。入選書籍必須「是好書,也是好看的書」。
- 以兒童及青少年讀者為中心來評量,具啟發性、創意、圖文俱佳的書。
- 具出版之指標性、前瞻性。
➤初選:從2209本書中,選出614本成人書、248本童書
整年度每週進行。Openbook編輯部廣邀出版社提供新書資訊,每週匯集最新出版的新書和即將出版的電子檔書稿,由選書小組集中閱讀。以一個下午的時間,讀畢後進行逐本討論,各自發表意見並投票,過半數者即成為年度好書的初選書單。
選書小組分一般書籍組與兒童&青少年圖書組,前者每週開會一次,後者每月選書一次。小組成員來自不同領域,一年一屆,每屆更新。選書期間,選書小組對外匿名,以期保有獨立性,不受人情干擾。選書小組並針對入選書籍,撰寫OB短評或童書短評。
#2024年11月到2025年10月評選期間,我們讀了2209本書,選出614本一般書籍以及248本童書
#感謝不能叫出名字的每週選書小組,一整年辛勞選書(編輯部全體拜上)
➤複選:從862本書中,選出206本決選入圍名單
每年7月至10月進行。召集複選委員,4個月內分3到4次,針對所有初選作品檢視書單。
在614本成人書與248本童書,陸續汰選出當年度入圍決選,4大類共206本(含套書)的書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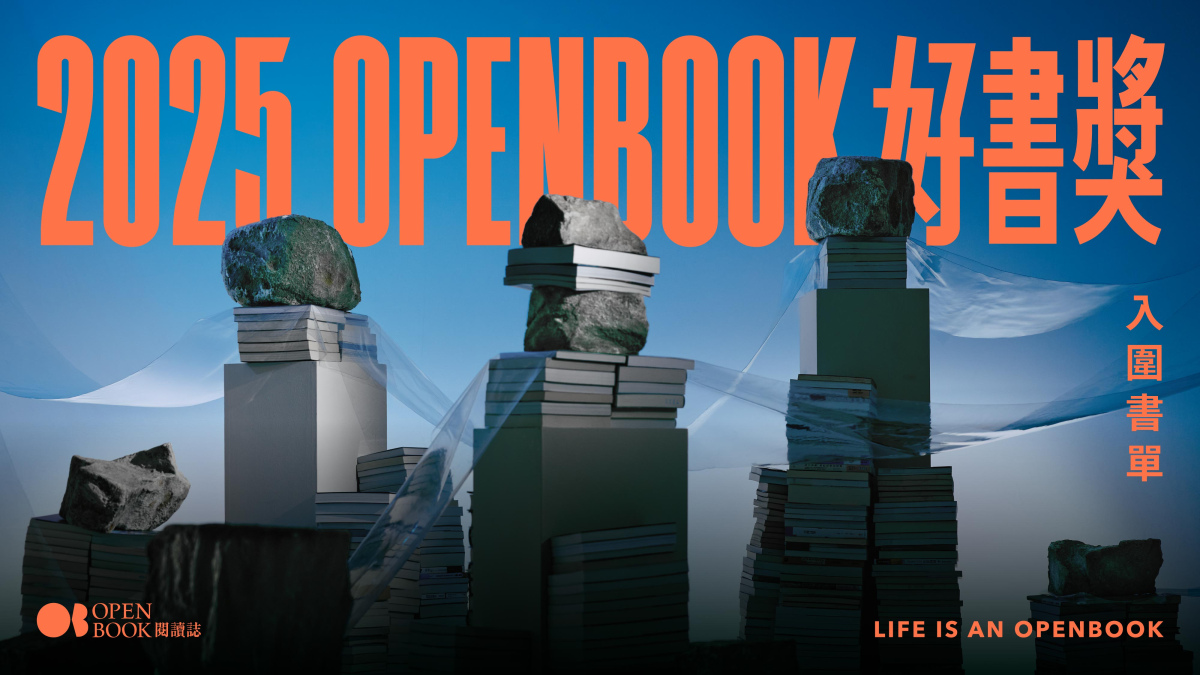
➤決選:從206本好書中精選出4大類Openbook年度選書
為期3個月。自8月開始,陸續將入圍作品寄給決選評審,要求必須詳讀每一部入圍書,並於11月中舉行會議。經過詳實縝密的討論評選後,得出最終推薦書單。
#一週一週緩慢前進,用一整年的時間,選出最值得推薦的作品
➤贈獎典禮
每年12月,邀請出版社、作家與媒體一同與會,頒發年度Openbook好書獎,向得獎作家及出版人致敬。
➤好書貼紙與國內外作家得獎影片
每本年度好書都會貼上Openbook好書獎的貼紙,並邀請國內外作家拍攝得獎影片。
➤全國圖書館好書獎聯展
Openbook閱讀誌透過不同方式,推廣所有得獎好書,讓作家與出版人的辛苦成果被更多人看見。希望藉由好書的閱讀討論,引起更深、更多元面向的對話。
邀請國家圖書館、全國各縣市超過500家公私立與校園圖書館,合作舉辦聯展,將用心選出的好書,推廣到台灣各鄉鎮市。







➤全國網路與實體書店好書獎聯展
Openbook好書獎,是全台與最多圖書館及書店合作的優良書籍獎項,感謝以下單位:全台「好書獎聯展」參展圖書館與獨立書店、Hyread電子書、MLD台鋁書屋、MOMO 書店 & MOMO Book、Rakuten Kobo Inc.、Readmoo讀墨電子書、 TAAZE 讀冊生活網路書店、TSUTAYA BOOKSTORE、UDN讀書吧、三民書局、中央書局、五南文化廣場、友善書業供給合作社、文訊、台灣雲端書庫、灰熊 iREAD、REEDS BOOKSTORE、金石堂、台南政大書城、紀伊國屋書店、現流冊店、書房有光、琅琅書店、博客來網路書店、誠品線上、墊腳石、麗文連鎖校園書局、民樂書坊、露天市集等,一起推廣Openbook好書獎。

➤台鐵區間車、捷運月台宣傳影片
- 在捷運月台電視、無線電視頻道、台鐵區間車都可以看見Openbook好書獎的宣傳影片。
- 為得獎作家拍攝肖像照與得獎影片,留下歷史的記憶,在贈獎典禮首度曝光後,提供給各大參展單位。
- 邀請國外獲獎作家,為台灣讀者拍攝得獎感言,在贈獎典禮首度曝光後,提供給各大參展單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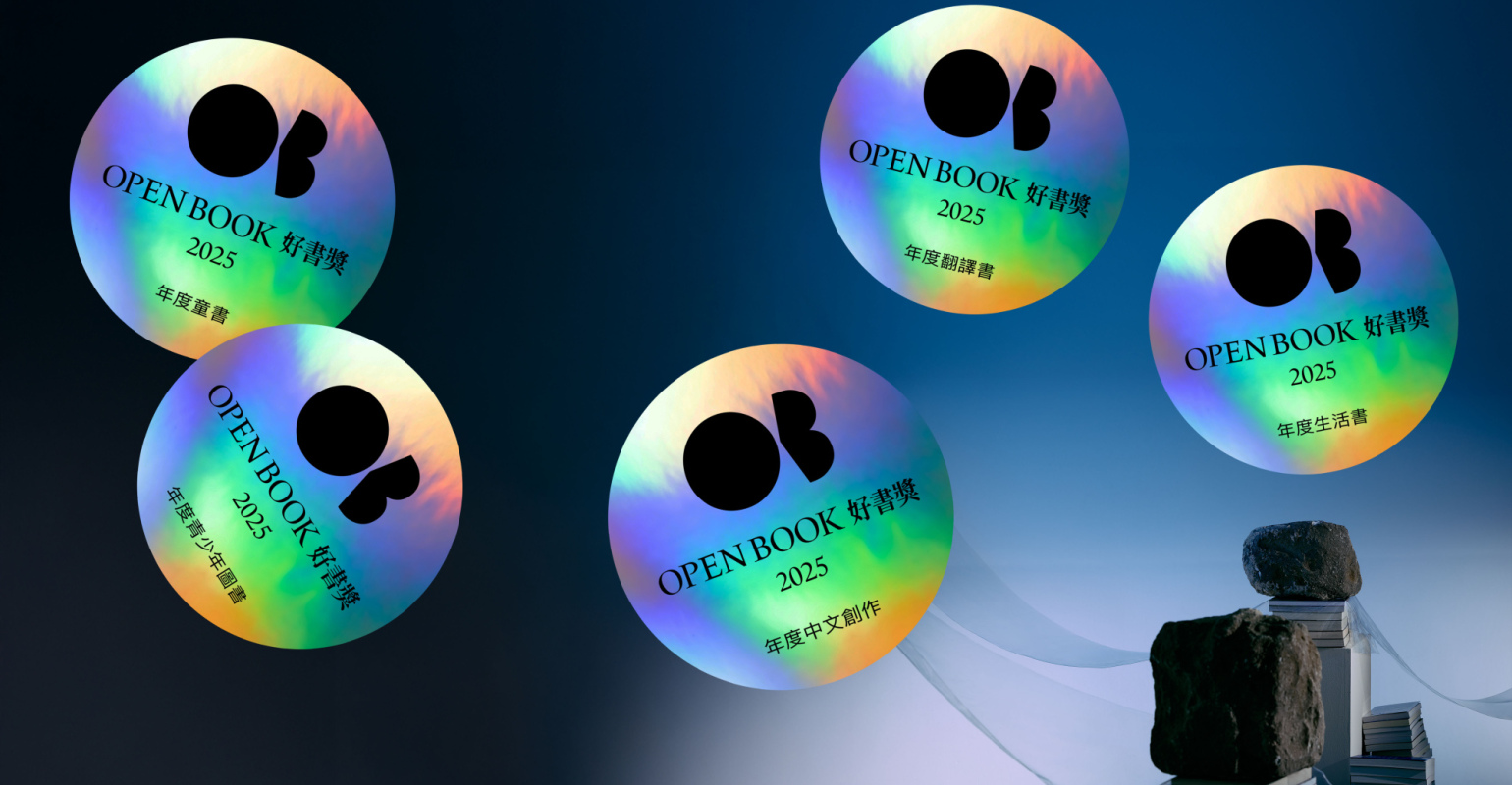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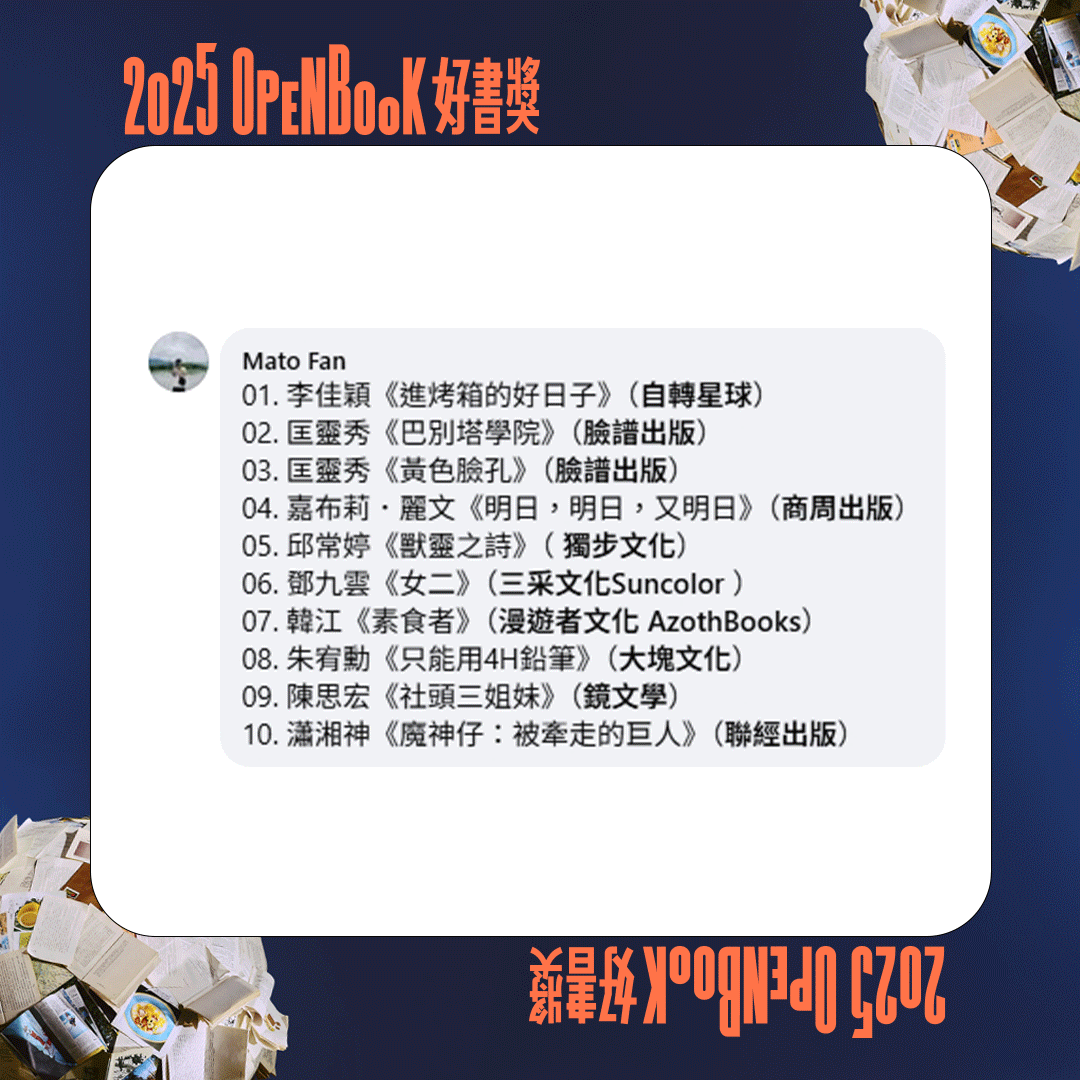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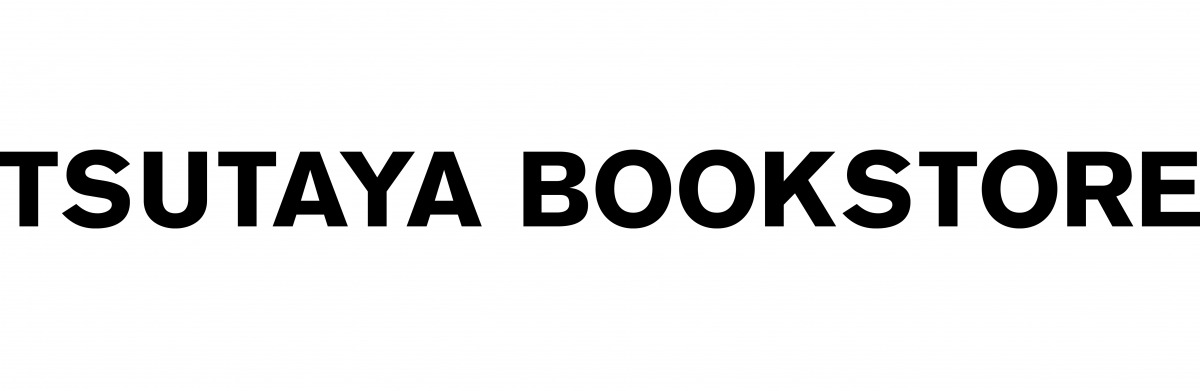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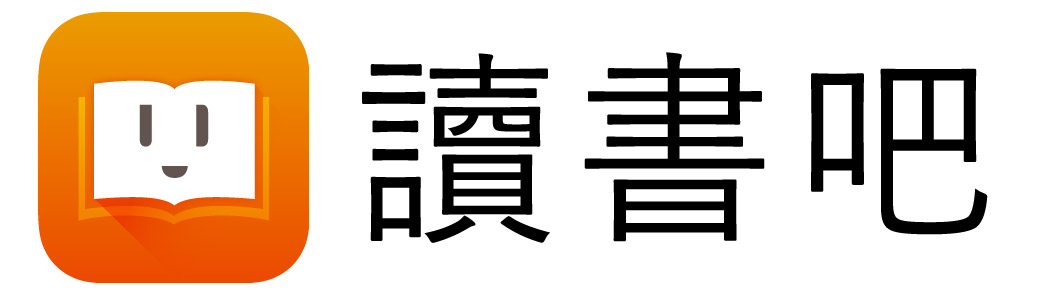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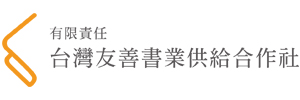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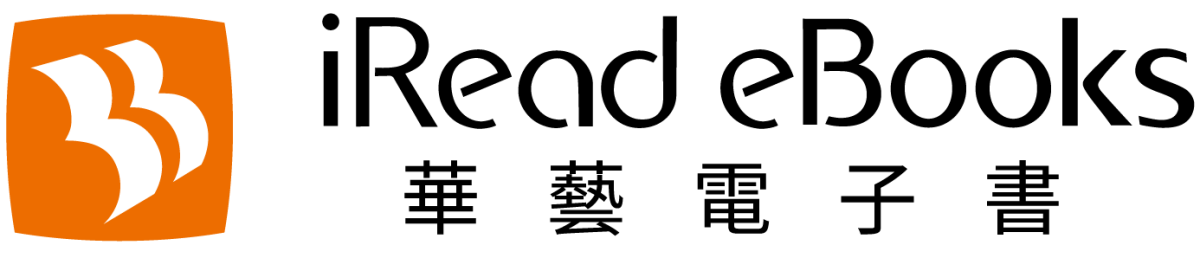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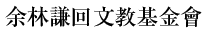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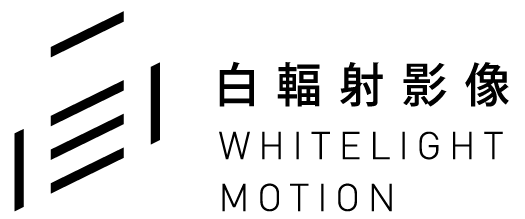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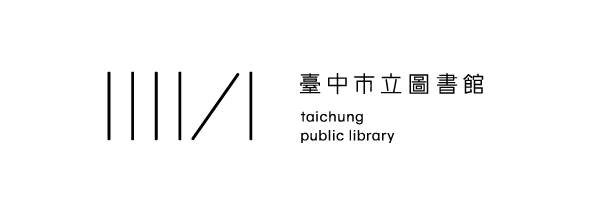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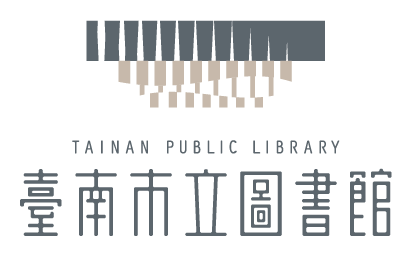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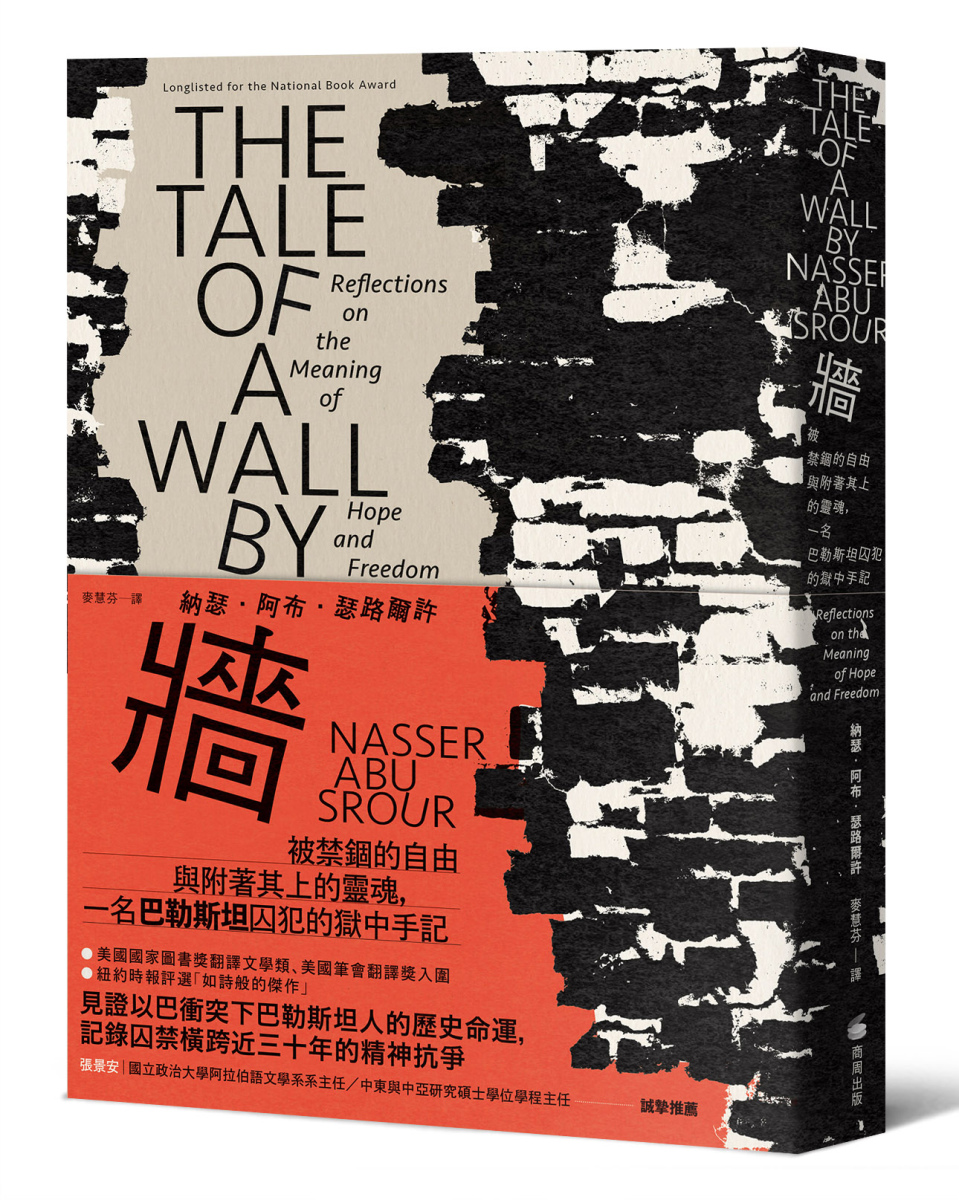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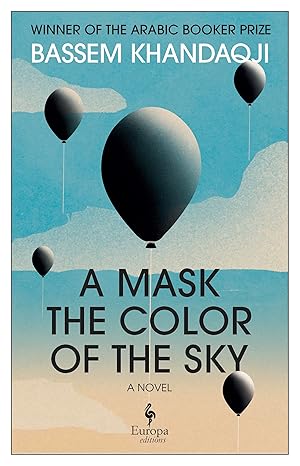
OB短評》#556豐富五感體驗的極品好書懶人包
●昆汀論塔倫提諾
Quentin par Tarantino
驚奇阿梅仔(Amazing Ameziane)著,江灝譯,木馬文化,850元
推薦原因: 知 樂
第一人稱的展開,彷彿由塔倫提諾親自帶我們步入他以影像構築的人生迷宮。圖像與文字雙線並行,致敬與解析交錯,既宛如他作品的風格,也猶如以電影手法剪接出導演自身的生命歷程。當讀者在閱讀中感受他的熱情、執念與創意,作品中的各種機關也隨之攤開在讀者眼前。【內容簡介➤】
●聲音的形狀
環境錄音入門──從聲音遇見世界
フィールド.レコーディング入門 響きのなかで世界と出会う
柳澤英輔著,黃大旺譯,二十張出版,400元
推薦原因: 知 實 樂
這本環境錄音入門音場遼闊,彷彿發現了第三隻耳朵,豆知識嘩啦啦傾囊而出,宅感十足,讓人想起最佳音效奬得主們上台領獎的臉。雖說作者的使命感超級强大,不過能出現如此周延又有延展性的操作手冊,也可見環境錄音已自成顯學。【內容簡介➤】
●軌道
Orbital
薩曼莎.哈維 (Samantha Harvey)著,章晉唯譯,潮浪文化,420元
推薦原因: 議 文 樂
失眠的薩曼莎.哈維以她特有的敏銳與詩意,帶領讀者進入太空。非日常的太空其實仍有專屬於太空的日常,而面對靜謐、壯美的遠方家園時,各種被重力牽引的獨白又悄然上演。詩性而凝練的筆法,弱化了情節,強化了意識流般的思索,使穩定軌道與無垠宇宙之間的形成張力,成就了敘事極簡、視野新鮮的太空美學。【內容簡介➤】
●伯朗咖啡和地瓜球,當然也有滷肉飯
楊迎楹、陳妙恩著,時報出版,350元
推薦原因: 樂
馬來西亞作家們的食欲、念想與文筆,呈現出臺灣小吃們旅外僑居的模樣。讓我們對小吃的理解,除了其來有自的身世,也多了進行式的時態。自流徙經驗化出的色香味,折射遷移、文化連結與生活情感,讓飲食成為跨地域記憶與身分流動的入口,也蒸薰出人生歷練的剪影。【內容簡介➤】
●哭聲(圖像版)
Sobbing (Graphic Novel)
李喬、阮光民著,前衛出版,500元
推薦原因: 文 樂
近年台灣文學的圖像小說化,似乎不能沒有阮光民。從日治時期的賴和、當代的吳明益,到這部重新詮釋戰後的李喬作品,將〈哭聲〉(1969)所描繪的蕃仔林與南洋兵細緻視覺化,並保留高度文學性。阮光民以忠於原著的圖像改編,為台灣文學史建立一條支線,是以圖像美學譜寫給當代讀者的台灣文學史。【內容簡介➤】
●擦亮記憶的星塵
陳育萱著,時報出版,450元
推薦原因: 文 樂
此作以科幻預言重新詮釋全球剛一起經歷過的末日疫言,以及正在發生中的戰時與動亂狀態。在此宏大背景下,小說以「記憶」為敘事節點,推進故事情節的同時、也成為轉折的機關,同時也讓小說本身充滿哲學辯證,指向「存在」究竟為何?【內容簡介➤】
●此地即世界
臺灣,世界史的現場
Taiwan: A Global History
故事StoryStudio著,有理文化,499元
推薦原因: 知 議 樂
台灣有時處在世界邊陲,被不同地緣政治角力擠壓到邊緣處;有時卻又成為世界中心,得以解釋並預示全球歷史變革。此書採中心視角,讓台灣巷弄地景作為容器,收容一部世界史的各種片段景象,讓帝國、戰爭等議題不只有全知、宏大敘事得以述說,也可以從一碗湯開展。【內容簡介➤】
●無人知曉的藝術家之淚與宰桐義大利麵
알려지지 않은 예술가의 눈물과 자이툰 파스타
朴相映(박상영)著,胡椒筒譯,潮浪文化,450元
推薦原因: 文 樂
朴相映具有自成一格的輕盈敘事能力,能將成長、認同、經濟、親密關係中的沉重課題提煉為一抹浮雲般的普世情感,讀者能與角色一樣停滯籠罩,也能隨風輕拂。如與書同名的篇章中,「宰桐」在該作出版當下(2017)明確指向韓國軍中恐同事件,但在小說中轉化成軍隊中特有的、奠基在不同身世背景的人情連帶,不乖張也說不上抵抗,正是朴相映的寫作力道。【內容簡介➤】
知識性.設計感.批判性.思想性.議題性.實用性.文學性. 閱讀樂趣.獨特性.公益性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