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前方地平線的等待:新譯版《追憶似水年華》譯者群談翻譯的心路歷程
他們動身。從巴黎近郊、里昂、台北與台灣各城出發。歷經數年視訊協談,如今實體晤面,齊聚在以普魯斯特作品中的文學符號為名的法式餐館裡。
他們是《追憶似水年華》(以下簡稱《追憶》)譯者群:邱瑞鑾、陳文瑤、許雅雯、石武耕、陳郁雯與林德祐(第六冊譯者馬向陽不克前來),統籌企劃吳坤墉,聯經出版公司發行人林載爵、副總經理王聰威、編務總監陳逸華、企劃主編黃榮慶及校稿江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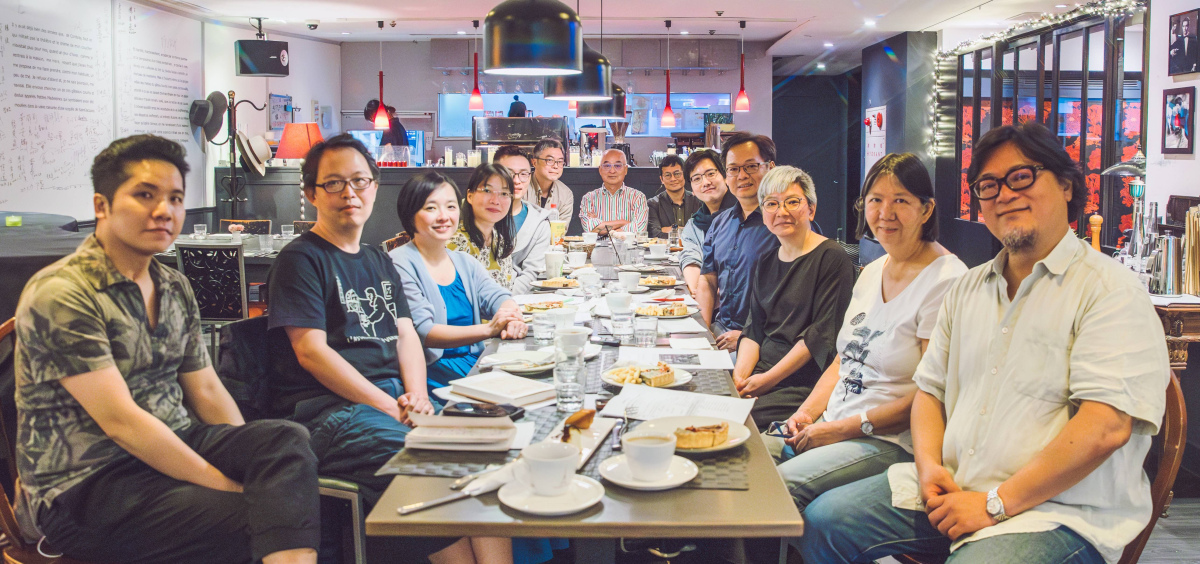
重譯普魯斯特鉅作之初,始於2020年10月的一場晚宴。酒過三巡,林載爵向出版人/譯者吳坤墉提及,舊版《追憶》套書為台灣唯一中譯本,是聯經出版的長銷品,但內文有部分訛誤,林發行人心生此書的重譯計畫,掛念多年。
曾任「台灣法語譯者協會」理事長的吳坤墉擔起統籌企劃之責,以譯筆優異、且適宜團隊合作為考量,打造前所未有的譯者陣容。
世人為何需要一套《追憶似水年華》全新譯本?面對此提問,眾譯者有所共識:文字易老,30、40年前的中文與當代語感不同,經典需要不斷被重譯,好在新時代中產生新的脈絡。
「我們可以把普魯斯特的作品想像成一個前方地平線的等待,每隔一段時間,用一個新的語彙重新詮釋。」林德祐說道。翻譯過程中,他不時回頭參考前譯,發現許多小錯,乃因普魯斯特文字的難以詮釋,導致的誤判瑕疵。而此回翻譯依據的原文版,法國的Gallimard出版社在書中加上許多編注,讓譯者們釐清不少線索,好糾正舊版,建立更正確化的譯本。
石武耕認為,整體社會,無論台灣或世界華語語系,顯然比20、30年前更接近普魯斯特在百年前所架構的世界。現在人們普遍擁有更貼近書中氛圍或處境的生活經驗,比如:文青、出櫃、政黨對立,或賣弄不成反露餡等情境。在有更充足的物質與精神資源的前提下,譯者能操作以譯文所構成的文字遊戲。
許多譯者在接下重責時,皆曾想過自己是否越級打怪。
邱瑞鑾在60歲生日當天接獲合作邀約。身為獨譯西蒙・波娃《第二性》的資深譯者,她花了2個星期密集閱讀《追憶》,進行段落試譯,參考坊間分析普魯斯特長句的專書後方才應允。「普魯斯特是個思路清晰的人,但這點常被長句所掩蓋。長句把讀者搞得摸不著頭緒。一旦把前後文弄清楚了,會發現他細膩而清晰的思路。有些句子,他為了製造特別效果,把總結放末句,身為譯者不能破梗。句子的型塑安排,有時甚至跟文本象徵連結。」她說。
眾人帶著各自的生命與職業歷練步入文本。

曾從事華語教學的許雅雯,對原文的標點符號使用習慣保持不同意見。《追憶》中大量使用分號與逗號,但面對中文讀者與華語文法結構,她有時選擇以不同方式收束,「中文分號一般代表並列主題,必須是講一同件事,可能是不同的面向或層次、同類排比才行。但普魯斯特的用法很多時候是補充說明,想要加一些佐證,用分號先分開。」許雅雯解釋道。
過去她大部分翻譯小說,但《追憶》讓她質疑,這是小說嗎?抑或屬於散文或隨筆的狀態?順序非線性,有主線,但中間會冒出大量論述。該換語氣嗎?她無法用純粹翻譯小說的方式前進。
先前大多翻譯社科類書籍的陳郁雯指出,社科類領域是可預測的,詞彙較固定,脈絡有其框架,譯者將作者文字表現出來,確定不失真即可。而文學作品書寫的畫面或感覺,有其不確定性,這勢必牽涉到譯者對自身過去經驗的想像。她的翻譯步調因此慢了下來,早期調整自身節奏時,曾一天只翻譯了200字。
陳文瑤大多翻譯圖像小說,平時注意圖像跟文字間的呼應。她說翻譯《追憶》之際,需在腦海裡添加畫面感,方便進入文字。她參照了第二冊《在花樣少女倩影下》的漫畫版本,並從中獲得建築樣貌等資訊。
這本書的第二部場景發生於海畔,陳文瑤是海邊長大的小孩,書裡的諸多海景形容,讓她在翻譯時,反覆調度兒時記憶:關於海的聲音、陽光投擲在海上的花樣、海浪形狀,岩石底的陰影等等。
普魯斯特的法語魔力,婉轉於長句與繁複的詞彙間。眾人踟躕,前進,彎越過層疊迷宮抵達文本核心。普通讀者又該如何閱讀普魯斯特耗盡一生心血的文學結晶?
眾譯者以為,若覺得《追憶》7冊書過於龐大,可根據自身有興趣的主題,如:愛情、衰老、嫉妒、死亡、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歐洲社交場、關乎猶太認同的德雷弗斯事件,或作者間接表達的酷兒形象、人文藝術等,都是能令讀者有所收穫的切入點,進而尋找屬於自己的普魯斯特瑪德蓮時刻(Madeleine Mo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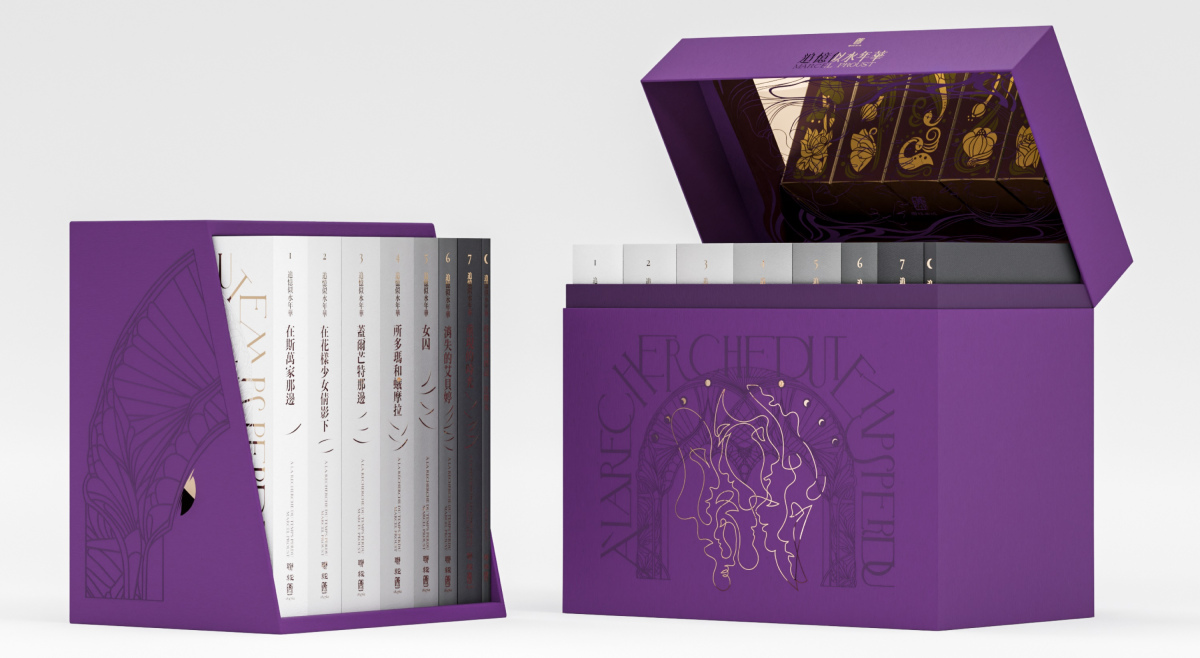
|
追憶似水年華 |
|
作者簡介:馬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 出生於巴黎一個富裕且極具文化氣息的家庭,父親是知名醫學教授,母親則來自猶太銀行世家。自幼體弱多病,長年受哮喘困擾,使他有更多時間沉浸於閱讀與寫作,培養出細膩的觀察力與豐富的內心世界,並對文學與藝術產生濃厚興趣。青年時期,活躍於巴黎上流社會沙龍,結識眾多文人與藝術家,這些經歷成為日後他筆下作品描繪社會場景的豐富素材。 早年投身文學,曾翻譯英國藝評家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的著作,並創作詩歌與小說。作品中不乏對時間與記憶的哲學思索,認為生命的真實不限於表面的事件,更深藏在記憶中那些微妙的感官瞬間。1907年,開始構思並創作《追憶似水年華》,前後歷經十餘年,將自傳色彩、社會觀察與心理剖析融合,形成獨特的敘事風格。書中以長句和意識流技巧,細膩刻畫人物內心,開創了現代小說的新境界。 1913年,《在斯萬家那邊》(Du côté de chez Swann)遭多家出版社拒絕,最終自費出版,遂逐漸獲得文壇肯定。1919年,《在花樣少女倩影下》(À l'ombre des jeunes filles en fleurs)出版,並榮獲龔固爾文學獎,奠定其文學地位。然而1922年,他因病辭世,生前未能親見全套作品出版。除《追憶似水年華》外,早期作品包括創作短篇集《歡樂時光》(Les Plaisirs et les jours)及未完成長篇《讓.桑特伊》(Jean Santeuil),有文學評論集《駁聖伯夫》(Contre Sainte-Beuve)等,展現其對文學與藝術的廣泛關注。 普魯斯特對時間、記憶與藝術的深刻探討,使其作品在世界文學史上享有不可動搖的地位,至今仍影響無數創作者與讀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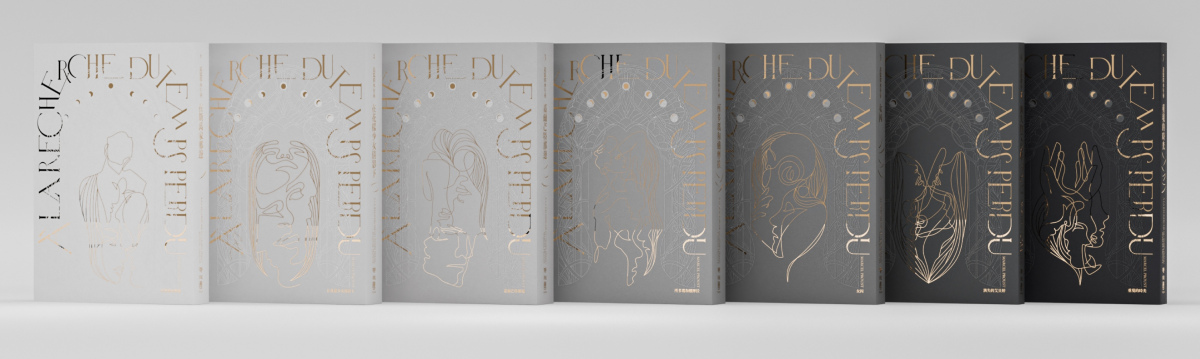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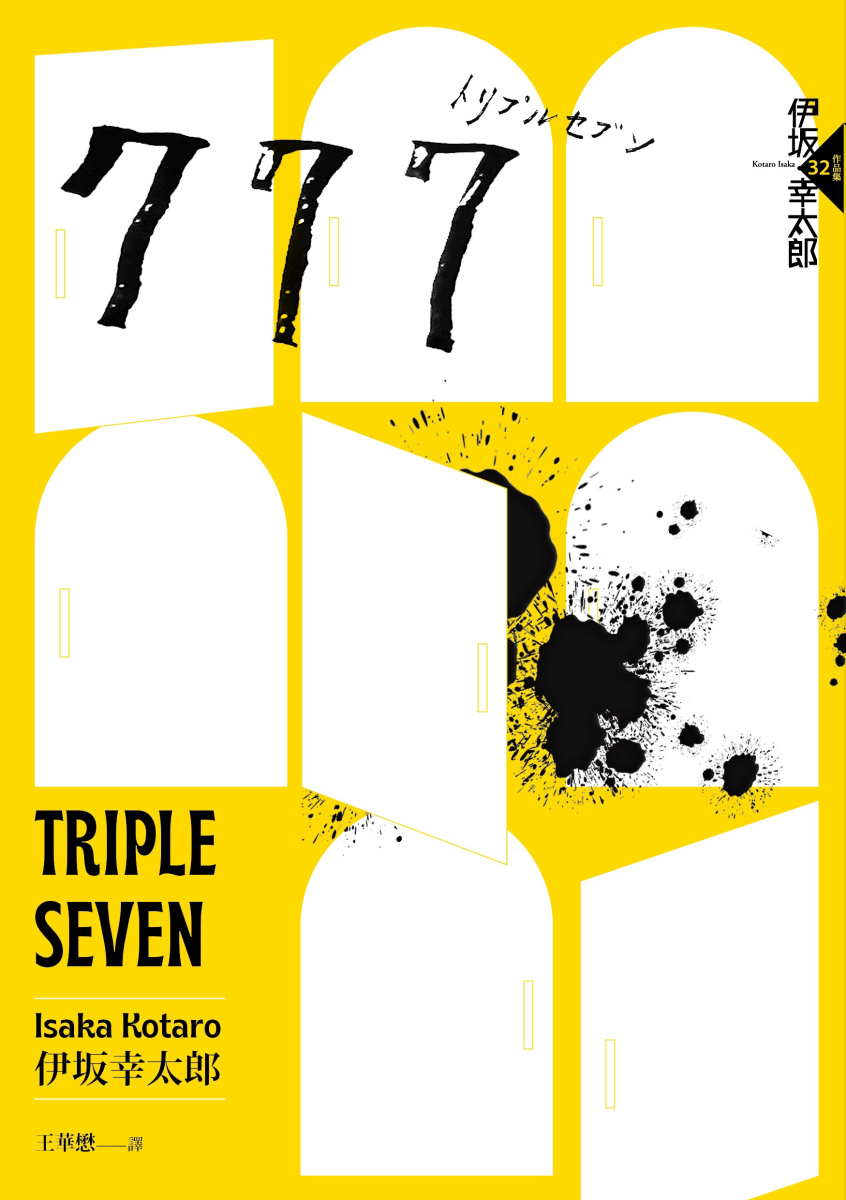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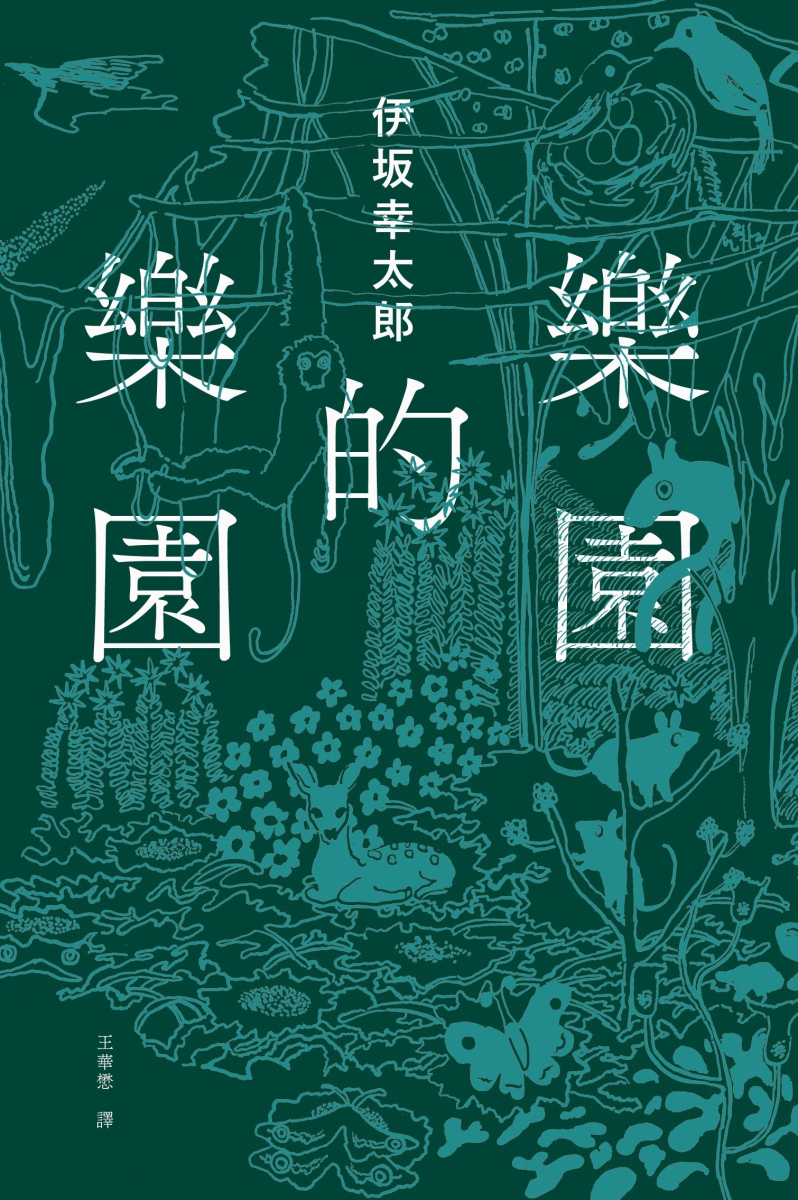 樂園的樂園
樂園的樂園
閱讀隨身聽S13E3》遠離創傷、面對童年與療癒自我的勇氣:訪作家曾多聞
童年的創傷或許不止於自身,也可能跨越世代,對後代的心理與行為發生負面影響。在美國擔任記者多年的曾多聞,以為自己在成年後已經逃離家庭暴力的陰影,卻逐漸覺察到原生家庭的傷痛,仍不時影響著情緒與人際。在積極療癒的過程,她逐漸長出面對創傷的力氣與勇氣,更加認識自我,反思婚姻、家庭生活與親子關係,阻止創傷代代相傳。
「愛與傷的總和」專題系列的第一場,邀請到近期出版《代際創傷:讓傷害到我為止》的曾多聞跨洋接受「閱讀隨身聽」專訪,分享她覺知、梳理傷痛的歷程。
【精華摘要】
➤書寫童年創傷的因緣
主持人:這本《代際創傷》看到書名就讓人滿有感的,是否有讀者曾經表達,看到書名觸動了什麼?也可能有些聽眾還不知道你的遭遇和這本書的內容。
曾多聞:會寫這本書,一方面是個人的成長,另一方面也是時代的改變。大約10年前,我替一家雜誌寫了一篇關於固執的文章,源自德國的大學所做的研究,指出固執這個人格特質,多半是基因造成的。固執的小孩經常也有固執的父母,親子衝突可能特別激烈,但還是有辦法克服。
我覺得自己就是一個固執的人,有固執的媽媽、還有兩個固執的小孩。小時候我媽媽處理親子意見不合的方式,就是先打我一頓,所以我常常傷痕累累的。等到我自己當了媽媽,面對我固執的兒子,已經不用打罵,而是用聆聽跟引導的方式。
當時我由自己的經驗出發,討論面對固執的小孩,為人父母可以如何處理。但文章完成後,編輯說我的童年經驗對讀者來說太衝擊了,所以沒有辦法刊登那篇文章。
之後我就開始在自己的部落格上書寫童年經驗,得到很多的讀者迴響。從雜誌沒有辦法刊出文章,到有出版社邀請我出書,可見這個社會對於兒童虐待這個曾經是禁忌的話題,已經有了反省的勇氣。
主持人:人們對於「家」 或許希望對外呈現父慈子孝、光鮮亮麗的形象,但這說不定是一個假象。我認為雜誌應該揭露家庭關係裡的種種面向,然後對讀者有所幫助。但是他們選擇不刊登,你的看法?
曾多聞:我覺得當時的社會風氣可能還沒辦法接受,有人打破「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這一點。我爸爸是工程師,有很好的收入,媽媽是家庭主婦,待人接物都謙和有禮。在外人眼中,我們是一個模範家庭,但是外人看不見,關起門來的時候,父母是怎麼對待我的。因為我從小被打,我也以為被打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但是有一天,醫生問了我身上的傷,我回答是被打的之後,媽媽馬上就否認,說是我自己跟妹妹打架弄傷的。回到家媽媽警告我不能再跟別人說我被打,那一天我才第一次意識到,原來打人或被打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如何覺知傷痛的影響
主持人:那你怎麼長成現在這樣健康、開朗的樣子?你如何理解自己受到的待遇,是對我好的,或者那是不愛我呢?
曾多聞:其實很多人直到長大,都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受過創傷的。因為被虐待的小孩,不會停止愛父母,只會停止愛自己,不會意識到受到的待遇可能是不對的,通常會責怪自己。
我改變的契機是大概20年前,我一個人來美國求學,當時抱著再也不要回台灣的決心,而留學生的平均成績要達到一定標準,才能有合法的居留身分。在美國的第一個學期,有一個科目沒有達到80分,我就非常慌張,害怕被遣返,但其實不至於。
我去找教授爭取分數的時候緊張得哭了,現在還記得當時教授驚訝看著我的樣子,他說不知道為什麼我反應這麼大,這不是特別不好的成績。他建議我去健康中心諮詢,那時候我很抗拒,說我很正常、沒有病,只是不想回台灣啊。
教授說在美國很多人都會去諮商,這很普通,跟我說就去聊一聊,先去一次就好。之後我展開長達5年的憂鬱症治療,才逐漸意識到創傷造成的影響,也才走出童年陰影、走入婚姻生活。現在我不敢說是很開朗了,但至少是個溫和堅定的母親。
主持人:當你有機會可以遠走的時候,是義無反顧地遠離這個家庭。回過頭來看,這個離家的行動也許已經是抗拒傷害的表現了?
曾多聞:我覺得那個時候離開家的心態,是有點自暴自棄,覺得反正你們都不喜歡我、都討厭我,那我就離你們遠一點好了。
離家來美國留學,是第一次的出走,到寫下這本書,已經過了20年,可以說是第二次的出走。因為一直到2年前,我都還沒有放棄跟父母和解的希望,也一直努力。但是最後我認清了失敗,才答應寫下這本書,心平氣和地原諒過去,然後放下。
主持人:你提到教授建議你去諮商、看心理醫生的經驗,我們的文化好像覺得看心理醫生就是精神病、是恥辱的,最好不要去。但就像是每個人都會感冒、去看醫生,若心理有一些狀況,自己沒辦法處理,那就尋求幫助。首先要有病識感,這往往就是最困難的,關於病識感的建立,你有什麼看法?
曾多聞:對,我在接受專業協助之前,也從來沒有想過我需要被療癒,或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受傷的。一直以為只要我更努力、做得更好,父母就會喜歡我,我的問題就解決了。
現在也常常接到讀者朋友來信,徵詢我的看法。但我不是專業的心理諮商師,能做的首先是同理他們,告訴他們你不是自己一個人。也想在這裡跟大家說:不要用AI當心理醫生,去諮詢它們是很危險的,要尋求專業的協助。
➤無意識的創傷傳遞,有意識的療癒與改變
主持人:會不會最需要得到諮詢或幫助的,也許是你的父母?
曾多聞:學生時期接受諮商,心理醫師確實建議我跟家人一起尋求專業協助。但那時還沒有讓父母知道,一方面因為我跟父母親的關係不好,一方面也覺得,我把自己的事處理好就好了。
後來我結婚生子,父母來美國看我時,我才第一次告訴他們我曾經接受心理治療,也許我們可以考慮接受家庭治療。可是我父母聽了非常生氣,不但不接受建議,甚至不相信我真的有憂鬱病史。
主持人:關於「代際創傷」的根源,或許是因為世代之間的差距非常大。近100年來人類生活的世界,其實變化很大,家庭這個機制也受到很多挑戰。我想父母那一代,對於精神疾病或許有很強的排斥,可能光提及就有非常大的反感。
曾多聞:對,我們這一代的家庭型態,可能是百年來改變最大的——或許未來的變化更大,而代際創傷可能一直都存在,只是我們現在才意識到而已。目前這個概念已經比較普遍被認識,個體受到的創傷,在個體自身沒有察覺的情況下 ,不經意間傳遞到下一代身上。而我們這一代的幸運是,有機會去覺察,即使沒辦法改變父母,但我們可以幫助自己。
主持人:人不能選擇爸媽、也不能選擇兄弟姐妹,如果困在家庭中感到痛苦,沒有辦法改變的話,能做的好像就是逃跑,但是身體逃跑不見得心理就放下了。我閱讀這本書的時候,也會感到有種懼怕,因為遺傳的力量很大、環境的影響也非常重要。雖然抗拒父母做的事,終有一天我會變成父母那樣的人嗎?你有這樣的恐懼或擔憂嗎?
曾多聞:是,我們可能沒辦法改變父母,但是仍然有力量可以改變自己,斬斷代際傷痛。療癒不是等別人道歉,是自己要覺悟。而關於環境的影響,雖然我不幸生長在一個有暴力問題的家庭,但是也遇到過伸出援手的,例如剛才提到的大學教授,還有中學時期鼓勵我寫作的導師。
有一次我的兒子調皮、頂嘴,我對他大喊後轉進房間關上門,他也受到很大驚嚇。當時話一說出口我就後悔了,我在婚前接受多年心理治療,婚後也持續看診,是覺得自己已經準備好的情況才生下孩子,而許多努力在一次親子衝突後就破功了。
那時覺得很挫折,冷靜下來後,我告訴兒子,每個人都會有做錯事的時候。我想我總有一天要跟他解釋,我的童年經驗,以及我如何走出來。我確實害怕成為跟媽媽一樣的人,但也只能繼續努力,有過錯也不要放棄,要想辦法修正。
主持人:那你現在會用什麼方式或態度來看母親呢?
曾多聞:我少女時期很恨媽媽,但是現在回想起來,其實我並不瞭解她。我不知道她小時候發生過什麼事,我想她一定有發生過什麼事,但她從來不說。
我長年擔任記者,採訪過在美國社會引發廣泛關注的幾宗虐兒致死案件,這些涉案的母親,她們本身無一例外都有被虐待、或被家暴的經歷,這就是代際創傷。
➤以文字與書自我陪伴
主持人:你從小就喜歡寫作,即使父母不願意你寫作,但你還是繼續寫,表示你有很強的動力,也可能寫作就成為一個窗口,或者自然的療癒方式。可以這樣說嗎?
曾多聞:的確是,可能覺得自己一定很不好才會常常被打,很自卑,在外面不太敢交朋友,心事沒有人可以說,那就寫下來。
主持人:喜歡寫作的人,通常也有相當多閱讀。在處理代際創傷時,是否有對你有幫助的書?請為我們介紹幾本。
曾多聞:我近年來比較少接觸中文書,而談到跟童年、創傷或修復有關的書籍,有幾本喜歡的書,給大家參考。首先是《Hungry Ghost》,作者是Victoria Ying,這是一本成人漫畫,畫得很漂亮,內容是關於厭食症、家庭關係,還有學習愛自己,這本書探討了複雜的母女關係。
第二本是Saba Tahir的《All My Rage》,這是一本寫實的少年小說,主角是兩個來自巴基斯坦移民家庭少男、少女,描寫關於愛和原諒的故事。
還有一本《Everything Sad is Untrue》,是伊朗裔美籍作家Daniel Nayeri的回憶錄,以類似《一千零一夜》的奇幻手法,描述他8歲的時候跟媽媽還有姊姊,因為在伊朗受到宗教迫害,逃難來美國的往事,穿插他的家族歷史,我覺得寫得非常好。
➤距離與文化差異拉出的空間
主持人:你現在在美國,空間上距離原生家庭比較遠,這個距離對你的感受或人生或許都有幫助。但另一方面,在異國的環境裡,對你而言是否有些文化差異或衝突呢?
曾多聞:文化衝突我比較沒有深刻感受,不過我覺得,來到美國除了讓我能夠跟原生家庭拉開時空距離,有助於我的檢討和自省以外,美國人對於家庭暴力、療癒、創傷這些議題比較開放的態度,也有助於我這些年來的心理復健。
主持人:《代際創傷》這本書以及相關的議題,提醒我們有時候不只看到問題的表象而已,如果能更相信或落實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的話,代與代之間的創傷或許才有可能減低或不再傳遞。
曾多聞:曾有讀者問我,你都已經18歲了還會被打,應該有力氣可以跑啊?但是有一些東西,是比力氣更能控制人的行動,例如恐懼感、罪惡感。
不管別人對你做了什麼,如果想要改變別人、改寫過去,是不可能的,但你可以改變自己,成為更好的人,所以不要為虐待孩子的父母找理由。這句話也可以用在我自己身上,如果我用父母對待我的方式對待我的孩子,那就是我的錯,不能再歸咎於我父母。●
主持人:吳家恆,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畢業,英國愛丁堡大學音樂碩士,遊走媒體、出版、表演藝術多年,曾任職天下雜誌、時報出版、音樂時代、遠流出版、雲門舞集、臺中國家歌劇院。除了在大學授課,在臺中古典音樂臺擔任主持人之外,也從事翻譯,譯有《心動之處》、《舒伯特的冬之旅》、《馬基維利》、《光影交舞石頭記》等書。
片頭、片尾音樂:微光古樂集The Gleam Ensemble Taiwan
➤閱讀隨身聽,聆聽導引:
➤線上聆聽
|教學藝術家、作家楊雨樵|資深日語譯者詹慕如|山岳探險作家崔祖錫、雪羊(上)|山岳探險作家崔祖錫、雪羊(下)|大稻埕食家昌正浩|社會學者戴伯芬|漫遊文化副總編輯張貝雯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