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短評》#358 一口飲下幽幽生活史的極品好書懶人包
●班雅明:多重面向
詹明信重讀班雅明
The Benjamin Files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著,莊仲黎譯,商周出版,750元
推薦原因: 知 思 樂
詹明信以八旬高齡之姿,繪製出這幅班雅明的心靈地圖,頗有掀開底牌的壯絕,間接也解釋了班雅明何以成為後現代/解構風潮中的寵兒。兩個跨界心靈隔了一世紀短兵相接,不慍不火,卻又電光石火,每個段落都是高壓辨證,但也不妨信手翻開一頁,當成神諭卡來用——還有什麼比這更班雅明?這一冊是重知識分子的buffet吃到飽,也是輕知識分子的吉光靈感池。【內容簡介➤】
●NFT大未來
理解非同質化貨幣的第一本書!概念、應用、交易與製作的全方位指南
NFT레볼루션:현실과 메타버스를 넘나드는 새로운 경제 생태계의 탄생
成素羅(성소라)、羅夫.胡佛(Rolf Hoefer)、史考特.麥勞克林(Scott McLaughlin)著,黃莞婷、李于珊、宋佩芬、顏崇安譯,高寶出版,499元
推薦原因: 知 議
以近幾年發生的藝術交易、創作定價案例討論「數位所有權」的概念與實作,閱讀此書很可以快速地掌握「非同質化貨幣」(non-fungible token)的現象與趨勢、爭議與風險。對於一個新興現象或體制系統,此書仰賴資訊即時收集以進行階段性分析,因此書中整理了非常近期的產業與市場狀況,也針對性質、媒介、概念多元且歧異的藝術創作領域提出問題與看法。【內容簡介➤】
●草莓與灰燼
房慧真著,麥田出版,380元
推薦原因: 文 樂
充滿厚度與重量的文集,卻冠上輕忽甜美的書名,作者穿梭連結世間非輕即重、孰黑孰白的簡易二元觀點的立場,成就一本十分少見、能夠出入個人歷史與他者情感的散文論述集。從各篇標題即可推敲作者向文學與思想巨人致意用典,但目光隨即從外國月亮移向光照不及的陰暗魍魎,由此以自持的正義重新度量城市的失衡之處,乃至星球的不義所在。【內容簡介➤】
●開動了!老台中
歷史小說家的街頭飲食踏查
楊双子著,林凡瑜(Fanyu)繪,玉山社,380元
推薦原因: 實 樂
台灣小吃飲食民族誌多集中在記錄「老」城,北如萬華迪化街大稻埕,南在府城甜甜醬汁與魚鮮。台中?不老也不新,但夾在南北之間,雜燴了什麼樣的胃/味?擅於考證俗民材料的楊双子,從日治時期少女吃什麼的想像出發,連結到自己生活親密過的街區、四處移動後的獵食、或是存活的依附,記錄踏查台中舊城區的飲食。每篇散文都不以「年份」「名氣」「正統」為號召,作者的個人記憶就是軸心,讀來私房也充滿故事趣味。【內容簡介➤】
●地鐵站
何致和著,木馬文化,460元
推薦原因: 樂
地鐵站與死亡,日常空間直接衝撞了生命的極限。每天的熙來攘往,工作交辦與個人失意,使得死亡既像出軌,又像終點。我們也許都曾經在趕赴工作的座位上,極度疲倦的車程中,望著同乘者或自己映現在車窗的臉龐,問人生,問何為。《地鐵站》將我們心中若隱若現的感受和疑問立體起來,放射出去,又交織而成一幅城市圖卷,也是一個時代註腳。【內容簡介➤】
●鰻漫回家路
世界上最神祕的魚,還有我與父親
Ålevangeliet
帕特里克.斯文森(Patrik Svensson)著,陳佳琳譯,啟明出版,380元
推薦原因: 知 思 樂 益
從輕文獻、輕科學的角度出發,書寫鰻魚降河洄游的生態,旁及父子捕鰻的家族傳承,清澄的文風排比人鰻之間的類似儀式,別具半透明的神祕感。馬尾藻海的深不可測,祖母教父親如何探尋水源,緩緩行文中出現這些奇幻的段落,有如地上極光,踩之暈眩。【內容簡介➤】
●飢餓信號!
一次解開身心之謎的飲食心理學
Hunger, Frust und Schokolade: Die Psychologie des Essens
米歇爾.馬赫特(Michael Macht)著,王榮輝譯,菓子文化,450元
推薦原因: 知 議 實 益
又是一本知識可口的飲食科普,不過作者的功德,在於完全放大吃的情感面和情緒面,一旦覺察洞察到了這一點,理當可以有效降低肥胖、三高、口腔癌、食道癌、腸胃炎、大腸癌的風險。【內容簡介➤】
●曲水流雲
浮生九十年
金慶雲著,聯合文學,500元
推薦原因: 樂 益
台灣重要聲樂家金慶雲女士的回憶錄,涵蓋了近當代台灣,乃至華人聲樂歷史發展的系譜與細節,是少見的聲樂藝術歷史資料。然而除去作者聲樂家、樂評人、音樂教育者等身分,這也是一本十分驚人的記憶之書,從個人出發回想重構的諸多經驗細節與人際交往,讀來歷歷在目,大歷史的起伏流轉也清晰重現,是一本兼具藝術史與女性史重要性的佳作。【內容簡介➤】
●被統治的藝術
中華帝國晚期的日常政治
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 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宋怡明(Michael Szonyi)著,鐘逸明譯,聯經出版,490元
推薦原因: 知 議 樂 益
作者穿梭於文獻與田野之間,勾勒出明代世襲軍戶在帝國規範箝制之下的日常。這部將中國社會關係內裡外翻之作,令人見識到史學的洞見與扎實的調查功力如何並陳。那些幽微的、潛伏於帝國榮華之下翻騰的、蜿蜒轉進的一個個無名基層庶民生活的故事,顯示日常政治做為中國百姓的求生法和防身術,已長久浸潤成思維的一部分。這些場景和應對,今天在臺灣的我們讀來也不會感到陌生,除了是社會文化方面的因緣,也因為這些來自真人真事的故事中的角色,很可能就是你我的先人。【內容簡介➤】
●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5冊)
中華的成立、江南的發展、草原的稱霸、陸海的交會、中國的形成
シリーズ 中国の歴史
渡邊信一郎、丸橋充拓、古松崇志、檀上寬、岡本隆司著 ,詹慕如、林琪禎、黃耀進、郭婷玉、郭凡嘉譯,聯經出版,1750元
推薦原因: 知 樂
在這個鄰近的龐大政體令人感到壓力的時代,日本研究中國史的中堅學者們提供了從深層處理的攻略。透過政治體與經濟重心的發展、外緣勢力的進入、國際關係的運作原理,說明「中國」的形成軌跡。意旨清晰,論述扼要,且仍顧及時間軸。藉由回望和梳理,這套書回應了時代的焦慮,不只帶來屬於21世紀日本東洋史學界的視角,更寄望在與歷史的對話中,賦予人們觀看混沌世局的清澄視野,是了解而非外部想當然爾的誤解。【內容簡介➤】
知識性.設計感.批判性.思想性.議題性.實用性.文學性.閱讀樂趣.獨特性.公益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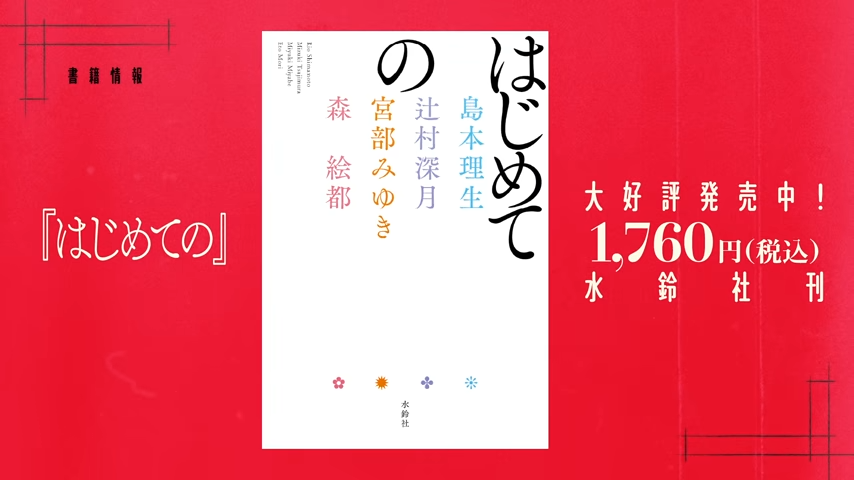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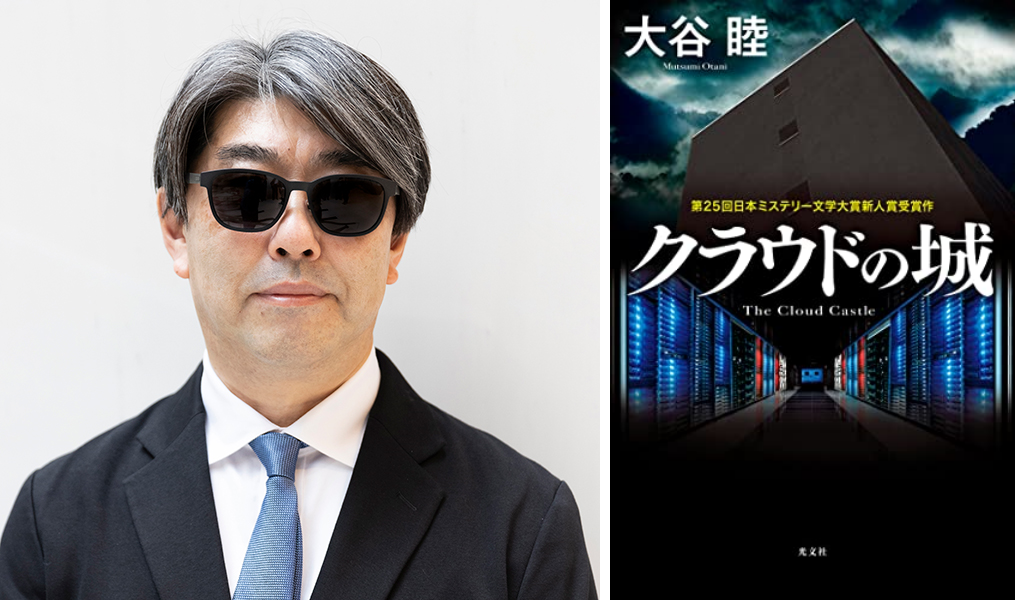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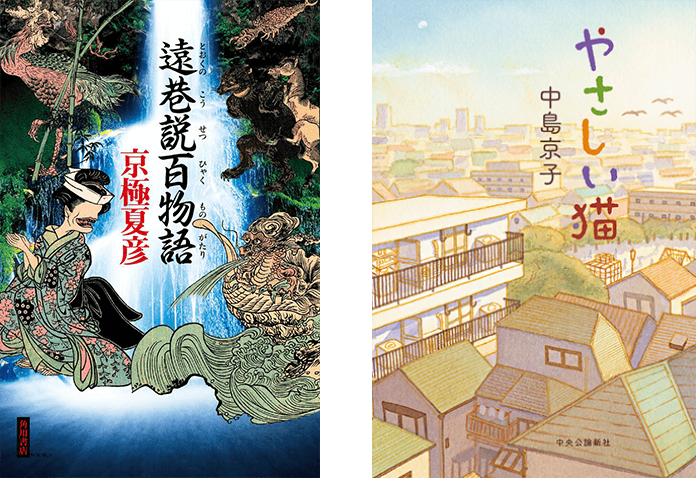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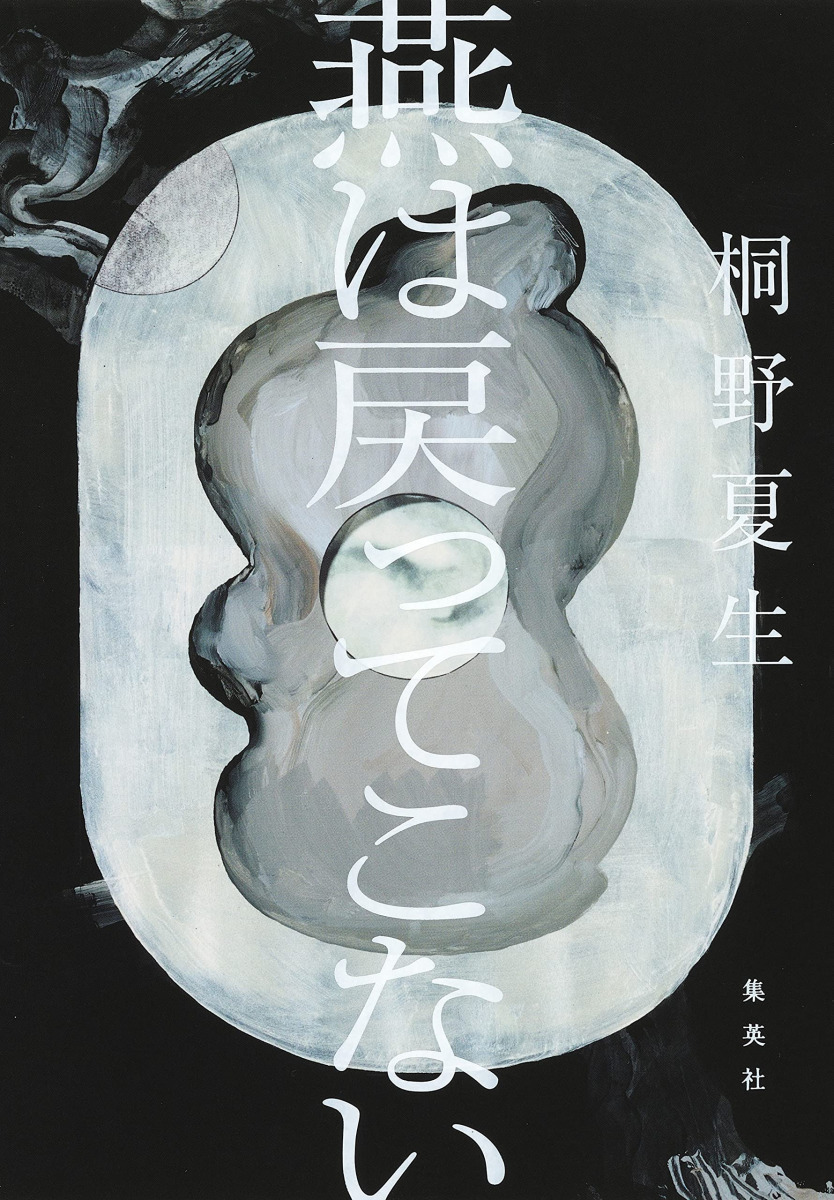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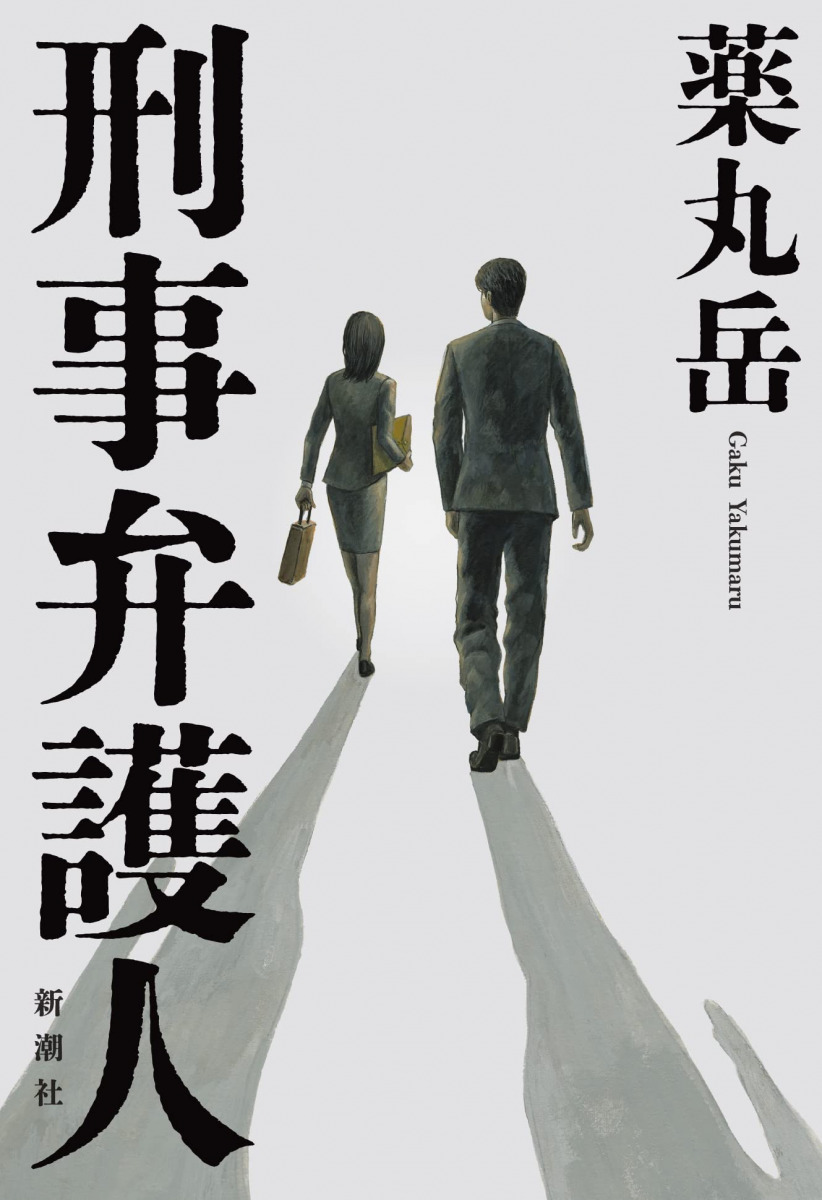 ■憑藉《天使之刃》、《和不是A的你》、〈黃昏〉等作獲得多項推理文學獎的小說家藥丸岳,於本月中出版新作《刑事辯護人》(新潮社),透過年輕女律師承接的有罪率高達99.9%的刑事案件,挑戰日本司法制度的問題。埼玉縣警署的女警官垂水涼香,疑似犯下殺害男公關的罪嫌。相信涼香清白的女律師持月凛子,與事務所的同事一同為涼香奔走。然而,他們所收集的證詞,卻滿滿都是謊言。身為律師的她,是否真該為惡質刑案的兇手辯護呢?律師與警察的信念,又是為誰而存在?藥丸岳在經過17年的構思與完善的取材後,寫下屬於現代日本的《罪與罰》。
■憑藉《天使之刃》、《和不是A的你》、〈黃昏〉等作獲得多項推理文學獎的小說家藥丸岳,於本月中出版新作《刑事辯護人》(新潮社),透過年輕女律師承接的有罪率高達99.9%的刑事案件,挑戰日本司法制度的問題。埼玉縣警署的女警官垂水涼香,疑似犯下殺害男公關的罪嫌。相信涼香清白的女律師持月凛子,與事務所的同事一同為涼香奔走。然而,他們所收集的證詞,卻滿滿都是謊言。身為律師的她,是否真該為惡質刑案的兇手辯護呢?律師與警察的信念,又是為誰而存在?藥丸岳在經過17年的構思與完善的取材後,寫下屬於現代日本的《罪與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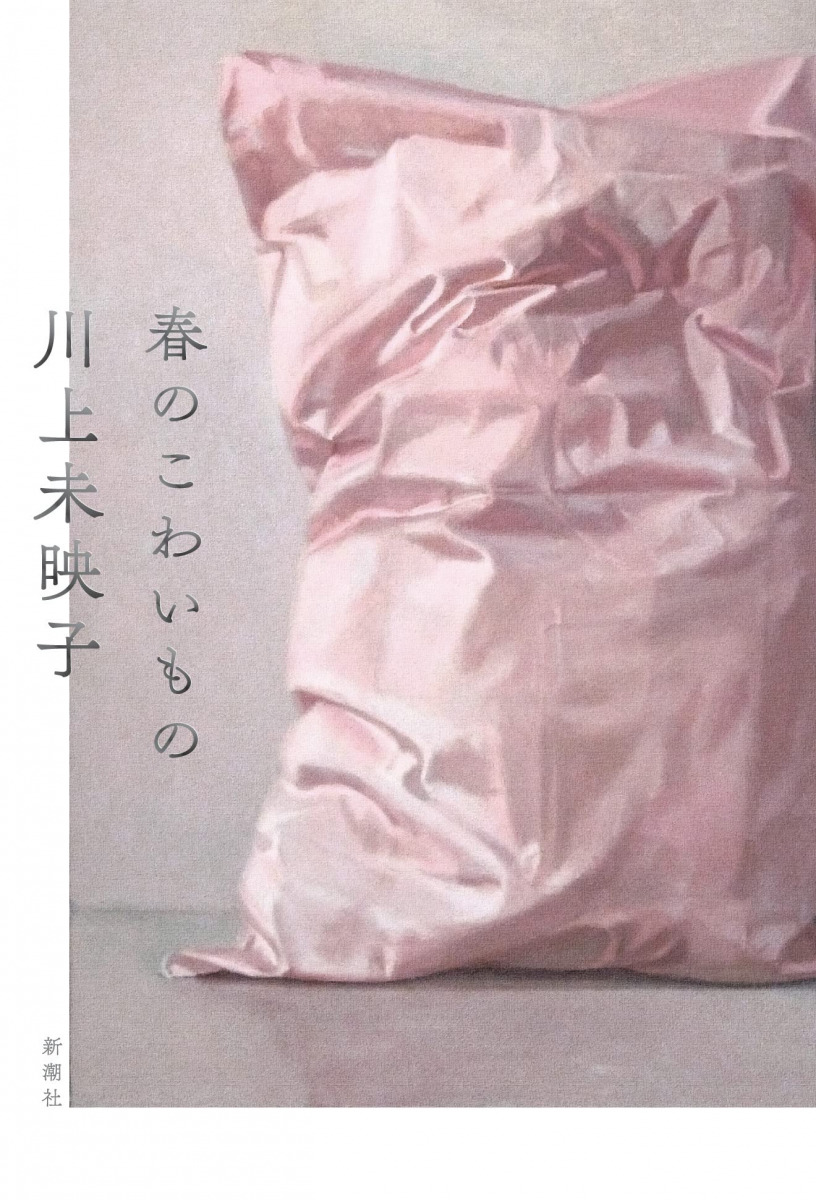 ■全球暢銷小說《乳與卵》、《夏的故事》作者川上未映子,於上個月底推出新作《春天的可怕事物》(新潮社),講述在疫情爆發之前,東京6名男女所體驗的、極盡甘美的地獄巡禮。
■全球暢銷小說《乳與卵》、《夏的故事》作者川上未映子,於上個月底推出新作《春天的可怕事物》(新潮社),講述在疫情爆發之前,東京6名男女所體驗的、極盡甘美的地獄巡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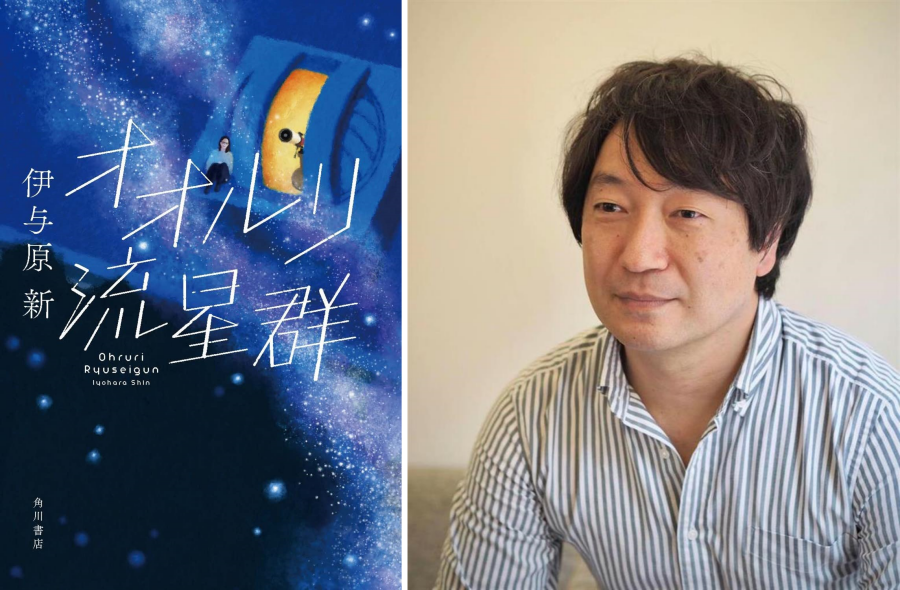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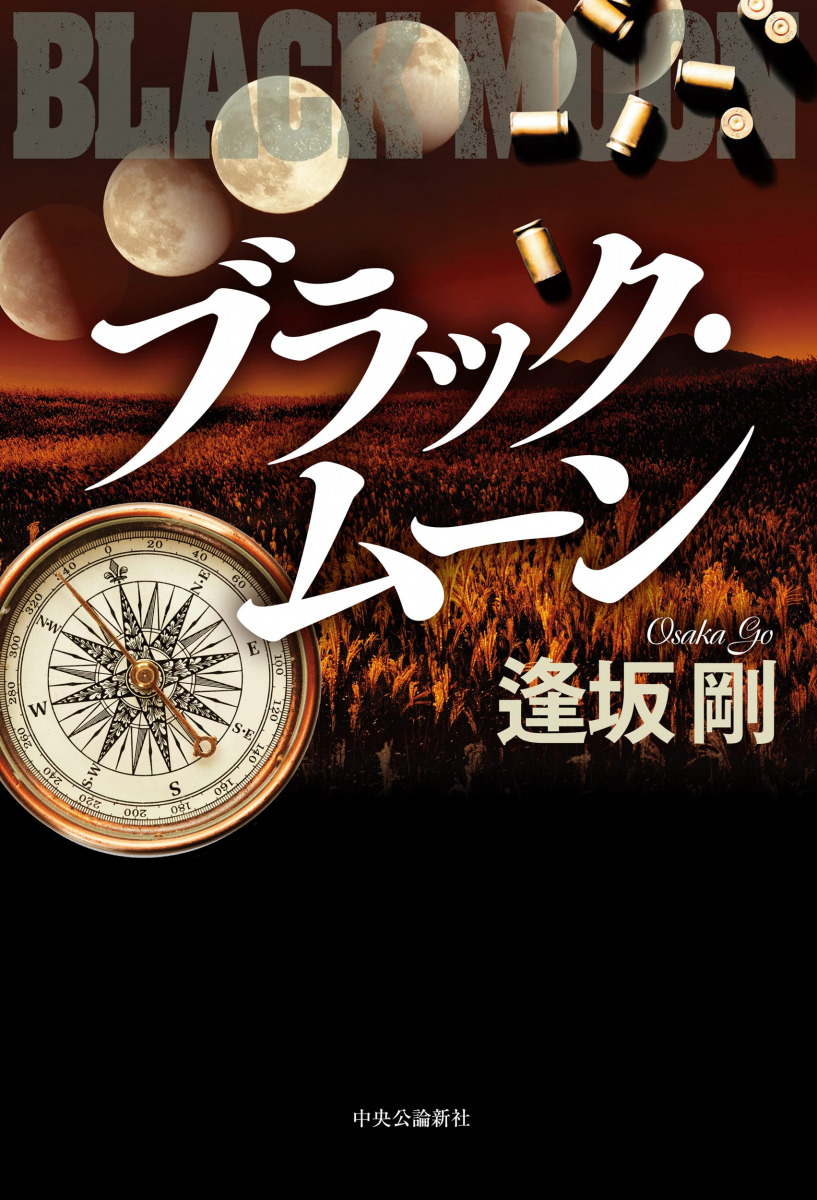 ■曾以《刺客死於格拉那達》、《卡迪斯紅星》、《搜尋平藏》摘得多項文學大獎的推理小說家逢坂剛,在上個月底出版新作《Black Moon黑月》(中央公論新社),繼《無盡的追尋》與《最後的決鬥者》後,再添一部以土方歲三為主角的西部冒險故事。新選組副組長土方歲三,本該殞命於箱館。但實際上,頭部中彈的他只是失去了記憶,改名為内藤隼人,與愛慕他的時枝由良一同浪跡美國西部。某天,隼人遇見了前來追殺他的原新撰組成員高脇,並且在與高脇決鬥之後跌落懸崖。瀕死的他被名為黑月的神祕女性所救,而在隼人行蹤不明後,由良、皮琪、博那等人,也遭遇了巨大的轉機。失去記憶的土方副隊長,這次將開啟怎麼樣的武士之旅呢?
■曾以《刺客死於格拉那達》、《卡迪斯紅星》、《搜尋平藏》摘得多項文學大獎的推理小說家逢坂剛,在上個月底出版新作《Black Moon黑月》(中央公論新社),繼《無盡的追尋》與《最後的決鬥者》後,再添一部以土方歲三為主角的西部冒險故事。新選組副組長土方歲三,本該殞命於箱館。但實際上,頭部中彈的他只是失去了記憶,改名為内藤隼人,與愛慕他的時枝由良一同浪跡美國西部。某天,隼人遇見了前來追殺他的原新撰組成員高脇,並且在與高脇決鬥之後跌落懸崖。瀕死的他被名為黑月的神祕女性所救,而在隼人行蹤不明後,由良、皮琪、博那等人,也遭遇了巨大的轉機。失去記憶的土方副隊長,這次將開啟怎麼樣的武士之旅呢?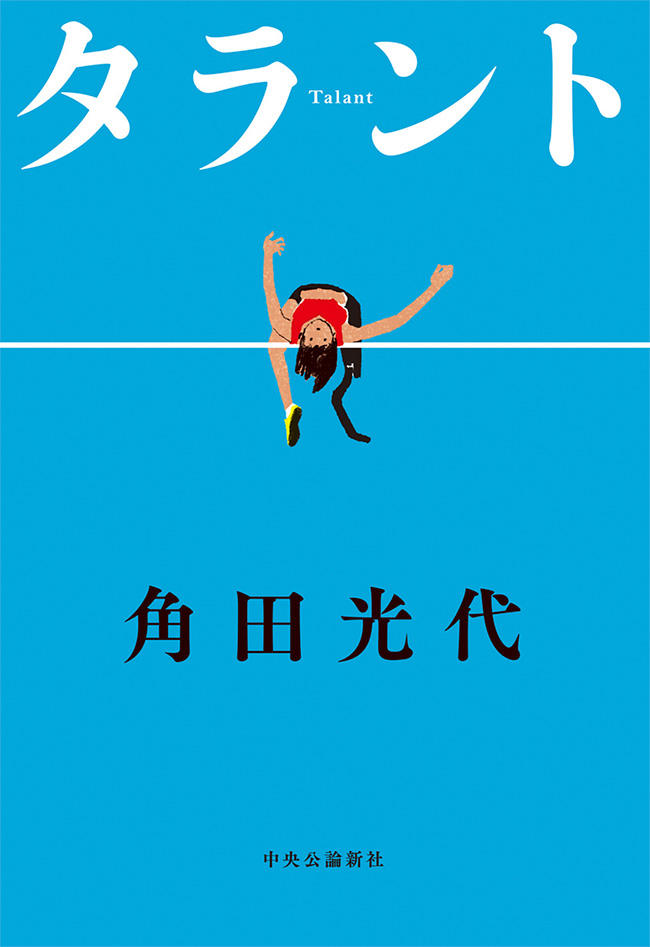 ■《空中庭園》、《第八日的蟬》、《紙之月》作者角田光代,上個月底推出感人而勵志的長篇小說《
■《空中庭園》、《第八日的蟬》、《紙之月》作者角田光代,上個月底推出感人而勵志的長篇小說《
書評》唱歌是原住民說故事、記憶族群歷史的能力:讀《那個用歌說故事的人》
這是一本看似輕鬆的對話紀錄,也像是尚未變裝成學術樣式的零散田野筆記,但是顛覆的力道和批判的自省,仍然夾藏在字句之中隱隱發光。在閱讀這本書之前,我們必須拋開本來對「音樂」和「歌曲」的成見,聽見那不受五線譜束縛的聲音,來自土地和生活的旋律。
在課堂上講述原住民文學與歌謠的歷史時,總會得到不少學生驚訝和自責的回饋,因為我們的國民教育,多半只引導學生用「遺址考古」的眼光來看待一直在島嶼上生活著的原住民族,在「史前史」之後,原住民族生存的身影被塗抹為一片空白。
這本書,正能帶領我們看見、聽見那被隱藏在教科書歷史、人類學調查筆記角落的生命故事和歌謠。貫串全書主軸的,是Calaw Mayaw林信來教授和女兒Ado Kaliting Pacidal阿洛.卡力亭.巴奇辣的對話,藉由女兒阿洛和執筆者藍雨楨的提問,一頁一頁翻開父親記憶的寶庫,以及上千首珍貴的阿美族歌謠紀錄,共構出以阿美族為主體的歌謠史片段。
➤林信來:60年代民歌採集運動,少數的原住民參與者
第一部分將讀者帶回60年代的「民歌採集運動」現場。這個在台灣歌謠史上必須一提的民歌採集運動,由史惟亮、許常惠等人發起,回應當時「需要我們自己的中國音樂文化」的欲求,進一步大規模的採集原住民族、福佬、客家等歌謠的運動,轟動一時。
然而,這場幾乎可以說是以原住民族歌謠為重心的採集活動,卻僅有兩位原住民身分的參與者,其一是1967年5月李哲洋、劉五男前往花東採集阿美族歌謠時,同行的馬蘭部落阿美族音樂家李泰祥;而另一位則是本書的主角林信來教授。
我們雖然可以在當時1967年暑期民歌團的工作筆記裡看到林信來的名字,發現團隊十分仰賴林信來「熟悉地理環境」的優勢,以及能讀到他巧遇同窗進而協助錄音、山地議員請喝酒因而採錄的成果豐碩等紀錄,但除此之外,這場民族文化運動的主導權和發言權,都不在原住民族的手上,他們僅是被觀看、被紀錄、被詮釋的一群。
而這正是這本書最珍貴的地方之一:透過林信來的訪談和回憶,我們終於有機會一窺當時這場運動中被隱匿、消聲的阿美族青年,在當時的採集工作裡,如何擔任起語言、文化翻譯、曲調辨識和分類的重責大任,並且怎麼看待這場轟轟烈烈的民歌採集運動。撰文者藍雨楨一方面以對話呈現林信來的回憶,另一方面也佐以其他論述資料,為讀者勾勒出更為清晰的歷史圖像。這些不被記錄在官方書面資料裡的記憶和經驗,也恰巧凸顯了林信來在1972年,走訪了至少28個部落採錄歌謠的契機。
➤以烏托邦想像或現代版權概念理解原住民歌謠,恐徒勞無功
當時的史惟亮與許常惠二人,對於民歌採錄的理念抱持著「純粹」、「不受汙染」的想像,剔除了所有帶有日本調、天主聖歌色彩或是流行元素的歌謠,僅記錄二人理想中「純淨」的古調。這個接近尋覓烏托邦世界的採錄準則,以現在的眼光來看,當然注定是不可得的。
何謂純粹?何謂傳統?那些不被記錄下來的歌,是不是才更能說明原住民族如何面對了不同時間區段的外來者?怎麼適應不斷變動著的外部世界?每一首曲調的語言、旋律、節奏的變遷和混雜,都回應了歌者當下的生命狀態。林信來因而跳脫漢人民族音樂學的觀點,轉而回到阿美族Radiw的邏輯裡,用自己的方式採錄歌謠。
阿美族的「Radiw」到底是什麼?具體的內涵是什麼?最重要的精神又是什麼?也是全書最重要的部分。
這個Radiw,如果以漢語直接翻譯,應近似於「歌謠」,但卻不只是,也不盡然相同於漢語的「歌謠」。跟台灣多數的原住民族一樣,在阿美語中,並沒有「音樂」這樣的詞彙,只有Radiw,或是動詞的Romadiw,唱歌。唱歌就是最原始的文學,是一種言說,一種敘事的方式,甚至能夠超越語言,達到與天地神靈的溝通。
在版權的概念正式進駐部落之前,歌是一種生活的狀態,一種分享,也是體驗當下的形式。同一首歌給不同人唱,會有不一樣的情緒,不一樣的靈魂,增增減減,傳到隔壁部落,又長成不同的樣子。就如同在日治時期開始創作歌謠的陸森寶並不在意歌曲的「所有權」,反倒認為自己寫的歌能被族人分享和傳唱,才是意義與樂趣所在。
如果用現當代流行音樂的角度來看,每一首歌謠應有獨立的歌名、詞曲,著作、製作也都有各自的版權所屬。但若用這樣的概念理解「Radiw」不僅太過貧乏,也像是要將每一道綿延起伏的海浪區分開來一般的徒勞無功。
➤Radiw,呼應了「什麼是阿美族人」的內涵
這本書的輯二回到Radiw的邏輯,為讀者介紹林信來如何跳脫外來者觀點的學術框架,建立屬於Pangcah的歌謠分類方式。
Radiw的意義幾乎可以指向「什麼是阿美族人」的內涵:說明Pangcah起源的創世神話開始唱起的祖源歌;祭儀歌謠作為與神靈溝通的語言,需更嚴謹的措辭和遵守唱歌的時間點和場合;擅長以歌唱的方式說故事的人被稱為mikimad,藉由吟唱述說部落的傳說和歷史,也承載祖先留給子孫的訓誡和勸勉,因需有高度的文學和吟唱功力,為人所敬重;日常生活的互相答唱,是一種言說溝通的方式,在年齡階層裡或特定的情境裡,也藉由歌唱說明自己屬於這個群體,說明自己在社會上的位置、階序;工作時唱歌,也順便談戀愛,如何表明自己的愛意,也正是以身體勞動來證明;時代政權轉換下,講述苦力、勞役、分離與思念、戰爭的歌謠,都說明阿美族人在那個時代顛沛流離的艱難處境,每一次唱歌,都在唱一段歷史。
可以說,Radiw串起了阿美族人每個階段的生命變化,從最小的日常生活,到最深刻的生命涵養,同時也是一種生命、身體的實踐,透過每一次的歌唱,證成作為真正的阿美族人的存在。
➤以漢語為中心的採集終難盡善,以口述填補官方歷史的空缺
這本書某種程度上也顛覆了「原住民很會唱歌」這樣的刻板印象。在漢語語境裡的「很會唱歌」讓我們直接聯想音準、鐵肺、音域等等技巧性的詮釋,但在本書豐富龐雜的Radiw詮釋之後,應能感受到在阿美語語境裡的「很會唱歌」,更像是一種說故事、記憶族群歷史的能力。唱歌唱的並不是音準或彰顯個人,唱的是一種集體記憶和生活實踐。
非常有趣的是,這本書的撰述者藍雨楨並非阿美族人,我們可以在林信來和女兒阿洛深刻的對話背後,看到那個讓自己退居後線的記錄者的位置,並嘗試讓這些訪談內容與其他的文獻史料對話,拼湊出更為完整的阿美族歌謠的版塊。
這本書大量的混語書寫,正說明了藍雨楨嘗試進入阿美族語的語境當中,站在阿美族的觀點與立場,重新理解民歌採集運動、原住民傳統歌謠或現當代的原住民流行音樂創作。這種還原田野現場漢語/阿美語交雜使用的撰述方式,也讓讀者不得不進入阿美族語的語境當中,而不是粗暴的將這些詞彙以不適切的漢語直接翻譯。
如同林信來在訪談中提及的,過往在整理採集來的歌謠時,總用當時漢語為中心的思維在限制自己,因此做了過多的翻譯潤飾,不甚符合阿美語歌詞的涵義。但閱讀此書,未被頻繁加註的阿美語詞彙,則仰賴讀者勤勞查找上下文,甚或從一整個章節探尋該詞彙的真正涵義,而不讓讀者輕易的獲得一個簡便但不甚精確的漢語翻譯。
不論這個書寫的策略是有意或是無意,在語言的呈現上,都和這本書意圖以口述填補官方歷史空缺,並顛覆不適切的學術框架的基進觀點不謀而合,也迫使讀者拋開成見,沉浸於海洋一般的Radiw之中。●
Radiw no O'rip
口述:Calaw Mayaw林信來、Ado Kaliting Pacidal阿洛.卡力亭.巴奇辣
撰述:藍雨楨
出版:玉山社
定價:38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Calaw Mayaw 林信來
出生於花蓮玉里,國立臺東大學音樂學系副教授。1967年參與民歌採集運動之東隊行程。自1970年代起,長期投入阿美族歌謠採集與研究,亦曾參與中研院、文建會委託之阿美族音樂調查研究計畫。著有《Banzah A Ladiu台灣阿美族民謠謠詞研究》(1982)、《臺灣卑南族及其民謠曲調研究》(1985)、〈南王聚落之音樂〉收錄於《臺灣土著祭儀及歌舞民俗活動之研究》(1987)、《宜灣阿美族豐年祭歌謠》(1988)。
Ado Kaliting Pacidal 阿洛・卡力亭・巴奇辣
國立東華大學民間文學博士,電視節目製作人、導演、演員、創作歌手、主持人,長年耕耘原住民族社會文化議題。音樂專輯《Cidal Fulad太陽月亮》(2013)、《Sasela’an氣息》(2020)入圍多項金曲獎;2015年電影《太陽的孩子》入圍金馬獎最佳新演員;2016年電視節目《吹過島嶼的歌》獲金鐘獎教育文化節目主持人獎;2019年主編書籍《吹過島嶼的歌》。只要太平洋的海浪不斷拍打,我們的歌就會一直唱下去。
藍雨楨
宜蘭人,國立清華大學人類所碩士。長期參與跨國藝術計劃的策展製作。在印尼田野研究期間,結下與南島的深厚緣分,希望以人類學觀點,持續拓展更多元的文化議題。近年與友人共同經營Trans/Voices Project,關注台灣和印尼跨國移工的藝文實踐,合著出版《歌自遠方來:印尼移工歌謠採集與場景書寫2021》。目前從事寫作、翻譯與藝文策展。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