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欣,1984年生,是詩人,也是藝術工作者,出版【獸的三部曲】:剪紙詩集《妖獸》(2012)、版畫詩集《失語獸》(2016)、圖文詩集《負子獸》(2018),以及與阿米合著的《她是青銅器我是琉璃》(2013),並主編《媽媽+1:二十首絕望與希望的媽媽之歌》(2018)。
專訪當天是豔熱的日子,一群人都在抹汗,長衣長褲的潘家欣卻泰然自若,似乎不被天氣侷限,像是自身有恆溫系統。回答問題時她眼神堅定,幾乎像是沒有情緒,平靜無獸性,也不妖異,十足知識分子,跟她詩歌滿滿的強悍與炸裂,有著頗大差異。唯潘家欣說話精簡,每一句都彷如刺拳,又跟她的詩歌相符──最短,也就最有威力。
▉想被容納在龐大如宇宙的農場
小學三、四年級就開始讀童詩,還有很多童話,包含王爾德,甚至早在小二、小三,潘家欣就喜歡讀雄獅出版的一系列民間采集詩歌、傳說與童謠,乃至雄獅在《國語日報》推出的民藝小專欄,如剪紙、扯鈴等,都算是她最早的文學養分。
談起詩歌進入自身生命的狀態,潘家欣是斷然的,「我就是莫名地被吸引,沒有理由。」她停頓幾秒,復又提起尼爾.蓋曼(Neil Gaiman)半自傳奇幻小說《萊緹的遺忘之海》,裡面有他的童年故事,包含總是在想像一個農場,不是人類的,而是容納各種奇異生命龐大如宇宙般的農場。「他說自己從小就喜歡讀神話,沒有為什麼,就是覺得更棒。」
潘家欣也分享小時候讀到神話的種種激動,「比如夸父追日,我的毛會豎起來,真的感受到人為了追求,可以變成多麼巨大的存在。」她十分喜歡《山海經》裡的刑天,「讀完就哭,覺得他超帥,當時不知道為什麼。現在想起來,可能是我很早就對於神話所蘊藏的集體潛意識,有所回應吧。如刑天膽敢犯神的反叛意念,我相信是人類共同的經驗。」
潘家欣表示,小三、小四就寫以自然為主的童詩,到了小五,「因為遭受霸凌,所以開始關心自己的情緒。詩歌能幫我處理那些內在壓力。後來寫的童詩,就變成在描繪大自然時,會放入自身的情緒。」
她也將詩作投稿至《國語日報》,領取稿費,對小學生來說,是滿新鮮的事。隨後,潘家欣談到霸凌,主要是人際關係的障礙,並沒有發展為肢體動作,多是被排擠與孤立,還有言語方面的羞辱。
「我就是個怪小孩啦,同學都有共同語言、共同祕密。我卻一心一意地看天上的雲和地上的花草,比如學校外面的風鈴木、羊蹄甲,我會瞧到發傻,根本不會有人想理我。」她神情安靜地分析自己的童年樣貌。
▉反覆閱讀的
小學二年級,潘家欣在父母的安排下去學畫,雙親是她藝術創作的重要推手。父母給她的自由度很高,加上他們對美的事物有著一定程度的敏感,「他們都是有藝術天分的人。父親是古典的、憂鬱、有一致性的藝術路線,像他很會寫書法。母親則是天馬行空,有時候會覺得她是外星人,比較是當代藝術的系統,雖然她可能沒有意識到。」
潘家欣分享一件母親的藝術舉動:「家裡養著一隻小白頭翁,活了兩年後,病死。媽媽的反應不是拿盒子來葬牠,而是去拿手機來拍攝鳥的遺照。」一講起看似傳統、實則行為有藝術直覺的母親,潘家欣的眼裡都是笑意,「我受到他們滿大的影響,一種是穩定長遠的古典,一種是直觀的當代感,我則是兩種不同藝術系統碰撞下的產物吧。」
迄今她仍反覆閱讀的詩人作品並不多,主要是波特萊爾(Charles P. Baudelaire)的散文詩,「始終具有啟示性,關於我的生命疑問,他的散文詩歌能夠提供我解釋。辛波絲卡(Wisława Szymborska)其實也可以對我有所啟發,只是她比較偏於實用,不像波特萊爾是萬用性。」
台灣則是葉青、阿米和馬尼尼為。「葉青非常嚴謹地在創作,她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阿米則是瞬間的天分,像是有詩歌之神附身,可以說靈感體的畢現。馬尼尼為則是濃密激烈地爆發,而且感覺後面還有東西持續在產生。」

更決定性的影響是鴻鴻創辦的《衛生紙+》詩刊,「那可能是我詩歌寫作的轉折點。」潘家欣直言:「它啟發一整個世代,關於面對現代詩的困境,前輩詩人們集體形成的限制,如何進行翻倒的動作,包括鴻鴻會容許平凡、冗長乃至累贅的詩作,都是關於詩歌的主體與可能性的探索。《衛生紙+》其實是大型策展的概念,它對詩歌語言的實驗性、關懷主題等等方向,做出全新的推進。」
▉《妖獸》:自我性與純感覺展演的擺盪
不想要散漫式收錄詩作,潘家欣決定採用主題性編集,「我認為詩集的本身就應該是一個完整的概念呈現,而且從一開始就決定是【獸的三部曲】。我滿喜歡古希臘戲劇的形式,總會在三部曲後,再搭配一齣鬧劇,也就是在心靈獲得昇華之後,你還是得回歸到人世,面對柴米油鹽。」所以,在詩集三部曲後,她尚有一本獸的喜劇在醞釀與整理中。
 《妖獸》封面的貓,是潘家欣返回台南定居前兩年反覆畫的獸形,「原先是青銅器上的饕餮紋,也運用了臣字眼。我覺得牠是我的守護獸。這本詩集就是在處理圖騰。但我不是依據單一主題去創作,而是把有符合生命圖騰的詩選擇出來。」
《妖獸》封面的貓,是潘家欣返回台南定居前兩年反覆畫的獸形,「原先是青銅器上的饕餮紋,也運用了臣字眼。我覺得牠是我的守護獸。這本詩集就是在處理圖騰。但我不是依據單一主題去創作,而是把有符合生命圖騰的詩選擇出來。」
剪紙藝術的融入,則是因為「我讀師大美術系,而且一路以來都是美術班體系,很自然就會想要結合。」跨越在詩歌與藝術,潘家欣對兩者的判分是:「基本上使用的腦袋根本上就不同,思考完全是不一樣的。文學是語言與邏輯為主,藝術就是視覺體驗的傳達,畫面充滿直覺。」在潘家欣的觀察,文學圈的瘋子很少,只是自我性比較強,美術班則多的是怪人,比如去偷紅綠燈的學長,並非為了創作,就只是單純的惡作劇,幾乎是不經思維的純感覺展演。
大學時期,如何在兩種腦袋切換,也頗讓潘家欣困擾,不過,她誠實地看見自身藝術天分的不足。以比例來說,「天分只有20%,大多是後天的訓練。不過,」潘家欣眼神熒亮亮,「在詩歌方面則是創造的天分比技術的養成多。」現今潘家欣並不會急迫於作畫,詩歌在她的創作裡的比重更大,也就成為自然而然的選擇。
而所有文學類型中,潘家欣獨鍾詩歌,則是由於「詩歌與藝術在創作上有很接近的血緣。」詩也是更傾向於直覺經驗的噴發,無須顧慮邏輯、秩序,讓語言和個體性擁有最為驚奇、自由的開展。
另外,她也坦承,《妖獸》一開始不是每首詩歌都有對應的剪紙作品,是美編陳采瑩的建議,而潘家欣並不排斥別人的想法加入。詩集中的剪紙圖,大部分都是具象表現,但有些是抽象,如〈雪季〉的剪紙圖是火焰,隱喻嚴寒生命裡可能的燃燒與溫暖,「我想要用圖像闡釋事物更內在深層的形意。但這也有個狀況,就是我的系統不穩定。」
同一本詩集的圖形演繹有不一樣的路徑,是不穩定的表現,對她來說有時形成困擾。潘家欣說:「有些內在穩定一致的創作者,會渴求不確定性。我則是站在另一邊,反而希望自己能穩定。不穩定也許很迷人,但不會是完美作品的基礎。」

▉《失語獸》:帶著傷痕的人才能完成下一輪進化
提及以散文詩體編選的《失語獸》,潘家欣說: 「相對於分行詩,散文詩似乎是邊緣、弱勢的,更之外的東西。我想用散文詩形式,跨出對現代詩就是分行詩的定義。」定名為失語,可視為她對散文詩的定義,亦即失去原先分行詩歌的樣態,也算是溶解術。她進一步說明:「但與其說散文詩是分行詩的失落之變,不如講是對散文的解構,讓語言形式崩壞與異裂,從而看看會產生什麼新的力量。」
另外,潘家欣也破題說:「裡面的詩大多是情緒不好的時候寫下,像〈雞雞森林〉是在面對好像活在外星世界的男學生們,覺得他們都是用雞雞在想事情,心理的衝突很大。」她苦笑:「整本詩集全是負能量的東西,滿中二。」
詩作中常見激烈語調與凶猛直接的意象,起因於現實生活中存有太多令人無法輕易放過的事物。潘家欣說:「因為不甘心,因為想要做出什麼改變,才會怒氣衝天。我想,在絕望的世界中,憤怒可以讓人持續活著,而不至於自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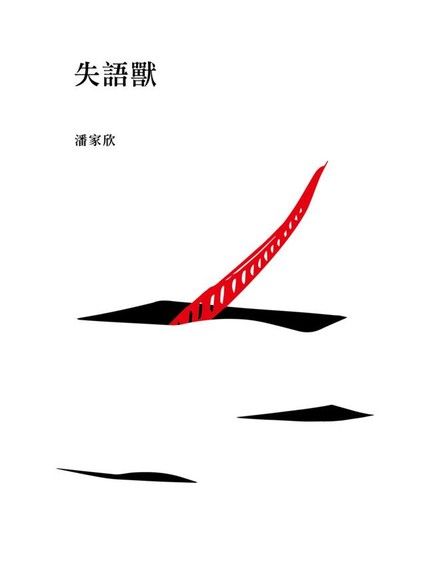 《失語獸》另一特點是結合版畫,「版畫是一種間接藝術,」潘家欣說:「要先做版,才能成像,不是直接產出。在製作時,挺像在進行思覺的反芻,得要有過程,歷經失敗,有滿多間接性的因素存在。」
《失語獸》另一特點是結合版畫,「版畫是一種間接藝術,」潘家欣說:「要先做版,才能成像,不是直接產出。在製作時,挺像在進行思覺的反芻,得要有過程,歷經失敗,有滿多間接性的因素存在。」
版畫創作與她藉由散文詩創作去探義詩歌的定型,進行再挖掘的動作,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亦如隔山打牛。畫作依舊晃走實象與抽象之間,有些很具體,有些概念性強,這亦是潘家欣的詩歌特技,在一篇篇具象詩題下游移各種意念的演出。
潘家欣也認同,人的性格與其創作必然有著隱微的對應關係。「我覺得自己是充滿裂痕的人。不管是在社會生活,還是個人心理,好像都有各種細細小小的斷裂。」而就像電影《分裂》所預示,唯帶著傷痕的人方可完成人類的下一輪進化。
▉《負子獸》,真正地生而為人
「《妖獸》是青銅,《失語獸》是鑽石,《負子獸》是原礦。」潘家欣如是說。她對【獸的三部曲】有著清晰的理解與定位。她雖然不抗拒與人合作,但前兩本詩集,因為對作品的高度自覺,還是在一定嚴厲程度的控制之下,到了《負子獸》,「我變得柔軟而隨和,」她彎著嘴淡淡笑著,「甚至設計希望放我的手寫字在最後一頁,即使不覺得自己的字好看,但也同意了。」
 書衣上有一版畫,是戴著獸面具的懷孕女子,「那是我送給陳夏民的,他建議一定要放。還有負子獸三個書法字,是我抓著女兒蘑菇的手,握毛筆一起寫的,小孩有她的意志,她也想寫,所以出力在抗衡我。裡面的潑墨也是蘑菇玩的。」《負子獸》因之就成為一種共同創作。而詩集裡的圖創是剪紙與塗鴉,更為抽象,也更有符號感,潘家欣說:「這一次沒有要求自己得有完整思維、邏輯,隨性創作。」於是,《負子獸》整體就變得更樸拙,無雕無琢不華不巧。
書衣上有一版畫,是戴著獸面具的懷孕女子,「那是我送給陳夏民的,他建議一定要放。還有負子獸三個書法字,是我抓著女兒蘑菇的手,握毛筆一起寫的,小孩有她的意志,她也想寫,所以出力在抗衡我。裡面的潑墨也是蘑菇玩的。」《負子獸》因之就成為一種共同創作。而詩集裡的圖創是剪紙與塗鴉,更為抽象,也更有符號感,潘家欣說:「這一次沒有要求自己得有完整思維、邏輯,隨性創作。」於是,《負子獸》整體就變得更樸拙,無雕無琢不華不巧。
造成這種轉變的主因,自然就是女兒的出生,《負子獸》也以詩歌加散文的方式,記錄她成為母親的時光。潘家欣說:「我的進化是因為蘑菇。嬰兒還無法表達自我,所以很多事她都是非得這樣不可的,想哭就哭,想屎尿就屎尿,沒辦法控制。我得要順從她的意志。」甚至就連婚姻也由於蘑菇的訓練而有所進化,「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慣性,難以改變的,我先生也不過如此。一旦體認到這一點,在相處上也就能多一些轉圜。」
而《負子獸》的重要意義在於成為人的過程,「我身為人類,且是人類的通道這件事終於被確定。從青少年時期以來,一直覺得自己不屬於地球,好像身體裡存有另種生命。但懷孕與生產,算是讓我歷經身心的重新創造,真正地生而為人吧。」
她談到某種隱喻也似的內在心理感受,「我總覺得自己不是純人類,而是被人的形體困住,一直不知道要怎麼使弄,怎麼跟人類建立關係。所以長期以來,都在學習任何運用人類的身體、他們的思考方式,理解並適應他們的社會構成。」
她想了想後,又再補充:「為什麼我會對獸物那麼感興趣?也是因為我就是會夢見牠們,變成牠們。我甚至會在夢裡面飛,那是更龐大、更自由的感官經驗。而文字幫助我在清醒時捕捉重溯那樣的極限感。」
問到為何要成為人?潘家欣神情靜靜地講:「不變成人,不調適的話,根本沒辦法好好生活啊,而且也會造成周邊親友的困擾。何況從現在去看,會覺得人這種生物也有值得尊敬的地方,我也會想重新挖掘人類的共同命運究竟是什麼。」
專訪後,進行視覺拍攝時,穿著白長衣、綠長褲的潘家欣,拿著綠石竹放在臉下方拍照,像自帶小森林,有一種山神的味道。她也會跟攝影師討論姿勢,以及構圖,試著演現出人與植物的祕密關係。潘家欣外表的平靜自在,彷如仙靈感,跟其劇烈翻騰的心靈風景,具有鮮明反差,也恰恰與綠石竹幽靜的綠意,那樣平靜地爆裂的生命力,隱隱相近吧。●

Tags:
「詩人計畫」希望透過專訪,探尋詩人廣袤的心靈,縱述創作與生命史,捕捉日常中詩意展現的瞬間。此計畫由詩評人沈眠與Openbook閱讀誌共同企劃,視覺構成由攝影師王志元與設計師蘇伊涵合作,不定期刊登。
潘家欣,1984年生,是詩人,也是藝術工作者,出版【獸的三部曲】:剪紙詩集《妖獸》(2012)、版畫詩集《失語獸》(2016)、圖文詩集《負子獸》(2018),以及與阿米合著的《她是青銅器我是琉璃》(2013),並主編《媽媽+1:二十首絕望與希望的媽媽之歌》(2018)。
專訪當天是豔熱的日子,一群人都在抹汗,長衣長褲的潘家欣卻泰然自若,似乎不被天氣侷限,像是自身有恆溫系統。回答問題時她眼神堅定,幾乎像是沒有情緒,平靜無獸性,也不妖異,十足知識分子,跟她詩歌滿滿的強悍與炸裂,有著頗大差異。唯潘家欣說話精簡,每一句都彷如刺拳,又跟她的詩歌相符──最短,也就最有威力。
▉想被容納在龐大如宇宙的農場
小學三、四年級就開始讀童詩,還有很多童話,包含王爾德,甚至早在小二、小三,潘家欣就喜歡讀雄獅出版的一系列民間采集詩歌、傳說與童謠,乃至雄獅在《國語日報》推出的民藝小專欄,如剪紙、扯鈴等,都算是她最早的文學養分。
談起詩歌進入自身生命的狀態,潘家欣是斷然的,「我就是莫名地被吸引,沒有理由。」她停頓幾秒,復又提起尼爾.蓋曼(Neil Gaiman)半自傳奇幻小說《萊緹的遺忘之海》,裡面有他的童年故事,包含總是在想像一個農場,不是人類的,而是容納各種奇異生命龐大如宇宙般的農場。「他說自己從小就喜歡讀神話,沒有為什麼,就是覺得更棒。」
潘家欣也分享小時候讀到神話的種種激動,「比如夸父追日,我的毛會豎起來,真的感受到人為了追求,可以變成多麼巨大的存在。」她十分喜歡《山海經》裡的刑天,「讀完就哭,覺得他超帥,當時不知道為什麼。現在想起來,可能是我很早就對於神話所蘊藏的集體潛意識,有所回應吧。如刑天膽敢犯神的反叛意念,我相信是人類共同的經驗。」
潘家欣表示,小三、小四就寫以自然為主的童詩,到了小五,「因為遭受霸凌,所以開始關心自己的情緒。詩歌能幫我處理那些內在壓力。後來寫的童詩,就變成在描繪大自然時,會放入自身的情緒。」
她也將詩作投稿至《國語日報》,領取稿費,對小學生來說,是滿新鮮的事。隨後,潘家欣談到霸凌,主要是人際關係的障礙,並沒有發展為肢體動作,多是被排擠與孤立,還有言語方面的羞辱。
「我就是個怪小孩啦,同學都有共同語言、共同祕密。我卻一心一意地看天上的雲和地上的花草,比如學校外面的風鈴木、羊蹄甲,我會瞧到發傻,根本不會有人想理我。」她神情安靜地分析自己的童年樣貌。
▉反覆閱讀的
小學二年級,潘家欣在父母的安排下去學畫,雙親是她藝術創作的重要推手。父母給她的自由度很高,加上他們對美的事物有著一定程度的敏感,「他們都是有藝術天分的人。父親是古典的、憂鬱、有一致性的藝術路線,像他很會寫書法。母親則是天馬行空,有時候會覺得她是外星人,比較是當代藝術的系統,雖然她可能沒有意識到。」
潘家欣分享一件母親的藝術舉動:「家裡養著一隻小白頭翁,活了兩年後,病死。媽媽的反應不是拿盒子來葬牠,而是去拿手機來拍攝鳥的遺照。」一講起看似傳統、實則行為有藝術直覺的母親,潘家欣的眼裡都是笑意,「我受到他們滿大的影響,一種是穩定長遠的古典,一種是直觀的當代感,我則是兩種不同藝術系統碰撞下的產物吧。」
迄今她仍反覆閱讀的詩人作品並不多,主要是波特萊爾(Charles P. Baudelaire)的散文詩,「始終具有啟示性,關於我的生命疑問,他的散文詩歌能夠提供我解釋。辛波絲卡(Wisława Szymborska)其實也可以對我有所啟發,只是她比較偏於實用,不像波特萊爾是萬用性。」
台灣則是葉青、阿米和馬尼尼為。「葉青非常嚴謹地在創作,她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阿米則是瞬間的天分,像是有詩歌之神附身,可以說靈感體的畢現。馬尼尼為則是濃密激烈地爆發,而且感覺後面還有東西持續在產生。」
更決定性的影響是鴻鴻創辦的《衛生紙+》詩刊,「那可能是我詩歌寫作的轉折點。」潘家欣直言:「它啟發一整個世代,關於面對現代詩的困境,前輩詩人們集體形成的限制,如何進行翻倒的動作,包括鴻鴻會容許平凡、冗長乃至累贅的詩作,都是關於詩歌的主體與可能性的探索。《衛生紙+》其實是大型策展的概念,它對詩歌語言的實驗性、關懷主題等等方向,做出全新的推進。」
▉《妖獸》:自我性與純感覺展演的擺盪
不想要散漫式收錄詩作,潘家欣決定採用主題性編集,「我認為詩集的本身就應該是一個完整的概念呈現,而且從一開始就決定是【獸的三部曲】。我滿喜歡古希臘戲劇的形式,總會在三部曲後,再搭配一齣鬧劇,也就是在心靈獲得昇華之後,你還是得回歸到人世,面對柴米油鹽。」所以,在詩集三部曲後,她尚有一本獸的喜劇在醞釀與整理中。
剪紙藝術的融入,則是因為「我讀師大美術系,而且一路以來都是美術班體系,很自然就會想要結合。」跨越在詩歌與藝術,潘家欣對兩者的判分是:「基本上使用的腦袋根本上就不同,思考完全是不一樣的。文學是語言與邏輯為主,藝術就是視覺體驗的傳達,畫面充滿直覺。」在潘家欣的觀察,文學圈的瘋子很少,只是自我性比較強,美術班則多的是怪人,比如去偷紅綠燈的學長,並非為了創作,就只是單純的惡作劇,幾乎是不經思維的純感覺展演。
大學時期,如何在兩種腦袋切換,也頗讓潘家欣困擾,不過,她誠實地看見自身藝術天分的不足。以比例來說,「天分只有20%,大多是後天的訓練。不過,」潘家欣眼神熒亮亮,「在詩歌方面則是創造的天分比技術的養成多。」現今潘家欣並不會急迫於作畫,詩歌在她的創作裡的比重更大,也就成為自然而然的選擇。
而所有文學類型中,潘家欣獨鍾詩歌,則是由於「詩歌與藝術在創作上有很接近的血緣。」詩也是更傾向於直覺經驗的噴發,無須顧慮邏輯、秩序,讓語言和個體性擁有最為驚奇、自由的開展。
另外,她也坦承,《妖獸》一開始不是每首詩歌都有對應的剪紙作品,是美編陳采瑩的建議,而潘家欣並不排斥別人的想法加入。詩集中的剪紙圖,大部分都是具象表現,但有些是抽象,如〈雪季〉的剪紙圖是火焰,隱喻嚴寒生命裡可能的燃燒與溫暖,「我想要用圖像闡釋事物更內在深層的形意。但這也有個狀況,就是我的系統不穩定。」
同一本詩集的圖形演繹有不一樣的路徑,是不穩定的表現,對她來說有時形成困擾。潘家欣說:「有些內在穩定一致的創作者,會渴求不確定性。我則是站在另一邊,反而希望自己能穩定。不穩定也許很迷人,但不會是完美作品的基礎。」
▉《失語獸》:帶著傷痕的人才能完成下一輪進化
提及以散文詩體編選的《失語獸》,潘家欣說: 「相對於分行詩,散文詩似乎是邊緣、弱勢的,更之外的東西。我想用散文詩形式,跨出對現代詩就是分行詩的定義。」定名為失語,可視為她對散文詩的定義,亦即失去原先分行詩歌的樣態,也算是溶解術。她進一步說明:「但與其說散文詩是分行詩的失落之變,不如講是對散文的解構,讓語言形式崩壞與異裂,從而看看會產生什麼新的力量。」
另外,潘家欣也破題說:「裡面的詩大多是情緒不好的時候寫下,像〈雞雞森林〉是在面對好像活在外星世界的男學生們,覺得他們都是用雞雞在想事情,心理的衝突很大。」她苦笑:「整本詩集全是負能量的東西,滿中二。」
詩作中常見激烈語調與凶猛直接的意象,起因於現實生活中存有太多令人無法輕易放過的事物。潘家欣說:「因為不甘心,因為想要做出什麼改變,才會怒氣衝天。我想,在絕望的世界中,憤怒可以讓人持續活著,而不至於自毀。」
版畫創作與她藉由散文詩創作去探義詩歌的定型,進行再挖掘的動作,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亦如隔山打牛。畫作依舊晃走實象與抽象之間,有些很具體,有些概念性強,這亦是潘家欣的詩歌特技,在一篇篇具象詩題下游移各種意念的演出。
潘家欣也認同,人的性格與其創作必然有著隱微的對應關係。「我覺得自己是充滿裂痕的人。不管是在社會生活,還是個人心理,好像都有各種細細小小的斷裂。」而就像電影《分裂》所預示,唯帶著傷痕的人方可完成人類的下一輪進化。
▉《負子獸》,真正地生而為人
「《妖獸》是青銅,《失語獸》是鑽石,《負子獸》是原礦。」潘家欣如是說。她對【獸的三部曲】有著清晰的理解與定位。她雖然不抗拒與人合作,但前兩本詩集,因為對作品的高度自覺,還是在一定嚴厲程度的控制之下,到了《負子獸》,「我變得柔軟而隨和,」她彎著嘴淡淡笑著,「甚至設計希望放我的手寫字在最後一頁,即使不覺得自己的字好看,但也同意了。」
造成這種轉變的主因,自然就是女兒的出生,《負子獸》也以詩歌加散文的方式,記錄她成為母親的時光。潘家欣說:「我的進化是因為蘑菇。嬰兒還無法表達自我,所以很多事她都是非得這樣不可的,想哭就哭,想屎尿就屎尿,沒辦法控制。我得要順從她的意志。」甚至就連婚姻也由於蘑菇的訓練而有所進化,「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慣性,難以改變的,我先生也不過如此。一旦體認到這一點,在相處上也就能多一些轉圜。」
而《負子獸》的重要意義在於成為人的過程,「我身為人類,且是人類的通道這件事終於被確定。從青少年時期以來,一直覺得自己不屬於地球,好像身體裡存有另種生命。但懷孕與生產,算是讓我歷經身心的重新創造,真正地生而為人吧。」
她談到某種隱喻也似的內在心理感受,「我總覺得自己不是純人類,而是被人的形體困住,一直不知道要怎麼使弄,怎麼跟人類建立關係。所以長期以來,都在學習任何運用人類的身體、他們的思考方式,理解並適應他們的社會構成。」
她想了想後,又再補充:「為什麼我會對獸物那麼感興趣?也是因為我就是會夢見牠們,變成牠們。我甚至會在夢裡面飛,那是更龐大、更自由的感官經驗。而文字幫助我在清醒時捕捉重溯那樣的極限感。」
問到為何要成為人?潘家欣神情靜靜地講:「不變成人,不調適的話,根本沒辦法好好生活啊,而且也會造成周邊親友的困擾。何況從現在去看,會覺得人這種生物也有值得尊敬的地方,我也會想重新挖掘人類的共同命運究竟是什麼。」
專訪後,進行視覺拍攝時,穿著白長衣、綠長褲的潘家欣,拿著綠石竹放在臉下方拍照,像自帶小森林,有一種山神的味道。她也會跟攝影師討論姿勢,以及構圖,試著演現出人與植物的祕密關係。潘家欣外表的平靜自在,彷如仙靈感,跟其劇烈翻騰的心靈風景,具有鮮明反差,也恰恰與綠石竹幽靜的綠意,那樣平靜地爆裂的生命力,隱隱相近吧。●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
閱讀通信 vol.370》當我在書裡讀到你的時候
延伸閱讀
人物》寫作是絕不迴避的誠實──厭世系詩人始祖隱匿與《永無止境的現在》
閱讀更多
專訪》在地上社會,他們的地下生活:作家林峰毅與詩人德尉
閱讀更多
捕獲外星詩人1》詩是宇宙中孤獨的探偵器:訪詩人黃裕邦與陳昭淵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