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自我為何搖晃?
鄧小樺:我在台灣發現,很多女性都很願意照顧人,但是假如問她,你自己想要怎樣?她就會反過來問我:啊,我想要怎樣?這讓我想起這次對談題目的前半部分——女性的自我。
在我們的文化裡,到底有沒有鼓勵女性從小去追尋自我、堅持自我?面對這個世界的各種衝擊時,我們的自我會受到多大的搖晃?為什麼在台灣,女性照顧家庭好像是必然的責任?就算女性出去上班,還是要照顧家庭。這種責任是誰加諸女性?這種文化又是怎樣形成?
 張瑋軒:我是家裡的第二個女兒,姐姐大我6歲。可以想像當我媽媽懷著我時,家裡人有多失望。又是女孩。當女性第一胎懷的是女兒,很多人的第一句話是:「沒關係,還可以再生一個。」如果一舉得男,她得到的祝賀通常是:「可以休息了。」
張瑋軒:我是家裡的第二個女兒,姐姐大我6歲。可以想像當我媽媽懷著我時,家裡人有多失望。又是女孩。當女性第一胎懷的是女兒,很多人的第一句話是:「沒關係,還可以再生一個。」如果一舉得男,她得到的祝賀通常是:「可以休息了。」
我從小就發現,原來我的出現,不一定帶給媽媽福氣,反而可能帶給她很多在家族中的挑戰或者壓力。小時候我一直在想,我是誰?作為一個女兒,帶給家庭、世界的,又是怎樣的關係?
到小學的第一天,那是自我與世界的第一次相通。我興沖沖地想,可以去迎接這個世界了。老師在台上問,有沒有人想當班長?沒有人舉手,我就舉手說,我想當班長。老師看到後,卻問我隔壁的男同學,你願意當班長嗎?然後對我說,你是女生,那當副班長。
那位男同學可能根本不想當班長,但作為男性,他沒有拒絕的權利,被迫要成為這個世界的棟樑。而我卻因為性別,被告知「因為你是女生,你當副班長」、「因為你是女生,學業不用太好」、「因為你是女生,乖乖的就好」。
女性的自我,很多時候是被恐嚇塑造的。不要出頭、不要給老師添麻煩、不要太優秀。女性的自我形象在形成過程中,常常受到以愛為名的恐嚇。
成年後,女性又缺乏role model可以參考,自我形象就很難形成。女性需要非常刻意地訓練,不要活在社會的規訓裡頭。如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言,我們像是監獄裡以為是主體的被動體。我很相信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所說的:「女人不是生而為女人,而是成為女人。」同理,所有的性別都一樣。所以當我們談女權,並非僅僅為女性謀取權利,我們在談的是所有人。在這個世界,所有人都需要有機會,好好地、無所畏懼地實現自我。
➤誰是男權社會的既得利益者?
閭丘露薇:性別更多是由社會所塑造,而不僅僅是生理上的差異,因此「gender」取代了「sex」這個字。我們未來希望性別角色裡的「男」和「女」到底是什麼樣子?這不僅關乎女性的境遇,也關乎男性的境遇,以及大家的成長背景。
我成長於80年代的上海,整個學習經歷中,從未遇到像像瑋軒所描述的性別歧視問題。我還記得小學時的role model是居里夫人(Marie Curie)。在80年代,大陸其實滿鼓勵大家成為專業人士。
張瑋軒:是因為當時中國一胎化的政策嗎?
 閭丘露薇:大陸當時剛剛改革開放,需要勞動力。相對來說,女性在那時獲得比較平等的機會。這解釋了為什麼當年(中國)共產黨以及蘇聯,在革命的過程中,會成為全球性別平等的role model。
閭丘露薇:大陸當時剛剛改革開放,需要勞動力。相對來說,女性在那時獲得比較平等的機會。這解釋了為什麼當年(中國)共產黨以及蘇聯,在革命的過程中,會成為全球性別平等的role model。
但作為一個專制的制度,當它要縮減(人民權益)的時候,你會發現第一個權益受損的(族群)就是LGBTQ,接著是女性。我們現在看中國在過去10年裡,女性的權益和地位不斷地倒退。這是必然的。甚至最近幾年,LGBTQ也不能提了。這也是必然的。
張瑋軒:她/他們會成為被犧牲的那一群人。
閭丘露薇:對,因為它依然是一個男權的社會。只不過當它需要勞動力來填補的時候,會給你一些機會。整個成長過程中,雖然我好像沒有受到太多的性別規範,以至於後來在電影、傳媒、傳播界做了這麼多年,我可以去採訪戰地⋯⋯
鄧小樺:她當時採訪中國所有領導人,譬如胡錦濤。
閭丘露薇:甚至我也以為是靠自己的努力,但反思後,其實我也是男權社會的得益者——它需要有女性去作點綴。女性得到一些機會,譬如成為全球華人第一個戰地女記者,就會有不匹配的榮譽。戰地記者應該是男女都可以做的事情,但因為不平等,所以女記者一下子就變得很有名。
張瑋軒:為什麼推動性別公平平權、多元共融這麼難?就是因為握有權力的人,通常是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大可不變,而閭丘老師覺察到自己也享受了父權社會的紅利,對我來說特別難得。很多成功的女性領導,會否認自己曾享受了紅利。而沒有成功的女性,尤其後輩,則很容易會質疑自己不夠好,產生冒牌者症候群。她們在有意識或無意識中,選擇讓自己的職涯之路不要太有野心。
➤社會鼓勵怎樣的「優秀」女性?
 鄧小樺:對於女性而言,什麼叫優秀?比如有人說,女性要成為母親才比較完整。而男性讀書成為博士,就是到達頂峰。好像女性成為博士,婚姻就會堪虞,就沒辦法通向「完整」的那條路。因此我們也要思考女性的自我要怎麼確立。譬如一個人學術、創作方面很有成就,但他把自己的身體弄壞了,家裡一團糟,這又算不算優秀呢?
鄧小樺:對於女性而言,什麼叫優秀?比如有人說,女性要成為母親才比較完整。而男性讀書成為博士,就是到達頂峰。好像女性成為博士,婚姻就會堪虞,就沒辦法通向「完整」的那條路。因此我們也要思考女性的自我要怎麼確立。譬如一個人學術、創作方面很有成就,但他把自己的身體弄壞了,家裡一團糟,這又算不算優秀呢?
閭丘露薇:如果是男博士的話,他就是一個「埋頭學術的人」。如果是女性的話,她就是個「對生活不負責任的人」。
鄧小樺:對。關於優秀,社會給男女提供的想像路徑並不一樣。你們覺得社會鼓勵怎樣的優秀?你們自己又覺得怎樣算優秀?
張瑋軒:作為目前尚未懷孕的女性,我真的很常會被問,「你有要懷孕嗎?」緊隨著下一句是,「你再不生,子宮、卵巢就沒辦法生。」另一種人會以非常惋惜的眼光看著我,「你這樣會錯過身為女性最大的快樂。」這時我會對他說:「我覺得創業也是女性可以經歷到的,非常難得的快樂。但我不會要求你應該也要創業。」
對於自我的想像,是基於什麼去建立出來?自我本來就是虛無飄渺的事情。需要不斷地自我叩問:我是誰?我喜歡什麼?在怎樣的處境下,我會感到滿足、快樂?工作時更快樂,還是照顧孩子的時候更快樂?
女性主義發展時,也曾有誤區,認為會工作的女性比較優秀。我認為這大錯特錯,會工作的女性只是代表她有一個選項——當我想工作時,我可以工作。所謂的完整、幸福、優秀應該是:了解自己,勇敢地行動,去嘗試、去努力、去不斷地犯錯、不斷在過程中學習。這樣才有機會把想像的自我與真實的自我作連結與整合。
閭丘露薇:社會怎麼定義一個性別?世界不斷變化,可能進步,也可能退步。拿中國大陸來說,社會在退步。80年代,職業女性是很多女性的role model。但現在大陸女性的role model可能是娛樂明星,或是一個好媽媽。
台灣也在不斷變化,如果去看Netflix,現在很多台灣出品的大女主電視劇,你會覺得台灣進步滿大的。性別意識的構造是由社會的規範——家庭、學校、社會、媒體環境等等所形塑,所以每個人都有責任,都要想自己到底想怎樣。
舉個例子,90年代中,我從大陸移民到香港,從來沒有人來問我:「你結不結婚?你為什麼還單身?」這是受西方社會影響的結果,人和人交往之間有非常明晰的界線。界線建立起來,其實對自我發展有非常大的幫助,因為沒有那麼累。有時候人情味會和界線混淆在一起,人們過度關心和自己不相干的人的生活。親密的人之間也應該有界線,不應該有感情的勒索。
➤兩岸三地的性別意識有何差異?
張瑋軒:為什麼大家對上海女人會有一種海派的印象?跟上海很早就接近西方文明,以及當時的交際花文化有關。而香港長期被英國殖民,亦有其歷史淵源。台灣的歷史則是接受日本統治,然後經歷不同的政權移轉。某程度上,台灣缺少性別角色覺醒的時代,這是我的觀察。
從宏觀來看,台灣經歷太多次政權移轉,從暴力殘忍,到現在邁向民主的進程。很多時候,性別問題會在優先排序裡被放到最後一位。這是我不樂見但情有可原,時代的脈動還輪不到這個題目。
當還沒輪到這個題目時,走在前面的人,就會特別辛苦。所有人都會覺得,這沒有很重要,為什麼要來吵這題。「女性已經可以讀書了,為什麼還覺得不公平?」、「女性也可以投票了,為什麼還覺得不公平?」我創業的時候,有人對我說:「女性現在都可以工作了,你還要怎麼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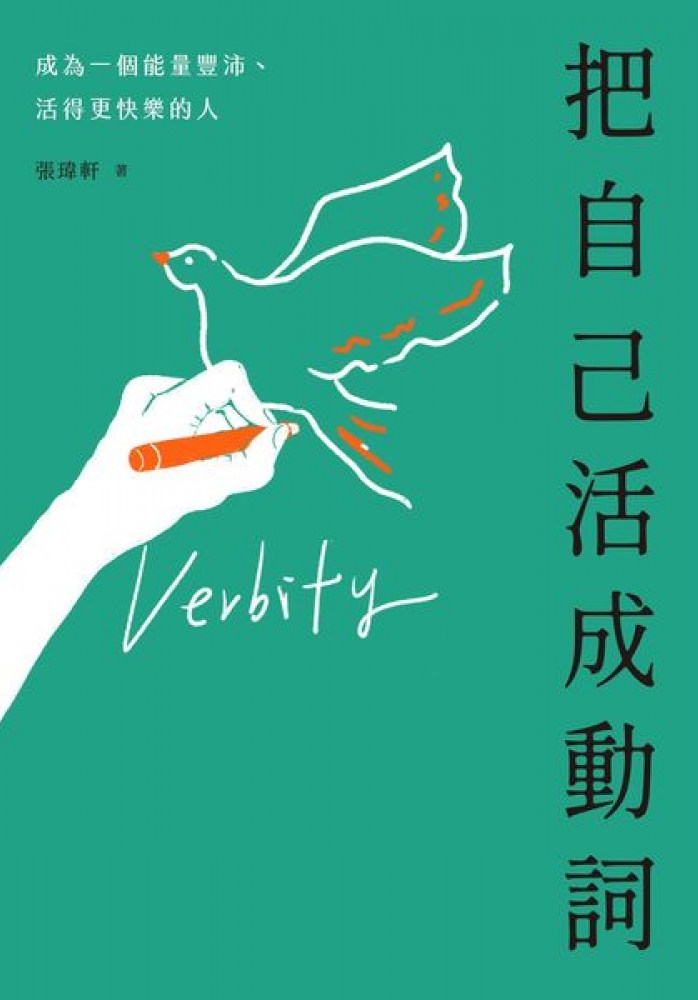 女性都可以工作,這樣就滿足了嗎?100人以上的公司裡,主管階層的性別比例是9比1,九成是男性。所以女性已經可以工作,足夠嗎?性別角色的重大改變,需要歷史的宏觀結構去推波助瀾。譬如二戰期間,美國經濟大蕭條,需要更多勞動力進入到市場當中。當時很多男人都死在戰場上,就需要更多女性投入到職場。
女性都可以工作,這樣就滿足了嗎?100人以上的公司裡,主管階層的性別比例是9比1,九成是男性。所以女性已經可以工作,足夠嗎?性別角色的重大改變,需要歷史的宏觀結構去推波助瀾。譬如二戰期間,美國經濟大蕭條,需要更多勞動力進入到市場當中。當時很多男人都死在戰場上,就需要更多女性投入到職場。
但如果我們並非身處變化劇烈的時代當中,卻想要劇烈地改變性別角色,就需要集體的意識,和我們深度的自覺。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能只靠一個人。不能只靠一個閭丘露薇,一個鄧小樺,或是一個張瑋軒。它需要靠我們所有人,不只是女性,而是要邀請更多男性加入對話。只有對話,我們才有可能避免對立,這個時代才有辦法像太極輪盤一樣去轉變。
鄧小樺:香港被稱作為亞洲性別平等的天花板。香港女人的兇,並不是演出來的,而是混合了上海女人的兇,加上西方女性的自由。來到台灣的時候,我覺得社會相對比較傳統,所以特別想建立一些以女性為主的討論空間,讓大家可互相分享、鼓勵一下。
在我的眼裡,男性、女性不是競爭的狀態,而是大家都可以自由選擇,自己想做和適合做的事情。但我一直在糾結,到底我們要不要撕掉「女性」這個標籤?性別到底是本質性的差異,還是我們要提倡的價值?譬如提出這是一個「女性的方法」,有沒有問題?
 閭丘露薇:性別不平等的社會對男性來說,也是不公平的。男性群體裡,就缺少了多樣化的存在。這也就是為什麼同性戀,在男性群體裡會受到霸凌。這是相輔相成的問題。
閭丘露薇:性別不平等的社會對男性來說,也是不公平的。男性群體裡,就缺少了多樣化的存在。這也就是為什麼同性戀,在男性群體裡會受到霸凌。這是相輔相成的問題。
當我們討論性別平等、多元化的社會時,不能只討論女性的性別形象是怎樣。有一個詞,叫Toxic masculinity,即有毒的男性氣質,怎樣改變它也非常重要。另外講到香港,很多人覺得香港的男女很平等,因為很早就訂立了性別平等條例、設置平等機會委員會。按數據來看,女性的就業率,或者女性高管的比例,相對來說可能比台灣要多一點。但反過來看,台灣實現了同婚,在香港還沒有實現,而且路漫漫不知道何時。
說老實話,我覺得香港社會滿保守。90年代訂立了性別平等條例,以為(性別不平等的)問題解決了。慢慢積累,現在有越來越多新的問題。我在香港教授性別課,發現討論性別議題時,反而是中國大陸來的學生,尤其是女生,對性別議題的意識比香港的同學要高很多。
而有意思的是,我問香港男生為什麼來修讀我這門課,他們告訴我,覺得港女好厲害,就來看看這個課到底教什麼。他們覺得香港的女權意識,已經讓男生很受迫害。這可能是很多香港人的想法,所以我覺得,香港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如何追尋、堅持自我?
張瑋軒:我傾向不去想標籤,男人就是怎樣,女人就是怎樣;香港女人就是怎樣,台灣男人就是怎樣。標籤化是我想要打破的事情,每一個人身上都有很多元的呈現。作為一個主體,有沒有能力去勇敢的在各個場合呈現自己的標籤跟自己的傾向,才是我關注的。
有時候我會想,陽性氣質跟陰性氣質深耕在我們的文化之中,陰陽本來就指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指的是,男性能不能夠在生長過程中,理解到自己的脆弱,坦承自己的情感需求。同理可證,在陰性氣質裡,怎麼樣去培養我們的陽性氣質,包含韌性、膽氣、氣派,或者是決定力等等。
鄧小樺:這是一個需要持續被討論的問題,就像語言一樣,它是有概念的。概念被我們的文化塑成,但我們不使用語言溝通也不是一個方法。只能一邊使用,一邊反省。
觀眾提問:如何在質疑中堅定找尋自我?
張瑋軒:女性主義不是只為女性服務,而是學會看見目前既存權力結構中的不公。權力結構包含種族、金錢、階級、教育、信仰、年紀、身形、婚戀狀態、家庭人口……各種我們可以想得到把人類以群分的方式,它都可能是迫害,跟被迫害。
我很希望普羅大眾都可以學習女性主義或性別研究,它就像戴上眼鏡,突然之間你會覺察到很多。我們可以學會為自己採取行動——當我聽見有人說:「再不生你的子宮會壞掉」,我就會說:「這是我的子宮,謝謝你的幫忙,但這是我的子宮。」或是我聽見有人說,「瑋軒你現在是創業的CEO,為什麼上台要穿裙子?」所以我每次上台演講,都會穿裙子。
我們可以透過每一天的行動,來跟這個世界產生對話。我們要對抗或嘗試鬆動權力結構的唯一辦法,就是每天發聲,讓我們身邊的人多看到一點點、多理解一點點。
閭丘露薇:我覺得真正的朋友是,會聆聽並且包容你的決定。當你為自己的錯誤後悔或反省的時候,他會在你身邊。這才是你需要在意和傾聽的朋友。如果他給你一些決斷的意見,不用太在意。你要想,假如因為聽了他的話而做決定,要承受後果的時候,這個人早就不知道去哪了,他根本不會在乎你所承受的負面結果。

Tags:
左起鄧小樺、閭丘露薇、張瑋軒
編按:曾赴伊拉克戰爭的華人女記者、《浮世薔薇》作者閭丘露薇,與女力社群媒體「女人迷」創辦人、《把自己活成動詞》作者張瑋軒,日前在台北國際書展以「女性:自我與世界」為題,展開身為女性的思索。人生經歷豐富的二人,透過檢視兩岸三地的歷史與社會背景,開拓身為女子的可能,持續發問。
➤女性自我為何搖晃?
鄧小樺:我在台灣發現,很多女性都很願意照顧人,但是假如問她,你自己想要怎樣?她就會反過來問我:啊,我想要怎樣?這讓我想起這次對談題目的前半部分——女性的自我。
在我們的文化裡,到底有沒有鼓勵女性從小去追尋自我、堅持自我?面對這個世界的各種衝擊時,我們的自我會受到多大的搖晃?為什麼在台灣,女性照顧家庭好像是必然的責任?就算女性出去上班,還是要照顧家庭。這種責任是誰加諸女性?這種文化又是怎樣形成?
我從小就發現,原來我的出現,不一定帶給媽媽福氣,反而可能帶給她很多在家族中的挑戰或者壓力。小時候我一直在想,我是誰?作為一個女兒,帶給家庭、世界的,又是怎樣的關係?
到小學的第一天,那是自我與世界的第一次相通。我興沖沖地想,可以去迎接這個世界了。老師在台上問,有沒有人想當班長?沒有人舉手,我就舉手說,我想當班長。老師看到後,卻問我隔壁的男同學,你願意當班長嗎?然後對我說,你是女生,那當副班長。
那位男同學可能根本不想當班長,但作為男性,他沒有拒絕的權利,被迫要成為這個世界的棟樑。而我卻因為性別,被告知「因為你是女生,你當副班長」、「因為你是女生,學業不用太好」、「因為你是女生,乖乖的就好」。
女性的自我,很多時候是被恐嚇塑造的。不要出頭、不要給老師添麻煩、不要太優秀。女性的自我形象在形成過程中,常常受到以愛為名的恐嚇。
成年後,女性又缺乏role model可以參考,自我形象就很難形成。女性需要非常刻意地訓練,不要活在社會的規訓裡頭。如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言,我們像是監獄裡以為是主體的被動體。我很相信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所說的:「女人不是生而為女人,而是成為女人。」同理,所有的性別都一樣。所以當我們談女權,並非僅僅為女性謀取權利,我們在談的是所有人。在這個世界,所有人都需要有機會,好好地、無所畏懼地實現自我。
➤誰是男權社會的既得利益者?
閭丘露薇:性別更多是由社會所塑造,而不僅僅是生理上的差異,因此「gender」取代了「sex」這個字。我們未來希望性別角色裡的「男」和「女」到底是什麼樣子?這不僅關乎女性的境遇,也關乎男性的境遇,以及大家的成長背景。
我成長於80年代的上海,整個學習經歷中,從未遇到像像瑋軒所描述的性別歧視問題。我還記得小學時的role model是居里夫人(Marie Curie)。在80年代,大陸其實滿鼓勵大家成為專業人士。
張瑋軒:是因為當時中國一胎化的政策嗎?
但作為一個專制的制度,當它要縮減(人民權益)的時候,你會發現第一個權益受損的(族群)就是LGBTQ,接著是女性。我們現在看中國在過去10年裡,女性的權益和地位不斷地倒退。這是必然的。甚至最近幾年,LGBTQ也不能提了。這也是必然的。
張瑋軒:她/他們會成為被犧牲的那一群人。
閭丘露薇:對,因為它依然是一個男權的社會。只不過當它需要勞動力來填補的時候,會給你一些機會。整個成長過程中,雖然我好像沒有受到太多的性別規範,以至於後來在電影、傳媒、傳播界做了這麼多年,我可以去採訪戰地⋯⋯
鄧小樺:她當時採訪中國所有領導人,譬如胡錦濤。
閭丘露薇:甚至我也以為是靠自己的努力,但反思後,其實我也是男權社會的得益者——它需要有女性去作點綴。女性得到一些機會,譬如成為全球華人第一個戰地女記者,就會有不匹配的榮譽。戰地記者應該是男女都可以做的事情,但因為不平等,所以女記者一下子就變得很有名。
張瑋軒:為什麼推動性別公平平權、多元共融這麼難?就是因為握有權力的人,通常是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大可不變,而閭丘老師覺察到自己也享受了父權社會的紅利,對我來說特別難得。很多成功的女性領導,會否認自己曾享受了紅利。而沒有成功的女性,尤其後輩,則很容易會質疑自己不夠好,產生冒牌者症候群。她們在有意識或無意識中,選擇讓自己的職涯之路不要太有野心。
➤社會鼓勵怎樣的「優秀」女性?
閭丘露薇:如果是男博士的話,他就是一個「埋頭學術的人」。如果是女性的話,她就是個「對生活不負責任的人」。
鄧小樺:對。關於優秀,社會給男女提供的想像路徑並不一樣。你們覺得社會鼓勵怎樣的優秀?你們自己又覺得怎樣算優秀?
張瑋軒:作為目前尚未懷孕的女性,我真的很常會被問,「你有要懷孕嗎?」緊隨著下一句是,「你再不生,子宮、卵巢就沒辦法生。」另一種人會以非常惋惜的眼光看著我,「你這樣會錯過身為女性最大的快樂。」這時我會對他說:「我覺得創業也是女性可以經歷到的,非常難得的快樂。但我不會要求你應該也要創業。」
對於自我的想像,是基於什麼去建立出來?自我本來就是虛無飄渺的事情。需要不斷地自我叩問:我是誰?我喜歡什麼?在怎樣的處境下,我會感到滿足、快樂?工作時更快樂,還是照顧孩子的時候更快樂?
女性主義發展時,也曾有誤區,認為會工作的女性比較優秀。我認為這大錯特錯,會工作的女性只是代表她有一個選項——當我想工作時,我可以工作。所謂的完整、幸福、優秀應該是:了解自己,勇敢地行動,去嘗試、去努力、去不斷地犯錯、不斷在過程中學習。這樣才有機會把想像的自我與真實的自我作連結與整合。
閭丘露薇:社會怎麼定義一個性別?世界不斷變化,可能進步,也可能退步。拿中國大陸來說,社會在退步。80年代,職業女性是很多女性的role model。但現在大陸女性的role model可能是娛樂明星,或是一個好媽媽。
台灣也在不斷變化,如果去看Netflix,現在很多台灣出品的大女主電視劇,你會覺得台灣進步滿大的。性別意識的構造是由社會的規範——家庭、學校、社會、媒體環境等等所形塑,所以每個人都有責任,都要想自己到底想怎樣。
舉個例子,90年代中,我從大陸移民到香港,從來沒有人來問我:「你結不結婚?你為什麼還單身?」這是受西方社會影響的結果,人和人交往之間有非常明晰的界線。界線建立起來,其實對自我發展有非常大的幫助,因為沒有那麼累。有時候人情味會和界線混淆在一起,人們過度關心和自己不相干的人的生活。親密的人之間也應該有界線,不應該有感情的勒索。
➤兩岸三地的性別意識有何差異?
張瑋軒:為什麼大家對上海女人會有一種海派的印象?跟上海很早就接近西方文明,以及當時的交際花文化有關。而香港長期被英國殖民,亦有其歷史淵源。台灣的歷史則是接受日本統治,然後經歷不同的政權移轉。某程度上,台灣缺少性別角色覺醒的時代,這是我的觀察。
從宏觀來看,台灣經歷太多次政權移轉,從暴力殘忍,到現在邁向民主的進程。很多時候,性別問題會在優先排序裡被放到最後一位。這是我不樂見但情有可原,時代的脈動還輪不到這個題目。
當還沒輪到這個題目時,走在前面的人,就會特別辛苦。所有人都會覺得,這沒有很重要,為什麼要來吵這題。「女性已經可以讀書了,為什麼還覺得不公平?」、「女性也可以投票了,為什麼還覺得不公平?」我創業的時候,有人對我說:「女性現在都可以工作了,你還要怎麼樣?」
但如果我們並非身處變化劇烈的時代當中,卻想要劇烈地改變性別角色,就需要集體的意識,和我們深度的自覺。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能只靠一個人。不能只靠一個閭丘露薇,一個鄧小樺,或是一個張瑋軒。它需要靠我們所有人,不只是女性,而是要邀請更多男性加入對話。只有對話,我們才有可能避免對立,這個時代才有辦法像太極輪盤一樣去轉變。
鄧小樺:香港被稱作為亞洲性別平等的天花板。香港女人的兇,並不是演出來的,而是混合了上海女人的兇,加上西方女性的自由。來到台灣的時候,我覺得社會相對比較傳統,所以特別想建立一些以女性為主的討論空間,讓大家可互相分享、鼓勵一下。
在我的眼裡,男性、女性不是競爭的狀態,而是大家都可以自由選擇,自己想做和適合做的事情。但我一直在糾結,到底我們要不要撕掉「女性」這個標籤?性別到底是本質性的差異,還是我們要提倡的價值?譬如提出這是一個「女性的方法」,有沒有問題?
當我們討論性別平等、多元化的社會時,不能只討論女性的性別形象是怎樣。有一個詞,叫Toxic masculinity,即有毒的男性氣質,怎樣改變它也非常重要。另外講到香港,很多人覺得香港的男女很平等,因為很早就訂立了性別平等條例、設置平等機會委員會。按數據來看,女性的就業率,或者女性高管的比例,相對來說可能比台灣要多一點。但反過來看,台灣實現了同婚,在香港還沒有實現,而且路漫漫不知道何時。
說老實話,我覺得香港社會滿保守。90年代訂立了性別平等條例,以為(性別不平等的)問題解決了。慢慢積累,現在有越來越多新的問題。我在香港教授性別課,發現討論性別議題時,反而是中國大陸來的學生,尤其是女生,對性別議題的意識比香港的同學要高很多。
而有意思的是,我問香港男生為什麼來修讀我這門課,他們告訴我,覺得港女好厲害,就來看看這個課到底教什麼。他們覺得香港的女權意識,已經讓男生很受迫害。這可能是很多香港人的想法,所以我覺得,香港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如何追尋、堅持自我?
張瑋軒:我傾向不去想標籤,男人就是怎樣,女人就是怎樣;香港女人就是怎樣,台灣男人就是怎樣。標籤化是我想要打破的事情,每一個人身上都有很多元的呈現。作為一個主體,有沒有能力去勇敢的在各個場合呈現自己的標籤跟自己的傾向,才是我關注的。
有時候我會想,陽性氣質跟陰性氣質深耕在我們的文化之中,陰陽本來就指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指的是,男性能不能夠在生長過程中,理解到自己的脆弱,坦承自己的情感需求。同理可證,在陰性氣質裡,怎麼樣去培養我們的陽性氣質,包含韌性、膽氣、氣派,或者是決定力等等。
鄧小樺:這是一個需要持續被討論的問題,就像語言一樣,它是有概念的。概念被我們的文化塑成,但我們不使用語言溝通也不是一個方法。只能一邊使用,一邊反省。
觀眾提問:如何在質疑中堅定找尋自我?
張瑋軒:女性主義不是只為女性服務,而是學會看見目前既存權力結構中的不公。權力結構包含種族、金錢、階級、教育、信仰、年紀、身形、婚戀狀態、家庭人口……各種我們可以想得到把人類以群分的方式,它都可能是迫害,跟被迫害。
我很希望普羅大眾都可以學習女性主義或性別研究,它就像戴上眼鏡,突然之間你會覺察到很多。我們可以學會為自己採取行動——當我聽見有人說:「再不生你的子宮會壞掉」,我就會說:「這是我的子宮,謝謝你的幫忙,但這是我的子宮。」或是我聽見有人說,「瑋軒你現在是創業的CEO,為什麼上台要穿裙子?」所以我每次上台演講,都會穿裙子。
我們可以透過每一天的行動,來跟這個世界產生對話。我們要對抗或嘗試鬆動權力結構的唯一辦法,就是每天發聲,讓我們身邊的人多看到一點點、多理解一點點。
閭丘露薇:我覺得真正的朋友是,會聆聽並且包容你的決定。當你為自己的錯誤後悔或反省的時候,他會在你身邊。這才是你需要在意和傾聽的朋友。如果他給你一些決斷的意見,不用太在意。你要想,假如因為聽了他的話而做決定,要承受後果的時候,這個人早就不知道去哪了,他根本不會在乎你所承受的負面結果。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
閱讀通信 vol.366》為什麼要叫勇者,不叫英雄?
延伸閱讀
人物》是時代把你實現了:訪《我香港,我街道》系列主編鄧小樺
編按:2021年6月,香港《蘋果日報》編輯部遭到突擊搜查、母公司壹傳媒高層被警方依港區國安法拘捕,並遭凍結銀行帳戶與資金而被迫停止營運,於6月24日以「港人雨中痛別... 閱讀更多
對談》理解的艱難:胡慕情與張娟芬談《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
編按:鏡文學文化組採訪主任胡慕情日前出版《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深度剖析2009年震驚全台的林于如連環弒親案。全書分三部分,首先呈現親訪死刑犯過程,其次完整披露林于如自傳,... 閱讀更多
對談》花開少女如何成為親愛的共犯—從性別到類型的小說之旅:陳雪vs楊双子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