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整理/郭如梅(北海道大學文學院人文學專攻表現文化論講座博士生)
國立中興大學自2021年起設立「川流台灣文學駐校作家」,首任邀請作家楊双子擔任。4月下旬,同樣曾於2017年在中興大學駐校的作家陳雪應邀,針對如何從性別書寫出發進而結合類型的寫作趨勢與楊双子進行對談,由台文所所長陳國偉擔任主持。

左起:中興大學台文所所長陳國偉、作家陳雪、作家楊双子
***
 陳國偉:這次安排陳雪與楊双子兩代中興大學駐校作家對談,二位有很多共同點,都是台灣女同志婚姻非常重要的代表,卻從來沒有公開對談過。陳雪是台中人,1995年以《惡女書》出道後,在同志跟性別領域上有很多重要的代表作。後來她不僅投入鄉土題材,這幾年更嘗試結合犯罪推理的書寫。楊双子也是台中人,畢業於中興台文所,雙胞胎妹妹若暉病逝後,投身百合歷史的相關創作。
陳國偉:這次安排陳雪與楊双子兩代中興大學駐校作家對談,二位有很多共同點,都是台灣女同志婚姻非常重要的代表,卻從來沒有公開對談過。陳雪是台中人,1995年以《惡女書》出道後,在同志跟性別領域上有很多重要的代表作。後來她不僅投入鄉土題材,這幾年更嘗試結合犯罪推理的書寫。楊双子也是台中人,畢業於中興台文所,雙胞胎妹妹若暉病逝後,投身百合歷史的相關創作。
本次對談,希望請她們分享自己的創作歷程與轉變。首先想請陳雪談談為何當初進入文壇時會以性別為主題,後來又開始創作《橋上的孩子》這類鄉土定位的作品。
■當她們從自身開始思考性別
陳雪:我開始寫作大概是1990年代解嚴之後,那時大家最關注的,就是政治跟性別。性別的問題對那時候的我也是很切身的問題,因為我比較像是雙性戀,喜歡男生也喜歡女生。在那個時代,你會對這樣的性向感到一些困惑,能閱讀的東西也不多,所以對一個寫作的初學者來說,它就是非常好的領域。也就是說,我想寫還沒有看過的東西,想寫還沒有人寫過的東西,而它剛好也是我關注的。
所以我的第一本書《惡女書》跟自己的故事沒有什麼關係,但我寫得非常大膽,因為對我來說,我的小說就是我跟世界產生衝突的一個方式。可是後來當我寫完《惡魔的女兒》,我忽然覺得我衝撞出來的那個位置,其實也不是屬於我的位置。
2000年我去了一趟美國,在美國放空的那段時期,我想起小時候跟父母在橋上賣東西。這讓我很清楚的意識到,假設我要釐清我自己是誰,必須要回到我的家鄉、我的童年,回到那個可能真的傷害、離散產生的源頭,所以我開始寫了《橋上的孩子》、《陳春天》、《附魔者》這三部曲。

我覺得今天我跟双子的對談會非常有意思,因為我們兩個處理的元素很像,但路徑不太一樣,可以做為很好的對照。
陳國偉:双子自己是研究言情小說出身的,也從事言情小說創作,後來寫《花開時節》把性別跟歷史做連結,這是妳一開始就想寫的東西嗎?為什麼一開始就想這樣處理性別?
楊双子:我9歲就開始想要創作,但當時是想成為漫畫家。直到今天,台灣市面上都還是以少年漫畫為大宗,在這種情況之下,一個9歲的女孩要開始創作,會遇到的很大問題是:自己設計了很多角色,結果回頭來看都是男性角色。
直到國中之後,我才意識到,我根本不知道女生可以進行什麼冒險。那時候甚至做了一個夢,我變成一個既不是男生也不是女生的孩子,醒來真的覺得是場惡夢。可是在那個當下,我突然接受了:好,我今後是個女孩,我要來創作女孩的故事。後來在寫言情小說的經驗中,也逐漸在既有的羅曼史內理解,那樣的女主角並不是我想要當的女孩,所以言情小說寫到後來我也有點後繼無力,才開始轉向其他路線。但自始至終,性別一直都是我很在意的題目。

作家楊双子
■從類型通往社會與歷史
陳國偉:双子是出道的時候就很清楚要選擇類型來創作,陳雪則是一直到了2015年才陸續寫了《摩天大樓》、《無父之城》跟《親愛的共犯》。為什麼陳雪會開始想要在小說中結合推理犯罪的類型元素?原來那些性別、創傷或自己的經驗,也會想繼續放進創作裡面嗎?
陳雪:我覺得我的小說有幾個階段。寫完《迷宮中的戀人》時候覺得,我把我自己的病治得差不多了,終於可以成為一個比較完整的人,那下一步我該怎麼出發?
那時我已經在台北住很多年了,台北有很多外地來的人,我想寫這些人在台北這個城市的狀態。有段時間我住在像摩天大樓一樣的住商混合大樓,我認為摩天大樓是台北城市非常適合的隱喻。我一直很想寫謀殺案,所以開始動筆寫《摩天大樓》的時候,我把犯罪題材放進去。但起初很尷尬跟猶豫,因為台灣的純文學作家其實已經有很標準的路線,你知道什麼東西可以寫,什麼東西寫了就會「逼——」這樣……(全場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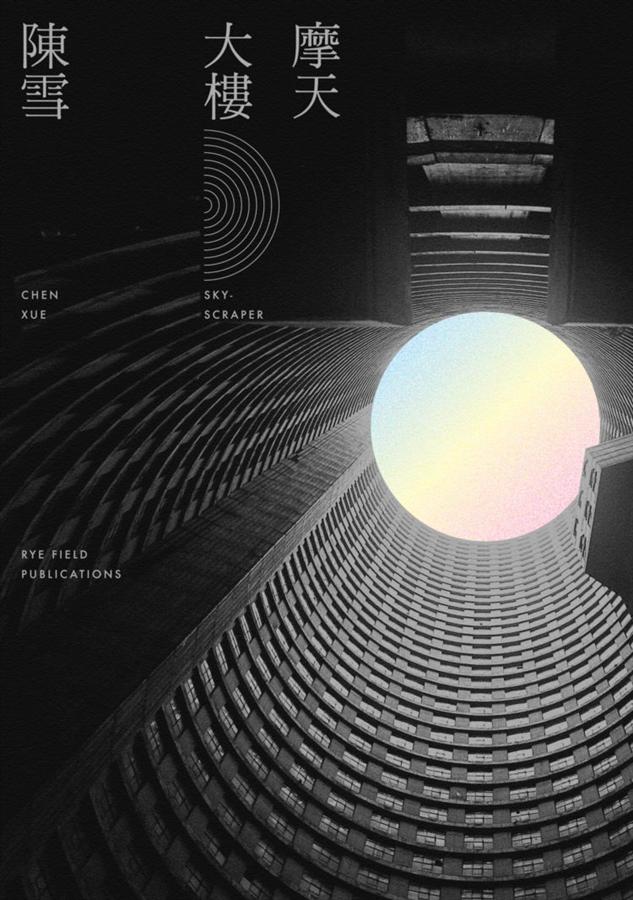 但我就是特別叛逆的人,所以《摩天大樓》是本很奇怪的小說,它有謀殺案,但沒有破案,是個滿實驗性的寫法。那可以算是我自己的「小說元年」,之後寫《無父之城》時,我又被「逼——」了,但我必須要承認,在寫那些東西的時候,做為小說家的我真的很快樂。
但我就是特別叛逆的人,所以《摩天大樓》是本很奇怪的小說,它有謀殺案,但沒有破案,是個滿實驗性的寫法。那可以算是我自己的「小說元年」,之後寫《無父之城》時,我又被「逼——」了,但我必須要承認,在寫那些東西的時候,做為小說家的我真的很快樂。
我覺得小說家還是要忠於內心的呼喚,現在的我會想要處理社會上的問題,而我的內在肯定有一些呼應。這是我年輕時的文學養成,像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影響,我想要追問罪與罰、善與惡,人到底是什麼,人性的試探這些問題。這些是從年輕時代就種在我心裡的,只是現在我採取了更戲劇性的結合來創作。
陳國偉:正如剛剛陳雪提到的,研究者都會注意到《惡女書》的罪與罰,王德威老師在《摩天大樓》的序中,也從這個脈絡連結下來。當然大家其實可以用不一樣的角度來看這些作品,因為世界文學中其實有很多用類型來寫純文學的大師,像是波赫士、卡爾維諾、瑪格麗特.愛特伍、石黑一雄、奧罕.帕慕克等等。
双子做為不一樣脈絡出身的寫作世代,一開始就跟類型密切相關,而且顯然很有意識要打破類型。妳自己當時是怎麼有意識要進行這樣的結合?
楊双子:其實我預設的目標讀者幾乎沒有讀我的小說,有幾個可能的理由,其中最關鍵的應該是:百合迷群在追求的,跟我寫出來的東西不一樣。我知道怎麼做會更符合百合迷群的需求,可是,我覺得那不是我要做的事情。
以前寫言情小說時,我後面有兩部作品是接連被退稿的,主要原因是我嘗試觸及的議題太接近現實社會,而不只是停留在以愛情為主軸的故事。像我第4本言情小說的男女主角就涉及到貧窮的背景,言情小說很少處理貧窮,當時編輯還打電話來說,有一個段落要不要乾脆拿掉,因為她覺得好慘喔。所以很明顯的,我想寫的內容就不適合繼續留在言情小說的世界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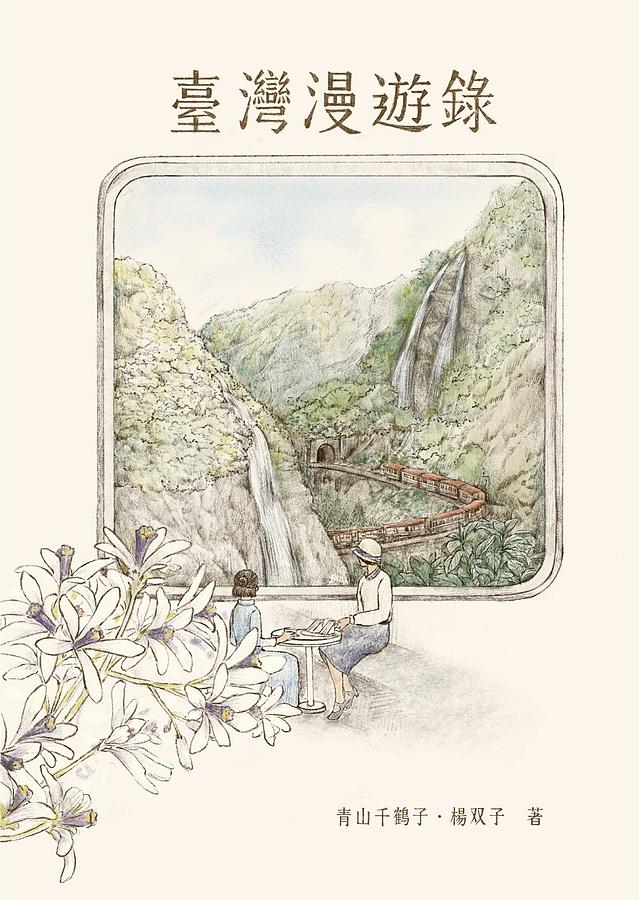 我寫的百合小說,其實主要是在探尋「愛」到底是什麼。像最近的《臺灣漫遊錄》,我寫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的百合關係,故事發展起來感覺她們應該是要終成眷屬,但我的答案是不會,因為愛是無法跨越殖民地政權運作底下的種族與其他障礙的。即使如此,我沒有放棄去書寫愛,我認為正是有愛無法企及的事情,才更接近愛,可是這不是百合迷群要看的東西。因此相較起來,我自己本身的創作在純文學界似乎更被重視,遠遠超過百合迷群的世界,這真的是我始料未及的。
我寫的百合小說,其實主要是在探尋「愛」到底是什麼。像最近的《臺灣漫遊錄》,我寫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的百合關係,故事發展起來感覺她們應該是要終成眷屬,但我的答案是不會,因為愛是無法跨越殖民地政權運作底下的種族與其他障礙的。即使如此,我沒有放棄去書寫愛,我認為正是有愛無法企及的事情,才更接近愛,可是這不是百合迷群要看的東西。因此相較起來,我自己本身的創作在純文學界似乎更被重視,遠遠超過百合迷群的世界,這真的是我始料未及的。
陳國偉:既然殖民政權是愛不能跨越的,那麼百合關係如果要終成眷屬,是不是離開了那個歷史階段就有可能?而且即便如此,為什麼妳還是會特別想要結合歷史來書寫?
楊双子:我們家族在成功嶺山腳下生活了至少兩百年,明明已經在這裡生活那麼久了,可是我小時候因為在眷村長大,就以為自己是外省人,而且有很強的中國認同。我們姊妹18歲時還存錢去中國旅遊,但那也是幻滅的開始。2008年野草莓學運,當時為了要準備考台文所,我讀了很多戰前作家的作品,才更清楚意識到,原來我們根本有著截然不同的土地經驗。剛好這個階段,言情小說我也寫不下去了,所以開始萌生這樣的念頭:我應該來寫這塊土地的事情。創作對我來說,最終還是回歸到我生命裡面在意的事情,而國族認同是很重要的一塊。
■附身 vs Excel表的寫作方法論
陳國偉:身為讀者,我們十分好奇兩位是以怎樣的寫作方式進行的。陳雪剛剛提到有自己的寫作方式,要不要談談那是怎樣的狀態?

作家陳雪
陳雪:其實我建議你們最好不要學我,因為我的方法可能只適合我自己。
以前寫純文學時,基本上有了一個畫面就開始啟動了。但我很重視小說結構,例如寫《附魔者》,它就是多人輪唱、多聲部的轉換;到了《摩天大樓》,我想用場所來界定空間,再讓故事長出來;再到了《無父之城》,我就是想要安排警探這樣的角色,所以小說開場就出現的私家偵探,本來是個刑警。我讓小說從一個人物開始,然後接續不同的人物出來敘述。我沒有預先寫大綱,就是用很直覺的方法把小說串接起來。
我正在寫的作品是關於連續殺人魔,但起心動念其實很簡單,我只是想要寫一個人,他的父親是個兇手,後來就變成連續殺人。但寫到後來,我壓力大到都落髮了。為什麼壓力那麼大?因為我沒有先預設結局,所以寫到後面一直沒辦法破案!(全場大笑)
當然我最後還是破案了,因為《摩天大樓》之前有改編成電視劇,所以認識了一些影視公司的人,他們很喜歡我的作品,就一直跟我說:陳雪老師妳不要怕,妳的這種推理方式,叫作「情感推理」!(全場大笑)
我這種寫法就像附身一樣,每天都要附身一個角色才有辦法寫,因為我就是用情感推理。有一天我剛好附身寫到最後重要的場景時,我就跟伴侶阿早(早餐人)意外起了很大的衝突,因為我正好在兇手的心理狀態。後來我跟她說:那個不是我,是小說裡面那個誰,但我又說不清,因為她還沒看小說。我就想,哎呀這個傷害、這種副作用實在很大耶!所以我認識双子之後,每次她跟我講她怎麼擬大綱寫小說,我都好崇拜她。
楊双子:救命啊(笑)
陳雪:我每天都在那個情感泥淖裡面自己盤旋,害得阿早一直很害怕。她以前只是我的改稿者,現在還變成受害者,所以等成品出來後讓你們看看,是不是需要進入楊双子整治時間。
楊双子:不敢啊,救命啊(笑)。我們這樣好像是在討論演技的方法論之類的議題,其實大家的作法真的都很不相同。像我跟作家瀟湘神都是寫類型小說出身的,基本上還是要有大綱,才能知道最後故事要走到哪裡。我自己會有3個大綱:第一個會很簡單,通常開頭結尾都很明確。至於如何從開頭走到結尾的中間部分,我會切成4份,就是起承轉合。這是來自寫言情小說的經驗,通常每一章大概只有5000字,為了要符合它的故事框架,合理分配情節,所以必須要有大綱。
除了章節大綱外,我還會有一個人物設計表,把小說裡面出場的主角和主要配角全部列出來。在寫《花開時節》的時候,他們家族從17世紀開始的祖先我都想好了:如何從漳州來到台灣,叫什麼名字,生了幾個兒子,我全部都會先寫下來。所以會有一個很龐大的人物表,甚至我有做一個Excel表……
陳雪:Excel表!?(全場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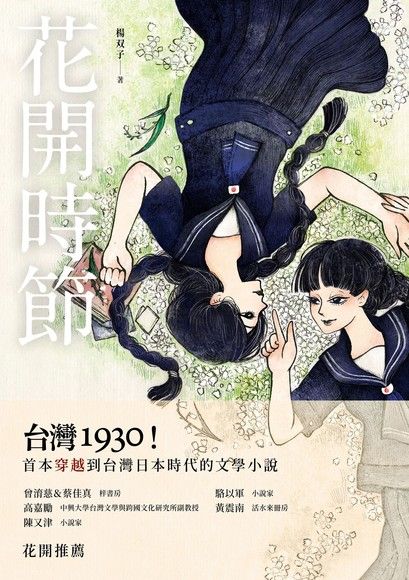 楊双子:對,所有的角色!從女主角的祖先開始放在第一個,他是哪一年來台灣的,他幾歲,他的所有重要親屬,全都放上去。譬如說,故事會從1926年寫到1939年,就可以對應每個人在哪個時間點是幾歲。這個系統其實是妹妹若暉一手建置的,因為她是歷史系出身的,非常擅長製作年表,甚至像《花開時節》所有主配角的星座我都一清二楚。(全場大笑)
楊双子:對,所有的角色!從女主角的祖先開始放在第一個,他是哪一年來台灣的,他幾歲,他的所有重要親屬,全都放上去。譬如說,故事會從1926年寫到1939年,就可以對應每個人在哪個時間點是幾歲。這個系統其實是妹妹若暉一手建置的,因為她是歷史系出身的,非常擅長製作年表,甚至像《花開時節》所有主配角的星座我都一清二楚。(全場大笑)
我覺得這很關鍵,不只對應我們對星座的認知,還牽涉到角色出生的那年,可能剛好有一場流行病,那就可以清楚對應。像《花開時節》中惠風哥哥其實還有個弟弟,但因為流行性感冒死去了,雖然這個小說裡完全沒有寫到——所以這也是我第一次提到他們家還有另外一個男孩。(全場笑)
透過那個Excel表,包括《花開時節》故事結束之後,到戰後整個家族的所有事情都已經列明,只是沒有寫出來而已。所以後來在談改編時,我被問到惠風哥哥後來怎麼了?……這裡讓我爆個雷:其實戰後他突然理解到,他有必須承擔的責任,因為他是這個地方的頭人,必須出來為大家爭取,所以就在白色恐怖當中死去了。對,雖然在《花開時節》中完全沒有寫到,但其實他的故事早已有了清楚的結局。
■重新丈量文學史的尺度
陳國偉:從兩位剛剛對寫作形式的說明,大家見證到兩種完全不同型態的創作者,也可以感受到與各自原有寫作的脈絡跟特色,有很明確的關係。我知道兩位也有相當程度的私交,很好奇兩位怎麼看彼此最近書寫的類型和狀態?
陳雪:我認識双子就是我在中興大學擔任駐校作家的時候,她送了我一本《花開時節》。當時我沒想過這是歷史百合或什麼類型,但老實說我還滿震驚的,因為那時候我就覺得她的作品非常獨特。双子所使用的小說語言真的超厲害,她可以把漢語、日語、台語融合成一種書面語,自成一種聲調,她的強項是她已經可以把那個時代的聲音展現出來。
楊双子:謝謝陳雪老師,好害羞,真的非常感謝。我自己寫百合小說,但它跟女同志小說是不一樣的。然而我可以做出不一樣,就是因為前面有人開了女同志文學的先河。這件事情毫無疑問,只要跟我同年齡的寫作者,只要我們是女同志的話,不可能不受到陳雪老師的影響。
當我看到《惡女書》、《蝴蝶的記號》這樣的作品時,我開始思考,該如何呈現只有我們這個世代才能呈現的東西?我不可能再選擇去回應女同志文學,因為太難了,陳雪老師已經樹立了典範,所以我從動漫畫的百合文化出發。乍看之下這好像是截然不同的取徑,但因為我很清晰理解到,台灣的女同志文學已經走到很難超越的高度,所以我才走了另外一條目前還沒有人嘗試的道路。其實這個想法也跟陳雪老師的初衷有點像,我想寫百合是因為我想看,所以就由我來實踐。
另外,陳雪老師所說的「小說元年」,對我來說是非常驚豔的。因為從研究者的角度來看,陳雪老師在文學史的定位,其實在2015年之前就已經很明確且無法撼動了。讓我意外且驚豔的是,陳雪老師開始嘗試的犯罪小說類型,呼應了我們一直在談的「中間文學」:雖然處理嚴肅的命題,但是用相對娛樂的手段來寫,而吸引更多讀者加入閱讀的行列,並且意識到這些議題是當代社會必須去面對的。
要同時兼顧可讀性、想處理的嚴肅命題,以及文學的技術和藝術性,這些要怎麼融合在一起並不容易,但陳雪老師願意去做。我相信接下來台灣的文學創作,會因爲陳雪老師的行為產生重要變化,文學史一定會因此轉向的。

陳國偉:的確,台灣純文學作家跨界寫類型的其實很多,其中科幻就是大宗,但為什麼寫犯罪就會出現「逼——」,這的確是耐人尋味的現象。兩位都提到希望自己的寫作提供不一樣的視角,那麼對於妳們來說,會期待藉由自己現在的寫作,去跟台灣既有的文學創作傳統或環境形成怎樣的對話呢?
陳雪:我自己的話,因為我的作品已經比較多,所以會多得到一點自由吧!既然過去已經很認真的交了那麼多的作業了,到了這個年紀,希望可以寫一些自己很感興趣的,比方說台灣的懸案,或是台灣曾經發生過的重大社會事件。
我想強調的是,小說應該是跟隨著時代而生的。這些脈動應該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呈現?雖然這搞不好也是我的中年議題,就算有兩邊不討好的危險,但我想要跟隨著時代革新。這種改變是需要勇氣的,比方說明天回去,我就要開始研究Excel了(全場大笑),但其實你知道一個作家已經寫了二十幾本書,到了50歲,感覺自己還在學新的東西,是很快樂的。如果我可以做點什麼,也許就是作「中間」的橋樑,可以跟年輕人這樣在一起,我覺得很快樂。
陳國偉:双子做為年輕一代,妳希望自己對現在的文學場域帶來什麼改變?
楊双子:我覺得陳雪老師跟駱以軍老師為首的這個世代,是非常疼愛我們這些晚輩創作者的。如果有所謂文壇的話,我們不必去文壇裡面拜碼頭,我們可以更快去思考台灣跟這個世界的關係,跟台灣這個國家的關係。我們要做的是,用文學來跟世界對話,來思考台灣未來到底要走到哪裡去。
而我的書寫是希望可以提供思辨:到底哪個路線是我們最適合、最想要的那個未來。我真的很感謝前面很多前輩的努力,進行了挑戰跟解放,以致於我們可以更自由地去回應這個世界的問題。●

Tags:
作家陳雪(左)與楊双子
文字整理/郭如梅(北海道大學文學院人文學專攻表現文化論講座博士生)
國立中興大學自2021年起設立「川流台灣文學駐校作家」,首任邀請作家楊双子擔任。4月下旬,同樣曾於2017年在中興大學駐校的作家陳雪應邀,針對如何從性別書寫出發進而結合類型的寫作趨勢與楊双子進行對談,由台文所所長陳國偉擔任主持。
***
本次對談,希望請她們分享自己的創作歷程與轉變。首先想請陳雪談談為何當初進入文壇時會以性別為主題,後來又開始創作《橋上的孩子》這類鄉土定位的作品。
■當她們從自身開始思考性別
陳雪:我開始寫作大概是1990年代解嚴之後,那時大家最關注的,就是政治跟性別。性別的問題對那時候的我也是很切身的問題,因為我比較像是雙性戀,喜歡男生也喜歡女生。在那個時代,你會對這樣的性向感到一些困惑,能閱讀的東西也不多,所以對一個寫作的初學者來說,它就是非常好的領域。也就是說,我想寫還沒有看過的東西,想寫還沒有人寫過的東西,而它剛好也是我關注的。
所以我的第一本書《惡女書》跟自己的故事沒有什麼關係,但我寫得非常大膽,因為對我來說,我的小說就是我跟世界產生衝突的一個方式。可是後來當我寫完《惡魔的女兒》,我忽然覺得我衝撞出來的那個位置,其實也不是屬於我的位置。
2000年我去了一趟美國,在美國放空的那段時期,我想起小時候跟父母在橋上賣東西。這讓我很清楚的意識到,假設我要釐清我自己是誰,必須要回到我的家鄉、我的童年,回到那個可能真的傷害、離散產生的源頭,所以我開始寫了《橋上的孩子》、《陳春天》、《附魔者》這三部曲。
我覺得今天我跟双子的對談會非常有意思,因為我們兩個處理的元素很像,但路徑不太一樣,可以做為很好的對照。
陳國偉:双子自己是研究言情小說出身的,也從事言情小說創作,後來寫《花開時節》把性別跟歷史做連結,這是妳一開始就想寫的東西嗎?為什麼一開始就想這樣處理性別?
楊双子:我9歲就開始想要創作,但當時是想成為漫畫家。直到今天,台灣市面上都還是以少年漫畫為大宗,在這種情況之下,一個9歲的女孩要開始創作,會遇到的很大問題是:自己設計了很多角色,結果回頭來看都是男性角色。
直到國中之後,我才意識到,我根本不知道女生可以進行什麼冒險。那時候甚至做了一個夢,我變成一個既不是男生也不是女生的孩子,醒來真的覺得是場惡夢。可是在那個當下,我突然接受了:好,我今後是個女孩,我要來創作女孩的故事。後來在寫言情小說的經驗中,也逐漸在既有的羅曼史內理解,那樣的女主角並不是我想要當的女孩,所以言情小說寫到後來我也有點後繼無力,才開始轉向其他路線。但自始至終,性別一直都是我很在意的題目。
■從類型通往社會與歷史
陳國偉:双子是出道的時候就很清楚要選擇類型來創作,陳雪則是一直到了2015年才陸續寫了《摩天大樓》、《無父之城》跟《親愛的共犯》。為什麼陳雪會開始想要在小說中結合推理犯罪的類型元素?原來那些性別、創傷或自己的經驗,也會想繼續放進創作裡面嗎?
陳雪:我覺得我的小說有幾個階段。寫完《迷宮中的戀人》時候覺得,我把我自己的病治得差不多了,終於可以成為一個比較完整的人,那下一步我該怎麼出發?
那時我已經在台北住很多年了,台北有很多外地來的人,我想寫這些人在台北這個城市的狀態。有段時間我住在像摩天大樓一樣的住商混合大樓,我認為摩天大樓是台北城市非常適合的隱喻。我一直很想寫謀殺案,所以開始動筆寫《摩天大樓》的時候,我把犯罪題材放進去。但起初很尷尬跟猶豫,因為台灣的純文學作家其實已經有很標準的路線,你知道什麼東西可以寫,什麼東西寫了就會「逼——」這樣……(全場大笑)
我覺得小說家還是要忠於內心的呼喚,現在的我會想要處理社會上的問題,而我的內在肯定有一些呼應。這是我年輕時的文學養成,像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影響,我想要追問罪與罰、善與惡,人到底是什麼,人性的試探這些問題。這些是從年輕時代就種在我心裡的,只是現在我採取了更戲劇性的結合來創作。
陳國偉:正如剛剛陳雪提到的,研究者都會注意到《惡女書》的罪與罰,王德威老師在《摩天大樓》的序中,也從這個脈絡連結下來。當然大家其實可以用不一樣的角度來看這些作品,因為世界文學中其實有很多用類型來寫純文學的大師,像是波赫士、卡爾維諾、瑪格麗特.愛特伍、石黑一雄、奧罕.帕慕克等等。
双子做為不一樣脈絡出身的寫作世代,一開始就跟類型密切相關,而且顯然很有意識要打破類型。妳自己當時是怎麼有意識要進行這樣的結合?
楊双子:其實我預設的目標讀者幾乎沒有讀我的小說,有幾個可能的理由,其中最關鍵的應該是:百合迷群在追求的,跟我寫出來的東西不一樣。我知道怎麼做會更符合百合迷群的需求,可是,我覺得那不是我要做的事情。
以前寫言情小說時,我後面有兩部作品是接連被退稿的,主要原因是我嘗試觸及的議題太接近現實社會,而不只是停留在以愛情為主軸的故事。像我第4本言情小說的男女主角就涉及到貧窮的背景,言情小說很少處理貧窮,當時編輯還打電話來說,有一個段落要不要乾脆拿掉,因為她覺得好慘喔。所以很明顯的,我想寫的內容就不適合繼續留在言情小說的世界裡。
陳國偉:既然殖民政權是愛不能跨越的,那麼百合關係如果要終成眷屬,是不是離開了那個歷史階段就有可能?而且即便如此,為什麼妳還是會特別想要結合歷史來書寫?
楊双子:我們家族在成功嶺山腳下生活了至少兩百年,明明已經在這裡生活那麼久了,可是我小時候因為在眷村長大,就以為自己是外省人,而且有很強的中國認同。我們姊妹18歲時還存錢去中國旅遊,但那也是幻滅的開始。2008年野草莓學運,當時為了要準備考台文所,我讀了很多戰前作家的作品,才更清楚意識到,原來我們根本有著截然不同的土地經驗。剛好這個階段,言情小說我也寫不下去了,所以開始萌生這樣的念頭:我應該來寫這塊土地的事情。創作對我來說,最終還是回歸到我生命裡面在意的事情,而國族認同是很重要的一塊。
■附身 vs Excel表的寫作方法論
陳國偉:身為讀者,我們十分好奇兩位是以怎樣的寫作方式進行的。陳雪剛剛提到有自己的寫作方式,要不要談談那是怎樣的狀態?
陳雪:其實我建議你們最好不要學我,因為我的方法可能只適合我自己。
以前寫純文學時,基本上有了一個畫面就開始啟動了。但我很重視小說結構,例如寫《附魔者》,它就是多人輪唱、多聲部的轉換;到了《摩天大樓》,我想用場所來界定空間,再讓故事長出來;再到了《無父之城》,我就是想要安排警探這樣的角色,所以小說開場就出現的私家偵探,本來是個刑警。我讓小說從一個人物開始,然後接續不同的人物出來敘述。我沒有預先寫大綱,就是用很直覺的方法把小說串接起來。
我正在寫的作品是關於連續殺人魔,但起心動念其實很簡單,我只是想要寫一個人,他的父親是個兇手,後來就變成連續殺人。但寫到後來,我壓力大到都落髮了。為什麼壓力那麼大?因為我沒有先預設結局,所以寫到後面一直沒辦法破案!(全場大笑)
當然我最後還是破案了,因為《摩天大樓》之前有改編成電視劇,所以認識了一些影視公司的人,他們很喜歡我的作品,就一直跟我說:陳雪老師妳不要怕,妳的這種推理方式,叫作「情感推理」!(全場大笑)
我這種寫法就像附身一樣,每天都要附身一個角色才有辦法寫,因為我就是用情感推理。有一天我剛好附身寫到最後重要的場景時,我就跟伴侶阿早(早餐人)意外起了很大的衝突,因為我正好在兇手的心理狀態。後來我跟她說:那個不是我,是小說裡面那個誰,但我又說不清,因為她還沒看小說。我就想,哎呀這個傷害、這種副作用實在很大耶!所以我認識双子之後,每次她跟我講她怎麼擬大綱寫小說,我都好崇拜她。
楊双子:救命啊(笑)
陳雪:我每天都在那個情感泥淖裡面自己盤旋,害得阿早一直很害怕。她以前只是我的改稿者,現在還變成受害者,所以等成品出來後讓你們看看,是不是需要進入楊双子整治時間。
楊双子:不敢啊,救命啊(笑)。我們這樣好像是在討論演技的方法論之類的議題,其實大家的作法真的都很不相同。像我跟作家瀟湘神都是寫類型小說出身的,基本上還是要有大綱,才能知道最後故事要走到哪裡。我自己會有3個大綱:第一個會很簡單,通常開頭結尾都很明確。至於如何從開頭走到結尾的中間部分,我會切成4份,就是起承轉合。這是來自寫言情小說的經驗,通常每一章大概只有5000字,為了要符合它的故事框架,合理分配情節,所以必須要有大綱。
除了章節大綱外,我還會有一個人物設計表,把小說裡面出場的主角和主要配角全部列出來。在寫《花開時節》的時候,他們家族從17世紀開始的祖先我都想好了:如何從漳州來到台灣,叫什麼名字,生了幾個兒子,我全部都會先寫下來。所以會有一個很龐大的人物表,甚至我有做一個Excel表……
陳雪:Excel表!?(全場笑)
我覺得這很關鍵,不只對應我們對星座的認知,還牽涉到角色出生的那年,可能剛好有一場流行病,那就可以清楚對應。像《花開時節》中惠風哥哥其實還有個弟弟,但因為流行性感冒死去了,雖然這個小說裡完全沒有寫到——所以這也是我第一次提到他們家還有另外一個男孩。(全場笑)
透過那個Excel表,包括《花開時節》故事結束之後,到戰後整個家族的所有事情都已經列明,只是沒有寫出來而已。所以後來在談改編時,我被問到惠風哥哥後來怎麼了?……這裡讓我爆個雷:其實戰後他突然理解到,他有必須承擔的責任,因為他是這個地方的頭人,必須出來為大家爭取,所以就在白色恐怖當中死去了。對,雖然在《花開時節》中完全沒有寫到,但其實他的故事早已有了清楚的結局。
■重新丈量文學史的尺度
陳國偉:從兩位剛剛對寫作形式的說明,大家見證到兩種完全不同型態的創作者,也可以感受到與各自原有寫作的脈絡跟特色,有很明確的關係。我知道兩位也有相當程度的私交,很好奇兩位怎麼看彼此最近書寫的類型和狀態?
陳雪:我認識双子就是我在中興大學擔任駐校作家的時候,她送了我一本《花開時節》。當時我沒想過這是歷史百合或什麼類型,但老實說我還滿震驚的,因為那時候我就覺得她的作品非常獨特。双子所使用的小說語言真的超厲害,她可以把漢語、日語、台語融合成一種書面語,自成一種聲調,她的強項是她已經可以把那個時代的聲音展現出來。
楊双子:謝謝陳雪老師,好害羞,真的非常感謝。我自己寫百合小說,但它跟女同志小說是不一樣的。然而我可以做出不一樣,就是因為前面有人開了女同志文學的先河。這件事情毫無疑問,只要跟我同年齡的寫作者,只要我們是女同志的話,不可能不受到陳雪老師的影響。
當我看到《惡女書》、《蝴蝶的記號》這樣的作品時,我開始思考,該如何呈現只有我們這個世代才能呈現的東西?我不可能再選擇去回應女同志文學,因為太難了,陳雪老師已經樹立了典範,所以我從動漫畫的百合文化出發。乍看之下這好像是截然不同的取徑,但因為我很清晰理解到,台灣的女同志文學已經走到很難超越的高度,所以我才走了另外一條目前還沒有人嘗試的道路。其實這個想法也跟陳雪老師的初衷有點像,我想寫百合是因為我想看,所以就由我來實踐。
另外,陳雪老師所說的「小說元年」,對我來說是非常驚豔的。因為從研究者的角度來看,陳雪老師在文學史的定位,其實在2015年之前就已經很明確且無法撼動了。讓我意外且驚豔的是,陳雪老師開始嘗試的犯罪小說類型,呼應了我們一直在談的「中間文學」:雖然處理嚴肅的命題,但是用相對娛樂的手段來寫,而吸引更多讀者加入閱讀的行列,並且意識到這些議題是當代社會必須去面對的。
要同時兼顧可讀性、想處理的嚴肅命題,以及文學的技術和藝術性,這些要怎麼融合在一起並不容易,但陳雪老師願意去做。我相信接下來台灣的文學創作,會因爲陳雪老師的行為產生重要變化,文學史一定會因此轉向的。
陳國偉:的確,台灣純文學作家跨界寫類型的其實很多,其中科幻就是大宗,但為什麼寫犯罪就會出現「逼——」,這的確是耐人尋味的現象。兩位都提到希望自己的寫作提供不一樣的視角,那麼對於妳們來說,會期待藉由自己現在的寫作,去跟台灣既有的文學創作傳統或環境形成怎樣的對話呢?
陳雪:我自己的話,因為我的作品已經比較多,所以會多得到一點自由吧!既然過去已經很認真的交了那麼多的作業了,到了這個年紀,希望可以寫一些自己很感興趣的,比方說台灣的懸案,或是台灣曾經發生過的重大社會事件。
我想強調的是,小說應該是跟隨著時代而生的。這些脈動應該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呈現?雖然這搞不好也是我的中年議題,就算有兩邊不討好的危險,但我想要跟隨著時代革新。這種改變是需要勇氣的,比方說明天回去,我就要開始研究Excel了(全場大笑),但其實你知道一個作家已經寫了二十幾本書,到了50歲,感覺自己還在學新的東西,是很快樂的。如果我可以做點什麼,也許就是作「中間」的橋樑,可以跟年輕人這樣在一起,我覺得很快樂。
陳國偉:双子做為年輕一代,妳希望自己對現在的文學場域帶來什麼改變?
楊双子:我覺得陳雪老師跟駱以軍老師為首的這個世代,是非常疼愛我們這些晚輩創作者的。如果有所謂文壇的話,我們不必去文壇裡面拜碼頭,我們可以更快去思考台灣跟這個世界的關係,跟台灣這個國家的關係。我們要做的是,用文學來跟世界對話,來思考台灣未來到底要走到哪裡去。
而我的書寫是希望可以提供思辨:到底哪個路線是我們最適合、最想要的那個未來。我真的很感謝前面很多前輩的努力,進行了挑戰跟解放,以致於我們可以更自由地去回應這個世界的問題。●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
閱讀通信 vol.369》出烤箱的好日子
延伸閱讀
人物》創造作者的小說?如何穿越,怎樣再現?專訪《臺灣漫遊錄》作者楊双子
閱讀更多
專訪》對亡國感與歷史真相缺席的凝視:訪駱以軍《明朝》與陳雪《無父之城》
閱讀更多
書評》「穿越」是為了愛與改變:評楊双子《花開時節》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