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星或喜歡一位公眾人物……這件事情給予的精神與力量,讓我們擁有繼續生活的動力,我很喜歡這樣的力量。
在韓國導演吳洗娟的紀錄片《成粉》與新書《那一天,我追的歐巴成為了罪犯》台灣分享會上,一位自言是第一代韓流粉絲的讀者,與同為追星族的吳洗娟分享這段話,引起全場讀者的熱淚。
這是筆者參加過最多人流淚、與會讀者最踴躍分享瘡疤的新書分享會。情緒跨越了語言的隔閡,說明因為追星而受傷的經驗,有著跨國性與普遍性。
2019年「鄭俊英群聊事件 」爆發,吳洗娟追隨多年的偶像一夕成為罪犯,「群組中與朋友的那些對話實在令人難以啟齒。那些厭女、侮蔑女性的行為所燃起的怒火,將我們共同的美好回憶都燒成了灰燼。」
吳洗娟相信不是只有她一人面臨這樣的心碎,於是她啟動紀錄片拍攝計畫:尋找同好,邀請同被偶像背叛的粉絲說出自己的心聲。
➤如何建立健康的偶像文化,粉絲觀點應該被加入 在韓國,甚至多數東亞社會,追星族有時會被視為無知的一群人。偶像犯罪了,粉絲更蒙上難以洗脫的羞恥。
「K-pop產業中所有媒體的鎂光燈都聚焦在明星跟大公司上,但粉絲的心聲卻鮮為人知。」吳洗娟在接受Openbook的專訪時如此說明,這也是她出書的初衷。
韓國偶像文化產業鏈在全球都獲得巨大成功,更是許多國家仿效的對象。然而,外表光鮮亮麗、流量與金錢兼收的偶像文化,卻衍生出許多社會問題,特別是粉絲的身心問題。「我個人認為大家應該一起努力,營造更健全的偶像粉絲文化。」
如何營造健全的偶像文化?如何讓粉絲保持平穩的生活日常?這是吳洗娟對K-pop產業的重要提問。
VIDEO
➤追星或許美好,但也如同沒有安全裝置的雲霄飛車 吳洗娟在書中分享自己的經歷,偶像無疑是她青春期以來自我形塑的重要環節。她與母親約定考全校第一名,就可以去看演唱會, 她做到了,所以15歲時,她一個人搭高鐵從釜山到首爾,20歲時考上首爾的大學,這些動力全都來自追星。
「長大成人後回頭看這段經歷,粉絲團體就像小社會,因為和同好交流,那時的我學會了待人接物。」吳洗娟回憶:「追星過程中,苦悶的生活好像得到了慰藉與紓壓。」
分享會裡也有讀者提到相似的經歷:「追星為我帶來極大的情緒價值,讓我找到理想中的自己。為了偶像努力學習另外一種語言、克服困難,一個人飛去國外看他。我很喜歡努力的自己。」讀者也認為,如果偶像行為破壞了這些準則,沒辦法繼續愛下去是很痛苦的。
「這該死的雲霄飛車竟然不是我想下車就能下的,甚至連最低限度的安全裝置都沒有,讓我直接摔了下去。」吳洗娟在書中如此比喻。
吳洗娟(左)於紀錄片《成粉》與新書《那一天,我追的歐巴成為了罪犯》台灣分享會
➤人設崩壞:喜歡上的究竟是流行文化工業的產品,還是真正的人? 粉絲一方面很清楚偶像是由龐大產業鏈打造出的一種商品,但另一方面,追星又真真實實地承載了一些美好的想望。2023年世新大學紀旻均的碩士論文《解構烏托邦:韓國偶像經營與粉絲追星的數位民俗誌紀錄》描繪了K-pop的烏托邦如何建構。
首先,透過練習生制度,可以拉長粉絲的關注時間,進而培養期待感與成長見證,加強信任與忠誠度。其次,對偶像的形象塑造與道德要求,包括善良的正面形象,可引起共鳴。也藉由偶像的影響力,在公益推廣中達成社會責任與形象的雙重獲益。再來,運用上節目或自製綜藝強調團魂,讓粉絲感受團體成員之間共同追求目標與夢想的信念,同時透過整齊劃一的舞蹈和練習過程紀錄,表現出成員之間的相互支持與幫助,以此累積共同經歷與回憶,引起粉絲對團體的認同與感動。
新書發表會上,讀者向吳洗娟請教,自己喜歡的可能只是韓國流行文化與造型工業包裝下的光鮮商品,「會不會我們喜歡這些人時,喜歡的是一個假的東西?如果我們追求的是真實的感受,應該如何分辨?」
吳洗娟分享,其實她自己常被朋友挖苦「很容易喜歡上眼神猥褻的人」,引起全場哄堂大笑。她也非常同意,經紀公司有很多方式去包裝明星的人設,粉絲能看到的只是明星最光鮮亮麗的一部份,「分辨是非常困難的」。
接受Openbook專訪時,吳洗娟分享了更多她的看法。她認為,明星的公開形象跟私人生活會有巨大落差,除了因為公司的包裝,很多時候也是因為粉絲尋找偶像的蛛絲馬跡,自行認定或想像而產生的結果。其實不僅偶像,多數人的公開與私人生活,本身就差異很大,「即使是公司相處10年的同事,你也很難知道他回家之後的模樣。」
但這種落差之間確實存在許多結構性的引導。比如當一位練習生已累積了多年的練習,粉絲會有惻隱之心想支持他;但若是偶像只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就出道,則可以包裝成「天才」,讓粉絲相信他的天份。也就是說,在偶像出道之前,他們的私人生活已經充滿了窺視與來自外界的想像,而私人生活是粉絲很難拒絕的蜜糖,這是K-pop典型的行銷手段。
當偶像的公開工作與私人生活難以切分時,人設的真實與虛假,自然也難以辨別。
「粉絲看到的偶像,是由公司所提供,最光鮮亮麗的部分。這是追星時,一定要給自己設定的心理防線。」吳洗娟提醒。
➤購買過熱,增加年輕粉絲的不理智消費與經濟負擔 若同意韓國看似光鮮亮麗的流行偶像工業,對粉絲身心不一定健康與正向,吳洗娟認為,這並非單方面的問題,而是明星、公司和粉絲三角關係都出現問題。而其中經紀公司如何行銷與經營藝人,是偶像文化體質是否健康的關鍵環節。
「現在韓國追星文化最大的問題是『購買過熱』。」吳洗娟透露她最近聽到的訊息:如果是頂尖的明星,粉絲可能要先消費100萬至200萬韓元(約新台幣2萬4000到4萬8000元),才有可能得到簽名會的入場保障。
這便是目前極具爭議的「小卡」文化。小卡是韓國偶像專輯或周邊商品中的附贈卡片,通常印有偶像的肖像,以隨機形式附贈於專輯中。同一專輯可能包含不同成員的照片,以鼓勵粉絲購買多份專輯,收集完整套卡,具有收藏價值。這是經紀公司增加營收的重要手段。
很多人買了CD根本不聽,只把小卡抽走,其他都送到育幼院。也有知名偶像團體的專輯,在小卡被抽走後,CD被遺棄街頭,宛如垃圾。「近期已經出現『我們根本不需要這種垃圾』的聲音,不但浪費資源,也會造成環境汙染。」吳洗娟說明,雖然有公司推出「可溶解在水中的CD」,聽起來很環保,實際上,只要不製造就可以了。
K-pop能形成強勢且獨特的流行浪潮,其中偶像明星自我揭露隱私所創造的獨特親密感,是凝聚粉絲相當重要的方式與文化。雖然許多韓國藝人因此深受私生飯 騷擾之苦,然而撇除極端現象與個人行為,將藝人的隱私公開化,一直是韓國經紀公司的宣傳手法,比如Bubble泡泡 與直播 文化。
經紀公司為追求利益而推動的過度消費,除了鋪張浪費,也可能造成青少年或經濟能力有限的粉絲巨大的經濟負擔和不理智消費行為,比如購買過多CD、訂閱偶像的泡泡。此外,粉絲之間也容易形成競爭或嫉妒,甚至是心理壓力,造成憂鬱與沮喪。
➤維特效應:偶像的輕生,也會造成粉絲的憂鬱或自殺 與會讀者也分享自己的糾結:「我追星追了很久,原本想說,追星就是我快樂就好。後來發現,其實我的偶像不快樂,所以我好像也沒有很快樂。後來,偶像走了…… 最近,另一個偶像犯罪了,應該被抓去關了…… 我也不忍看那些新聞。現在我的想法是,他有在呼吸就好了,只要他活著,沒有走掉,活著就好了。」
本報導雖然主要聚焦於男性偶像性犯罪與女性粉絲的心路歷程,然而,若將視野關注於偶像與(青少年)粉絲的依賴關係,已有許多報導指出,偶像明星的自殺與社會整體的自殺率,有明顯的正相關。
韓國藝人金鐘鉉、雪莉和具荷拉的自殺事件後,皆引發了顯著上升的自殺率;而日本藝人竹內結子和三浦春馬的自殺事件,也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和憂慮,自殺率在青少年和年輕成年人中有所上升。尤其在媒體大量報導後,模仿自殺的風險增加,這樣的現象被廣泛稱為「維特效應」,也成為追星現象的意外風險。
左起韓國藝人金鐘鉉、雪莉和具荷拉、日本明星三浦春馬和竹內結子(wiki)
➤女性粉絲的角色衝突:助浪者、包庇者、被歧視者,也可能是性犯罪的被害者 鄭俊英群聊事件中,他偷拍與下手的對象正是他的女性粉絲。而前BIGBANG成員勝利的「Burning Sun事件 」中,涉案夜店同樣利用偶像名氣吸引大批粉絲,對年輕女性進行迷姦。這些事件皆顯露出男性偶像利用他們與女性粉絲之間高度的權力不對等,進行性犯罪。這也是韓國偶像工業中極度黑暗的一面。
在書中,吳洗娟除了作為粉絲,她對自己女性的性別身分相當有意識:
我相當不齒厭女犯罪,而且對公眾人物的負面事件反應很敏感,從來沒想過自己喜歡的藝人會成為性犯罪者……除了讓我感受到莫大的背叛,也讓我對曾支持過他的事實感到自責。因為曾經喜歡過,所以更生氣、更羞愧、更迷茫……
《成粉》中所有受訪的粉絲都是女性,也反映了吳洗娟希望為女性發聲的立場。K-pop男偶像與女粉絲的結構位置中,女性是幫助男偶像成名的助浪者、維護者,在偶像出事之後,她們可能被旁人歧視為某種程度的性犯罪協助者。而最令人心驚的案例是:女性粉絲成為性犯罪(潛在)的被害者,一切皆因為她們曾經信任了某位偶像。
吳洗娟的母親(左)分享:「如果一個人真的受傷時,不會說出自己真的受傷了,只會把這些痛苦埋在心中。 當她真的可以說出來時,其實已經走出來了。看到女兒完成紀錄片、寫完書之後,我有種安心的感覺。女兒走出傷痛了,也變得成熟了。像是完成一件什麼事,我為她感到驕傲。」
在《那一天,我追的歐巴成為了罪犯》中,吳洗娟採訪了2016年首位揭發鄭俊英犯罪事實的記者朴孝實,這是書中相當值得省思的段落。當時的吳洗娟與社會大眾普遍誤以為朴孝實是無端指控,對她相當反感,吳洗娟曾在自己的日記中寫下對朴孝實的不滿。直到黑暗的事實被揭露,她才意識到自己當初的錯誤。
後來拍攝紀錄片時,她將朴孝實列為受訪者,並真誠地向她道歉。新書發表會時,吳洗娟難過地分享,紀錄片採訪時,她得知朴孝實在那幾年由於報導此案,不停遭受批評,因為精神壓力過大,數次流產,導致終生不孕,令人惋惜。
基於隱私的關係,吳洗娟並未在書中與紀錄片揭露此事,儘管這能使她的紀錄片與書籍更具衝擊力。隨著今年5月BBC紀錄片《揭露韓流明星聊天室裡的祕密》同樣採訪了朴孝實,並公開此事,吳洗娟才於新書發表會時分享。
她進一步說明:「其實留言攻擊朴孝實的人,並不完全是粉絲,而是極右的厭女團體,時間持續了非常久。」雖然吳洗娟僅在日記中寫下批評,照理說並無需公開向朴孝實道歉,但作為粉絲也作為女性,吳洗娟仍感受到自己的愧疚。
從性犯罪、網路霸凌到媒體與社會環境,這些現象顯示了對男偶像犯罪的輕拿輕放,而女性粉絲與新聞業者卻無論身體或心靈,都滿是傷痕。
VIDEO
➤追星,也是友情的美好旅程 「你想要多少快樂,就得承擔多少風險。」吳洗娟道出「追星」本質上存在著兩面性。然而,有些風險已然超過了個人能承受的範圍,如本文所述及的性犯罪、女性粉絲的角色衝突與維特效應等等。
《那一天,我追的歐巴成為了罪犯》,韓國原書名「《成粉》日記」,是吳洗娟紀錄片拍攝過程的日記隨筆。如果想研究韓國偶像工業的結構問題,這本書並非上佳之選,但若想理解K-pop粉絲的心聲,這本書是罕見的血淚集。
細讀本書,吳洗娟仍肯定追星的正面意義,書中透過因鄭俊英事件受傷甚深的記者朴孝實的分享,道出追星的正面觀點:「如果可以從藝人身上得到正面影響也不錯。但明星也是人,都不是完美的嘛,我認為要求明星當個完人就太苛刻了…… 人生苦短,喜歡一個人怎麼會是壞事呢,當然是好事。」
紀錄片上映後,吳洗娟收到最令她印象深刻的觀眾回饋是:「這是一部關於友情的紀錄片」。她很認同,因為過去曾經一起喜歡鄭俊英的粉絲,都是有著共同興趣或喜好的人,彼此可以很自然地相處,甚至不需要過多的說明,就能心領神會。吳洗娟分享:「回憶追星這段時間,並不是見到(偶像)這個人的瞬間印象最深刻,而是一起排隊,跟其他人成為朋友。這些回憶也是非常美好的部分。」
「拍攝這部紀錄片,拜訪每位受訪者的過程,每個人都像一個車站,我開著一輛車靠上去,聊了一下天,車又開走了。兩個人都會得到一些什麼,或許平撫了一些內心的憤怒。」紀錄片的拍攝與出書,對吳洗娟而言,也是一趟療癒的歷程。
➤什麼是「成功的粉絲」?不是偶像認識你,而是從追星裡得到成長 紀錄片名稱是「成粉」,無論書籍或影片,想討論的也是粉絲圈內部的提問:「什麼是成功的粉絲?」讓偶像認識你?收集完整小卡?或者成功參加簽名會?健康的偶像文化,應該是偶像能從粉絲處得到支持,而粉絲則能在追星的過程中獲得價值,雙方都藉此得到力量。
比如,曾有位偶像的作品涉及性別用詞不當,經過粉絲提醒後,從此創作上避免了這類疏漏。又比如,偶像推薦自己喜歡的書籍,粉絲也熱情地找書來閱讀,既刺激了出版市場,雙方身心亦都能成長。這些都是互惠的案例。
從反轉過去「成功粉絲」的定義,吳洗娟希望營造對粉絲更健康的偶像文化。書中的一段話,具體道出了本書的宗旨:
小時候覺得能被喜歡的藝人認出來才算是成功的粉絲,但我現在不這樣想了。我認為能透過藝人,使自己的人生更加成長,那才是真正成功的粉絲。而且就算距離很遠,仍能真心為那個人的人生加油,我覺得這才是健康的追星方式。追星這件事本身就是走入、深入一個人的人生,再將此轉化為自己的人生,就像一種憧憬。但還是要隨時牢記,這個人跟我們一樣都是平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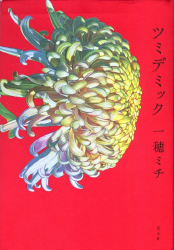 直木獎得主一穗最初以BL小說發跡,著有《愛情可以分割嗎?》、《
直木獎得主一穗最初以BL小說發跡,著有《愛情可以分割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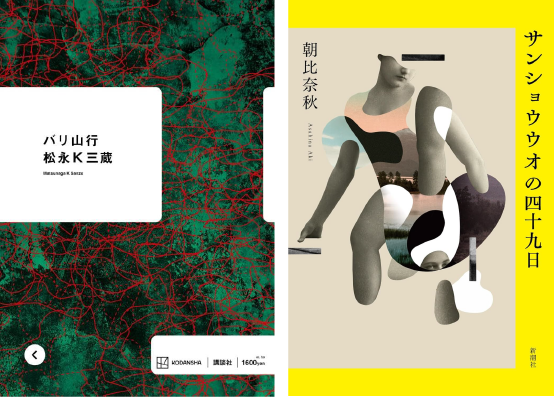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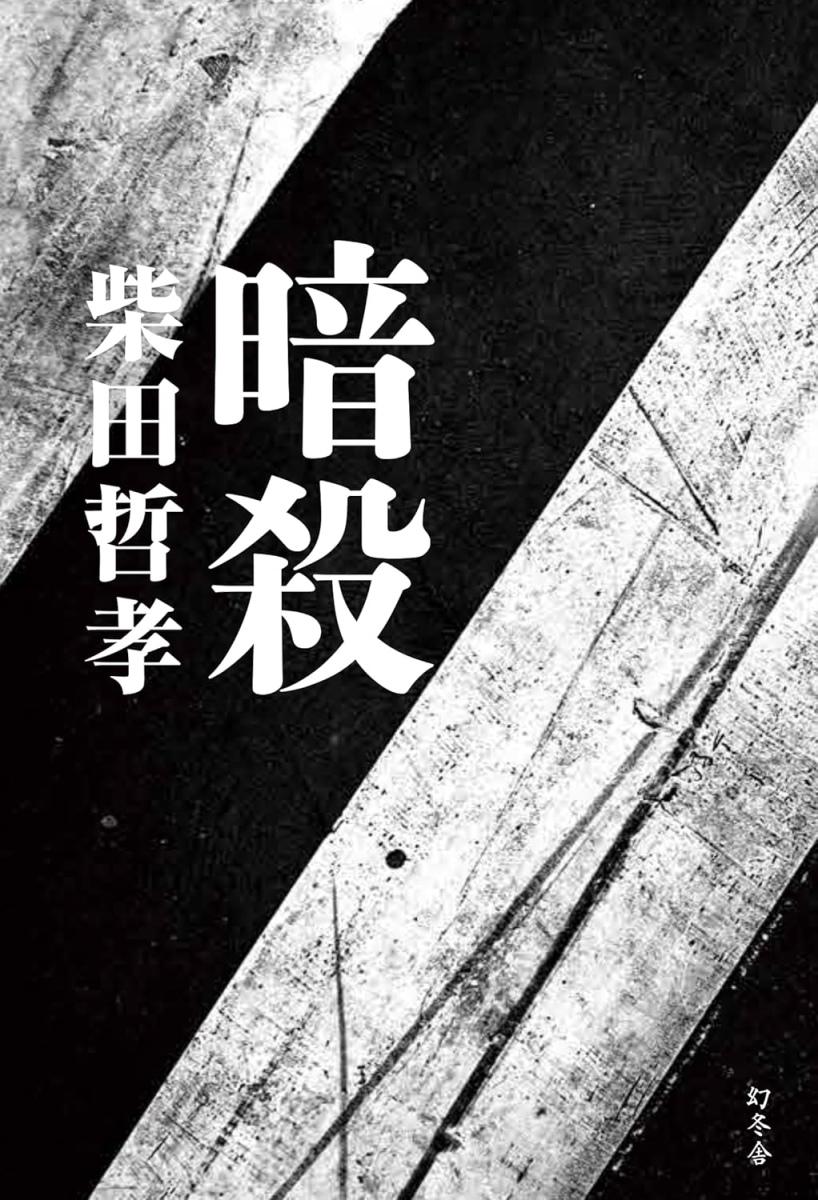 ■2006年以《下山事件:最後的證言》成為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及日本冒險小説協會大獎雙冠王的柴田哲孝,上個月推出新作《暗殺》(幻冬舍),講述日本首相槍擊事件,書籍發行前便引發熱烈討論。
■2006年以《下山事件:最後的證言》成為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及日本冒險小説協會大獎雙冠王的柴田哲孝,上個月推出新作《暗殺》(幻冬舍),講述日本首相槍擊事件,書籍發行前便引發熱烈討論。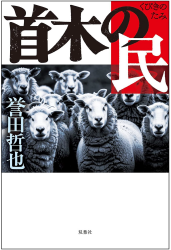 ■著有《妖之華》、《野獸之城》、《草莓之夜》的暢銷推理作家譽田哲也,於上個月中推出全新社會派警探小說:《首木之民》(双葉社)。
■著有《妖之華》、《野獸之城》、《草莓之夜》的暢銷推理作家譽田哲也,於上個月中推出全新社會派警探小說:《首木之民》(双葉社)。 ■《罪的留白》、《神樂坂怪談》、《夜的路標》作者蘆澤央,思索「若有一個冥婚配對軟體會怎樣?」,架構全新科幻懸疑小說集《魂婚殉情》(早川書房)。
■《罪的留白》、《神樂坂怪談》、《夜的路標》作者蘆澤央,思索「若有一個冥婚配對軟體會怎樣?」,架構全新科幻懸疑小說集《魂婚殉情》(早川書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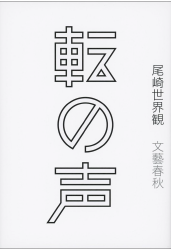 ■身兼歌手與作家雙重身分的尾崎世界觀,於本月中推出新作《轉之聲》(文藝春秋),從自身在音樂圈的經歷,探索文學領域的巔峰。
■身兼歌手與作家雙重身分的尾崎世界觀,於本月中推出新作《轉之聲》(文藝春秋),從自身在音樂圈的經歷,探索文學領域的巔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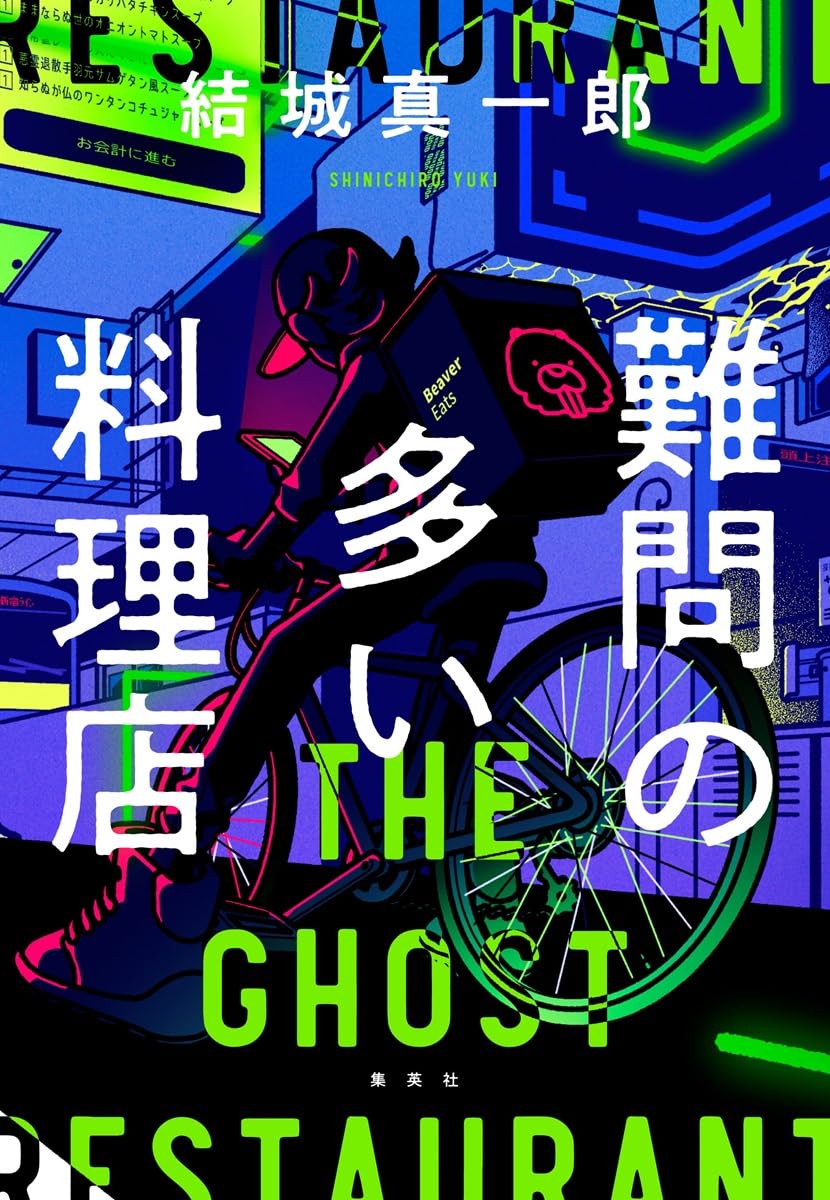 ■兩年前以話題作《#我要說出真相》炙手可熱的推理界新星結城真一郎,於今年6月底再推新作《諸多難題料理店》(集英社)。
■兩年前以話題作《#我要說出真相》炙手可熱的推理界新星結城真一郎,於今年6月底再推新作《諸多難題料理店》(集英社)。
專訪》性犯罪、人設崩壞、購買過熱,K-pop追星血淚:吳洗娟《那一天,我追的歐巴成為了罪犯》
在韓國導演吳洗娟的紀錄片《成粉》與新書《那一天,我追的歐巴成為了罪犯》台灣分享會上,一位自言是第一代韓流粉絲的讀者,與同為追星族的吳洗娟分享這段話,引起全場讀者的熱淚。
這是筆者參加過最多人流淚、與會讀者最踴躍分享瘡疤的新書分享會。情緒跨越了語言的隔閡,說明因為追星而受傷的經驗,有著跨國性與普遍性。
2019年「鄭俊英群聊事件」爆發,吳洗娟追隨多年的偶像一夕成為罪犯,「群組中與朋友的那些對話實在令人難以啟齒。那些厭女、侮蔑女性的行為所燃起的怒火,將我們共同的美好回憶都燒成了灰燼。」
吳洗娟相信不是只有她一人面臨這樣的心碎,於是她啟動紀錄片拍攝計畫:尋找同好,邀請同被偶像背叛的粉絲說出自己的心聲。
➤如何建立健康的偶像文化,粉絲觀點應該被加入
在韓國,甚至多數東亞社會,追星族有時會被視為無知的一群人。偶像犯罪了,粉絲更蒙上難以洗脫的羞恥。
「K-pop產業中所有媒體的鎂光燈都聚焦在明星跟大公司上,但粉絲的心聲卻鮮為人知。」吳洗娟在接受Openbook的專訪時如此說明,這也是她出書的初衷。
韓國偶像文化產業鏈在全球都獲得巨大成功,更是許多國家仿效的對象。然而,外表光鮮亮麗、流量與金錢兼收的偶像文化,卻衍生出許多社會問題,特別是粉絲的身心問題。「我個人認為大家應該一起努力,營造更健全的偶像粉絲文化。」
如何營造健全的偶像文化?如何讓粉絲保持平穩的生活日常?這是吳洗娟對K-pop產業的重要提問。
➤追星或許美好,但也如同沒有安全裝置的雲霄飛車
吳洗娟在書中分享自己的經歷,偶像無疑是她青春期以來自我形塑的重要環節。她與母親約定考全校第一名,就可以去看演唱會, 她做到了,所以15歲時,她一個人搭高鐵從釜山到首爾,20歲時考上首爾的大學,這些動力全都來自追星。
「長大成人後回頭看這段經歷,粉絲團體就像小社會,因為和同好交流,那時的我學會了待人接物。」吳洗娟回憶:「追星過程中,苦悶的生活好像得到了慰藉與紓壓。」
分享會裡也有讀者提到相似的經歷:「追星為我帶來極大的情緒價值,讓我找到理想中的自己。為了偶像努力學習另外一種語言、克服困難,一個人飛去國外看他。我很喜歡努力的自己。」讀者也認為,如果偶像行為破壞了這些準則,沒辦法繼續愛下去是很痛苦的。
「這該死的雲霄飛車竟然不是我想下車就能下的,甚至連最低限度的安全裝置都沒有,讓我直接摔了下去。」吳洗娟在書中如此比喻。
➤人設崩壞:喜歡上的究竟是流行文化工業的產品,還是真正的人?
粉絲一方面很清楚偶像是由龐大產業鏈打造出的一種商品,但另一方面,追星又真真實實地承載了一些美好的想望。2023年世新大學紀旻均的碩士論文《解構烏托邦:韓國偶像經營與粉絲追星的數位民俗誌紀錄》描繪了K-pop的烏托邦如何建構。
首先,透過練習生制度,可以拉長粉絲的關注時間,進而培養期待感與成長見證,加強信任與忠誠度。其次,對偶像的形象塑造與道德要求,包括善良的正面形象,可引起共鳴。也藉由偶像的影響力,在公益推廣中達成社會責任與形象的雙重獲益。再來,運用上節目或自製綜藝強調團魂,讓粉絲感受團體成員之間共同追求目標與夢想的信念,同時透過整齊劃一的舞蹈和練習過程紀錄,表現出成員之間的相互支持與幫助,以此累積共同經歷與回憶,引起粉絲對團體的認同與感動。
新書發表會上,讀者向吳洗娟請教,自己喜歡的可能只是韓國流行文化與造型工業包裝下的光鮮商品,「會不會我們喜歡這些人時,喜歡的是一個假的東西?如果我們追求的是真實的感受,應該如何分辨?」
吳洗娟分享,其實她自己常被朋友挖苦「很容易喜歡上眼神猥褻的人」,引起全場哄堂大笑。她也非常同意,經紀公司有很多方式去包裝明星的人設,粉絲能看到的只是明星最光鮮亮麗的一部份,「分辨是非常困難的」。
接受Openbook專訪時,吳洗娟分享了更多她的看法。她認為,明星的公開形象跟私人生活會有巨大落差,除了因為公司的包裝,很多時候也是因為粉絲尋找偶像的蛛絲馬跡,自行認定或想像而產生的結果。其實不僅偶像,多數人的公開與私人生活,本身就差異很大,「即使是公司相處10年的同事,你也很難知道他回家之後的模樣。」
但這種落差之間確實存在許多結構性的引導。比如當一位練習生已累積了多年的練習,粉絲會有惻隱之心想支持他;但若是偶像只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就出道,則可以包裝成「天才」,讓粉絲相信他的天份。也就是說,在偶像出道之前,他們的私人生活已經充滿了窺視與來自外界的想像,而私人生活是粉絲很難拒絕的蜜糖,這是K-pop典型的行銷手段。
當偶像的公開工作與私人生活難以切分時,人設的真實與虛假,自然也難以辨別。
「粉絲看到的偶像,是由公司所提供,最光鮮亮麗的部分。這是追星時,一定要給自己設定的心理防線。」吳洗娟提醒。
➤購買過熱,增加年輕粉絲的不理智消費與經濟負擔
若同意韓國看似光鮮亮麗的流行偶像工業,對粉絲身心不一定健康與正向,吳洗娟認為,這並非單方面的問題,而是明星、公司和粉絲三角關係都出現問題。而其中經紀公司如何行銷與經營藝人,是偶像文化體質是否健康的關鍵環節。
「現在韓國追星文化最大的問題是『購買過熱』。」吳洗娟透露她最近聽到的訊息:如果是頂尖的明星,粉絲可能要先消費100萬至200萬韓元(約新台幣2萬4000到4萬8000元),才有可能得到簽名會的入場保障。
這便是目前極具爭議的「小卡」文化。小卡是韓國偶像專輯或周邊商品中的附贈卡片,通常印有偶像的肖像,以隨機形式附贈於專輯中。同一專輯可能包含不同成員的照片,以鼓勵粉絲購買多份專輯,收集完整套卡,具有收藏價值。這是經紀公司增加營收的重要手段。
很多人買了CD根本不聽,只把小卡抽走,其他都送到育幼院。也有知名偶像團體的專輯,在小卡被抽走後,CD被遺棄街頭,宛如垃圾。「近期已經出現『我們根本不需要這種垃圾』的聲音,不但浪費資源,也會造成環境汙染。」吳洗娟說明,雖然有公司推出「可溶解在水中的CD」,聽起來很環保,實際上,只要不製造就可以了。
K-pop能形成強勢且獨特的流行浪潮,其中偶像明星自我揭露隱私所創造的獨特親密感,是凝聚粉絲相當重要的方式與文化。雖然許多韓國藝人因此深受私生飯騷擾之苦,然而撇除極端現象與個人行為,將藝人的隱私公開化,一直是韓國經紀公司的宣傳手法,比如Bubble泡泡與直播文化。
經紀公司為追求利益而推動的過度消費,除了鋪張浪費,也可能造成青少年或經濟能力有限的粉絲巨大的經濟負擔和不理智消費行為,比如購買過多CD、訂閱偶像的泡泡。此外,粉絲之間也容易形成競爭或嫉妒,甚至是心理壓力,造成憂鬱與沮喪。
➤維特效應:偶像的輕生,也會造成粉絲的憂鬱或自殺
與會讀者也分享自己的糾結:「我追星追了很久,原本想說,追星就是我快樂就好。後來發現,其實我的偶像不快樂,所以我好像也沒有很快樂。後來,偶像走了……最近,另一個偶像犯罪了,應該被抓去關了……我也不忍看那些新聞。現在我的想法是,他有在呼吸就好了,只要他活著,沒有走掉,活著就好了。」
本報導雖然主要聚焦於男性偶像性犯罪與女性粉絲的心路歷程,然而,若將視野關注於偶像與(青少年)粉絲的依賴關係,已有許多報導指出,偶像明星的自殺與社會整體的自殺率,有明顯的正相關。
韓國藝人金鐘鉉、雪莉和具荷拉的自殺事件後,皆引發了顯著上升的自殺率;而日本藝人竹內結子和三浦春馬的自殺事件,也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和憂慮,自殺率在青少年和年輕成年人中有所上升。尤其在媒體大量報導後,模仿自殺的風險增加,這樣的現象被廣泛稱為「維特效應」,也成為追星現象的意外風險。
➤女性粉絲的角色衝突:助浪者、包庇者、被歧視者,也可能是性犯罪的被害者
鄭俊英群聊事件中,他偷拍與下手的對象正是他的女性粉絲。而前BIGBANG成員勝利的「Burning Sun事件」中,涉案夜店同樣利用偶像名氣吸引大批粉絲,對年輕女性進行迷姦。這些事件皆顯露出男性偶像利用他們與女性粉絲之間高度的權力不對等,進行性犯罪。這也是韓國偶像工業中極度黑暗的一面。
在書中,吳洗娟除了作為粉絲,她對自己女性的性別身分相當有意識:
《成粉》中所有受訪的粉絲都是女性,也反映了吳洗娟希望為女性發聲的立場。K-pop男偶像與女粉絲的結構位置中,女性是幫助男偶像成名的助浪者、維護者,在偶像出事之後,她們可能被旁人歧視為某種程度的性犯罪協助者。而最令人心驚的案例是:女性粉絲成為性犯罪(潛在)的被害者,一切皆因為她們曾經信任了某位偶像。
在《那一天,我追的歐巴成為了罪犯》中,吳洗娟採訪了2016年首位揭發鄭俊英犯罪事實的記者朴孝實,這是書中相當值得省思的段落。當時的吳洗娟與社會大眾普遍誤以為朴孝實是無端指控,對她相當反感,吳洗娟曾在自己的日記中寫下對朴孝實的不滿。直到黑暗的事實被揭露,她才意識到自己當初的錯誤。
後來拍攝紀錄片時,她將朴孝實列為受訪者,並真誠地向她道歉。新書發表會時,吳洗娟難過地分享,紀錄片採訪時,她得知朴孝實在那幾年由於報導此案,不停遭受批評,因為精神壓力過大,數次流產,導致終生不孕,令人惋惜。
基於隱私的關係,吳洗娟並未在書中與紀錄片揭露此事,儘管這能使她的紀錄片與書籍更具衝擊力。隨著今年5月BBC紀錄片《揭露韓流明星聊天室裡的祕密》同樣採訪了朴孝實,並公開此事,吳洗娟才於新書發表會時分享。
她進一步說明:「其實留言攻擊朴孝實的人,並不完全是粉絲,而是極右的厭女團體,時間持續了非常久。」雖然吳洗娟僅在日記中寫下批評,照理說並無需公開向朴孝實道歉,但作為粉絲也作為女性,吳洗娟仍感受到自己的愧疚。
從性犯罪、網路霸凌到媒體與社會環境,這些現象顯示了對男偶像犯罪的輕拿輕放,而女性粉絲與新聞業者卻無論身體或心靈,都滿是傷痕。
➤追星,也是友情的美好旅程
「你想要多少快樂,就得承擔多少風險。」吳洗娟道出「追星」本質上存在著兩面性。然而,有些風險已然超過了個人能承受的範圍,如本文所述及的性犯罪、女性粉絲的角色衝突與維特效應等等。
《那一天,我追的歐巴成為了罪犯》,韓國原書名「《成粉》日記」,是吳洗娟紀錄片拍攝過程的日記隨筆。如果想研究韓國偶像工業的結構問題,這本書並非上佳之選,但若想理解K-pop粉絲的心聲,這本書是罕見的血淚集。
細讀本書,吳洗娟仍肯定追星的正面意義,書中透過因鄭俊英事件受傷甚深的記者朴孝實的分享,道出追星的正面觀點:「如果可以從藝人身上得到正面影響也不錯。但明星也是人,都不是完美的嘛,我認為要求明星當個完人就太苛刻了……人生苦短,喜歡一個人怎麼會是壞事呢,當然是好事。」
紀錄片上映後,吳洗娟收到最令她印象深刻的觀眾回饋是:「這是一部關於友情的紀錄片」。她很認同,因為過去曾經一起喜歡鄭俊英的粉絲,都是有著共同興趣或喜好的人,彼此可以很自然地相處,甚至不需要過多的說明,就能心領神會。吳洗娟分享:「回憶追星這段時間,並不是見到(偶像)這個人的瞬間印象最深刻,而是一起排隊,跟其他人成為朋友。這些回憶也是非常美好的部分。」
「拍攝這部紀錄片,拜訪每位受訪者的過程,每個人都像一個車站,我開著一輛車靠上去,聊了一下天,車又開走了。兩個人都會得到一些什麼,或許平撫了一些內心的憤怒。」紀錄片的拍攝與出書,對吳洗娟而言,也是一趟療癒的歷程。
➤什麼是「成功的粉絲」?不是偶像認識你,而是從追星裡得到成長
紀錄片名稱是「成粉」,無論書籍或影片,想討論的也是粉絲圈內部的提問:「什麼是成功的粉絲?」讓偶像認識你?收集完整小卡?或者成功參加簽名會?健康的偶像文化,應該是偶像能從粉絲處得到支持,而粉絲則能在追星的過程中獲得價值,雙方都藉此得到力量。
比如,曾有位偶像的作品涉及性別用詞不當,經過粉絲提醒後,從此創作上避免了這類疏漏。又比如,偶像推薦自己喜歡的書籍,粉絲也熱情地找書來閱讀,既刺激了出版市場,雙方身心亦都能成長。這些都是互惠的案例。
從反轉過去「成功粉絲」的定義,吳洗娟希望營造對粉絲更健康的偶像文化。書中的一段話,具體道出了本書的宗旨: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