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談》我還年輕,我想能逃跑就逃跑:陳國偉vs.何玟珒談《那一天我們跟在雞屁股後面尋路》
與談人:
陳國偉(中興大學台文與跨國文化所優聘副教授兼所長)
何玟珒(作家)
下午兩點,線上對談的視訊畫面上首先出現的是陳國偉教授,背景設定是陽光明媚的房間;稍後上線的何玟珒,背景窗外則是綿綿細雨。不同的天氣選擇似乎預示了,此次對談的70後與90後(類千禧)世代對世界的想像。
➤在搖搖晃晃的校車上寫作
何玟珒的小說讀來不像多數純文學作品,每則短篇的流暢度都宛如類型文學,兼融了同人文或BL創作中人物立體、情節飽滿的痕跡。這不禁讓讀者好奇她的創作養成。
何玟珒回憶創作的起點,因為高中就讀升學主義私校,所以只能利用搭校車的通勤路上,搖搖晃晃地用手機打字寫作。「好厲害,那時候都不會暈車……」她有些飄走地喃喃自道。
創作之路從同人文、BL小說跨到投稿文學獎,何玟珒不好意思地表示,一開始寫作只是為了讓自己或朋友開心:「決定要投文學獎時,我覺得這些東西(同人文)不太好意思讓比我年長的前輩老師看,有一點太害羞了!」
既然要比賽,當然志在得獎,何玟珒參考先前的得獎作品,輔以自己在台文系學得的文學理論,猜想評審老師會想看什麼樣的作品。陳國偉問她,同人/BL與純文學的書寫策略有無差別,何玟珒用力思考了一下,說自己不太擅長寫文本時空是凝滯的、充滿人文哲理的那種小說類型。「我好像沒有那個腦袋……」
「我會想辦法在8000字或1萬2000字之間讓劇情可以往前走。至於劇情往前走這件事情,BL小說表述的……是兩個人怎麼談戀愛,然後在結尾的時候走向一個……身心大和諧的套路。」
每次句子的中斷,何玟珒都是支支吾吾地想確保陳國偉接收到她含蓄的BL電波。這場對談中,「身心大和諧」成了最大分貝數的關鍵詞。「為了要『身心大和諧』,角色兩人必須要往前走,所以會強迫劇情的推動。」何玟珒這麼說。
陳國偉注意到,何玟珒作品裡有許多涉及鄉土、家族、故鄉的親屬關係,「會選擇這些題材或角度去寫,跟妳在學校的學習有關嗎?或者這也是妳觀察這些文學獎之後得到的心得?」

何玟珒坦承兩部分都有。文學獎總是有些重要的文學母題反覆出現,例如鄉土、故鄉跟家族。「要比賽的時候,大概會知道,如果我寫的東西跟前輩寫的一樣,那我可能就是沿襲前人路。套句草東沒有派對的歌詞『我想說的前人都已經說過了』,所以會去思考,用一些相較之前不一樣的寫法。」
「雖然可能也沒有很不一樣——可能是我讀得太少,才會以為自己寫得很不一樣,但其實沒有,呵呵。」何玟珒語速飛快地自嘲補充:「如果用韓國女團比喻,韓國女團很多會翻唱前輩偶像的舞台表演,可是她們翻唱的過程當中也會想要加入自己團體的特色,然後讓自己的舞台可以有自己的樣子。」
➤格格不入的地標
話題來到與新書同名的短篇,也是最令人驚豔的〈那一天我們跟在雞屁股後面尋路〉。陳國偉說,「中國城」出現在台南這麼本土的地區,是一種格格不入的存在,故事中也將這種差異對應到主角弟弟的性別錯置上。在台南的地景之中選擇中國城,似乎蘊含了對國族的一些思考。
何玟珒馬上為我們補充一堂台南中國城的歷史課:中國城在日治時期先是日本人興建的港口,變成中國城之後又由荷蘭的建築團隊改建為河樂廣場的親水公園。「所以那一塊小小的地方,哇靠!它有台灣、日本、中國、荷蘭,一整個就是台灣史的縮影。」

何玟珒起先是以「這樣好酷」的念頭而把中國城放到文章裡,後來發現,不管是中國城沉重的建築量體,或是現在的親水公園,都不適合在台南被建造起來。中國城是因其鋼筋水泥不適合在一直有海風的岸邊;親水公園則是冬天缺水,夏天也會因為暴雨導致水質汙濁,無法親水。
「不管什麼樣的建築物,在那裡被打造的瞬間,其實都不適合台南這座城市。但不管它到底適不適合,它就是被建造了,所以台南人或觀光客就是用一種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態跟這些建築物相處。這件事情好像也可以呼應到歷史上台灣人民對殖民者的一些態度。」
何玟珒認為,台灣人常常被迫去適應這塊土地上發生的事。而適應的概念也延伸到小說中主角跨性別的弟弟「咩咩」身上:「咩咩他是『個體』,比起群體來說,他更有能動性對他身體的空間去做一些改變,所以相較於建築物來說,他就自己去改動了自己身體的樣子。」
小說裡,何玟珒用中國城的歇山式屋頂象徵父權封建,對比親水公園當中女體的象徵,建築空間從封閉的商場變成開放的露天親水公園,類比社會風氣對於性別的想法較趨開放。何玟珒說,她把很多「亂七八糟」的想法都塞到這一篇。
➤那一天我們跟著何玟珒逃跑
從地景向下聚焦到家庭,陳國偉觀察到,何玟珒作品中的家庭都存在著戲劇般的張力。小說裡面數則令人印象深刻的短篇就是各種家庭劇場,主角們看待性與身體的價值觀,最後總帶來家庭裡的衝突。
「家庭的樣子有很多種,正常的家庭應該會供應一個人的生長所需,但是有些家庭的暗面,這樣子的功能是毀壞的。另一個層面是家庭供應很多東西,雖然我們常常說親情之愛是不求回報,可實際來看不太可能。」何玟珒透過小說拋出大哉問:「所以到頭來,人要用多少時間、心力,或是其他東西去予以回饋才足夠呢?有些人並不是生來就是想出生在這個家庭,或這樣的身體,對於這樣的個體來說,他們的回報又要怎麼在家庭跟自己之間取得平衡?」
何玟珒提到反送中運動時,有個香港父親舉報自己的孩子。「本來應該要予以小孩子保護的地方,卻變成大人為了服膺國家的力量,捨棄了自己跟小孩的血緣。這件事情在台灣戒嚴時期的時候應該也是發生不少……」

最後她得出一個結論:「人生下來就是一個單獨的個體,所以也沒辦法因為任何原因,去影響另一個個體自己的決定,即便彼此的關係是親人也一樣。」
小說裡家庭劇場變成恐怖劇場,陳國偉坦承閱讀時常常受到震撼,也能感覺其中處理了很多親緣的顛倒、變異,甚至逃離。時代改變很多傳統的倫理關係,包含人們如何看待家庭與親緣,對何玟珒來說,用小說去重新檢視家庭的倫理關係,存在重要的意義。
「雖然說是親緣,可有時候親緣說不定也是惡緣呢。」何玟珒試圖用輕鬆的語調來淡化句子的沉重:「如果是壞的緣分,就盡力的逃跑。」她以自己的個性舉例:「我是那種關注於自身完好的人,所以如果有某些東西讓我覺得好像受到侵犯、沒辦法再忍受下去了,我就會逃跑。」
傳統的倫理關係奠基在不可以逃跑的基礎上。以長照為例,父母生病後,倫理要求子孫肩負起長照的責任,如果子孫逃跑,照顧父母的責任就得外包給外傭或是政府,造成別人的麻煩。

「所有的倫理關係都是想要讓人不要逃跑,我開始想,這樣把一個人固定在不能逃跑的位置上,對人真的是好事嗎?不知道能不能鼓勵大家逃跑,就是如果撐不下去的話,還是逃跑一下吧。」說到這裡,何玟珒突然意識到什麼的慌張說明:「這樣好不負責任喔……這是個人立場,不代表跟我同輩的人都這樣不負責任,沒有,這是我的問題而已。」
除了家庭的描寫,讀者在何玟珒的小說中也能強烈感受到民俗的存在。銜接到前述的「不能逃跑」,所謂民俗或習俗,本身也具有強大的約束力,會與性別、婚姻、家庭產生衝突。何玟珒刻意安排這些元素,譬如〈疼痛轉生〉有同志兒子附身阿嬤的橋段。
因為對現實中「不可以逃跑」的事情感到困惑與些許憤怒,所以她為小說的主角提供了逃跑的路徑,告訴自己這樣也可以,對不能逃跑的事情吐口水也可以。
信仰或民俗內含的神聖性,在何玟珒眼中並不那麼禁忌。「可能因為我很年輕,又是一個很無知的狀態,所以就覺得說不定很多東西都可以重新討論。」但同時她也明白,覺得傳統倫理、信仰、民俗很重要,不容挑戰的人,一定也有其理論跟想法去堅固他們的信念。
「我不清楚他們的想法是什麼,就是因為我很無知,還不太知道這些事情,所以才會輕易地說:『我們來討論。』但也許它其實是不可以被討論的我也不知道。」何玟珒小心翼翼地用但書來掩飾看似年少輕狂的發言。反而陳國偉鼓勵地說:「有些東西就是年輕人才有勇氣挑戰,我覺得這樣子沒什麼不好,本來文學就可以挑戰很多東西。」
➤是想像,還是代言?
陳國偉笑說,整本小說集讀起來有種「親近感」,題材充滿了老年、死亡、沒有愛情的婚姻、照顧者,都是非常中年人的日常,但對照何玟珒的年紀則反差強大。何玟珒表示,選擇書寫中年人的日常,除了想在校園文學獎中脫穎而出,還有一層原因是「如果我老了以後怎麼辦」的想像訓練。
「如果我長大以後不小心走進婚姻的墳場,然後有一個角色是我必須承擔的,那會怎麼樣?所以我去捏塑人物,然後想像他被置於一個困境裡,會做出什麼樣的反應?我覺得這很有挑(ㄏㄠˇ)戰(ㄨㄢˊ)性,去想他會怎麼樣解決困境,最後再寫成小說。」
講到這裡,何玟珒再度切換成BL模式:「說不定我的想像力是來自於先前寫BL的經驗。我是一個生理女性,基本上BL發生的所有事情我都不可能有那樣的經驗,所以就是用想像力跟田野調查弄出來。塑造一個想像中的角色,去經歷我沒有過的經驗,我很習慣。」
何玟珒用想像的方式為中老年的角色代聲,卻也擔心為不屬於自己的族群書寫,會弱化弱勢族群本身的聲音,譬如身為原生漢人卻去寫新住民的故事。
「文學裡面,其實本來就很難不去書寫到你之外的族群。」陳國偉為她解憂:「文學必須要去反映你所觀察到的這個世界,這個世界不可能只有你自己。」這樣的擔憂,從日治時期的知識分子對於他們能否代言底層人民,就已經出現了很多討論。LGBT、原住民、新住民、移工等等被主流族群邊緣化的族群,是需要被看到的。陳國偉說:「強化還是弱化,真正的關鍵還是在書寫的態度,而不只是書寫者的身分。」
由當事人發聲是最理想的,但現實上有其困難。比如台灣人大部分看不懂新住民的母語,新住民得學會中文才能將話語散布出去,他們等於面臨了台灣過去跨語作家的困境,造成這類書寫很多時候需要他者來進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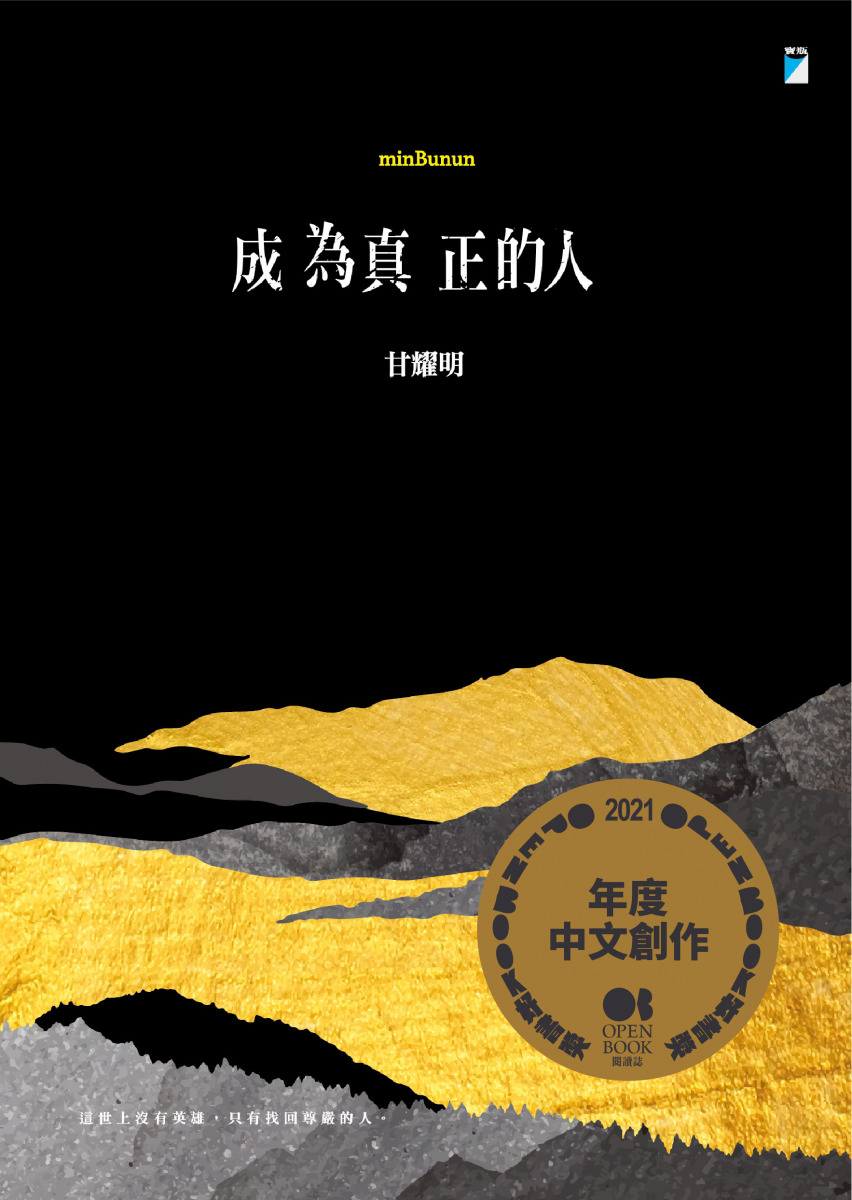
「良性的生態是:這個問題大家都關心,有許多不同角度,而書寫的態度則是善意的、相互溝通的,去書寫各種問題處境。」陳國偉以去年甘耀明的《成為真正的人》為例,他寫原住民跟同志的題材,尺度拿捏得宜,也寫就了一部情感真摯的小說。這樣的代言狀況,是現今台灣文學場域裡常見的,也有助於促進多元對話。
「我覺得好的生態是鼓勵弱勢族群發聲,也容許其他族群或其他位置的發言者跟他們對話。」陳國偉說。
➤想改編BL作品……嗎?
陳國偉對IP議題的熟悉度,讓何玟珒特別想聊聊台灣的IP改編。
影像時代強勢來臨,文學的生存面臨很大的危機。「無可諱言的,影視化或跨媒體改編其實是文學的重要出路之一。」陳國偉直接點出結論:「透過IP改編,其實可以讓更多大眾注意或接受文學。像我因為教課,意外得知很多大一大二同學看過《斯卡羅》跟《天橋上的魔術師》電視劇,它其實回頭帶動了小說的販售。」

除了重新產生內需,IP改編也讓台灣有機會走出國際,陸續有越來越多作品被翻譯到國外去。《想見你》、《誰是被害者》、《華燈初上》已經打開了中國以外的市場,包括東亞和東南亞。
「IP、影視化、跨媒介改編,提供了文學可以延續的空間跟能量,我覺得是滿值得重視的一條路徑。」陳國偉說。
何玟珒回應,她創作的當下並沒有想過太多作品的未來,「能寫完就功德圓滿了!」但創作之後,的確也期待能有機會被改編成漫畫、廣播劇等等。「可是如果我的小說有很多內心獨白,要畫成漫畫的時候就會變得非常困擾……」
「但空煩惱也沒有用。」何玟珒豁達地結束這一回合。
➤純文學、BL類型我都要!
兩人聊到小說集的推薦序,何玟珒尷尬地說,看到作家張亦絢提到「黑色幽默」跟「喜劇」,還特地去查兩者的定義。結果查黑色幽默的時候,只跑出周杰倫的〈黑色幽默〉,此語引起會議室裡眾人會意哄笑。
針對張亦絢提到的「引入喜劇的天分」,何玟珒表示她並沒有刻意去用所謂喜劇或黑色幽默的方式寫作,畢竟這兩者她都要查Google了。「可能就是對不能逃跑的東西感覺到一點生氣,然後就會很想要去戳它一下。」
寫完後回頭讀起,何玟珒才發現某些地方有滿滿的諷刺感。「像〈一個男人的攝影史〉,講社會大眾覺得某個攝影師拍的作品非常有人道關懷精神,可我那個時候想,他說不定只是想要拍色色而已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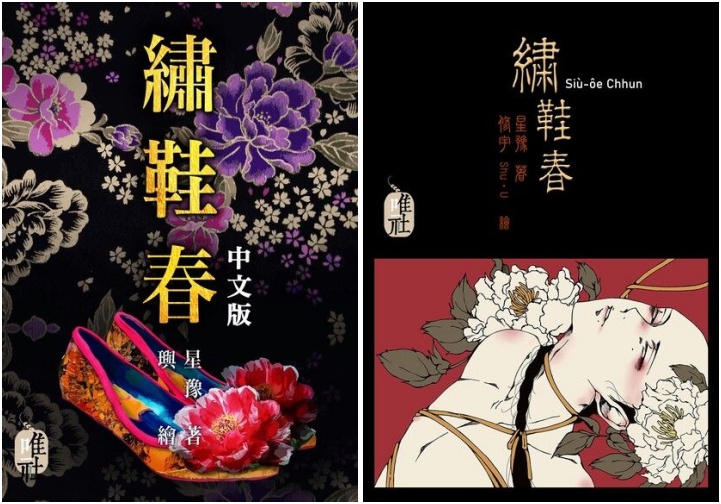
「冠冕堂皇的東西底下,有可能不是那麼冠冕堂皇。」她分析自己作品喜劇感的可能來源:這樣的喜劇或黑色幽默,來源跟同人創作常見的「吐嘈」或「自我解嘲」路線沒有關係。何玟珒說她將純文學創作與BL文分很開:純文學有想進行的思考,BL則是為了讓讀者和自己看了開心。
同時跨足純文學與類型作品的何玟珒,好奇陳國偉會如何評價好的純文學跟類型。這個話題開啟了陳國偉課堂上侃侃而談的模式:純文學的目的是為了讓讀者開啟不一樣的視野,透過陌生化的經驗讓讀者花心力去思考作者想傳遞的訊息;類型或大眾文學則是先滿足讀者,有愉快的閱讀經驗,再去談傳遞的訊息。
「評價好的純文學或類型文學,最直覺的方式就是把它們放在各自的文類脈絡,然後看這個作品怎麼回應這個脈絡:它是不是有所突破、是不是有新意?」陳國偉說,台灣的純文學長期以來受到現代主義美學的影響,文學獎評審很難避免這個影響,包含是否有精準的描繪、作者如何處理小說的核心等等。
「可是純文學跟大眾文學都各自在尋找突破,比如純文學作家越來越多會用類型的方式來寫作,類型文學也有跨類型的現象。」陳國偉總結道:「所以我會盡量引入更多不同的角度跟標準,做綜合的判斷。所謂的好跟不好,其實是相對的。」
➤文學不孤獨,它很炫炮
陳國偉留意到,台灣二、三十歲的作家,都樂於嘗試把各自的文化養成或創作養分放進小說裡。比如何玟珒寫同人文,喜歡BL,或像楊双子、瀟湘神、陳又津的各種嘗試。其中有個明顯的趨向是,越來越多人試圖把大眾類型結合進純文學的創作,或試圖在兩者間找到新的平衡點。
「大家的世界觀也已經不一樣了,因為我們認知這個世界的方式不一樣。」陳國偉說,人們對於一個整體的故事,已經不見得那麼在乎。現代人消費與著迷的是角色,角色元素來自像大數據的資料庫,文學也逐漸走向這個狀況。人們活在片斷的資訊時代,看著懶人包或YouTuber的整理,代表時代不想要去追求全貌。
「甚至講極端一點,那個全貌可能也已經不在了,我們永遠都只能夠用比較片斷的方式,去接近某個我們以為的全貌,或我們想講的全貌。」
所以寫作者真的需要去追逐那個全貌嗎?陳國偉解析說:「以玟珒的作品為例,讀者看到的全部都是從角色的經驗進去,作者也不見得有義務要秀出家庭的全貌。更重要的其實不在於認識這個家庭的面貌,玟珒沒義務要告訴我們這個時代的家庭變得怎麼樣,她只想讓讀者看到大魔王在那個地方,然後為什麼要逃。這個部分其實是一個切片式的角度進去的,所以就會特別看到那個被放大的怪異、黑色幽默、喜劇,〈電梯上樓〉的結局就是這樣的一個安排。」
「它們的開放性和可能性,這些我們以為叫碎片的東西,其實反而是有更多的可能性。」陳國偉語氣中充滿對新可能的期待。
關於現代的碎片化,何玟珒回應道,她寫作的同時總是網路開著,通訊軟體、FB、噗浪、推特、YouTube都連線,娛樂快速的進入到寫作時間,往往一兩個小時後發現進度遲緩——只有在沒有網路的狀況下,才可以真的很認真寫作。
但何玟珒也認為,並不是坐在電腦前,從敲下第一個字到完成最後一個字才叫寫小說。她分享一位傳統戲曲老師的經驗,連走路都想著要怎樣去把雲手或戲腔鍛鍊得更好:「沒有坐在電腦前的時候,腦袋還是會不斷想著等一下角色要怎麼繼續做他該做的事情,好像無時無刻都是跟創作勾在一起的狀態。」

提到資料庫之說,何玟珒分享她知道的同齡創作者,其實對於寫出完整的小說並不太感興趣,卻會花很多心力去塑造一個角色。他們不是透過小說去發展角色,而是在人物設定當中不斷塞入故事,變成一個以角色為主的檔案。這些設定中的故事並沒有完全串起來,可即便只是人設的檔案,他們也都覺得很滿足。
這些創作者如果想要一部完整的小說,就會把人設發給一些文字工作者,讓他們去完成小說。那樣的小說不能賣,只為了讓角色創造者有個用自己的角色寫的小說,讓他們留存而已。
「這樣是否會影響作品的特色?我不知道,但是一個人負責角色的創作,然後另一個人負責小說的創造,我覺得這樣的互助合作有種莫名其妙的美感。」何玟珒顯得很開心。
對談最後,一直以溫和語調談話的何玟珒,用十分高亢的方式作結。「常常說寫文學是孤獨的,沒有!文學才不孤獨!現在你可以跟別人一起互相合作完成一部小說欸!超級炫炮的!」●
|
|
|
作者簡介:何玟珒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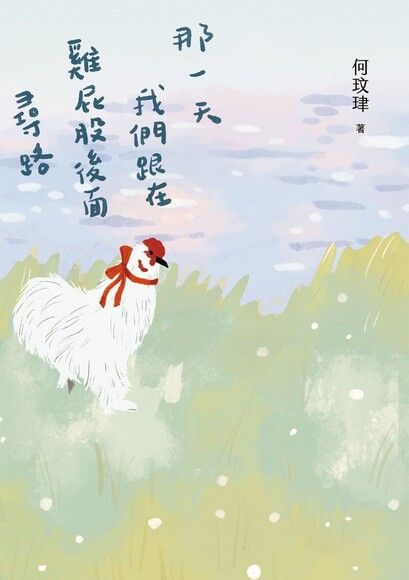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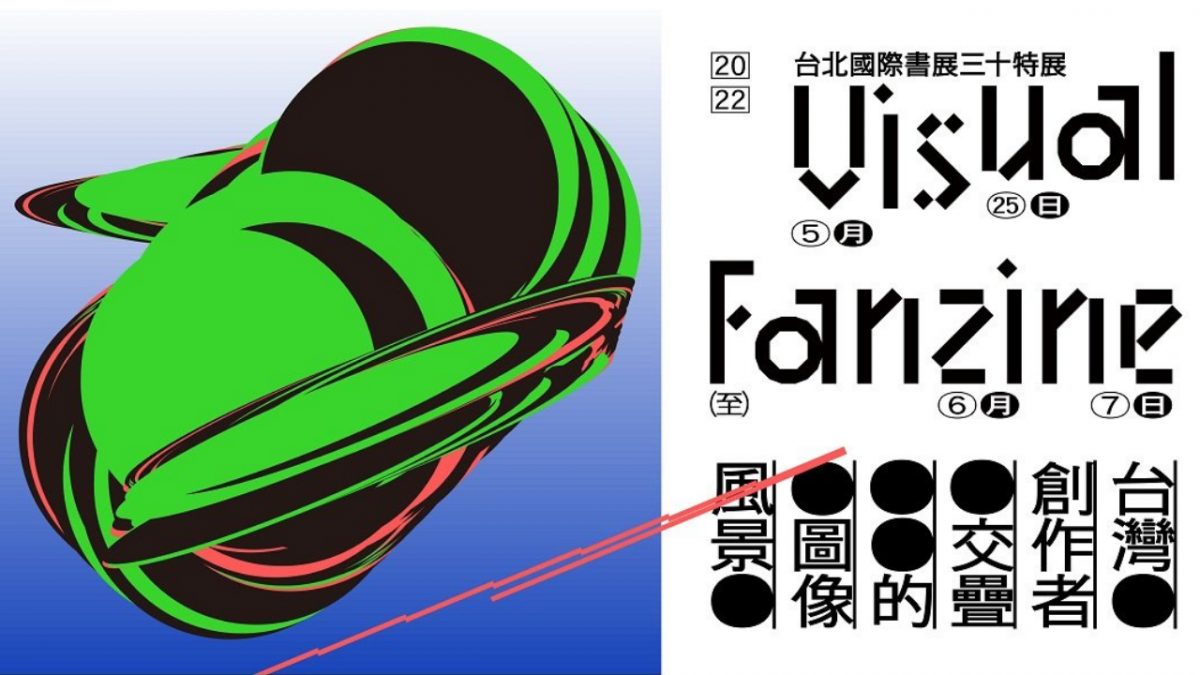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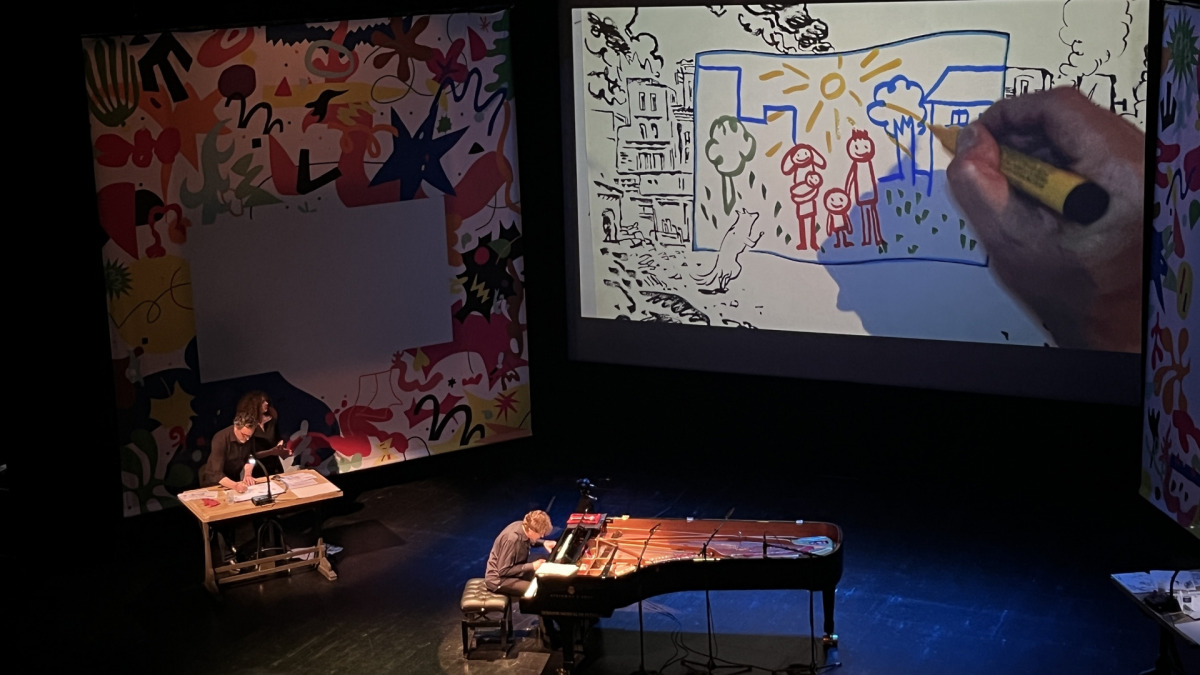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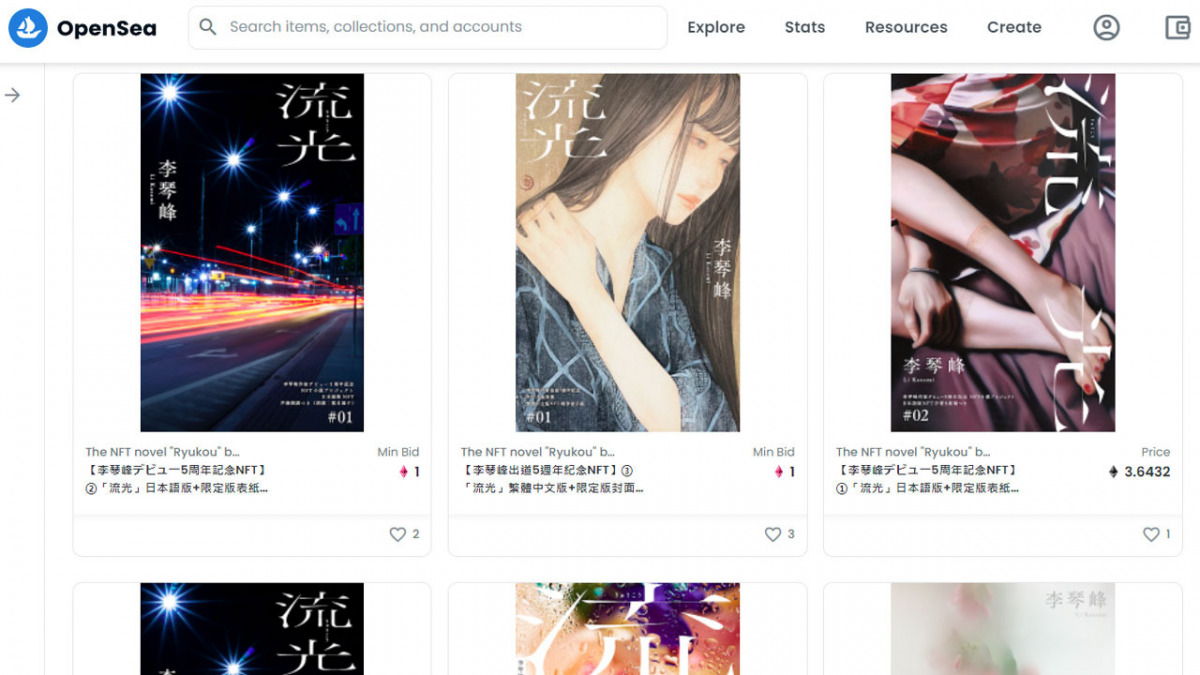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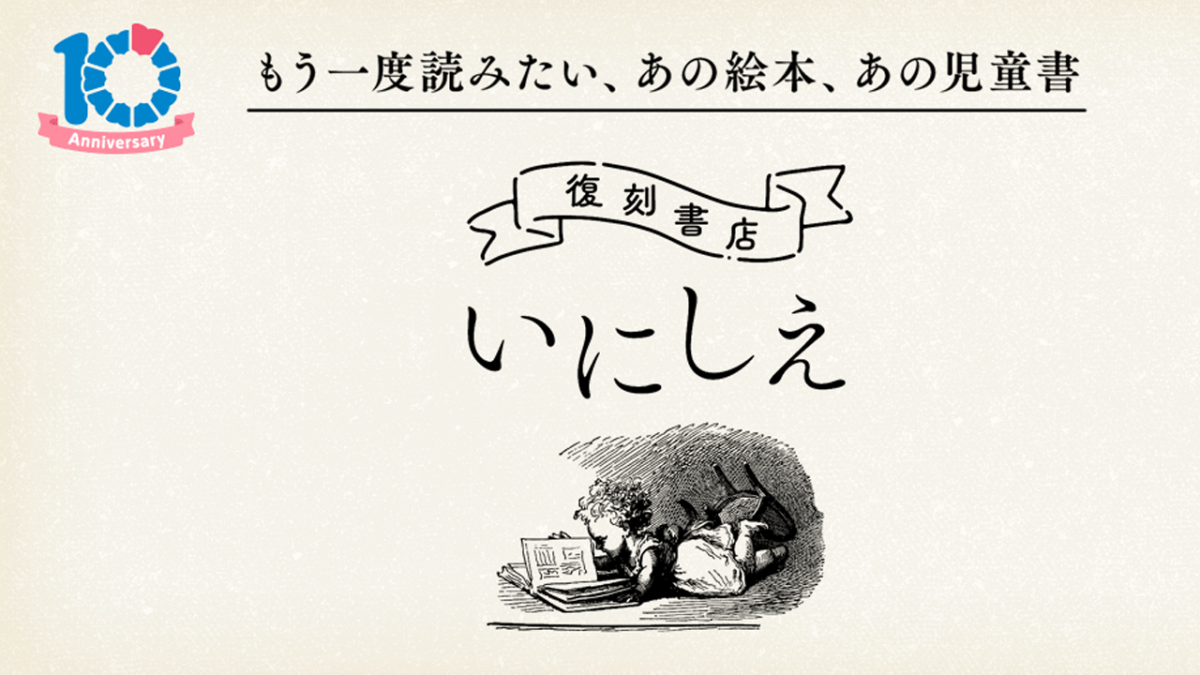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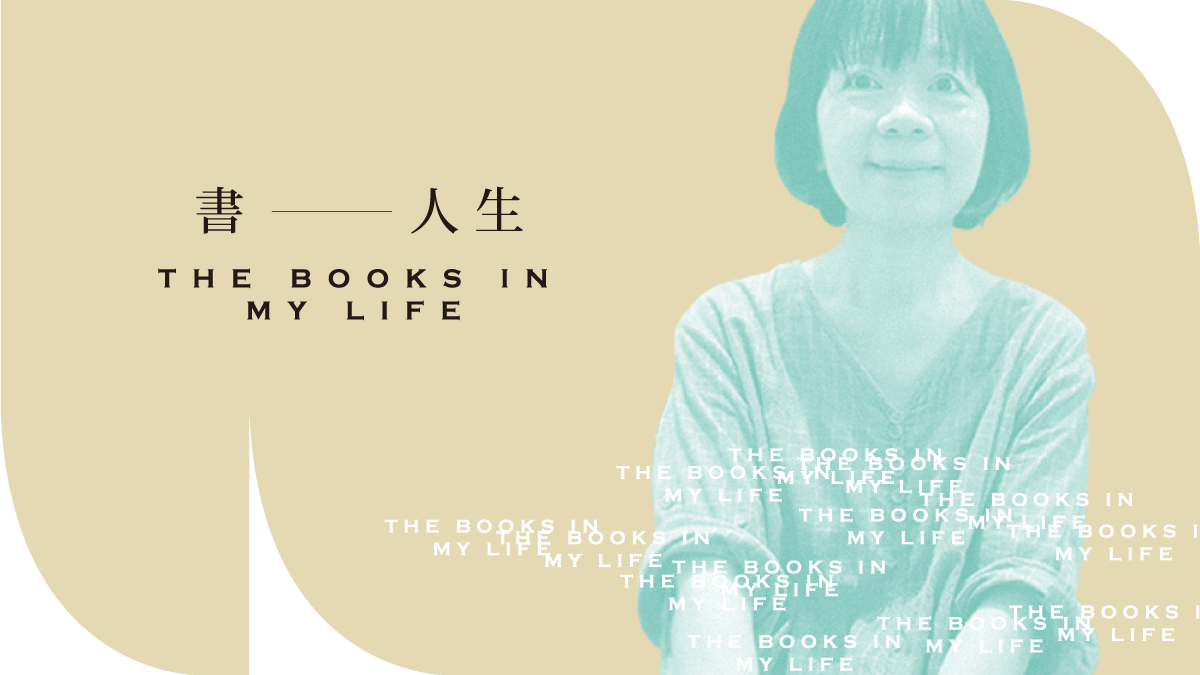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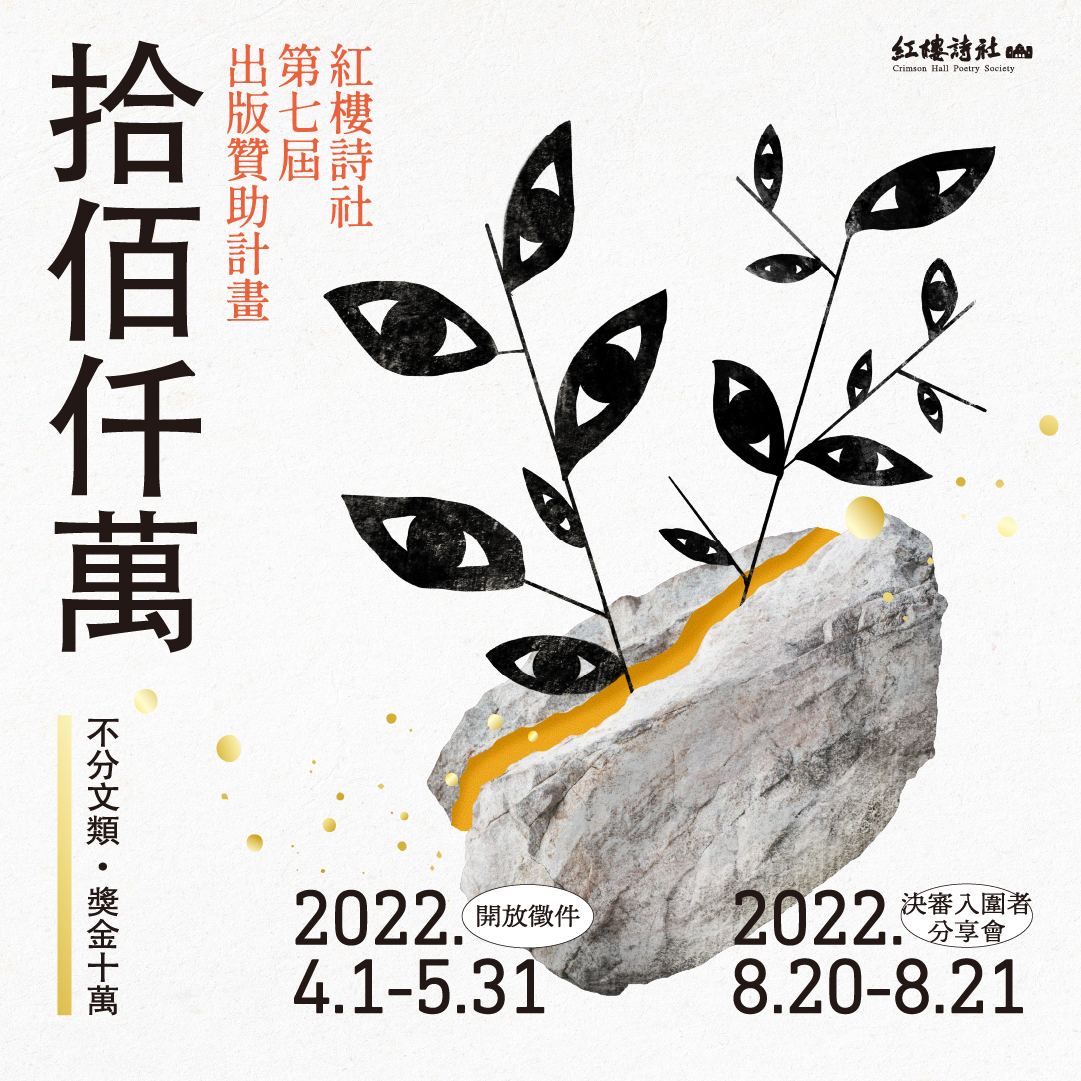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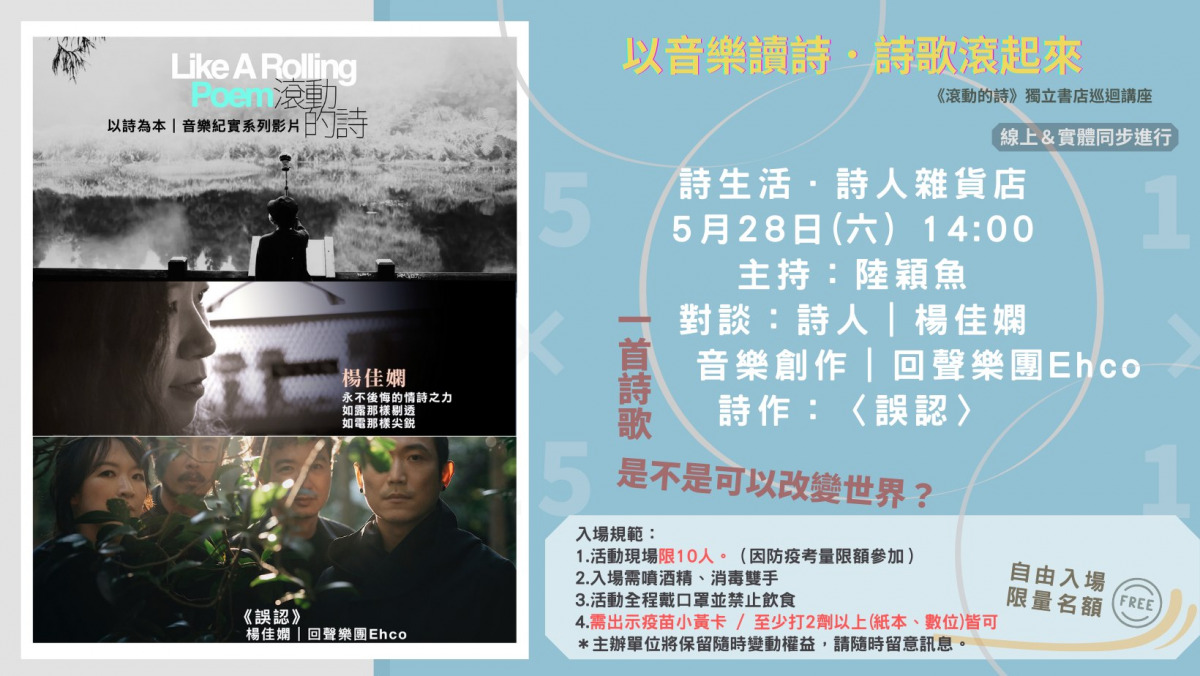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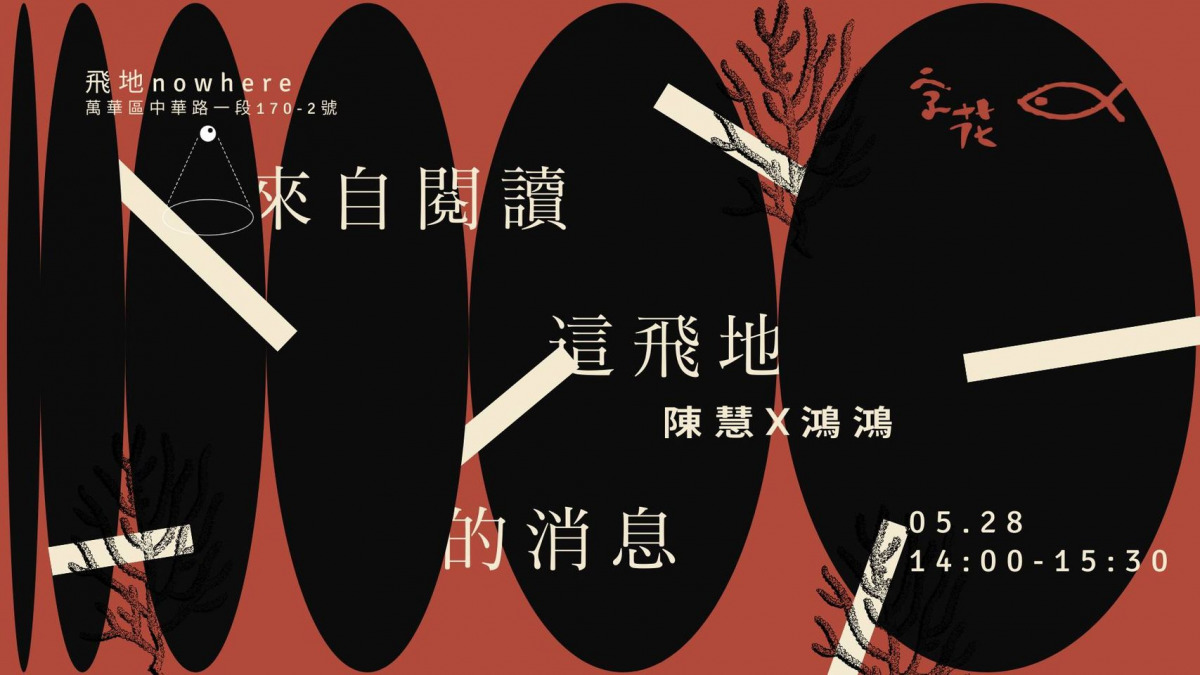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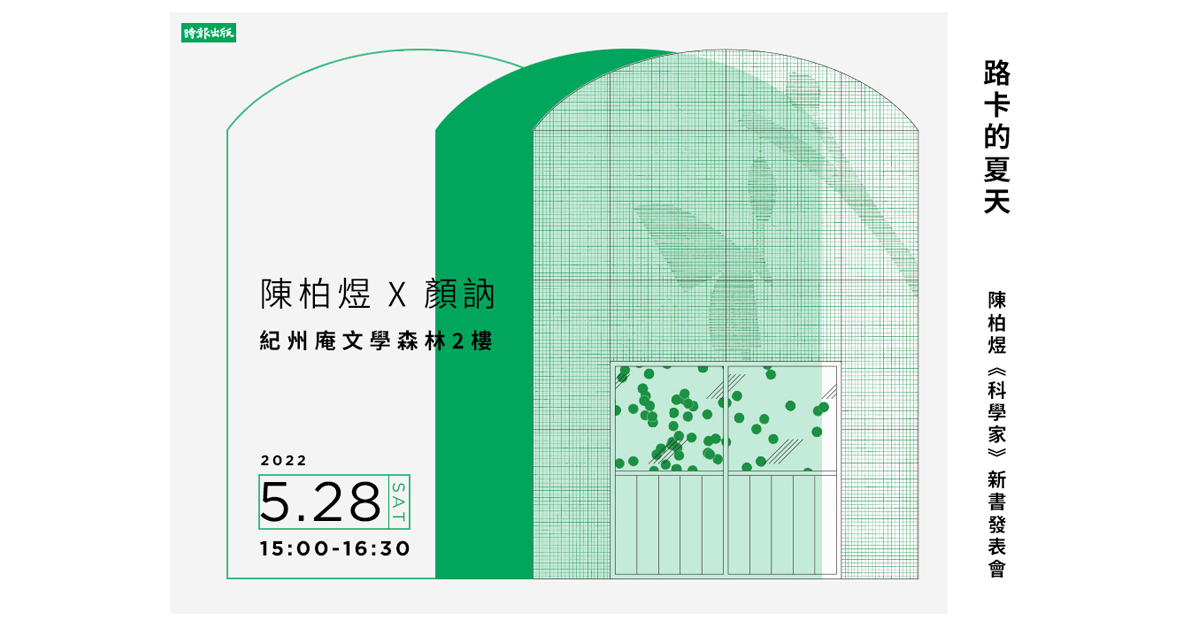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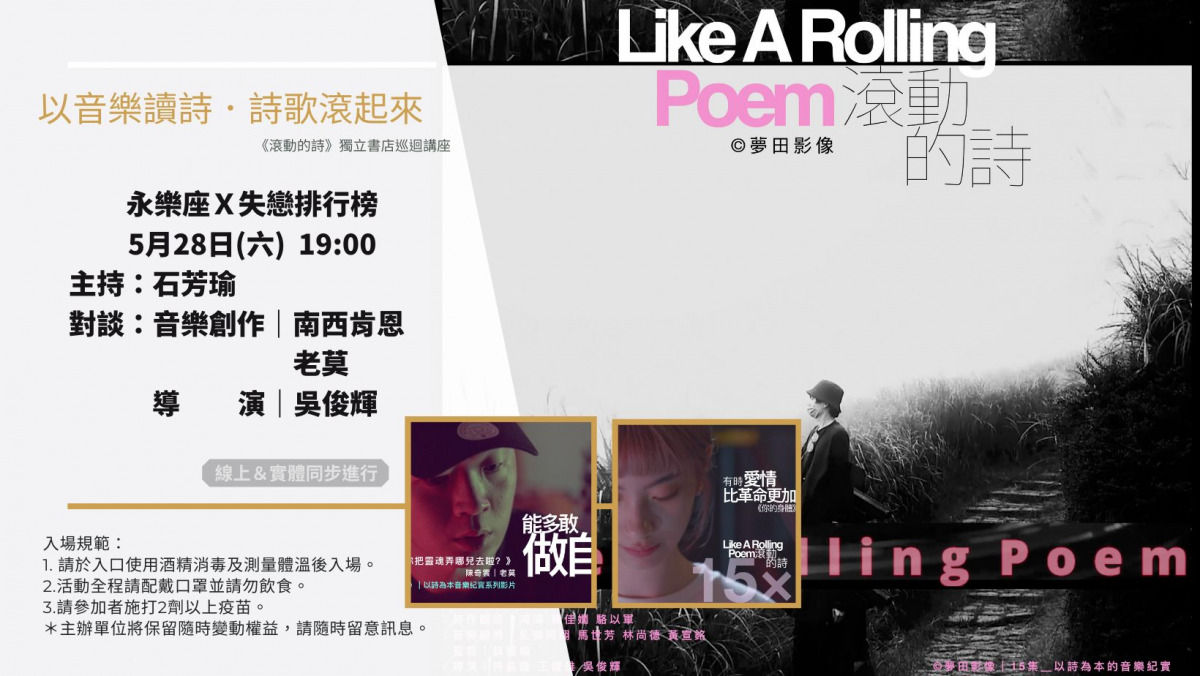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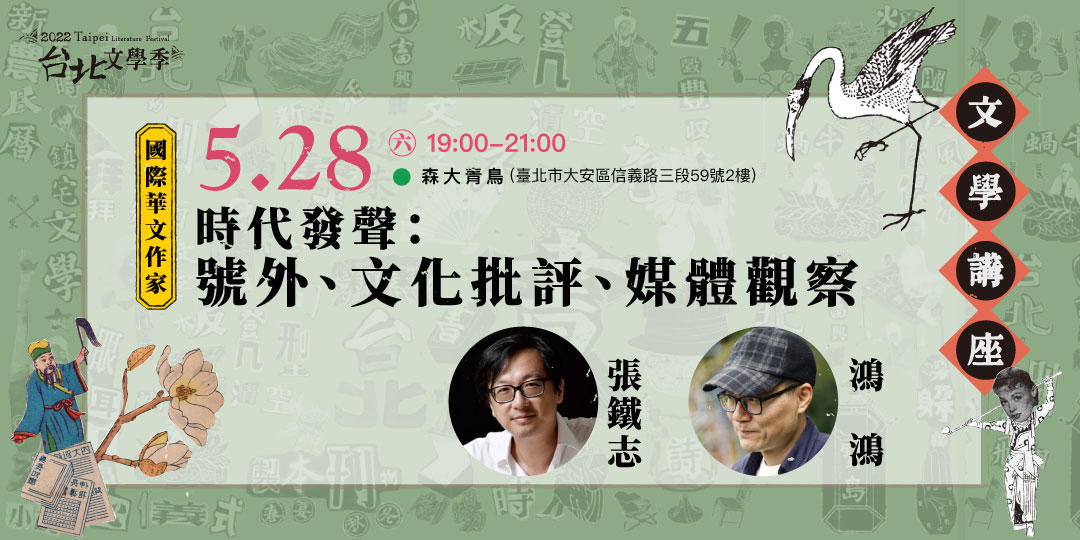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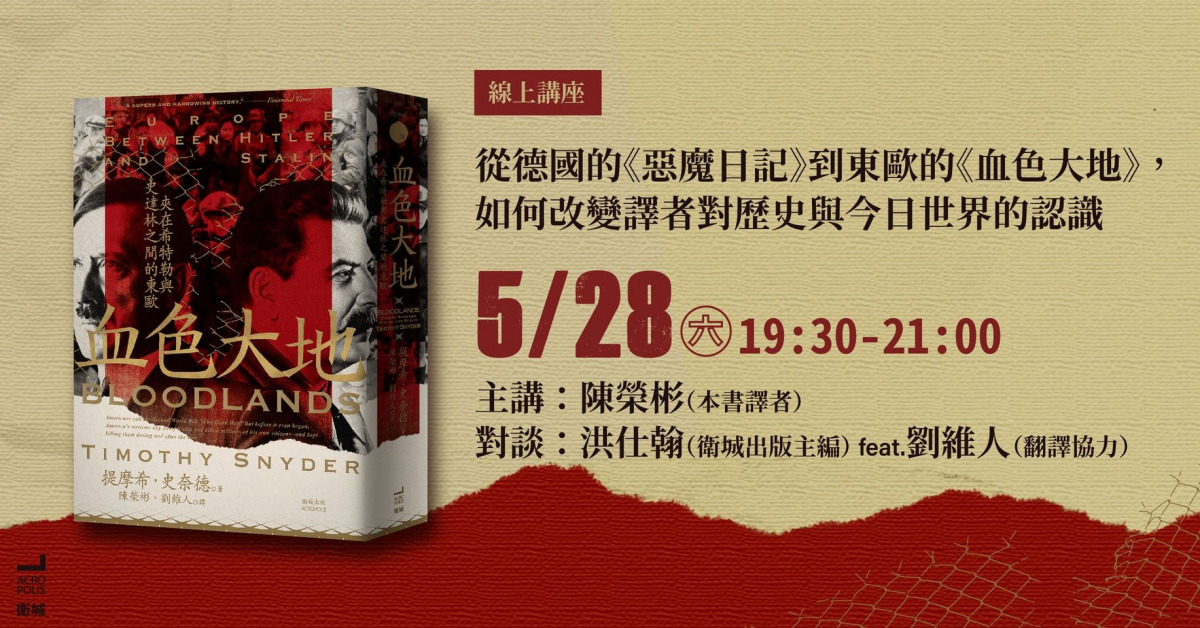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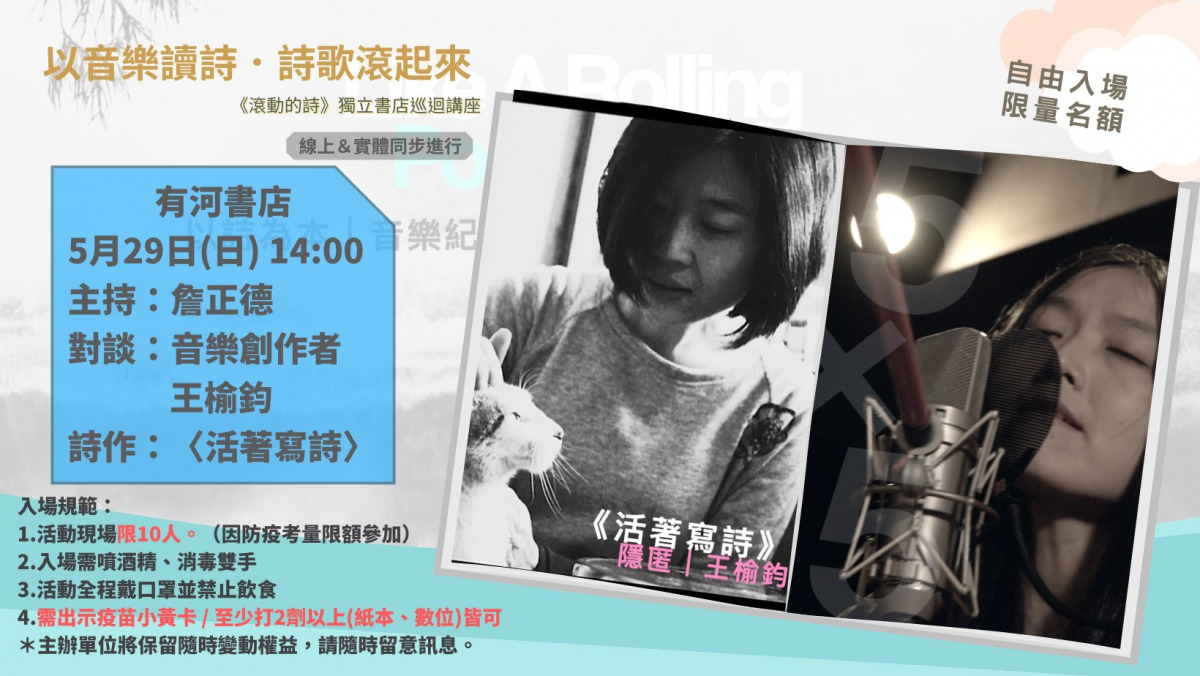



童書短評》#88 陪孩子在逃跑中尋得安心之處
●打開冰箱拿出來!
れいぞうこからとーって!
文、圖:竹與井香子(竹与井かこ),蘇懿禎譯,步步出版,320元
推薦原因: 趣 圖
適讀年齡:學齡前、小學低年級(4-8歲)
沒有小孩抗拒得了冰箱的誘惑,清清涼涼,密密層層,隨時都能挖出好吃的東西,難怪不管爸媽怎麼唸,小手還是一直忍不住去開開關關。這本書大方獻上好幾款不同風格、藏放各式生鮮蔬果的冰箱,讓孩子化身小幫手,可以按著清單以及故事對話進行一次次的食物尋寶遊戲,形式簡單但內容豐富,可以盡情開關玩不膩,再也不用擔心被罵啦。雖然是給低齡孩子看的繪本,藝術美感與細節處理卻毫不含糊,每戶人家的廚房裝潢、冰箱造型、內裝食材都有著不一樣的色調及風格,版面恰到好處不混亂,從圖像處理可看出對小讀者的尊重,不把他們當作幼稚無知的對象打發。【內容簡介➤】
●勇闖工研院實驗室1
生活科技的祕密基地
劉詩媛著,Tai Pera、Salt&Finger繪,幼獅文化,340元
推薦原因: 知
適讀年齡:小學高年級、國中(11-15歲)
用懸疑偵探與趣味解密的漫畫形式,來介紹台灣最大的產業技術研發機構——工研院,如此嶄新突破的創意與執行,為本土科普書的關注題材與表現手法帶來更多可能性。隨著輕快步調一路往下讀,工研院裡的部門實驗室及設備器材逐一亮相,原來每種都與生活息息相關,舉凡LED燈泡測試、廢汙水處理、紫外線測量、新冠病毒檢測……等等,都是工研院日以繼夜且獨步全球的工作業務呢!透過專業工程師的紙上導覽,工研院不再是遙遠冰冷的名詞,如果美術編排可以更活潑些,善用圖像增加趣味,這趟知識旅程必定更圓滿了!【內容簡介➤】
●林間奇遇
Capricieuse
文:碧雅翠絲.方塔內(Béatrice Fontanel),圖:露西.帕拉桑(Lucile Placin),尉遲秀譯,字畝文化,350元
推薦原因: 圖
適讀年齡:學齡前-小學中、低年級(4-10歲)
魔幻又濃烈,讀起來很有「拇指姑娘」童話味道。看著迷你女孩倏地墜入森林,小小身軀急躁穿梭在巨大繁花間,一步步邁向驚奇收束,小讀者的心裡肯定興起濃濃遐想,彷彿自己便是其中主角,體會了一場張力十足的夢幻旅程。圖畫主調採用少見的特殊螢光色,看似斑斕突兀卻又意外豐富和諧,從頭到尾散發出一股謎樣氣息,開啟不同以往的視覺經驗。【內容簡介➤】
●好想好想吃起司棒!
はいチーズ
文、圖:長谷川義史,林真美譯,維京出版,300元
推薦原因: 趣 文
適讀年齡:學齡前、小學低年級(4-8歲)
這本書的副作用太多了!首先是笑到臉頰發酸,接著是忍不住想吃起司棒,看看到底滋味如何?最後則是敲開記憶大門,回想自己遭遇過的相似尷尬時刻,大人也好,小孩也罷,生命中就是會有連舒伯特也無言以對的時刻啊。只能說長谷川義史真是太厲害了,用看似爆笑的極短篇故事,道盡了人性中的渴望、嫉羨、失落、無奈,這讓人再三咀嚼的複雜滋味,豈止一根小小起司棒!?書中小男孩一枝獨秀的誇張台詞與生動演出,絕對具有影帝級的戲劇實力,每頁每幕都堪稱經典,帶著讀者洗一場心情三溫暖。【內容簡介➤】
●最後的戰象
大象林旺三部曲
文、圖:李如青,步步出版,1200元
推薦原因: 知 文 圖
適讀年齡:小學中、高年級(9-12歲)
李如青的畫筆細膩如鏡,擅長刻畫史地題材,這回新作以大象林旺為主角,用磅礡罕見的三大冊篇幅,為牠傳奇的一生留下印記。從遙遠滇緬的幼年工作象阿美時代開始,到經歷砲火成為戰象輾轉流離,最後落腳台北成為家喻戶曉的動物明星,大象林旺隨著時代沉浮,在無數的命運交叉路上篤篤而行,書中每一幅如照片般詳實的插畫,都是牠真真切切踏履過的痕跡,如今靜靜流淌紙頁上,勾起好幾代讀者的無限回憶。【內容簡介➤】
●漫漫長夜
那些在夜晚工作的人們
All Through the Night──People Who Work While We Sleep
文:波莉.費博(Polly Faber),圖:海莉葉.哈伯戴(Harriet Hobday),劉清彥譯,青林國際出版,350元
推薦原因: 知 圖
適讀年齡:小學中、低年級(7-10歲)
夜晚主題總能引起孩子的興趣,他們好奇著自己沉睡時外頭世界發生的所有事:究竟那些不滅的燈火、不眠的人們、不休的機器,在做些什麼又為何忙碌呢?這本以夜間職業為主題的故事,解答了孩子的渴望與疑問。全書用充滿愛意與敬意的眼光,帶領孩子一一走訪燈火通明的工作現場,近距離了解值班醫護、媒體記者、貨運司機、交通維修等從業人員,是如何跨越白天與黑夜的界線,爭取時間堅守崗位,在太陽即將升起前為眾人打理好一切。生動的圖像與情節巧妙串連成一個有溫度的故事,把閱讀與生活經驗拉得更加開闊。【內容簡介➤】
●歡迎來我家!
世界上最奇妙的10種住家
Make Yourself at Home
文、圖:辛妮.托普(Signe Torp),黃茉莉譯,上誼文化,380元
推薦原因: 知 趣 圖
適讀年齡:小學中、高年級(9-12歲)
10個分布世界各地的小朋友,用親切的第一人稱導覽自己家:就地取材的北極冰屋、錯縱深入的地下洞穴、房間多到數不清的古堡,以及彷如搖籃的狹長運河船……,每一家的建材格局景觀動線都大大不同,讓人好想親自去住一晚體驗看看。作者非常用心呈現資料,不僅知識完備易讀,圖像更如同畫冊般生動繽紛,用全幅拉頁大器展示房舍裡裡外外的人物與擺設細節,把遠端生活完整拉到讀者眼前,讀起來過癮極了。【內容簡介➤】
●小雞逃跑記
ひよこは にげます
文、圖:五味太郎,游珮芸譯,信誼基金出版,220元
推薦原因: 趣 文 圖
適讀年齡:0-3歲
小雞們離家逃跑了,邁開細細小小的腳ㄚ子,在外頭繞了好大一圈,最後又投回父母懷抱。看似簡單卻意味深長的結局,精準表達出幼兒想證明自己長大的微妙心理,他們彷彿是為了歸來而一次次逃跑,也知道爸媽眼光其實如影隨形,所以安然享受這看似遊戲卻也驚險萬分的過程。年近八旬的五味太郎果然薑是老的辣,信手拈來即是經典,用不輟創作告訴我們,一本好的幼幼書就該如此:視覺焦點集中,核心概念清楚,並極度靠近孩子的心,因此經得起時空考驗,吸引一代又一代的新讀者。【內容簡介➤】
●無事的守護神
Patron Saints of Nothing
蘭迪.里貝(Randy Ribay)著,朱崇旻譯,博識圖書出版,360元
推薦原因: 文
適讀年齡:高中職(16-18歲)
得知同齡表弟在家鄉菲律賓被槍殺的消息,17歲的傑伊決定從美國飛回去,踏上那片與他血緣相近卻不甚熟悉的土地,去悼憐來不及茁壯的青春,並追尋死因背後種種的謎題。透過回溯兩人之前的來往通信,情節逐步開展,一步步施展張力,文化與種族衝擊迎面而來,更擴及菲律賓現今強腕掃毒政策所延伸的維安手段及警察暴力議題。讀者們拾著這些緊密交織的敘事線索與元素,慢慢鬆動原先預設的觀點,直抵故事高潮核心,在文字裡尋得救贖與慈悲,擁抱真相繼續走下去。【內容簡介➤】
●我想聽見你的聲音
The Dog Who Lost His Bark
歐因.柯弗(Eoin Colfer)著,P. J. 林區(P.J. Lynch)繪,趙永芬譯,小麥田出版,280元
推薦原因: 文 圖
適讀年齡:小學高年級、國中(11-15歲)
一隻不出聲的小狗,一個面臨父母離異的男孩,心中各有難以言說的焦慮及困惑,想被傾聽及陪伴,卻害怕遭受再一次的遺棄傷害。在彼此溫暖支持下,兩顆渴望的心靈找回久違的勇氣,想讓大家聽見他們的聲音……。短巧又動人的一本小說,作者在有限篇幅裡施展寫作技巧,文章段落簡單清晰,卻細膩描寫出人與寵物的複雜情感,純熟布局層次並收束故事。筆觸溫柔的黑白插圖,為文字適度添加氣氛想像,吸引讀者一步步投入故事裡,全然感受角色的內在外在處境。【內容簡介➤】
知識性.趣味性.文學性.圖像表現.創意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