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短評》#341 刺激味蕾與情感的極品好書懶人包
●祝福的意思
等路台文版
洪明道著,九歌文化,320元
推薦原因: 文 獨
文學獎得獎作品的台語文譯寫與新編版,由作者還原華文版作品已明顯在場的台語口氣和台文典故,還附上台語有聲書,讓閱讀跨媒介語言,也多方進擊、實驗台文書寫的可能。小說作品描寫的主題、人物、俗常景致、有諸多內涵都是隔著語言如隔山,但讀來更深的體悟就在於,這些涵納台語的容器一直都在,而非台語使之存在。【內容簡介➤】
●裴社長廚房手記
名菜復刻及大廚祕方,還有父子記憶中的家常滋味
裴偉著,鏡文學,600元
推薦原因: 實
從家常小菜到名廚祕方、在地小吃到中外大菜、一人獨食到親友共食,整本書以流暢的文字與分享的口氣,寫就的不只是味覺的饗宴,也是情感的盛會。而讓這部作品稍微不同於其他製作亦十分精良、內容獨到的食譜或烹飪書的地方,在於寫作與記錄的起點:跨越三代父子間的連結。食物傳達的不只是基本的身體需求或文化品味,每道菜色背後都隱隱帶著濃厚的情感。【內容簡介➤】
●全魚解構與料理
採購、分切、熟成、醃製,從魚肉、魚鱗到內臟,天才主廚完整分解與利用一條魚的烹飪新思維,探究魚類料理與飲食的真價值
The Whole Fish Cookbook: New Ways to Cook, Eat and Think
喬許.尼蘭德(Josh Niland)著,林潔盈譯,積木文化,1280元
推薦原因: 設 實
相信許多喜歡烹飪的朋友都曾提到自己不敢殺魚(當然不敢殺的還有許多活體動物),但這本書近乎生物學式的知識呈現,對各種類肉食魚的細緻解剖、醃製、烹調提供高度實用的說明指引,或許能讓讀者對於「殺」的恐懼轉換為「敬」的珍惜與自省。書中收錄的魚類與烹調方式主要是西式魚類料理為主,也因此對以往嘗過的魚類菜色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內容簡介➤】
●咖啡帝國
勞動、剝削與資本主義,一部全球貿易下的咖啡上癮史
Coffeeland: One Man's Dark Empire and the Making of Our Favorite Drug
奧古斯丁.塞奇威克(Augustine Sedgewick)著,盧相如譯,臺灣商務出版,620元
推薦原因: 知 議 樂
咖啡與全球化貿易的關係今日已廣為人所知。本書則選擇講述一個英國商人如何一步步在薩爾瓦多建立咖啡王國的故事。作者妙筆生花,描繪了19世紀晚期至20世紀上半葉,英國工業城市的經營管理之術如何隨著人遠渡重洋,在中美洲重新落地,轉化而生根。故事說著咖啡從作物變成量產商品的千絲萬縷,也勾勒出一個人,亦是一個家族在異國奮鬥發展的足跡。【內容簡介➤】
●廣告與它們的產地
東京廣告人的台日廣告觀察筆記
東京碎片(uedada)著,歐兆苓譯,大塊文化,450元
推薦原因: 思 議 樂
與其說這是本廣告案例集,不如說它是以廣告為對象的文化比較研究。隱藏在生活化敍事背後的剖析論說,基底是作者自身的廣告從業經驗,銳利洞察力加乘,然後以廣告閱聽者的角度,穿梭於廣告、產品、時光之流、地域差異、乃至各種名哏之間,在那些被掩蓋於數十秒目不暇給的嬉笑鬧罵聲光效果中,輕鬆煉製出背後的核心。除了激發創意的指南功能,也讓讀者一邊拍案叫絕,一邊看穿廣告,登上消費社會的制高點。【內容簡介➤】
●神婆的歡喜生活
Pyone Yue Le kandaw khandaw Mupar Ye Yue Le Kandaw Khandaw Mupar
努努伊.茵瓦(Nu Nu Yi Innwa)著,罕麗姝譯,時報出版,350元
推薦原因: 文 樂 獨
1994年出版的緬甸文學經典,融合神話信仰與性傾向議題,將傳統廟會中棲息的跨性別生靈、與深植習俗文化的經濟模式做了精彩紀錄。小說描寫「當崩」信仰活動中的形色人物,核心人物神婆的姿態、衣著、舞蹈、習性、愛恨、危難都鮮活浮在紙上。對於緬甸不甚熟悉的台灣讀者,打開此書有如打開一道窗,眼前鋪展的是色彩斑斕的故事,與生命最本質的樣態。【內容簡介➤】
●如蝶翩翩1、2
나빌레라 1
原作:HUN(최종훈),漫畫:JIMMY,台灣角川,380元
推薦原因: 樂
這是一部療癒又帶著深層意味的作品。漫畫作為媒材,正呼應了如此一個樸實又夢幻的故事。全彩的印刷也提供了較一般漫畫更佳的閱讀體驗。實現夢想的掙扎與美好,提醒我們回觀自己的生活內涵,也映照出(韓國)社會對於老年人乃至老人生活的期待。而這些映像又折射成對於「老人」看法與態度的反省。【如蝶翩翩1:內容簡介➤】【如蝶翩翩2:內容簡介➤】
●我跌的坑中神確實存在
私のジャンルに「神」がいます
真田つづる著,黛西譯,台灣角川,300元
推薦原因: 樂 獨
以日本同人誌次文化的「二次創作」(二創)為主題的民族誌學式漫畫,對於這一特定的創作方式、生態、作品都有細緻刻畫,但漫畫更凸顯的是創作的心靈。因在他人影子下創作發生的各種情緒與自我衝突,外顯的嫉妒、親現、恐懼等狀態,是創作的附屬品?還是主旋律?透過這一情感主題,讓二創的世界有了充滿人性的描繪。【內容簡介➤】
●兩封合格通知書
졸업
尹異形(윤이형)著,陳聖薇譯,麥田出版,299元
推薦原因: 議 樂 益
在近未來的韓國,一個19歲少女收到兩封合格通知,一封是給腦子的、一封是給卵子的。前者代表個人自由與智識的理想追求,後者則是工具化的身體與保證的財富生活。那麼,要上大學?還是生小孩?社會與眾親友已有了答案,但是少女本人(也是讀者你我)呢?從這樣聰明精彩的設定發展小說敘事,其中對當今社會價值的的寫實批判一點都不科幻不虛構,是韓國近幾年女性主義批判書寫中的一部佳作。【內容簡介➤】
●香港現形記
傘下的人著,一人出版社,365元
推薦原因: 議 益
延續前作《我們的最後進化》記錄了雨傘運動以來香港人的抗爭行動,此書是新一階段的沉澱與反省。將編輯主軸拉向自由的「表達」、「記錄」與「傳承」,以各方人士的文字篇章討論了《國安法》對於自由的箝制與人們的應對之道。對於街頭之外的事件(如醫護、六四紀念、蘋果日報)也有深刻討論與時代迴響。【內容簡介➤】
知識性.設計感.批判性.思想性.議題性.實用性.文學性. 閱讀樂趣.獨特性.公益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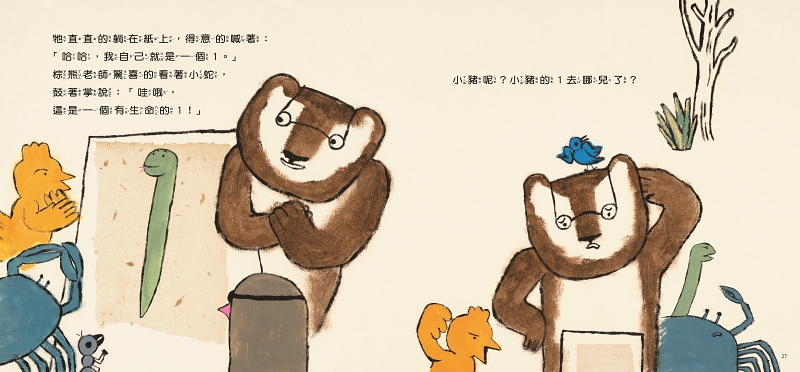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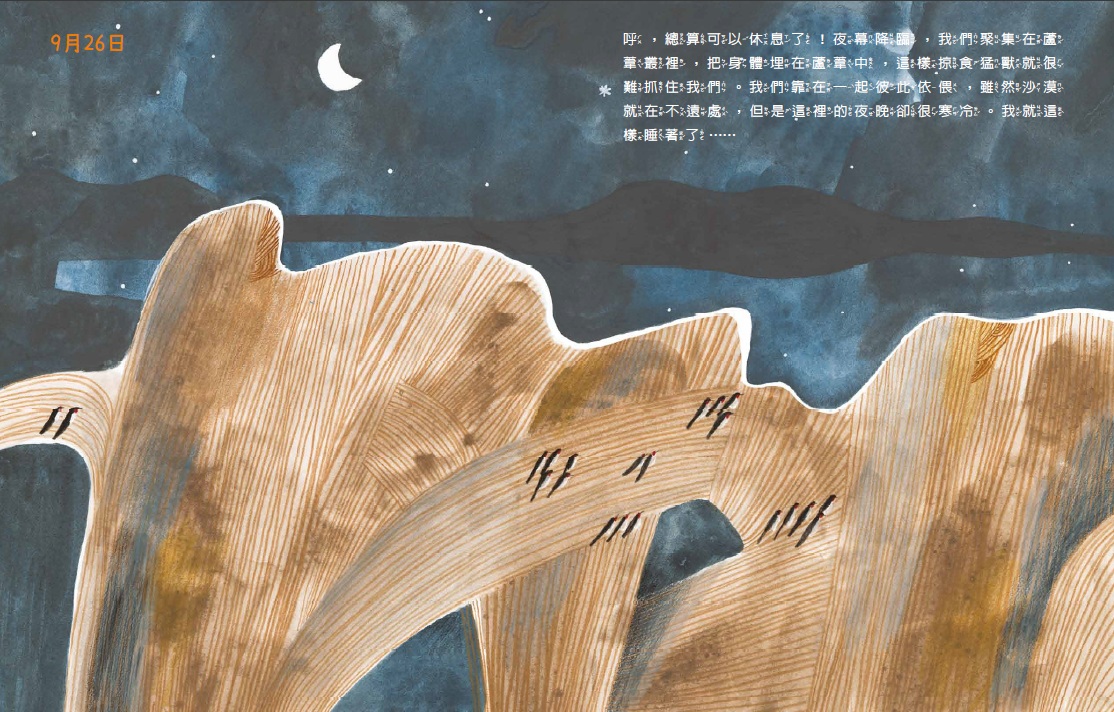


年度論壇 I》面對疫情,內容產業超進化,現實這魔王,打倒它就是了:葉美瑤vs洪凱西
2021年Openbook好書獎將於12/1揭曉,今年的前導活動主題設定為「閱讀未來式」,11/3第一場就邀請到雲門舞集副執行總監洪凱西與新經典文化總編輯葉美瑤為先發主講,暢談疫情肆虐近兩年的雲端經驗與內容產業的進化。本活動並首度於youtube和FB同步直播,希望與現場及在線收看的朋友,一起面對當前和未來的各種可能性。
■花兩、三年創作的作品,該怎麼辦?
2021年對台灣社會最大的衝擊當屬因疫情緊繃、進入三級警戒所造成的生活型態劇變。當各行各業都因疫情被迫調整變動,實體活動轉型線上成為文化界最普遍的因應策略。洪凱西形容表演藝術(尤其是劇場)是無法大量生產的手工業,每場演出都是人力所堆積,產業性質強調live的現場性、地域性,演出的每一刻都獨一無二,也因此疫情對表演藝術圈來說,就展現了類比與數位世界很大的鴻溝。
她說:「很多人會覺得,表演藝術『現場』是無可取代的,透過螢幕都不算數、都走味。雖然鴻溝是時代演進下必然的結果,但疫情激化、加劇了它的發展。」
她舉音樂圈為例,2000年左右,數位浪潮對音樂出版業造成了很大的震盪與爭論,「實體被取代了、夕陽產業」的說法也開始出現。「或許電子書出現時,出版業也曾有過同樣的討論,但我們看到實體書沒有被取代、閱讀並沒有消失,而音樂工業也依然存在(只是形式產生變化)。劇場界也正在經歷這個階段。」
相較於國際社會,台灣過去一年很幸運,國外劇場去年3、4月開始關閉了很長一段時間,台灣則相對安全。今年台灣因疫情衝擊關閉場館,表演藝術圈一片恐慌,因為好不容易花兩三年創作的作品,沒有地方發表、沒有演出、沒有觀眾,也沒有收益。洪凱西坦言,直到兩個月前她都還很焦慮。
但劇場的產品特性,是可以跨領域吸納各種養分、產生新的內容與展演形式。洪凱西說:「我發現台灣人很厲害,這個月開始,我就看到很多迸發的新創意,越來越多參與式作品紅了起來,觀看性作品也有不少嘗試在線上發表。」
■《神不在的小鎮》,把自由廣場變成超大故事場景
由於觀察到群眾行為已逐漸產生改變,因此本次論壇洪凱西帶來幾則參與式案例,用以分析最近的劇場發展。首先是日前造成洗版風潮的話題劇作《神不在的小鎮》,兩廳院打造小城鎮實體演出(三維),整個自由廣場就是一個超大型故事場景。「有點像紐約的Sleep No More或是密室逃脫,觀眾可以跟著一個角色的故事線走(所以很多人都說跑得很累)。」
「觀眾也可以選擇上兩廳院的youtube頻道觀看直播影片(二維),會看到比較完整的故事。此外還有虛擬世界的角色扮演遊戲(四維),可以自設稱號上線玩,可以對話,也有共同體驗與虛擬社交性。」
《神不在的小鎮》3種維度、3個觀看角度,試圖讓群眾從不同視角體會網路時代下虛虛實實的人心。目前線上部分,兩廳院到11/30都開放民眾免費觀賞,四維虛擬遊戲空間體驗則是每晚7:30-10:30,有限定人數,要排隊進場。
由於洪凱西對最近的元宇宙充滿興趣,所以今年台北新藝術博覽會的NFT線上展廳也引起她的注意。跟《神不在的小鎮》一樣,進入這個虛擬會場可以選擇分身四處走動自行探索,點擊作品也會出現購買資訊。
■參與性與自主性,如何應用在劇場?
上述兩個案例,洪凱西主要思索其參與性與自主性,如何套用在劇場上,讓群眾更樂於親近表演藝術,但都需要投入鉅資。不過也有些方式門檻較低,是大家都容易做到的,例如安娜琪舞蹈劇場,就利用Gather Town的特性,同樣可以選擇分身,像闖關的概念,進去不同房間,點擊還可以看直播,某種程度結合了虛擬空間與現場表演。此外,Gather Town有很多工具可以共做,加上群眾在同一時間聚集在同一空間(人多才好玩),因此也具有劇場儀式性與社交性。
「Gather Town可以蓋很多東西,安娜琪一開始創立一個會議平台,蓋著蓋著就蓋出小鎮,已經很龐大了。比較知名的運用還有端傳媒,蓋了虛擬辦公室及展室。這是不用花大錢,用既有平台與工具,就能做出的線上體驗。」
洪凱西還舉了年輕團隊:明日和合製作所的作品。在所有場館關閉的時候,他們很快就在6月初產出了《和合快遞》--送演出到你家(所以觀眾『訂』的是藝術家)。
她說:「和合集結了25個藝術家,根據不同的屬性客製,每位20-30分鐘。像我訂的藝術家是算命師,透過IG直播跟你互動。他們善用了大家習慣的工具,做到不一樣的演出,有舞蹈、畫家、設計等,引起很大的迴響。」有了6月的成功經驗,和合發展出親子快遞,有故事、角色性的互動,或是很多不同形式的手作,讓親子可以一起在家觀看。
最後一個案例,洪凱西分享文化部台日交流計畫的Taiwan NOW,也是虛擬空間,有很多視覺藝術、電影、表演藝術作品,直到年底都在線上展出,其形式也非常值得參考。
■YouTube直播,2、3天內觀看紀錄破萬
雖然是不同產業,但葉美瑤感受出版業跟表演藝術圈面對疫情的難關如出一轍,且覺得現實並沒有讓自己變得更強,她只是想辦法活下來。她說:「所以我很高興聽到各種很炫的雲端經驗與不同的解決方法,反觀我的方式可能比較傳統,只是稍微在困境中做一點突破,都是簡單的例子。」
葉美瑤提及,2019年新經典第一次與3家小型出版社合作參加國際書展,就拿下展場設計銅牌獎,且創下3場幾乎是當年人潮最多的活動,因此決定2020年大張旗鼓再加碼。她說:「我們還把題目定作『過得還不錯的一年』,簡直是跟自己開了一個天大玩笑。2021年我們捲土重來,安排非常多有趣的活動,還搭上《Verse》雜誌和線上平台方格子,沒想到書展又停辦一年。」
當所有人為書展停辦各自不知所措時,原本是科技人的啟明出版社發行人林聖修,很不甘心地說:「我有技術,可以做線上書展,願意一起嗎?」於是在短短五、六天內,所有人爆肝式不眠不休,從張羅直播道具到最後終於完成上線。
葉美瑤說:「雖然都是現在大家用得很習慣了的工具,但當時那瞬間我們文科人光是組裝設備就很難,建檔也是我自己一筆一筆熬夜輸入,沒想到有些活動上youtube直播,兩三天內觀看紀錄就破萬,還有國際友人與日本作家跟我們連線。」
她表示,做這件事絕不是想逞英雄,只是不願讓所有心血又再度虛擲。至於有沒有賺錢?她笑稱:「當然沒有!因為線上書展無法讓讀者當場購書給作家簽名。但這件事沒有白費,後來也啟動了週三讀書會線上直播的契機。」
■直播節目,嘉惠全球閱聽大眾
同樣成為直播契機的,還有「村上春樹音樂會」。過去非常低調的村上春樹,這幾年相當與人為善,很願意出來拋頭露面,2018年Tokyo FM為他製作《村上Radio》,今年Tokyo FM慶祝開台50週年,又再度邀請村上舉辦音樂會,所有書迷都非常興奮,包括葉美瑤。
「我在國際書展累完後看到村上音樂會網路宣傳,有實體活動(在Tokyo FM Hall舉行),漂亮的卡司包括大西順子、小野Lisa,還有坂本龍一的女兒坂本美雨、鋼琴家山下洋輔等超強組合,海外也可以購票線上觀賞,從2/14情人節翌日無限暢看10天,只要台幣一千多元。」
「我當時一邊享受一邊思考:他到底做對了哪些事情?這些我將來可以參考嗎?當然舉辦這場活動想必所費不貲,但做為海外聽眾,我突然感受到疫情難得對我的好處,居然是用這麼便宜又方便的方式,接收到如此高品質的節目。」
■週三讀書會,邀來詹宏志,募資7天破百萬
這件事也啟發葉美瑤幫詹宏志的週三讀書會線上版募資的想像。1920年代,文協仕紳在台中除了辦學,也創立中央書局,做為吸收先進知識的沙龍。百年之後,詹宏志接任上善基金會董事長,中央書局老店重生、恢復沙龍傳統,詹宏志為此開辦12場週三讀書會,希望中部當地的年輕人來聽。
葉美瑤說:「聽過詹先生講書的人都知道非常精彩,且這次難得有12場,開出來又都是很經典的書單,所以我們抱著一個想錄下來的心情,讓喜歡詹先生演講的人都可以線上收看。」
但詹宏志的初衷,是希望讓讀者免費收看,所以葉美瑤想到利用募資方式,來幫助中央書局未來續辦一整年的講座,也就是後來新開的30場週三讀書會,現在進行到馬世芳,接下來是李明璁、顏擇雅、詹偉雄等人。
「用了村上春樹線上直播的概念,讀者報名後拿到密碼就可以收看。當時沒有想到的是,募資7天就破百萬(最後結案160萬),要不是詹先生覺得驚動太多社會資源,不希望再宣傳了,不然會有更多讀者加入。因為我後來才知道大家的資訊有落差,有些人則是還不適應線上模式——不過我想,現在大家應該都適應了。」
葉美瑤發現,許多美國作家也開始在線上分享書,包括上完媒體再把youtube連結放上臉書。她說:「疫情以來最大收穫是過去難得露臉的作家,通通在網路上看到了(有些需付費、有些免費)。我常半夜或凌晨起床看到睡著,這些都啟發我--世界一家,只要語言相通,資源都在線上。」
接著葉美瑤談到《十月終結戰》的出版。遭逢5月疫情緊張,很多地方不能去、書店不開了,通路也降低採購量。「這對出版社很致命,新書雖然跟劇場的現場性不一樣,可是宣傳也有所謂黃金期,在不知道疫情何時結束的情況下,無法宣傳,所印的書都會白費。」
■把書當門票:出版社、作者與獨立書店站在一起
10場說書活動讓葉美瑤對書倒背如流,也確實帶動了業績。「大家都很高興,常常當天講完,書店就賣了5-10本,但重要的不是業績有多了不起,而是原來這招是可行的——過去不知道可以用google meet跟讀者互動的書店,之後就能自己找讀者玩了。也有很多縣市發現只要支持一點錢,就可以讓書店跟讀者交流,後來就遍地開花了。」
葉美瑤坦言,實體活動比較累但有其價值,尤其線上活動沒有「現場」可以翻書、買書,所以是目前遇到的核心問題。不過她後來從強納森.法蘭岑(Jonathan Franzen)身上學到的招數,或許可以幫助業界解決這個問題。
法蘭岑是個傳統熱愛閱讀的人,很討厭網路、社群與亞馬遜等數位科技。但在疫情下,他知道書店與出版業需要他的支持,因此他排出與7位作家的對談,並跟許多獨立書店合作,作法是「把書當門票」,讀者只要跟書店買書,就可參加實體或線上活動,這是台灣可以借鏡的地方。
■Bookshop.org實體獨立書店成立網店,與亞馬遜爭市占
幫助獨立書店並不是濫情,對讀者、對出版社而言,都是很重要的一環。Bookshop.org創辦人Andy Hunter曾推算過,2020年亞馬遜的銷售占書市50-60%,到了2025年,預估將占有美國80%圖書市場。因此他去年初募資架設Bookshop.org,任何獨立書店都可以在上面擁有自己的頁面,得以跟亞馬遜競爭。讀者也獲益,因為疫情下亞馬遜把書視為「不重要物資」,有時出貨慢到一週,在Bookshop.org,讀者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書店,而且三天內發貨。
Bookshop.org在疫情下逆勢成長,一年下來幫獨立書店增加了150萬美金收入。葉美瑤說:「書店自己賣書當然利潤比較高,讀者上這裡買也沒有比較便宜,但書店可以省去倉儲與寄貨,讀者也藉此支持了獨立書店存在的價值。」
bookshop.org還有很厲害的一招。國外書評(包括《紐約時報》)底下購書連結到亞馬遜,可獲得亞馬遜4.5%回饋,bookshop.org的話則回饋10%,這件事讓大家開始動手改文章下面的連結。去年11月,擁有更多老書店、上網率也更差的英國拜託Andy Hunter開Bookshop.org,同樣幫英國增加非常多營收。今年5月,據說已拓展到西班牙(但難題是西班牙沒有適合的發貨商)。
葉美瑤說:「總而言之,疫情下最重要的環節是大家的行為都改成線上了。我們始終想像閱讀的多樣化,很需要實體書店及大眾的支持,關於這點我覺得有解,但誰來做?怎麼做?也希望很快會有答案。」
■習慣線上活動的人,是藝文圈可開發的新族群
從兩位主講人的分享,可以感覺出面對疫情挑戰,劇場比較傾向將內容線上化,是一種轉型,而出版方面的案例,則是聚焦在行銷的線上化。產業面對考驗,從業者的工作心態或行為模式,是否有必要調整或改變?
對此,洪凱西表示自己感到既樂觀又悲觀,她認為迎接未來,首要是放棄對立。「我覺得現場性已經不是唯一實體,尤其VR開始普及,元宇宙(metaverse)絕對會來到,且近在眼前。所有事情會有虛擬與實體兩個世界,虛擬世界裡還是有朋友、有活動、有商業,跟所處的現實世界一樣,甚至更沒有界線。它仍是你的現場,它依舊有沉浸的臨場感來『打破第四道牆』,這是一定會發生的趨勢,不用去抗拒,擁抱它就好。」
不過眼前線上、數位產品的成本非常高,表演藝術所做的各種嘗試所得收益都不足以cover。此外,發展過程勢必有些人無法跟上,但洪凱西也樂觀認為,內容為王的產業,好作品變換什麼形式都能運作,在科技之下會更加明顯。
「喜歡進劇場的人,不喜歡到線上,反之習慣線上活動的人,你提供這樣的產品線,反而有機會開啟接觸,過去我們原本沒有這個機會的。」書也是如此,美國Tik Tok盛行,連帶引領了Book Tok風潮,就讓大家嘖嘖稱奇。「所以不同的接觸管道跟形式,不見得會互相取代,我反而樂觀認為是新市場、新領地。」
葉美瑤則表示,她兩個年輕的孩子,常能快速反應傳統宣傳方式是否有效,例如他們會說「你臉書寫那麼長,我沒興趣」,但他們會願意聽信他所相信的人寫的文章,就像前述所說,分潤給介紹書的KOL,這比亞馬遜用大數據告訴你「你可能會對這些書感興趣」來得有效多,她認為推薦或說服的管道已經改變。
她也看重現場的價值。「老實說我在現場收穫最多,線上經驗相形破碎。可是很多人對現場有抗性,我們辦很多活動,即便對方覺得好棒還謝謝你,但只要知道有線上,就不會來現場。這件事一直在發生,主辦者要開始思考,你必須在現場追加什麼?為他開一瓶酒嗎?(笑)或是創造哪些現場才有的互動機會,才能吸引群眾?」
■Q&A
以下是開放現場及線上觀眾的提問,邀請兩位主講人作答。
➤電子書在疫情期間銷售有無提升?
葉美瑤:有的,連出版社都很認真趕製電子書。疫情期間我們就做了好幾次與電子書上市同步的線上活動,聽眾聽完可以馬上購買,效果非常直接。
➤針對現場表演,舞者若沒有觀眾會有差異性的影響嗎?
洪凱西:表演者在台上可以感受到現場觀眾的熱情,觀眾自己也可以感受到整場的氛圍。我們上週剛在池上完成演出,在現場,你可以感覺風、聽見鳥、看到雲飛過來,以及遠山與景色的變換。
但我還是覺得現場跟虛擬都可以看。在疫情期間,我們打破地域性,看到很多平常沒機會看的。台灣的網路穿透力很強,透過數位管道,可以接觸到更多人、幾年才去一次的偏鄉,從推廣角度是非常好的發展。
➤線上活動技術與資金都需要更大規模支援,會不會有大者恆大的排擠效應?
葉美瑤:不至於,因為工具越來越便宜。年輕時我在電視製作公司工作過,那時機器很大很重,現在則是越來越方便了。我們做線上書展時,雖然選了較貴的器材,但其實也有平價的。我覺得真正重點是設計跟策畫安排,器材的話,現在連手機都可以直播,不是大問題。雖然有更多人力可以集思廣益、更多作家可以連番上陣,贏面確實可能比較大,但我仍然覺得小有小的價值。
洪凱西:昨天我也在思考這個問題,就是科技經費特別高。不過在表演藝術界,我樂觀覺得應該不會大者恆大。現在工具越來越多,比較高端的工具像VR,成本也在慢慢降低,對比兩年前已經差很多,還會再往下降。比較不一樣的是,表演藝術內容跟形式一直不斷變化、進化,所以可以用很簡單的方式,做出有力的、感動人心的作品。工具百百種的時候,端看怎麼利用工具來創作,去進到觀眾心裡,所以我認為不太會有這問題。
葉美瑤:像《魷魚遊戲》9集製作費才相當於美國一部《柏捷頓家族》(Bridgerton)一集的費用,但它所創造出來的價值大家已經看到了。
➤BTS線上演唱真的很精采,1200票價還可以看重播,表演者結尾都感覺超累超崩潰。
洪凱西:過去一年我研究很多國外付費觀看案例,都沒有人理我——台灣資訊太發達便利,大家覺得選擇太多,所以不相信有人會付費。但好的作品大家還是願意花錢的,不過重點要能『回看』。我們不能要求全世界觀眾都像美瑤一樣半夜兩點爬起來看60分鐘直播。至於回放多久?如何讓作品保持現場性與特定性?則是可以討論的。我想每種工具都有小啟發,教我們怎麼做,像這次我們的池上作品有錄下來,11月底要做線上付費的播映,後來我們選擇回放期限是20小時。
➤疫情限制,多了線上觀賞,實體表演招攬觀眾是否難度增加?
洪凱西:為什麼有人只喜歡看現場演出?那是因為螢幕裡的視角是受鏡頭控制的,受限於別人提供你看什麼,但現場則可以自己決定我要看什麼,這點很不一樣,建構故事的經驗也會很不同,這是實體演出的迷人之處。在池上,包括彩排我看了4次,雖然是同樣的結構,但你會改變焦點,就有新發現,我反而覺得實體加虛擬,會慢慢養成更廣大的觀眾群。
➤市場增加很多疫情文學或電影、戲劇,作者和學者都把疫下社會視為亟需關注的議題和現象,包括心靈、社會等各種描寫,編輯要如何評估現象化之下,單一作品的好壞?
葉美瑤:我前陣子聽podcast,《紐約客》編輯就曾回答過這個問題,認為這並不是好的現象。一窩蜂而來的書,不會是《紐約客》最想選的,讀者也不見得愛看。我們現在去看《愛在瘟疫蔓延時》等作品,並不是因為講的是瘟疫,而是別的原因,這個題材並沒有特別的保證。我會出《十月終結戰》,是為了警示,不是為了對照疫情。我不會特別去選這樣的題材,所以這題對我不會是個難題。
➤BTS演唱會如果願意付更多錢,可以同時看5個攝影機畫面,觀眾就是自己的導播。
洪凱西:去年一個線上藝術節,有作品是人在家裡演出,但擺了很多攝影機,這是我看到多視角的開頭。多視角有趣的正是「讓觀眾自己選擇」,例如花100元可以選3個,200元可以全選等,給我們很多啟發。雲門也在討論是否要開始做5G的布局。
葉美瑤:BTS真的是一個特殊的團,你可能特別喜歡某個成員,所以願意為他前面那台攝影機加錢。
➤推薦書
洪凱西:《十月終結戰》很好看,我可以一頁接著一頁,一天之內看完。此外推薦今年我覺得很好看的《地方設計:萃取土地魅力、挖掘地方價值,日本頂尖設計團隊公開操作秘訣,打造全新感動經濟!》,談到的創意每一頁都讓我腦袋小宇宙爆炸,非常精彩。
葉美瑤:我想推薦最近過世的陳柔縉老師的書,她有非常多作品,史哲類現在大家也很愛讀,今年真的是特別適合推薦她的書的一年。●
➤年度論壇完整影片觀賞
▇2021Openbook好書獎
▇來看看超過350位讀者的年度好書吧!
▇得獎好書,各大網路與實體書店熱烈推廣中
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贊助:
合作夥伴: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