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隨身聽S5EP9》文膽煉成術,國家元首的政治與思考高度 ft.東美總編李靜宜、允晨發行人廖志峰
政治人物的發言稿撰稿人(文膽)向來是相當神祕的工作,隱身在幕僚群中,發言稿不僅需要說明政策,更要展現氣度和高度。本集相當難得地邀請到曾任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文膽的東美出版總編輯、翻譯家李靜宜,也邀請到具有撰寫文稿經驗,更編纂過多部言論集與人物傳記的允晨文化發行人廖志峰。本集節目不僅聚焦文膽,也思考同樣隱身文字背後的編輯,兩種職業的異與同,讀者千萬別錯過了。
【精彩內容摘錄】
➤文膽,文膽,是為文嘗膽,還是為文有膽?
廖志峰:文膽、文膽,為文嘗膽。大家知道「嘗膽」是很苦的事,有點像命題作文,老闆給你一個題目、方向,我們要把它發揮、組合出來,很難超越老闆給的範疇,又得思考如何將意念傳遞出來,如果讓它更清楚、立體。
作家跟編輯的訓練中,對文字都有一定的專業與專精。文字是要修練的,做為政治性的公告,訴求要清楚,要顧及政治人物的需求和受眾的期待,文膽的角色要居中完成,是類似仲介的角色。
李靜宜:我覺得(文膽)跟作家本身的身分,有一點點不太一樣。多半的作家可以為所欲為,想寫什麼就寫什麼;但是替別人寫稿子,必須以另一方的眼光、高度、語彙,用一個有邏輯的方式呈現出來。在寫作的過程,需要考慮的因素很多,不只命題本身。
儘管我們從小寫了很多命題的作文,但這些命題的作文多半在表達個人的意思,但是為政治人物寫東西時,文膽要表達的其實是他的「意志」,不管是他對政策的闡述,或對特定政治環境的情感投射。你必須先了解「他究竟要講給誰聽」、「他想要表達什麼」,從這些問題反推,才能具體思考文稿的內容。
在我過往的經驗中,其實花最多力氣的倒不是真正動手去寫這件事,而是在構思的過程中,如何在龐雜的素材中,進行挑選、組合。並不能說需要具備豐富的經驗,但對於整個所處的環境,以及為他撰寫文稿的這個對象,必須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才能做到。
➤總統看過的書,文膽都要看?
李靜宜:不同政治人物思考的方式不一樣,應對事物的方式也不同,甚至想打動的對象也不一樣,撰寫文稿時要將這些因素都考慮進去,我覺得很難。國外有很多專業寫手,可以幫不同的總統寫稿子,他們有些人可以做到這樣,但就我來說,是很困難的事。因為終究要對一個人有深刻的了解與認識,長時間很近距離的觀察,才有辦法完成。
比方說像登輝先生接見賓客時,我其實不太愛去,不過重要賓客我大多會到場,儘管我有時不進去,但幾乎他所有會客的紀要、談話紀錄,我全部都要閱讀。因為需要知道他最近在想什麼、關注怎樣的問題,將他盡其所思所想放進文稿中,才能貼近他的想法。
主持人:妳曾提到登輝先生是一位非常愛閱讀的老闆,所以他看的書妳也要跟著看?
李靜宜:對,他最近讀什麼書,我都要盡量把書找來看,所以我經常說,有一位愛讀書的老闆,其實是件非常可怕的事,因為你必須不停地追趕他的速度,真的非常可怕。
➤一部好的言論集,能經過時間的考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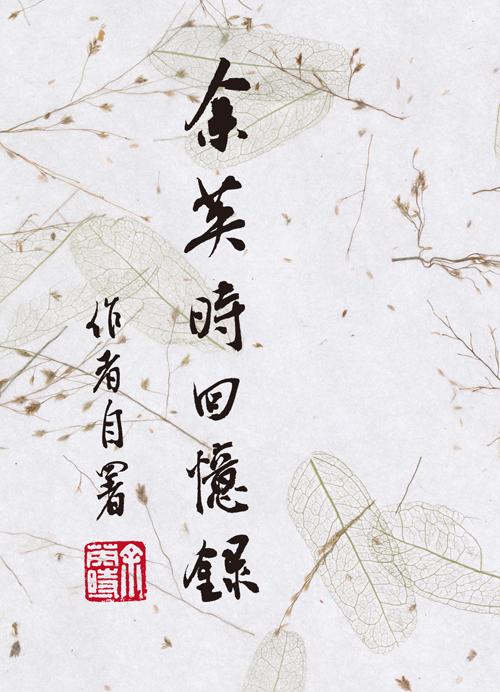 廖志峰:無論撰寫文稿或出版書籍,首先要對工作的對象懷抱情感。以編輯來說,需要先協助作者讓文稿眉目清楚,例如允晨出版的《余英時回憶錄》,一開始是第三人稱的口述,後來變成第一人稱撰述的自傳,中間當然經過很長時間的溝通。
廖志峰:無論撰寫文稿或出版書籍,首先要對工作的對象懷抱情感。以編輯來說,需要先協助作者讓文稿眉目清楚,例如允晨出版的《余英時回憶錄》,一開始是第三人稱的口述,後來變成第一人稱撰述的自傳,中間當然經過很長時間的溝通。
以文膽而言,老闆可能只列幾個重點,你必須像在編書、寫文案一樣,要能合理的謀篇,又能感動人,若要使讀者閱讀或聆聽後對生命有更深層的思索,那文案也必須做對方向。
順便補充一下,我突然想到,以前曾編過李前總統的言論集,其中的文章有多少篇是靜宜寫的?猜想應該為數不少。我認為一部好的言論集,如果本身學養俱足,那文章是經得起考驗的。講述者本身對時事、對政治、對世界的看法,在文章中是清晰可見的,我認為好的文膽,就是要讓這些文章能清楚、深刻,賦予生命力。
➤編輯與文膽,隱身文字後的兩種職業
李靜宜:「文膽」跟「編輯」的角色,的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們都隱身文字之後,榮耀屬於作者。
主持人:問題是編輯的,榮耀是作者的。(笑)
李靜宜:通常我們手上會有很多素材,要從中間組合出邏輯,將它炒出一盤菜,抓出幾個亮點,標誌出文稿的重點——總要有一個可以做為標題的東西。跟書的文案一樣,究竟這本書為何出版?究竟想打動誰?抓出一兩句重點,或者一段話來打動他。即便是同一位作者或同一位政治人物,在不同的場合,也要需要講出不同的話,都必須先替他考慮到市場和言語的展現方式。這點,文膽跟編輯其實非常相像。
廖志峰:今天做一個文膽,平常就應該隨時吸收、準備,不管在哪一位政治人物身旁,他所關心的領域,你必須跟著關心,如果完全不關心或沒有興趣,那是做不好文膽工作的。這跟編輯很像,如果編輯對所選的書,對該主題、作者毫無興趣,我相信書出來的樣子,或書最終的情況一定很糟。「寫作」是很好的練習,第一是紀錄,其次是整理,第三是練習。
➤語言的輕重
李靜宜:一位政治人物,特別是「總統」的角色,表達一句話,必須具備一定的高度和力量。打動人的方式有很多種,在文氣和語句上,既使同一句話,使用不同的表述方式時,打動人的力量也是不一樣。
主持人:文膽必須不停衡量力道的輕重。
李靜宜:對!我運氣好一點,小時候受過很多演講的訓練,參加過很多演講比賽,我能用朗讀的方式,先將文稿唸出來。中文的寫作,因為是自己的母語,我們常常不太注意文法。但其實有時候文法是有影響的,比方一個句子著重動詞跟著重受詞,力道是不一樣的。
我經常要用很奇怪的方式解釋給別人聽:為什麼一定要選這個字,不能換一個方式說。這種事情發生一、兩次後,同僚也可以接受了,就是因為考量了朗讀的效果。
主持人:登輝先生也從善如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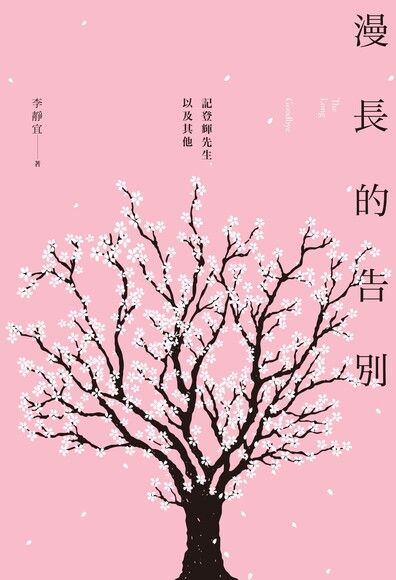
李靜宜:對,我覺得他基本上是從善如流的。還有一點,我其實也會注意到,因為每一個人講話時,都有不同的特性,像登輝先生因為國語不是主要使用的語言,所以有一些音可能沒有辦法唸得好,或者是發得不清楚,那些詞彙就要盡量避開。這都是寫作的過程中要注意的。
我認為最重要,還是回到剛剛志峰說的,撰寫文稿很重視邏輯的梳理。文章希望打動人,一定要講道理,讓人理解演說者的內容。這樣的角色,其實跟我平常另一個工作「翻譯」的功能也很接近。
➤文字的力量來自閱讀,文學尤是
李靜宜:相信文字的力量,文字的力量來自閱讀。儘管很多人認為政治人物的撰稿人,或許比較需要知道的是政治情勢,但我覺得之所以能寫這些東西,最重要的原因來自於大量閱讀的積累。閱讀的素養不是專業的東西,很多也來自於文學,文學帶給讀者想像力,文字之美的鑑賞力,也蘊含對很多人生的邏輯。我認為「閱讀」是有志於從事文字或文膽工作的人,十分需要重視的事情。
廖志峰:我在閱讀中得到豐厚的養分,它像洞穴,可以安穩地躲在裡頭。閱讀予人力量,如何展現這份力量呢?透過文字啊,不然還有什麼呢?所以我想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都需要閱讀,它是很重要的積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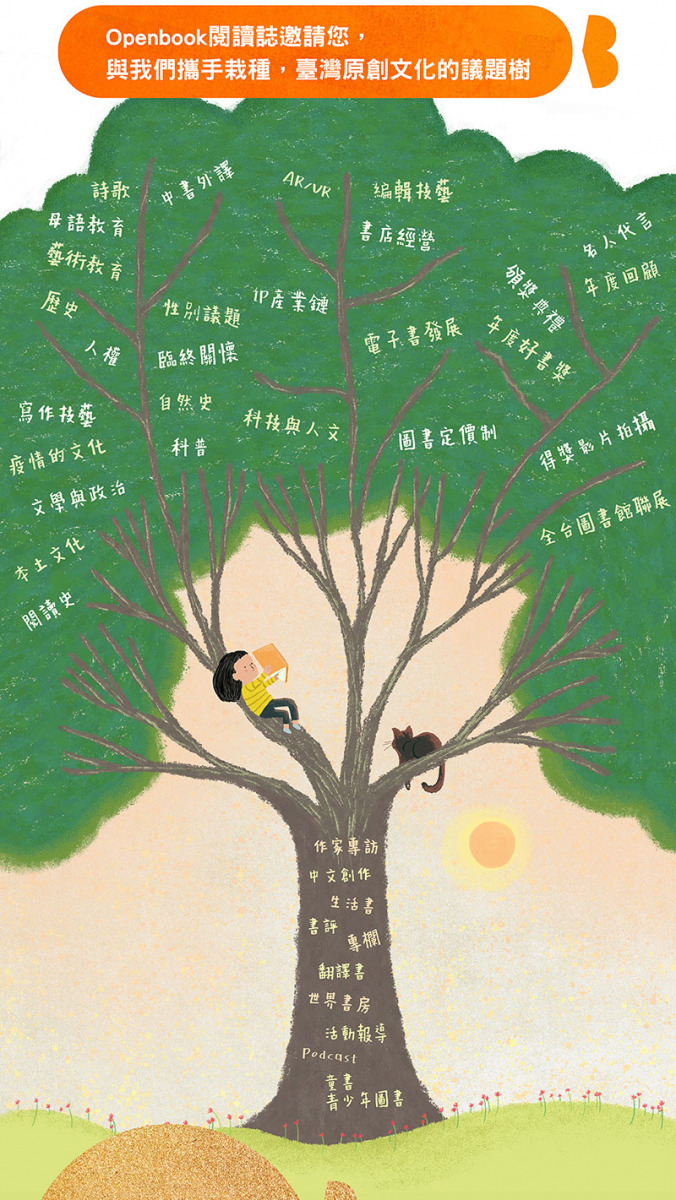
主持人:吳家恆,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畢業,英國愛丁堡大學音樂碩士,遊走媒體、出版、表演藝術多年,曾任職天下雜誌、時報出版、音樂時代、遠流出版、雲門舞集、臺中國家歌劇院。除了在大學授課,在臺中古典音樂台擔任主持人之外,也從事翻譯,譯有《心動之處》、《舒伯特的冬之旅》、《馬基維利》、《光影交舞石頭記》等書。
片頭、片尾音樂:微光古樂集The Gleam Ensemble Taiw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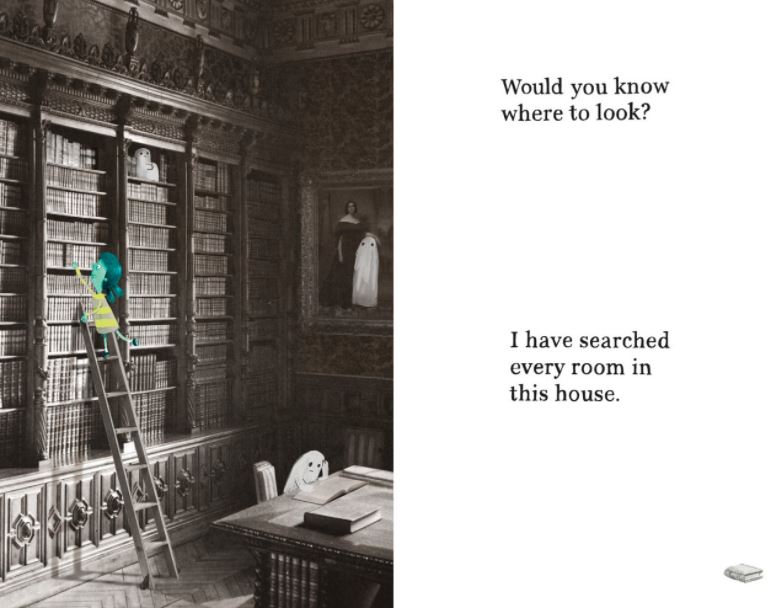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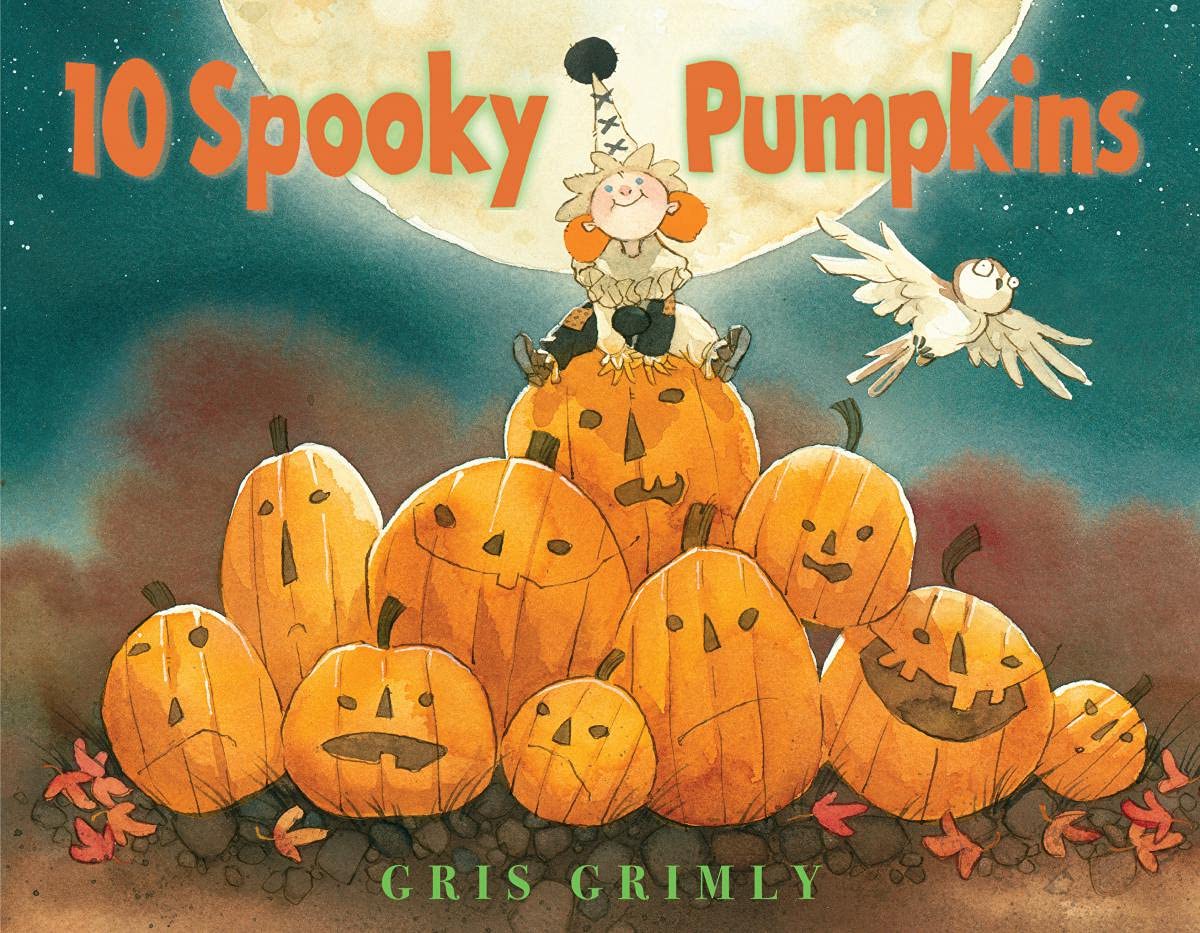 ■最後要介紹的繪本是Gris Grimly的《
■最後要介紹的繪本是Gris Grimly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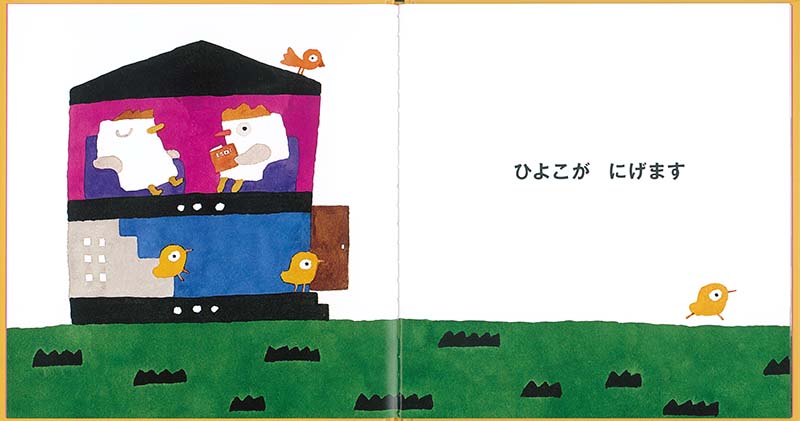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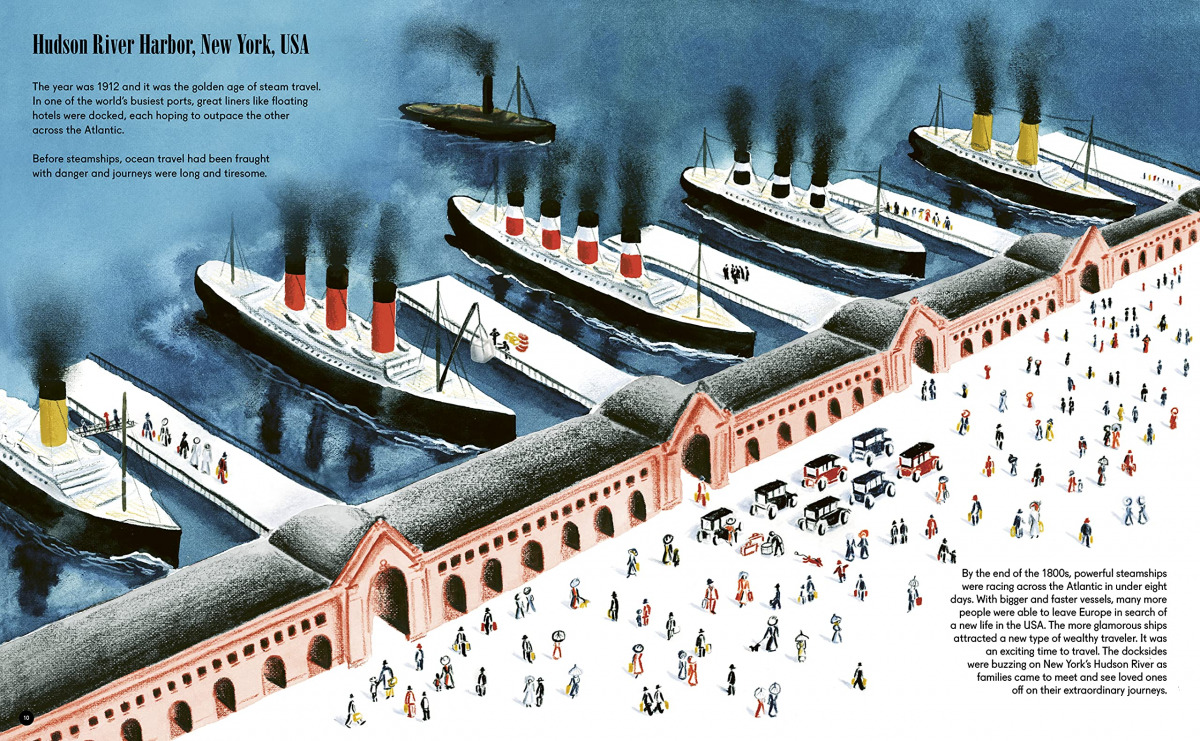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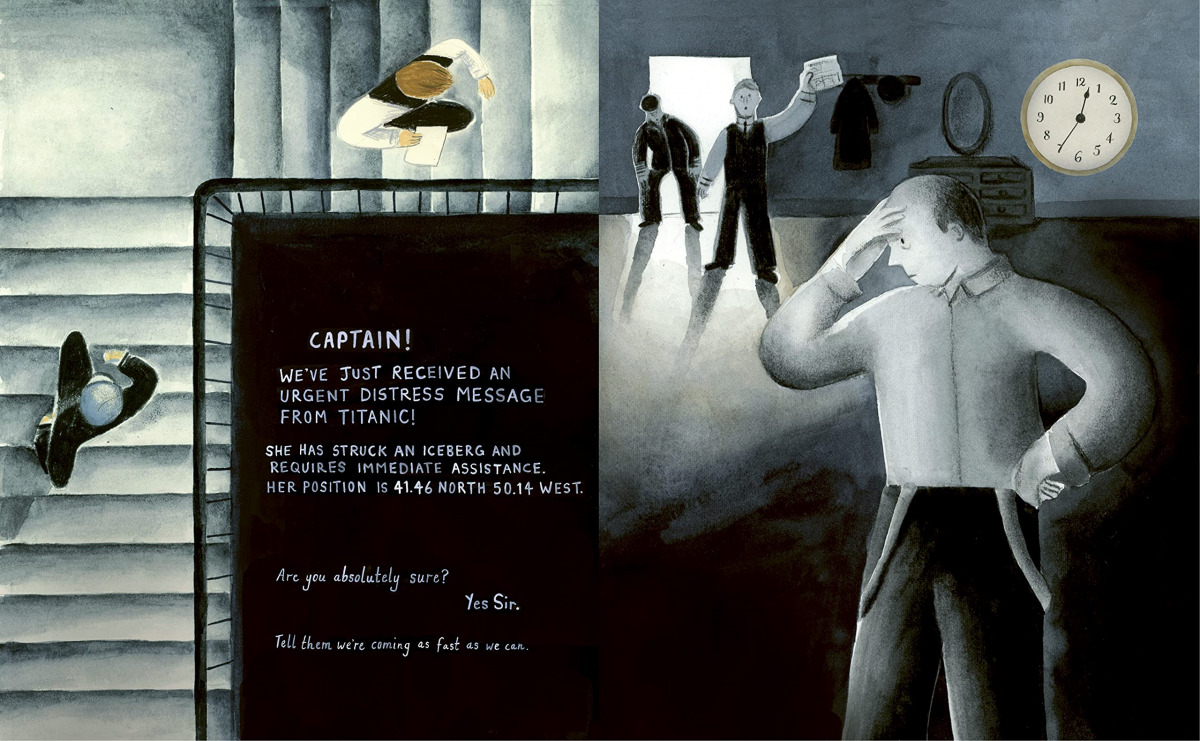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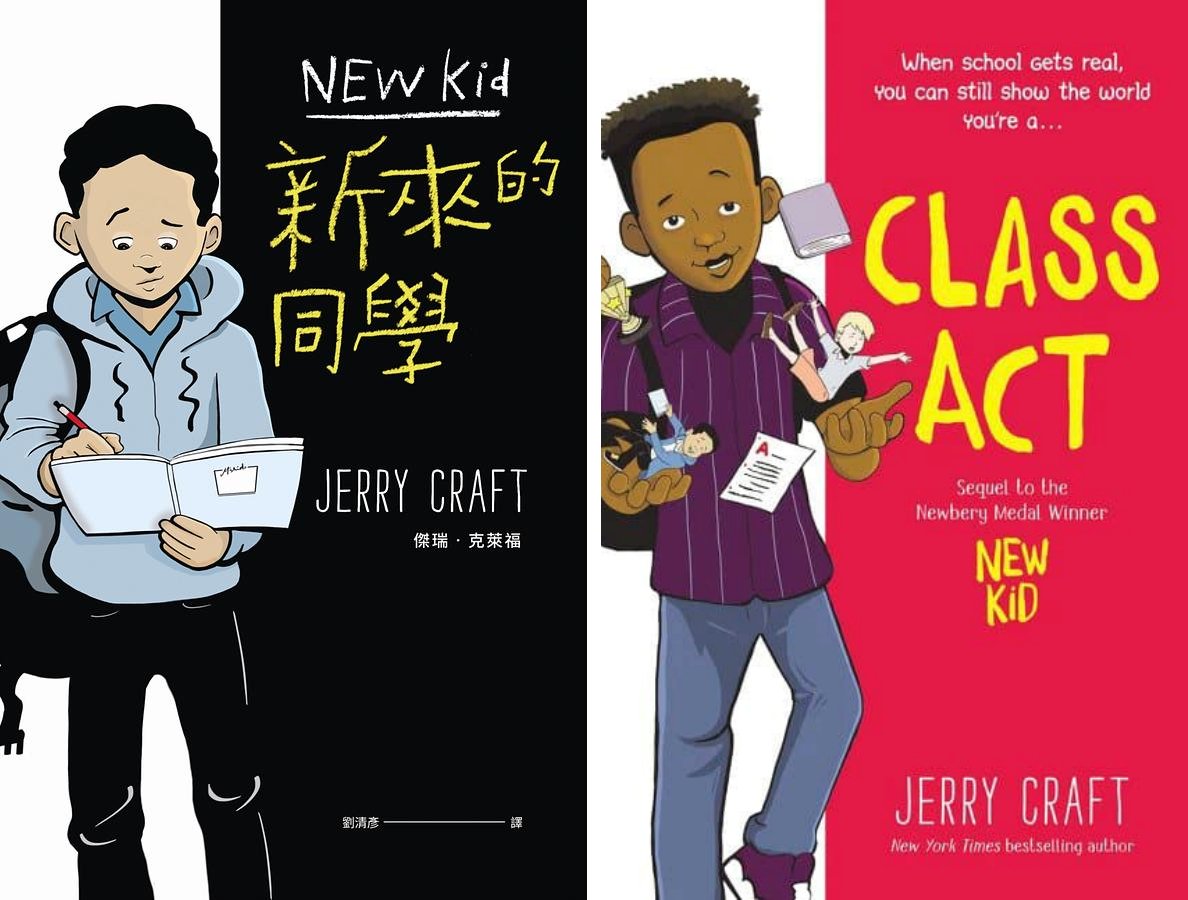
OB短評》#337 深入情感夾層的極品好書懶人包
●感情百物
張亦絢著,木馬文化,450元
推薦原因: 文 樂
本書有如替代容器,裝載了作者腦袋中與物件有關的百種奇思異想、理論辯證、情感記憶,精悍短篇中有著密度極高的思考與感受。以「感情」與「私物」為引,每個物件發展出來的文字極個人又超越個人,讀來多有共鳴又視角獨特,閱讀時經常發出「啊,我還真沒這樣想過!」的快感或疑惑。涵納作者感情的百物,經過文字輸出後又有了新的情感體驗。【內容簡介➤】
●百耳袋
謝鑫佑著,時報出版,400元
推薦原因: 文 樂
以日本、印度、台灣等不同地區的神話為引線,透過4篇短篇小說發射各種虛實共構的奇想與怪談,是讀來並不太過奇幻、但也現實未滿的趣味之作。4篇故事皆以家族、人際關係為平面,怪奇事件/事物的出現則讓日常熟悉的人事景物產生皺摺,干擾理所當然的世界觀,也讓傳統「寓言」體的神話有了精彩的現代詮釋。【內容簡介➤】
●情熱書店
史上最偏心!書店店員的東京獨立書店一手訪談
池內佑介著,小寫創意出版,480元
推薦原因: 議 樂 獨 益
對於「實體書店」懷有憧憬與情感的讀者,對於本書的熱情將更有感觸。由作者親自挑選、拜訪數次後完成的訪談記錄,不讓獨立書店只等於文青或抱怨書價的陣地,更跨越政治、國族、文化,呈現更多元樣貌,包括在日本開韓文書店的挑戰、極左派的政治實踐與出版刊物的關係、農業出版、古書的經營等,與書交織出的則是無限寬廣的期待與想像、失落與堅持。【內容簡介➤】
●追尋寧靜
一場顛覆聽覺經驗的田野踏查,探索聲音的未知領域
In Pursuit of Silence:Listening for Meaning in a World of Noise Paperback
喬治.普羅契尼克(George Prochnik)著,韓絜光譯,漫遊者文化,420元
推薦原因: 知 思 議 樂 獨
本書以寧靜(silence)為題,透過不同空間(生物實驗室、禪園、大賣場、隱修院、聽障空間等)與不同專業領域(生物學家、科學家、工程師、僧侶、建築師、行銷人員和聾啞學校等)提供對於聲音的多元認知與獨到見解。寧靜既是物理的、生物的、心靈的、文化的,也是現代人生活中永遠的空缺與追尋,作者將個人的聲音之旅,譜寫成一本難以定義又令人驚艷的文集。【內容簡介➤】
●大腦韌性
高齡化時代最重要的健康資產
Keep Sharp: Build a Better Brain at Any Age
桑賈伊.古普塔(Sanjay Gupta)著,張瓊懿譯,行路出版,480元
推薦原因: 知 實 益
作者引領我們進入大腦的世界,希望透過了解其運作,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降低認知衰退帶來的人生損傷。本書兼擅知識普及與實用養生,在腦知識的基礎上,為大腦量身設計鍛鍊菜單以及各式照護對策。明朗樂觀的態度具有安定人心的作用。文字流暢清晰,深入淺出,擺脫了衛教手冊的乏味與科學專書的深奧。【內容簡介➤】
●小聚會
68道宴客菜,與朋友在家輕鬆喝很多杯(一杯怎麼夠)
Recipes for the Small Gatherings
比才著,有鹿文化,480元
推薦原因: 設 實 樂
這是本一開始翻閱就會想念食物與朋友的實用食譜與餐酒書,在美麗的餐點圖片、清楚的製作執行指引文字下,有其獨特的待客美學,你會很希望某個朋友擁有這本書,然後你可以在行事曆上記下那位朋友的邀請。在台灣同類型自製書中,本書也樹立了一定的美感高標,文圖構成有平衡感、照片中精心的擺盤與器物都讓視覺十分享受。在無法群聚社交的疫情下,本書不僅是給下一場宴席的備忘錄,也是期待下一次相聚的美好動力。【內容簡介➤】
●原來,食物這樣煮才好吃!
從用油、調味、熱鍋、選食材到保存,150個讓菜色更美味、廚藝更進步的料理科學
150 Food Science Questions Answered
BRYAN LE著,王曼璇譯,聯經出版公司,450元
推薦原因: 知 實 樂
對許多人來說,料理這件事已有太多資本、傳統、人情、人際甚至性別、種族因素的作用,有時更被視為是天生的技術能力,誰能煮、誰來煮、怎麼煮、怎麼吃,有著各種文化因素影響。本書加入一個新的因素——「科學」,因此解放了料理的各種門檻,只要在舉世共通的科學原理、化學組成、物理反應中掌握食物的「國際語言」,不論是新手入門或是高手精益求精,有本祕笈在手應能喜迎各種美味挑戰。【內容簡介➤】
●歌唱臺灣
連續殖民下臺語歌曲的變遷
陳培豐著,衛城出版,480元
推薦原因: 知 議 樂 益
本書探索臺語歌曲的身世。一般以為早期臺語流行歌是日本民謠歌曲的挪用仿作翻唱,作者則轉調指出這是台灣人在殖民統治下自我摸索、找尋出口的吞吐之音。本書延續作者先前關於台灣人表述中精神世界的關注,為語言文字譜上音符曲調,也走進娛樂這種表面華美其實更深層潛在的境地,帶來了音樂史、娛樂史的另一模樣。以學術的文字處理原本依靠聽覺接收感受的音樂、曲調和歌唱,著實不易。【內容簡介➤】
●腓尼基人
一群被發明的祖先、一個「不存在」的民族
In Search of the Phoenicians
約瑟芬.奎因(Josephine Quinn)著,王約譯,馬可孛羅文化,580元
推薦原因: 知 批 議 樂
「腓尼基人」向來被視為歐洲文明礎石的一部分,特別是由其移徙經商、四海為家所帶出的新元素。本書卻解構了將「腓尼基人」理解為一個穩固「民族」的陳說,重新檢視材料,勾勒出「腓尼基族」的生成。對「民族」的反思是近年歷史研究的熱門取向,本書也將這個議題上溯至西方古文明的基礎,並且提醒我們「群體」和「民族」的差異。作者的問題明確,觀點闡述明晰,論點不因大量材料而淹沒,值得台灣讀者藉此反身思索。【內容簡介➤】
●從人到鬼,從鬼到人
日本戰犯與中國的審判
Men to Devils, Devils to Men: Japanese War Crimes and Chinese Justice
顧若鵬(Barak Kushner)著,江威儀譯,遠足文化,680元
推薦原因: 知 思 議 益
歷來觀看日本二戰敗戰之後「人」的處理,多聚焦於甲級戰犯這些「罪魁禍首」。英國歷史學者顧若鵬則將視線轉移至乙、丙級戰犯,他並非要羅列或釐清這些戰犯的責任,而是試圖透過名單背後所牽連的處置行動,讓世人看見世界秩序如何在不同力量的角力中再建。如蜉蝣般的個人,身處國家/國際體制中的荒謬感亦由此顯現。台灣的命運也隨著國民政府在此間的進退行止擺盪了。【內容簡介➤】
知識性.設計感.批判性.思想性.議題性.實用性.文學性. 閱讀樂趣.獨特性.公益性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