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談》俯拾皆是的文學生活:甘耀明╳李崇建
一群生猛的「新」生代寫作者,有感於台灣小說界沒有文學浪潮,認真創起一個叫6P的團體,利用當時的網路站台創立「小說家讀者」,企圖帶領讀者好好啃食每本小說。沒多久,「小說家讀者」擴增版圖成了8P,更大膽地走出網路、搶救新秀,企圖以瘋狂的方式改變台灣文壇。然而光芒有多大,罵名就有多響亮,最後這個團體沒有一點交代就消聲匿跡,但對他們而言,只是驕傲地轉身離開,因為他們為那個時代留下最風光、也是對文學最真誠的時光。
如今已消失的8P,各自走上適於他們的路,也從「新」生代熟成至「中」生代,偶有結盟合作,創造各種文學光景。其中的甘耀明與李崇建,這對從大學時期就以文相濡的好同學,從討論文學、投稿文學獎、全人中學教書、開辦作文班、合作寫書,如今還有很多已規畫好的題材作品正著手分工書寫。
一位是專注在台灣鄉土書寫的小說家,一位是多方發展的親職教育工作者,文訊雜誌社為這對「書寫夥伴」特別策畫一場對談,在潔晰明亮的台中中央書店裡,讓讀者一同認識他們如何從生活中,信手拈來各自的文學夢想。
▉相知,相惜,成就書寫實驗大冒險
李崇建首先坦然表示已經離文學很遠了。他和甘耀明是東海大學中文系的同學,當時的他們曾徹夜談論文學,在文學獎裡較勁、相惜。畢業後他們還一同到山中任教,創辦千樹成林作文班,甚至一起在寶瓶出版小說。
「耀明是渾然天成的寫作者」,李崇建引諾貝爾得主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曾說的:創作者分成兩種,一種是天生、渾然天成的,一種是感傷的。他指出甘耀明的文筆某部分比他優秀,因為文學存在創作者的某種特色與侷限,「我這種通俗的寫作者,無法理解他所組織與架構的小說,但那就是藝術品。」李崇建說自己屬於感傷的,會透過組織與整理,寫就另種脈絡與創作,也因此才會踏入教育界,並透過書寫傳遞理念。
於是,他實驗性地與甘耀明合作,自己負責企畫書寫的題材與內容,而文章就交由甘耀明負責。「因為他很天真,文筆又好,出版社基於對甘耀明的肯定,也對這樣的題材有興趣,於是達成我做為一位創作者想達到的目標。」從《沒有圍牆的學校》開啟合作書寫,其後《對話的力量》、《閱讀深動力》與《薩提爾的守護之心》,及至預計年底出版的兩本童書《透明人》與《藍眼叔叔》,都是令他們難以預料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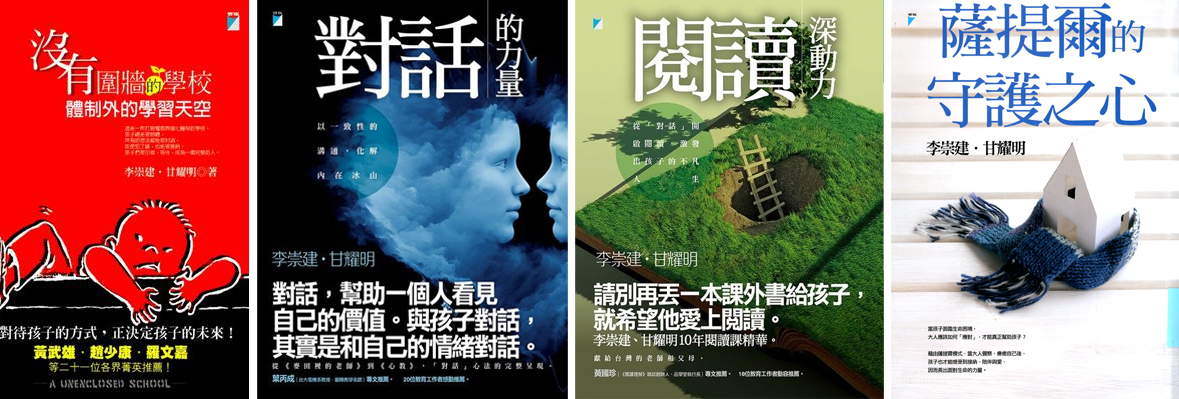
在李崇建大膽表明惜才之情後,甘耀明也娓娓道出兩人自文壇出道以來的種種,包括那段總是在大放厥詞的8P時代。很少參與講座活動的甘耀明,自覺不是那麼擅長運用言語表達,也覺得改變不了什麼。《沒有圍牆的學校》出版時,兩人都默默無名,在新竹誠品舉辦的講座無人參與,書局店員來問怎麼辦,李崇建邀請店員當聽眾。甘耀明回憶,「他真的很有群眾魅力,過程中連路過的人都停下來聽到講座結束。」他們的知名度,就在李崇建的能言善道下開啟了。
甘耀明岔題回憶2011年到德國交流的場景,語氣裡滿是欽佩的口吻:「即使是下著雨的天氣,讀者仍願意搭上40分鐘的車程前來柏林郊區的萬湖參與講座,但講座過程中,作家也只是默默地念著自己的稿,讀者卻不減熱絡地聽到最後。因為那樣的閱讀對他們而言,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
談到口中毀譽參半的8P時代,甘耀明說,「我覺得那時的我們很風光耶!」那時年輕氣盛的他們很敢玩,單純只為了掀起閱讀小說的浪潮,從網路讀書會、徵文到報刊撰寫專欄,「我們大放厥詞地談論文學,但那就是我們六年級世代的創意,只是想讓文學變得更有意思。」人不輕狂枉少年,大概就是這種感覺吧!
▉俯拾皆是,也是要有天份跟底子撐腰
「每次提到創作的機緣,不得不提到被性騷擾的經驗。」李崇建坦然訴說自己18歲時看電影被老人摸大腿、當兵時被士官長猥䙝的故事。但生命是有韌性的,即使日子過得很苦,也總得找到一扇救贖的窗口發洩。「這些心靈受到的痛苦或抱怨,甚至自己的夢想,就寄託在日記,兩年下來寫了6本日記。加上從小就喜歡讀詩詞歌賦,也把詩詞寫入這些苦痛裡。」
或許發覺自己在創作上的天份,退伍後的李崇建積極考進東海中文系,也為了想申請獎學金開始創作,「我可是班上第一個得東海文學獎的喔!」李崇建隨即看著甘耀明想證明這個事實,甘耀明則只是笑著頻頻點頭。
因為愛創作,大學時的李崇建把生活裡的大小事情寫進故事裡。當時他愛戀一位女同學,雖然一年跟她講不到三句話,可每天看著她走路、看著她上課,連她掉落的紙條都默默收著。這段說不出口的情感,化成獲得系上文學獎的〈暗戀小扎〉。李崇建還自曝,當時有位評審是靜宜大學的教授,因為太喜歡這篇〈暗戀小扎〉,就拿來當教學範例,誰知弟弟正是這堂課上的學生,看了哥哥的暗戀文章被當成範例,覺得丟臉至極。
李崇建也寫古典詩。他曾與當時的學弟、今台師大國文系教授徐國能一同瘋狂寫詩投稿,不僅每戰必捷,也一同創下了許多趣事。其中之一是當時規定每個獎項只能投一次,兩人投稿數量過多,不得不借用他人之名。徐國能以班上男同學之名,投了一首〈夜談三首〉,李崇建讀後覺得有感,也借用女同學之名另投一首〈夜談三首次韻友人〉。揭曉時,他獲獎了。李崇建說,幸好結果如此,否則不相識、只提供名字的兩位同學恐怕是要來場情感革命了。甘耀明在一旁笑說,每次聽李崇建講這些過往回憶,都覺得歷歷在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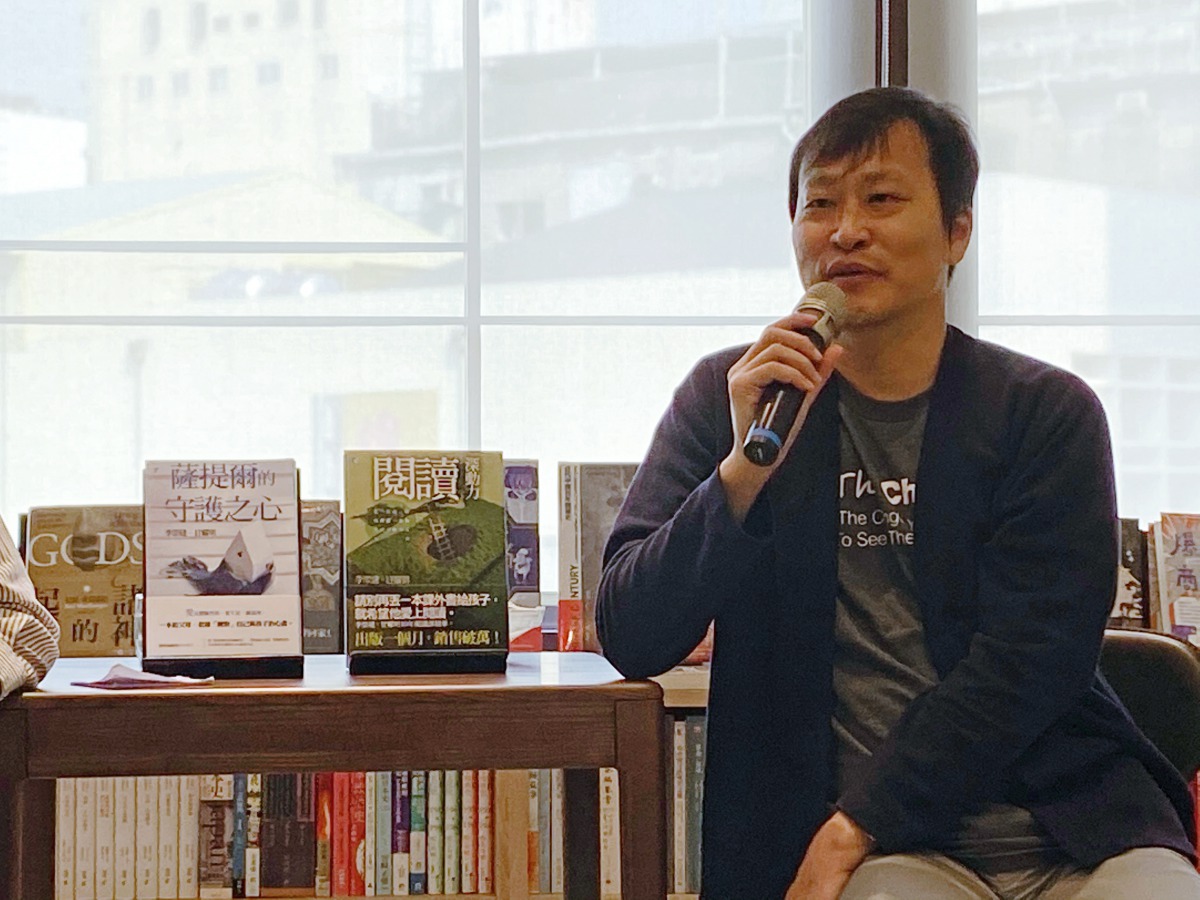
相較於李崇建的瘋狂行徑,甘耀明說自己是在傳統SOP底下教育出來的孩子,接受古典式的教育,從小被要求背詩、練書法,「差點走上公務員的人生。父母總是期望孩子能過得安穩平順,但往往彼此的想法都有落差。」
考大學選填志願,猶豫著該選什麼科系時,一日甘耀明載隔壁女同學回家,隨口問了她的志願,就也不經意地選填中文系。大一時曾因為古典文學科目過多而心生放棄的他,卻因為一篇暑假作業,成就現在的小說家。
「他的內在是叛逆的,表面說不喜歡,可是卻為了一篇不喜歡的東西琢磨了3個月,還寫了8大張稿紙。」李崇建以心理的角度分析著,實則憐惜眼前這位天生的寫作者。甘耀明則回應:「那份作業我得了甲上上,感覺很虛幻,而且教授覺得我很適合念中文系,不知怎的……就覺得好像應該留下來繼續念中文。」
「其實那時有意識到,創作,就是在寫貼近內在的東西。」甘耀明開始說起村上春樹如何成為村上春樹的故事。一場球賽、一顆被接住的外野球,村上頓悟到自己可以成為一名小說家,但故事並非如此平順。
「他被自己的語言框住,但腦袋有此作品的圖像。」
「他都在看經典作品,因為他本身是位譯者。」
「可是他明明英文很破呀。」
「他想到用翻譯體的概念去書寫。」
「他用破英文書寫他想要寫的東西,然後翻成日文。」
兩人突然很有默契地一句接著一句,訴說村上如何創造出村上體,「很多人都覺得他永遠不會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因為人都很習慣侷限了」,連結尾也接得如此生動有默契。
▉得失心不要太重,因為失敗總是笑著看你瘋顛
談到大學時期的閱讀與參與文學獎的經驗,甘耀明說他當時是不太看小說的,創作也都是以散文為主,反而是他們的同學、目前是東海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的陳慶元小說讀得最兇。
「陳慶元都讀黃凡、張大春,全都是後設型的小說,連寫的小說也都是如此。」李崇建在甘耀明提起老同學的名字時,像汽水罐被打開似地湧出過往競爭失敗的「氣」體。當時他與陳慶元的創作都以詩為主,表面上以文相濡,但其實心裡較勁得狠。大三那年,兩人都參加了五四文藝節散文獎,「我心底就是有個聲音,覺得第一名會是我的。」然而卻在一個清晨接到陳慶元歡欣無比的獲獎消息,「心都撕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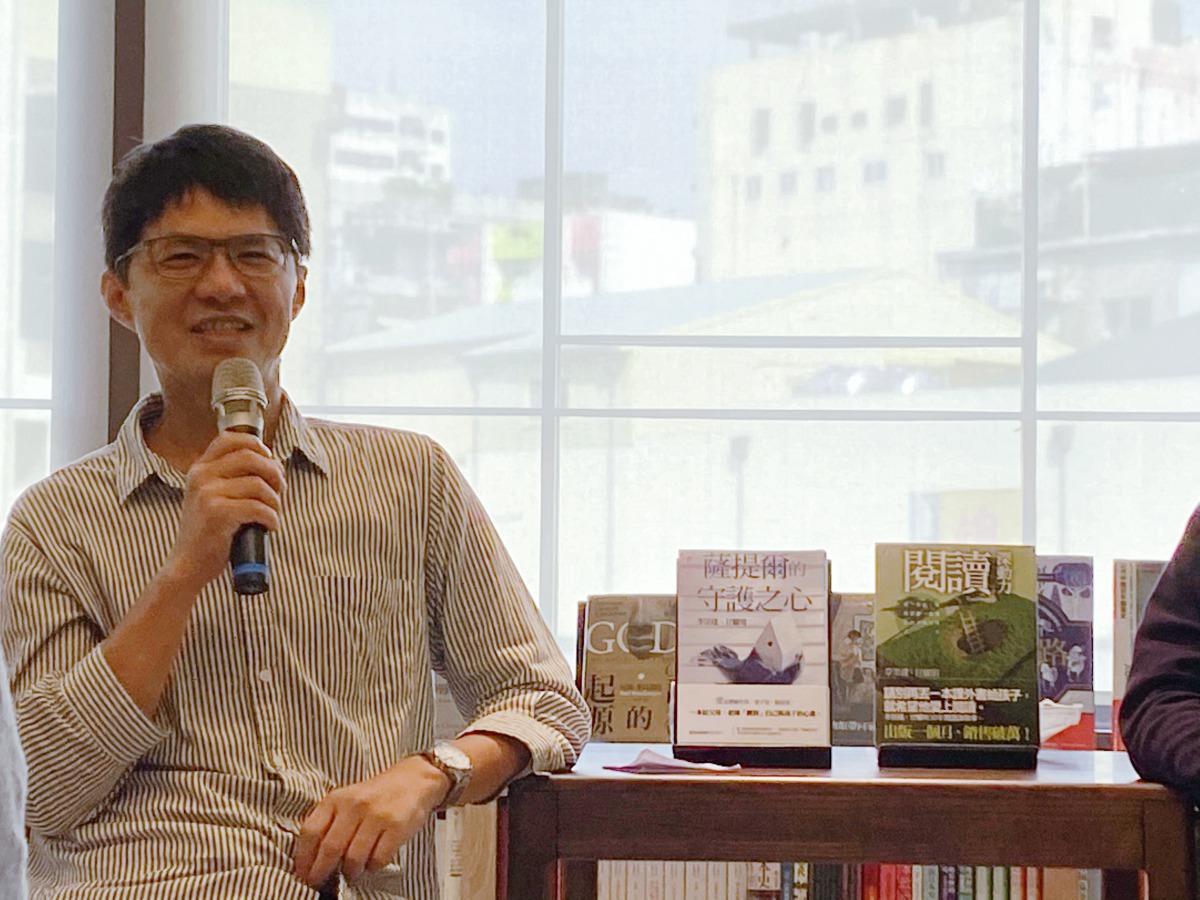
李崇建的妹妹也是作家,身為哥哥的他,卻打從心底覺得妹妹不會創作。有一年他投稿南投縣文學獎,妹妹獲得當年小說組第二名,自己則一個獎項也沒有。憶起這些過往,李崇建覺得創作的路上都是有個契機跟引子在引領著大夥,很有趣,年少的自己總是痴人夢想著會得名。
甘耀明回憶說,大學時期嘗試寫過詩、散文、小說,也參與過劇本寫作,但他一直偏愛小說。後來參加系上舉辦的「夔鳳文學獎」,意外獲得第一名。當時還有位學姐買了個麵包請他,封他為「小說王子」,他以為文學好像很簡單,自己似乎能夠寫些小說,就這麼誤打誤撞地寫下去,直到後來認真思考小說的本質時,才發現書寫的過程其實很困難。
「有人可以一起大言不慚、一起討論創作、討論文學,創作才會變得有趣。」李崇建覺得自己和甘耀明之所以不同,在於他和另一群同學把文學當成生活的一部分,大家互相感染,互相學習與成長。而從未與他們這群人一同討論的甘耀明,卻默默地在校園內辦起刊物。
▉創作要有空間發表,才能被看見
1994年,甘耀明和曾獲聯合報散文獎、中央日報文學獎的陳慶元,創立《距離》文學雙月刊,曾掀起東海的文學創作風氣。甘耀明說,「因為寫了很多東西,也很晚才參加校外的文學獎比賽,主要是希望有空間可以去發表、出版,所以辦了這本月刊,前後也有六、七年吧!」
文學獎是很好的發表場域,也是對創作者的肯定。當時很多創作者的奮鬥目標是「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兩人因為對寫作都有期待,因此李崇建也跟著踏入小說領域,「但好像長得沒完的假期,還要布局。」李崇建的第一篇短篇小說〈狗奪〉完成時,甘耀明反覆看了三次,覺得寫得很好。1998年,李崇建的〈上邪!〉獲得第12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短篇小說佳作,甘耀明的〈上關刀夜殺虎姑婆〉則落選了,但他還是很開心,因為評審之一的陳映真喜歡這篇作品,甚至提出「新鄉土派」的詞彙,「覺得滿有意思的,雖然還是沒有辦法抹平自己摃龜的小小遺憾。」

李崇建鼓勵喜歡創作的人大膽地寫,不要只想著怎麼寫好,那樣反而會受到侷限而寫不出來。他談起兩人一起去山上體制外的教育教書,還做過很多不同領域的工作,「這些生命經驗,都是書寫的來源」。甘耀明後來大膽跨出步伐,毅然離開教育場域,只為了專心寫小說,至今仍投注許多能量在小說創作,「回頭檢視耀明的創作歷程,他才是那個一直享受在文學創作裡的人呢!」
這兩位大學時期就結識的夥伴,實踐的路途上還有很多夢想與期待,他們找到各自擅長的領域,保有各自的創作方式,彼此看重,也彼此包容。相信在文學路上,他們能透過一本書,一場講座,帶給讀者長久深遠的影響力。
這場座談會後,李崇建在臉書留下這段文字:
會後與耀明在中區散步,少年時代繁盛的民族路,如今凋零殘舊,難以想像,我們在柳川步行,在中華路吃臭豆腐,喝了一碗蓮子湯,感覺青春走過的路,即使凋零殘舊了,都有著美麗的初衷,在秋日傍晚的步子仍輕盈。●

 【第九屆臺中文學獎 徵文活動開始囉!】
【第九屆臺中文學獎 徵文活動開始囉!】
你也喜歡創作嗎?臺中文學獎創作獎不受國籍、居住地等限制,只要以繁體中文創作就可以參加,有機會抱走最高獎金12萬元唷!
收件日期:即日起至109年11月2日(一)
報名方式:請至臺中文化局網站下載報名表
獎項共分8類:
1. 小說
2. 散文
3. 新詩
4. 古典詩
5. 臺語客語詩
6. 童話
7. 國高中職生散文
8. 國高中職生閱讀心得




書.人生.小熊老師》書,舊城,夢或者黎明
我究竟是如何成為一個「書店」老闆的?
過去長年擔任編輯,一個讀書、寫書、評書、編過書當然也愛書的人,如今成了書店老闆,這角色的轉換似乎只是剛好而已。我開的這家書店,不那麼正統,在許多人眼中它更接近一個「閱讀空間」或「文化空間」,而不太是(或不只是)個賣書的地方。一望直覺是家咖啡店,聞咖啡香而來的客人確實比為書而來的多很多,也沒什麼不好,用書把喝咖啡的人包圍,書香交融咖啡香,潛移默化,最近且最遙遠的催眠。一轉眼五年過去,其實第二年我便清楚意識到自己是個失敗的生意人,不過,因為「文化過動」體質而持導致的諸多嘗試,讓我和內人韋瑋確實玩出了閱讀活動各種假鬼假怪的可能。
到底,我這個人的「書緣」,源自何時何地?
從上小學開始,我就是個經常被寄在「書店」的小孩,父母在百貨公司專心致志地血拼時,安撫躁動兒童的天堂就是百貨公司裡的圖書區。我和大我一個年級的姊姊,屁股往地板上一坐,書本攤開,馬上就安靜下來——大人逛他們的,小孩讀自己的。小孩乖乖「被托兒」的獎賞,就是能夠選一本書買回家。台中市中區的黃金年代,大大百貨、龍心百貨、遠東百貨,是理所當然的休閒風景,而我關於百貨公司的童年記憶,除了小時候最愛吃的港式飲茶,就只有書了。一本又一本兒童讀物——《白蛇傳》《西遊記》《小飛俠》……把當時三民路舊家頂樓幾個高大書櫃塞得滿滿,小學同學裡大概沒幾位家中的書能長成這樣一面書牆的。在信用合作社上班的父親一度認真考慮改行開書店,「家裡開書店」的夢我作了好幾年,不了了之三十年後,這個早就忘得一乾二淨的童夢,竟然實現了。
現在被稱為「舊城」而亟待復興的中區,當年可是台中最摩登的地帶,於我,也曾是家之所在。小時候有人問我打哪來?只要回答:「我家就在台中公園斜對面。」大家就一清二楚了。這個家,大門正對面是光復國小,出門左轉公園路會接上中華路夜市,出門往右直走不一會兒就到第二市場。再多走幾步,是百貨公司般的五星級書店「中央書局」,無論圖書或文具,應有盡有。近年搜查台中文學地景資料,才知這家書店正是詩人路寒袖念台中一中時蹺課躲藏之處,繼續溯源,書店創立之初,日治時期重要文人林獻堂、林幼春曾任股東。
家在三民路時,小學到國中,婚紗街的盛況不斷綿延,媽媽開的長春理髮廳夾在櫛比鱗次的婚紗店當中。樓上住家,樓下開店,理髮廳打烊後就是我的閱讀天地,厚厚椅墊、高高在上的理髮椅,成了我的閱讀寶座。讀報的興趣就在這裡養成,因為店裡有幫客人準備等候席,茶几疊放了不少消磨時間的刊物,許多客人理髮時手上總離不開一本雜誌或一份報紙,所以店裡隨時都有兩三份報紙供人翻閱。當然,也有當年最受歡迎的《時報周刊》。
長大後研究文學,發現好幾位重要文人都待過《時報周刊》,譬如商禽。還不識商禽的我,一開始追的是蔡志忠、朱德庸的漫畫。後來上大學念社會學系、出社會進雜誌社和報社工作,並且樂在其中,都可能與這段兒少時期的「啟蒙」有關。報紙影響讀者看世界的角度,店裡的報紙從《中央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慢慢遞嬗到《台灣時報》、《自由時報》,透露著父親著政治思想的轉性。只記得店裡訂閱的報紙剛換成《自由時報》時,我讀得渾身不自在,感覺報紙裡呈現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明明該被打屁股的暴民抗爭,在這份報紙裡卻被敘說得那麼天經地義、造反有理。
成為李登輝信徒的父親,某天下班後心血來潮騎摩托載我到三民路上的一家「台灣本土文化書局」,與店主攀談一晌,丟下一句:「有什麼想看的書就買吧,我晚一點再來結帳。」說完就去辦他的事了。印象中那家書店陳列的書種,內容對中學生而言偏硬,最後我竟挑不到一本想帶回家的書——也許微微震顫於「原來這世上存在著這樣的書店啊!」但也可能是當下我更想到公園路轉角去吃大麵羹。說也奇怪,「本土」此後成為街談巷議的關鍵詞,我也變得愈來愈喜歡聽大人聊政治,報紙社論是我愛讀的欄目,民意論壇則是最具張力的版面,讓人讀到血脈賁張。
長春理髮廳曾歷經兩度遭遇祝融。第一回,我們一家子住在樓上,起火點是樓下的廚房,及時滅火,真是萬幸。第二回,我們已舉家遷移到霧峰,回到祖輩所在的家鄉,母親從「到樓下開店」變成「去城區上班」。這一回,城區的店遭大火吞噬。城區的家,與城區的遠東百貨走上同樣的命運,一燒,再燒,終致灰飛煙滅。那幾場大火,預告著中城的沒落。
中區一蹶不振二十多年,不惑之年再回來,縣市已合併,台中縣消失了,台中市變大了,中區變得更小了。舊家對面的光復國小早已不是一班動輒六十位學生的明星大校,附近的第二市場成了觀光客的市場,晃悠一圈,陌生大於熟悉。那家台灣本土文化書局還在,外觀歷盡滄桑,店裡多了一隻貓。
這一回,我可以挑到無數本想看的書,當中有不少霧峰林家文獻圖書,對於正在霧峰從事文化社造的我,如入寶窟,最後帶走了鍾喬《阿罩霧將軍》、潘樵《台灣尋櫟記》以及日本漫畫家杉作《為什麼貓都叫不來》。挑這三本書,除了內容涉及此時此刻關心的文史與環境教育,當然還有些許紀念意義——阿罩霧是霧峰古名,青剛櫟是台灣黑熊的美食,櫟樹又可連上台中文學濫觴「櫟社」,櫟社成立於日治時期的霧峰林家萊園並活躍於城區……至於,為何要選一本貓書?除了跟店主人的話題三句不離貓,我開在霧峰的書店「熊與貓」店名就有個貓,貓書當然不可或缺。
開書店,不就是希望更多人跟閱讀產生連結?既然學不會賣書,還是能想辦法推推閱讀吧!2017年起,我家「熊與貓咖啡書房」改成只在周末兩天迎客,周一到周五,我們四處游擊,讓閱讀活動轉場於霧峰及其周邊的台中城南區帶。從霧峰、大里一直綿延到城區——學校、社區、市集、餐廳、街頭、田邊、山村、溪床,都是閱讀場域;走讀、漂書、真人圖書館、文學美食趴,都是活動形式。別人看我們,上山下海,不亦「閱」乎!在地人文客廳、文藝復興基地、閱讀公關公司、友善土地智庫,這些美麗的封號,我都欣然接受,有時也會在爭取獎補助的提案報告書裡這麼往自己臉上貼金。但回到書房,開著一家店,也就是守著而已,無關乎賺不賺錢,無關乎夢想偉大,就只是守著自己當守且能守的。
當初在商業登記時,與會計師在「書坊」和「書房」之間僵持許久——實在不喜歡用書坊,那容易讓人聯想到租書店;但書房被認為不是營業空間,所以被審理機關打回票。即便正式立案名稱妥協為「熊與貓書店」,招牌還是硬要打上「書房」兩字(最後還加了咖啡),寓有作家書房開放之意。
兒時在長春理髮廳的空間經驗,重現於充滿咖啡香的書房,打烊後,不開店的日子也有戲,客人的桌子就是我的書桌。游移在各桌之間,看心情來選用桌子,這是我史上擁有最多書桌的書房,每個桌子都有一或多本攤開的書,包括那隻喜歡依心情臥上不同桌子的三花貓,在牠攤開的睡姿裡,彷彿也有我的夢或者黎明。●
小熊老師
本名林德俊,筆名小熊老師。於社區大學及坊間寫作班、文藝營教授新詩、散文、報導文學、廣告文案、藝文跨界等。曾獲五四文藝獎、林榮三文學獎、乾坤詩獎、創世紀詩獎等。著有《樂善好詩》《阿罩霧的時光綠廊》《玩詩練功房》《黑翅鳶尋家記》等書。經營熊與貓咖啡書房及熊與貓台北松山驛站兩個文化空間,從事文化節點串聯,推動在地文藝復興和友善土地的社區行動。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