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中旬萬物萌發的驚蟄與春分之交,被推崇為台中清水必拍景點的海灣繪本館,歡欣迎來5周年館慶。除了盛大舉行草地派對及春日市集,館內同步展出在地插畫家王書曼個人特展,一起領略其作品3度入選義大利波隆那兒童插畫展的魅力。
本文偕同讀者走入海灣繪本館春意盎然的館慶現場,同樂之餘,也將回顧該館歷年來精心策畫的繪本展覽與主題活動,從中了解海灣創立以來的理念精神與協作方式,如何持續引入繪本能量,讓大小觀眾彷彿被「吸入」繪本世界之中,讓繪本的美好在生活場域產生意義,在心內萌芽。
➤春天張開擁抱的大手,召喚海灣好友重返魔法森林
海灣繪本館5周年,春日市集與草地派對一景。
「這裡真的很好拍!」喜扮浪漫花仙子與唯美小公主的網美,絕對會愛上這個春日市集。位於港區藝術中心對面、清水眷村文化園區後方,置身稻浪中央的海灣繪本館,本次館慶邀請了20位創作型特色品牌職人共襄盛舉,在園區各處運用花露香氛、春日花束、植感手作等浪漫素材妝點會場,並採擷春季限定花果、香草入饌私廚料理,一次讓視覺、味覺、嗅覺都好滿足。
草地派對有魔術、音樂、故事劇場等精彩表演,其他還有日本西川流專家規畫的和服禮儀和浴衣體驗、大地藝術共織營的「裂布編織」手作教學,現場挑戰試作杯墊、鍋墊、動物小窩、置物提籃等,讓舊衣重獲新生。館方也準備了小朋友限定的好玩活動:尖尖故事屋與孩子們分享呼應季節的繪本故事《春天真的來了》,以此為主題進行集體彩繪,運用手心或畫筆,自在地將繽紛多彩的顏料塗抹於白紙,描繪出春天的樣貌。參加小小獨角鯨成長訓練營的孩子,則可戴上獨特的彩虹小角,化身為一頭小角鯨,學習控制頭上的角,安全愉快地與小夥伴在園區律動。
自認永遠懷揣18歲少女心的黃淑娥,是海灣文化創意協會理事長,也是催生本次館慶花開燦爛的策展人。她表示,因為疫情,海灣沉寂了很長一段時間,去年市集也停辦了。為了回應整年沒見的好友們,海灣在本次館慶裡刻意創造許多儀式感,猶如大自然對世界發布萬象復甦的信息,不只召喚繪本小精靈們回到這座魔法森林,也宣告海灣在後疫情時代重新張開擁抱的大手,溫暖地面對群眾,迎接嶄新開始。
尖尖故事屋分享《春天真的來了》繪本,讓孩子們盡情彩繪。
➤主打清水在地創作者,向世界展現豐沛能量 滿溢奇想風格的海灣繪本館,最廣為人知的象徵就是療癒系代表「大翅鯨」了!今年,畫風夢幻且熱愛海洋的創作者查理宛豬,以超過2周的時間駐地,親手將筆觸細緻、色彩飽滿的大翅鯨與鯨寶寶繪製在館牆:背著三幢繪本屋的大鯨魚溫暖展翅,守護翅脊下的鯨寶寶。鯨背上的小屋以繪本為結構,揉合蒸氣龐克元素與懷舊美學,彷彿時間之流使尾鰭齒輪轉動,承載海灣繪本館的大翅鯨,在想像力的汪洋裡游過數載春夏秋冬。
海灣繪本館內,天花板垂掛的白蓬蓬雲朵大翅鯨也翻新。策展經理蘇鈞偉趁著疫情諸多外務停擺的空檔,將館內損毀汰換下來的繪本打成紙漿,以循環再生的概念,讓這些服務過眾多讀者的退役繪本們重生為大翅鯨立體裝置2.0,繼續佇留在海灣,俯瞰館內,守護著大家。
蘇鈞偉將大翅鯨從棉花雲朵狀翻新為紙漿立體裝置藝術。
「5年前,我們以在地創作者玉米辰的作品作為開館示範;5年後,就像大翅鯨的洄游一樣,我們也希望展覽主題回歸到在地創作者身上,藉此讓大家看見——只要有豐沛的創作能量,即便在偏鄉,也能向世界發光。」
負責統籌海灣所有展覽規畫設計的蘇鈞偉,是南藝大視覺藝術出身,曾參與創作台灣燈會主燈,有扎實的立體裝置經驗。他在為Openbook進行導覽時,說明了本次主打王書曼的意義,不只在為創作者帶來信心,也能為人們帶來各種參與的想像。
王書曼過去總是將自己隱身在清水家中與作品背後,無論採訪、演講或展覽都鮮少答應外界邀請。她指著自己眼睛上的黑輪回應道:「不是我拒絕跟外面接觸,而是我真的花去所有時間埋首工作堆裡(已經到了媽媽會跑來問我『要不要餵你吃飯?』的地步)。這次之所以會答應辦展,是因為對清水有一份使命感,此外也是被海灣繪本館的理念與熱情給深深打動。」
➤「繪本。與我們之間」化故事為情境,4種展間各異其趣
王書曼主題展「繪本。與我們之間」,觀眾第一眼見到的入口意象,取自她描繪祖孫情感的作品《爺爺的散步道》。海灣利用館內廊道模擬書中場景,連同網路募集到的祖孫故事及照片合併展出。觀眾進入廊道,即走入繪本之中,並在此遇見他者的真實人生。館方希望藉此觸發每個觀眾心中深藏的回憶、重拾親情帶來的感動,讓《爺爺的散步道》不單單只是繪本故事,也是大家有所共鳴的故事。
穿過廊道來到第一展間,這裡可供讀者近距離了解一部優秀作品如何誕生。其間陳列的物件:工作檯面上的顏料、畫材、工具與現場創作情境,全由王書曼一手布置。展場也陳列插畫家創作至今的所有繪本作品,並設置閱讀角,供親子在模擬的插畫家工作室裡佇留欣賞。
插畫家王書曼一手布置的模擬創作現場,讓大小朋友有如踏入工作室。
第二展間主題是《火燒厝》。中央擺設金旺機車紙紮實品,討喜地令人跨越了禁忌的刻版印象。現場還提供紙紮材料讓觀眾祈福許願:只要裁下紙片、寫上心願的話,貼到玉皇大帝的「天公座」竹篾上,待展期結束,海灣就會將這件獨特的共創作品焚燒「化掉」,把眾人的祈願傳遞給神明,藉此讓大家了解,無論天上人間,紙紮文化最根本的心意其實是「祝福」。
王書曼以《火燒厝》繪本為主題布置的第二展間,中央擺設金旺機車紙紮實品,增添懷舊感。
第三展間是繪本《爸爸的秘密基地》,講述父子相偕探索夜間大自然,尋找最美的祕密。海灣利用螢光漆打造出暗房,再提供紫光燈作為觀眾的探索工具。一打開手電筒,就會發現漆黑夜空裡有銀河閃爍發亮,地面是生態河道,牆上是滿山滿谷的螢火蟲匯聚的神祕森林(還藏有許多小彩蛋!)。暗房內,揭示了螢火蟲的成長過程:河道上的螢火蟲在水中產卵,幼蟲爬到土壤化為蛹,破蛹而出的螢火蟲會再回到河裡產卵,完成一輪生態循環。
蘇鈞偉笑說:「小朋友進來這間,幾乎全都黏住不想走。」他最期待親子能將這次看展經驗帶回現實生活,一起去現地認識真正的生態環境。
最後一個展間,平日供學齡前小朋友活動、學習與創作。本次挑選適合幼幼閱讀的《小廚師阿諾》、《誰的花花繩》與《我們都是“蜴”術家》,搭配花花繩編織成的小帳篷,牆上發表的是《小廚師阿諾》著色比賽成果展。
「童年的經驗,會影響我們長大成為什麼樣的人、想為別人做什麼樣的事。」王書曼說:「小時候爸爸都帶我們去美術館(不然就是公園外丹功運動),結果就是家裡4個小孩都畫畫。我覺得這次主題展詮釋得滿好,如果我還是個孩子,一定每天來報到。我想爸媽若常帶小朋友來這裡玩,說不定長大後他很快就能發現自己喜歡的事物。」
➤海灣共創精神:讓觀眾體驗故事情境,不再「旁觀繪本」 本次王書曼繪本特展定調為「我們之間」——我們跟繪本之間、我們跟海灣之間、我們跟作者之間。事實上,這樣的概念也適合說明海灣歷來舉辦每一場主題展的心意。
館長玉米辰表示:「海灣繪本館的架構有幾個想像。首先,清水畢竟是偏鄉,過去接觸創作者的機會並不多,所以我們有個企圖是拉創作者進場,展現作品的同時也讓親子可以接觸到作者,這個經驗是偏鄉比較少有的。」他說:「這同時也是海灣基本的核心引擎,圍繞這個核心的參與者,扮演的角色將不再純粹只是個觀眾,許多非繪本、圖像的創作者也可以參與進來,轉化各種形式、活絡這個場域。」
海灣繪本館館長玉米辰。
此外,志工是海灣很重要的動力。即便志工最初加入海灣是為了自家小孩的成長體驗,但孩子長大後,依然有很多家長留下來成為志工,服務更多喜歡繪本的大小朋友。大家在此參與、學習、收獲,相對地也願意貢獻己力、付出回饋。玉米辰說:「相較於物質與金錢的投入,這樣的能量反而是比較大的。經營志工隊其實很辛苦,但過程中慢慢找到大家不同的專長與扮演的角色,也就慢慢形塑出支持館場持續運轉的動能。」
回顧海灣5周年來的主題展,運用多媒體的裝置或形式,理解創作者作品精神後,打破紙上閱讀的限制,營造出十足趣味又具有高互動性的實體場景,接著再把讀者拉進繪本故事情境來,正是海灣的拿手絕活,也是幾年來蘇鈞偉帶領志工隊參與共創的成果。他說:「我們塑造繪本情境所產生的帶入感,會觸發觀眾自己的過往經驗,讓讀者不再只是個『旁觀繪本』的人。」
➤「等待天使系列繪本展」:一場走入罕病世界的沉浸式邀請
《亞斯的國王新衣》展間,讓觀眾感受主角完全被喜愛的昆蟲所圍繞的內心世界。
讓觀眾感同身受的帶入感,展現在2020年「等待天使系列繪本展」尤為鮮明。該系列介紹罕病的故事,4個展間分別介紹自閉、腦麻、妥瑞與亞斯的孩童。蘇鈞偉把入口設計成一扇門,作為觀眾走入同理罕病世界的邀請。
《弟弟的世界》描述主角因拯救小鳥而逐漸敞開心胸、接納世界。觀眾可以從小鳥的視角(例如:一同渴望地凝視窗外自由的世界),來理解自閉男孩不同階段的心境轉變。
《啄木鳥女孩》主角只剩脖子和頭可以活動,於是她用頭部裝置的畫筆來點出畫作。這是個悲傷的房間,天花板的雲朵滴下淚來,窗上是啄木鳥女孩點出的畫作,窗框裡,就是她躺在床上看向戶外的景像。
《青蛙小王子》改編自經典童話青蛙王子。妥瑞男孩喜歡游泳,所以整個展間化為水池,甚至有荷葉漂在水面(天花板)上,令人有如置身池底,感覺相當沉浸。
《亞斯的國王新衣》改編自國王的新衣。故事中的主角對昆蟲極度狂愛,因此展間完整重建他的房間,讓大家感受亞斯男孩專注的眼裡只有昆蟲,他的世界完全被昆蟲所圍繞。
遊客在《啄木鳥女孩》展覽入口。天花板的雲朵滴下淚來的布置頗具巧思。
➤重現繪本裡的真實:展間裡竟然有雜糧攤子與池塘?! 海灣擅長把繪本裡具有代表性的物件,建置到現實世界。透過實體化,讓讀者的美好幻想成真,賦予閱讀過程更多實感,同時也打造愉快的觀展經驗,令人會心一笑。
王書曼《火燒厝》展間中,紙紮機車便是典型一例,是貨真價實的市面傳統款式。去年,當海灣展出曾陽晴經典繪本《媽媽,買綠豆》時,也把菜市場裡的雜糧攤子復刻出來。攤位上五彩繽紛的豆豆,可直接作為黏貼畫的素材,讓孩子發揮創意、盡情創作運用。展出生態繪本《水雉的浮葉》時的工程更浩大,幾乎把整座水生植物生態池搬進展間裡,菱角也成為孩子模擬書中水雉的創作材料。
2018年張秀毓版畫繪本《阿婆的燈籠樹》展覽期間,舉辦了版畫藏書票實作,也引導小朋友用襪子手作柿子(書中的金黃色小燈籠)。張又然《藍色小洋裝》展出時,館方則設計了植物藍染體驗活動,參照繪本封面的色澤與氛圍,在藍天綠地間創建了一座藍染迷宮,吸引不少網友前來打卡拍照。
在幼幼專屬的展間,海灣貼心設置一面磁鐵牆。在這片牆上,曾經運用《亞斯的國王新衣》設計簡單的科普小遊戲,讓學齡前孩子玩玩昆蟲跟名牌的配對,也曾將《出大甲城》裡的藝閣、陣頭、花車、鑼鼓隊、神明的鑾駕等圖像一一拆解成獨立元件,讓孩子們自由排列組合,學習自己說故事。
➤展覽回顧:邀請讀者與作者、議題互相對話
創作者Ballboss在海灣繪本館外分享作品《出大甲城》。
「對話」也是海灣布展重視的一環,讓作者與讀者有機會平視對話。除了本次王書曼特展布置的個人工作室,過去《子兒吐吐》25周年展,海灣也重現了李瑾倫旅居英國時的創作空間,展出多年來作家與她的粉絲們分別帶著小豬「胖臉兒」等三隻娃娃環遊世界的照片。Ballboss展出《出大甲城》時也有多媒體規畫,用投影方式供讀者觀看他的創作紀錄,包括在英國時的發想、繪畫手法與效果。
與作者對話之外,海灣也積極邀請觀眾與議題對話。除了前述「等待天使」關懷罕病兒童之外,另有「被愛被看見」人權繪本展,突顯政治受害者的生命歷程。《愛唱歌的小熊》、《說好不要哭》、《希望小提琴》分別以白色恐怖受難者蔡焜霖、陳欽生、陳孟和等人的親身經驗為藍本,讓讀者可以體會大時代下身不由己的苦處。生態環保方面,則有《斯氏紫斑蝶的傳說》、《水雉的浮葉》、《幸運的一群》等,讓孩子們珍惜生態環境。海灣並邀請相關領域專家舉辦繪本主題沙龍,為小朋友規畫生態主題的周末故事派活動,進而加深對繪本主旨的印象與了解。
海灣也邀請不具繪本專業、但對圖像充滿熱情的素人,以創作作品為媒介與觀眾對話。像是2018年舉辦過自閉症女孩林依慧與媽媽蔡威君共同創作的《瑪莉不說話》原畫展;2019年為9歲的妥瑞小李子所創作的《月亮婆婆愛吃糖》、《驕傲的小吉》舉辦繪本展。
「被愛被看見」人權繪本展,一頭白髮的蔡焜霖正翻閱內頁。
➤展覽回顧:邀請志工與讀者參與共同創作
對話之餘,與海灣進行更深度連結的方式,就是開放共同創作了。共同創作分為兩種型態:開放一般大眾報名參加,或者讓志工參與協助。
本次主題展規畫的《火燒厝》天公座祈願、《爺爺的散步道》祖孫故事募集、《小廚師阿諾》的著色比賽成果展,都是屬於開放大眾參加的共創活動。志工參與的部分則包括布置《爺爺的散步道》廊道中翩翩散落的樹葉;協作《啄木鳥女孩》天花板上的雲朵、雨滴,還有啄木鳥裝;動手創造出《亞斯的國王新衣》生態箱裡黏土做的昆蟲以及給參觀者戴的甲蟲帽。連以繪本紙漿打造的大翅鯨,其實也都是蘇鈞偉帶領志工一步步製作出來的!
蘇鈞偉表示,相較於大眾型的開放體驗,邀請志工加入館員行列,一同捲起袖子、合作展前籌備的美術與陳設作業,更能讓志工們切身感受繪本空間所創造出來的氛圍,是如何在自己手中從零到有、具現成型,再巧妙地傳遞給觀展者。
「海灣繪本館包括我在內只有3位館員(而且平均年齡不到30歲),所以必須借助志工們的能力,才有辦法製作這麼多裝置。志工隊成員有各式各樣的經驗專長、才藝及興趣。這些組成可以做哪些事情,讓我們的工作變得非常有機。」蘇鈞偉說。
海灣繪本館的工作人員與志工合照。
➤ 開繪本館就像 桃太郎打怪,需要小動物來幫忙
3位館員中,暱稱采采的蔡采縈是海灣協會發起人之一,也是現任執行長。「在稻田中央這麼偏僻的地方開繪本館很少見,一開始地方上的民眾還以為我們是帶小朋友畫畫的安親班。我們3個就像桃太郎打怪一樣,幸好一路上有很多小動物來幫忙。」自2017年海灣繪本館開館後,家長漸漸在這裡聚集,也開始一起腦力激盪,想做些對社會、對環境有幫助的事,也得到了一些成就感、找到生活的意義。
海灣志工來自四面八方,蔡采縈如數家珍地分享:「像隊長就不是我們海線在地人,而是山線那邊的大里人,還有遠從台北來的家長加入志工,她的老家並不在中部,所以完全是衝著海灣繪本館而來。」
在數位時代,地點已經不是問題,認同才是把人凝聚在一起的原因,就像「飛地」的概念,海灣散發出不受區域限制的吸引力。
「鄉下不會變都市,我們也不期待變都市,而是把連在地人都未必看見的優點端出來,讓有共同想法的人,無分遠近都可以加進來。」談到這,蔡采縈接著說:「透過繪本這個敲門磚,可與民眾對話、可以發現議題、可以共創,還可以把這裡當成自己的一部分——海灣繪本生活圈就是我們的目標。」
王書曼在認識海灣後,羨慕來到這裡的小朋友能接觸豐富資源與多元體驗,說讓人很想重讀小學、幼稚園。蔡采縈也深有同感:「我小時候認識的書只有課本,而且只在上學時才會打開它。直到國中,朋友帶我去圖書館,才發現原來書是這種東西,跟我想的不一樣,而且裡面一定找得到你感興趣的所有一切。當時也因為喜歡那個環境,我才知道原來自己能念書。」
成長過程中的這份美好發現,讓她長大成人後,也想透過海灣持續分享給大家。蔡采縈還笑道,如今已經有民眾會跑來對她說:「你們在這裡實在太棒了!如果有人想把你們趕走,我一定第一個拉白布條對抗到底!」
➤後疫情時代:聚焦本土、培訓講師,讓繪本的美好開枝散葉
海灣繪本館內陳列眾多兒童繪本。
海灣館舍平日有大、中、小班的「趣淘PG共學團」,有興趣的民眾也可加入社群,一起共學。假日,海灣繪本館開放一般群眾參觀,除了定期舉辦「周末故事派」跟「故事接接力」,打開繪本說故事、玩遊戲、做手作,大人也可參加。炎炎夏日,海灣更會針對國小學童,舉辦每梯次5至7天的暑假夏令營,內容從自然生態、藝術雕塑到料理課程,無所不包,也帶小朋友接觸繪本提到的實物實景實地,活動相當多元。此外,海灣也積極進行故事種子講師的培訓,讓繪本的美好能透過故事講師,開枝散葉。
去年因應嚴峻疫情,實體活動無法如期舉行,海灣便開始嘗試發展多媒體故事培訓、錄製並發布線上故事派影片,同時,也著手創設多媒體課程、多媒體讀書會。接下來,海灣預計會成立專屬線上頻道與節目,以讓讀者接觸繪本、認識海灣的管道更加多元。藏書方面,海灣在今年度也有大幅度調整。過去海灣廣收國內外繪本,如今則聚焦於台灣原創繪本,希望能以更多的精力與能量,關注並支持台灣繪本作家。
黃淑娥表示:「近年,台灣本土繪本作家創作量相當大又豐富,因此現階段我們將以發掘本土能量為核心,用幾年的時間先把根扎得更深更穩一點,未來我們將打開不同的視野,與歐美、日本進行交流,屆時就有更大的能量向國際自我介紹了。」●
【繪本。與我們之間 ——王書曼繪本特展 】
地點:海灣繪本館(臺中市清水區中社路54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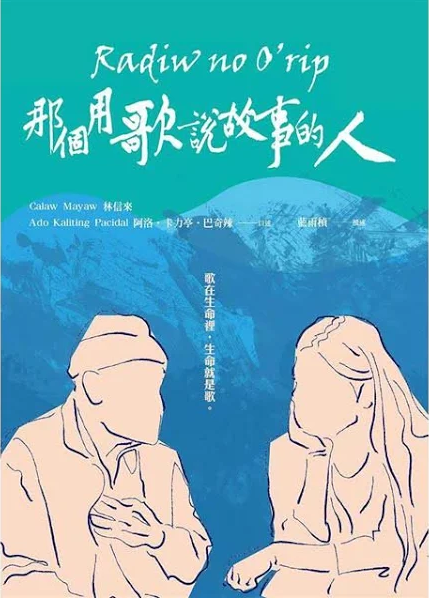


報導》清水海灣繪本館創立5周年!隨大翅鯨乘風破浪,徜徉圖像之海
3月中旬萬物萌發的驚蟄與春分之交,被推崇為台中清水必拍景點的海灣繪本館,歡欣迎來5周年館慶。除了盛大舉行草地派對及春日市集,館內同步展出在地插畫家王書曼個人特展,一起領略其作品3度入選義大利波隆那兒童插畫展的魅力。
本文偕同讀者走入海灣繪本館春意盎然的館慶現場,同樂之餘,也將回顧該館歷年來精心策畫的繪本展覽與主題活動,從中了解海灣創立以來的理念精神與協作方式,如何持續引入繪本能量,讓大小觀眾彷彿被「吸入」繪本世界之中,讓繪本的美好在生活場域產生意義,在心內萌芽。
➤春天張開擁抱的大手,召喚海灣好友重返魔法森林
「這裡真的很好拍!」喜扮浪漫花仙子與唯美小公主的網美,絕對會愛上這個春日市集。位於港區藝術中心對面、清水眷村文化園區後方,置身稻浪中央的海灣繪本館,本次館慶邀請了20位創作型特色品牌職人共襄盛舉,在園區各處運用花露香氛、春日花束、植感手作等浪漫素材妝點會場,並採擷春季限定花果、香草入饌私廚料理,一次讓視覺、味覺、嗅覺都好滿足。
草地派對有魔術、音樂、故事劇場等精彩表演,其他還有日本西川流專家規畫的和服禮儀和浴衣體驗、大地藝術共織營的「裂布編織」手作教學,現場挑戰試作杯墊、鍋墊、動物小窩、置物提籃等,讓舊衣重獲新生。館方也準備了小朋友限定的好玩活動:尖尖故事屋與孩子們分享呼應季節的繪本故事《春天真的來了》,以此為主題進行集體彩繪,運用手心或畫筆,自在地將繽紛多彩的顏料塗抹於白紙,描繪出春天的樣貌。參加小小獨角鯨成長訓練營的孩子,則可戴上獨特的彩虹小角,化身為一頭小角鯨,學習控制頭上的角,安全愉快地與小夥伴在園區律動。
自認永遠懷揣18歲少女心的黃淑娥,是海灣文化創意協會理事長,也是催生本次館慶花開燦爛的策展人。她表示,因為疫情,海灣沉寂了很長一段時間,去年市集也停辦了。為了回應整年沒見的好友們,海灣在本次館慶裡刻意創造許多儀式感,猶如大自然對世界發布萬象復甦的信息,不只召喚繪本小精靈們回到這座魔法森林,也宣告海灣在後疫情時代重新張開擁抱的大手,溫暖地面對群眾,迎接嶄新開始。
➤主打清水在地創作者,向世界展現豐沛能量
滿溢奇想風格的海灣繪本館,最廣為人知的象徵就是療癒系代表「大翅鯨」了!今年,畫風夢幻且熱愛海洋的創作者查理宛豬,以超過2周的時間駐地,親手將筆觸細緻、色彩飽滿的大翅鯨與鯨寶寶繪製在館牆:背著三幢繪本屋的大鯨魚溫暖展翅,守護翅脊下的鯨寶寶。鯨背上的小屋以繪本為結構,揉合蒸氣龐克元素與懷舊美學,彷彿時間之流使尾鰭齒輪轉動,承載海灣繪本館的大翅鯨,在想像力的汪洋裡游過數載春夏秋冬。
海灣繪本館內,天花板垂掛的白蓬蓬雲朵大翅鯨也翻新。策展經理蘇鈞偉趁著疫情諸多外務停擺的空檔,將館內損毀汰換下來的繪本打成紙漿,以循環再生的概念,讓這些服務過眾多讀者的退役繪本們重生為大翅鯨立體裝置2.0,繼續佇留在海灣,俯瞰館內,守護著大家。
「5年前,我們以在地創作者玉米辰的作品作為開館示範;5年後,就像大翅鯨的洄游一樣,我們也希望展覽主題回歸到在地創作者身上,藉此讓大家看見——只要有豐沛的創作能量,即便在偏鄉,也能向世界發光。」
負責統籌海灣所有展覽規畫設計的蘇鈞偉,是南藝大視覺藝術出身,曾參與創作台灣燈會主燈,有扎實的立體裝置經驗。他在為Openbook進行導覽時,說明了本次主打王書曼的意義,不只在為創作者帶來信心,也能為人們帶來各種參與的想像。
王書曼過去總是將自己隱身在清水家中與作品背後,無論採訪、演講或展覽都鮮少答應外界邀請。她指著自己眼睛上的黑輪回應道:「不是我拒絕跟外面接觸,而是我真的花去所有時間埋首工作堆裡(已經到了媽媽會跑來問我『要不要餵你吃飯?』的地步)。這次之所以會答應辦展,是因為對清水有一份使命感,此外也是被海灣繪本館的理念與熱情給深深打動。」
➤「繪本。與我們之間」化故事為情境,4種展間各異其趣
王書曼主題展「繪本。與我們之間」,觀眾第一眼見到的入口意象,取自她描繪祖孫情感的作品《爺爺的散步道》。海灣利用館內廊道模擬書中場景,連同網路募集到的祖孫故事及照片合併展出。觀眾進入廊道,即走入繪本之中,並在此遇見他者的真實人生。館方希望藉此觸發每個觀眾心中深藏的回憶、重拾親情帶來的感動,讓《爺爺的散步道》不單單只是繪本故事,也是大家有所共鳴的故事。
穿過廊道來到第一展間,這裡可供讀者近距離了解一部優秀作品如何誕生。其間陳列的物件:工作檯面上的顏料、畫材、工具與現場創作情境,全由王書曼一手布置。展場也陳列插畫家創作至今的所有繪本作品,並設置閱讀角,供親子在模擬的插畫家工作室裡佇留欣賞。
第二展間主題是《火燒厝》。中央擺設金旺機車紙紮實品,討喜地令人跨越了禁忌的刻版印象。現場還提供紙紮材料讓觀眾祈福許願:只要裁下紙片、寫上心願的話,貼到玉皇大帝的「天公座」竹篾上,待展期結束,海灣就會將這件獨特的共創作品焚燒「化掉」,把眾人的祈願傳遞給神明,藉此讓大家了解,無論天上人間,紙紮文化最根本的心意其實是「祝福」。
第三展間是繪本《爸爸的秘密基地》,講述父子相偕探索夜間大自然,尋找最美的祕密。海灣利用螢光漆打造出暗房,再提供紫光燈作為觀眾的探索工具。一打開手電筒,就會發現漆黑夜空裡有銀河閃爍發亮,地面是生態河道,牆上是滿山滿谷的螢火蟲匯聚的神祕森林(還藏有許多小彩蛋!)。暗房內,揭示了螢火蟲的成長過程:河道上的螢火蟲在水中產卵,幼蟲爬到土壤化為蛹,破蛹而出的螢火蟲會再回到河裡產卵,完成一輪生態循環。
蘇鈞偉笑說:「小朋友進來這間,幾乎全都黏住不想走。」他最期待親子能將這次看展經驗帶回現實生活,一起去現地認識真正的生態環境。
最後一個展間,平日供學齡前小朋友活動、學習與創作。本次挑選適合幼幼閱讀的《小廚師阿諾》、《誰的花花繩》與《我們都是“蜴”術家》,搭配花花繩編織成的小帳篷,牆上發表的是《小廚師阿諾》著色比賽成果展。
「童年的經驗,會影響我們長大成為什麼樣的人、想為別人做什麼樣的事。」王書曼說:「小時候爸爸都帶我們去美術館(不然就是公園外丹功運動),結果就是家裡4個小孩都畫畫。我覺得這次主題展詮釋得滿好,如果我還是個孩子,一定每天來報到。我想爸媽若常帶小朋友來這裡玩,說不定長大後他很快就能發現自己喜歡的事物。」
➤海灣共創精神:讓觀眾體驗故事情境,不再「旁觀繪本」
本次王書曼繪本特展定調為「我們之間」——我們跟繪本之間、我們跟海灣之間、我們跟作者之間。事實上,這樣的概念也適合說明海灣歷來舉辦每一場主題展的心意。
館長玉米辰表示:「海灣繪本館的架構有幾個想像。首先,清水畢竟是偏鄉,過去接觸創作者的機會並不多,所以我們有個企圖是拉創作者進場,展現作品的同時也讓親子可以接觸到作者,這個經驗是偏鄉比較少有的。」他說:「這同時也是海灣基本的核心引擎,圍繞這個核心的參與者,扮演的角色將不再純粹只是個觀眾,許多非繪本、圖像的創作者也可以參與進來,轉化各種形式、活絡這個場域。」
此外,志工是海灣很重要的動力。即便志工最初加入海灣是為了自家小孩的成長體驗,但孩子長大後,依然有很多家長留下來成為志工,服務更多喜歡繪本的大小朋友。大家在此參與、學習、收獲,相對地也願意貢獻己力、付出回饋。玉米辰說:「相較於物質與金錢的投入,這樣的能量反而是比較大的。經營志工隊其實很辛苦,但過程中慢慢找到大家不同的專長與扮演的角色,也就慢慢形塑出支持館場持續運轉的動能。」
回顧海灣5周年來的主題展,運用多媒體的裝置或形式,理解創作者作品精神後,打破紙上閱讀的限制,營造出十足趣味又具有高互動性的實體場景,接著再把讀者拉進繪本故事情境來,正是海灣的拿手絕活,也是幾年來蘇鈞偉帶領志工隊參與共創的成果。他說:「我們塑造繪本情境所產生的帶入感,會觸發觀眾自己的過往經驗,讓讀者不再只是個『旁觀繪本』的人。」
➤「等待天使系列繪本展」:一場走入罕病世界的沉浸式邀請
讓觀眾感同身受的帶入感,展現在2020年「等待天使系列繪本展」尤為鮮明。該系列介紹罕病的故事,4個展間分別介紹自閉、腦麻、妥瑞與亞斯的孩童。蘇鈞偉把入口設計成一扇門,作為觀眾走入同理罕病世界的邀請。
《弟弟的世界》描述主角因拯救小鳥而逐漸敞開心胸、接納世界。觀眾可以從小鳥的視角(例如:一同渴望地凝視窗外自由的世界),來理解自閉男孩不同階段的心境轉變。
《啄木鳥女孩》主角只剩脖子和頭可以活動,於是她用頭部裝置的畫筆來點出畫作。這是個悲傷的房間,天花板的雲朵滴下淚來,窗上是啄木鳥女孩點出的畫作,窗框裡,就是她躺在床上看向戶外的景像。
《青蛙小王子》改編自經典童話青蛙王子。妥瑞男孩喜歡游泳,所以整個展間化為水池,甚至有荷葉漂在水面(天花板)上,令人有如置身池底,感覺相當沉浸。
《亞斯的國王新衣》改編自國王的新衣。故事中的主角對昆蟲極度狂愛,因此展間完整重建他的房間,讓大家感受亞斯男孩專注的眼裡只有昆蟲,他的世界完全被昆蟲所圍繞。
➤重現繪本裡的真實:展間裡竟然有雜糧攤子與池塘?!
海灣擅長把繪本裡具有代表性的物件,建置到現實世界。透過實體化,讓讀者的美好幻想成真,賦予閱讀過程更多實感,同時也打造愉快的觀展經驗,令人會心一笑。
王書曼《火燒厝》展間中,紙紮機車便是典型一例,是貨真價實的市面傳統款式。去年,當海灣展出曾陽晴經典繪本《媽媽,買綠豆》時,也把菜市場裡的雜糧攤子復刻出來。攤位上五彩繽紛的豆豆,可直接作為黏貼畫的素材,讓孩子發揮創意、盡情創作運用。展出生態繪本《水雉的浮葉》時的工程更浩大,幾乎把整座水生植物生態池搬進展間裡,菱角也成為孩子模擬書中水雉的創作材料。
2018年張秀毓版畫繪本《阿婆的燈籠樹》展覽期間,舉辦了版畫藏書票實作,也引導小朋友用襪子手作柿子(書中的金黃色小燈籠)。張又然《藍色小洋裝》展出時,館方則設計了植物藍染體驗活動,參照繪本封面的色澤與氛圍,在藍天綠地間創建了一座藍染迷宮,吸引不少網友前來打卡拍照。
在幼幼專屬的展間,海灣貼心設置一面磁鐵牆。在這片牆上,曾經運用《亞斯的國王新衣》設計簡單的科普小遊戲,讓學齡前孩子玩玩昆蟲跟名牌的配對,也曾將《出大甲城》裡的藝閣、陣頭、花車、鑼鼓隊、神明的鑾駕等圖像一一拆解成獨立元件,讓孩子們自由排列組合,學習自己說故事。
➤展覽回顧:邀請讀者與作者、議題互相對話
「對話」也是海灣布展重視的一環,讓作者與讀者有機會平視對話。除了本次王書曼特展布置的個人工作室,過去《子兒吐吐》25周年展,海灣也重現了李瑾倫旅居英國時的創作空間,展出多年來作家與她的粉絲們分別帶著小豬「胖臉兒」等三隻娃娃環遊世界的照片。Ballboss展出《出大甲城》時也有多媒體規畫,用投影方式供讀者觀看他的創作紀錄,包括在英國時的發想、繪畫手法與效果。
與作者對話之外,海灣也積極邀請觀眾與議題對話。除了前述「等待天使」關懷罕病兒童之外,另有「被愛被看見」人權繪本展,突顯政治受害者的生命歷程。《愛唱歌的小熊》、《說好不要哭》、《希望小提琴》分別以白色恐怖受難者蔡焜霖、陳欽生、陳孟和等人的親身經驗為藍本,讓讀者可以體會大時代下身不由己的苦處。生態環保方面,則有《斯氏紫斑蝶的傳說》、《水雉的浮葉》、《幸運的一群》等,讓孩子們珍惜生態環境。海灣並邀請相關領域專家舉辦繪本主題沙龍,為小朋友規畫生態主題的周末故事派活動,進而加深對繪本主旨的印象與了解。
海灣也邀請不具繪本專業、但對圖像充滿熱情的素人,以創作作品為媒介與觀眾對話。像是2018年舉辦過自閉症女孩林依慧與媽媽蔡威君共同創作的《瑪莉不說話》原畫展;2019年為9歲的妥瑞小李子所創作的《月亮婆婆愛吃糖》、《驕傲的小吉》舉辦繪本展。
➤展覽回顧:邀請志工與讀者參與共同創作
對話之餘,與海灣進行更深度連結的方式,就是開放共同創作了。共同創作分為兩種型態:開放一般大眾報名參加,或者讓志工參與協助。
本次主題展規畫的《火燒厝》天公座祈願、《爺爺的散步道》祖孫故事募集、《小廚師阿諾》的著色比賽成果展,都是屬於開放大眾參加的共創活動。志工參與的部分則包括布置《爺爺的散步道》廊道中翩翩散落的樹葉;協作《啄木鳥女孩》天花板上的雲朵、雨滴,還有啄木鳥裝;動手創造出《亞斯的國王新衣》生態箱裡黏土做的昆蟲以及給參觀者戴的甲蟲帽。連以繪本紙漿打造的大翅鯨,其實也都是蘇鈞偉帶領志工一步步製作出來的!
蘇鈞偉表示,相較於大眾型的開放體驗,邀請志工加入館員行列,一同捲起袖子、合作展前籌備的美術與陳設作業,更能讓志工們切身感受繪本空間所創造出來的氛圍,是如何在自己手中從零到有、具現成型,再巧妙地傳遞給觀展者。
「海灣繪本館包括我在內只有3位館員(而且平均年齡不到30歲),所以必須借助志工們的能力,才有辦法製作這麼多裝置。志工隊成員有各式各樣的經驗專長、才藝及興趣。這些組成可以做哪些事情,讓我們的工作變得非常有機。」蘇鈞偉說。
➤ 開繪本館就像桃太郎打怪,需要小動物來幫忙
3位館員中,暱稱采采的蔡采縈是海灣協會發起人之一,也是現任執行長。「在稻田中央這麼偏僻的地方開繪本館很少見,一開始地方上的民眾還以為我們是帶小朋友畫畫的安親班。我們3個就像桃太郎打怪一樣,幸好一路上有很多小動物來幫忙。」自2017年海灣繪本館開館後,家長漸漸在這裡聚集,也開始一起腦力激盪,想做些對社會、對環境有幫助的事,也得到了一些成就感、找到生活的意義。
海灣志工來自四面八方,蔡采縈如數家珍地分享:「像隊長就不是我們海線在地人,而是山線那邊的大里人,還有遠從台北來的家長加入志工,她的老家並不在中部,所以完全是衝著海灣繪本館而來。」
在數位時代,地點已經不是問題,認同才是把人凝聚在一起的原因,就像「飛地」的概念,海灣散發出不受區域限制的吸引力。
「鄉下不會變都市,我們也不期待變都市,而是把連在地人都未必看見的優點端出來,讓有共同想法的人,無分遠近都可以加進來。」談到這,蔡采縈接著說:「透過繪本這個敲門磚,可與民眾對話、可以發現議題、可以共創,還可以把這裡當成自己的一部分——海灣繪本生活圈就是我們的目標。」
王書曼在認識海灣後,羨慕來到這裡的小朋友能接觸豐富資源與多元體驗,說讓人很想重讀小學、幼稚園。蔡采縈也深有同感:「我小時候認識的書只有課本,而且只在上學時才會打開它。直到國中,朋友帶我去圖書館,才發現原來書是這種東西,跟我想的不一樣,而且裡面一定找得到你感興趣的所有一切。當時也因為喜歡那個環境,我才知道原來自己能念書。」
成長過程中的這份美好發現,讓她長大成人後,也想透過海灣持續分享給大家。蔡采縈還笑道,如今已經有民眾會跑來對她說:「你們在這裡實在太棒了!如果有人想把你們趕走,我一定第一個拉白布條對抗到底!」
➤後疫情時代:聚焦本土、培訓講師,讓繪本的美好開枝散葉
海灣館舍平日有大、中、小班的「趣淘PG共學團」,有興趣的民眾也可加入社群,一起共學。假日,海灣繪本館開放一般群眾參觀,除了定期舉辦「周末故事派」跟「故事接接力」,打開繪本說故事、玩遊戲、做手作,大人也可參加。炎炎夏日,海灣更會針對國小學童,舉辦每梯次5至7天的暑假夏令營,內容從自然生態、藝術雕塑到料理課程,無所不包,也帶小朋友接觸繪本提到的實物實景實地,活動相當多元。此外,海灣也積極進行故事種子講師的培訓,讓繪本的美好能透過故事講師,開枝散葉。
去年因應嚴峻疫情,實體活動無法如期舉行,海灣便開始嘗試發展多媒體故事培訓、錄製並發布線上故事派影片,同時,也著手創設多媒體課程、多媒體讀書會。接下來,海灣預計會成立專屬線上頻道與節目,以讓讀者接觸繪本、認識海灣的管道更加多元。藏書方面,海灣在今年度也有大幅度調整。過去海灣廣收國內外繪本,如今則聚焦於台灣原創繪本,希望能以更多的精力與能量,關注並支持台灣繪本作家。
黃淑娥表示:「近年,台灣本土繪本作家創作量相當大又豐富,因此現階段我們將以發掘本土能量為核心,用幾年的時間先把根扎得更深更穩一點,未來我們將打開不同的視野,與歐美、日本進行交流,屆時就有更大的能量向國際自我介紹了。」●
【繪本。與我們之間——王書曼繪本特展】
地點:海灣繪本館(臺中市清水區中社路54號)
日期:2022/3/13-6/5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