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砒霜留給自己
Mr. Pizza著,逗點文創結社,350元
推薦原因: 文 樂
本書的主角大多為青少年,正處於青春的尷尬期。針對此一尷尬期為題材的作品當然很多,但作者更具體而微地描述了今日香港的生活情狀。在這個已經全球化的時代,本書展現了香港慘綠少年的地方書寫。【內容簡介➤】
●嬰兒涉過淺塘
羅毓嘉著,寶瓶文化,280元
推薦原因: 議 文 樂
作者的文風向來有種嘩啦啦的射精感,施之於社會批判尤其爽氣,簡直解氣,就算你不知道他在講什麼,照樣可以在那些噴出來的字句裡得到救贖的快感。
本書以詩寫政治社會等議題,用字準確,少有曖昧的空間,批判的針灸針針扎在穴位上,入肉三分,逼人直視現實,銳不可當。【內容簡介➤】
●Comme un chef:一個作家的料理練習曲
Comme un chef : Une autobiographie culinaire
文字:貝涅.彼特(Benoît Peeters),漫畫:海月水母(Aurélia Aurita),韓書妍譯,積木文化,550元
推薦原因: 文 樂
本書是用料理來介紹法國思想的漫畫書,運用食物勾勒出深層的法國文化,令人非常欣喜。漫畫呈現了在法國文化潮流裡,哲學、料理、電影與漫畫具有同樣的崇高地位,都是藝術的創作形式。譬如貝涅.彼特的指導教授因羅蘭巴特意外過世,改向電影符號學者Christian Metz求學,結果寫不出論文的結果也讓人會心一笑,這一切的交匯讓人感受到法國文化的獨特。【內容簡介➤】
●食與時
透過秒、分、時、日、週、月、年,看時間的鬼斧神工如何成就美味
The Missing Ingredient: The Curious Role of Time in Food and Flavour
珍妮.林弗特(Jenny Linford)著,呂奕欣譯,臉譜出版,420元
推薦原因: 知 思 樂 獨
汆燙要快,多個幾秒肉就老了;醃蘿蔔求慢,20年的老菜脯入湯甘甜如天堂。作者剔出料理中時間這個度量衡,細說烹飪史上,老饕如何發現光陰會成就不同風味,拿捏快慢,切出人類飲食史上美味多汁的剖面。
下廚者皆知,烹飪除了食材原料外,最能展現烹飪功力的就是「火侯」的掌握。本書成功運用了時間這個維度去討論烹飪,非常有意思。另外,作者亦提出極具啟發性的概念,特別是目前強調以文化史概念來建構食物史的討論,將全書拉到新的討論高度。【內容簡介➤】
●高爾基公園
Gorky Park
馬丁.克魯茲.史密斯(Martin Cruz Smith)著,巫聿文、彭臨桂譯,聯經出版,480元
推薦原因: 樂 獨
冷戰時期的美蘇對抗,特別是相關的諜報戰情節,長期地支配了親西方陣營娛樂論述的發展。這本經典諜報小說,透過細緻的文學描述手法,再次引領讀者回到那個看似遙遠的冷戰情境。【內容簡介➤】
●橫尾忠則×9位經典創作者的生命對話
不是因為長壽而創造,而是因為創造而長壽
橫尾忠則著,李璦祺譯,大田出版,399元
推薦原因: 樂 獨 益
橫尾忠則與他的同輩大家對談,各個都是領一時風騷的傳奇人物,東拉西扯,不打高空,卻處處風景。一大部分都在談老之已至,卻毫無朽氣,不時迸出一兩句可以裱起來的金句,像燒透了的炭,暖烘烘地不見火苗。活到老,玩到老,看來也唯有創意和玩興,才是歲月不敗的抗老仙丹。
透過作者高超的訪談與撰文,9位高齡創作者呈現出對生命發展的強烈好奇心,讀來令人欽羨,同時也產生更多力量。【內容簡介➤】
●犬之島
犬ヶ島
原作:威斯‧安德森(Wes Anderson),漫畫:望月峰太郎(望月ミネタロウ),馬世儀譯,大塊文化,280元
推薦原因: 思 議 樂 獨
相較於動畫強調人狗之間的情誼,望月峰太郎的漫畫創作分外冷峻,粗獷筆觸突顯末日的荒涼氛圍。被流放的狗群如賤民,與國家機器對峙,賦予這個故事較為政治的現實意涵。【內容簡介➤】
●犬之島 動畫電影製作特輯
威斯.安德森作品集
The Wes Anderson Collection: Isle of Dogs
蘿倫.威佛(Lauren Wilford)、萊恩.史蒂文生(Ryan Stevenson)著,俞智敏、李建興、林潔盈譯,大塊文化,980元
推薦原因: 樂 獨
導演想推動情節或渲染氣氛,即便只是一分鐘24格,都需要技術人員的技藝心血促成。本書是細節控的最愛,從戲偶管理、動畫製作、攝影和配音,所有幕後人員全上陣將眉角一一道來,詳解動畫電影,完整呈現從導演意念到畫面成果的流程。詳盡的說明、豐富的圖片搭配清楚明瞭的圖說,可看到作者引導讀者思緒的用心。【內容簡介➤】
知識性.設計感.批判性.思想性.議題性.實用性.文學性. 閱讀樂趣.獨特性.公益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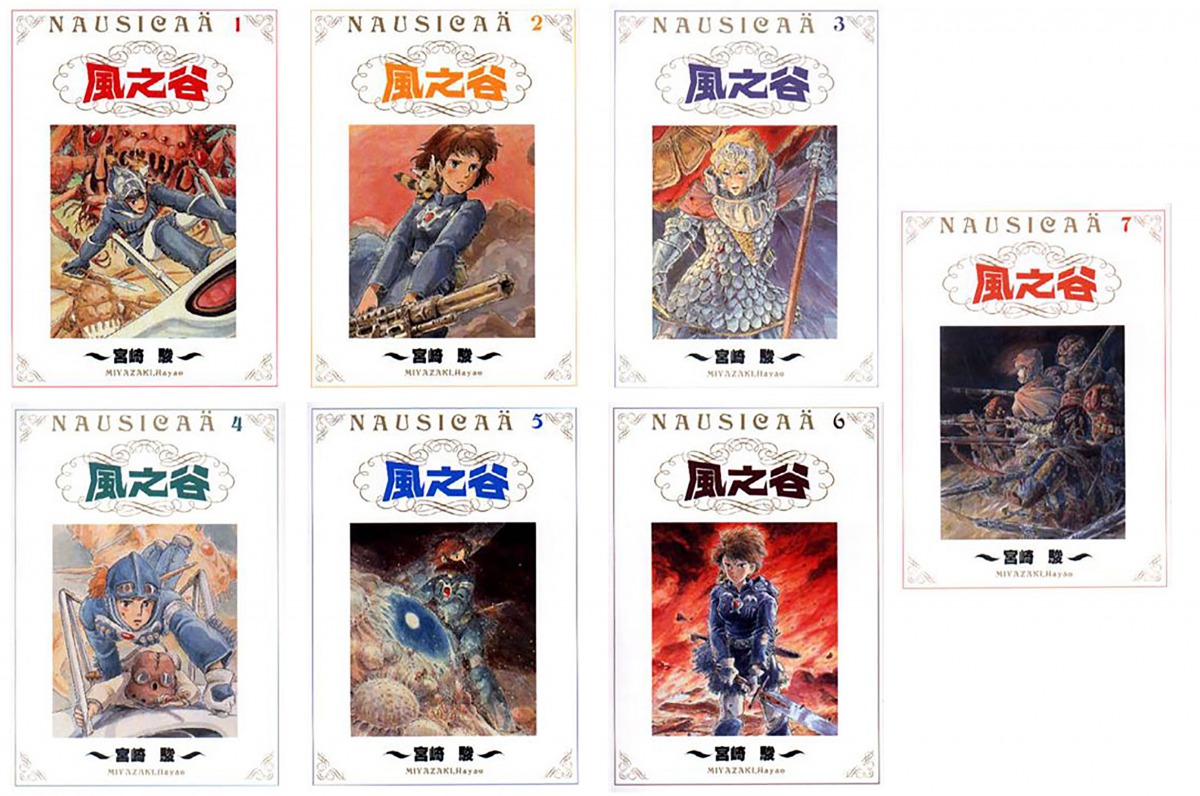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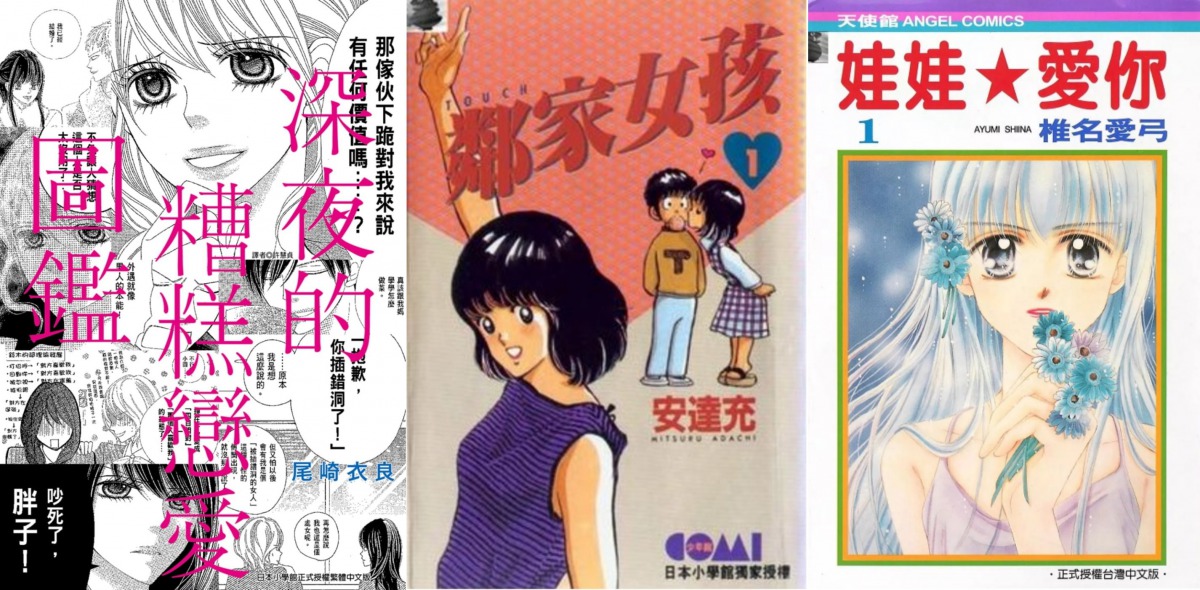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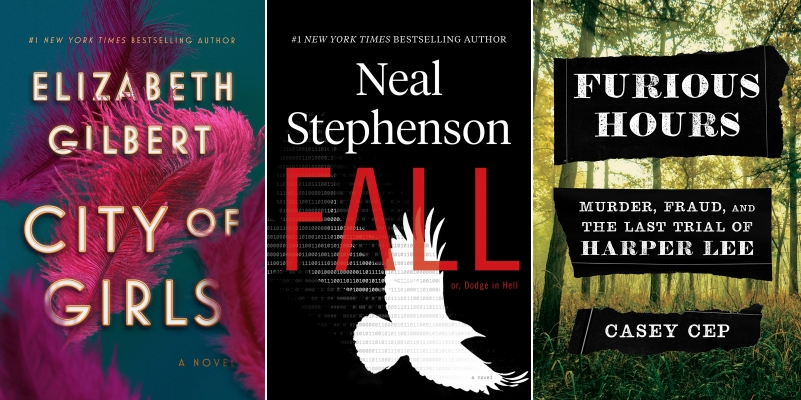

OB短評》#186 颯爽解氣的極品好書懶人包
●把砒霜留給自己
Mr. Pizza著,逗點文創結社,350元
推薦原因: 文 樂
本書的主角大多為青少年,正處於青春的尷尬期。針對此一尷尬期為題材的作品當然很多,但作者更具體而微地描述了今日香港的生活情狀。在這個已經全球化的時代,本書展現了香港慘綠少年的地方書寫。【內容簡介➤】
●嬰兒涉過淺塘
羅毓嘉著,寶瓶文化,280元
推薦原因: 議 文 樂
作者的文風向來有種嘩啦啦的射精感,施之於社會批判尤其爽氣,簡直解氣,就算你不知道他在講什麼,照樣可以在那些噴出來的字句裡得到救贖的快感。
本書以詩寫政治社會等議題,用字準確,少有曖昧的空間,批判的針灸針針扎在穴位上,入肉三分,逼人直視現實,銳不可當。【內容簡介➤】
●Comme un chef:一個作家的料理練習曲
Comme un chef : Une autobiographie culinaire
文字:貝涅.彼特(Benoît Peeters),漫畫:海月水母(Aurélia Aurita),韓書妍譯,積木文化,550元
推薦原因: 文 樂
本書是用料理來介紹法國思想的漫畫書,運用食物勾勒出深層的法國文化,令人非常欣喜。漫畫呈現了在法國文化潮流裡,哲學、料理、電影與漫畫具有同樣的崇高地位,都是藝術的創作形式。譬如貝涅.彼特的指導教授因羅蘭巴特意外過世,改向電影符號學者Christian Metz求學,結果寫不出論文的結果也讓人會心一笑,這一切的交匯讓人感受到法國文化的獨特。【內容簡介➤】
●食與時
透過秒、分、時、日、週、月、年,看時間的鬼斧神工如何成就美味
The Missing Ingredient: The Curious Role of Time in Food and Flavour
珍妮.林弗特(Jenny Linford)著,呂奕欣譯,臉譜出版,420元
推薦原因: 知 思 樂 獨
汆燙要快,多個幾秒肉就老了;醃蘿蔔求慢,20年的老菜脯入湯甘甜如天堂。作者剔出料理中時間這個度量衡,細說烹飪史上,老饕如何發現光陰會成就不同風味,拿捏快慢,切出人類飲食史上美味多汁的剖面。
下廚者皆知,烹飪除了食材原料外,最能展現烹飪功力的就是「火侯」的掌握。本書成功運用了時間這個維度去討論烹飪,非常有意思。另外,作者亦提出極具啟發性的概念,特別是目前強調以文化史概念來建構食物史的討論,將全書拉到新的討論高度。【內容簡介➤】
●高爾基公園
Gorky Park
馬丁.克魯茲.史密斯(Martin Cruz Smith)著,巫聿文、彭臨桂譯,聯經出版,480元
推薦原因: 樂 獨
冷戰時期的美蘇對抗,特別是相關的諜報戰情節,長期地支配了親西方陣營娛樂論述的發展。這本經典諜報小說,透過細緻的文學描述手法,再次引領讀者回到那個看似遙遠的冷戰情境。【內容簡介➤】
●橫尾忠則×9位經典創作者的生命對話
不是因為長壽而創造,而是因為創造而長壽
橫尾忠則著,李璦祺譯,大田出版,399元
推薦原因: 樂 獨 益
橫尾忠則與他的同輩大家對談,各個都是領一時風騷的傳奇人物,東拉西扯,不打高空,卻處處風景。一大部分都在談老之已至,卻毫無朽氣,不時迸出一兩句可以裱起來的金句,像燒透了的炭,暖烘烘地不見火苗。活到老,玩到老,看來也唯有創意和玩興,才是歲月不敗的抗老仙丹。
透過作者高超的訪談與撰文,9位高齡創作者呈現出對生命發展的強烈好奇心,讀來令人欽羨,同時也產生更多力量。【內容簡介➤】
●犬之島
犬ヶ島
原作:威斯‧安德森(Wes Anderson),漫畫:望月峰太郎(望月ミネタロウ),馬世儀譯,大塊文化,280元
推薦原因: 思 議 樂 獨
相較於動畫強調人狗之間的情誼,望月峰太郎的漫畫創作分外冷峻,粗獷筆觸突顯末日的荒涼氛圍。被流放的狗群如賤民,與國家機器對峙,賦予這個故事較為政治的現實意涵。【內容簡介➤】
●犬之島 動畫電影製作特輯
威斯.安德森作品集
The Wes Anderson Collection: Isle of Dogs
蘿倫.威佛(Lauren Wilford)、萊恩.史蒂文生(Ryan Stevenson)著,俞智敏、李建興、林潔盈譯,大塊文化,980元
推薦原因: 樂 獨
導演想推動情節或渲染氣氛,即便只是一分鐘24格,都需要技術人員的技藝心血促成。本書是細節控的最愛,從戲偶管理、動畫製作、攝影和配音,所有幕後人員全上陣將眉角一一道來,詳解動畫電影,完整呈現從導演意念到畫面成果的流程。詳盡的說明、豐富的圖片搭配清楚明瞭的圖說,可看到作者引導讀者思緒的用心。【內容簡介➤】
知識性.設計感.批判性.思想性.議題性.實用性.文學性. 閱讀樂趣.獨特性.公益性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