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題》來自迷宮的情書:蘿倫.葛洛芙《瑪麗迷宮》寫作幕後
2015年,美國小說家蘿倫.葛洛芙(Lauren Groff)以《完美婚姻》(Fates and Furies)登上暢銷書榜、備受書評讚譽。接下來幾年,各界都對她的下一部長篇小說充滿期待。
2021年秋天,在Covid-19疫情開始獲得控制之際,葛洛芙交出了《瑪麗迷宮》(Matrix)這部歷史小說,帶領讀者回到12世紀的古老英格蘭,經歷修女院內一場全新的革命。
葛洛芙曾表示,這個故事一方面源自她長期對中古法語文學的喜愛,又剛好碰到一個機緣,對當時的修女生活有了種種新的了解。而另一方面,則來自她身處這個時代,內心深處不時有一種暫時擺脫男性的渴望,很想「生活在一個沒有男人的世界,一下子就好。」
於是,這一次,女性是主角、是配角,是所有的角色。
這一次,男性只是幕後陪襯的模糊形影,而且盡皆無名——書裡沒有提到任何男性之名,連神、連國王都不例外。
➤12世紀的「教母」
英文書名Matrix,在本書中有兩個意思。最主要的意義,就是此字源自拉丁文的mater,意為母親。另外一個比較不重要的意義,是指封蠟印模(seal matrix):古代的信件以蠟封口後、在蠟上蓋出印痕的模具(印章)。
故事一開始,17歲的瑪麗獨自騎馬來到英格蘭鄉間,初次看到她的新家:山丘上的修女院。那是冬季的尾聲,細雨中一片毫無生氣的灰天灰地,令人絕望。
在書中,瑪麗是母親被強暴而產下的私生女。以當時的法律,在母親過世後,孤女瑪麗不能繼承任何財產,勢必飽受親族欺辱。於是她只能逃離法蘭西家鄉,渡海來到英格蘭宮廷,投靠同父異母的英格蘭國王。

瑪麗身材高大,會4種語文,能言善辯,還能騎馬使劍,甚至曾跟隨母親、阿姨們參加過第二次十字軍東征。然而,雖然血緣上貴為英格蘭王室的庶出公主,她卻沒有美貌、沒有任何當時女性所應有的「美德」,於是被王室認為很難嫁掉。最後,就像那個年代貴族人家排行比較後面、性格或長相比較不討喜的女兒,瑪麗就被遣去鄉下一所王室修女院,名義上是擔任副院長,其實形同放逐。
在這裡,瑪麗從一個滿心想逃離的憤怒少女,逐漸蛻變為成熟強大的領導人。她發揮經營天賦,善用修女姐妹們的各種才能,把糧食短缺、飽受疾病肆虐的修女院一手救起。她渴望權力又擅長權術,對內收服各種不同性格的姐妹與依附修女院的佃農,對外編織自己的情報網,抵抗男性當道的教會與現實世界。日後她接手院長,更是得心應手,造迷宮、建新院、築水壩,把這所修女院打造成欣欣向榮、富甲一方的女性樂園。
如果要用一句話介紹這本書中的瑪麗,最準確的說法,應該就是《美國今日報》(USA Today)書評中的形容:一個12世紀、穿著修女會衣的麥可.柯里昂。(Michael Corleone,電影《教父》的主人翁。)
➤原型人物:法蘭西的瑪麗
葛洛芙一直喜愛、熟讀中世紀女詩人法蘭西的瑪麗(Marie de France)的作品,在就讀安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期間,還曾經考慮主修中世紀法語,而且長年來自己私下一直在寫詩。

幾年前,在哈佛大學雷德克里夫學院(Radcliffe College)提供的傑出人才駐校計畫期間,葛洛芙聽了一位同時間駐校、專門研究中古宗教女性歷史的學者凱蒂.布吉許(Katie Bugyis)的演講,據葛洛芙的形容,當時她覺得就像是「腦袋裡爆出彩虹」。本來她正在摸索中的幾個寫作計畫,其中一個就與中世紀有關,她說她當下就知道,下一個要寫的就是這個:中世紀修女院中女人的故事;而且她長年深愛的女詩人法蘭西的瑪麗,就會是書中的主角。
法蘭西的瑪麗是據知第一位以法文創作的女詩人,歷史上的資料十分稀少,而且多半出於推測。不過正因為可信史料極度缺乏,也就給了葛洛芙一張幾乎完全空白的畫布,讓她能夠以虛構的故事,重新創造出歷史。
凱蒂.布吉許在演講中指出,根據文件和考古挖掘出牙齒殘骸中的檢驗結果,現代學者發現中世紀的修女曾經從事經書抄寫,以及為手抄本繪製裝飾插圖的工作——以往這些工作是男性限定,因為當時大家公認,只有男性有能力、有資格做。
歷史學界對於中世紀修女生活的種種新發現,讓葛洛芙一聽就迷上了,還一再找布吉許求教、長談。經由布吉許的介紹,葛洛芙發現中世紀修女院的生活,完全不同於一般想像中的枯燥無聊,而是複雜、知性,而且充滿機會與可能性。「她們困在自己的時代和性別中,卻有辦法以她們不該從事的書寫,予以反抗。」葛洛芙說。而中世紀種種豐富的神話、魔法、傳說,也為本書的內容增色不少。
➤不同的黑暗,一樣的光
葛洛芙曾在訪談中表示,活在當今這個時代,面對專制主義抬頭、全球暖化等等問題,她努力思索種種痛苦、憤怒、悲傷,覺得太壓倒性、太難以承受了,讓她感覺自己無法理智地掌握,給這個時代公正的評價。
「我不想直視現狀,因為我知道我的觀察會失敗。」葛洛芙說,於是她愈來愈相信,回顧過去,才是記錄這個時代最好的方式。
在《瑪麗迷宮》中,她帶領讀者的目光回到9個世紀前,看到了眾多不凡的女性,如何在那個所謂的「黑暗時代」中持續發出耀眼的光。「當女人接受任務時,竟然能做得這麼好!她們的能力似乎無可限量。」書中的瑪麗這麼說。
對照今日世界的女性處境,儘管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但是女性力量的強大、所能達到的成就,在某些地方已經不再是妄想或寓言,而是逐一成為現實了——只要她們能得到應有的機會。
本書卷首題獻是「獻給我所有的姐妹們」。的確,這本以12世紀女神、仙女、女性所編織的歷史小說,正是一部獻給21世紀所有姐妹的情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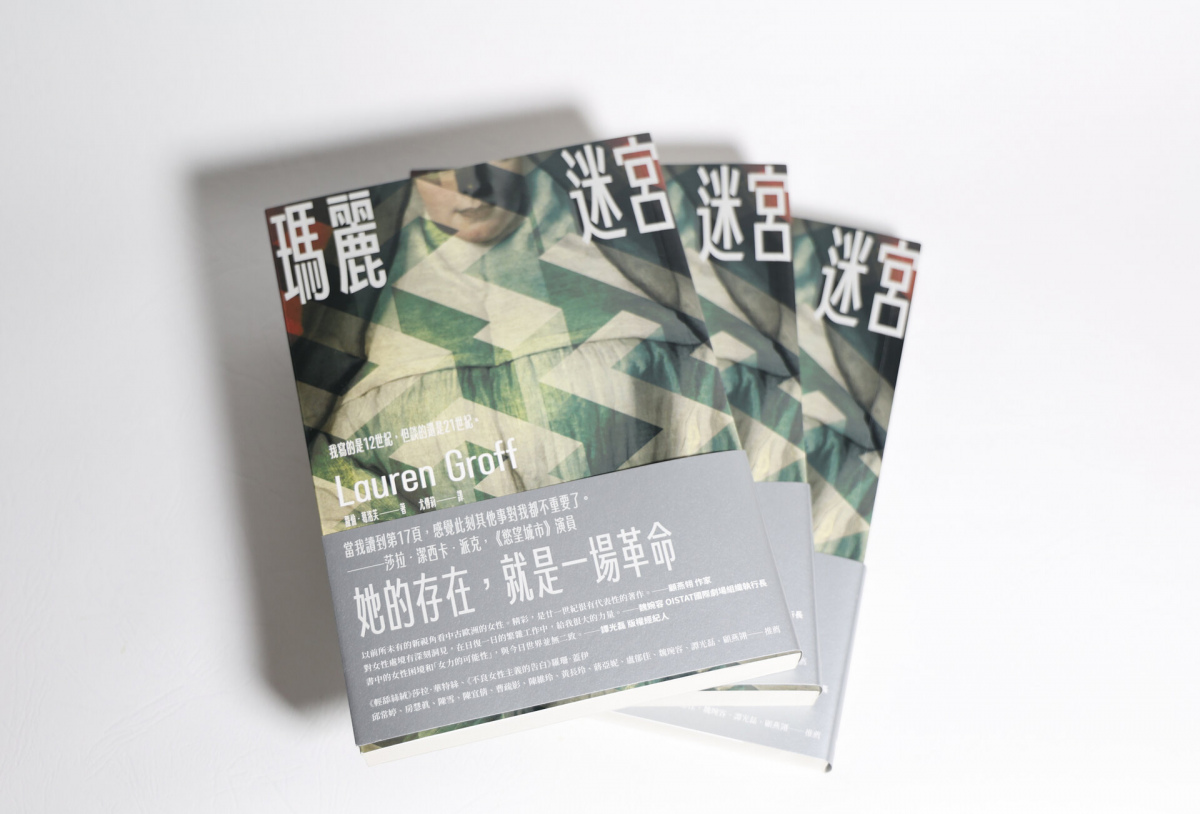
|
|
|
作者簡介:蘿倫.葛洛芙 .當代美國最優秀的作家之一 第一部小說《坦柏頓暗影》在她29歲時出版,迅速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榜,亦開啟她的作家生涯。如今,《紐約時報書評》形容她具有「罕見天賦」,《洛杉磯書評》指稱她是美國最優秀的作家之一,《紐約客》認為她的作品具備「史詩般革新力量」。 第三本長篇著作《完美婚姻》於2015年上市,因敘事結構精巧,主題富含寓意,先獲全美各大主流與時尚媒體盛讚;同年10月,入圍美國國家圖書獎,年底榮獲美國前總統歐巴馬選書、亞馬遜年度選書,引發好萊塢名媛於社群網站上傳書影、分享心得。叫好叫座極佳口碑,堪稱該年度小說最大贏家。 以2018年出版的小說集《佛羅里達》二度入圍美國國家圖書獎決選,榮獲該年故事獎首獎;2021推出第四部長篇小說《瑪麗迷宮》,再闖進美國國家書卷獎決選名單,獲頒佛羅里達圖書獎金牌獎、喬伊斯.卡洛.奧茲文學獎,入選歐巴馬2021年度愛書、20多家媒體評選年度最佳書籍,再度擄獲書迷的心。 她的作品散見《紐約客》、《大西洋月刊》,短篇小說〈L. Debard And Aliette〉被村上春樹編選進戀愛小說選集。同時多次入選《美國最佳短篇小說》選集。她曾贏得保羅.鮑爾斯獎虛構類獎、美國筆會歐.亨利獎、「手推車」獎和古根漢獎學金,入圍國家圖書評論協會獎。她的小說世界裡,無論描述戀人、親友或陌生人初次見面,都以秀異文采,創造出生動、非比尋常的世界。 個人網站:laurengroff.com/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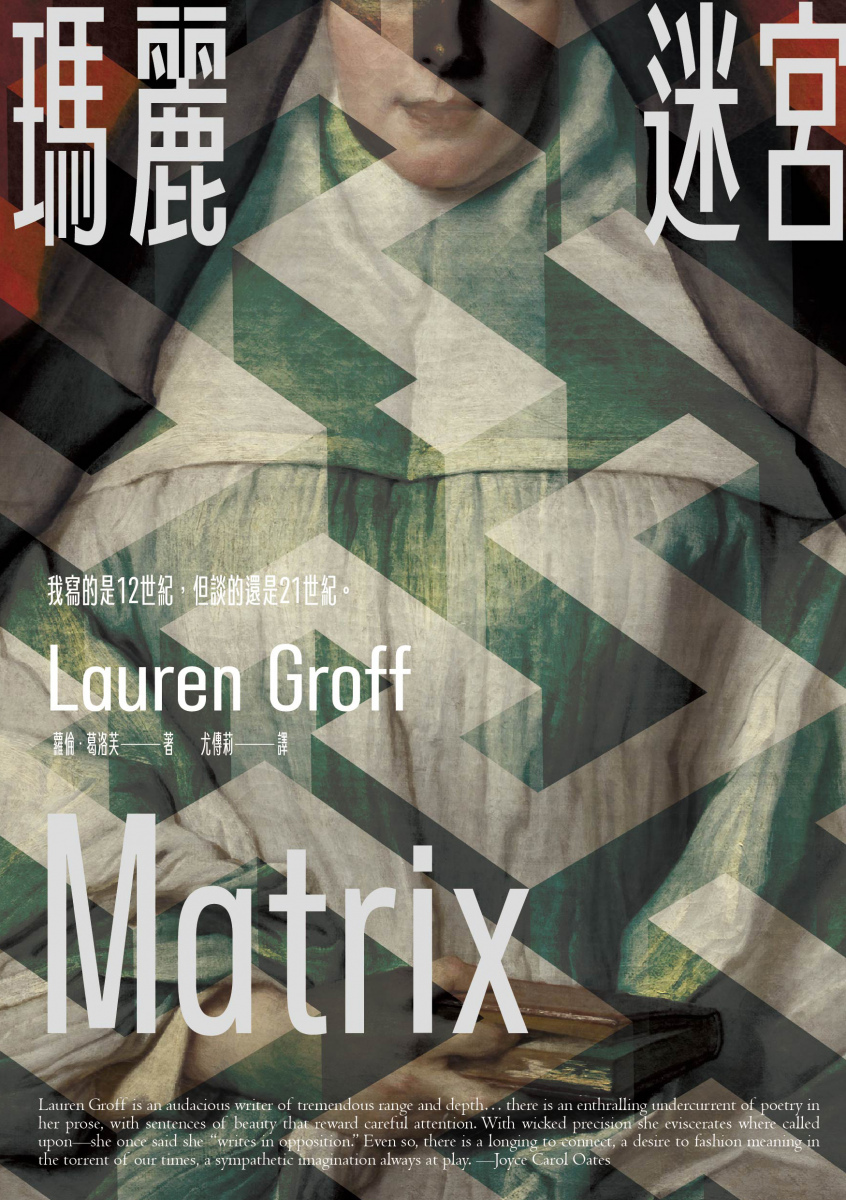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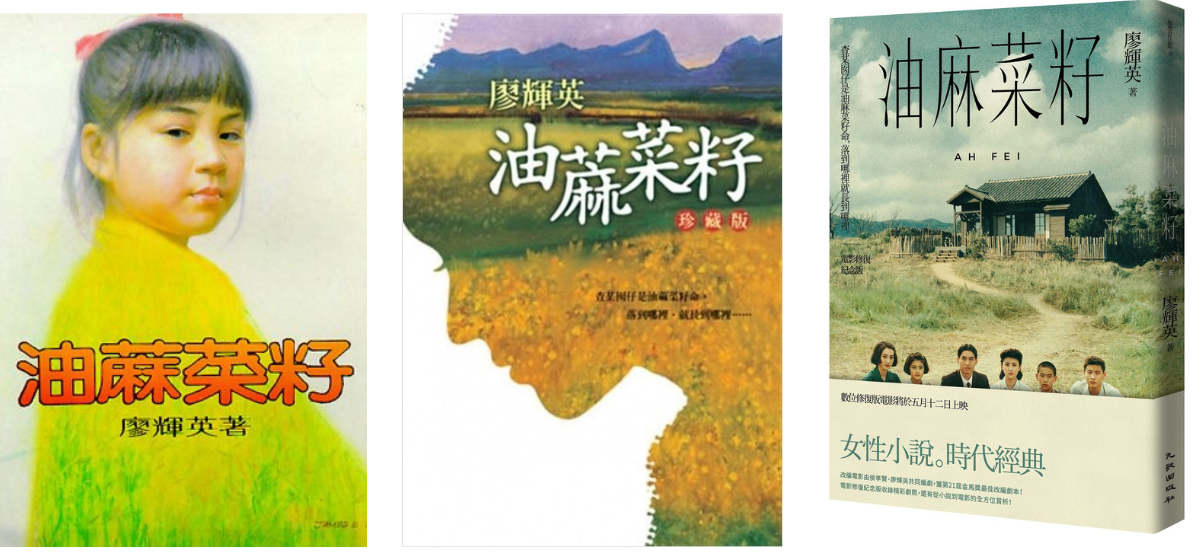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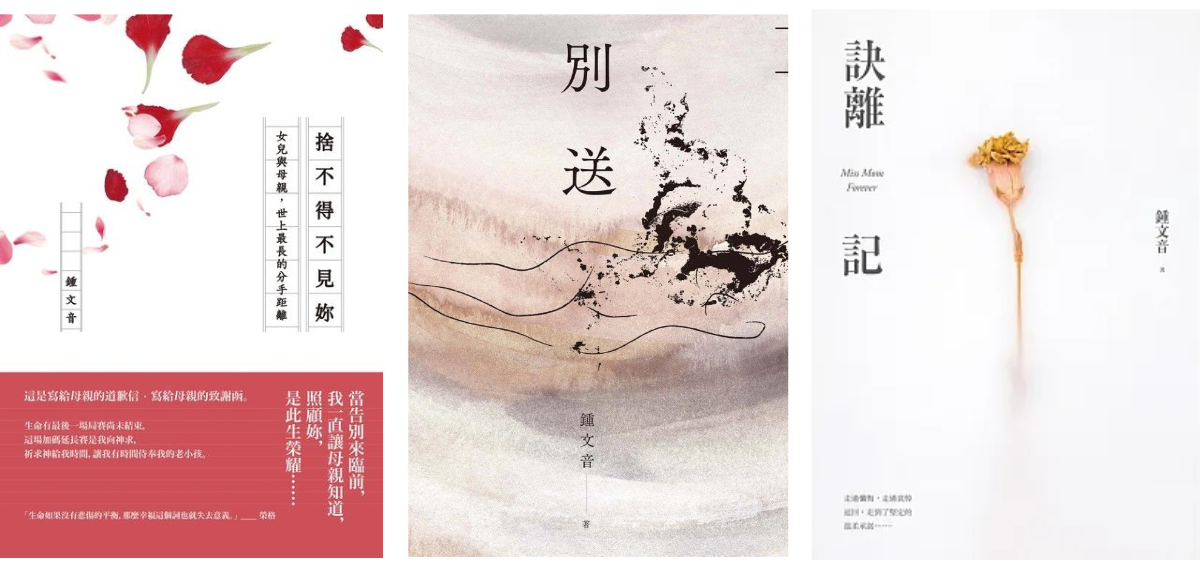

閱讀隨身聽S9EP2》譯者尉遲秀/關於米蘭.昆德拉和那些江湖傳言 ft.台灣法語譯者協會
捷克裔法國籍文學大師米蘭.昆德拉於今(2023)年7月辭世,全球讀者紛紛表示不捨與哀悼。在台灣,提起昆德拉,多數人都會想到他的專屬譯者尉遲秀,他與昆德拉曾因翻譯有不少來往,Openbook閱讀誌特別邀請尉遲秀,分享他所認識的米蘭.昆德拉。另外,尉遲秀也在去年底接任台灣法語譯者協會理事長,他也將分享協會如何在台灣凝聚法語翻譯的能量。節目精彩,請別錯過了。
【精華摘錄】
➤米蘭.昆德拉:「如果您覺得這邊不清楚的話,請把這句刪掉。」
尉遲秀: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一些江湖的傳說,描述我跟昆德拉來往密切。但其實我們並沒有實際見過面,來往主要通過傳真。討論的經過,通常是我在翻譯過程中,看見一些細節的問題。因為他的文字算非常清楚的,在極少數的細節處,一些無關宏旨的描述,因為翻譯連個逗點過不去就是過不去,我便會去問他。他也會回信解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有補上一句說:「如果您覺得這邊不清楚的話,請把這句刪掉」。哇,我看到這句時,壓力好大,腦袋出現的畫面是,我問一句,台灣的讀者就少了一句。
主持人:有時候可能是作者感到不耐煩?
尉遲秀:倒也不是,他是很真誠的,他認為作品應該要很清楚地表達,既然這個細節會造成不明白,那刪掉也是選項之一。他自己寫的一些東西跟詞源學有關,他也曾提過希望把整章拿掉,因為那是他在歐洲語境下探討歐洲的語言。後來我還是把該章保留,因為我覺得那些討論其實繁體中文讀者是可以理解的,但他認為可能會不夠清楚。但他並沒有任何的不悅,他認為文字應該很清楚,不應該有不清楚的表達在作品中。
主持人:他也會用這樣的態度,面對不同語言的譯者嗎?
尉遲秀:這我就不知道了。不過,他曾花兩年的時間,把所有作品的捷克文本通通整理成法文版本,審閱出一套版本。此後,他會要求所有的譯者用最新那版的法文本。當時做翻譯,都會收到新的法文本或他剛寫好的打字稿,有時候會在旁邊空白處,上面、旁邊、下面、側面這類紙張空白的地方,看見他的手寫字。他會提及翻譯時需要留意的地方。
舉個例子,小說《無知》因為是他後來用法文寫的,所以台灣翻譯時,我拿到的是打字稿,上面有幾頁,有他用手寫交代譯者的文字。我印象最深是關於「字詞的重複」。因為法國人對重複用字是非常不喜歡的,很多同義字,比如先用這個字,下次提到時會換一個同義字,重複用字彷彿語言能力不夠好。可是昆德拉特別交代:有些字會重複出現,這是刻意的,請不要用同義字替換,他把這些重複的字圈起來……
➤把敘事的溫度調低
主持人:會不會有另外一個困難,比如有時讀法文,會覺得有韻味。可是翻譯到中文時,反而好像沒什麼文采……
尉遲秀:這在所有翻譯裡都可能出現。其實昆德拉第一個遇到的,反而是他的法文遭到某些作家的批評,認為他的法文就是不好。但以我的法文程度來看,並沒有感受到任何他們提到的問題。在紀錄片《米蘭.昆德拉:從玩笑到無謂的盛宴》裡面,也有看到其他法文作家,對他的文體非常推崇。
我自己翻譯時,反倒覺得中文世界早期的譯本,過於凸顯辭藻,變得更美或華麗一些。我們最早讀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是韓少功先生的譯本。韓少功是小說家,文采不在話下。我不太確定裡面有些問題,是英文譯本造成的(編按:韓少功是依據英文譯本翻譯的),還是韓少功先生用他的方式表現出來的。
我自己讀時,當年就非常喜歡。即使翻譯完,很多地方跟韓少功先生處理方式不一樣,但至今拿他譯本閱讀仍津津有味。像「媚俗」這些字詞,其實都是他翻譯出來。書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雖然有人批評詞意上跟昆德拉有些不同,但是我們還是覺得它很美,出版社也保留原來最早用的書名。
真的要說我跟過去的譯本有何不同,我覺得我很努力把文字的溫度降低一點。雖然講得好像我事前就努力這樣做,但這其實是我後來才發現的,我希望把敘事溫度調低。
➤法語譯者,為何其他語言的譯者感到羨慕?
主持人:最後談到你另外一個身分,你是現任臺灣法語譯者協會的理事長,身兼在臺灣推廣法語與翻譯的重任。
尉遲秀:法國文化部常常會編很多預算在推廣他們自己的文化。所以法語譯者比較受惠,比如法語翻譯會有很多活動在舉辦,特別是為文學、翻譯或出版,法國出版業在臺灣的國際書展,從很早就開始參與主題館。幾乎每隔幾年就辦大型主題館。另外,他們每年在臺灣一定都有固定的海外文化的預算,譯者可以申請居留補助,到法國住1到3個月,提供生活費與住宿費,到法國感受各種文化的變化,但好像沒有提供機票。
主持人:聽起來福利很多。
尉遲秀:對,臺灣出版社也都知道有些書可以申請法國的出版補助,所以同行對於法語譯者得到的外來勢力的幫助都滿羨慕的。
做譯者還是辛苦的工作,法國文化部會編一小筆預算,讓法語譯者協會辦活動,我們跟法國在台協會一直有很長期的互動,他們有些活動也邀請我們來參與,也支持我們主辦的活動。另一個重要的合作夥伴是信鴿法國書店,其實信鴿像是我們的宿主,我們的協會也是寄生在上面……
我們譯者協會有一個翻譯獎,由法國巴黎銀行贊助,首獎有台幣5萬元的獎金,也是很不錯的獎勵與鼓勵,一年文學,一年非文學,兩年相互輪流。主要是獎勵譯者……●
報導》周桂音與其譯作《唯一的玫瑰》獲2022台灣法語譯者協會-法國巴黎銀行翻譯獎文學類首獎
主持人:吳家恆,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畢業,英國愛丁堡大學音樂碩士,遊走媒體、出版、表演藝術多年,曾任職天下雜誌、時報出版、音樂時代、遠流出版、雲門舞集、臺中國家歌劇院。除了在大學授課,在臺中古典音樂臺擔任主持人之外,也從事翻譯,譯有《心動之處》、《舒伯特的冬之旅》、《馬基維利》、《光影交舞石頭記》等書。
片頭、片尾音樂:微光古樂集The Gleam Ensemble Taiwan
閱讀通信 vol.368》台北國際書展,來襲!
➤閱讀隨身聽,聆聽導引:
➤線上聆聽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