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努力也是餘生:寺尾哲也《努力是癮》對談朱宥勳《只能用4H鉛筆》
寺尾哲也《努力是癮》的新書分享會,邀請同樣出版新作《只能用4H鉛筆》的朱宥勳對談。起初以為是當日的大雨,使現場相對乾爽的兩人看起來可親可愛,然而座談開始後才明白,讓這兩位雙雙變得可愛的原因,是因為這回他們談的是散文,而非小說。
一則是創作故事,一則是打造空間,散文屬於後者,他們創造了讓讀者能近距離靠近作者的空間。雖然筆觸仍然鋒利,但散文的自由讓作者本人也能稍稍放鬆肩膀。雖然如此,寺尾哲也在分享會一開始,似乎還是有些緊張,話一出口,直接口誤:「今天談的這本《努力是餘生》……」
「呃,『努力是……』?」朱宥勳忍不住詢問。
「啊啊不是啦,《努力是癮》才對。」
「你不要急著說出真心話啊。」
全場哄然大笑。
這大概就是當日蔓延整場分享會的氣氛,而最初無意之間的口誤,恰也可說是本場分享會的核心主軸。
➤乾淨的文字,且把自己藏得同樣乾淨的內容
無論是小說或者散文,寺尾哲也的筆觸的確都有股鋒利感。朱宥勳引郭松棻的話來描述:把文章白膩的脂肪剔掉,剩下的就是那個尋覓的筋骨。「你會發現整篇文章看下來,基本上無法多刪一句話。」他說。
那是寺尾的努力,即便是散文也要乾乾淨淨。
「不過一開始決定要寫這部散文的時候,我是一直處在撞牆期的。」寺尾坦白。
說起散文,無可避免談論長年以來爭執不休的論點,亦即其中的真實與否。只是,若論及真實,是否就得不斷自揭傷疤?
寺尾分享:「關於散文,我第一時間想到的是『不想寫成什麼』的樣子。比方說,我不想要大量的自我揭露、不想太過日常、不想太過瑣碎。」他說自己一路刪減到最後,才發現內心其實有個理想的原型:「那就是李維菁《老派約會之必要》。她有一大章節不斷不斷在寫別人,各種奇怪精彩之事,但那本書仍被歸在一個廣義的散文框架之中。」
朱宥勳同意,但接著補充:「可是我覺得真正高明的散文,是擅長『蓋牌』的。」他解釋,不知是否源自長年以來的小說訓練,自己在回到散文面向的時候,也習慣用簡單特點來拉出人物的主線,「像是在《只能用4H鉛筆》中,有一篇我很少談論的、談到第一段婚姻離婚前的事情。看完以後你可能會覺得已經完全認識這個角色、認識我或者我的前妻,但其實不會知道我們真正離婚的理由。」
朱宥勳說,那是散文家的圓滑。三個特點就能連成一面,像是編織一張大網,能夠輕盈包覆住讀者,「我們不會編造完全不存在的事情,但也絕對能夠選擇性不說。」
在《努力是癮》之中,寺尾哲也瀟灑潑出了數十個篇章,其中包括同事、同學與家人。雖說本書開宗明義便下了一個警示語:「本書出場之人物特徵、性別……皆經過映射、變造與模糊化……」然而,入戲的讀者其實難以區別真偽。
雖說如此,善於轉換、雕刻細節的作者,其實也不真的「消費」了誰。畢竟散文之真情,其實在於作者便是自身田野調查的對象,看似在描述觀察其他對象,也都是從自己腦袋裡掏挖的場景重現。是的,即便散文,作者也能夠妥妥地把自己埋進文字裡。
➤身在主流預設的陽剛氣質中,我們是否還有另一個選擇?
至於,這兩本散文埋了哪些呢?二位作家找到其中的共同核心,那便是同樣身為男性作者,其陽剛氣質的存廢與否。
寺尾首先指出《只能用4H鉛筆》細膩剖析,男性在社會中許多隱而不談的事實。「例如宥勳寫到穿衣這件事情之於男性的意義。普遍男生到底有多討厭買衣服呢?這讓我想到我以前在Google的同事,幾乎都超討厭買衣服,大概三年進行一次採買,採買當天還會請假,請假原因說出:『我要去買衣服』的那個臉……好像收到教召一樣,非常不悅。」
然而這樣顯露在外表、對於衣服的不重視,其實隱於其後的,是陽剛氣質「對於無用之物」的反感。「除非我們會因為這個衣服,得到更好的工作或機會,才會開始慢慢注重打扮,否則通常對於外在的整理不會特別注意。這就是一種對於實用性的執著。」寺尾結論。
朱宥勳回應,反觀《努力是癮》,雖說通篇並無提及「陽剛」二字,但其實也像是手工縝密的縫線一樣,老早就縫在字裡行間。「寺尾表現的,是一種更隱性的陽剛氣質,就是『努力』這件事情。」
「男性長年以來,都是被放在『主流』的預設值,所以若是男性總統,我們會直接稱其總統,卻要在女性總統前方加上一個女字。這樣被擺在預設值的我們,其實很難知道自己到底長什麼樣子,甚至就連自己可能也看不太清楚。許多思考方式、形式邏輯恐怕就只得順著主流思維走動。」朱宥勳說,又如其中對於男性期待的「努力」、「撐起一個家」……此般意向,也往往是其預設的範疇之一。
因此,朱宥勳說自己在看《努力是癮》時,腦袋一直浮現出兩個關鍵字:一是「功績主義」,二是「倦怠社會」,兩者看似極端卻互為因果。前者以最高效率取得人生唯一的目標,「可是我們從來不問,自己真的需要這個東西嗎?」至於後者,則是「既然衝不到頂點,不如躺平吧。」
「確實如此。」寺尾哲也回應,他過去在大公司工作也有同樣的疑惑。當整個市場都不斷在宣揚「多元與包容」,「可是卻無法接受不聰明的人,好像把『用人唯才』這件事情當作是『唯一的標準答案』,只要你不夠強就理應被淘汰。這不是很奇怪嗎?」
巔峰或者最末,二者碰撞以後的狀態都不會快樂,卻是漸漸擴散在這個社會中的氛圍。
朱宥勳表示:「我不敢說散文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文學本意就是提出問題的人。如果看完以後讀者覺得與書中描述有呼應,才能有意識的去知道,自己還有其他的選擇。」

➤接下來是像子彈一樣的好消息大放送
分享會尾聲,寺尾哲也同步公開一則好消息:《子彈是餘生》目前已售出全球英文版權給美國出版集團Harper Collins旗下的HarperVia,也就是《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英文版的出版公司,預計明年下半年問世。華語電影的改編計畫也正熱烈展開,寺尾透露他在改編計畫中也身兼編劇,和導演合作進行劇本開發。
說到這裡,朱宥勳提議:「如果我是美國出版方,已經知道要怎麼宣傳那本小說了:你們想知道台積電競爭的祕密在哪裡嗎?各種痛苦與哀愁都聚集在這本書了。想知道我們有多崩潰,就來看《子彈是餘生》吧?」
雖然是這樣玩笑的起頭,寺尾卻接住這話題,表示自己下一部長篇小說的構想,正是以台積電為出發。
「你真的要寫啊?」朱宥勳問。
「聽一些朋友講述裡面的經驗,就覺得我們這些資訊工程師其實過得還滿爽的,跟台積電真的沒得比,他們扭曲的程度絕對更勝一籌。」寺尾說。
接下來的談話,感覺二人已切換成小說家的人格頻道在交流。
實際上,分享會上朱宥勳亦曾詢問:「會不會擔心寫作主題過於重複?」畢竟無論《子彈是餘生》或《努力是癮》都直指工程師的痛點。寺尾坦承,當然偶爾會擔心,可是,「我後來覺得,讀者好像也滿期待作者重複鑽研同一個主題、重新站在你的主場,讓這個故事變成一個獨屬於你、既強大又能召喚共感的能力。」
因此,也請讀者們放心期待,寺尾哲也是不會那麼輕易放過工程師的祕辛的,他正繼續努力!●
|
|
|
作者簡介:寺尾哲也 |
|
|
|
作者簡介:朱宥勳 |


 努力是癮
努力是癮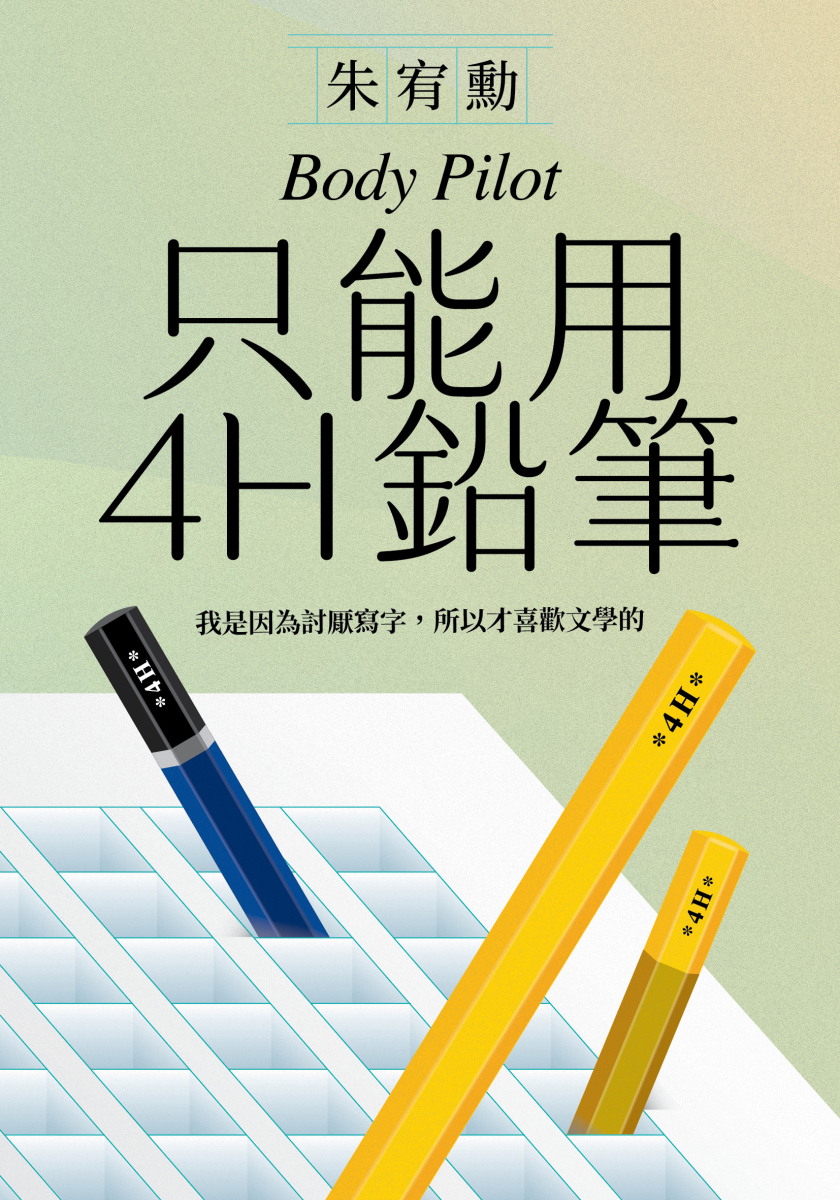 只能用4H鉛筆
只能用4H鉛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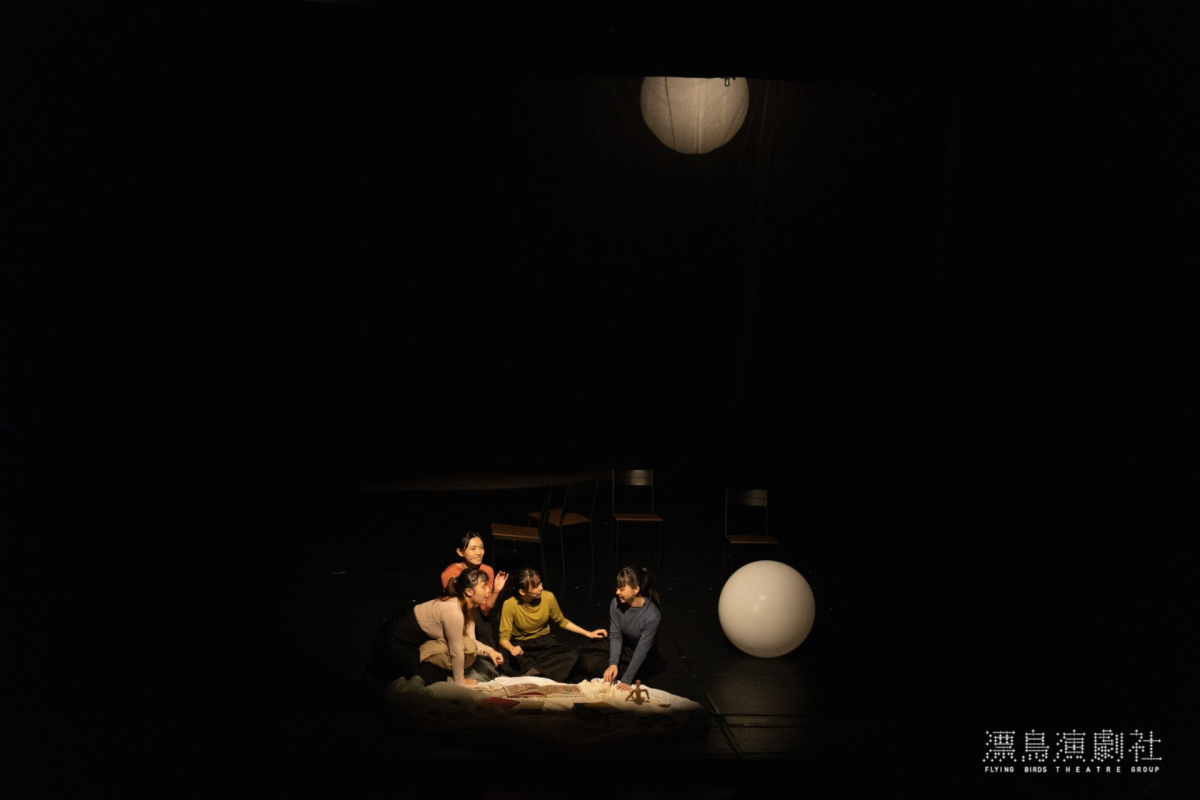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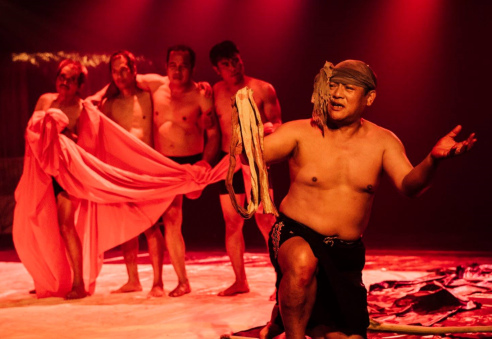




OB短評》#498滿是奇幻與荒謬想像的極品好書懶人包
●勝利之城
Victory City
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著,閻紀宇譯,雙囍出版,550元
推薦原因: 文 樂 獨
魯西迪遇襲後的復出之作,佈局宏偉,出入神話與史實,熔奇幻、宗教、諷喻、荒謬於一爐,頗有印度史詩的筆意。成住壞空如過往雲煙,繁縟華美,讀來毫無黏滯之感。這是作者的自況之書,也是獻給莽莽人間的曼荼羅。【內容簡介➤】
●王者歸程
「大博弈」下的阿富汗,與第一次英阿戰爭
Return of a King
威廉・達爾林普(William Dalrymple)著,鄭煥昇譯,馬可孛羅出版,860元
推薦原因: 知 樂
延續對於東印度公司的關注,達爾林普這次走出印度,進入阿富汗。他將阿富汗本地的史詩、書寫與傳說翻騰,加入鮮活的故事力,梳理了19世紀上半葉英國的阿富汗入侵。在史識與敍事力兼具的重建中,提供19世紀東西戰爭的另一片視野,明白勾勒出英國勢力如何於內亞擴張,更讓人不禁產生今日世界其來有自的既視感。【內容簡介➤】
●人造怪物
Man Made Monsters
安卓雅.L.羅傑斯(Andrea L. Rogers)著,傑夫.艾德華茲(Jeff Edwards)繪,葉旻臻譯,燈籠出版,500元
推薦原因: 議 文 樂
切羅基印第安的生活世界,忽然闖入了吸血鬼、喪屍、ET、鹿女等各種主流非主流的異形。天馬行空的想像,慧黠詭異的嫁接,精巧影射了美國的社會問題與原民處境,恐怖又搞怪,令人好生興奮。【內容簡介➤】
●紫馬
李世成著,印刻出版,300元
推薦原因: 文 樂
小說描寫一名底層青年的生存經驗,及圍繞在他身邊的家庭、社會系統的失能。在社會寫實的框架下,作者以獨特的敘事(僅有人稱、無角色名)與時空感(交錯與誤置),讓角色的心靈不只有磨礪,亦帶有魔幻,讀來深具感染力,更創造出華文小說少有的閱讀經驗。【內容簡介➤】
●第一事物
楊智傑著,雙囍出版,400元
推薦原因: 文 樂
以文字發出清脆聲響,將生活直送到以詩為名的字裡行間,而在詩與詩之間,聲音卻消失得理所當然。這本詩集帶著許多尋常典故、共感的經驗,創造了直直前行的閱讀節奏,不留連殘響、餘味,亦如不斷推進的生活、持續翻動的書頁。【內容簡介➤】
●鳥的禮物
새의 선물
殷熙耕(은희경)著,簡郁璇譯,漫遊者文化,490元
推薦原因: 文 樂 獨
12歲的少女冷眼看人間,也看著自己,執意保持距離的目光有如藏鋒的小刀,深深劃開早年韓劇裡的女子處境,乃至於一切的平庸與變態。這本90年代的經典,也冥冥預告了日後的陰性書寫,從韓江、朴相映到歐膩科幻。【內容簡介➤】
●詛咒・封印版
呪詛・封印版
花輪和一著,黃鴻硯譯,鯨嶼文化,420元
推薦原因: 設 思 文 樂 獨
從無慘繪走向民間怪談,這裡的花輪和一相對地平心靜氣,出入怨念與祈福,甚至飄出幾分侘寂感。圓滾滾的造型詭異而幽默,像極了靈界的住民,特別如影隨形。這部漫畫是因果的結界,到此一遊,你有一部分會一直留在這裡。【內容簡介➤】
●進烤箱的好日子
李佳穎著,自轉星球文化,420元
推薦原因: 議 樂 獨
遊走於回憶與虛構的青春記事,成長的惶惑,肉體的懵懂,斤斤計較的情緒沾黏,都被回望的小針刀一一刮解,鬆爽無比。有了此等剎那即永恆的魔法,不論什麼時候進烤箱,都是真金不怕火煉的。【內容簡介➤】
知識性.設計感.批判性.思想性.議題性.實用性.文學性. 閱讀樂趣.獨特性.公益性
【2/6國際書展講座】書寫、行動與反思:和島嶼互動的幾種方式
閱讀通信 vol.366》為什麼要叫勇者,不叫英雄?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