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賤售戰,下》面對惡性競爭,出版人不卑微!圖書定價制怎麼推?業界協商再現端倪,能否得到共識?
➤博客來削價促銷引爭議,大家怎麼看?
這次博客來風波引起討論熱潮,但近年來每次折扣爭議,最終總因業界無法達成共識,而無所作為。畢竟,各出版社與通路往來各有不同條件與考量。
在這波討論中,某不具名出版人透露,目前浮出檯面的多是出版社對電商折扣的不滿,然而實際上,博客來不只正與另一電商MOMO搶市占,也會比較出版社與其他書店的進貨或折讓%數等合約條件,透過斷貨、減少曝光等方式,與出版社重新談判,「折扣只是種種商業手段的其中之一」。他認為出版人對博客來根本「錯誤期待」,「它就是一個企業經營的電商。」
他提到,有的出版社一方面不滿電商的折扣,但可能為了業績或其他考量,卻給團媽(團購主)們更低折數,沒有維持自家書籍在市場上的折扣。在業績低谷時,出版社需要通路帶來的營業額而就此妥協,固然可以理解,但低價惡性競爭或薄利多銷雖然保住了眼前的生存,出版因此走向低利潤的後果,卻是由整個產業來承擔。
除了業界,相關社群也有多元聲音。例如有讀者指出:「沒有人能夠對抗市場的力量。理想不行、同情也不行的。」「擁護折扣、和願意高價買的消費者,通路本來就該分眾行銷,出版社用理想找消費者買單只是同溫層取暖!」認為這件事情的徵結既然是在商業端,那麼想要解決也只能從商業端來思考解方。
作為電商,博客來被指落後不求進步,讀者直白表示:「20多年前博客來效仿亞馬遜開始在網路賣書,結果現在亞馬遜都飛上雲端、太空了,博客來還在搞低價折扣!不要說認真運用新科技了,連網頁都常年如昔地不長進。」

汪達數位出版創辦人董福興也指出,台灣電商的資安問題、使用者體驗不佳,網路書店包括媒體的分眾、引流、關鍵字搜尋等電子商務的基本經營能力薄弱。另有讀者認為,區塊鏈出版或許是能與當前的市場困境抗衡的管道。
遠流出版社董事長王榮文則坦言,很難預期出版界有共同的主張,但過去業界確實與金石堂、誠品書店都曾因不同議題而有過集體協商,因此他鼓勵年輕出版人揭竿起義,發起連署、提出行動,與通路對決。
但相較於業界成立強力的公協會,王榮文認為應籌組研究性質的「出版智庫」,才能長期研議產業問題。他援引律師蕭雄淋2022年6月在台北書展「出版力論壇」的發言表示,出版業不像唱片、電影業都有成立相關團體保障產業權利,因此建議成立出版智庫,其功能包括「對政府的法令遊說、研究出版的轉型方法、作為其他行業的策略聯盟的聯繫平台」等。
王榮文表示,過去出版界推動成立的台北書展基金會,曾被期待承擔智庫功能,後來因預算人力有限,而無餘力,因此他建請文化部所屬的文策院編列預算,籌組出版智庫。

➤文化部將盡快介入協調,研議圖書零售折扣限制
在眾多因電商平台掀起的折扣爭議中,出版產業主管機關文化部持何種立場?新任文化部長史哲表示,為保護扶植出版產業,將基於其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盡快協助出版產業與公平交易委員會(簡稱公平會)溝通,提出圖書零售折扣限制;並參考國外立法例,與出版單位、通路業者持續溝通,研議維護出版業者合理利潤空間的方案。
由於多位出版業者表示,因《公平交易法》所限,出版社無法集體串連與通路商談折扣限制。如今文化部表態將介入協調,公平會委員洪財隆也回應,其實並非完全不可行,出版業者可事先向公平會申請「聯合行為許可」,公平會立案後,將由委員根據《公平法》第14至16條,有關「聯合行為之定義、禁止、例外許可」等規定,以及第19條「限制轉售價格」的內容與例外情況,進行審議。

➤圖書定價制是政府介入市場嗎?
台灣書業慘澹已非一日之寒,而每當通路價格廝殺,「圖書定價制」這個議題便會再度被重提。
簡單來說,圖書定價制即圖書需依照定價銷售,不打折或者折扣限度需受規範。其立論的基礎在於,書籍除了是商品,也具有文化承載意義。
但另一方面,以政府力量介入立法,必定受到自由市場派的質疑。就算姑且不論商業利益,因為台灣走過漫長言論管控的戒嚴時代,出於對出版自由的捍衛,部分文化人對於官方「看不見的那隻手」,也心存排拒。
這是為何這個制度在台提出十餘年來,出版界始終正反意見相抗的原因之一。過去文化部曾多次召集業界商談、委託學者研究,並考量社會公眾反應,加上制度牽涉財政部、公平會,至今仍不敢貿然推行。

➤回歸合理新書售價、停止業者自我壓榨是重點
文化部從首任部長龍應台時代開始研議圖書定價制,到了鄭麗君任內,為了避免「圖書統一定價」或「定價銷售制度」等名稱造成誤解,擬改名「新書售價規範」,提出草案送交行政院文化會報,規範的是新書在一定期間內的折扣範圍。
2020年獨立書店不滿電商雙11下殺折扣、串連歇業一天時,當時的部長李永得曾在受訪時表示,圖書定價制是兩面刃,預估實施前兩年,市場規模將萎縮一成五到兩成,需要業界尋求共識。
確實,業界反對圖書定價制的另一理由,即是擔憂少了折扣誘因,讀者更不願買書,書市業績將整體衰退。但文化部也曾根據研究報告指出,制度初始造成的買氣下降,大約兩年陣痛期後,可望回歸市場常態。

許多人質疑,出版產業一邊高喊創作自由,為何又一邊要求政府「保護」?畢竟對消費者來說,從衛生紙、吸塵器到化妝品都能打折,為什麼書本不能?甚至有人認為,推行定價制,等於把出版產業的危機怪罪到選擇折扣的消費者身上。
專研出版產業、曾多次參與業界座談及政策建議的臺大社會系專案助理教授李令儀說明,雖然商業邏輯下,市場由價格決定,但製造商仍應保有利潤空間,「如今出版業的低利潤,造成產業每個環節都在自我壓榨,也使創作者受到嚴重剝削。」版稅降低,創作者不受鼓勵,對文創的發展自然會造成戕害。而且如本刊先前的報導所述,多年來,出版社為了因應新書79折等固定折扣,早在制定書價時就先膨脹定價,以為撿到便宜的讀者,以及進貨價不如大通路的小型書店,其實都共同負擔了書價調漲的部分。
【延伸閱讀】新書打不打折?公民討論熱烈,建議上市6個月內,售價不得低於定價95折
李令儀澄清:圖書定價制並非保護或拯救產業,也不是反對通路自由競爭,「而是讓強勢通路之外的小書店、獨立書店,立足在同一個起跑點上,促進健康的競爭。」
當前的書市景況是,小型書店的書籍進價甚至比大通路的折扣售價還高,生存不易,而誠品、金石堂等連鎖書店則不斷收店,「書店變少,書無處可賣,新書起印量不斷下滑。現在有些書籍起印量只有大約800到1200本,造成印製成本增加,書價只能不斷提高。」
因此李令儀認為,理想的情況下,定價制實施後,書籍能回歸合理的定價,出版社也能獲得合理利潤,不管書店規模大小都能平等競爭,通路多元而共榮。

➤欲恢復書市秩序,避免進價落差,有賴對等協商機制與配套措施
業界咸認,大約10年前網路書店尚未坐大時,是台灣推行圖書定價制最好的時機,如今消費者早就習慣網購與折扣,限制削價的良辰已過。
但在這次博客來折扣風波中,過去對圖書定價制持保留態度的時報出版公司董事長趙政岷,明確表態支持圖書定價制,並推論此刻若重新調查,業界的支持度應會提高,因為相較於過去,「來自通路的壓力更大,出版社利潤更低,大環境與過去已有很大不同。」
趙政岷表示,這兩年幸而有政府提供疫情紓困方案,以及2021年3月起實施的圖書免徵營業稅辦法,對出版產業有所裨益。他期待文化部更積極推動圖書定價制,「畢竟出版業是否健全發展,關乎創作自由、文化多元,簡直是國安問題了。」
春山出版社總編輯莊瑞琳則持相反看法並提出不同主張,認為:「沒有折扣的年代,已經回不去了。」她認同圖書定價制的理念,但也體認到多年來因為各種因素而窒礙難行,因此業界不該再依賴官方立法,而應該「由業內組織強力的產業公會,一起面對大通路進價過低、小書店進價過高的問題進行協商,讓產業恢復正常的市場秩序。」

這個想法也呼應了前任文化部長鄭麗君所言,若業界有自己完善的協商機制,其實不需要政府介入立法。圖書定價制推行與否,關鍵仍在於業界是否達成共識。
另一位不具名的出版社業務表示,圖書定價制「不該是推或不推的是非題,而是要有完整的配套,對各種『例外情況』的規範要很明確。」例如受折扣限制的圖書品項與類型、書籍出版時間年份,甚至境外網站如何控管等等。這些原則之外的彈性條款等細節,也都是業界關切的。
總結來說,李令儀坦言疫情後的景氣尚未復甦,物價上漲,民生消費優先於購書的文化消費,現在來談圖書定價「有點陳義過高」,恐怕一時挽救不了書市。不過即使如此,她強調「出版人可以不用這麼卑微」,而應強硬態度,與通路談判。
立委陳培瑜關注書業折扣亂象,近期預計邀請出版業者、政府機關及專家學者進行商討。而既然文化部已正面回應,將協助出版業者與公平會溝通,打破法令關卡,出版人若正視產業長遠的存續問題,也該「硬起來」有所作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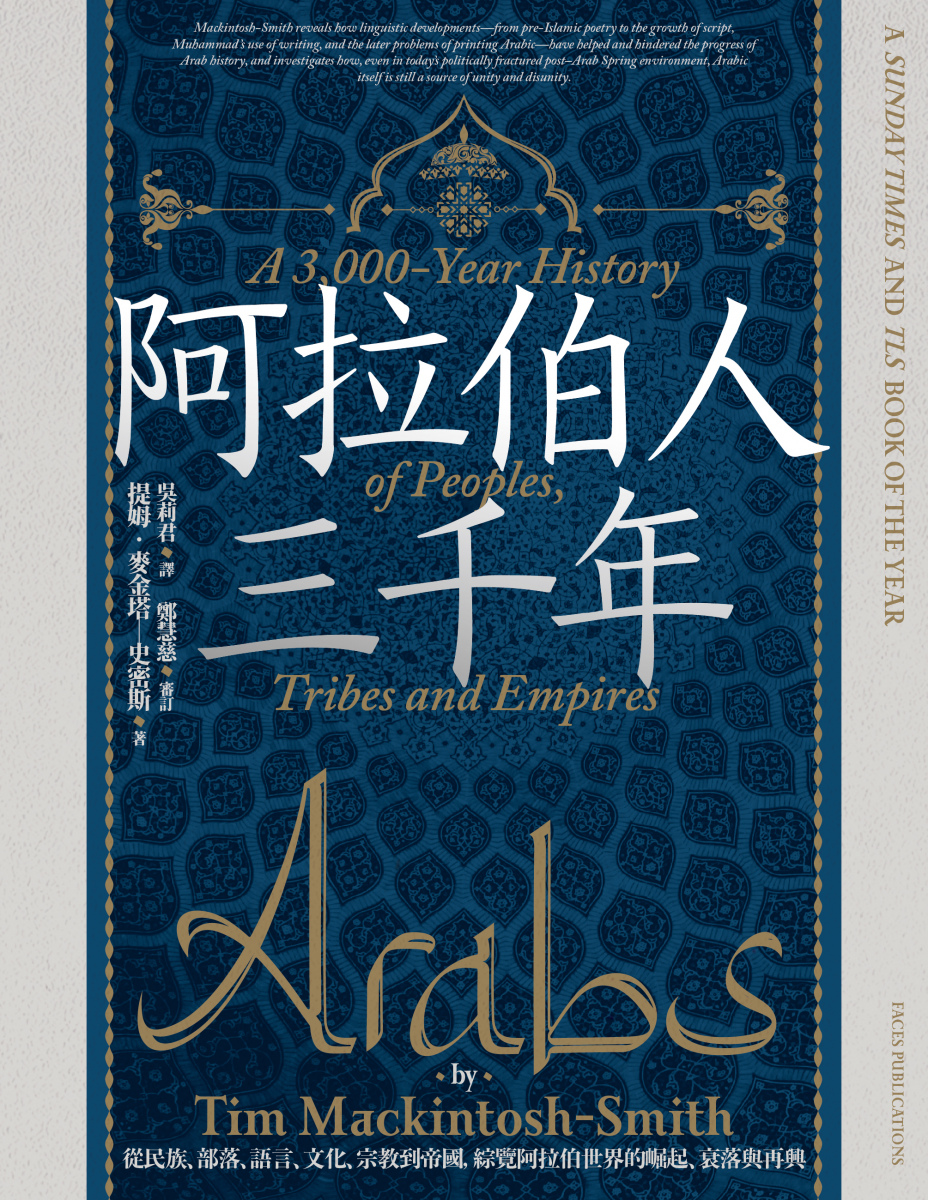
評論》在至痛摯愛各種之間,我們書寫——論安妮.艾諾的文學風格
沒有陰道,亦無子宮。我的身體是座荒涼的空城。它未曾等待,與迎接任何事物。它唯一的作用,是排斥。
讀畢安妮.艾諾作品,我滑開銀幕,在新底稿上敲寫這行字。
身為創作者,貫穿安妮.艾諾作品的最大特質,許是「共感」(l’empathie)。將自我溶解於群體,用串連起的複數經驗感同身受,在不同的生命節點,叩問當時對應的政治經濟,與法律情境。
異秀之人必然無比挑惕,有甚至近乎偏執的完美主義。安妮・艾諾此方特質,或反映在她回覆外界評價其作時所貼上的任何標籤分類。
當人們議論「自我虛構」(l’autofiction);她強調此生多數創作,近少虛構成分。文學研究者奈莉・沃芙(Nelly Wolf)以為《位置》(la Place)可視作安妮・艾諾的分水嶺,先前的首三部作品《空衣櫥》(les Armoires Vides)、《他們所說的或空無》(Ce qu’ils disent ou rien)、《冰凍的女人》(la Femme Gelée)雖皆以第一人稱撰寫,但可視為「虛構的第一人稱」,內文裡仍有小說式的戲法,風格可與法國戰前的人民文學相提並論。
當今評論慣用她當年訪談中,論及書寫時所提供的詞彙:「平面的書寫」(l’écriture plate)。一種無過度修飾的,揚棄隱喻與詩歌般雕花洋溢,如打磨至極薄而利的刀尖,能穿刺,與割裂(「我對文字的想像,是石頭與刀。」安妮.艾諾道)。她的字句化為清水模,灰泥,硬磚與尖瓦,架構出一座後工業時代諾曼第冷調廠房,窗外寒陰。承認自身承襲賽林(Louis-Ferdinand Céline)以來的「暴力書寫」(l’écriture de la violence)傳統,但近年艾諾對舊有定義搖晃浮動,遂複言:文學不可能是平面的,當時她所指,僅為一種手法,以表社會學式的客觀性。純事件,不起任何作用,不挾帶私人特質,與讀者間不存在任何複雜性。「我今天或許會稱之為『事實書寫』(l’écriture factuelle)」。她說。就安妮.艾諾而言,書寫本該走得比文件與報導更遠,其中包含對形式與說話聲音的考量。
人們議論自傳。
「我拒絕歸類於任何一個明確的種類,無論是小說或自傳。」她態度堅定地回覆。
人們議論陰性書寫。她聳起雙肩。
唯獨「自我的社會學式傳記」(l’autosociobiographie),這由她開創的新詞能獲得艾諾認可。其中傳記指涉的對象,是生活中的他者。「活在他者之中」(être au milieu de)對艾諾甚為重要,她曾言與人群的分離與所在間的拉扯,是她寫作的動員支點。
之間是游移,模糊,永遠的進行式。拒絕任何加以綑綁的符號。
之間擺盪的距離總有粗略範圍,那是艾諾政治上的左傾態度。階級、統治與被統治、被剝削的、癖性(l’habitus)。艾諾不諱言受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影響,而馬克思主義亦屬其研究範疇。從務農的文盲祖父,由工廠作業人員轉為開設雜貨咖啡店小本生意人的父親,再至受高等教育的她,所歷經的階級轉移,艾諾以家族書寫回應:父逝後所寫的《位置》,以母親為主軸的《一個女人》(Une Femme),直言叛逃原有階級感受的《羞恥》(la Honte)等皆為此系列代表作。
儘管不將自身與陰性書寫掛鉤,但主題上,擺盪於階級意識另一端的,是艾諾對女性處境的關注。
看似泛泛,《簡單的熱情》(la Passion Simple)與《事件》二作,可明確勾勒出艾諾對這議題的「次擺盪」。
《簡單的熱情》是一本外遇之書。
「這夏天,我第一次在電視頻道Canal+上,看了限制級電影。」艾諾如斯開場。為期兩年。孩子早已離家就學,艾諾與自蘇聯東歐國家的外交官A相遇。A總穿聖羅蘭的西裝,Cerruti領帶,喜愛名車。他說話文雅,不諳粗語。A已婚,為防妻子疑心,他僅於難得的閒暇時刻走長長的路,只為找一架可用的電話亭。
想見你。A說。
待A馳騁遠去,她不洗床單,只為保留他遺下的精液氣息。
思念嚙咬,翻騰。活在等待中(羅蘭巴特般的戀人啊)而不能主動聯繫,艾諾神思恍惚。熱情焚殆理性。若今天能聽見A的聲音,她願捐數百法郎給慈善機構,艾諾祈禱。她接受丹麥學術座談僅為了寄明信片給A任職的大使館(他沒有收到)。她重複所有動作,穿同樣的衣服看同樣的書,預約牙醫,只因A當時或之前之後掛了通電話給她。
寫幽會時當面給予,看完即撕的信。
為他買新衣服新口紅新鞋(她認為在A面前有重複打扮是對這關係的污辱與不敬)。
看所有關於他國家相關的書籍。
《簡單的熱情》如此深刻,帶點極簡主義,是關於激情的炭筆素描。但一如她所有著作,靈肉經驗叩問的,終究是書寫(「妳之後不要寫一本與我有關的書。」A說。)
「我認為寫作必須朝此方向:性愛場面激發的印象,這種不安,驚愕,與道德判斷的懸置。」艾諾另於書中回覆:「然而我沒有寫一本關於他的書,也不是關於我。我僅還諸於那並非為他所撰,他或許也不會看到的文字。這單獨的存在帶領著我。一種禮物的移轉。」
特定情境的瞬息心緒導發共感,召喚群體。
一次,當艾諾在家裸身,朝冰箱走,欲取啤酒之際,她想到了那些女人們,已婚的,未婚的,作母親的,那些在童年午后居住區偷偷迎接男人們的複數群體。
艾諾亦猜臆,一群複數的女性穿越過A的身體。
A離開巴黎後,她決定前往診所作愛滋檢測。在寂靜的診所等待,她憶起60年代自身的非法墮胎經歷。等候區繁雜種族,性傾向的人與身體,流轉成《事件》一書的起頭。
歷經千辛萬苦曲折迂迴,她終於讓一個女子將探條置入體內(她在去程想起逃往英國的科索沃難民們)。
五天。
返校區,和友人O一齊去電影俱樂部看《波坦金戰艦》,席間她下腹劇烈疼痛。她回宿舍房間休憩。她強烈地想要拉屎,快速地跑至走廊另端的廁所,宛若投擲一枚手榴彈,腳下激起的水花噴濺至身側牆壁。
低頭目睹下體垂掛一條紅紅的線,一名小小的浴者。
Mizuko,水子。日文裡的小產嬰兒。艾諾想到。
(從羊水至盥洗廁間污濁液體再到冥河的輪迴?遠岸的我如此疑惑,未有答案。)
她將它捧於手心,沈重地走回房間。她要求O抄起剪刀裁截臍帶。
《事件》描述的肉體疼痛與心靈震盪,不依時間的反覆沖刷而淡稀輕盈。出血過多,墮胎後續入院治療所遭受的待遇,(「為什麼不告訴我妳是名大學生?」急救後,一名夜間實習醫生如此責怪艾諾。)面對墮胎,工廠女工與文科大學生的差別待遇,未婚待產婦女遭受的冷眼,階級內部隱含的微型結構。法國學運前國家機器的不平等與失衡運作,自是眾人討論焦點。
但更令我動容的,是書中許多關於遭受此等重大「事件」後,關於書寫的反思與叩問。
「我不是一個修水管的工人。」(手術房裡,面對艾諾諸多疑問的醫師大聲道)。
「妳需要處方簽。」(出院後,艾諾步入藥局欲購子宮止痛錠,藥師冰冷回覆。)
Formica塑料貼版的牆,裝置探條的盆子右側有一把髮刷。手榴彈。
生命中,微小,看似不具任何重要性的碎片斷語,為何在三十多年洪荒滌洗後,依然頑強存在?那意料之外的堅硬事遺,成了艾諾用於拼湊「真理」(la vérité)的標記與符碼。
描繪真理,是書寫的唯一使命。
除理念上的緊密契合,《事件》於我,更似劃開一道裂口,屬於記憶,疤痕越擴越大,深埋著疼痛真理愛與迷惘。疤痕擺盪,在安妮.艾諾與我之間。
多年後為了重返現場,艾諾搭乘地鐵回到巴黎十七區(那名為她安裝探條的女士居所)。
她在 Malesherbes 站下車。(那是我居住巴黎時,每日通勤至研究所就學的唯一座標。)她經過卡赫汀涅通道(那是巴黎索邦外語學院斜後側一條窄仄小巷。)。
她在那裡被生死穿越(我在那裡被生死穿越。)
「之間」幻作水紋蕩漾,漣漪。記憶與共感跨越時空,種族,性別而來。
但不似安妮.艾諾與同她相連的諸多女性群體。
我的身體無能生育,它唯一承接的,僅有書寫與死亡。●
(文章授權轉載自「虛詞」,原標題與連結:〈【2022諾貝爾文學獎】在至痛摯愛各種之間,我們書寫——論安妮・艾諾的文學風格〉
閱讀通信 vol.368》台北國際書展,來襲!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