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我想選擇錯誤,關於生命的100種可能:評川上未映子《夏的故事》
川上未映子的《夏的故事》,前作是芥川獎得獎作品《乳與卵》。《乳與卵》承載了2008年夏天三個女人對身體的不同想像:夏子在東京一邊打工一邊努力成為作家、姊姊卷子從大阪來訪東京打算隆乳、卷子的女兒綠子對初經和即將成為「女人」的一切感到厭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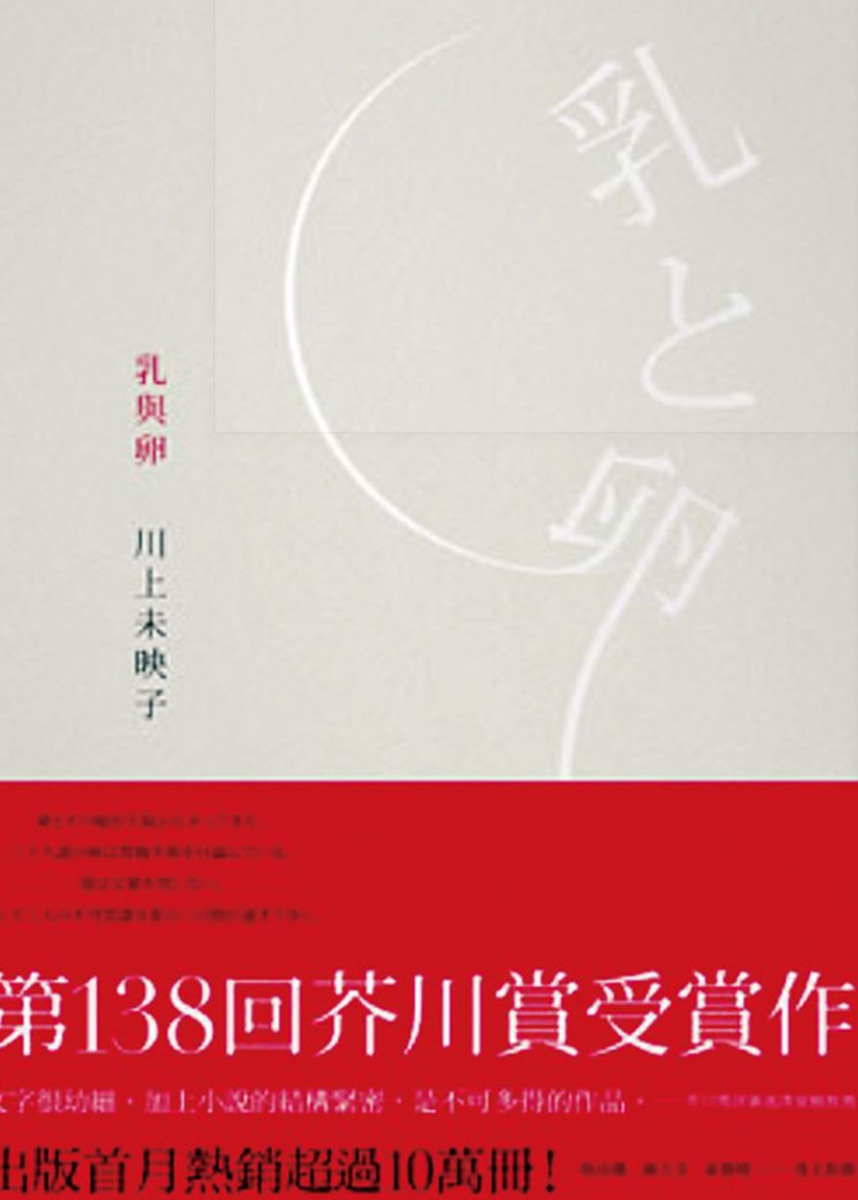 時序來到2016,延續前作的女性身體議題,在第二部中終於成為作家的夏子想用不一樣的方式生孩子。透過夏子和其他女性的交流,故事從身體議題更加擴大,展開了關於生育、生命和性別期待的多元討論。
時序來到2016,延續前作的女性身體議題,在第二部中終於成為作家的夏子想用不一樣的方式生孩子。透過夏子和其他女性的交流,故事從身體議題更加擴大,展開了關於生育、生命和性別期待的多元討論。
若說第一部是女性身體想像的進行式,第二部就是探索這個想像的未來式。《夏的故事》中遍佈著女性在當代社會的每一種選擇和沒有選擇。
➤選擇和沒有選擇其一:身體樣貌
「什麼樣的身體才美?」是個不停變動的文化價值觀問題。然而女人身體的每個部位怎樣才美,在當代社會不只是文化問題,更交織了父權凝視對女體的期待和規訓,透過影視文化傳遞到每個女人身上。
想要隆乳的卷子厭棄自己的身體,那因為生育而乳頭黑且乳房扁的身體,著迷於粉色的乳頭和堅挺的乳房。這樣的想望既是個人的,也不只是個人的。女兒綠子對初經感到厭惡,對成為「女人」的一切感到不自在,也許正因母親作為鏡像展現出的焦慮。許多年輕女孩都有過對女性身分的拒斥,與其說是拒絕女性身分、拒絕成為女人,不如說是對關於女人的刻板印象和標籤感到抗拒。綠子透過母親,看到了那個未來可能充滿身體焦慮的自己。
對「女人」身體的想像不只是對自己身體的期待,也可能成為群體區分的工具。
夏子在澡堂遇到了一位「T」,擁有著進行過平胸手術的女體。當她跟沒有乳房的女人同室裸身而感到不自在,正好引導讀者去思考:乳房就等於女人嗎?若這位T因為慾望女體而需要被質疑身在女子澡堂的正當性,跟T在一起的女人難道不也慾望著女體嗎?真正讓夏子感到不自在的,恐怕不是T慾望著女人,而是因為沒有乳房的身體挑戰了「什麼是女人」的想像。
女人究竟是什麼?談身體、也談生育,那些社會認為關於女人的事,在《夏的故事》裡眾聲喧嘩著。

➤選擇和沒有選擇其二:生育
夏子未婚也沒有對象、對性沒興趣,但渴望見到自己的孩子,因此開始規畫接受捐贈取得精子。為了瞭解這個孩子即將面對的未來,除了閱讀用AID(精子捐贈)誕生的孩子們成年後的訪談,更參與相關的研討活動,希望能進一步了解當事人。
絕大多數的孩子在被生下來之前,並沒有同樣的機會被關照他們可能面對的將來。然而即使夏子竭盡所能做好準備,想要用AID獨自生下孩子的母親仍會被貼上自私的標籤,認為她們剝奪了孩子擁有父親的權利。哎呀這話實在耳熟,護家盟在反對同志生養的時候不也是這樣說嗎?然而這世上有父有母卻被疏於照顧的孩子何其多,異性戀誕下的孩子也非人人能享受與父母的親密,為何只有非正典的生育方式被過度嚴格看待呢?
若要說讓孩子沒有父親的女人自私,夏子在尋找捐贈者的過程中遇到的,對自己精子過度著迷、只把讓人懷孕當做成就的男子不自私嗎?難道這樣的男人真的適合成為父親嗎?這名男子表面上看似是個極端值,但無論是在《夏的故事》裡或是在現實社會中,只有捐精功能、只會讓人懷孕的「父親」還少過嗎?
捐精生子之所以引發眾人的焦慮,進一步需要用輿論的道德框架壓住如夏子這樣的女人,在我看來是因為,一旦女人脫離婚姻束縛追求自己想要的未來——包括生子,就等於為女性自主開啟了一個終極篇章,讓她們做出「我無論如何都不需要男人」的選擇。此舉簡直從頭到尾都在動搖保守派心中的傳統價值,更挑戰以男性為中心的父權社會體制。
既然所有人都沒有辦法選擇是否要被生下來,但可以選擇讓別人——也就是自己的孩子怎樣被生下來,那你們打算做怎樣的選擇呢?

➤選擇和沒有選擇其三:日本的社會結構
日本在多數台灣人心中是「進步國家」,在疫情前大概每個月打開臉書都會有朋友到日本旅遊,日本文化深入台灣社會。我們對日本的認識都留在光鮮的那一面,跟著夏子則可以看到日本的另一面,無論是窄小幽暗的樓梯或是打工的酒吧街,都是觀光客沒有機會看到的日本。童年的窮困加上「不要給他人添麻煩」的日式精神,在成長過程中或多或少對夏子的心靈產生了束縛。《夏的故事》帶我們走進真正的日本社會,去看見生命的每一種樣子。
川上刺穿日本社會的銳利之筆不只談女性個人、談日本社會的底層,也進一步把女性議題拉到結構層次進行觀察,透過AID研討會的悠悠之口看穿社會對未婚生育的不友善、利用酒後的女性友人對話直指社會中的男性優勢。
然而不被社會接受的未婚生育,在少子化嚴重的現代社會早有學者提出可能是門解方。
2018年歐盟平均的婚外生育率是41.3%,在法國,每100個新生兒其中就有60人的家長沒有婚姻關係。可以維持住生育率的已開發國家,有很高比例的出生都是來自未婚生育。然而台日等東亞國家屬於超低婚外生育、超低生育率的一群。婚外生育率台灣是3.8%、日本2.3%,總生育率則是台1.07人、日1.38人。
倘若未婚生育在亞洲社會的污名能夠去除,當生育不必跟婚姻家庭綁在一起,僅只是人生的其中一種選擇,甚至當家庭的想像可以更多元一點,夏子可能就不再需要是「選擇錯誤」,如善百合子這樣「不想被生下來」的痛苦也會少一點吧。
初識《夏的故事》以為是部曲高和寡的文學獨奏,卻驚喜發現它是跨文化的女性處境之歌。數度利用酒後談天的對話猝不及防地說破了父權社會的虛偽:「以為有屌就了不起」、「沒有生活能力卻愛吹噓,還要人安撫他的壞心情」、「活在隨時都有女人滿足他們需求的世界」,讀來暢快得像是加入了夏子和女性友人們的酒局,即使沒喝也跟著醉了!●
|
|
|
作者簡介:川上未映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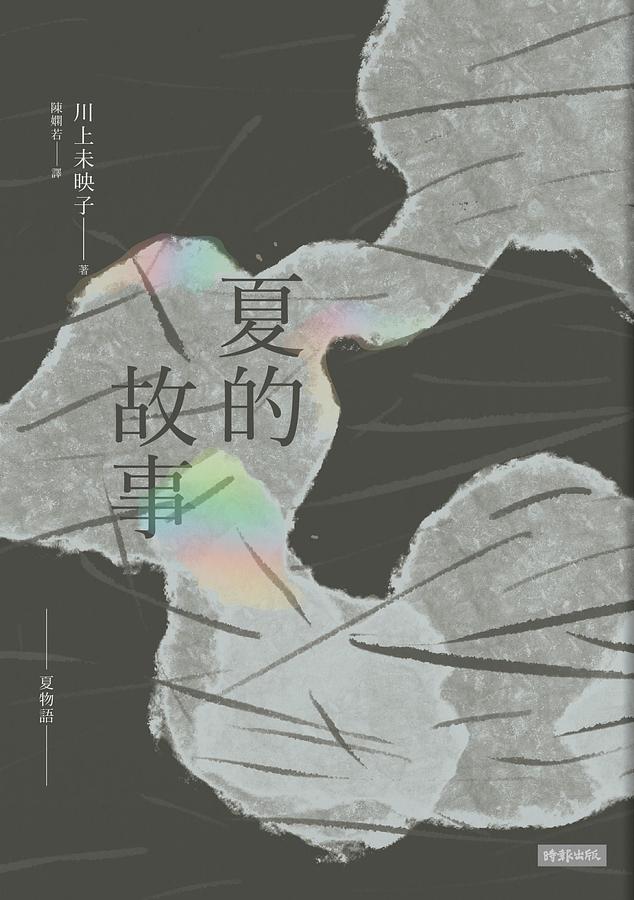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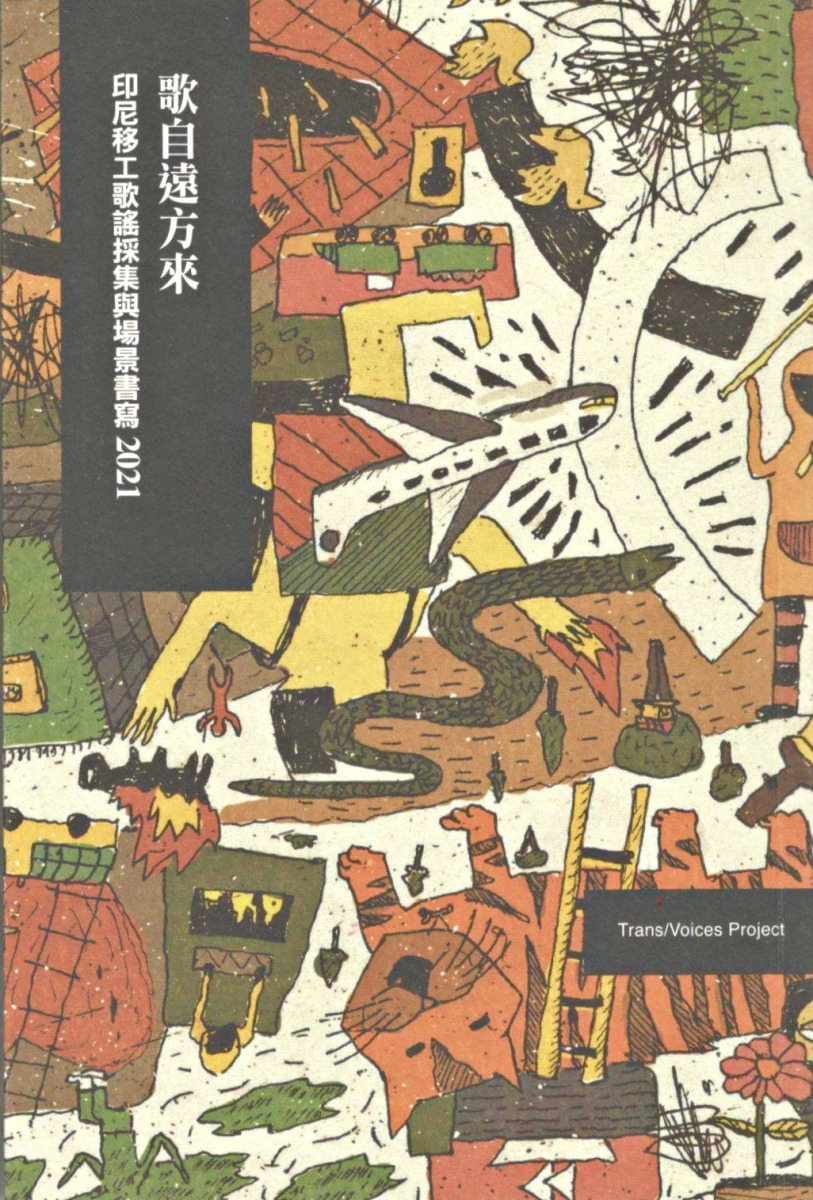
書評》沉鬱迷離的滅絕者之歌:評《影之島》
記得多年前,曾在《青蛙大浩劫》這本書中讀到一種令人難忘的生物,那是只棲息於哥斯大黎加蒙特維多山頂艾爾分矮林(Elfin Forest)中的金蟾(golden toad)。所有見過金蟾的人,無不驚艷於牠們虹彩般的螢光色,尤其身長只有大約兩英吋的雄蟾,宛如散落一地,光芒閃爍的寶石。
但這種迷人生物從1964年被科學界首度發現及賦予學名Bufo periglenes後,不到30年間竟已再無目擊紀錄。生物學家瑪莎.克朗伯(Martha Crump)可能是最後一位目睹金蟾繁殖季的人,1987年,她看到大量聚集的雄蟾「在薄霧中閃閃發亮」,隔年,數量銳減到不足一打,再過一年的春天,她只見到一隻,在那之後,「就再沒人見過金蟾了」。(註)
這隻無緣得見,甚至難以憑空想像的「最後一隻」金蟾,卻因此銘刻在我的記憶中許久。想到牠如何獨自在雨林中,以鳴聲召喚著永遠不可能出現的同伴,就覺得悵然。而在閱讀了《影之島》後,那隻孤獨的金蟾在我心中因此有了去處——他想必已經棲息在影之島,因為「所有已經不存在的動物,他們的靈魂都住在這裡」。
不過,所謂「影之島」,並非「彩虹橋」式的溫暖安慰或自我說服,相反地,這座向阿諾德.勃克林(Arnold Böcklin)著名畫作《死之島》(Die Toteninsel)致敬的島嶼,匯聚的是終極的死亡形式:滅絕。但是,《影之島》並未採取一般在處理滅絕動物主題時,常見的哀愁憑弔或譴責控訴人類行為的模式。大衛.卡利(Davide Calì)以冷靜內斂的敘事口吻,搭配克勞岱雅.帕瑪魯奇(Claudia Palmarucci)靈動流轉的繪圖風格,構築成一首既迷離又沉鬱的滅絕者之歌。
迷離氛圍的核心來自於夢。故事的開頭,我們看見一座在「渴望沼澤」和「往日時光瀑布」之間的夢境矮林,其中有位專門捕捉惡夢的小袋鼠醫生。小袋鼠醫生總是騎著他忠心的澳洲野犬「天狼星」,幫助為惡夢所苦的動物們,把「擠呼呼的」、「喘吁吁的」、「彎彎曲曲」或「窸窸窣窣」的各式各樣惡夢們,捉起來吃掉。但是有一天,他遇見了一位新病人,帶來一個前所未見的夢。小袋鼠醫生查找了所有的書籍,發現這無以名之的夢,原來是「沒有夢」。已經滅絕的袋狼沒有夢。因為他是一個不知道自己已經滅絕的靈魂,或者說,鬼魂。
鬼魂不知道自己的命運,不知道那無以名之的空洞就是虛無本身。如同卡通裡面不知不覺衝出懸崖的角色們,總要向下看的那一刻才會墜落,袋狼不滿意「沒有夢」的診斷,但被揭露命運之後,他也只能啟程前往影之島。影之島,既是作家為滅絕動物想像的溫柔的歸宿,也是一座死滅版的方舟、沉鬱的靈魂紀念碑。
於是讀者將會回頭理解,最初打開扉頁時,映入眼簾的「動物圖鑑」,其實是影之島的部分居民清單:袋狼、棕褐紅光蛇、大綠雀、平塔島象龜、大海雀、公爵龍蝨……一長串的死者,他們曾經各有各的好夢與惡夢,如今俱往矣。
更耐人尋味的是,在這本書中,包括主角袋狼在內,這些滅絕動物全都沒有自己的「故事」。這也是《影之島》迥異於我們所熟悉的滅絕動物敘事之處,一如「沒有夢」,他們滅絕的過程與理由同樣也是一片空白,因為那是連死者本身都無能理解的,超越個體經驗所能及的概念。
然而文字敘事上的刻意留白,正是圖像敘事延展的起點。一個個圖錄,讓讀者得以「停格」與「駐足」,開始思考:他們遭遇了什麼?如果借用漫畫家史考特.麥克勞德(Scott McCloud)對漫畫中時空特色的形容:「雙眼在沿著眼前的空間移動的同時,其實也穿越了時間……你的眼睛看到哪裡,那裡就是此刻。但與此同時,你的眼睛也會看見周遭過去跟未來的景物。」(註)
雖然漫畫和繪本在圖像呈現的方式上並不相同,但同樣能以廣義的圖像敘事來理解。圖像中的各種細節,不只將過去帶到此刻,也打開了文字敘事未必能及的複雜度與多義性——尤其是像帕瑪魯奇這樣的藝術家。
因此,若省略圖像在這本書中扮演的角色,就絕對無法充分理解《影之島》的價值。帕瑪魯奇雜揉、轉化了若干藝術史上的經典作品(註),讓我們在富麗有之、奇詭有之、細膩有之的不同風格畫作之間,看見動物的夢境與過去、看見我們曾經與不曾想像過的世界。而書末,還有一群夢境越來越稀薄,隨時都可能啟程前往影之島的動物清單:黑白花狨、馬來穿山甲、寬白眉長尾猴……
「但他們有一天會回來嗎?」「誰知道呢……」在故事尾聲,卡利留下這樣一個既不知提問者是誰,也沒有答案的對話。提問的背後,是無數想要尋找目擊、重建基因、重現與召喚滅絕生物的渴望;沒有答案,則是因為有更多值得回頭追溯、往下追問的問題。但,誰知道呢,答案說不定就在那些彎彎曲曲、窸窸窣窣的夢境裡。當我們透過作者與畫家的眼睛看見動物的夢,看見他們同樣擁有的渴望與恐懼,說不定我們就能在夢中,與他們的夢境相遇。●
L’isola delle ombre
作者:大衛.卡利(Davide Calì)
繪者:克勞岱雅.帕瑪魯奇(Claudia Palmarucci)
譯者:穆卓芸
出版:大塊文化
定價:52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大衛.卡利(Davide Calì)
擁有近百本作品的繪本作家。1972年生於瑞士,主修會計,不過對圖文的熱愛和掌握度,似乎勝過了數字感。興趣廣泛,漫畫、插圖、童書、劇場、教育都有所涉獵。善於經營故事的結構和節奏,帶來層次豐富的閱讀體驗。他筆下的故事主題非常多樣,在國際書壇獲獎連連,曾獲IBBY國際青少年文學獎、法國巴歐巴童書獎 (Baobab Prize)。
繪者簡介:克勞岱雅.帕瑪魯奇(Claudia Palmarucci)
自由插畫家。1985年生於義大利,畢業於馬切拉塔美術學院(Accademia di Belle Arti di Macerata),專攻裝飾藝術和插畫藝術。家鄉的地景潛移默化形塑了她古典雅緻的繪畫風格,她曾說「每看一眼,都是誘發。」群山環繞的小城、年代久遠的村莊、古老靜謐的修道院,這些都深刻影響了她的構圖和色彩。
她的作品常有清晰的藝術史參考座標,自言繪畫是一種方式,能夠不折不扣地了解他人與自己。她曾三度入選波隆那插畫展,2020年以傳記繪本《瑪麗.居禮》(Marie Curie. Nel Paese Della Scienza)榮獲波隆那拉加茲獎( Bologna Ragazzi Award )。「每一頁,每張圖,都是仔細且深入的探究成果。」這句評語適用於她目前出版的多數作品。
【Openbook國際書展參戰(;・`д・´)】
2/6(五)歡迎加入玩耍!•̀.̫•́✧書寫、行動與反思:和島嶼互動的幾種方式
閱讀通信 vol.368》台北國際書展,來襲!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