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被故事餵養長大,從一年之中最好的那天談起: 林俊頴《七月爍爁》
從春日起頭,延續清明的雨水,林俊頴新作《七月爍爁 》從「一年之中上好的時日」開始,小說中的台語底蘊,為小人物的光彩加厚。通篇鏗鏘的語感以及節奏,是他耗費數年時光一路轉折,尋找最適合自己的語詞聲音——這點,或許是台語文學書寫最難解,同時最耀眼的地方。
難是難在有諸多語詞仍舊尋不著最對的那個字,但耀眼也是如此,既然沒有既定的答案,那麼就讓小說家以其自身背景、故事情感、角色設定,一步步讓語詞走進字的含義之中。
「歸根究柢,你可以把台語文書寫當作是我自己的強迫症,我創作上一種正經的玩笑。」林俊頴說。他當然知道在創作之初,就以台語確認書寫方向會是一種限制,此執迷的結果必然會創造一種美學,同時也會帶來限制。可是「我父母兩邊都生長在彰化,台語也是我的母語,倘若欲書寫過去時代的角色,則必然要從這一步開始寫起。」
因此,對於《七月爍爁》我們可以這樣認識:此書並不聚焦鄉愁了。這本長篇小說起源於日光清明的斗鎮,一位「傳說中」的七舅公回到家鄉,一屋子的「莊腳人」迎接他。像是某種時代的匯聚,一方是家族的期待,凱旋而歸;另一方是佇留原地的人,裹足等待。這兩句話,幾乎便是台灣的斷代史,為我們捕捉大家族的影像切片。
➤被祖母餵養故事長大的孩子
林俊頴的確是大家族的孩子。但講得更清楚一點,應是:他是大家族出生的孩子。他的外祖母是家族的老么,生在名門望族,是彰化北斗鎮的大戶人家,光是哥哥就有9個。
至於大家族,從來不缺故事材料。
林俊頴回憶:「我出生的時候,祖母才45歲。」這樣的年紀差距,使他和祖母之間的交流毫無問題,沒事就往她那跑去。而祖母經常掛在嘴上的「了不起的哥哥們」,幾乎變成林俊頴兒時「想像的玩伴」。
「祖母的哥哥就是我舅公嘛。從前有錢人家裡會盡其所能讓孩子去留學,我的舅公即是如此。經常聽祖母提說哪個去日本唸書,哪個當了醫生、哪個經商。」林俊頴笑說,聽祖母談及這些哥哥們,語氣中都沒有惆悵,盡是光芒與喜悅,好像家人之間的功成名就都是綁在一起的。
而當時年幼的林俊頴也沒有意識到,祖母餵養給他的家人之事,會成為他小說的重要依托。
「我確實有個舅公去日本讀書,且當舅公的醫生起碼就兩個。其中一個舅公甚至是彰化的大人物,還被記載在北斗鎮的地方誌上。」林俊頴說,世上能有幾個人,看地方誌如看自家家族史?望族的後輩看史書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總而言之,那個讓祖母心心念念、希望也能行醫的這個孫子,後來成了小說家,並將他耳聞的舅公們好好揉捏,形塑成小說中的角色原型,化作集各種光彩於一身的七舅公。林俊頴想知道:「這個角色幾乎可以說是家鄉人一輩子的心願與美夢。而這樣的人回到原生家庭、看到這個被殖民過的家鄉,重新走到自己的起點,又會是怎麼樣呢?」

➤台語之於創作者的餘裕
既然都回到原生家庭,則必然也得回到原生語言。
事實上,林俊頴對於台語文的意識啟蒙得很早。在政大中文就讀期間,受教於文字學名家簡宗梧教授,課堂上簡宗梧便曾經提醒,台語在文字學上公認是保留最多古漢語音恣意的語種,循著音聲慢慢追本溯源,多能夠找到每一個字的源頭。
「但我承認我就是個寫作的人,不是文字學者。」林俊頴說,他創作的意志,帶來了語言思考上的自由與靈活,卻不代表他沒有費苦心在這條路上。
起初,創作《我不可告人的鄉愁》,那是他台語文學創作的第一步。如今想起來,他自嘲那是「瞎子摸象」。如同他給自己設下的文字實驗,雖說他研究得樂在其中,但仍時時感受到折磨。「我甚至覺得不只是折磨自己,也折磨讀者。回想起來,那時候的創作必定造成很大的閱讀障礙。我的想法還不是那麼成熟,多憑著一股魯莽的勇氣跟衝勁去執行它。」
相隔十多年,重新啟動台語書寫,面對《七月爍爁》,此刻林俊頴想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如何用台語和讀者靠近,而非如何拉著讀者一起靠近台語。
他說:「這幾年我也擔任一些文學獎的評審,看到以台語文書寫的小說,都是憂喜參半。一來是喜見這樣的形式越來越多人嘗試,但二來是,文章的用字連我這種母語是台語的人讀來都很辛苦,有不少甚至要用猜的,那其他讀者怎麼辦呢?」換個角度思考,他清楚意識到書寫最終的目的仍是與讀者交流往來,倘若一開始就構築一個閱讀的高牆,那麼有多少人能夠爬過?
「所以,這一次我決定要放輕鬆,用比較寬裕的心來走向我的理想國。」林俊頴說。
對創作者來說,台語書寫可以是個挑戰,但也不妨將它當作是本然的利器——借力使力,憑靠語言的古老底蘊,清清淡淡就能夠帶出一種意味深藏的歷史感。
林俊頴的「寬裕」之說,旨在讓看不懂台語的人也能夠望文生義,以上下文脈絡推斷字裡行間的意思。當然最後的結果未必「精準」,不過這畢竟是小說,小說的終點永遠只存在讀者的腦中,即便最後與原創的想像不盡相同,那或許也是創作的迷人所在。

➤讓小說乍現的那道光
又是台語書寫,又是原生家族,這些關鍵字往往離不開苦情的想像。然而綜觀整本《七月爍爁》,又是那樣熠熠生輝。箇中道理,須繞回觸發林俊頴創作的那道閃電。
他記得非常清楚,2019年5月,台灣的同婚專法通過。在此之前台灣各家媒體對於民法、專法,或者同志是否需要異性戀的專制婚姻,種種方向早已討論得鞭辟入裡。林俊頴回憶,當時看著這一系列討論,忽然有種很奇異的光彩照入心間。
他是這樣形容的:「不知道為什麼,使我想到一個很久很久以前的新聞畫面:英國黛安娜王妃出車禍死掉的時候,葬禮上她的兄弟姐妹都站了出來……這應該是一個很尋常的畫面,可是讓我情不自禁連結到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的《我們都是食人族》,裡面提到一段話:『遠方照耀了近處,近處也能照亮遠方』。而彼此照耀這件事情,套用在家庭結構上,讓一切連接起來的支點就是婚姻。婚姻本身就是一個建制,連結到家庭結構、人民關係、宗族的成立。讓沒有王室血統的人能夠出現在王室葬禮上,也讓遠方的兩人連結起一道光。」
這就是林俊頴的閃電。
他想起祖母說給他聽的舅公們,如何因為婚姻而建構起其他的枝葉。想起生為望族的祖母當初自由戀愛嫁給佃農祖父,一度引發的話題與衝突。想起台灣從過去的大家族傳統,到此刻不婚不生,其它遠看殘破,近看或可說是小巧精緻的各種婚姻狀態。
於是,林俊頴知道此刻的台灣切片他要從哪裡入筆——綜看這幾十年來台灣人對於婚姻的想像及其變化,投身其中,那也像是掉進一層又一層的多元宇宙,從大至小的家族場域中看待社會與人的連結。重新書寫他的鄉鎮,將北斗幻化為斗鎮,為無法復返的鄉土也照進一道新的雷電。
因此,一切才這樣合情合理。故事必然得從那一天說起:「一年之中上好的時日,春寒才消解,清明的雨水亦未來臨……此時,傳說中的七舅公取著傳說中的日本妻後軫來故鄉。」●

|
|
|
作者簡介:林俊頴 1960年生,彰化北斗人。政治大學中文系畢業,紐約市立大學Queens College大眾傳播碩士。曾任職報社、電視台、廣告公司。著有小說集《鏡花園》、《善女人》、《玫瑰阿修羅》、《大暑》、《是誰在唱歌》、《焚燒創世紀》、《夏夜微笑》等,散文集《日出在遠方》。 《我不可告人的鄉愁》獲2012年台北國際書展大獎與金鼎獎,並於同年獲邀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IWP);《某某人的夢》獲2015年台北國際書展大獎與金鼎獎;《猛暑》獲2018年台灣文學獎之金典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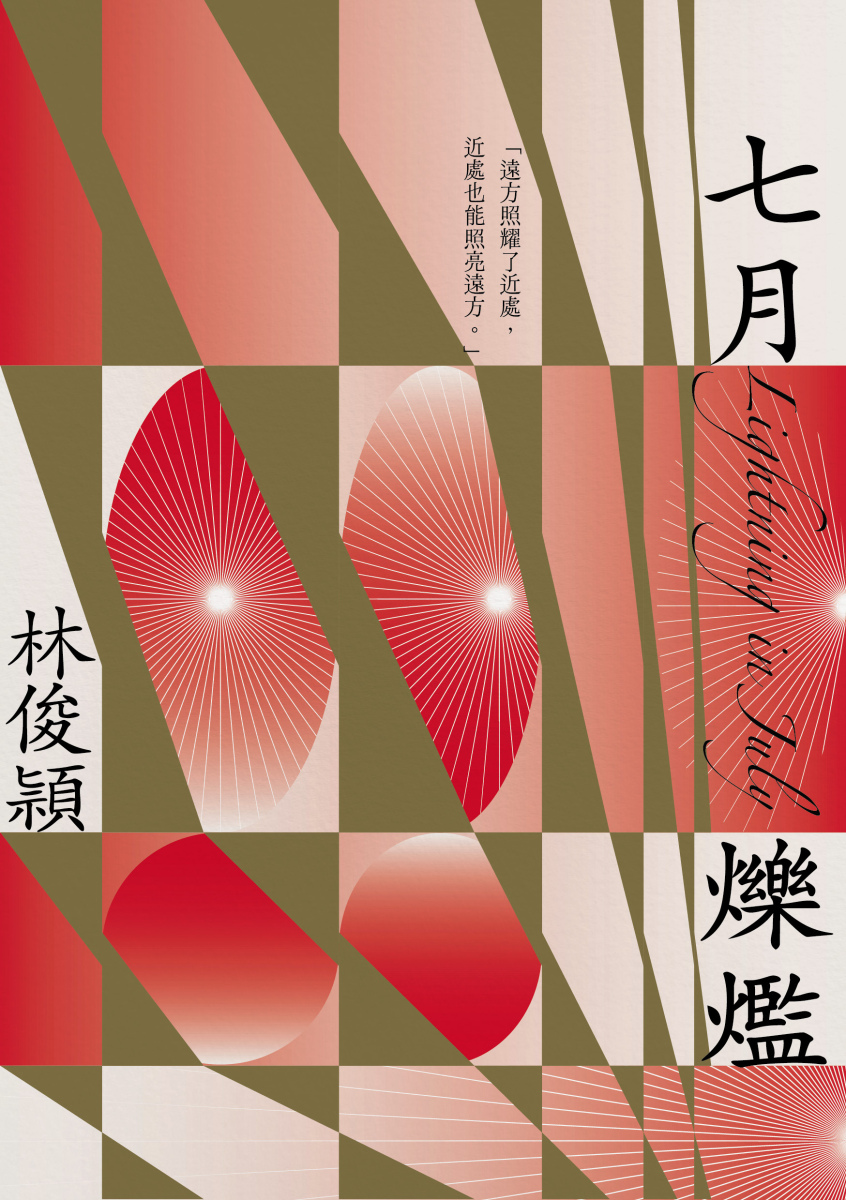 七月爍爁
七月爍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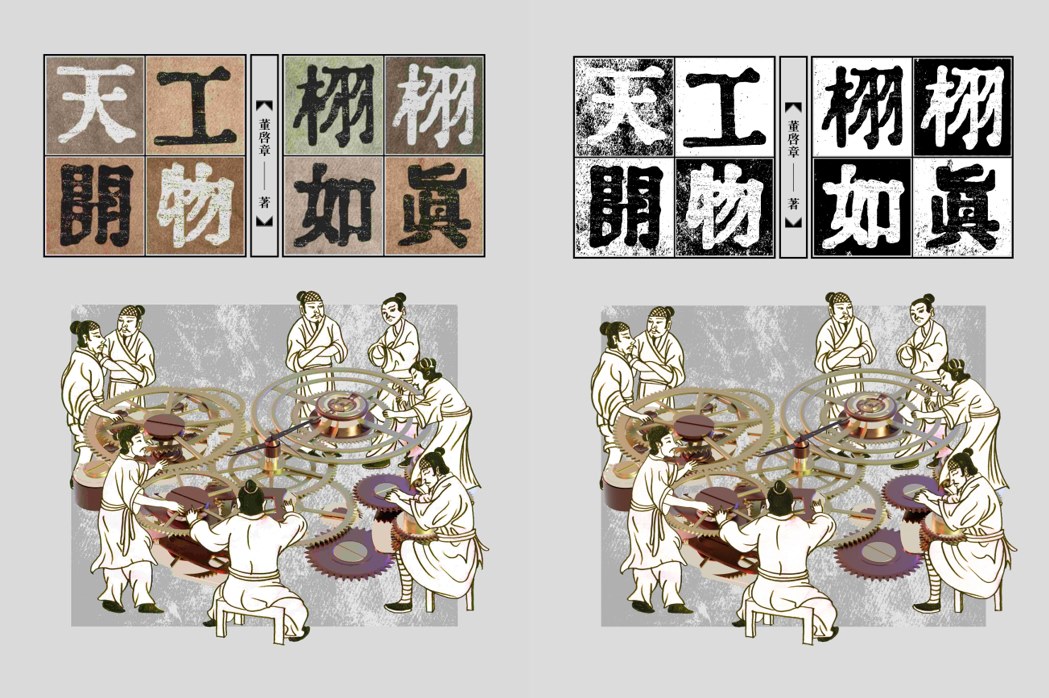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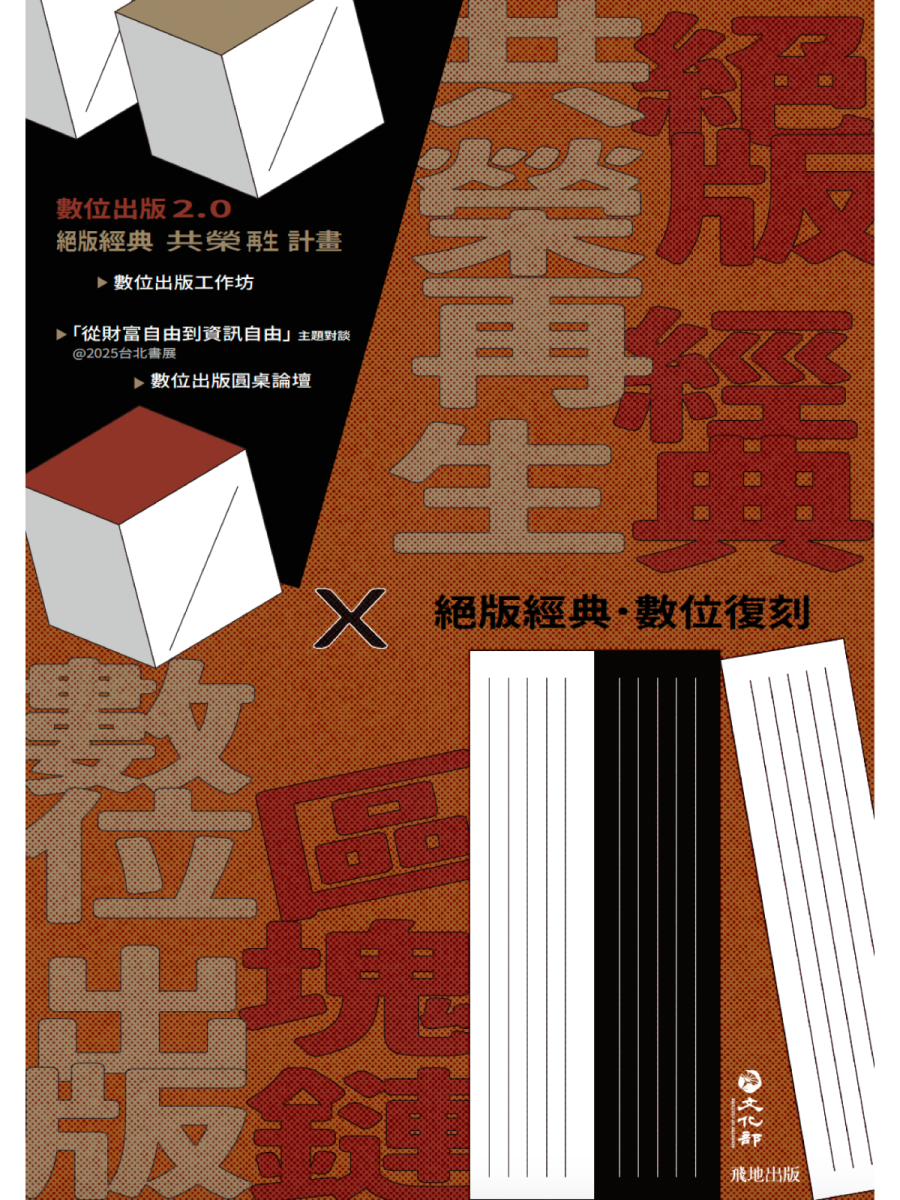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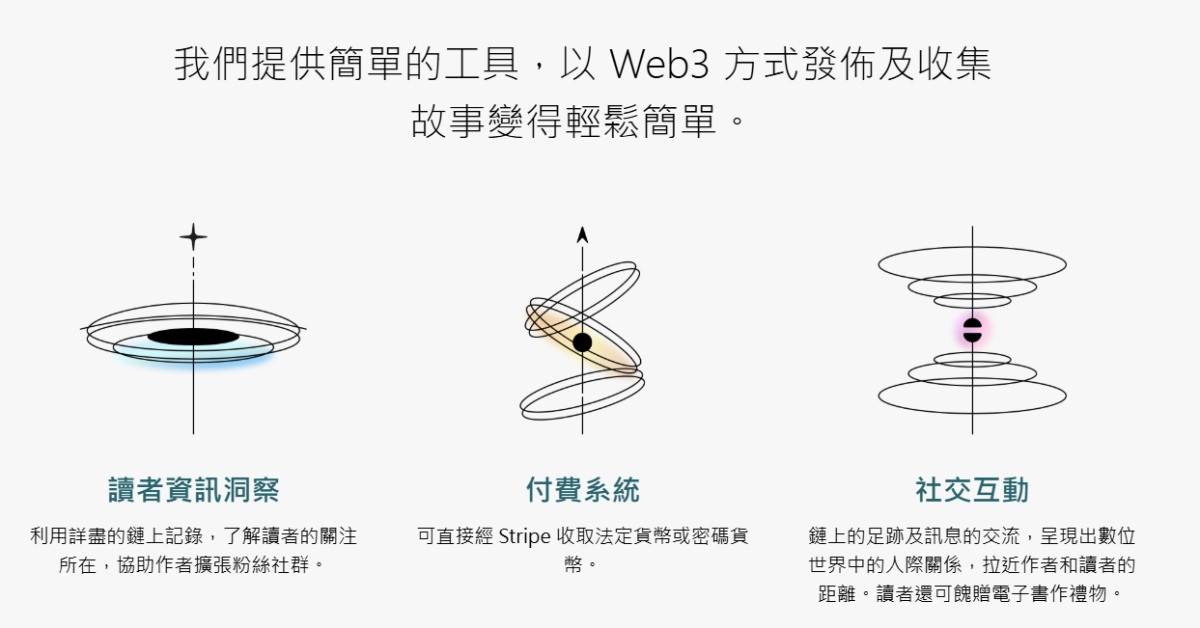

漫評》調和混搭類型的神祕調味料是「人情味」:評《大魔法搜查線》
➤本格推理與奇幻冒險的豐盛拼盤
故事主角警長兼魔法使雅迪妮絲.德布西進入帕加瑪總督府,面對著形形色色的要角:有權有勢的貴族、各有矛盾的警方一局二局、風靡全國的「勇氣的歌姬」、勢如水火的獵人公會與反獵捕聯盟勢力,當他喊出:「帕加馬的恐懼、無名焚風、行動天災,帶走足足三十三條人命的連環殺人兇手──紅伯爵,就在我們之中!」我們知道,一場熱鬧的本格推理與奇幻冒險遊戲,就此展開!
《大魔法搜查線RESET》是以香港推理小說名家陳浩基的《大魔法搜查線》小說為基礎,由台灣漫畫家霖羯進行故事修改與作畫推出的奇幻推理漫畫。
故事的世界觀是經典的日式奇幻設定:在聖騎士海明頓戰勝魔王後,進入了各種種族和諧共存的太平盛世。出場種族除了人類、精靈、矮人、魔族外,還有魔物與龍等定番。代表物理與魔法的鬥氣與六屬性魔法,也是故事中必備的技能和冒險要素。社會結構也沿用奇幻最常見的前現代歐洲封建貴族制度。
故事場景發生在異人之都帕加瑪,雖然有著多元開放的優點,但也因為多種族混雜,種族、階級和立場間的矛盾與歧視,成為不安的潛在因子。
當主角雅迪妮絲剛進入帕加瑪任職警長不久,即發生了連續殺人案,於是,推理開始了!
幻想世界中的「推理」要如何進行?答案是:只要世界觀有明確的規則,就可以依循世界觀的邏輯進行推理。幻想與推理不但不違背,只要混搭得巧妙,就可以玩出新意。
所以,《大魔法搜查線RESET》的樂趣,就是欣賞陳浩基和霖羯怎麼在奇幻與推理兩種經典規則之間,彼此交織、誤導、翻轉、揭密,展開這場既嚴謹又幻想,既辦案又冒險的混搭盛宴。
➤無敵的人情味
為了整合壯闊冒險的奇幻與邏輯嚴密的推理,《大魔法搜查線RESET》的祕密調味料是:人情味。
身在魔法與巨龍的世界,主角群也身兼異能,但他們的職業是司法體系的「警察」。所以,對於主角雅迪妮絲來說,戰鬥並非必要,更多的時間在守護市民的日常。
也就是說,在奇幻和推理兩個規則底下,《大魔法搜查線RESET》有第三套規則讓兩者能夠並行不悖,那就是警察身為司法單位的限制和倫理、體制下不同派系的權力和階級。
這個制度和視角的限制,讓我們將情感關注在這個幻想世界的日常。連環殺人魔紅伯爵並非唯一的案件。宮廷丑角之女,不喜歡戰爭、也不受重視的雅迪妮絲隸屬專門打雜的萬事科,比起展開壯闊的史詩冒險、與邪惡魔法使或巨龍戰鬥,更常處理的是巨星演唱會維安、尋找走失小貓或兒童,調和捕獵或禁獵不同立場等工作。處處展現陳浩基擅長的社會議題,以及霖羯獨到的日常輕喜劇風格,讓故事的推進幽默暢快又發人省思。
也正因為以警察視角切入,故事的內在主題在點滴日常間清晰卻不刻意的展現:推理揭密真正揭露的,不僅是「誰是兇手」的謎題,也呈現了我們真實世界存在的矛盾:性別、階級、種族、職業、權力結構僵化的壓迫與偏見的誤導,以及突破偏見的勇氣。
所以,故事中的小丑、英雄、貴族、平民、歌姬、怪物、兇手、偵探這些類型經典形象,都在縝密的布局中一一翻轉,最終看到真實的人性。
但大量描繪生活細節的輕喜劇風格,會不會讓奇幻和推理失焦?別擔心,這可是陳浩基。
基於推理評論的倫理,本文不能洩露線索,但我可以保證:每一個以日常呈現的要素,最後在解篇,都有巧妙、完整的解答。
➤什麼是台灣類型故事,或曰:帕加瑪在哪裡?
推理與奇幻都始於歐美,爾後日本吸收並演化為日系推理和勇者魔王的異世界。香港作家陳浩基轉化後,推出輕小說風格的《大魔法搜查線》,最後,台灣漫畫家霖羯的畫筆下,成功創作出這部台灣類型傑作。
台灣的類型故事是什麼?我相信這個問題,是我這代的創作者、評論者、出版者與讀者要共同面對的難題。《大魔法搜查線RESET》,為我們提供一個很好的範例。
台灣的類型故事是什麼?台灣要素該如何呈現?很多創作者致力於描寫台灣的真實歷史或人文社會議題,當然令人讚賞。但是,在幻想天馬行空的奇幻故事中,即使表面上沒有任何地名或場景直接指涉台灣,我們也應該要有自信:我們可以呈現唯有台灣人可以呈現的台灣味。
溫柔包容的人情味,來自於我們每天所成長、生活、深愛的,兼容並蓄的多元自由社會。多元不僅體現在類型要素的運用,也在人文精神的刻畫。這不僅僅是口號或教條,如故事中所呈現,開放包容需要的是面對未知、彼此理解、擺脫成見蛻變的勇氣。
所以,帕加馬是哪裡?我想,可以是曾經庇護了逃離極權中國,最後在英國制度下茁壯的香港創作者,也是如今,不管在制度、言論自由、出版多元,乃至性別都銳意走在東亞最開放的道路上的台灣。
我想,從這點來看,香港與台灣創作者的合作,更有深遠的意義:我們有著共同的願景,也面對共同的敵人。多元自由的帕加馬,是我們共同守護的信念。●
作者:霖羯、陳浩基
出版:獨步文化
定價:70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
霖羯
漫畫家,暱稱音同「林傑」,出身台灣基隆的漫畫家。畫風俐落活潑,帶有少年漫畫風格,擅長帶有喜劇節奏的輕快故事,作品包括《牧神的足音》、《退休勇者》系列、《荒鷲》系列等作。2022年開始改編陳浩基同名原作《大魔法搜查線》,並以全新《大魔法搜查線RESET》問世,目前在台灣亂搭網站上連載原創成人BL漫畫《最惡契約》,也用「熾羽」一名在同人場上走跳。
陳浩基
本書原案,作品《13.67》獲得2017年度日本「週刊文春推理Best 10(海外部門)」及「本格推理Best 10(海外部門)」兩大推理排行榜冠軍,為首次上榜亞洲作品。另著有推理小說《遺忘.刑警》、《網內人》、科幻小說《S.T.E.P.》(與寵物先生合著)、《闇黑密使》(與高普合著)、《大魔法搜查線》、《氣球人》、《山羊獰笑的剎那》、《第歐根尼變奏曲》等多部作品。
閱讀通信 vol.371》我有故事,你有真心嗎?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