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漫電訊報13》漫改影視的兩難:多方角力注定無法皆大歡喜嗎?
一月底,《SEXY田中小姐》漫畫的改編電視劇爆出原著者告白親撰劇本的來龍去脈,當人們還在為此爭論時,卻急遽發展成不可挽回的憾事。雖然還有許多不明確的部分尚待釐清,但如果時間能夠回轉的話,真希望有人能及時安慰老師:「請不用為一次失敗的合作結果暗自神傷自責,希望老師用更多精彩的創作超越這一切,相信還會有其他優秀的影劇製作群帶來改編機會……」
影劇改編會出現的問題,其實遠在漫畫開始受人改編之前,就在許許多多小說作品發生過了。首先因為不同表現媒介帶來的美學差異(即使同樣以影像為主,連續靜態圖片的漫畫還是與動畫影劇的動態表現有所不同),自然要做出一定程度的變動來轉換原作的精彩之處。
此外也因為篇幅問題,原作劇情段落、角色戲份的時間分配不一定契合影劇的片長,改編者也因此需要對情節及人物進行刪除或增補,尤其若是改編尚在連載中的作品,還要配合影劇篇幅給出故事的高潮與完結段落,甚至可能需要準備原作沒有的新創劇情。這一切都極有可能讓影劇版本的故事出現天壤之別的變化,不可不慎。
不過,很多人看到影視改編爭端時會自然地靠往原著至上的立場,但至少對觀眾來說,「大改原著」本身絕非罪惡。
一些作品為人稱頌的導演,也有著「原作粉碎機」的稱號。像是宮崎駿(《魔女宅急便》、《霍爾的移動城堡》其實都有原作,被他做了非常大幅度的變動)、押井守(《福星小子》電視版就放任製作群恣意加入各種原創要素,到了他擔綱編劇的「劇場版2綺麗夢中人」,更是讓作者高橋留美子說出「這是押井守的福星小子」劃清界線),他們擁有自己的創作風格與見解,原著對其來說更像是作為一種靈感依託,說好聽是「有獨特的詮釋方式」,說難聽點或許是「借題發揮」、「借殼上市」。
但這些歷經時間考驗的地位成就顯示出,如果動畫作品本身有吸引人的獨到風格,其實不管原作者做何感想,觀眾是會認可的。另一種「不照漫畫原著改編」的例子,則是像「漫威電影宇宙」這樣的作品。雖然有著通透漫威漫畫的總監來執掌全局,讓影劇的角色、事件與要素不致跳脫漫畫過遠,但也確實從來不會照搬原著情節發展來演,更多是作為一種靈感與致敬的來源。而最終評定各部電影好看與否的,也不是原著漫畫的讀者,而是更為廣大的全球電影觀眾。
當然,絕大多數的影劇改編並非由上述那些獨特的製作人士經手,主要是由既有電視電影公司的影劇產製工業進行。影劇公司與電視製作人的考量是將影視產品的商務成果放在優先位置,而且以電視劇來說,他們希望優先吸引的不是已經熟悉原著的讀者,而是平日觀看各種影劇,可能根本沒有漫畫閱讀習慣的另一批客群。因此製作方面很可能會根據影劇界的經驗提出各種合理乃至不合理的改動需求,把一些容易對目標客群取得成功的劇情模式套用進來。
例如,要有充分篇幅的戀愛劇、人情劇,甚至還有要突顯特定演藝明星、因而加強飾演角色戲分之類的業界要求。這類要求也不是專對漫畫改編而來,就算是原創影劇也一樣,只是有了原著可供比較,更讓觀眾讀者容易意會到差異而已。如果洽商改編案子的製作人在原著上面尋求的,只是便於配合檔期制式出產影劇的故事素材,安排改編人員時就很可能會組成一個對原著並無共鳴、或者錯誤解讀原著要旨的製作團隊,有意無意地造成改編成果出現重大落差。
過去幾十年的業界生態如此,在漫畫的社會地位還不高時,多數漫畫原作者對於改編影視也往往不會抱著太高的期待。如果能忠實呈現自然最好,如果內容改動過大或者成果不盡人意,也就保持著友善的距離,當作是一次打書廣告的機會就好。近來隨著漫畫社會地位的提高、原作者高度參與帶來改編成功的作品越來越多,使得影視製作方更願意讓原作者在企劃中有更多提出意見的空間,同時也提昇了作者對成果的期待程度。
但是對自身原著的忠實性重視到什麼程度、接受改動的開放程度,每位作者自然不會相同,如果影劇製作人與代為洽商的出版方沒有真的理解「作者能接受的改編底限」在哪裡,即使簽訂了合約,也不能保證整個計畫有協調出一個彼此都真心同意的共識。影劇改編背離原著期待而引來失敗危機,最大的癥結或許不是個別改編細節的忠實與否,而是讓原著與改編雙方的共識溝通出現嚴重斷裂、各行其是。
例如這次《SEXY田中小姐》事件,就是在原著與改編雙方並沒有建立起基本共識的情況下倉促成行,只有約定好「作者會確認劇本是否忠於原著,並視需要改動」,影視製作人對於雙方的見解鴻溝卻消極應對,自始至終沒有安排製作群與原作者預先見面討論,而放任他們用自己慣有的方式改動原始故事寫成每一集劇本稿,造成作者需要逐一勞神反覆修改,到最後還必須親自下來寫劇本,卻招來(可能不知原著方與電視台約定細節的)影劇編劇的不滿。
如果編輯能協助作者當機立斷審慎評估,在更動部分可能會超出容許界線、監修工作無法負荷的不利條件下斷然中止改編企劃,或許就沒有後續這些爭議與悲劇了。
同樣由小學館漫畫改編、由同一位編劇家負責編劇、同樣出現異於原著角色安排的影劇《勿說是推理》,卻是由導演製作人主動爭取改編,而且請來原作者也高度認可的主角演員,作者也不時前往拍攝現場與工作人員交流,劇本部分只需要負責提供各種意見發想、追加部分台詞,最終卻得來備受好評的結果,可以說是完全顛倒過來的案例。
擁有諸多亮眼改編紀錄、甚至獲得國際影視改編合作的集英社,其成就也不是一蹴可及。十五年前他們率先進軍好萊塢的《七龍珠:全新進化》,也率先成了一樁大慘案,讓人們對美國改編日本漫畫徹底失去信心。十五年來隨著日本漫畫國際市場持續開拓、產業地位與資源優勢不斷增強,出版社也持續發展改進影視合作的交涉立約辦法。
最近與網飛合作推出了叫好又叫座的《航海王》影集,就是成功協商將作者的意向優先放到最關鍵:相較於《七龍珠:全新進化》鳥山明空有執行製作人的虛位,製作團隊卻可以不需要聽從他的建議,《航海王》則能約定只要作者尾田榮一郎不滿意,這耗費超過一億美金的影集就不被允許公開。
這樣將原作者的把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再配合製作群積極與他來回交涉討論各種更動細節、甚至配合他的要求重拍或刪除部份拍攝結果,才能達成製作規模如此龐大,卻又在尊重原著與變更內容達成平衡的影劇成果。代表原著方的出版社該作到的,或許就是這樣談好合約規範、對改編團隊做出合宜的底限限制,讓原作者不需要被動期待對方的善意,就能夠在各自利益與規範的合約運作下,確保原著、改編者、觀眾三方都能獲得滿意的結果。接下來就是需要整個業界建立起完善的制度,讓這些成功的交涉不再是「特例」而能成為「基本慣例」。●
(文章授權轉載自「CCC追漫台」,原標題與連結:〈漫改影視的兩難:多方角力注定無法皆大歡喜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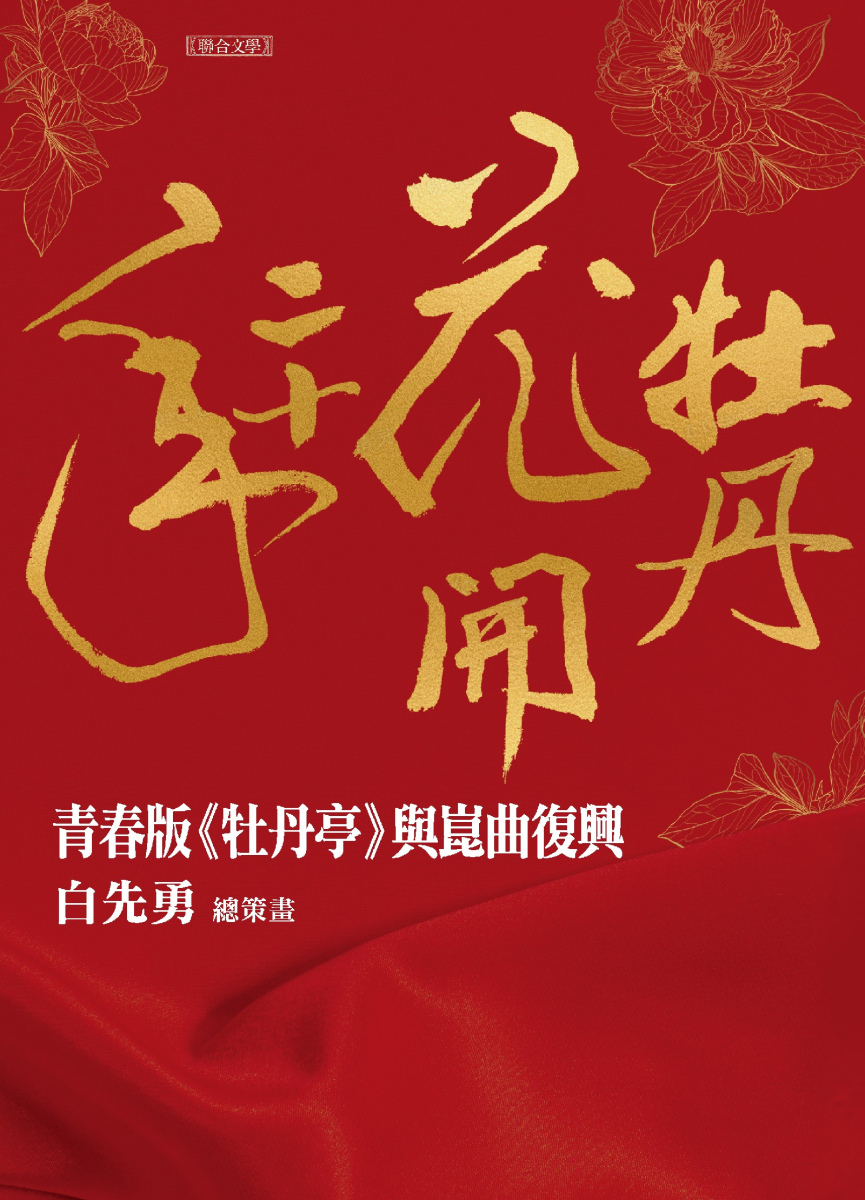 牡丹花開二十年:青春版《牡丹亭》與崑曲復興
牡丹花開二十年:青春版《牡丹亭》與崑曲復興
現場》俄烏戰爭兩年後,烏克蘭人的抵抗故事:波蘭記者皮涅日克與臺灣《報導者》對談側記
波蘭報導記者帕維爾・皮涅日克(Paweł Pieniążek)耗時9個月撰寫《戰火下我們依然喝咖啡:烏克蘭人的抵抗故事》,描述2022年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以來,烏國平民的抵抗生活。去年11月推出繁體中文版的這部動人的報導文學,記錄烏克蘭人在戰火中如何團結起來,維持日常運作,在面對死亡威脅之際又如何堅守家園、展現出堅韌意志。
2月臺北國際書展,衛城出版與波蘭在臺協會共同邀請到皮涅日克,跟臺灣讀者分享他在戰地採訪的經驗,並與臺灣獨立媒體《報導者》營運長兼總主筆李雪莉對談。
➤戰火下我們依然生活
今年是俄烏戰爭兩週年,地球另一端的戰事逐漸成為日常的背景,但對一些人來說,戰場的遭遇依然歷歷在目。演講開頭,皮涅日克首先回顧他對俄烏戰爭初期的記憶。2022年2月,他與友人待在烏克蘭北邊,距離俄羅斯邊境40公里的一座城市。數月以來,當地局勢都十分嚴峻。原先計劃遷徙的人們,因為無法預測戰爭是否開打而取消車票,害怕轟炸的居民也購買膠帶貼緊房屋門窗。
24日清晨,皮涅日克在爆炸聲中驚醒,隨即與友人打包行李離家。街上商店大多關閉,周圍不斷傳來空襲警報與轟炸聲,人群陷入慌亂。一夕之間,烏克蘭首都基輔從一座生氣蓬勃的城市,變成充滿瓦礫廢墟的空城。為了盡快掌握戰況,皮涅日克投入不間斷的採訪工作。他走遍烏克蘭各大城市,採訪受到戰火波及的人們,也向過往熟悉的街道告別。戰爭帶走日常熟悉的景物,從壅塞的交通、牆上的塗鴉到根著的居民。然而,戰爭也賦予烏克蘭人抵抗的勇氣。
某日,當空襲警報暫緩,皮涅日克與友人在基輔遊蕩。他們無意間看到一家販售咖啡、薯條與花的奇異酒吧,發覺並非所有烏克蘭人都選擇離開家園。漸漸地,城裡一些商店開始重新營運,供應躲避空襲的平民免費熱食或咖啡。人民也重新集結合作,在自身崗位發揮職責。
從修復鐵路到維繫通訊,從救助傷患到尋常的勞動休養,在戰時體制下,烏克蘭人透過維繫日常生活,向敵人宣示他們頑強的意志。這股意志成為前線士兵不可或缺的心靈支柱。
➤從無聲到有聲的煙硝
當俄烏戰爭爆發時,同樣身處戰場的是《報導者》的記者們。2022年,報導者團隊派駐三人前往烏克蘭,在當地進行為期5個月的採訪。期間,他們歷經戰事加劇,在當地投保的戰爭險從台幣5000元飆升到6萬元,也見證烏克蘭人勇敢的抵抗。
回臺灣後,《報導者》出版《烏克蘭的不可能戰爭》一書,記錄他們在戰火下目睹的烏克蘭社會。這本書探討戰爭時期烏克蘭面臨的國防、經濟、人道與能源安全等課題,為臺灣讀者提供認識與應對戰爭的借鏡。在這場講座上,李雪莉從臺灣媒體人視角,對《戰火下我們依然喝咖啡》與《烏克蘭的不可能戰爭》兩本書,提出引人深思的見解。
戰爭的起點常是無聲的煙硝。2014年,烏克蘭發生廣場革命。當時,烏克蘭人民在首都基輔發起示威,抗議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擱置與歐盟的協議,並策動強化俄烏關係。同一年,在烏克蘭領空,一架馬來西亞航空班機被俄羅斯軍隊擊中,造成289名乘客罹難。從烏克蘭國內的民主抗爭運動,到地緣政治引發的意外事件,都令人警覺鄰近強國的步步進逼。
廣場革命過後,俄羅斯加緊侵略烏克蘭的腳步,透過文攻武嚇,俄羅斯極盡所能否定烏克蘭國家的獨立性。2021年,俄羅斯總統普丁在官方網站上發布7000字長文,直指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為不可分割的民族,並將兩國的紛爭訴諸於歷史悲劇。
這段論述讓李雪莉想起習近平在2019年發表的〈告臺灣同胞四十週年〉演講。她指出無論是俄羅斯或中共的領導者,都藉由偶然的歷史發展,合理化侵略鄰國的行動,並以溫情敦厚的敘事包裝清洗其他種族的野心。許久以前,戰爭的跡象早已存在於獨裁者的話語中。
假使語言是臆測與挑動人心的利器,那在危急時刻,資訊的傳播與接收便成為影響戰事的關鍵。如同李雪莉提及,當俄烏戰爭開打後,資訊戰成為不容小覷的攻擊。無論是俄羅斯透過《Russia Today》等媒體,在以中共為首的華語世界散布假消息;或者俄羅斯官方以「普丁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等用語,混淆掩蓋其侵略目的,資訊的清洗與替換,是當代混合形戰爭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資訊戰就像輸出能源跟武器。」李雪莉表示,尤其當臺灣與烏克蘭一樣,受到歷史淵源與多族群背景影響,國內都面臨認同差異的問題,培養媒體判讀能力成為應對戰爭的重要措施。
儘管烏克蘭遭受戰火侵襲,《烏克蘭的不可能戰爭》與《戰火下我們依然喝咖啡》二書都記載了烏克蘭人的頑強抵抗。《烏克蘭的不可能戰爭》揭示烏國人民以小搏大、有如大衛對抗歌利亞巨人般守護家園的勇氣;《戰火下我們依然喝咖啡》的原版書名,本身就是波蘭文中的「抵抗」(Opór)。戰爭的無情跟犧牲是兩本書的作者一再想傳遞給讀者的訊息,然而這兩本書卻也傳達了希望。如同李雪莉引用書中文字說道:「要是在這一切過後,我們還保有健康的心智,那我會感到非常驕傲。」
➤兩年後的我們,在創傷中持續抵抗
俄烏戰爭爆發滿兩年,戰事的膠著與國際局勢的詭譎變化,讓人擔憂眼前的苦難將沒有盡頭。皮涅日克與李雪莉長期追蹤烏克蘭議題,都意識到西方社會與臺灣對戰爭的關注漸趨沉寂。以歐洲為例,李雪莉提到近期一份民調指出,歐洲有將近兩成到四成人民完全不在意戰爭結果。而在美國,受到保守黨勢力佔據的國會,更出現「如果美墨邊境不築圍牆,美國將停止贊助烏克蘭」的聲音。民主國家願意投入多少資源對抗這場不人道戰役,是烏克蘭能否勝利的關鍵。
回過頭看烏克蘭,隨著戰事延續,烏克蘭社會逐漸變得筋疲力竭。皮涅日克提到,相較於兩年前烏克蘭受到許多盟友援助,近期國際提供的支援愈來愈少。尤其當烏克蘭作為小國,每每在戰場上失去人力與物資,都會蒙受巨大傷害。
國家層級如此,個人生命更難逃劇烈震盪。皮涅日克還在烏克蘭從事報導工作時,曾遇到一名砍柴維生的男子。當時,俄羅斯軍隊常在烏克蘭中部、東部與南部進行轟炸。皮涅日克記得他在採訪男子時,周遭不斷有飛彈飛過,讓他與同事反覆撲倒進行掩護。而那名男子不僅不為所動,甚至對此感到奇怪。
男人的妻子、女兒都在戰爭中喪生,他與自己的兄弟失散,也對現實劇變失去情緒。他的遭遇,只是集體人民的縮影。兩年來,烏克蘭人被迫學會適應空襲,在戰火侵襲下,可能堅韌可能脆弱、可能麻痺可能激憤地生活。有的人不幸殞命,像《戰火中我們依然喝咖啡》寫到的第一個女性受訪者,其餘的人則不輕言放棄,即便他們已身心俱疲。
講座最後,皮涅日克談起戰爭對自身的改變。2014年,他初次前往烏克蘭報導廣場革命時只是一名大學生;如今10年過去,長年身處於戰地,讓他對緊急狀態的適應力大幅增加,但對戰事的關注與憂慮,也無可避免引致身心的疲倦。話雖如此,皮涅日克仍不忘提醒眾人,兩年來身處在戰火中的烏克蘭人民,並沒有時間休息。當戰爭的資訊逐漸淡化成背景,他期望有更多人給予烏克蘭支持。
在《戰火下我們依然喝咖啡》開頭,皮涅日克引用知名歷史學家提摩西・史奈德(Timothy Snyder)《暴政》一書對如何抵抗暴君的探討,作為全書的精神指引。其中史奈德提出的一項指南,令皮涅日克印象深刻,那就是在危難發生時要盡可能維持勇敢。
「每個人在緊急狀態中都能做出貢獻,當戰爭爆發時,你不一定要是士兵。」皮涅日克說道,即便是在離戰爭很遠的地方,無論你是一名記者、喜劇演員、咖啡店店員或家庭主婦,都可以發揮自己的角色。「勇敢的定義因人而異,你不一定要戰鬥,但可以在離前線很遠的地方盡力支持前線軍隊。」
當危難發生時,我們可能恐慌與憤怒,也可能對未來感到憂慮徬徨。但皮涅日克寫下《戰火下我們依然喝咖啡》,讓我們看見烏克蘭人如何不被情緒擊潰,在如同冷酷異境的現實世界,盡力守護家園、維繫日常生活的溫暖與希望。這本書對當前此時的臺灣,無疑帶來深遠的啟發。●
Opór. Ukraińcy wobec rosyjskiej inwazji
作者:帕維爾.皮涅日克(Paweł Pieniążek)
譯者:鄭凱庭
出版:衛城出版
定價:45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帕維爾.皮涅日克(Paweł Pieniążek)
波蘭報導記者,曾報導烏克蘭、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等地的戰爭與武裝衝突,亦是馬航17號空難發生後抵達現場的第一批記者。2015年榮獲美國耶魯大學波因特基金會頒發給優秀媒體人的獎學金,並於2019年榮獲波蘭MediaTory記者獎。著有《來自新俄羅斯的問候:烏克蘭戰爭的目擊者》與《一場改變我們的戰爭》等著作。
War in Ukraine
作者:劉致昕、楊子磊、《報導者》團隊
出版:春山出版
定價:56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
劉致昕
臺南人。政大外交學系畢。
曾任《商業周刊》記者、《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駐臺助理記者,現為《報導者》副總編輯。
出版著作:《真相製造:從聖戰士媽媽、極權政府、網軍教練、境外勢力、打假部隊、內容農場主人到政府小編》。
曾獲獎項:金鼎獎、卓越新聞獎、人權新聞獎、亞洲出版協會新聞獎、吳舜文新聞獎、臺北國際書展大獎非文學類首獎。
《報導者》團隊
臺灣第一個由公益基金會成立的網路媒體。秉持深度、開放、非營利的精神,致力於公共領域的調查報導與深度報導,共同打造多元進步的社會與媒體環境。
攝影/楊子磊
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畢。曾獲卓越新聞獎、吳舜文新聞獎、亞洲出版協會新聞獎與台灣新聞攝影大賽年度最佳新聞照片。
主編簡介:李雪莉
《報導者》總編輯、臺大新聞所兼任助理教授,曾任《天下雜誌》副總編輯與影視中心總製作人。加拿大McGill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學人。臺灣卓越新聞獎、曾虛白新聞獎、亞洲出版協會新聞獎、香港人權新聞獎、臺北國際書展大獎編輯首獎得主。合著並主編《血淚漁場》、《廢墟少年》、《烈火黑潮》、《報導者事件簿》等書。以記者為志業。
閱讀通信 vol.369》出烤箱的好日子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