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隨身聽S5EP8》顏社主理人迪拉/寫下「後嘻哈時代」會發生的故事
2019年Leo王奪下金曲獎最佳國語男歌手獎,2021年則是蛋堡杜振熙獲得金曲獎最佳華語男歌手獎和最佳華語專輯獎,加上今(2021)年開播的嘻哈選秀綜藝節目《大嘻哈時代》斬獲口碑,在在宣告嘻哈已成為深受聽眾喜愛的重要音樂類型。本集閱讀隨身聽邀請到嘻哈音樂廠牌顏社的主理人迪拉,他在這波浪潮出現前,就已經有意識地通過策展、紀錄片、專書等不同方式,有脈絡地整理嘻哈音樂的台灣在地歷史。他如何看待近年嘻哈音樂的流行和變化?他口中的「後嘻哈時代」又是什麼呢?請別錯過本集精彩節目。
【精彩內容摘錄】
➤第一批開始用中文寫Hip-hop的人
迪拉:國外的嘻哈跟台灣的嘻哈音樂最大的差別,第一個是「中文」。3、4年前開始,中國有實境節目《中國有嘻哈》,今(2021)年台灣做第一個自己的嘻哈實境節目《大嘻哈時代》,都引起很大的迴響,像《大嘻哈時代》錄音前一天那集的直播,我看線上有兩萬多人同時觀看,我覺得那可能是台灣電視節目做直播相當驚人的數字。
所以我認為首先絕對是中文。這兩個節目都很強調「中文的饒舌歌詞要怎麼押」,畢竟這是外來的音樂。在歌詞上,英文子音母音沒有很多,所以押韻比較容易,但中文並不是這樣。我們當年花了很多時間研究:「怎麼樣讓中文的饒舌歌詞押韻且又有趣」,經過十幾年來慢慢努力跟演化,中文的饒舌系統也有非常不同於世界的區別。最早沒有人做,我的年代最早有熱狗MC HotDog、大支,還有包括顏社的蛋堡、國蛋等,都算是第一批開始試著寫中文Hip-hop,而且真的有發出作品的創作者。
➤饒舌音樂=批判?那只是一部分
迪拉:90年代的Hip-hop,那時美國有所謂的「東岸」跟「西岸」的饒舌明星,比如說西岸是2pac,東岸是Biggie,Netflix上可以找到他們的紀錄片,以前的創作者大多是通過他們的音樂、英文韻腳,去了解寫詞的容,再來仿作,套上自己的生活情境。有一種說法,強調「Hip-hop就是要Real」,強調真實,也源於90年代的美國。90年代相較於流行歌手偏泡泡糖音樂,歌詞不著邊際、青春、愛情、校園;Hip-hop跟搖滾音樂一樣,歌詞情境訴求真實。
這點可能也放在台灣。所以剛開始熱狗和大支他們做的東西,很多批判性的內容,如熱狗批判流行音樂、批判校園制度,大支則批判政治、社會不公。很多台灣人到現在聽Hip-hop,都還會認為饒舌音樂就是批判、Fighting、Battle,實際上,我覺得這只是一部分,只是因為大家喜歡看人家吵架嘛。
➤埋頭讀國外Hip-hop音樂雜誌的年代
迪拉:以前我們會閱讀很多國外的Hip-hop雜誌,它介紹許多國外Hip-hop的文化,不管是訪問製作人、歌手,或帶出文化脈絡,因為以前沒有維基百科,所以必須大量讀國外Hip-hop雜誌。偶爾也會有專書,可以多了解一些掌故,知道掌故後,在那時的Hip-hop社群,你就是一個學者,那個是非常社會學的。
閱讀歌詞時,因為CD裡沒有歌詞,好不容易後來國外開始有一些歌詞網站,我們也大量去看,打開歌詞網站配著音樂聽,確認歌詞的細節,裡面歌詞很多「黑話」,字典也查不到。那時網路開始出現我們奉為聖經的,叫《Urban Dictionary》,可以查黑話。當然它是英英字典,我們會上去查像「POPO」、「Five-O」等等,這些都是美國黑話對警察的代稱。
➤嘻哈囝系列計畫,希望歷史不只有成功者的故事
迪拉:之所以開始做《嘻哈囝:台灣饒舌故事》系列計畫,其實動機還蠻單純的。首先,我覺得自己滿幸運的,從台灣Hip-hop開始早期就加入,跟大部分所謂我們道上或我們生態圈的人,我都熟識,甚至一起奮鬥過的。我那時已經預知到接下來台灣的Hip-hop或中文Hip-hop會有一波大的浪潮,這是我嗅到的感覺。
第二,我認為當時是一個很好的時機,我了解脈絡,也有人脈跟一點點江湖地位,我把大家找來,做一個紀錄,不管是辦展、寫書或拍紀錄片,藉機把幾個團隊好好梳理梳理。我預設10年、20年以後,都還會是很重要的紀錄。事隔約3、4年,我相信如果現在再去訪問書中的人物,講法一定不一樣。
➤後嘻哈時代會發生的故事
迪拉:我試圖在做一個後嘻哈時代會發生的生活故事。像我現在顏社已經做了16年了,可能很多小朋友現在看到我已經會說:「我從小聽你們長大的。」很多跟我同年齡、一起長大的朋友,現在已經有小孩2、3個。我就想像跟我同齡的Hip-hop囝,他們現在的生活是什麼?我就是露營、做瑜珈,他如果開咖啡店,會不會像我一樣放大輪子在咖啡店門口?我就開始設計,譬如做瑜珈課、露營,這些東西都是我覺得後嘻哈時代應該要有的文明進步,講噁心一點是這樣。
講簡單一點,我不可能再把三十幾歲的Hip-hop囝拉來說,「我們一起到Legacy去Beatbox」,不可能,他們可能現在也不願意在車上放這麼激進、喧鬧的音樂了。那我要怎麼樣跟他們做連結?就是我也放我自己回家會聽的東西。
即便顏社已經是一個非常不商業的廠牌,但我現在還是要留意現在美國流行怎樣的聲音、台灣流行怎樣的聲音,那是我的工作。但我自己也已經改變了,下班之後是不聽這類型的音樂。
➤真正會做菜的人,不會認真看配方
真正會做菜的人是不怎麼認真看食譜裡面的配方的,像我可能做菜到一定程度,我買的食譜,最先當然是當A書來看,當Food Porn。第二個是看它有沒有什麼獨到的處理方式,像我喜歡日本飲食書,有一位飲食作家平松洋子,她就不會跟你講什麼步驟那些東西,她談自己與料理的淵源,也寫料理的特殊處理技巧,我覺得這個是有用的,對新手來說當然不一定是。
西點的確是比較科學實驗的,當然那些份量、數字比較有意義,但它還是有很多變因,包括食譜不會提室溫,發酵時間長短,除非有發酵箱,不然無法控制。所以它變因還是很多的,一切還是參考,如果是一位西點的熟手,他看那些資訊,我相信他也會知道配方跟份量,大概看一下就會用他自己的方式來做,不會照它的份量來做。
最近我最喜歡的書是已經九刷的《老派少女購物路線》,我一開始就買了。作者真的非常厲害,懂做菜的人會知道這個人真懂吃,也懂做菜。像舒哥(舒國治)的話,就知道他懂吃,但他不懂做菜(笑),從文字中就可以讀出來。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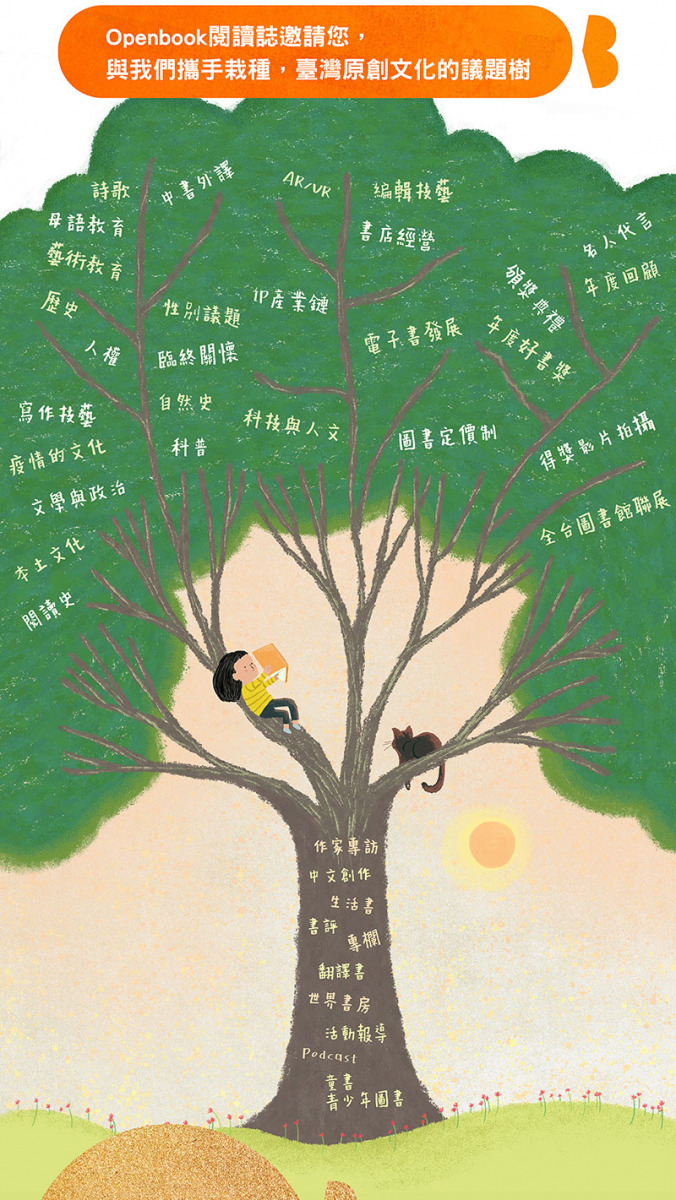
主持人:吳家恆,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畢業,英國愛丁堡大學音樂碩士,遊走媒體、出版、表演藝術多年,曾任職天下雜誌、時報出版、音樂時代、遠流出版、雲門舞集、臺中國家歌劇院。除了在大學授課,在臺中古典音樂台擔任主持人之外,也從事翻譯,譯有《心動之處》、《舒伯特的冬之旅》、《馬基維利》、《光影交舞石頭記》等書。
片頭:微光古樂集 The Gleam Ensemble Taiwan;片尾音樂:國蛋〈嘻哈囝〉,顏社提供。The Gleam Ensemble Taiw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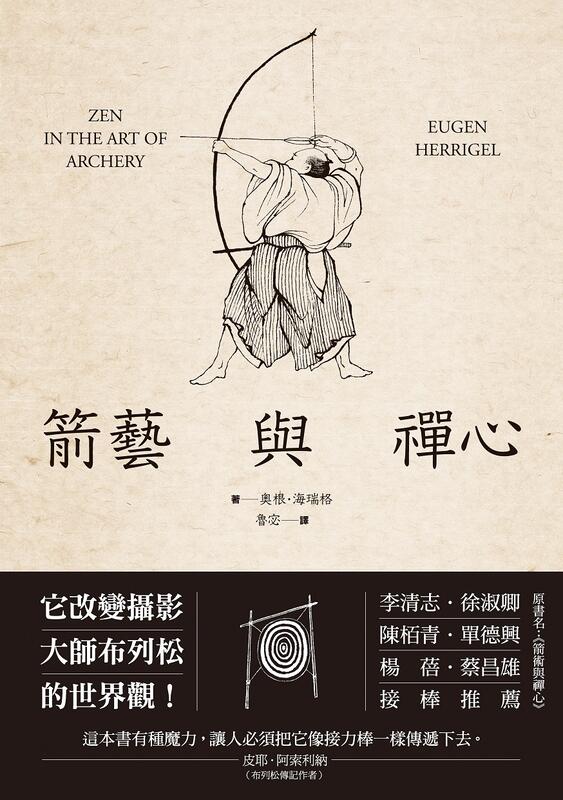 導演陳芯宜過去以紀錄片見長,主題觸角多變,囊括臺灣劇場、日本舞踏、社會運動、身體意識
導演陳芯宜過去以紀錄片見長,主題觸角多變,囊括臺灣劇場、日本舞踏、社會運動、身體意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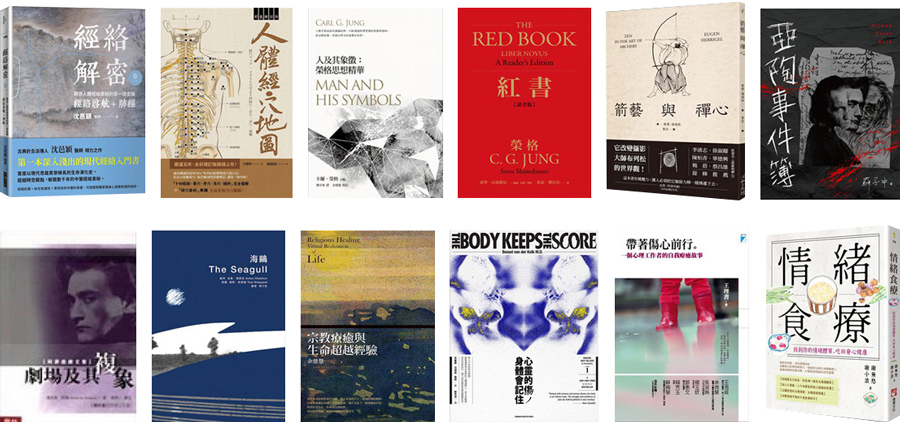
書評》當巨賈土豪橫行全球,中國對消費主義的操弄與自我否定:評《消費中國》
在疫情蔓延人間之前,東京銀座。
A君走進一間創業近90年的壽司名店,這是這趟日本之旅的重頭戲,也是最貴的一筆花費。但A君沒有太多遲疑,能用錢重溫的回憶,都是划算,尤其經過這幾年的波折,A君打定主意這次來日本,一定要重訪記憶裡的美好,宣示人生下一階段的開始。所以他省吃儉用了好一陣子,並硬生生把前次入門的午間套餐,打腫臉升級成高級晚餐。
傍晚按約定時間抵達,店面素雅依舊,女侍依例於門口迎接,一路引領到吧台,師傅已經就位。晚間只有兩種套餐,線上預約時就已選定其中便宜的項目,省去一些不自在的尷尬。稍稍寒喧,師傅老練地依序送上幾年來難忘的美味,每一道皆環環相扣,像一首流暢的曲目。
一切美好,直到中途來了一群中國觀光客。
三名女子,約莫二十多歲年紀,其中一人身穿專門租給觀光客的和服,應該是小團體的領頭,一路負責和店員、師傅對話。三人嗓門不小,一入店就擾亂原本的靜謐。然而真正讓氣氛尷尬的是,她們拒絕套餐,堅持單點。師傅頗有難色,幾經溝通無效,也只能配合。三人把銀座的壽司名店當成迴轉壽司,一盤又一盤點選最奢華的食材,反覆來回指名頂級鮪魚或海膽,每一盤端上來的壽司都伴隨著師傅不自在的笑容。
女子邊吃邊開箱剛剛在銀座購物的戰利品,各種只在雜誌上看過的名牌,佐著高單價的壽司,交織出濃郁的銅臭,也對映著A君的寒酸,整個晚上的愉悅就此戛然而止。
出於理性或感性,我們都相信這樣的經歷只是少數特例,但每個旅人在旅途上,似乎總遇過一兩次這類來自中國的暴發戶。他們在世界不同角落用難以想像的天價消費,展示著壓倒性的財力,就算是少數特例,但這樣巨賈土豪般的刻版印象始終深植人心。驚人的消費力,成為幾十年來中國崛起最具體而實際的現象,不時出現在日常生活或新聞報導中,每每看到,總讓人忍不住心底嘀咕:「這不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嗎?」
當然,面對這個帶點淡淡酸意的反問,多數人都能提出類似「共產主義早就只是空洞的旗號」,或者「消費欲望不是意識形態所能控制」等等常識般的回覆。正如同所有的「常識」,這樣的答案既對且錯,只能從表面層次提供表淺的印象,無法回應錯綜複雜的深層構造,導致看不清問題的本質。
葛凱(Karl Gerth)的新作《消費中國:資本主義的敵人如何成為消費主義的信徒》為這個「常識」的印象,提供了更全面整體的分析,以堅實的史料解析和理論推斷,呈現出消費現象和國家權力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
葛凱長期關注近現代中國消費主義,前兩本著作《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以專業的學術文字分析20世紀前「國貨運動」背後所具有的歷史意義;《中國好,世界就好?一個牛津大學教授對中國消費的25年深度觀察》則以平易近人的筆調,分析改革開放後中國消費市場蓬勃發展對世界造成的影響。《消費中國》則將焦點集中在1949年至1976年,毛澤東治下中國政治試圖對消費的控制。三者合觀,可說完成了一套關於中國百年消費現象的完整論述。
三本書擁有共通的觀察和主題,一方面從人們的消費和商品的流行,重新理解資本主義對近現代中國的深遠影響——對消費的渴望以及進而形成的消費文化,幾乎不受政治或社會更迭所左右,無論戰亂、承平,不管誰人主政,這條由眾人內心欲望匯集的長河,都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奔流不息。
另一方面,作者更進一步勾勒國家權力試圖駕御或利用這股龐大力量的努力,以民族主義為染劑,拼命想在消費行為之中染上自己的色彩,進一步擴張或鞏固統治。從國民政府的「國貨運動」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四舊運動」,不論統治者高舉的是儒家倫常或共產主義,又或者表面上對於舖張消費採取多激烈的抨擊,執政者總是主動且積極地運用人民對流行事物的消費,傳遞所欲打造的意識形態。
但對統治者而言,消費是一把雙面刃,是匹難以降服豢養的猛虎。其中聚合了太多人心虛榮、執念、貪求等等本能的衝動,那是政治權力始終無法徹底染指的私領域,蘊藏太多陽奉陰違的「弱者的抵抗」。如同作者所形容,試圖利用消費主義的統治者,最後多半會陷入騎虎難下的困境。
以《消費中國》書中毛澤東治下的中國為例,開篇以1970年代中葉至80年代期間中國人對「三大件」(手錶、腳踏車與縫紉機)的狂熱,顯示人們對於消費的渴望與需求始終未曾消失。這樣的消費熱潮,在表象層次或可簡單用文革結束、政治氣氛舒緩加以帶過,但在更深層的核心,則顯示整個毛澤東時代,政府從來沒有真正打算消滅人們的消費欲,而是想要加以操弄,張弛之間釋放出各種矛盾的訊息。一旦找到機會,這頭政府試圖豢養的野獸,就如猛虎出閘般不受控制。
葛凱認為「中共自我認定的社會主義國家並非資本主義的對立面,而是一個對工業資本主義實施控制的『國家-私人』光譜上不斷移動的點。」簡單來講,就是將資本的累積和分配,乃至個人購物在內的每一個環節,通通由國家主導,納入國家的控制。作者以「國家消費主義」來形容這樣的管控在消費端的體現。
透過各章的分析,由蘇聯的舶來風尚,廣告、海報或電影裡面的種種形象,對服務業的整頓,乃至暴力政治頂點的文化大革命,中共政權從來沒有打算要徹底抵制資本主義式的消費,而是想要引導消費的方向,打造出新的流行事物。就像在文化大革命風行的毛像章一樣,中共政府是意圖控制消費,而不是消滅消費。這樣的控制有出於政治目的,也有經濟目的,端看執政的需求,有些禁止,有些鼓勵,結果就是充滿矛盾。
然而,購物欲望又豈是那麼容易操縱。《消費中國》裡記錄了太多反作用力的例子,被禁止者等待時機反彈,受鼓勵者則淪為瘋狂。消費欲望如同《侏羅紀公園》裡的恐龍,總在官方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出路,當文革抄家都能成為變相的流行型錄,成為一窺上層流行的管道。紅衛兵展示抄家沒收物品,目的是揭露「資產階級的惡行」,結果反倒激起參觀群眾的購物欲,進而延伸出各式各樣的貪腐行徑。類似的例子都說明了,政府不只無法操控消費,這樣操弄的妄想,社會反而陷入比資本主義更誇張的不平等中。
如同英文書名簡潔明瞭指出的「無盡的資本主義:消費主義如何否定中國的共產革命」(Unending Capitalism:How Consumerism Negated China's Communist Revolution),中共對消費的操弄,最終反成為對自我的否定,尤其當改革開放後,政府有心朝向強化消費的政策,結果造就了一則又一則土豪軼事或印象。
閱讀葛凱三部關於近現代中國的著作,能獲得許多不同的思想刺激。除了專業層次的討論,譬如重新檢討冷戰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二元結構,或中共統治的本質為何等嚴肅的議題之外,對一般讀者來說,最吸引人的,或許還是他藉由每個人都習以為常的消費現象,去挖掘歷史意義的能力。因為如此貼近現實生活和人性,加上關注的是近現代百年的變化,書中所揭露的史學發現,往往都能找到對眼下世界的對應。
在《中國好,世界就好?》一書裡,葛凱反覆強調:「中國的未來和世界未來將受到中國這股消費主義熱潮的深遠影響。……全世界的問題都繞著中國轉。」當「共同富裕」成為新的口號,所有中國工商巨賈奉若聖經,這一次對資本或消費的控制,又會將中國或世界帶到什麼地方呢?
世間無數的A君們,想起那些被毀掉的旅程,只能忍不住打了個冷顫。●
Unending Capitalism: How Consumerism Negated China’s Communist Revolution
作者:葛凱(Karl Gerth)
譯者:陳雅馨、莊勝雄
出版:臺灣商務
定價:55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葛凱(Karl Gerth)
在哈佛大學專研中國消費歷史,師承著名漢學大師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一脈,受孔復禮(Philip Kuhn)與柯偉林(William Kirby)指導,於2000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先後任教於南卡羅來納大學與牛津大學,現為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歷史學系教授、Hwei-Chih and Julia Hsiu中國研究基金會首席講座教授。
1986年時大學三年級的葛凱首次訪問中國,從此他也踏上了日後三十餘年中國研究的漫漫長路。探討中國消費及資本主義問題的他,致力於建立近代中國消費主義的歷史演進脈絡,亦即「中國消費主義三部曲」。本書為三部曲的最後一部,補足了消費脈絡最後、最不為人知但最為重要的一塊,亦即毛澤東時期的消費文化概念。另外兩部分別為:《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中國好,世界就好?一個牛津大學教授對中國消費的25年深度觀察》
【Openbook國際書展參戰(;・`д・´)】
2/6(五)歡迎加入玩耍!•̀.̫•́✧書寫、行動與反思:和島嶼互動的幾種方式
閱讀通信 vol.368》台北國際書展,來襲!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