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我已投胎轉世三次,每一世我都是作家:專訪《女戰士》作者湯亭亭
湯亭亭一生獲獎無數,在美國文壇地位甚高,被譽為最具代表性的亞裔美國文學作家。今年3月,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慶祝50週年,便邀請湯亭亭擔任特邀講者。演講中,她回憶起首部作品《女戰士》出版時的困難:「當時有家拒絕了我的出版社告訴我,他們不能出版這本書,因為這等於是把貓拿給想買豬的人。」她說:「關於我的創作,這是我認識到的第一件事:我在讓人上當、變成冤大頭。」
《女戰士》於1976年出版,甫上市便一鳴驚人、造成轟動,原因之一就在於她以雜揉虛實的創作手法寫作回憶錄。然而,湯亭亭挑戰傳統敘事,以「說故事」作為創新自傳形式的語言工具,除了呈現一名華裔第二代的所思所想,實質上亦細膩且深刻地傳達了對於少數族裔文化的觀察與關懷。
後輩的一眾跨世代亞裔作家,從《喜福會》作者譚恩美、《同情者》作者阮越清、《Stay True保持真誠》作者徐華與《此生,你我皆短暫燦爛》作者王鷗行,都曾公開表達過對湯亭亭的景仰。徐華更表示,《女戰士》這本書「改變了美國文化」。2014年,湯亭亭獲頒美國國家藝術獎章,肯定她的著作「增進美國社會對亞裔的理解,身為作家的貢獻無庸置疑。」
➤來自傳承的寫作
湯亭亭著有《金山勇士》、《孫行者》、《第五和平書》等作品,是多產作家,也長期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擔任講師,寫作無疑占據她人生的重要部分。被問及驅使她寫作的原因,她語帶神祕地表示:「我覺得自己已經投胎轉世三次,而每一世我都是作家。在我會寫作之前,我唱詩歌,我說故事。」對於自己的寫作生涯,她肯定地說在成長過中,她一直都知道自己是個作家。實際上,她認為後天養育也是關鍵:她的祖父與母親都是說故事的高手,前者每天晚上都會在村裡的廣場上講故事,「而我的父親是一位詩人。」她補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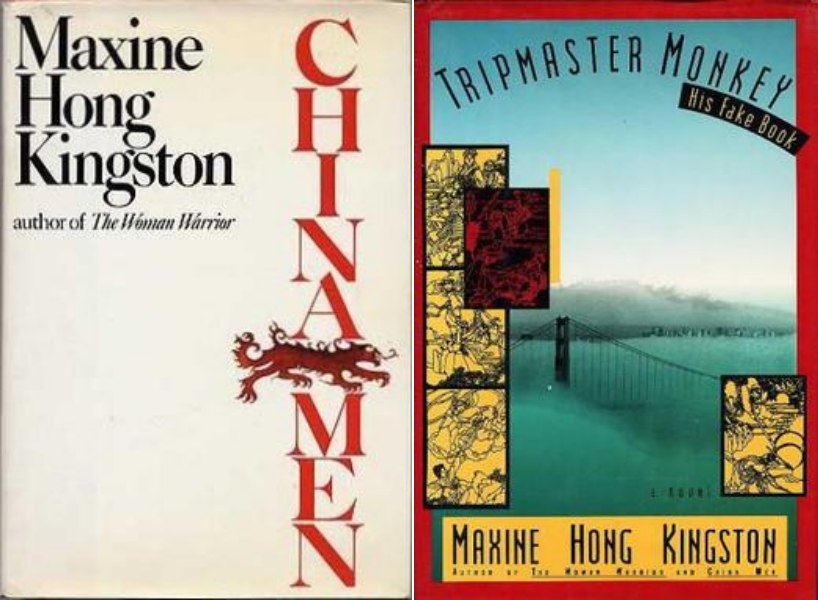
作為首部作品,《女戰士》以湯亭亭自身在加州史塔克頓的成長經歷為引,融合母親的口述故事、她自己或聽來或自行研究的中國傳說與古典文學,以及華裔美國人的歷史,結合現實與虛構,最終串起一連串家族女性與宿命之間的抗爭。湯亭亭形容自己是透過不斷「實驗」,才找到這種不太尋常的寫作方式。「我最初開始寫作,是為了理解我的母親,理解中國,理解中文這個語言,理解歷史,理解我們與生活周遭其他人的不同之處。」
從小到大,湯亭亭記得母親總是說著各種故事,時而順帶一提、時而又要她仔細聽好,但每當她追問起細節,母親卻又閉口不談。那些故事像是在測試她的心智是否足夠堅韌,如《女戰士》的首篇〈無名女〉,移民母親在女兒初經來潮時,將丈夫在中國農村的妹妹婚外懷孕而遭村人逼死的境遇告知女兒,為的就是要藉此警告她,「發生在她身上的事也可能發生在妳身上。別讓我們丟臉。妳可不想完全被人遺忘,好像從來沒出生過。」
如今回想童年往事,許多時刻是她創作的基石,古怪、複雜且微妙的故事從沒少過,「我所認識中國文化充滿了迷信與超自然,充滿了魔法與鬼魂。」而藉由寫作,湯亭亭在做的便是「試圖找出解釋」,她說,「我會馴服混亂。」透過「混合」的寫作方式、行走在「虛構與非虛構之間的寬廣邊界」,《女戰士》反倒為她指引出了一條整頓思路的道路,回到童年時刻,提取與書寫既是創作也是對現實的介入。
➤「非虛構小說」的可能
不過,若說回憶錄書寫關乎一探究竟人生經歷,是為了反思、紀錄,以及記憶,《女戰士》在跨越文類限制的同時,也凝視著眼前的時代。這也是湯亭亭一路寫來的文學信念,當她作為文化轉譯者「翻譯」母親的中國故事,或者投身退伍軍人寫作坊,並出版《第五和平書》以思考和平的概念與創傷敘事,她的寫作既在回應個人的困境,也面向族群或社會集體的創傷。
說故事有可能創造個人與集體的新生嗎?以寫作形式來說,湯亭亭分享自己是透過兩本書的出版,確信了所謂「非虛構小說」是可行的: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夜晚的大軍》(The Armies of the Night)與楚門.卡波提(Truman Capote)《冷血》(In Cold Blood)。兩本書皆於社會與思想產生巨變的1960年代出版,應用小說創作方法與技巧描述真實世界發生的事件,拼湊、理解並也重現了重要當事人的內在心理,捕捉了特定社會脈絡下的關鍵縮影。換句話說,面對時代浪潮,此二書提出的是一種新的文字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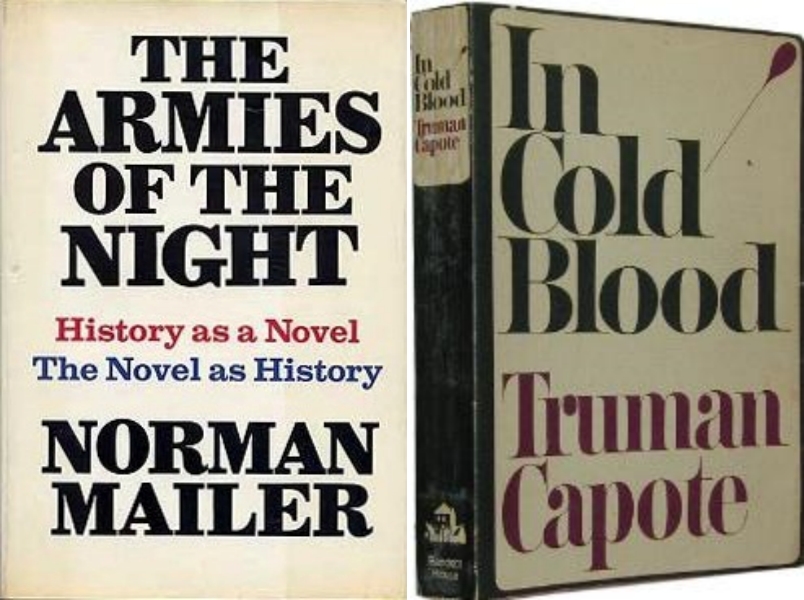
然而面對美國的社會現實,湯亭亭也意識到想像力的行使之於亞裔、之於移民,似乎並非是全然帶來光亮前途的魔法。「讀者可以看到我以這種方式寫作的原因。」提到另一本著作《金山勇士》(China Men)時,湯亭亭如此點出,她在該書講述了詩人父親前往美國時的兩個故事版本,「我的寫法讓人覺得,非法行事的一切似乎神奇到不是真的。我是在保護我的家人不被驅逐出境。」談到當前的美國,她也說她發現自己仍需小心地寫作,就因為「現任的美國總統威脅要無視憲法、驅逐擁有出生公民權的人們。」
➤真實身分
湯亭亭生於二戰,成長的年代經歷韓戰與越戰,加上身為移民第二代,她一直都心懷那些身心皆處於動盪不安之人。無論是《女戰士》還是《金山勇士》,都寫到在異鄉遠望故國的人,同時也有刻意擺脫過去而積極適應眼前生活、或者已完全融入美國生活的人,落地生根的過程中有盤根錯節的思緒與情感。就如她自己作為第二代,亦於書寫中反覆思索自身根源:
「華裔美國人,當你試著了解你內在哪些部分是華人,你怎麼分辨哪些是童年特有的,是貧困、瘋狂、家庭,是你母親用各種故事交織伴隨著你成長,哪些又是華人特有的?」
異鄉生活的困頓讓第一代移民幾乎捨去全部的自己,從職業到姓名,只為了融入美國社會。第二代則面對更艱困的境地,亞裔美籍,雙重的身分如何尋找到定義與平衡點?如何在雙重的文化中弄清楚自己的立場,以及自己到底是誰?對於何謂真實(Truth),湯亭亭似乎早就有答案。被問及創作多年來,「真實」的意義對她而言是否有所改變,她沉靜地回答:「我心中似乎有某種感覺存在——所謂的『真實』就像一塊石頭或一堵牆,某種堅硬實在的東西。我能感覺到某件事是真或假,是實際存在的還是假造的。」
➤亞裔的開花
回顧自己近50年來的作品,湯亭亭以各式文類創作,包含小說、散文、自傳、詩歌,將形式推到極限並且超越。一路走來,她的書寫除了自我表達之外,也廣泛地改變了美國的文學樣貌。正如譚恩美表示,最初正是《女戰士》讓她意識到,「亞裔美國人也可以寫故事,而且這些故事不必關於白人。」對於後輩將自己視為文學英雄,湯亭亭輕輕一語帶過,只說她很高興看見包含她在內的寫作者們可以藉由自己的作品來打造現實,就如她在《第五和平書》中所說的最後一句話:
「孩子們,各位,戰爭期間該做的事是:在毀滅的時刻,創造一些事物。一首詩。一場遊行。一個社群。一所學校。一個誓言。一個道德原則。一個和平時刻。」
近年來,亞裔美國文學與電影,在美國主流文化、甚至綜觀全世界的重要性,都有明顯的提升。越來越多亞裔作家與藝術家開始發聲、分享自身經驗,與此同時也有越來越多讀者/觀眾在聆聽這些聲音與故事,即便他們與這些創作者之間不一定擁有同樣的族裔背景。湯亭亭樂見這樣的改變,但也直言:「我希望我們的文學受到歡迎並不是暫時性的『趨勢』。」在她眼中,這些作品是「世界文學存在已久的一部分」,早已於世界扎根。就如《女戰士》中的女兒向母親提出,她們生命不完全只和某一小塊土地有連結,而是屬於這個地球。●
|
|
|
作者簡介:湯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 憑藉文學領域的卓越成績,她一生獲獎無數:1997年獲總統柯林頓頒發美國國家人文獎章;2006獲得亞裔美國文學獎終身成就獎;2008年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之美國文學傑出貢獻獎章;2011年獲得費茲傑羅美國文學終身成就獎;2013年獲總統歐巴馬頒發美國國家藝術獎章;2023年獲美國文理學院頒發文學領域傑出成就獎章。 另著有《孫行者》(Tripmaster Monkey)、《第五和平書》(The Fifth Book of Peace)、《寬廣人生》(I Love a Broad Margin to My Life)等。 |


 女戰士
女戰士





 社頭三姊妹
社頭三姊妹
2025臺北文學季》故事,從溫州開始:談國際華文作家張翎
➤緣起蘇偉貞:郵購新娘與溫州女人
印象中,從事編輯工作以來,接觸的作家以男性居多,女性作家則較少接觸。這可能和允晨多以人文學術、社會議題的出版取向有關,不過允晨也出版女性作家的作品,如洪素麗的《打狗樹仔》、韓秀《多餘的人》等。
2003年,我因出版小說家蘇偉貞所編選的《張愛玲的世界》續編,和偉貞姊有更多接觸。因偉貞姊的介紹,我才接觸到旅居加拿大的華文女作家張翎。
即使張翎早以《雁過藻溪》揚名中國文壇,我仍十分陌生。偉貞姊介紹出版的是另一部較新的作品《郵購新娘的故事》。初讀這部作品,我即被作者的敘述聲調和節奏所吸引,但我對書名卻頗保留,遲疑的理由是「郵購新娘」一詞雖然貼切故事,卻不是故事的全部,而且用語對臺灣讀者來說感覺有點隔膜,覺得少了某種更深的面向。
小說既然藉由一個來自溫州的「郵購新娘」訴說了家族三代女人的故事,我希望可以有一個書名把敘述的視野和格局拉大。但該怎麼拉大?
改書名的事和作者討論過,新書推出後,銷售和反應不惡,但我不知道張翎其實更喜歡原書名。這是當她來到臺灣時,我們有機會當面聊天時才知道的。過後我想:我的堅持是對的嗎?如果用「郵購新娘」為名,市場反應又會如何?
➤錯過的《金山》:命運與偶然
2008年,張翎就這樣在臺灣登場了。《溫州女人》出版之後沒多久,我將允晨的兩本出版品介紹給光磊,這兩本書就是張翎的《溫州女人》和李劼的《上海往事》。
那時臺灣版權代理的重要推手譚光磊正向海外推廣華文作家作品,如果記憶無誤,這是光磊代理張翎作品版權的開始,也因為這樣的契機,張翎在臺灣的第二本書《金山》,有了完全不一樣的命運。
但是這本書我卻錯過了。張翎曾將《金山》書稿寄來,那時是2010年底,我看完之後並沒有馬上決定。主要是卷帙龐大,而且是加拿大的一頁華人移民血淚史,我沒有把握處理好,所以遲疑了。這一遲疑,整本書的發展方向和作家的緣分也就此分途。張翎的新書,後來都在時報文化公司出版,深獲讀者喜愛。
雖然如此,我們仍然珍惜彼此的出版緣分。張翎於2012和2015年兩度來臺訪問,我們都會找出時間碰面敘舊,交換現況以及對文學出版的看法。記得我們曾去光點台北的2樓喝過咖啡,是一段愉快的時光。
➤時間的暗房:錯身仍有情
不過,2015年4月,我卻接到光磊的來信,問我想不想出版張翎的舊作「江南三部曲」(《溫州女人》、《望月》、《交錯的彼岸》),理由是《溫州女人》是允晨出版,這個系列適合允晨處理,我當下便應允。合作的案子談了一陣,後來不知道卡在什麼關節,戛然而止,最終沒有成案,也許那就是緣分吧。
這同一主題的三部作品,張翎早在《溫州女人》的出版序中就說了,只是我沒留意。這段記憶本來已遺忘,當我檢視過去的往返郵件,才又想起,不過時機已過。
2015年,張翎再度來台,擔任洪建全基金會主辦的第一屆銅鐘經典講座的主講人。我第一次在台下聽著張翎的演講,聽她如何做調查研究,打開一間又一間的時間暗房,尋找其中的故事,勾勒其中的脈絡。我深受感動——故事,原來是這樣寫出來的。
後來又一次見到張翎,是2018年11月,在國家圖書館舉辦的第5屆全球華文作家論壇暨第15屆海外華文女作家雙年會上。那次我主持作家韓秀的演講,講題是:探究、書寫截然不同的世界。
在會場裡也遇到小說家蘇偉貞,偉貞姊還笑著對我說:你什麼時候加入我們協會?之後,沒再見過張翎。疫情肆虐全球期間,一次我在臉書哀嘆書市的低迷,以及出版的慘狀,張翎在臉書留言,以實際購書行動支持鼓勵。這樣的情義,不敢忘懷。
➤出走與回望:離散者的戰爭
撇開個人與張翎的互動小節,這些年來張翎創作不斷,屢獲各種文學獎項,備受矚目。作品的主題始終緊扣生命的關懷和凝視,帶著女性獨有的細膩與堅韌,穿透讀者的心防。
張翎曾說:「傷痛給了我們活著的感覺。」正是緊扣著這樣的感覺,她才創作出一部又一部打動人心的作品。因為打動人心,作品被改編成電影也是水到渠成之事。
《餘震》改編成電影《唐山大地震》,由馮小剛執導,獲得亞太電影節最佳影片獎以及百花獎最佳影片獎。《空巢》改編成電影《一個溫州的女人》,獲得金雞百花電影節新片表彰獎和萬象國際華語電影節最佳中小成本影片獎。2019年起,張翎更化身編劇,和馮小剛導演合作電影《只有蕓知道》。創作的觸角和能量,令人讚嘆。
201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作家蒙迪安諾(Patrick Modiano)曾說,這麼多年來他所寫的,始終只是同一部作品。張翎也相仿,那些寫於不同時期的小說,還是有一些依稀的脈絡可以辨識:出走、成長、探險、回望。其間我總看到那個從水鄉走出的女子,在彼岸異鄉,立命安身。也因為作品的影響廣泛,有越來越多的研究生以張翎作品為研究對象,主題是離散,但在離散的主題之後,還有時代及命運。
在這些主題之外,張翎的小說情味,尤其顯現在節奏的明快,用語的鮮活,別成一種嫵媚與俏麗,十分具有穿透性。曾有女性讀者在博客來的讀者評論處留言:「女性寫女性的故事特別好看。」好看是因為有共感。張翎曾說,女人的每一個故事都是與歷史無言的抗爭,女人的戰爭,有時贏,有時輸。正是輸贏不定,抗爭不止,所以扣人心弦。
➤闊別多年,即將訪臺
2025年5月,闊別臺灣多年的張翎再度來臺參加 「臺北文學季」每年最重磅的單元「國際華文作家」,並將於5/24(六)至5/26(一),與作家平路、鍾文音、朱宥勳等展開系列座談,盛況可期,真是文學愛好者與書迷的福音。張翎本人的溫暖,小說作品的深度與廣度,留待讀者朋友自己體會,這篇小文所分享的,只是我所知的二三事,歡迎張翎再度訪臺。●
相關活動資訊 :
❑歷史的繼承與創造
講者|張翎 × 朱宥勳 × 平路
時間|5.24(六)14:00-16:00
地點|集思台大會議中心蘇格拉底廳
報名連結|(請點我)
❑筆下的女性,像水一樣生存
講者|張翎 × 楊翠 × 鍾文音
時間|5.25(日)14:00-16:00
地點|國家圖書館 1 樓簡報室
報名連結|(請點我)
❑旅行、踏查與書寫
講者|張翎 × 須文蔚 × 曾文娟
時間|5.26(一)13:20-15:10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B1會議室
報名連結|(請點我)
閱讀通信 vol.370》當我在書裡讀到你的時候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