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moo |Kobo |HyRead |Pubu |博客來 |想不同(熊老闆) |TCL |Booking遠流2.0閱讀計畫
【重點新機】
讀墨於書展首度亮相2026年新機,號稱「新世代國民機」的6吋mooInk Chill彩色電子書閱讀器,有迷月白與暗夜黑兩種顏色,搭配聯發科晶片,重量僅170克、6吋窄邊框手握輕盈。
規格全面升級更勝mooInk C,包括第三代彩色電子紙螢幕、4096色電容式觸控、150ppi彩色解析度、提升超過30%的色彩鮮豔度、降低60%藍光、7種色彩模式、3種滑桿調整等。
2026/2/3~2/8書展期間,單機預購NT$4,999(定價NT$7,299的68折),還有「一手包辦」套組預購價NT$5,599(定價NT$8,299的67折),內含mooInk Chill閱讀器、雙料透明保護殼、輕薄引磁片、雙磁圈手機支架。
mooInk Chill
6.13吋EInk Kaleido 3™ 彩色電子紙螢幕
824x1648(300ppi黑白)/412 x 824(150ppi彩色)
電容式觸控,彩色4096色/黑白16灰階
前導閱讀燈(搭載雙色燈,亮度和色溫調整功能)
實體按鍵翻頁/觸控螢幕翻頁(左右或上下滑動翻頁、點擊翻頁)
重量170克(不含保護殼)
尺寸15.9×8.0×0.84cm
儲存容量64GB eMMC
․PU 2.0GHz×4core
RAM 2GB LPDDR4
作業系統Android 10
螢幕按鍵手動旋轉(90/180)
電池容量2400mAh
充電時間約3小時~6.5小時
mooInk Chill
【攤位特點】
讀墨mooInk Nana彩色電子書閱讀器上市週年,於書展現場展示mooInk全系列與Pencil Remote鉛筆翻頁器供讀者親手操作體驗,買mooInk Nana就送超可愛氣囊支架。攤位並設有「開運扭蛋機」,會員出示「讀墨看書」App 登入畫面,即可扭蛋一次,人人有獎。
優惠方面,讀墨推出mooInk系列全年最優方案(最低6折起),買就送讀墨禮券NT$500,2/3~2/10買機啟用新機再送購書金NT$2,000。mooInk Nana彩色電子書閱讀器期間限定只要NT$7,399;搭配《我培育的S級們》與眾多熱門新書套組,最低NT$7,999起。此外還有讀墨首度推出的療癒系品牌周邊限時折扣71折起。
除實體攤位,線上活動「馬上賓果!馬不停蹄馬拉松」也熱鬧起跑。完成特定閱讀任務可領取專屬紀念徽章及紅利回饋;完成連線可再獲加碼獎勵。活動期間每日登入網站並完成簡單答題,立即領取紅利點數或優惠折價券(3本75折券2 張)。揪友加入再抽7吋mooInk Nana彩色電子書閱讀器
mooInk Nana
【書展優惠】
10.3吋Pro 2定價:NT$17,800 書展限定:NT$12,499(7折)
13.3吋Pro 2定價:NT$25,999 書展限定:NT$14,499(73折)
10.3吋Pro 2C定價:NT$19,800 書展限定:NT$15,499(6折)
13.3吋Pro 2C定價:NT$28,999 書展限定:NT$18,499(64折)
7 吋 7 吋 10.3 吋 (含手寫筆) 10.3 吋 (含手寫筆) 13.3 吋 (含手寫筆) 13.3 吋 (含手寫筆)
儲存容量
256GB
256GB
128GB
128GB
128GB
128GB
記憶體
2GB
2GB
2GB
2GB
2GB
2GB
原價
9,299
8,299
19,800
17,800
28,999
25,999
書展優惠價
7,399
7,499
14,499
12,499
18,499
15,499
※ 單位為新台幣(NT$)。2/3~2/10 期間啟用送購書金 NT$2,000,書展攤位另加贈讀墨禮券 NT$500。
Readmoo |Kobo |HyRead |Pubu |博客來 |想不同(熊老闆) |TCL |Booking遠流2.0閱讀計畫
書展現場集結樂天Kobo全系列電子閱讀器,讓讀者親身體驗不同機型的閱讀手感與功能特色。為回饋讀者10年來的支持,樂天Kobo祭出一年僅此一次的書展限定回饋,推出全年最超值的閱讀器優惠價格,並加贈購書金!而知名韓國小說家千明官與人氣創作者HOOK、鷹式一家Hiram等,更將帶來多達14場主題豐富的系列講座。
【攤位特點】
慶祝在台深耕邁入第10年,Kobo於本屆書展打造規模最大的互動展區,並與APUJAN聯名10周年限定商品,包括有星際收納包、宇宙碎片3件組、全球限量5套的10週年服裝。此外還有好玩的籤詩互動牆、拍照打卡免費拍貼活動(可任選一組10週年紀念框),邀讀者一同參與盛會。
閱讀器搭配購書金最高68折起,最多可省$1,680,還有購書金回饋,最高贈送$1,600。消費並贈每日限量好禮,包括有Readimal品牌徽章盲盒或樂天女孩2026桌曆,送完為止。
線上活動方面,書展期間全站75折,單筆滿$2,026再抽2026點樂天點數。樂天市場、PChome24h購物上的「樂天Kobo電子書」,也皆享同步優惠。
樂天Kobo閱讀器體驗區:從大尺寸書寫機型到彩色閱讀器、輕巧入門款全系列展示
「A Decade of Wonder」10週年限定互動體驗區:籤詩牆、KOL 個性簽名文字牆
「A Decade of Wonder」10週年限定活動:樂天Kobo 10週年限定紀念拍貼框
再度攜手國際時裝品牌 APUJAN 跨界合作:打造Kobo x APUJAN宇宙碎片三件組(胸針、吊飾、特殊造型貼紙),以及Kobo x APUJAN星際收納包
【書展優惠】
機型/螢幕尺寸/原價/書展現場優惠價
Readmoo |Kobo |HyRead |Pubu |博客來 |想不同(熊老闆) |TCL |Booking遠流2.0閱讀計畫
【攤位特點】
書展現場優惠方案包括:機殼組特價;滿萬元再享「手寫膜」或「幾米側翻殼」好禮二選一;周邊配件79折優惠,最低47元起;購買閱讀器並享加購「嗨讀訂閱服務」專屬優惠,再送實體商品百元折價券;完成登錄再抽眠豆腐、浩肯包、充電器等,總計高達45個中獎名額。
【主打機種】
主打與幾米品牌獨家聯名推出的彩色閱讀器Gaze Mini CC,號稱「會說故事的時光機」。採用最新6吋電子紙,色彩飽和度提升30%,並內建幾米電子萬年曆,結合一天一張的幾米圖文、24節氣、特殊節日,一鍵整合Google行事曆。
Gaze Mini CC幾米機
HyRead Gaze Mini CC
E lnk Kaleido 3第三代彩色電子紙螢幕,電容式觸控面板
解析度黑白1448X1072(300ppi)、彩色724X536(150ppi)
重量約195g
儲存容量32G(Micro SD最高可擴充至1TB)
觸控螢幕翻頁/按鍵翻頁
實體按鍵開機鍵、上下頁、返回及自定義快捷鍵
螢幕前置光源,搭載冷暖色溫調整功能
四核處理器1.8GHz
3G記憶體
Wi-Fi 2.4G+5G
Android 11開放式作業系統
電池2200mAh,充飽只要2.5小時
內建喇叭及麥克風
具備G-sensor 自動旋轉偵測
【書展優惠】
HyRead Gaze全系列均內建圖書館免費借書功能,書展限時優惠如下(機型方案/定價/現場活動價):
Mini+(6吋)套裝組/$7,480/$6,690
Pro Note(7.8吋)套裝組/$11,780/$10,990
Mini CC(6吋彩色)套裝組/$13,380/$12,099
Pro Note C(7.8吋彩色)套裝組/$16,180/$14,890
Pro X(10.3吋)套裝組/$19,990/$16,390
Pro XC(10.3吋彩色)套裝組/$23,380/$20,390
Readmoo |Kobo |HyRead |Pubu |博客來 |想不同(熊老闆) |TCL |Booking遠流2.0閱讀計畫
【攤位特點】
書展推出限定優惠:舊機換購Pubook閱讀器,現場換購立即折1,000元,品牌機況不設限,舊平板、閱讀器變身新Pubook(換購限Pubook 2 Pro 10.3"、Pubook Mobile 6.13"、Pubook Mobile BW 6.13")。現場購買第二台Pubook閱讀器系列,再省500元。
【主打機種】
Pubook Mobile 6.13 彩色/黑白閱讀器:為台灣第一支手機型開放式電子閱讀器,Pubook Mobile BW 黑白墨水屏同步登場。專為行動閱讀打造,可放進口袋,隨身好攜帶;單手滑讀,通勤也能輕鬆閱讀;跨不同平台可自由選書;漫畫、圖文書,彩色還原;開放系統,能安裝自己喜歡的 App,除了閱讀,也能延伸更多應用可能。
Pubook Mobile 6.13
157.4 x 80 x 8.3 mm
重量約185 g
6.13 吋 Kaleido 3 全平面螢幕
解析度彩色 824 x 412 ( 150 PPI ) / 黑白 1648 x 824(300 PPI)
前光冷暖雙色閱讀燈
電磁+電容(手觸控)
八核心處理器 2.2 GHz
Android 14 開放式系統
記憶體6 GB RAM + 128GB ROM
指紋辨識解鎖
內建喇叭及麥克風
G-sensor自動重力感應
電池容量3550 mAh,可充電鋰聚合物電池
Pubook Mobile
Pubook 2 Pro 10.3" 彩色閱讀器(含Pubook翻頁器手寫筆):獨家快速刷新技術,有效消除殘影;全新雙實體按鍵,可自訂螢幕刷新或其它功能,閱讀時音量鍵可做為翻頁鍵使用,操作直覺更升級;搭載Kaleido 3彩色電子紙技術,細緻顯色,大螢幕也護眼;支援手寫筆記,讀寫同步,內建Android 14系統,自由安裝更多App,自訂你的生產力工具。$19,990 搭配「飽讀Lifetime」,贈NT$2,000購書禮劵。
Pubook 2 Pro 10.3
10.3吋 Kaleido 3全平面螢幕
解析度黑白2480 x 1860(300ppi)、彩色1240 x 930(150ppi)
八核心處理器 2.2 GHz
6GB記憶體
128GB儲存空間
點擊、滑動或手寫筆觸控翻頁
EPUB 直橫排轉換功能、皮套開關感應、G-sensor 自動偵測旋轉螢幕方向
螢幕燈光雙色 LED
指紋辨識解鎖
Android 14 開放式系統
電池容量6000mAh
內建喇叭及麥克風
尺寸237 x 186 x 6 mm
重量約460 g
配件USB Type-C 傳輸線、磁吸式折疊站立皮套
Pubook 2 Pro 10.3
【特色周邊】
Pubook翻頁器手寫筆(含傳輸線、筆芯夾、備用筆芯3支):閱讀器專用全新工具,MIT台灣第一支閱讀器專用翻頁器手寫筆,一筆翻頁、隨手即寫;可適用於市面上多種品牌閱讀器,翻頁 × 手寫一筆搞定。$1,990
Pubook 翻頁器手寫筆
Readmoo |Kobo |HyRead |Pubu |博客來 |想不同(熊老闆) |TCL |Booking遠流2.0閱讀計畫
【主打機種】
博客來2026年全台首發預購限量300組的BookPad Kids 10.3吋鈦空銀兒童學練機。定價$20,800,超級早鳥$16,999,直降$3,801,再送總值超過5,000元6大豪禮,預計2026第四季交件。
【書展優惠】
書展現場推出限定組合:BooksPad 7.8 吋+ 專屬保護殼 $7,699(原價 $8,379)。單機預購驚喜價$6,999(定價 $7,299)。現場預購成功可參與扭蛋活動,有機會獲得黃金片或禮物卡,並可兌換閱讀咖啡。書展期間博客來線上加碼:指定 BooksPad 套書優惠組最高現折$50。此外還有閱讀器+電子套書(《藥師少女的獨語》1-15或《特殊傳說》新版)+保護殼$8,499起。
Readmoo |Kobo |HyRead |Pubu |博客來 |想不同(熊老闆) |TCL |Booking遠流2.0閱讀計畫
【攤位特點】
集結 BOOX、SUPERNOTE、iFLYTEK、 momobook、BIGME、Meebook等6大品牌,以「閱讀即生活」為主題,規劃「3大情境體驗區」,協助讀者精準選機。
專注閱讀(Deep Read):6-7吋輕便機種(如BOOX、Meebook),主打開放式系統,可跨平台安裝 App。
手寫靈感(Inked Idea):7.8-10.3吋機種(如SUPERNOTE),提供卓越的書寫阻尼感。
高效辦公(Peak Work):10.3吋以上大尺寸(如iFLYTEK、BIGME),支援 PDF 閱覽與語音轉文字。
並攜手《葛瑞絲的小宇宙》推出限量贈禮:購7.8吋以上機型,贈IP聯名帆布袋;購7吋以下機型,贈獨家設計IP月計畫組;現場追蹤官方社群,贈熊老闆限量紅包袋。
多品牌回饋:購BOOX、Meebook、BIGME等品牌,滿5,000元,享Hami 購書金或月讀包二擇一(可累計);BOOX全機型(Palma2 除外)單機享95折;BOOX書展指定套組,享92折;指定週邊並有同步特惠。
書展期間Satechi、Twelve South等週邊亦同步展出,提供一站式升級數位閱讀生活的完整提案。
Readmoo |Kobo |HyRead |Pubu |博客來 |想不同(熊老闆) |TCL |Booking遠流2.0閱讀計畫
書展期間TCL Mobile Taiwan 推出 NXTPAPER未來紙系列平板(11吋或14吋),主打色彩鮮明、無反光與流暢的閱讀體驗,這類具備護眼顯示技術的平板被視為閱讀器替代品,適合閱讀漫畫、雜誌及開放式系統書城與長時閱讀。現場限定的優惠價可直接至TCL書展攤位體驗洽詢。
Readmoo |Kobo |HyRead |Pubu |博客來 |想不同(熊老闆) |TCL |Booking遠流2.0閱讀計畫
繼2025「遠流50週年集資計畫」大成功,今年遠流與HyRead、mooInk閱讀器合作,在wabay挖貝推出分享包 × 閱讀器 × 名家書櫃的「Booking遠流2.0閱讀計畫」。
內容包括限定優惠,單本不到百元;千本以上全齡書庫,180天彈性選書;打破平台限制,可自由切換Booking遠流、HyRead、讀墨App,一本書只須買一次;從輕量入門到好友分享,提供多款閱讀包選購等。
加購HyRead Gaze系列方案:
HyRead mini+ 6吋黑白機 $6,098:比一本書還輕的入門款,重量不到200g,內建32G容量,可擴充至1T。
HyRead Pro Note C 7.8吋彩機 $12,900:接近書的開本,E Ink Kaleido 3第三代彩色電子紙螢幕,內建64G容量,可擴充至1T。無論漫畫、手寫筆記、學習文件,都能享受紙本書等級的細膩畫質。
HyRead Pro Note7.8吋黑白機 $8,990:專為閱讀加筆記的的人設計,E Ink CartaTM 1300電子紙,1404×1872高解析度(300PPI),內建64G容量,可擴充至1T,並支援microSD(TF)記憶卡擴充,更大儲存空間滿足書籍、筆記、多媒體資料需求。
加購mooInk系列方案:
mooInk Nana 7吋彩機 $7,800:精巧輕薄入門機種,機身分別為迷月白及暗夜黑;多段色彩與燈光微調,舒適繽紛;配備最新一代色彩演算法,讓Kaleido 3彩色電子紙螢幕可呈現超越4096色的視覺體驗,不但線條銳利細緻,色彩增豔飽和,看漫畫也不模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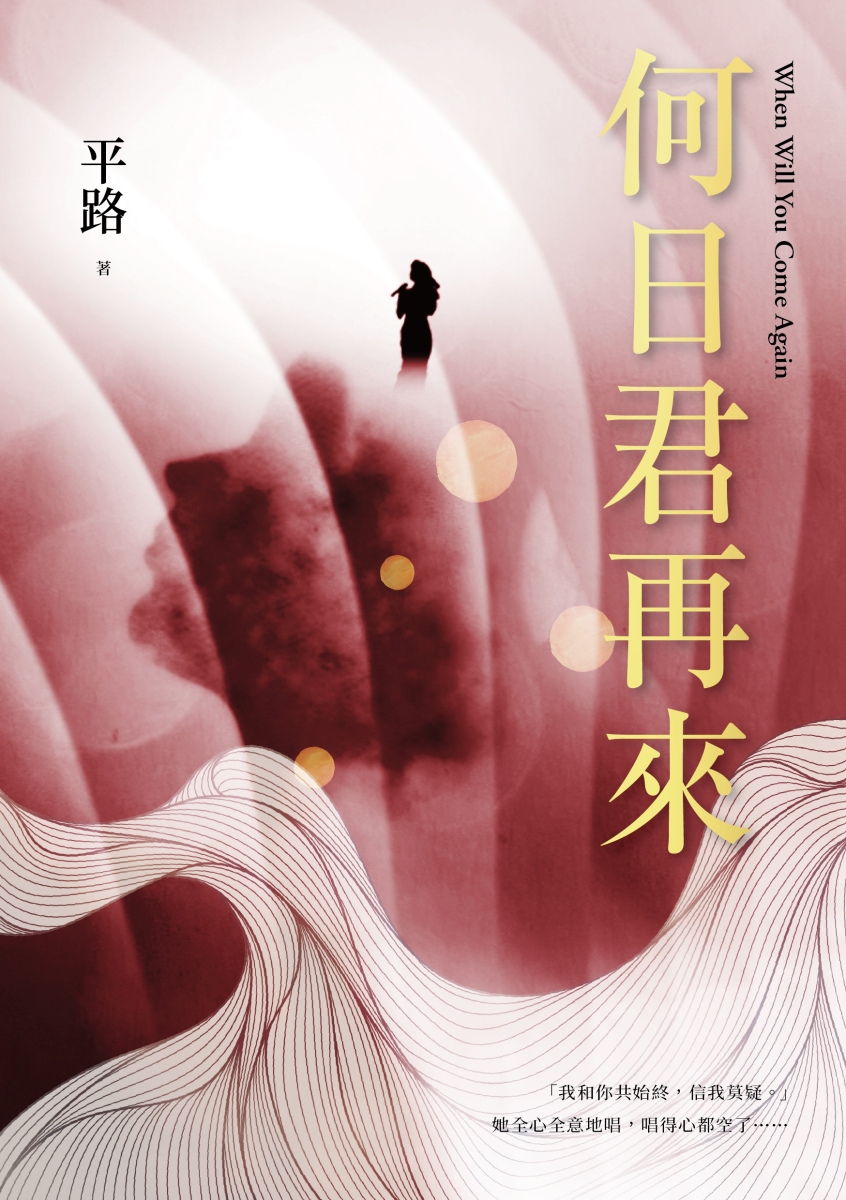 何日君再來
何日君再來
2026台北國際書展》閱讀器多如繁星,沒有最好,只有最得你眼那台
Readmoo|Kobo|HyRead|Pubu|博客來|想不同(熊老闆)|TCL|Booking遠流2.0閱讀計畫
➤Readmoo:歡迎加入馬拉松行列
【重點新機】
讀墨於書展首度亮相2026年新機,號稱「新世代國民機」的6吋mooInk Chill彩色電子書閱讀器,有迷月白與暗夜黑兩種顏色,搭配聯發科晶片,重量僅170克、6吋窄邊框手握輕盈。
規格全面升級更勝mooInk C,包括第三代彩色電子紙螢幕、4096色電容式觸控、150ppi彩色解析度、提升超過30%的色彩鮮豔度、降低60%藍光、7種色彩模式、3種滑桿調整等。
2026/2/3~2/8書展期間,單機預購NT$4,999(定價NT$7,299的68折),還有「一手包辦」套組預購價NT$5,599(定價NT$8,299的67折),內含mooInk Chill閱讀器、雙料透明保護殼、輕薄引磁片、雙磁圈手機支架。
mooInk Chill
【攤位特點】
讀墨mooInk Nana彩色電子書閱讀器上市週年,於書展現場展示mooInk全系列與Pencil Remote鉛筆翻頁器供讀者親手操作體驗,買mooInk Nana就送超可愛氣囊支架。攤位並設有「開運扭蛋機」,會員出示「讀墨看書」App 登入畫面,即可扭蛋一次,人人有獎。
優惠方面,讀墨推出mooInk系列全年最優方案(最低6折起),買就送讀墨禮券NT$500,2/3~2/10買機啟用新機再送購書金NT$2,000。mooInk Nana彩色電子書閱讀器期間限定只要NT$7,399;搭配《我培育的S級們》與眾多熱門新書套組,最低NT$7,999起。此外還有讀墨首度推出的療癒系品牌周邊限時折扣71折起。
除實體攤位,線上活動「馬上賓果!馬不停蹄馬拉松」也熱鬧起跑。完成特定閱讀任務可領取專屬紀念徽章及紅利回饋;完成連線可再獲加碼獎勵。活動期間每日登入網站並完成簡單答題,立即領取紅利點數或優惠折價券(3本75折券2 張)。揪友加入再抽7吋mooInk Nana彩色電子書閱讀器
【書展優惠】
mooInk Nana Color
mooInk Nana BW
mooInk Pro 2C
(含手寫筆)
mooInk Pro 2
(含手寫筆)
mooInk Pro 2C
(含手寫筆)
mooInk Pro 2
(含手寫筆)
※ 單位為新台幣(NT$)。2/3~2/10 期間啟用送購書金 NT$2,000,書展攤位另加贈讀墨禮券 NT$500。
Readmoo|Kobo|HyRead|Pubu|博客來|想不同(熊老闆)|TCL|Booking遠流2.0閱讀計畫
➤Kobo:樂天女孩陪你看
書展現場集結樂天Kobo全系列電子閱讀器,讓讀者親身體驗不同機型的閱讀手感與功能特色。為回饋讀者10年來的支持,樂天Kobo祭出一年僅此一次的書展限定回饋,推出全年最超值的閱讀器優惠價格,並加贈購書金!而知名韓國小說家千明官與人氣創作者HOOK、鷹式一家Hiram等,更將帶來多達14場主題豐富的系列講座。
【攤位特點】
慶祝在台深耕邁入第10年,Kobo於本屆書展打造規模最大的互動展區,並與APUJAN聯名10周年限定商品,包括有星際收納包、宇宙碎片3件組、全球限量5套的10週年服裝。此外還有好玩的籤詩互動牆、拍照打卡免費拍貼活動(可任選一組10週年紀念框),邀讀者一同參與盛會。
閱讀器搭配購書金最高68折起,最多可省$1,680,還有購書金回饋,最高贈送$1,600。消費並贈每日限量好禮,包括有Readimal品牌徽章盲盒或樂天女孩2026桌曆,送完為止。
線上活動方面,書展期間全站75折,單筆滿$2,026再抽2026點樂天點數。樂天市場、PChome24h購物上的「樂天Kobo電子書」,也皆享同步優惠。
【書展優惠】
機型/螢幕尺寸/原價/書展現場優惠價
Kobo Elipsa 2E(32GB)/10.3吋/$12,990/$11,310(含觸控筆)
Kobo Libra Colour(32GB)/7吋/$7,699/$6,610
Kobo Clara Colour(16GB)/6吋/$5,599/$4,910
Kobo Clara BW(16GB)/6吋/$4,899/$4,310
Readmoo|Kobo|HyRead|Pubu|博客來|想不同(熊老闆)|TCL|Booking遠流2.0閱讀計畫
➤HyRead:幾米聯名在這裡
【攤位特點】
書展現場優惠方案包括:機殼組特價;滿萬元再享「手寫膜」或「幾米側翻殼」好禮二選一;周邊配件79折優惠,最低47元起;購買閱讀器並享加購「嗨讀訂閱服務」專屬優惠,再送實體商品百元折價券;完成登錄再抽眠豆腐、浩肯包、充電器等,總計高達45個中獎名額。
【主打機種】
主打與幾米品牌獨家聯名推出的彩色閱讀器Gaze Mini CC,號稱「會說故事的時光機」。採用最新6吋電子紙,色彩飽和度提升30%,並內建幾米電子萬年曆,結合一天一張的幾米圖文、24節氣、特殊節日,一鍵整合Google行事曆。
HyRead Gaze Mini CC
【書展優惠】
HyRead Gaze全系列均內建圖書館免費借書功能,書展限時優惠如下(機型方案/定價/現場活動價):
Readmoo|Kobo|HyRead|Pubu|博客來|想不同(熊老闆)|TCL|Booking遠流2.0閱讀計畫
➤Pubu:手機型放口袋好方便
【攤位特點】
書展推出限定優惠:舊機換購Pubook閱讀器,現場換購立即折1,000元,品牌機況不設限,舊平板、閱讀器變身新Pubook(換購限Pubook 2 Pro 10.3"、Pubook Mobile 6.13"、Pubook Mobile BW 6.13")。現場購買第二台Pubook閱讀器系列,再省500元。
【主打機種】
Pubook Mobile 6.13 彩色/黑白閱讀器:為台灣第一支手機型開放式電子閱讀器,Pubook Mobile BW 黑白墨水屏同步登場。專為行動閱讀打造,可放進口袋,隨身好攜帶;單手滑讀,通勤也能輕鬆閱讀;跨不同平台可自由選書;漫畫、圖文書,彩色還原;開放系統,能安裝自己喜歡的 App,除了閱讀,也能延伸更多應用可能。
$9,490 搭配「飽讀Lifetime」,贈螢幕保護貼、清水殼、NT$1,000購書禮劵。$8,490 贈NT$1,000購書禮劵。
Pubook Mobile 6.13
Pubook 2 Pro 10.3" 彩色閱讀器(含Pubook翻頁器手寫筆):獨家快速刷新技術,有效消除殘影;全新雙實體按鍵,可自訂螢幕刷新或其它功能,閱讀時音量鍵可做為翻頁鍵使用,操作直覺更升級;搭載Kaleido 3彩色電子紙技術,細緻顯色,大螢幕也護眼;支援手寫筆記,讀寫同步,內建Android 14系統,自由安裝更多App,自訂你的生產力工具。$19,990 搭配「飽讀Lifetime」,贈NT$2,000購書禮劵。
Pubook 2 Pro 10.3
【特色周邊】
Pubook翻頁器手寫筆(含傳輸線、筆芯夾、備用筆芯3支):閱讀器專用全新工具,MIT台灣第一支閱讀器專用翻頁器手寫筆,一筆翻頁、隨手即寫;可適用於市面上多種品牌閱讀器,翻頁 × 手寫一筆搞定。$1,990
Readmoo|Kobo|HyRead|Pubu|博客來|想不同(熊老闆)|TCL|Booking遠流2.0閱讀計畫
➤博客來:超優惠兒童機
【主打機種】
博客來2026年全台首發預購限量300組的BookPad Kids 10.3吋鈦空銀兒童學練機。定價$20,800,超級早鳥$16,999,直降$3,801,再送總值超過5,000元6大豪禮,預計2026第四季交件。
【書展優惠】
書展現場推出限定組合:BooksPad 7.8 吋+ 專屬保護殼 $7,699(原價 $8,379)。單機預購驚喜價$6,999(定價 $7,299)。現場預購成功可參與扭蛋活動,有機會獲得黃金片或禮物卡,並可兌換閱讀咖啡。書展期間博客來線上加碼:指定 BooksPad 套書優惠組最高現折$50。此外還有閱讀器+電子套書(《藥師少女的獨語》1-15或《特殊傳說》新版)+保護殼$8,499起。
Readmoo|Kobo|HyRead|Pubu|博客來|想不同(熊老闆)|TCL|Booking遠流2.0閱讀計畫
➤想不同(熊老闆):6大品牌滿滿黑科技
【攤位特點】
集結 BOOX、SUPERNOTE、iFLYTEK、 momobook、BIGME、Meebook等6大品牌,以「閱讀即生活」為主題,規劃「3大情境體驗區」,協助讀者精準選機。
並攜手《葛瑞絲的小宇宙》推出限量贈禮:購7.8吋以上機型,贈IP聯名帆布袋;購7吋以下機型,贈獨家設計IP月計畫組;現場追蹤官方社群,贈熊老闆限量紅包袋。
多品牌回饋:購BOOX、Meebook、BIGME等品牌,滿5,000元,享Hami 購書金或月讀包二擇一(可累計);BOOX全機型(Palma2 除外)單機享95折;BOOX書展指定套組,享92折;指定週邊並有同步特惠。
書展期間Satechi、Twelve South等週邊亦同步展出,提供一站式升級數位閱讀生活的完整提案。
Readmoo|Kobo|HyRead|Pubu|博客來|想不同(熊老闆)|TCL|Booking遠流2.0閱讀計畫
➤TCL
書展期間TCL Mobile Taiwan 推出 NXTPAPER未來紙系列平板(11吋或14吋),主打色彩鮮明、無反光與流暢的閱讀體驗,這類具備護眼顯示技術的平板被視為閱讀器替代品,適合閱讀漫畫、雜誌及開放式系統書城與長時閱讀。現場限定的優惠價可直接至TCL書展攤位體驗洽詢。
Readmoo|Kobo|HyRead|Pubu|博客來|想不同(熊老闆)|TCL|Booking遠流2.0閱讀計畫
➤ Booking遠流2.0閱讀計畫
繼2025「遠流50週年集資計畫」大成功,今年遠流與HyRead、mooInk閱讀器合作,在wabay挖貝推出分享包 × 閱讀器 × 名家書櫃的「Booking遠流2.0閱讀計畫」。
內容包括限定優惠,單本不到百元;千本以上全齡書庫,180天彈性選書;打破平台限制,可自由切換Booking遠流、HyRead、讀墨App,一本書只須買一次;從輕量入門到好友分享,提供多款閱讀包選購等。
加購HyRead Gaze系列方案:
加購mooInk系列方案:
閱讀通信 vol.370》當我在書裡讀到你的時候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