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自己的書自己出?一想到庫存我險險焚書坑掉自己:潘柏霖、吳曉樂自費出版講座側記
➤自費出版前傳:國中的潘柏霖在 CWT賣同人誌
講座一開頭,潘柏霖先以自己為例,回顧起初不甚順利後續另闢蹊徑的詩集出版歷程。潘柏霖創作至今,13本著作中就有高達8本詩集都是透過自費出版面市。寫作之外,編輯、設計、印刷都不假手他人。這並非潘柏霖特立獨行,一切要回到他想推出首部詩集《1993》的2015年。
當時,詩集在台灣出版市場並不風行,在潘柏霖投石問路、洽談出書的過程裡,出版社不是杳無回音,就是語帶迂迴地暗示「出版詩集不會賣」。種種考量後,潘柏霖選擇自力救濟:「一開始我其實沒有覺得自費跟出版社有那麼大的區別。我就想說,那我自己做。」
不過,其實潘柏霖早在國中就體驗過自費印製文本並販賣的流程了——那是他與同好一起創作「同人誌」,拿到CWT 自產自銷的實戰經驗。「從國中開始在做CWT,我們會自己去印刷同人誌,所以在我的腦袋裡,我沒有覺得自己印書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潘柏霖表示:「CWT的經驗是個很完整的流程。」他認為,同人誌作者很習慣將自身創造的內容,變成可以具體販售的產品,這對於成為創作者以及自費出版都是很有效的訓練。
接著,他提到自售同人誌對心理的正向影響:「如果寫的CP沒那麼紅 ,大家拿書翻一下就走,可能很少人買,就會經驗到沒有人理你的狀態。從小經驗『沒有被選到』的感覺,後來心理素質會比較好,出書就比較不會擔心,因為你已經體會過了。」
潘柏霖也透露,詩人夏宇和宋尚緯自行出版詩集的成功前例,也在他選擇走向自費出版的康莊大道(?)上幫忙推了一把。

➤自費出版過程,需要編輯協力嗎?
要不要找編輯來加入,往往是許多人面對自費出版的首要考量。2014年透過出版社發行《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此後創作主題百變、至今筆耕不輟的作家吳曉樂強調,出書過程最不可省略的關鍵職務就是「編輯」。
目前以長篇小說為主要創作體裁的吳曉樂,自我剖析:「創作容易陷入一種自我完整的過程,需要有人從旁提醒,以免自己看的時候覺得很順,外人來看才發現:『同一個角色為什麼這邊姓陳、這邊姓黃、這邊又姓陳?』」她既誠實又不免有點誇張地幽默形容:「如果沒有編輯,可能我寫的一本小說裡面會有50個bug。」現場氛圍頓時輕鬆起來。
那麼,第一次出書就以詩集出擊的潘柏霖呢?
他表示,依據後來與出版社合作的經驗,由於詩的文體與小說大相徑庭,他遇過的出版編輯不太介入或更動詩集內容,最重要的功用是提供不同於創作者的切入觀點:「編輯可以給出不是你自己的視角。如果大家希望文本更客觀一點,即使是詩集,另外找編輯幫忙也會比較好一點。」他認為,創作者如果會「困在自己的視角」,無法脫離內容本身思考,就適合與編輯溝通討論。
不過,潘柏霖自費出版時,並沒有另外找編輯。為什麼呢?他說:「因為我比較不習慣與人合作、不想要給大家管。」直白程度一百分。
➤沒想過的自費出版技能:找通路、看紙價期貨、和2000本庫存一起睡ΣΣ(*゚д゚ノ)ノ
創作者在自費與出版社之間抉擇時,多半會考量通路經銷的問題。若交由出版社發書,好處是有經年合作的既定經銷商,如果選擇自費出版,這項重任就要自行承擔。
潘柏霖分享,前期他自費出版的書籍並沒有全面經銷,僅有自行販售及獨立書店寄售兩種通路。經過幾年作品與討論聲量的累積,2018年才與博客來、誠品等通路聯繫合作。他認為,通路要不要採購自己的書、採購多少量,並非一人之力能影響,出版社也不一定能確保通路採購的判斷。
創作者能夠主導與掌握的,主要還是網路社群的個人經營。
不比從前社群紅利較高的時候,潘柏霖表示,現在新人要透過網路社群快速凝聚大量的鐵粉,難度更高了。不過通路在考量選品時,也會將社群聲量納入參考指標。總之,資源與時間有限的創作者,若想解決通路問題,除了自己來,也可考慮找經銷商合作。

吳曉樂笑著透露,潘柏霖自費出版詩集也就罷了,居然連紙都自掏腰包買下。潘柏霖平時會看紙的期貨價格,為了買紙,甚至會花到6位數的金額,號稱「買紙大掌櫃」(出場音樂請下)。潘柏霖解釋,買紙其實並不算在一般自費出版的流程中,但由於自己對書籍選紙有堅持,之前遭逢疫情時,為了確保印書時紙量足夠,於是提前跟紙廠訂購。不過,他建議一般自費出版者可將紙的選項放寬。
接著,吳曉樂提出自費出版者最困擾的問題——「庫存」。庫存涉及空間租金、倉儲坪效與管理人力等綜合費用。當倉儲費用高過書籍販售的獲利,出版社在兩難下只得將書籍銷毀,以避免付出高額費用。自費出版創作者,該如何存放還沒賣出的書籍庫存?該預留多少倉儲費用?也都是必須先思考的。
潘柏霖就有和2000本作品睡在一起的經歷:「每天就是看這樣50箱,想著要快點把它處理完。所以自費出版時,我會自己先開預購,在預購開始、結束,到出貨之前,都先將庫存放在經銷商那邊。」他提到,當時書籍還沒轉換成現金,即使庫存空間有著落,仍然是相當大的精神壓力。
「每次結算會有表單顯示『剩餘庫存』,我看到剩餘庫存就會覺得煩。因為是自己出錢,等於是自己花錢買了這麼多東西,然後還賣不出去時的那種心情。」就像那句老話:有錢並非萬能,但沒錢就萬萬不能。

➤關於版稅計算,及自費出版究竟該準備多少錢?
選擇自費出版,代表沒有出版社提供的資源可運用。大家想必很好奇:從零開始自費出版一本書,究竟該準備多少資金?版稅又如何計算?吳曉樂先現場示範,和出版社合作的話版稅會如何計算。
她從首刷印量開始說起:「目前台灣首刷約1500到2000本,所以如果你看到一本書是再刷的話,就表示它應該已經賣到2000本以上了。但再刷的印量比較難判斷,有的是500本,也有1000本的。如果是500本的話,刷次就會跳得很快,假設已經賣到5000本的話,可能就已經跳到7刷了。」
接著進入定價與基礎版稅10%的乘法計算:「假設一本書定價是360元,以基礎版稅10%計算,作者每賣一本書拿到36塊。如果這位作者說他再刷了,以首刷2000本去算的話,就表示他的收入可能已經超過7萬塊了。」雖然版稅報酬較少,但吳曉樂認為和出版社合作是比較放鬆的。
潘柏霖表示,自費出版作者通常可以拿到30%的版稅,然而必須先投入資金,加上個體戶印書,印越少平均單價越高,因此無法像出版社,即使單次只印500、1000或2000本,賣完再追加也可以被接受。自費出版者印前就需要評估一次性的總印書量。
如果以印刷量500本、單本印刷費130元來粗估一本書的印刷費用,總共就需要6萬5000元的印刷費。若將整個自費出版流程納入,並以印刷總量1萬本來估算的話,一開始創作者就要準備7位數的成本費用了。
➤所有出版形式都是一體兩面
來到QA環節,有讀者詢問台上的兩位創作者,是否曾考慮透過募資的方式出書?潘柏霖認為,相較之下募資有其明確、特定的作用,影響範圍甚廣:「(募資)它會影響我們怎麼賣書、(讀者)怎麼買書,還有(販售)書的意義是什麼、在哪個地方賣。」如何進行募資這樣的商業模式,才能在自費出版中達到最適切的效果?潘柏霖自認還在摸索。吳曉樂也在一旁補充:比起其他方式,募資更帶有前期宣傳行銷、打響名號的功能。
許多創作者對於自費出版懷有浪漫想像,但過程並不容易。預備費用、可能面臨的庫存壓力都是創作者必須先自行估量的。吳曉樂提醒:「自費出版你可以握有主導權,可是要負擔的心理壓力其實也是很大的。自費出版與找出版社出書,兩者的優缺點就像一體兩面,重要的是創作者在意的、能夠承擔的是什麼。」●
|
「台灣出版民間真相與正解促進會」由作家吳曉樂、獨立書店現流冊店 hiān-lâu tsheh-tiàm、出版人A編工事中於2023年4月共同成立,每月邀請出版人、作家、譯者、通路等出版產業從業人員擔任對談嘉賓,舉辦實體講座,致力於推動出版真相普及,傳遞出版產業內外的正解資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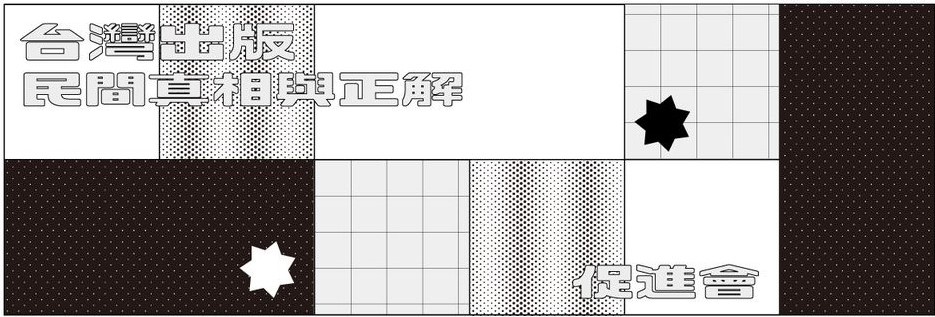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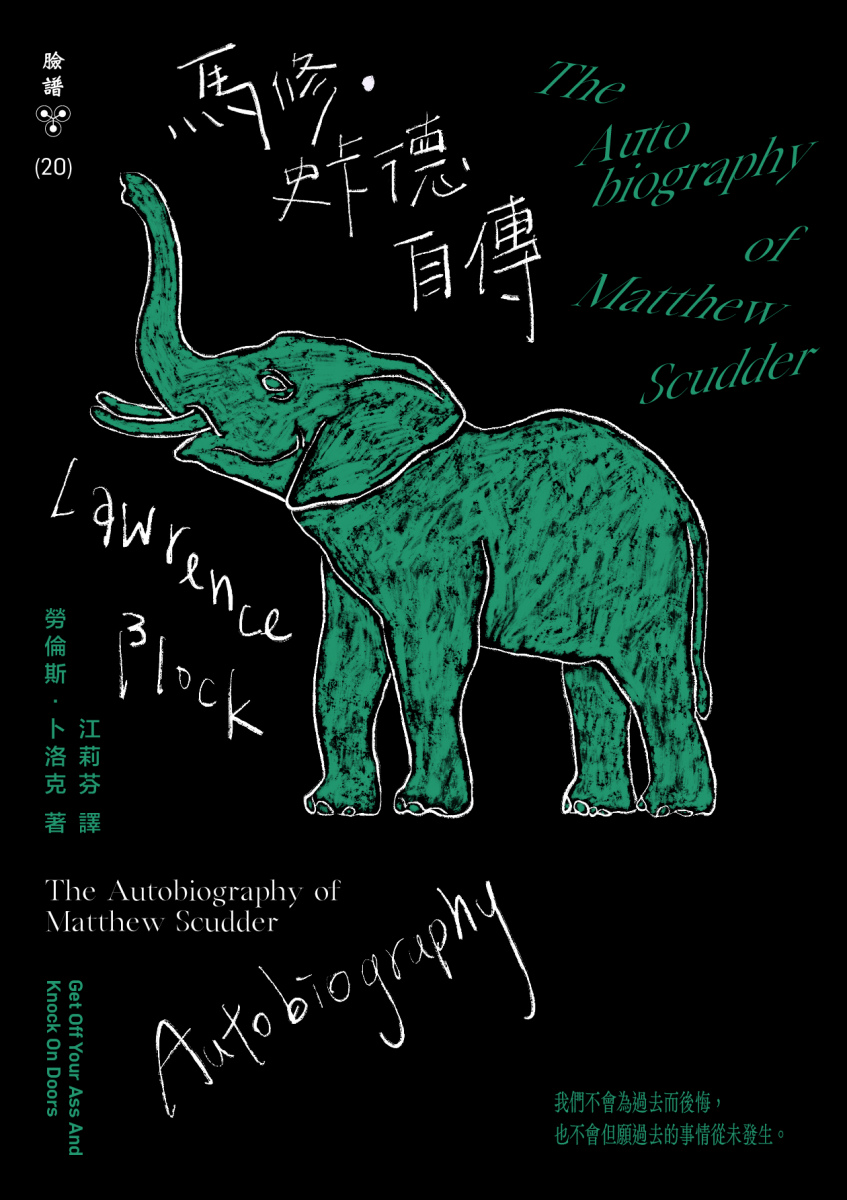
童書評》古典、創新、好聽、好看的圖畫故事書:《小木頭機器人和圓木公主》
標題有點長,不過確實是我在翻譯《小木頭機器人和圓木公主》的過程中不斷浮現出的句子。而且我認為這部作品為「圖畫故事如何兼具文學、藝術和娛樂」做了巧妙的示範,值得有心的讀者特別留意。
這本書的文圖作者湯姆.高爾德(Tom Gauld)是一位喜歡跟孩子一起玩的父親,他常常為兩個女兒編睡前故事。故事的靈感來源包括﹕他自己小時候很喜歡的故事書、他知道女兒很喜歡的故事書,以及他身為成人很喜歡的故事書。
他的目標是,編出來的故事要有他自己「有點奇特古怪」的風格感覺、同時又要有經典睡前故事的樣子。他很享受講這樣的睡前故事,以及在過程中跟孩子互動的樂趣。不過,我認為他嘗試創作兒童圖畫故事書,並不僅是因為有講故事的經驗和樂趣,而是因為他的專業和職業:他是出版界知名的漫畫家和插畫家。
高爾德在蘇格蘭鄉間長大,從小喜歡繪畫,立志從事與繪畫相關的創意工作。他先後在愛丁堡藝術學院、皇家藝術學院接受專業課程和訓練。他出版過漫畫書和圖像小說,受到專業獎項和商業市場的肯定。他現在每周為英國《衛報》畫文學漫畫,為《新科學人》畫科學漫畫,也經常為《紐約客》畫封面。
簡言之,他是被嚴苛、競爭激烈的國際出版市場「認證」過的插畫家。而且長期為報紙雜誌供稿,使他鍛鍊出既能表現獨特個人風格,又擅與讀者溝通的能力。他慣於用文字和圖像共同敘事,並能以最簡約的方式使讀者理解他想傳遞的訊息,因此他覺得自己或許能創作出理想的兒童圖畫書。他對童書和兒童讀者並不陌生,知道若要為兒童創作,必須調整原本的觀念或作法。不過他也堅持絕對不能失去原本對藝術創作的喜好和創意想像。
高爾德在這本圖畫書裡呈現的色調、造型與圖像風格,跟他的成人漫畫作品很接近。讀者可以一眼認出他偏好「冷靜的喜劇、表面平淡的對話、豐富的幕後(背景)細節、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的特色。
高爾德於雜誌《Saturday》刊登的漫畫專欄,圖像風格冷靜且帶幽默。
不同的是,他知道兒童閱讀圖畫書的方式,常是藉由成人的朗讀、講述,或小孩自己大聲唸,跟成人閱讀漫畫和小說的方式很不一樣。而且小孩會要求重複講讀,必須做到讓他們聽好幾遍也不厭倦。因此,除了視覺藝術的考量,還應重視唸給孩子聽的時候效果如何。
好聽的故事必須流暢易懂,文字乾淨清晰並斟酌語音節奏意象,講究表述意義時的邏輯和層次,製造適當的張力和懸疑,使讀者聽得明白並產生追隨角色和情節的好奇心。
其次,小孩對「臉」感興趣。高爾德的漫畫手法簡化到近乎抽象,人物無五官表情。但在這本圖畫書裡,角色都有臉和表情,讓小孩更易產生連結,也使故事更有情緒和情感氛圍。在他老練的工夫和縝密的考量下,這本書果然成為好聽又好看的作品,就算是沒有講故事經驗的成人讀給小孩聽,都不會失敗。
高爾德讀(唸)遍古老童話,認為這些經典的故事結構清楚完整,並以深刻的人性層面影響著不同的世代,方能在人類文化裡歷久不衰。他也喜歡許多現代圖畫書,最喜歡的例子之一是湯米.溫格爾(Tomi Ungerer)的《三個強盜》(讀者可在本書中發現向其致敬的圖像),既古怪又溫暖。他也很欣賞安野光雅的《旅之繪本》系列,小人物漫遊在美麗、靜謐的歐洲風景中,散發平和、詩意的感覺。
顯然許多精彩的童書經過高爾德的消化和吸收後滋養了他,創作出具有他個人風格和獨特魅力的作品。這本書能令現代讀者耳目一新,絕對跟圖像的藝術風格有關。他運用筆繪線條和電腦上色,讓畫面具有類似版畫的雅緻,充滿木質紋理的氣息,他又以現代漫畫的構圖方式靈活設計生動的畫面,達到古典與現代交融的效果。
書裡有許多古典童話的元素,國王、王后、公主、王子和在森林裡冒險。不過,讀者在熟悉易懂的故事架構下,會發現許多新奇和驚喜。意即,它有傳統公式的優點,卻不老套或沉悶。
國王和王后表現出比傳統更多的個性內涵,讓小孩深切感受到他們就是兩個很愛孩子的家長。王后的膚色並非傳統歐洲白人,反映出當代英國(及許多地方)家庭的真實景況。王子和公主不是情人而是兄妹,他們互相幫助和合作,發揮美好的人性品格與生活能力,才能共度難關。他們的困境並不來自壞人、邪惡的巫婆或怪物之類的角色。事實上,這本書裡沒有壞人。
人生的真相是,就算沒有壞人,我們的日子也會充滿磨難和挑戰。人本質上的有限和軟弱,讓生活總有意料不到的災禍和驚喜。王子因為馬戲團難得造訪而忘記叫醒妹妹,豈不是人(尤其是小孩)之常情,誰能怪他呢?他和女僕錯身而過,似乎暗藏「命運」的微妙嘲弄,令人有「如果當時怎樣怎樣就好了」的感受。女僕做的事不過是例行職責,誰知道正確的行為竟會產生可怕的後果?王子的天外橫禍對小妖精而言卻是天降好運,果然這個人的地獄可能是那個人的天堂啊!
故事情節很曲折離奇,卻都合情合理,角色塑造跟情節鋪陳息息相關,因此有說服力和吸引力。王子對甲蟲的善待,原來是連當事者都想像不到的伏筆。公主在森林裡即將功虧一簣時,敘事的軸線隨著角色的轉變而暫時休止,鏡頭轉到王宮,再跟著國王的視線轉回森林,情節有了奇妙的進展,再延續公主與王子的敘事主軸……
書中許多這樣巧妙設計的懸疑、轉折和驚奇,帶給讀者很大的滿足感和娛樂效果。公主和王子分別來自魔法和發明,代表古典和現代互相輝映。在跨頁的畫面上,發明家和女巫左右對照,實有許多相似之處。
高爾德講故事的手法很高明,我想因為他讀懂經典故事的核心概念,也就是人性;就童書而言,則是小孩基本的情感需要。
最神奇的魔法是愛。這本書是關於父母與小孩的親子感情,兄妹的手足感情,連甲蟲都是以家庭為單位。森林裡動物們接力友善幫助,也彰顯美好的情感力量才能激勵我們,勇敢的面對人生的挑戰。成功的角色不是孤獨的英雄,而是能為人著想、會互相幫助和合作的人。所以這本書有很高的普遍性(有些圖畫書會挑讀者的),適合每一個愛聽愛看故事的小孩。
英文有句俚語Sleep like a log,字面直譯是「睡得像一塊木頭」,就是睡得很熟的意思。高爾德每天晚上為女兒講完故事後,就用這句話祝她們睡得香甜。孩子們覺得這句話很好玩,常拿來開玩笑,玩著、笑著,變出了這個她們很喜歡的故事。這本古典、創新、好聽、好看的圖畫故事書,源自一位藝術家父親對孩子的愛與祝福,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分享其中的喜悅。●
The Little Wooden Robot and the Log Princess
作者:湯姆.高爾(Tom Gauld)
譯者:柯倩華
出版:小麥田出版
定價:42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湯姆.高爾(Tom Gauld)
1976年出生於蘇格蘭的艾伯丁,畢業於英國的皇家藝術學院,曾獲艾斯納獎,為英國的《衛報》繪製文學漫畫,為《新科學家》雜誌繪製科學漫畫。圖像小說作品有《哥利亞》 (Goliath)、《月亮警察》 (Mooncop),曾8次受邀為《紐約客》雜誌繪製封面。《小木頭機器人和圓木公主》是他第一本為兒童創作的圖畫書。在蘇格蘭鄉間長大的他,現與妻子及兩個女兒住在英國倫敦。
閱讀通信 vol.368》台北國際書展,來襲!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