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短評》#290 哀而不傷的極品好書懶人包
●少年與時間的洞穴
黃暐婷著,時報出版,420元
推薦原因: 文 樂
「時間」的概念是一種現代的發明,亦是抽象的存在,但透過現代鐘錶日曆等媒介具象化,應監獄、工廠、學校等實體制度而更發細緻。本書透過小說技藝,建構了一個成熟完整的世界觀,重探上述「時間」的身世與來世,以及透過時間引發的政治、文化、愛、人性等問題。小說更精心挪用了時間的斷裂與不連續——時差,帶出不同故事線的交錯與交集、引人入勝的迷霧。【內容簡介➤】
●山地話
馬翊航著,九歌出版,320元
推薦原因: 文 樂
馬翊航對文學語言的掌握、話語權力的探究深刻入骨,如千面鑽石的切割器。原住民的族群、同志身分、情慾探索……許多疊加起來較為沉重的議題,本書用更開闊的角度、輕巧甚至帶有幽默感的方式與讀者對話。在歡快的氣氛中,同時存在一個深沉的低音,透露著生命的沉重與無奈,層次豐富,十分動人。
馬翊航的散文接近他如何處理「作為血緣還是經驗」的原住民身分,反覆在成長、移動、探索與認同中撫摸時光、流出源源不絕的後山情思湧泉。【內容簡介➤】
●疫病與社會的十個關鍵詞
劉紹華著 ,春山出版,400元
推薦原因: 批 思 議 益
當疫情發展至此,已不只是某些人生病了那麼簡單。長期投入愛滋、麻瘋醫療人類學研究的作者挑選了10個關鍵詞,寫成10篇短文;以這10個大眾議論疫情時最易觸及的詞彙為媒介,重返歷史,提取概念,指出盲點,使當局者如你我得以擁有較寬的視野,從具時間深度的脈絡,理解疫病與人世糾葛而生的渾沌萬象。當病毒就在身邊,疫情成為日常,如何在病毒環伺中不失人性,使疫情不造成二次傷害,是本書最大的關心。【內容簡介➤】
●著陸何處
全球化、不平等與生態鉅變下,政治該何去何從?
Où atterrir? Comment s’orienter en politique
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著,陳榮泰、伍啟鴻譯,群學出版,320元
推薦原因: 批 思 議 獨
由臺北市立美術館主辦的「2020台北雙年展」主題為「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You and I Don’t Live on the Same Planet),策展人即是本書作者拉圖。他提出假設:全世界的人們不再對「生活在地球上的意義」有共識,但共識破局後並非事情就結束了,下一步要問的就是:面對全球經濟與生態危機,歷史的梳理與世界佈局將「著陸何處」。本書展現了拉圖長期對於現代性、政治哲學的思考與批判,回應的是當代的生態問題、民粹主義浪潮、移民危機等重大議題,為上述各個全球危機,指向世界「離地」之後該如何著陸。【內容簡介➤】
●牆國誌
中國如何控制網路
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How to Build and Control an Alternative Version of the Internet
詹姆斯.格里菲斯(James Griffiths)著,李屹譯,游擊文化,480元
推薦原因: 議 益
細論防火長城的來龍去脈,一窺中國網軍的大小動作,反中意味濃厚,但反得有理。槍桿子出政權,鍵盤也能敲出極權,這本高科技版的《1984》此時上市,尤具戰略價值。【內容簡介➤】
●SPQR
璀璨帝國,盛世羅馬,元老院與人民的榮光古史
SPQR: A History of Ancient Rome
瑪莉.畢爾德(Mary Beard)著,余淑慧、余淑娟譯,聯經出版,620元
推薦原因: 知 樂
現今世界文明的樣貌無法迴避古羅馬的遺產。作者在原來對羅馬的理解基礎之上,添入近年問世的考古、文獻、物質材料,並且以「公民」為概念,重新詮釋羅馬帝國的發展指向,呈現了帝國之閎壯,也指出歷史所遺留的問題。本書雖然卷帙浩繁,但筆調深入淺出,視野鼎新,為大眾煉鑄出的羅馬史,具有21世紀的意義。【內容簡介➤】
●科學怪人
為科學家、工程師及創作者設計,上百條專業評註、七篇跨學科論文,重探科幻小說原點
Frankenstein: Annotated for Scientists, Engineers, and Creators of All Kinds
瑪麗.雪萊(Mary Shelley)著,大衛.H.加斯(David H. Guston)、頓艾德.芬(Ed Finn)、傑森.史考特.羅伯特(Jason Scott Robert)編,黃佳瑜譯,麥田出版,499元
推薦原因: 知 樂 獨
由一群專業工程師、數理學家評註一本1818年出版的小說,不僅跨領域,而且非常跨時代。這裡的「跨」是連接而非分隔,200年前的科幻小說可以為當代科技想像帶來新的刺激,虛構世界與科學實證間的鴻溝亦被填起,本書不僅是一起重要的文學事件,也是人類世界對於未來想像的百年延續。
即使沒有閱讀《科學怪人》原著,應也對故事略有所聞,甚至在腦中幻想「怪人」的形象。本書將原著加工烹調成一道帶有傳統基底的創意菜色,一是註解者的導言與註解,二是作者的原著導言和生平年表,三是研究論文選粹。尤其對於故事中「罪」、「昭昭天命」、「同伴情誼」等說法的註解,深入文本創生當時的歷史脈絡、概念意義,剥皮剔骨地將故事的筋絡血脈曝露於我們眼前。讀者既能進入200年前故事誕生的情境,也能知悉隱藏於故事中的時代命題。【內容簡介➤】
●當政客都在說故事
破解政治敘事如何收攏民心、騙取選票!
The Art of Political Storytelling: Why Stories Win Votes in Post-truth Politics
菲利普.塞吉安特(Philip Seargeant)著,何玉方譯,商業週刊出版,400元
推薦原因: 批 思 議 益
當代政治活動是如何藉著各種「說故事」的手法攏絡民心?本書除了分析國際案例的敍事模式,更強調所謂「後真相」的概念,即真相不只是真假兩分,諸多操作可使單純的真實複雜化,虛虛實實,似是而非,卻又難以直斷其誤。作者析離出說故事的諸樣元素,從語辭選用、塑造過程到呈現樣式,而其討論過程也成為對於「真相」的辨證與闡釋,既可在「說故事」的故事中對政治文化有所了解,也有助於思索何謂事實(fact),何為真相(truth)。【內容簡介➤】
●房東阿嬤與我
大家さんと僕
矢部太郎著 ,緋華璃譯,新經典文化,300元
推薦原因: 樂
優雅的昭和阿嬤和二線搞笑藝人的青銀共居日常。天差地遠,宛如生活在平行宇宙的兩人,意外共譜了一首變奏曲。世代差異引起的笑點,人生閱歷累積的厚度,透過簡練的線條畫龍點睛,既支撐了在藝能界孤身奮鬥的作者,也讓忙忙碌碌的我們不知不覺暫時放下紛擾煩憂,會心一笑。【內容簡介➤】
●身為在台灣的新二代,我很害怕
劉育瑄著,創意市集,350元
推薦原因: 議
時光匆匆,新住民二代長大了,我們可能已經在很多場合相遇、共事。作者寫出自己在多重文化中跌跌撞撞的成長歷程,申訴新二代身在家鄉為異客的遭遇、感受、疑惑以及期待。所謂的新二代,不再是文化上的他者,而是一起生活在的同胞。【內容簡介➤】
知識性.設計感.批判性.思想性.議題性.實用性.文學性. 閱讀樂趣.獨特性.公益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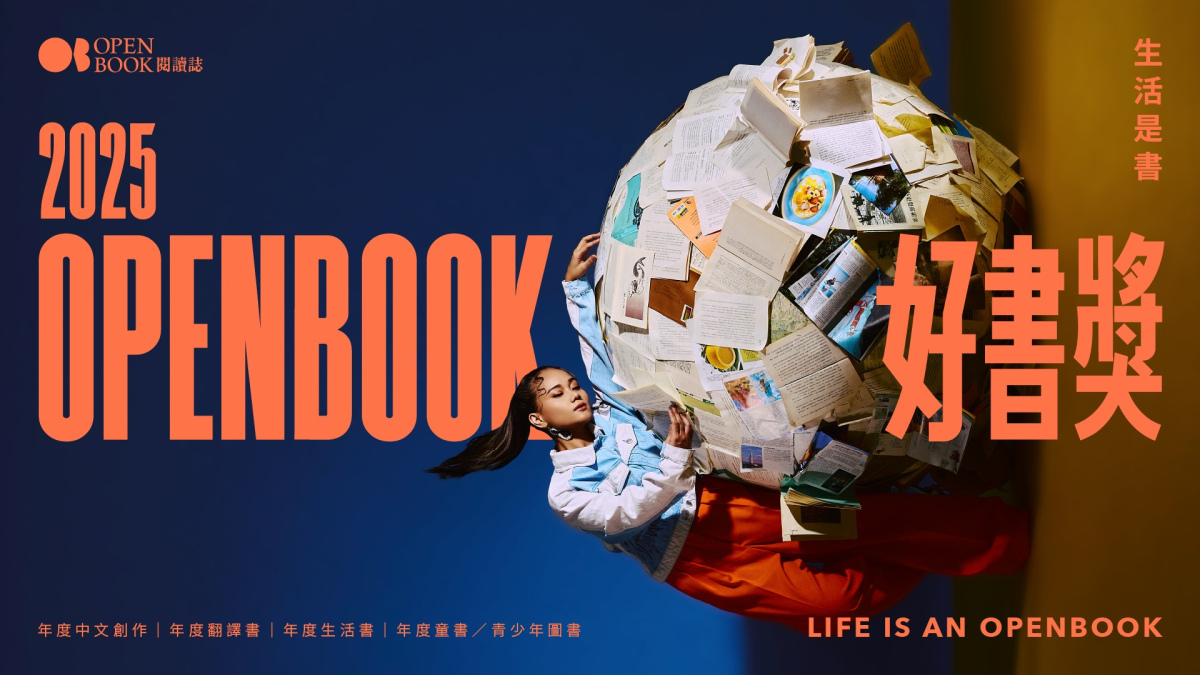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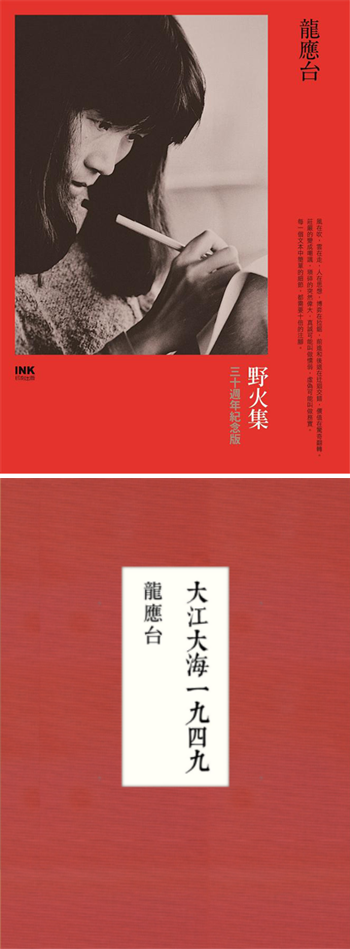 對於這樣直接的提問,龍應台沒有迴避地直言,寫《野火集》的時候是1985年,那時候需要天真,需要勇敢,而且生氣是可以立刻帶來改變的。但今天台灣所面對的敵人,已經不是單一的任何一個政府,現在的敵人藏在假裝公平的媒體、假裝正義的司法、假裝一切為人民的政府裡面。敵人就像是在人們的血液裡,而非某個外在的事物。這也是為什麼,人們更需要老師們為這片土地,教出更有思辨能力的下一代,去看穿這一切的假裝。她不是不生氣,她只是更焦慮。話鋒一轉,龍應台表示,新的挑戰,需要新的世代去面對、去處理,每個世代的人都該有自己的世代責任。
對於這樣直接的提問,龍應台沒有迴避地直言,寫《野火集》的時候是1985年,那時候需要天真,需要勇敢,而且生氣是可以立刻帶來改變的。但今天台灣所面對的敵人,已經不是單一的任何一個政府,現在的敵人藏在假裝公平的媒體、假裝正義的司法、假裝一切為人民的政府裡面。敵人就像是在人們的血液裡,而非某個外在的事物。這也是為什麼,人們更需要老師們為這片土地,教出更有思辨能力的下一代,去看穿這一切的假裝。她不是不生氣,她只是更焦慮。話鋒一轉,龍應台表示,新的挑戰,需要新的世代去面對、去處理,每個世代的人都該有自己的世代責任。
年度論壇2》竟然是水逆造就了梵谷?創作、AI、5G普及與閱讀的未來:胡晴舫X台灣AI Labs創辦人杜奕瑾對談
2020年Openbook好書獎即將於12月1日揭曉,這樁出版界的年度盛事,11月初先以3場論壇拉開序幕,第二場活動邀請到胡晴舫與杜奕瑾對談。
杜奕瑾也擁有多重身分,最知名的應是他大學時即創辦了電子布告欄批踢踢,被網友稱為PTT創世神。他同時也是AI的先驅,曾在微軟人工智慧部門擔任研發總監,也是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的創辦人。
不管是文策院或台灣AI實驗室,兩人目前擔負的都是永遠在前進與變化中的前瞻性任務,站在科技應用和政策的前緣,必然探觸到更多未來的可能性,看到了閱讀、文本與讀者之間更具開創性的關係。以下是本場論壇的菁華摘要。
OB:文策院在近日即將推出的TCCF創意內容大會,策畫了國際論壇及「未來內容展示體驗」展會,我們從其中感受到文策院對於未來內容創作的定義有多元的想像。請院長談談,從紙本的創作交流,到社群媒體的分眾時代,您如何看待書寫與閱讀的改變?文學/文本創作在未來會以什麼樣的形式存在?
胡晴舫:我三十多歲時有一本書《機械時代》,講當我們身邊所有東西都機械化、科技化了,所有的生活環境都變成無機感時,文學會不會消失、書寫會不會消失。《機械時代》是2003年寫的,過了快20年後寫的《群島》則是關於臉書。
人類是情感的動物,所以我們的所有創作都在抒發情感,都是溝通的慾望,想明白存在是怎麼一回事、世界是怎麼一回事、自己是怎麼一回事。
從《機械時代》到《群島》,我一直在思考情感會不會因為物質環境而改變。寫作是人類最原始的本能、最不需要成本,拿一隻筆、拿手機打字、送出一個表情符號都是寫作,都是表達。我對文學的想像沒有很拘束,對於文學被取代也沒有很悲觀(雖然我的文字看起來很悲觀)。我們生活在充滿各種條文的世界,包括填銀行貸款、用說明書,都是閱讀的動作,我對閱讀的定義很寬。
因為接了文策院這個工作,我的閱讀量大減,但電視劇看得很多。我曾說過一句話:「現在的電視劇是18世紀的長篇小說」,以前婦女要在晚上做針線活,夜晚很漫長,就有人來說書,從聽詩變成聽小說。聽故事的衝動從人類很古老的時候就開始,大家圍著篝火分享體驗,當有遠方的人來時,就可以分享奇幻的冒險故事。
我從來不會說文學不死、紙本長流。但只要有人類繼續繁衍下去,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小宇宙,就會有創作力的可能性,不斷找尋新的媒介,找到新的平台。你會問:新人類是否會因為科技的便利而懶惰於創作?我相信新人類會懂得駕馭被發明的東西,適應新的物質環境之後反思,重新調整。
我對人類的本性常常因為過度悲觀而有一種奇怪的樂觀。我覺得寫作者現在就像和服的師父,有些人會覺得有點土、沒有人要穿,但有慶典的時候還是會被欣賞。文學、書店、詩歌節越來越聖堂化,到書店拿一本書,會變成一種儀式性的感覺。閱讀可能在平板上完成,可能會被Podcast、被有聲書取代,可能會用別的方式完成。但我不覺得閱讀或文學會消失,只是用不同形式存在。
▇AI難以學習「無端推理、無端創造」從零開始最困難
OB:這幾年演算法快速成長,AI人工智慧也擁有創作能力,今天還有韓國電視台將以AI主播替代真人主播的消息傳出。許多人不免會擔憂:AI是否普遍取代人力,創作是不是也可以用演算法來計算。杜先生投身AI研發多年,除了之前轟動的「雅婷逐字稿」,在TCCF創意內容大會裡也將推出「雅婷音樂人機互動體驗」,請與我們分享AI科技智能在未來可以提供創作者怎樣的服務或應用。
杜奕瑾:我常被問到「AI人工智慧會不會取代人力」,我比較樂觀。目前AI走的主要方向是當人類有什麼習性、有什麼創作,AI就去學習,去做一樣風格的圖畫輸出或文字創造。
台灣AI實驗室有一個團隊,專門在做人機介面。大家傳統上覺得,人機介面是語音辨識、語音理解、人臉辨識,其實這是很基礎的認識。這背後代表的是一個人怎麼理解另一個人的話語、誰是誰。但當我們在講人和人的互動,很大部分不是文字和語言構成的,而可能是聲音(對應在音樂創作,AI理解聲音中人的情緒)以及畫面(對應在符號,AI理解人的感覺)。
當我們在講人工智慧創作,第一是先理解人之間的互動。人工智慧要聽得懂:你哼一首歌是快樂還是悲傷、你作畫是憂鬱或者難過,我們可以訓練人工智慧理解人相對應的情感。過去大家對於人工智慧如何創作,主要案例是:我們訓練出來的AI模型,可以反過來進行相對應的生成。以文字來說,只要供給AI幾個標題,AI就可以創造出一篇文章,讓人讀起來煞有其事、很有感覺。AI也可以寫詩或歌詞,或在假新聞應用上,以某件事為主題,訓練出check bug偵錯後,在全世界發布相同主題內容,帶領大家往某個方向去想,這都是人工智慧文字創作部分的能力。
但是創作當然不只有文字,比如說現在很多深偽(Deepfake)技術,可以創造出假的影片、假的人物。剛剛提到新聞主播,現在有人去研究,如何用人工智慧創造出比所有男人還帥的男性、比所有女生還美的女主播,甚至可以合成有磁性悅耳的男女聲音,都是使用人工智慧去創造相對應不存在的事情。從這樣的創造中,人可以感受到,就像人與人之間一般互動的體驗。
有人會問說,是否有了人工智慧之後,未來只要提供AI幾個大綱,透過大數據分析全世界的文章,人工智慧就可以像作家一樣寫出一篇有意義的文章?從這個角度來說是可行的。但要注意的是,人工智慧會從經驗中學習:什麼是帥哥、什麼是美女,AI可以在Deepfake技術上做出好看的人物並模仿人的互動,也可以模仿人寫歌寫詞畫畫,但這一切都是基於學習之後再創作。
所以其實人有一個東西,是人工智慧完全沒辦法產生的(也許未來可能有辦法,但現在還比較難)。人最難學習的其實是:無端推理、無端創造、從零開始創造一個從來沒有的東西。
比方說以AI去創作周杰倫風的音樂或梵谷風的圖畫,這個現在都做得到,只要先讓AI看大量梵谷的作品,之後隨便給它一張照片,就可以做成梵谷風。但要叫人工智慧變成一個大師,創造出新的作品風格就很難,因為人工智慧是基於學習後才創作的,比較難有這種無端的創作。同樣的,要讓人工智慧去學某個歌手的音樂風格,產生出相同感覺的旋律或情感的鋪陳,是可以做到的,但要讓人工智慧變成一個新的音樂家,創造從未聽過的音樂路數,就比較不容易。
所以從某種角度來說,人的原發性創作,人工智慧難以取代。這告訴我們,如果創作者或作品只是複製其他風格,以現在的AI技術可以做到相類似的效果;但如果創作者本身具有強烈的主觀想法,目前的人工智慧就比較難去取代。
再往下一步討論,人類本身也可以運用人工智慧。現在業界很多在討論的是:我們怎麼在人機互動中進行創作。譬如人常常心中會想到一個旋律,想寫下來,但他可能只會彈簡單的鋼琴。怎麼從簡單的鋼琴旋律,啟發其他的配樂、相關旋律、樂器,或者跟人聲互動?這部分其實可以透過人工智慧去延展創作。
我們台灣AI實驗室有個音樂團隊的計畫就是,先讓人工智慧從聽得懂音樂開始,讓AI知道這個歌手在唱什麼、鋼琴在談什麼、鼓在打什麼。當它聽過幾百萬首歌之後,我們反過來當一個真正的創作者來和它互動,給予人工智慧一段旋律,人工智慧會去想要怎麼和這個旋律配合。這就是我們正在實驗的:人機協作。
以前的音樂創作要找到專業的樂手才能有好的演奏品質,現在有AI和你協同創作,你可以先讓人工智慧和天團等級的厲害吉他手或鼓手學習,當你創作時,就可以利用人工智慧學到的元素去嘗試合奏、試驗。這次我們在TCCF創意內容大會展出「雅婷音樂人機互動體驗」,邀請現場來賓先進行一段簡單的彈奏,彈奏過程中人工智慧就可以即時和你互動,做出其他旋律。我們也請到一個AI主唱,當你彈奏時,它會跟著你去唱。你會聽到好像是人聲,但聽不出它是在唱什麼,因為在訓練的時候,我們先將感情和旋律創造出來,但還沒有賦予AI主唱語言(之後可以加入)。
以這個體驗來說,接下來其實可以想像的是:未來的藝術創作過程,人本身會變成像是導演,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主軸,但可以透過人工智慧更豐富化。就像假新聞是一種人機創作的寫作應用:只要列出幾個主要的議題,AI就可以做出煞有其事的假新聞。但這需要人先去做出主軸陳述,再由人工智慧去潤稿,增加故事的張力或敏感度。
▇創作本身是意外 科技會解放人類創造力
OB:當越來越多人有機會應用沉浸式的敘事媒介來創作,過去的接收者(讀者)未來也可能轉身成為創作者。新媒體的互動特性,大大改變了傳統從作者到讀者單向的敘事模式。請教作家胡晴舫,您對於這種參與式創作有何觀察,請分享您身為創作者的心情和想像。
胡晴舫:我想回應杜先生說的,關於創作這件事是「無端的創造」,這個「無端」,真是太對了。siri寫作和胡晴舫寫作有什麼差別?我會用意外來形容,我覺得創作本身是個意外。科技的重點就是機械時代,19世紀班雅明、波特萊爾等一批人就已經在討論科技的「機械複製」了,機械複製的好處是一切都非常完美精準,不會出錯。
但人是有弱點的,非常不完美。馬友友每次演奏巴哈都不一樣,因為他會犯錯。冰島作曲家Jóhann Jóhannsson是用電腦寫曲的,有人問他電腦演奏和真人樂團演奏的差別在哪?他說電腦的演奏非常完美,完全是我腦中所想,力道情感準確,但是人的演奏會有surprise,會超乎他的想像。
當你讀了別人的書再轉譯出來時,你本身就在創作。創作就是一個人原來、原始、原創的意念。假設你對種植小黃瓜很有想法,你讀了10本書,看了2部紀錄片,採訪5個小農,而當你述說你的小黃瓜哲學,我個人認為你已經在創作,因為你有你個人的世界觀。其實創作這件事就是世界觀,當我們講到VR、AR、各種R,其實也是在創作另外一個世界觀。世界觀、宇宙觀是所有小說的核心價值。
我相信AI非常好,我也相信我們可以駕馭它。梵谷是個意外,雖然AI可以模仿梵谷,可是梵谷是怎麼變成梵谷的?沒有人能知道。我要強調的是:意外是非常重要的,他可能是因為水逆發生的——水逆這件事就是意外嘛,為什麼就是諸事不順!所以下次水逆的時候,請大家放寬心情來想這件事:啊!人生正在跟你召喚,現在是你的創作期。我常常這樣安慰我自己(笑),每次有水逆的時候,我就覺得所有事情都會是我創作的養分。
我覺得,科技的好處是讓創作成本降低。以前只有大型的工作室有能力拍攝電影,但今年有一部國片《怪胎》,導演是用iphone拍的。科技會解放我們的創作力。作為人類,我其實不擔心這個創作力會往哪裡去。如果因為這樣文學就會死,那就算了吧。但是我覺得,文學一定不會死,文學是最廉價的創作方法。
我對科技沒有排拒,它讓我們每個人好像變成生活的策展人。當你在用社群媒體時,事實上你正在施展創造,你在想像一個不同樣子的你,你寫出來的文字或貼出來的照片,根本不像在沙發中看電視的你。對我來說這就是創作,它會讓每個人把自己的情感和想像力抒發出來。它或許會有點矯情,但創作這件事,本來就沒有在講真實的。
剛剛提到,當科技的使用工具改變時,是否會改變我們的創作方式?這是會的。我用筆寫作,用電腦寫作,或者因為老花眼必須讓siri幫我打字時,一定會寫出不一樣的東西。文策院很多人認為podcast可以幫助到寫作者,我有點不太同意。我認為podcast很重要,但它會創造出另外一批創作人,因為它的創作工具不一樣,是用聲音。podcast會訓練、創造出另一批說書人、演說家或者聲優,我覺得他們是另一種創作人,是和寫作不同的創作。
我覺得寫作是和自己對話,當你面對電腦或提筆時,那種孤獨感是非常巨大的。而當你在做podcast,你知道你是在和外面的人對話。當對話的對象不同、媒介不同,就是不同的創作了。
▇喪失敘事創新先機 就會被既有閱讀平台綁架
OB:5G高速率、低延遲、多連結的特性,使得VR/AR/XR等沉浸式新媒體的創作門檻大幅降低,接收端的普及率則更為提升。這些新媒體並不是最近才出現,但可能透過5G變得更簡便親民,這對於傳統敘事會帶來什麼影響?請杜先生分享,在5G即將引發的變革中,您個人最期待的影響?
杜奕瑾:人機互動體驗,除了以人工智慧去理解人的情感之外,我們也有在想AR、XR這類沉浸式體驗。人工智慧實驗室為什麼對音樂、圖像與藝術感興趣?有個很大的原因是,因為在閱讀的時候,我們只看到文字。文字其實可以賦予你很多的想像,過去的線上會議就只是文字交流,但要怎麼把文字,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透過更多的形式呈現、補足,讓人覺得沉浸在這種體感互動中?
關於沉浸式體驗,現在很多人開始在做360度環景,因為環景讓人有實際在當下的感覺,你的感知會比較全面。但在環景環場之外,不只有我們說的虛擬實境AR或VR,在虛實整合相關體驗之外,其實還會有感知的部分:有沒有可能讓使用者更能感受到創作者實際想表達的故事張力?以體驗的角度,我們持續思考如何運用新興科技,也就是5G,來做沉浸式體驗。
5G和沉浸式體驗的變革,意義之一是應用面的創新。過去我們從書本和文字中感受人要傳達的消息,手機普及後,開始有影片、音樂可以彼此傳達。那麼未來高頻寬的5G時代,難道還是用過去同樣的方式來進行人和人的互動?其實這還有很多想像的可能。
今年因為新冠肺炎的關係,出現很多線上化的國際展覽,線上會議平台也廣泛被使用。但在5G、沉浸式體驗更普及的未來,平台肯定不只有現在這些。最近就有人辦線上演唱會時,把每個參與者變成一個遊戲角色,主唱變成大魔王之類的,讓雙方進行互動。總之開始有各種不同的體驗嘗試。
5G和沉浸式體驗的變革意義之二,在於敘事的創新。我們怎麼透過虛實整合,以即時的運算去即時了解,做到新型態的互動體驗?我覺得這部分也有很多可以去想像。
為什麼敘事創新很重要?比方說蘋果手機出來前,沒有人知道智慧型手機未來的樣子,蘋果第一個定義出未來的閱讀介面是觸控螢幕,也就變成平台、內容的標準。臉書則定義出社群媒體的介面,自然而然它就成為平台,平台就掌握敘事的主要窗口。
但是,如果台灣本身所有敘事平台都被主流國際公司掌握了,會有怎樣的狀況?大家其實知道,現在大部分人的閱讀不是透過書本而是臉書,當臉書變成主要通路時,它掌握了你閱讀的內容。現在的內容工作者,不管是做影像、新聞或寫文章的,你的作品在臉書上要傳給使用者之前,是被平台挑選的。也就是說,當你沒有掌握到敘事創新,沒辦法變成全新的閱讀方式,你就會被既有的閱讀平台提供者把持。
舉個類似的例子:假設市場上很多有機小農在生產農產品,但中間被盤商壟斷,盤商可以在源頭拿低價,在終端賣高價。我們現在的閱讀媒介一旦被壟斷也是這種狀況,所有的創作者的利潤被不斷壓制,這也是現在雜誌、出版業的困境。
過去人們做藝文創作的時候,要是提供很好的內容,就會有很好的名聲或回報。但透過平台之後,他們是拿你的優質內容去推廣他想販賣的內容,而這種模式會讓環境生態往另一面發展,造就現在很多「精準行銷」加上「政治服務」,結果就是各種假資訊盛行在內容平台上。以社群媒體來說,等於他拿好的內容去推廣他可以賺錢的內容。再以傳統農產鏈來比喻,就像拿低價米去混有機米,再以高價賣出,一旦內容平台被一方壟斷,也會自然往這方向發展。
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有一個想法,就是在敘事創新、內容創新的部分,我們在思考如何去做到新的體驗創新。這裡的體驗創新,指的是傳遞的模式,不再是透過一個中心化的平台去傳遞。因為人和人之間要做到互動溝通,消息與內容的傳遞,不見得一定要透過中間的盤商啊。就像有機農產不一定要透過大盤商,才能到消費者手中。對於未來的體驗或敘事創新、媒介可能的面貌,我們歡迎大家一起來想。這些想法還在前瞻的實驗過程,我們的工作就是實驗,也歡迎大家一起和我們做實驗。
OB:請二位分享今年個人的閱讀,並推薦一本書。
杜奕瑾:我幫《唐鳳:我所看待的自由與未來》寫序,這本書寫他的思想、求學和就業歷程,我非常有共鳴的地方是,我們過去是比較工業的社會,訓練每個人成為工業社會的螺絲釘,對現在需要的天才類型其實是不利的。人最有價值的是什麼?就是剛剛說的「各種意外」、各種「無端的創作」。
我特別有共鳴的是,進入Internet的年代,很多知識都是從網路上學來的,從這種開源(Open Sourse)、開放分享的精神下不斷去嘗試和創造。真正最有想像力,能定義問題、能解決問題的,以PTT的角度來看就是「很有鄉民的精神」。所謂「鄉民的精神」,就是我們有不同的專業,我們共同看到一個問題,七嘴八舌之後,有了粗略的共識,大家拿出各自的本領,去嘗試共同完成。這種精神在這個時代尤其重要。
座談結束後的問答階段,現場讀者提出了許多精彩問題,特摘錄如下:
Q:請問杜老師未來是不是懂AI的人、事、物會大者恆大,形成占盡優勢的私人資產?這樣弱勢族群該如何翻身?該如何培養AI相關的基礎知識?
杜奕瑾:我們最近有很多醫療相關的討論,很多人問說AI會不會取代醫生?結論是不會,因為醫療有很多狀況是過去沒有看到的,需要人來做最後的推斷。可以確定的是,你今天如果不會使用AI的話,就像你不會使用Google一樣,會很狹隘。AI可以窮盡一切知識之後來幫你做一些決定,你不一定要會運算,但要知道怎麼使用它。微軟亞洲研究院院長洪小文說過一句話:「不要說AI會取代人類,應該說AI加上HI(Human Intelligence),人的智慧再加上人工智慧,可以給予人superpower。」要懂的是會運用,就像你要會使用網路,但不一定要會寫搜尋引擎。包容、接納它,就會自然而然占有優勢。
Q:常聽很多人說「看不懂小說/不看小說,因為無法想像文字描述的畫面」,也因此看影劇顯得簡單方便多了。但文字確實是挑戰自己吸收、轉譯能力的形式,「做好的」影視畫面映照的是製造者而非觀看者自身的想像。作為文字創作者,晴舫如何看待這些轉譯能力的差異、這樣的能力可以如何「訓練」呢?
胡晴舫:從作家的角度,我覺得一本小說人家看不下去,你要檢討。但我也覺得你一定找得到適合你的小說,就像看電影一樣。放輕鬆一點,不要把小說和詩都看得太遙不可及,我真心覺得閱讀是碰撞,又回到意外這件事。
Q:請問杜先生認為AI發展的極致是什麼呢?是否想像過它的可能性?例如具有自我意識。又,AI在現代世界的應用上,有什麼倫理問題可和我們分享嗎?
杜奕瑾:只要是人類經驗可以去學習的東西,就會有一個又一個AI的產品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之中。關於倫理的問題,當我們在學習的時候,這些個人資料該怎麼處理?人工智慧會不會有偏見?人工智慧是學人的,人會有偏見,那人工智慧也可能會有偏見。這些問題都和倫理有關。
Q:在出版業不斷萎縮下,全職寫作是個遙不可及的事,想知道院長有曾經嘗試過全職寫作嗎?又怎麼能在工作忙碌下,持續產出高品質的作品。
胡晴舫:我有一段很幸福的日子,15年都沒上班,因為我在中國工作存了一大筆錢。我大量的寫報紙專欄、大量供稿,每一年努力的寫書出來。能不能過日子?可以,但很辛苦,要非常非常有紀律。我還是認為寫作不會消失,就像我剛剛說的,寫作的成本是最廉價的,我很相信每個人都可以寫一本書,只要把你的生命故事寫出來,就勝過AI,然後AI就要學習你了。
Q:請問胡院長何時出新書?有考慮和雅婷合寫小說嗎?
胡晴舫:不會是明年,因為今年都沒寫。這是25年來第一次一整年沒寫一個字。未來十年我應該只會寫小說,我想寫犯罪小說、間諜小說,我開始覺得閱讀應該是一個樂趣。回到剛剛說的,如果小說讓你讀不下去,那是我的錯。●
閱讀通信 vol.361》跳躍的敘事線
▇2020Openbook好書獎
▇來看看超過250位讀者的年度好書吧!
▇得獎好書,各大網路與實體書店熱烈推廣中
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贊助:
合作夥伴: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