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短評》#227 凝鍊愛憎的極品好書懶人包
●跳水的小人
黃寶蓮著,印刻出版,300元
推薦原因: 文
11則短篇,寫的依然是作者鍾情的癡男怨女,儘管身經百戰,愛還是要愛,風月過招,點到為止,不再糾結黏膩,也不大需要虛以委蛇的文學機關。求不得,怨憎會,愛別離,悉入無為禪境,這真是冬夜威士忌的下酒料了。【內容簡介➤】
●思慕的城
陳家毅著,聯合文學出版,390元
推薦原因: 樂
或許因作者出身新加坡,分外關注地緣文化相近的東亞世界,敘寫日本、台灣、港澳、新加坡、曼谷、金邊等東北亞至東南亞的城市,串起一條風土文化鏈。以西方建築學養略帶距離觀察,混融東亞在地觀點,流露對心儀城市的微微思慕。
作者以新加坡視角的城市文化觀察,與台灣熟悉的日本與歐美視角有微妙的差距,對於台灣及東亞各國的建築與空間文化,本書提供了另類的觀察。【內容簡介➤】
●告訴我他是誰
Just Tell Me Who It Was
約翰.齊佛(John Cheever)著,余國芳譯,木馬文化,380元
推薦原因: 文
以為女人是傲骨賢妻,結果是絕望主婦;以為男人是有頭有臉的霸道總裁,內心卻藏著怯懦的小男孩。齊佛寫美國60、70年代的郊區生活,描述中產階級體面外表下,內在不斷蔓生棘刺。相較於其他短篇名家如歐康諾(Flannery O'connor)的怪誕陰鬱,或卡佛(Raymond Carver)的荒謬靈韻,齊佛最為「正常」,故事也更像身邊發生的日常瑣事,平凡而難以忽略。【內容簡介➤】
●回家之路
Homegoing
雅阿.吉亞西(Yaa Gyasi)著,李靜宜譯,春天出版,380元
推薦原因: 文 樂 獨
美國黑人文學的又一力作,本書將歷史溯源拉回到非洲,故事在殖民與蓄奴之間開展。以女性觀點看待迦納近代被殖民的歷史,一條線寫留在母國與殖民者抗爭的人民,一條線寫被販賣至美國成為黑奴。在桎梏與貧窮中掙扎的家族史,優美修辭與血腥現實對照強烈,新人作家一出手便是壯麗史詩,後勢看漲。【內容簡介➤】
●李香蘭與原節子
李香蘭と原節子
四方田犬彥著,詹慕如譯,黑眼睛文化,460元
推薦原因: 知 樂
本書介紹了兩位日本戰期到戰後的代表性演員,提供了犀利觀點的歷史考察,特別是戰後作為小津安二郎看板女主角的原節子,在戰前與帝國宣傳體制的種種事蹟,值得再三玩味。對於日本電影史感興趣的讀者,本書是不容錯過的精彩作品。【內容簡介➤】
●從科學月刊、保釣到左翼運動
林孝信的實踐之路
王智明、吳永毅、李淑珍、林正慧、林嘉黎、林麗雲、陳光興、陳宜中、陳美霞、陳瑞樺、劉源俊、歐素瑛、錢永祥、鍾秀梅、蘇淑芬著,聯經出版,480元
推薦原因: 益
作為保釣、社區大學以及科學啟蒙的代表人物,林孝信是當代台灣社會思想文化景觀中不可忽視的人物,本書提供了理解林孝信的許多重要面向。【內容簡介➤】
●為什麼要佔領街頭?
從太陽花、雨傘,到反送中運動
何明修著,左岸文化,420元
推薦原因: 知 議 獨 益
本書的寫作從台灣太陽花運動開始醞釀,歷經香港佔中以及反送中的運動,在香港成為全球焦點的此刻出版,可說是最為「著時」的作品。雖然處理的是當下發生的現象,但本書提供的思想深度以及歷史源流,有著非常紮實的分析。原書雖為英文學術作品,改寫相當成功,作為一般讀物也毫不遜色。【內容簡介➤】
●藻的秘密
誰讓氧氣出現?誰在海邊下毒?誰緩解了飢荒?從生物學、飲食文化、新興工業到環保議題,揭開藻類對人類的影響、傷害與拯救
Slime: How Algae Created Us, Plague Us, and Just Might Save Us
茹絲.卡辛吉(Ruth Kassinger)著,鄧子衿譯,臉譜出版,420元
推薦原因: 知 樂
近年來,科學書寫已走出傳統啟蒙式的敘事,轉而將自然連結社會的多元複雜面向完整呈現,本書提供了對藻類全面且豐富的介紹。【內容簡介➤】
●虛實妖怪百物語:序/破/急
京極夏彥著,林哲逸譯,台灣角川出版,420元
推薦原因: 樂
這回京極夏彥真是寫嗨了,古今妖魔傾巢而出。政府下令驅魔,實則遂行恐怖統治,一時人人自危,妖怪作家們首當其衝,一場正邪曖昧的大亂鬥就此揭開序幕,水木茂、荒俣宏和作者本人都被捲進了小說黑洞,頗有妖界嘉年華的味道。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本套三連作是巔峰之後的寫意潑墨,京粉必讀。【《虛實妖怪百物語:序》內容簡介➤】【《虛實妖怪百物語:破》內容簡介➤】【《虛實妖怪百物語:急》內容簡介➤】
●愛麗絲幻遊奇境
Alice in wonderland
圖文:蘇西.李(Suzy Lee),宋珮譯,大塊文化,450元
推薦原因: 設 文 樂 獨
運用素描、渲染與拼貼等手法,重新演繹《愛麗絲幻遊奇境》經典。作者安排壁爐為舞台,上演女孩追逐白兔奇詭又迷人的夢境,其間壁爐放大為真實人生的舞台,最後又回返作者家裡的壁爐,巧妙呼應了原典裡物體尺寸不斷變化的幻覺,而壁爐與舞台外框如電影銀幕般框取出現實,也模糊了虛實界線,是充滿哲思與電影感的超強圖文書。【內容簡介➤】
知識性.設計感.批判性.思想性.議題性.實用性.文學性. 閱讀樂趣.獨特性.公益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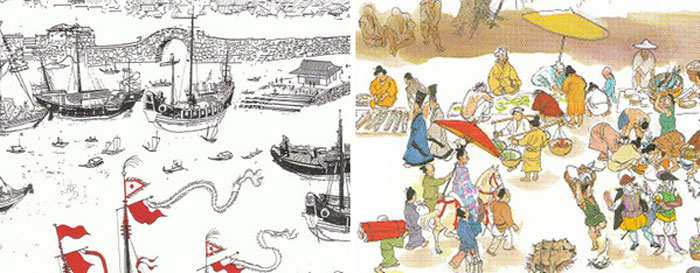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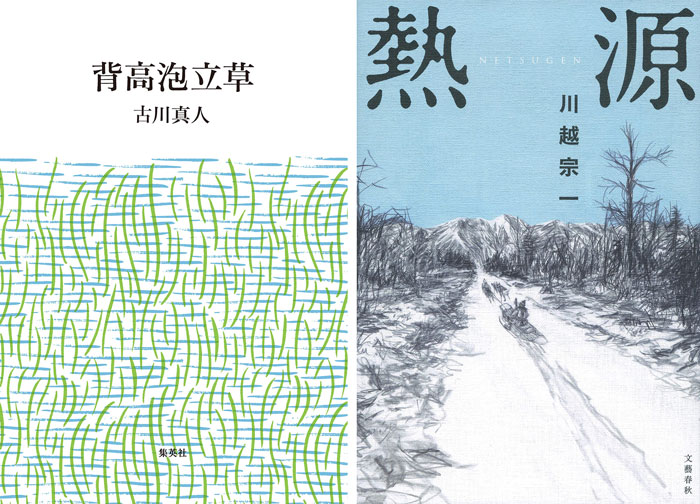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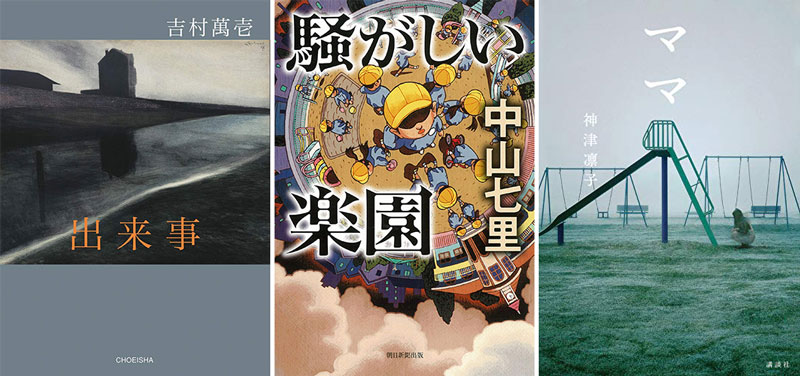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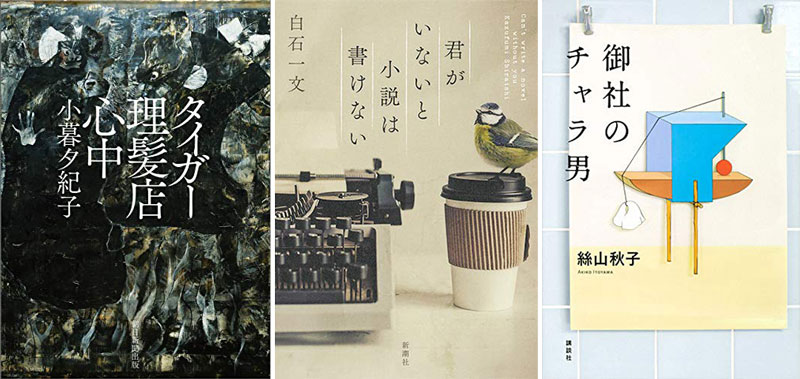
書.人生.黃子欽》閱讀的故事
小時候跟姐姐到安平外公家,發現一家「書店」,很多小朋友在板凳上看書,我們不客氣跟著進門,對整排書架東翻西翻,結果逛完出來時有個小孩跟我們收錢,「他看了幾本⋯⋯」「她看了哪幾本⋯⋯」,那時才知道,進來看是要付錢的,原來這叫租書店。
國中時為了考試晚上K書,一兩個鐘頭過去了,攤在眼前還是那兩頁,時間似乎靜止在無聲的刻度上,身體像坐牢,靈魂飛出去留著空殼杵在那裡,這像是一種超現實的閱讀體驗。
記得以前在書店上班,有次讀書節視覺發想,提到閱讀地點的使用——圖書館、教室、書房、書店、餐桌、浴室、海邊⋯⋯在陌生的地點打開書本、前往陌生的地點閱讀,像是雙重冒險。那時候的誠品似乎打造出一個閱讀姿勢——別人正在看更好看的書,而且外國的書更好看(更好賣,價格更高),書的結構被放大成為視覺焦點,書的身體成為展示主體,像一件藝術雕塑品。
自己接案後,閱讀常來自一種歉疚感。有時候是對陌生的書,產生「讀過了」的錯覺,可能因為書市平台的訊息讓人錯亂。那時候的閱讀經驗通常不是來自書,而是來自設計書的過程。似乎人找書,書也在找人,若在二手書市,這種感受可能更加強烈。我有時會想,閱讀經驗可以支援設計嗎?或是相反。或者說,書會來教我如何設計它嗎?
剛去書店上班時,當時的企劃部主管拿出一張方形DM來說明「一面形象一面行銷」的設計概念,後來我就用「作形象」的概念來做書店櫥窗——閱讀不拘手段,不限材料,書店的獨立空間「櫥窗」就是最佳的放空場所,就像歐洲拱廊街的入口櫥窗,可以在關鍵的近距離來呈現精緻的人文縮影。
《做愛情》書籍封面
2002年網路與書出版了《做愛情》,封面俯拍一箱一箱的愛情物件(攝影何經泰、設計張士勇),當時被這種視覺手法啓發,就將櫥窗的空間經驗轉到平面經驗,執行了《布爾喬亞》、《時尚考》、《黃金時代》、《咖啡精神》、《美食考》⋯⋯的裝幀。當時住頂樓加蓋,空間比較大,就將相關物件裝置起來,搭了一整面牆,再請攝影師來打光拍照,幾本書進行下來,像是經歷了歐洲中產階級的物件考。後來寺山修司的《幻想圖書館》,再借用了臺大標本館,開啟另一個奇幻攝影棚經驗,那些地震測試儀、蝙蝠、巨嘴鳥⋯⋯成了視覺道具,不可思議地收進了書中。這種從空間轉到平面的設計經驗,就像是將物件當成黑盒子,一一解碼轉譯再釋回給大眾。
左起:《布爾喬亞》、《時尚考》、《美食考》書籍封面
為報紙副刊畫插畫,也是一種特殊的經驗。當時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楊澤在挪威森林咖啡館看到拙作《不連續記憶體》,打開我的副刊拼貼經歷。記得其中一篇〈向學運世代或網路世代傾斜?〉,用了10張拼貼,左傾15度、右傾15度,像屏風一樣在版面中展開。袁哲生的〈羅漢池〉上下兩篇則是造景,一個後花園跟一個開滿奇花的池塘,羅漢腳獃立在其中。許舜英〈我們必須很有錢〉讓畫面闖入了富貴列車,李維菁的〈男朋友的妹妹〉則是兩個蒙面怪客的拼貼。後來也設計了《我是許涼涼》,讀到《家族盒子:陳順築》(維菁執筆)的記錄傳記時,感到雙重的失落,他(她)們倆人都英年早逝。
報紙副刊文〈向學運世代或網路世代傾斜〉插圖設計(黃子欽提供)
閱讀副刊是一種驚喜偶遇,文本會上下左右前後交會。跟雜誌不同,報紙版面很少留白,除了詩與插畫。說到「留白」,西方中世紀的祈禱書,內容塞得滿滿的,展現壯麗的恩典。早期東方線裝書,用竹簡線條排列,空間都不會輕易浪費。紙本的「留白」設計,似乎是消費跟慾望的起點,當留白產生的那一刻,讀者的想像空間也同時誕生。
詩集可能是留白最多的紙本,詩集常常是一種合理的反抗,閱讀台灣50、60年代的詩集,如楊喚《風景》、周夢蝶《孤獨國》、方思《夜》,朱沉冬《弦柱》⋯⋯小心翼翼白、人文白、超現實白、極簡白、日光燈白、象牙白……,詩集大量的「白」,跟主文一起呼吸,開啟想像,也將微小的雜訊放至極大,像窺探啞巴的內心世界。
最近幾年閱讀到30年代,感覺是喜悅的,尤其是相關的裝幀圖文,而這些內容其實也是反共抗俄、五四運動、左翼思潮的時代背景。30年代的書籍陸續研究出土,東亞文藝圈呼之欲出,似乎是個新的課題。記得小時候常看到大量圖案設計的書,後來才知道幾乎都來自30年代的東京與上海,美型模仿來自古典派,幾何結構的美感始自現代派,然後有了Art Deco都會摩登風格。日本西化後匯集傳統浮世繪與民藝素材,把裝飾圖案與字體,帶到東亞的高峰。20、30年代興盛的雜誌出版,給了40年代的「廣告畫」大量素材,各種標準字與圖案,都匯集到平面設計的系統中,形成一波風潮。所以歐美出版若要出早期的東亞「廣告畫」,japan跟china 這兩個主題剛好是兩本厚厚的磚塊書。
裝飾圖案跟流行雜誌不會同步,是之後的集結出版,比如工藝圖像、廣告插畫、各式LOGO標準字體。中國廣告畫是上海美女牌與城市影像,日本廣告畫有浮世繪與現代紋樣,台灣廣告畫的想像是什麼?八家將、媽祖、水牛、農村、青山綠水、竹藝、宮廟、原住民紋樣⋯⋯現有的想像基調是模糊的,但我相信一定會充滿台灣的活力。
很難想像中國在20、30年代,這麼依賴日本的文化輸入,包裝設計對傳統文人來說是較不入流的,不像書畫傳統。30年代有大量的裝幀都是書畫家「玩」出來的,但我卻覺得比起他們的水墨花鳥,這些玩票創作更有意思,更具現代精神。後來設計西西的《侯鳥》、《織巢》封面,讓我連結到作者的30年代,也用了一些紋飾來表達香港的現代精神。
《侯鳥》與《織巢》書籍封面
設計翁鬧的《破曉集》,則讓我重新體會「新感覺派」。戰爭天災摻雜了龐大的陌生壓迫訊息,戰爭結束洪水退掉,這種現實又讓人感覺是另一個夢,原有的生活節奏跟價值被推翻,「新感覺」可能也變成了「超現實」。或許翁鬧的夢想就是進入現代都會成為作家,而這種距離,像得不到的愛情一樣迷人。百年前歌頌機械主義、使用螺旋線條的未來派,跟物件詩一起曇花一現,而我在閱讀黃華成設計的《劇場》,或林亨泰早期的詩作中,也發現了這種跳躍性,跳過海峽與語言、跳過白色恐怖,甚至潛移到網路的向量圖,字形結構,台灣一直有著這種躍進的活力。
《破曉集》書籍設計(黃子欽提供)
雜七雜八的閱讀,會有一種感覺:歷史像一截斷尾求生的壁虎尾巴,從30年代到50、70,從解嚴到80、90,台灣的過去跟未來都有新的故事,有感性的「在地」經驗,三不五十「倒退嚕」也會看到新的風景。●
黃子欽
裝幀、拼貼、影像創作。近年花在做田野的時間比設計還多,希望能在台灣歷史、殖民經驗、文化混血、學術大眾、菁英普羅之間裡頭找到神奇的開關與創作的火花。想像「聳」跟「ㄍㄧㄤ」的距離,並提升至藝術性。認真閱讀新書資料卡,但執行設計時不太管讀者想什麼,做拼貼時讓自己很開心。認真時太嚴肅,亂搞創作也覺得別人看不懂,或許那個搞不清楚現實狀況的是真實的自己。
閱讀通信 vol.369》出烤箱的好日子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