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短評》#195 飛光幻麗的極品好書懶人包
●一百個影子
百의 그림자
黃貞殷(황정은)著,陳聖薇譯,凱特文化,250元
推薦原因: 文
寫國家暴力與資本主義體制壓榨下,在舊電子商場生活的人們。作者以影子的曖昧性質,比喻人們如遊魂般的晃盪處境,愛與存在都同樣飄忽不定,在明暗間游移。敘事冷冽節制,轉折處卻藏匿著幽微深沉的感情,以隱微筆法觀照現實,令人讚嘆。
疏離的文字,冷冽的風格,喃喃自語般的對話,這本不尋常的(愛情?)小說讓人想起早期的韓片,近逼虛無的肅殺之氣,卻又有種後現代的空氣感,夢幻泡影,識破一切,然而人畢竟還是有限的個體,還是只能使用帶著成見、辭不達意的破碎語言。【內容簡介➤】
●一草一天堂
英格蘭原野的自然觀察
Meadowland: The Private Life of an English Field
約翰.路易斯-斯坦伯爾(John Lewis-Stempel)著,羅亞琪譯,三民出版,350元
推薦原因: 議 文 樂 獨
自然書寫一直是老少咸宜的文類,本書作者透過書寫自然來分享各種知識,例如自然的「歲時」。這本自然觀察日誌樸直無華,有如清粥小菜,平淡中自有一股天地飽暖,其實也不用考量那麼多想出來的「生態」,只要把自己放進自然裡,老老實實去感覺、去體驗,自然自會自自然然。【內容簡介➤】
●碧娜,首爾天空下
Bitna, sous le ciel de Séoul
勒.克萊喬(J.M.G. Le Clézio)著,嚴慧瑩譯,臺灣商務,320元
推薦原因: 文 樂
勒・克萊喬喜歡遊走,也擅於描寫遊走人生,說起事來總讓人想起吟遊詩人,四處兜售流浪的故事。法國作家的筆調為首爾注入一股異樣的清新,所有的國仇家恨暴力衝突催淚灑狗血通通得到了淨化,行到水窮處,總還是可以坐看雲起時的。
然而,法國作家寫首爾人事,雖然竭力摹寫細節以求寫實,終究少了一層韓國文藝作品特有的緊迫黏滯,文字過分清爽。作者畢竟是高手,將碧娜的生活與口述的故事綴連起來,映照出城市居民共同的孤寂,好吸收好消化。【內容簡介➤】
●獻給國王的世界
十六世紀製圖師眼中的地理大發現
The World for a King: Pierre Desceliers’ World Map of 1550
切特.凡.杜澤(Chet Van Duzer)著,馮奕達譯,麥田出版,1200元
推薦原因: 知 設 樂 獨
古地圖的迷人之處在於當時仍有許多空白尚未命名,人們仰賴星空和水手帶回的傳說,想像廣袤海洋盡頭的世界。作者詳解這幅贈送給法王亨利二世的地圖,由諸多細節說明海妖、獸人族等圖案的象徵意義;同時也將圖上某些區域,對應到現今正確的地理位置,推衍製圖師或當時一般人的認知,讓讀者感受到16世紀人們對未知的強烈探索慾望。
書封這幅法國Dieppe系的地圖是當代的神品之一,在作者周延出色的解析之下,尚未完全除魅的海怪繼續興風作浪,澳大利亞若隱若現,波濤洶湧,飛光幻麗,每一頁都像《暴風雨》或《魔法師寶典》的場景。【內容簡介➤】
●社會不平等
為何國家越富裕,社會問題越多?
The Spirit Level: 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
理查.威金森(Richard Wilkinson)、凱特.皮凱特(Kate Pickett)著,黃佳瑜譯,時報出版,450元
推薦原因: 知 議 樂
在知識圈仍掙扎於偏左還是向右這問題時,現實中「新自由主義」的力量早已掌握了我們的生活,並結合國家機器,變成一個新型態的資本主義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消費」是關鍵,慾望(而非道德)已成為支撐這個體系的重要力量。在這樣的狀況下,討論「平等」概念顯得特別有意義,但究竟會變成空谷足音的清醒之言,或是自由主義者的單向獨白,仍需要進一步的觀察與思考。【內容簡介➤】
●每個人的短歷史
人類基因的故事
A Brief History of Everyone Who Ever Lived: The Human Story Retold Through Our Genes
亞當.拉塞福(Adam Rutherford)著,鄧子衿譯,八旗文化,480元
推薦原因: 知 議 樂
血液裡攜帶的DNA使人類得以追溯文字記載前的祖先,由個人延伸出不為人知的歷史。本書前半以基因檢視史料,後半破解關於種族與遺傳的種種迷思,令人重新思考相關的體質人類學研究。生物遺傳學不斷前進,文組生當自強,本書便是立論紮實的文組生遺傳學科普大補帖。
這部DNA系譜學簡直是人類演化的八卦精選,碇叩叩的科研成果全都成了稗官野史的強力支撐,三兩下就破解了各式各樣的人種迷思。我們今天的型態,也不過就是個暫時的過渡——這是開悟等級的人間正解。【內容簡介➤】
●引路者
導引山崎亮走上社區設計的大師們,探究英國社區設計如何發跡,重新回復工業社會所剝奪的人性與尊嚴
コミュニティデザインの源流 イギリス篇
山崎亮(Yamazaki Ryo)著,詹慕如譯,臉譜出版,460元
推薦原因: 思 議 益
後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產生了許多問題,「地方創生」與「循環經濟」一直是許多人持續討論的方向,也正逐漸形成一套論述與實踐的邏輯。本書打通了現今的社區設計與西方近代思想家之間的內在影響與聯繫,提供了地方創生實踐者將論述更加深化時的絕佳參考與指南。【內容簡介➤】
●創造現代世界的四大觀念
五位思想巨人,用自由、平等、演化、民主改變人類世界
The Shape of the New: Four Big Ideas and How They Made the Modern World
史考特.蒙哥馬利(Scott L. Montgomery)、 丹尼爾.希羅(Daniel Chirot)著,傅揚譯,聯經出版,560元
推薦原因: 知 思 議 樂
若對當今已耳熟能詳的「自由、平等、演化與民主政體」等4種觀念的形成過程感到好奇,本書提供了清晰的思路與答案。對這4個觀念已心有定見的讀者而言,本書也可提供新的脈絡供重新思索。【內容簡介➤】
知識性.設計感.批判性.思想性.議題性.實用性.文學性. 閱讀樂趣.獨特性.公益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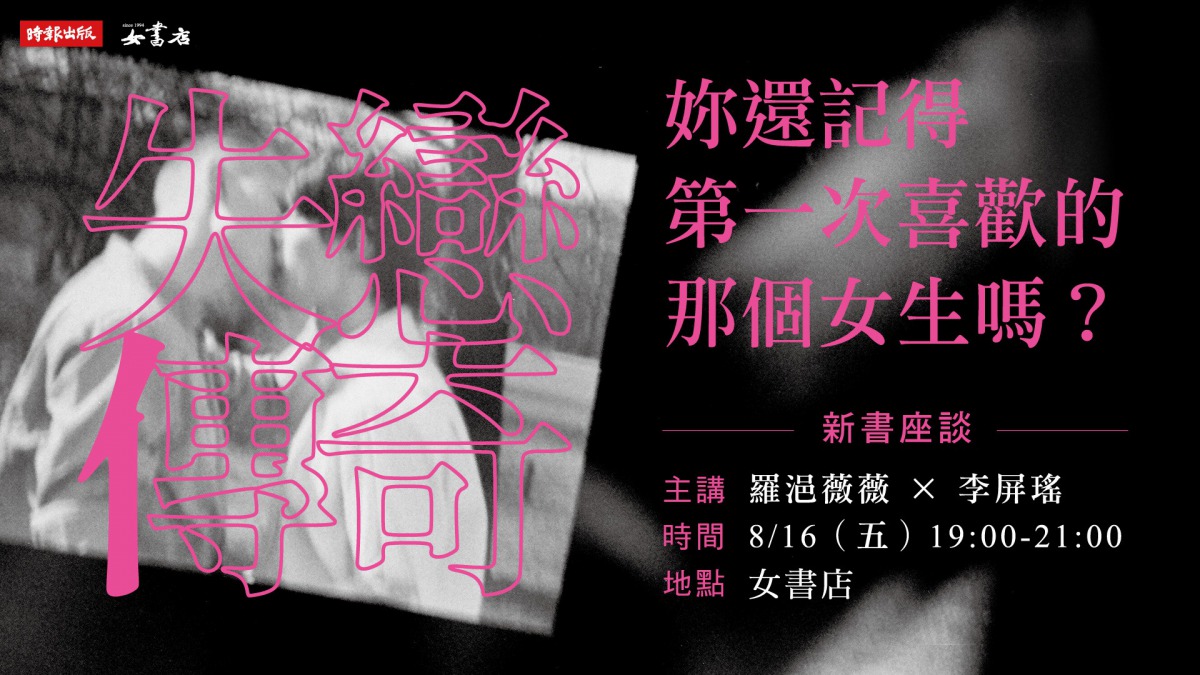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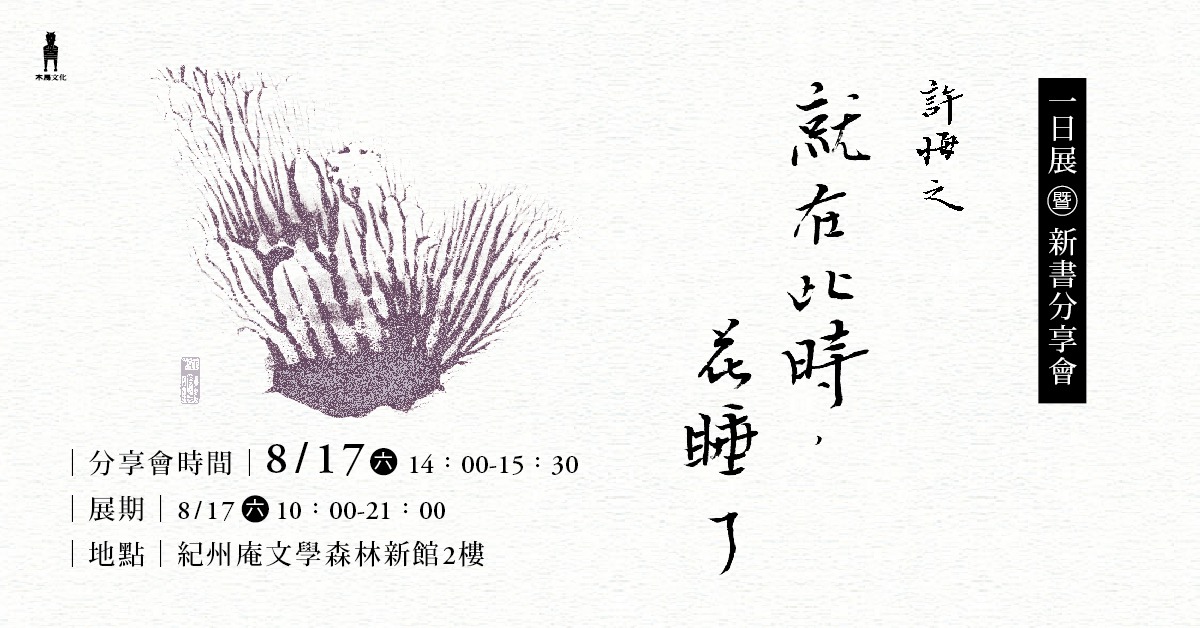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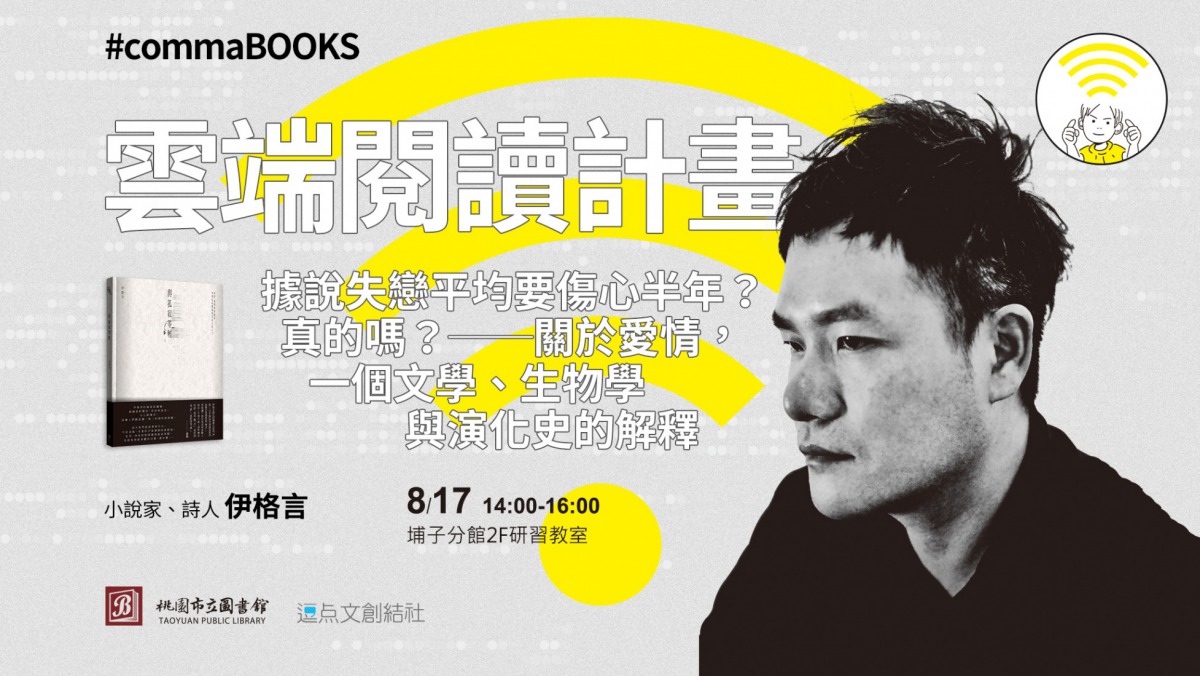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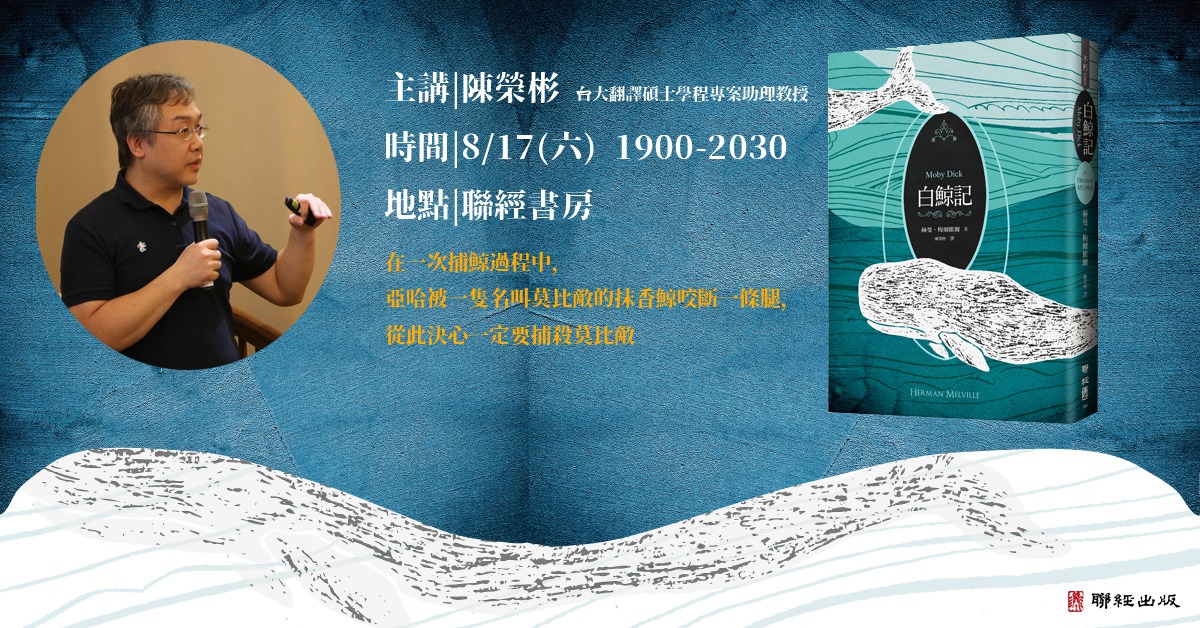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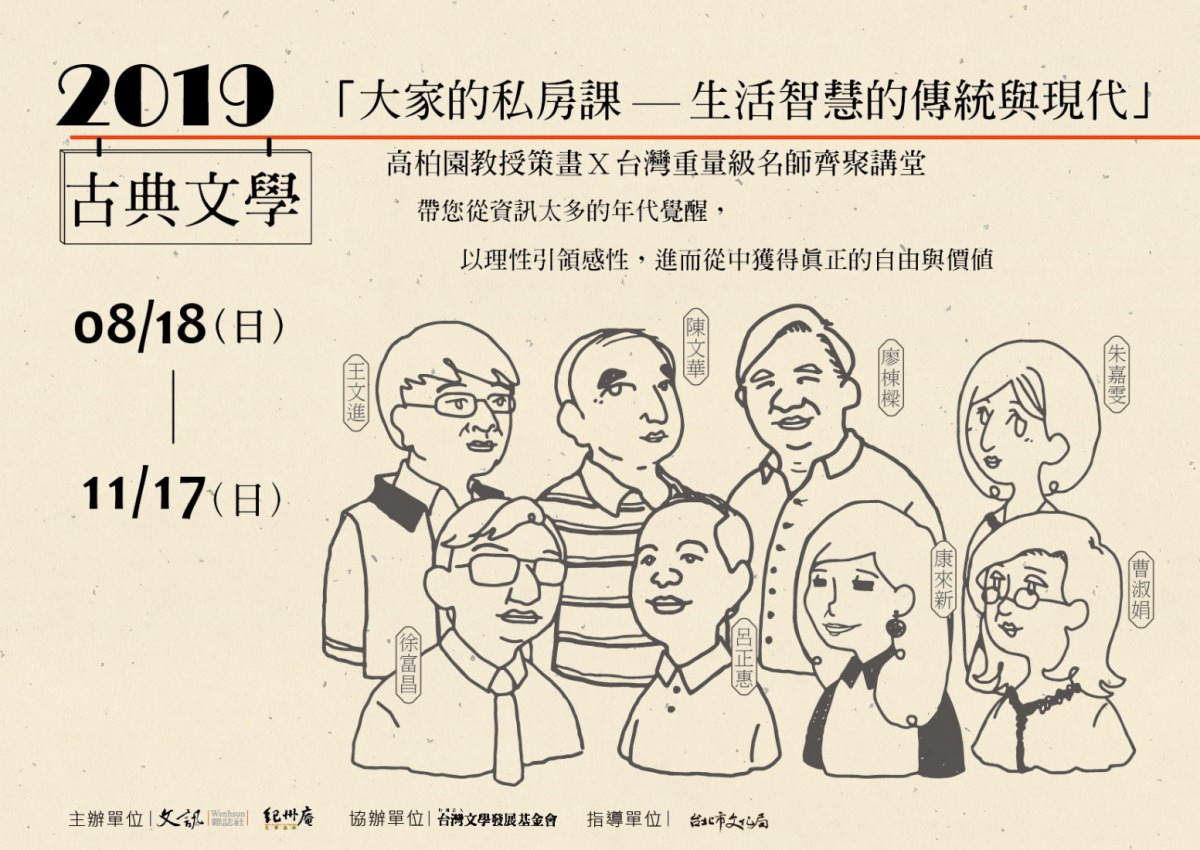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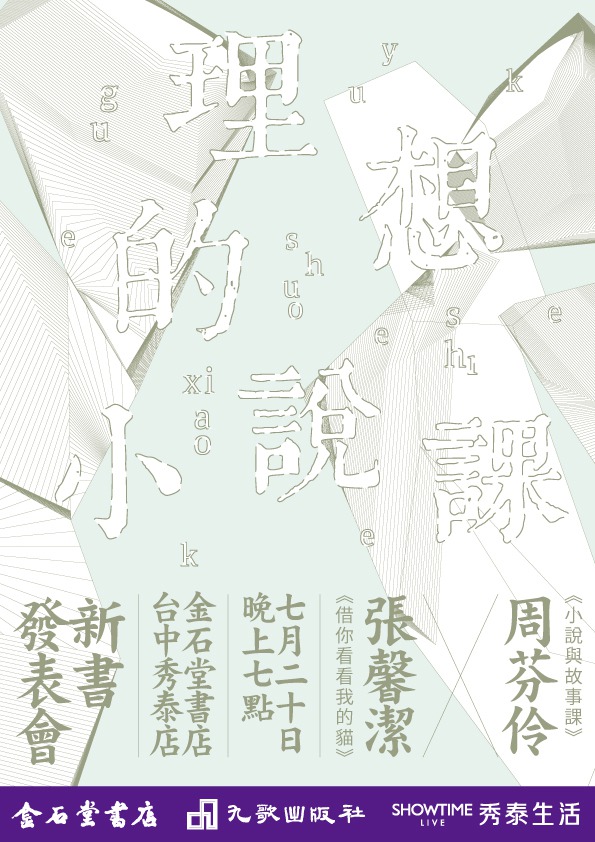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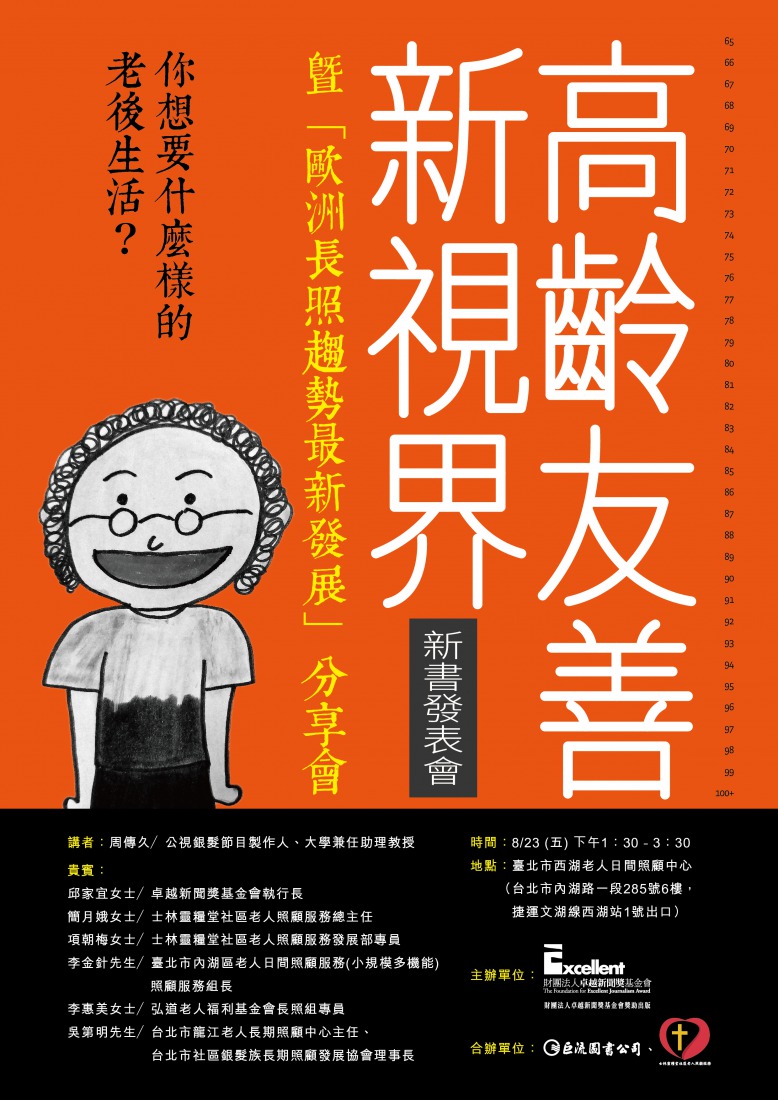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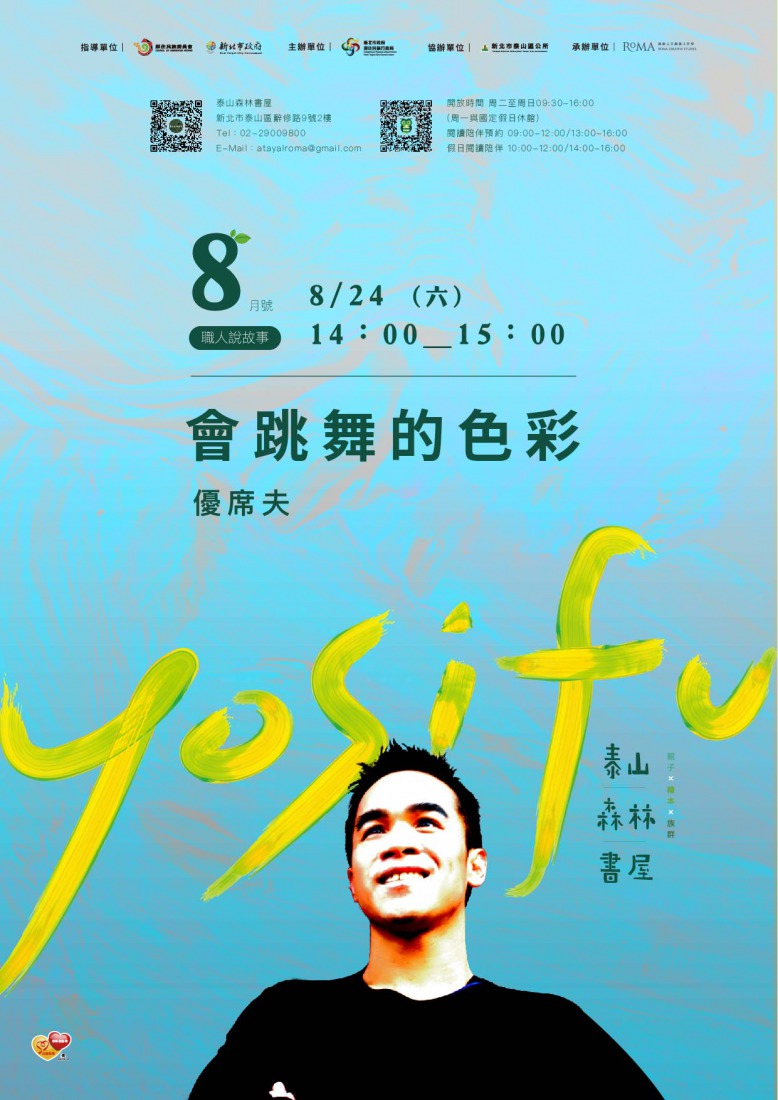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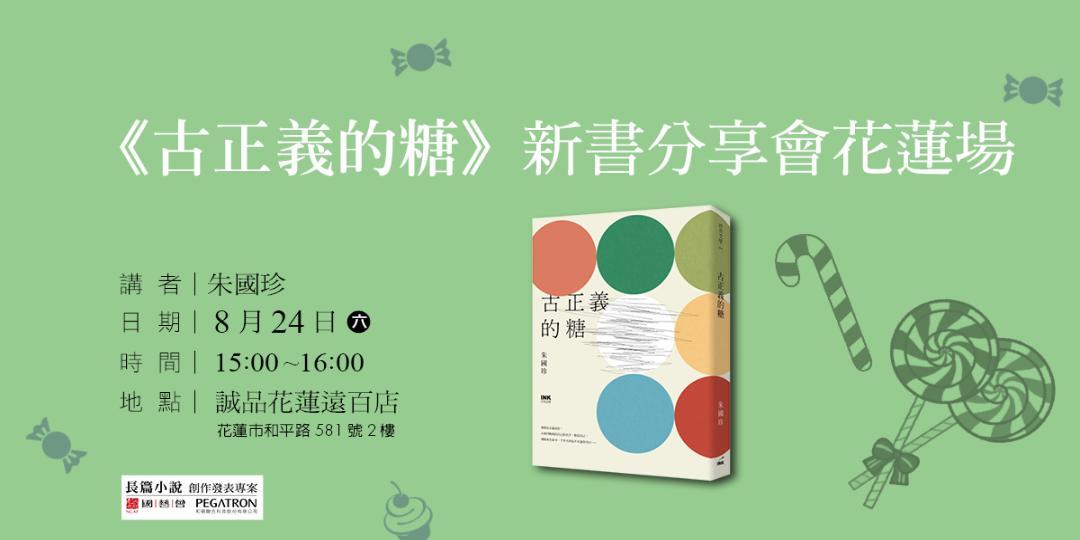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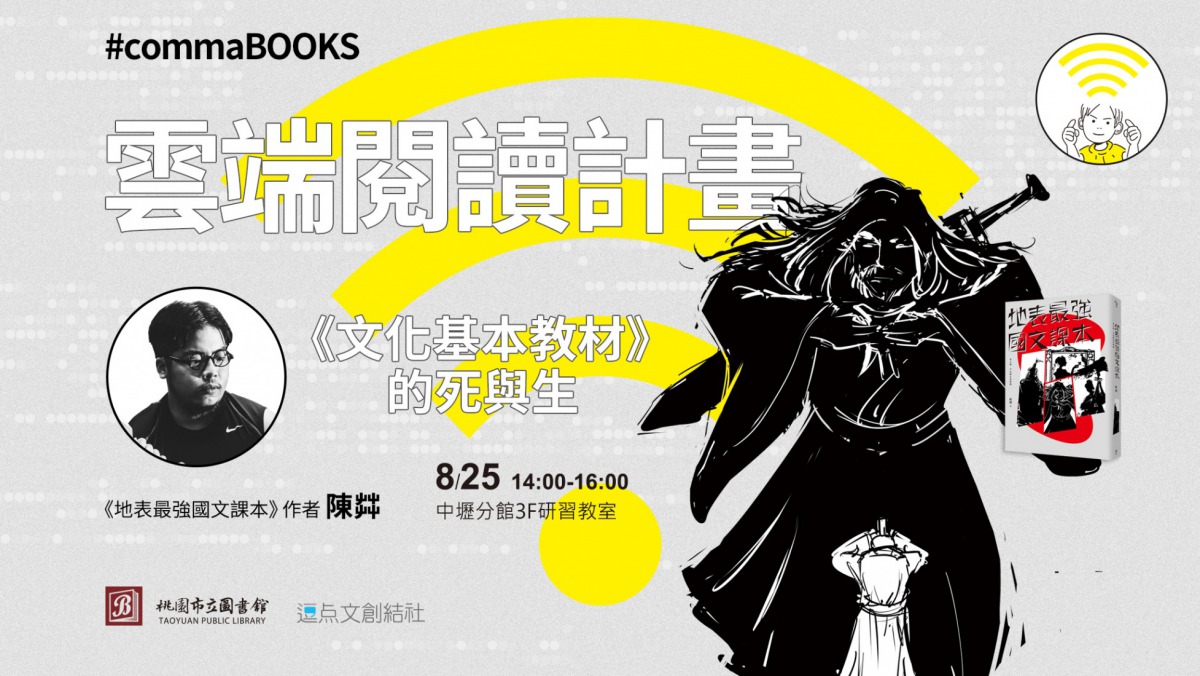
8月繪本大師》用創作寫自傳的圖畫書作家艾倫.賽伊(Allen Say)
隨身帶著艾倫.賽伊(Allen Say)的《Drawing from Memory》和《The Inker’s Shadow》兩本圖文傳記,在德國旅次間閱讀。第一站來到柏林,柏林是個背負著深沉歷史記憶的城市,創傷和重生交織成今日的風貌。班雅明曾在手書的《柏林童年》中,深情回眸幼時片段,那屬於個人生命中的靈光,標誌出這座城市無可挽回的過往,和時代終將消逝的隱喻。
個人的生命史和時代的變動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由班雅明,我想到賽伊於1994年獲得凱迪克大獎的作品《Grandfather’s Journey》,這本書是我認識這位創作者的起點。全書以27幅相同大小的圖畫組成,一張張類似人像照片的寫實水彩畫,閃動著流利淡雅的光影,組合成一本家族相簿,述說著賽伊家祖孫三代流離變遷的經歷。
圖畫中的人物表情大多若有所思,眼神幾乎沒有交集,像是被相機拍攝下來的停格靜態畫面。簡約的文字默默地連貫起這些「決定的瞬間」,反而使得讀者對圖像縫隙之間的弦外之音更加好奇。這本看似極端安靜的書,帶著強大的後座力,讓我一本、一本追隨賽伊創作的腳步,也因而發現:賽伊的每一本書,都像一塊心靈拼圖,記錄了他生命中的某一個片段。
賽伊原本的姓氏是清井(Seii),日文名浩一(Koichi),父親是個韓國孤兒,由居住上海的英國家庭扶養長大,母親則是出生在美國舊金山的日裔美人。在他1999年出版的《Tea with Milk》中,細述父母親的身世和兩人相識相戀的過程,深刻描繪這兩個擺盪在異文化之間的年輕人,身處於祖國卻好似異鄉人的困頓心情,和他們相濡以沫的情感。
賽伊於1937年8月28日出生在日本橫濱海邊的一個小漁村,童年玩伴大多是漁夫的小孩。媽媽害怕他會掉到海裡,總是把他留在家中禁止外出。在正式入學前,親自教他讀書識字,這使得賽伊在孩子群中特別受歡迎,就像他2005年的作品《紙戲人》(Kamishibai Man)一樣,可以讀漫畫書、說故事給小朋友們聽。
媽媽的策略成功了,他整天在家看漫畫書,於是就畫了起來,才四、五歲,心中已暗自決定:長大之後要成為漫畫家。心思敏感、善於觀察的賽伊,畫著眼前所見到的,以及想像中的一切,還不斷複製漫畫書中的圖畫。畫畫的時候他總是特別開心,完全不需要玩具、朋友或父母親的陪伴。他的父親為此很不高興,他期待賽伊成為「有用的人」,將來要自己賺錢營生。在父親的觀念裡,藝術家大多懶惰、邋遢,而且不值得尊敬。
每天只要父親出門去東京工作,賽伊就開始畫畫,然後在父親回家前把畫藏起來。1941年二戰轉劇,炸彈開始空投在賽伊居住的城市,母親帶著他和妹妹早苗(Sanae),疏散到廣島附近的鄉下,寄居在母親的伯父家。老宅中獨居的嚴厲老人讓賽伊又害怕又好奇,也成了他1974年出版的《Once Under Blossom Tree》的靈感來源。
4年之後,戰爭結束,然而一切也都毀滅了,橫濱的家已經毀於戰火,就在1945年8月他8歲生日時,美軍進駐日本。父親在九州佐世保找到工作,全家移居過去。小學六年賽伊唸了7間學校,常常得適應新的學校和老師,自然成為被同學欺侮的對象。只有小學一年級的導師森田稱讚他有畫畫的天分,在此之前從來沒有人這麼說。森田還把他的畫送去參加比賽,得到了第一名。
日美和平了,但賽伊的父母親卻離婚了,家庭的破碎讓他經歷了無限的痛苦。父親帶著他和妹妹離開母親,很快有了繼母。他想念在橫濱工作的媽媽,11歲時,媽媽將他接過來,安置在東京的外婆家,但長久獨居的外婆不喜歡和賽伊同住,總是說:「你又在畫畫了!」口吻就像他父親一樣,認為藝術家不值得信賴。
最後外婆提出交換條件:如果他能考上知名的私立中學,會另租一間公寓讓他自己住。入學考試非常困難,但想到可以一個人盡情畫畫,這個提議對賽伊非常有吸引力。就在13歲生日前,他搬進被他視為「藝術工作室」的簡陋住所,狂喜地投入人生另一個階段,《Drawing from Memory》書封上,那個凌空漂浮的少年,正是他當時心情的寫照。
在賽伊的心裡沒有「讀書」這件事,他經常自己寫假單翹課,沒日沒夜地躲在斗室裡不停畫著。直到有一則新聞觸動了他:有個大阪少年為了學習漫畫逃家,走了16天到東京,被漫畫家野呂新平收入門下。賽伊從小最喜愛的漫畫家正是野呂,小學一年級開始就看他的連環漫畫。偷偷收藏的漫畫書是不能讓父母發現的祕密寶藏,從書中他看到人生的第一隻恐龍,還有許多超自然的生物,都深深震撼了童稚的心靈。
於是賽伊登門請野呂大師收他為學徒,除了上學,13到15歲這段青春歲月,他都在老師的工作室度過。對這個失去家庭溫暖的少年來說,野呂既是教導他畫畫的老師,也是他心靈上的父親,形塑了他日後對藝術的態度和人生理念。賽伊於1979年出版了文字書《The Ink-Keeper’s Apprentice》,在2011年又重新繪寫為圖文書《Drawing from Memory》向老師致敬,也記誌這一段持續終生的師生情誼。
好不容易生活略為安定,父親突然要求賽伊和他的新家庭一起移民美國,猶如生命中的海嘯席捲而來,不覺步上了家族輪迴的宿命。賽伊為此非常猶豫和恐懼,老師卻鼓勵他:「旅行是最偉大的老師。」
帶著老師的教誨「每一次的畫畫不只是練習,而是發現的過程。」16歲的少年決定勇敢跨出探索的腳步。離開日本的前一晚,他燒毀了累積數年的素描和畫作,準備好做一個自由人,到新世界去追尋夢想。
1953年的夏天,賽伊剛在加州上岸,父親給了他10元美金,丟下一句「別讓我丟臉!」就把他送去一所朋友開設的軍事訓練學校。賽伊是唯一的非白種人,年紀比同學都大,英文程度只能看懂童書,口語表達也不流利,自然受到同儕的排擠。他必需兼做雜役,好負擔食宿,他住在儲藏室裡,卻想像那是梵谷作畫的房間。在那段孤絕的日子裡,他只能偷偷畫畫。他不知道自己是誰,有時他化身成野呂筆下連載漫畫的角色Kyusuke,自己和自己對話、爭辯、逃避痛苦的情緒……
賽伊越來越嚮往見到「真正的」美國,一年之後,他帶著簡單的行李和野呂送他的畫具箱逃離了軍校,終此一生,賽伊對暴力和戰爭深痛惡絕。這時,無情的父親和他斷絕了父子關係,走投無路的賽伊決定放手一搏,他走進小鎮裡的高中,要求校長讓他入學。素昧平生的校長傾聽了他的請求,讓他跳級4年讀高中,還安排他到印刷廠打工。賽伊後來回想起來,都覺得這是不可思議的美國夢。
高中藝術課老師非常欣賞賽伊繪畫的才華,特別為他申請了週末到洛杉磯進修藝術課程的獎學金,他因此結識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也開拓了藝術的視野。賽伊的人生行路或許顛簸坎坷,但若沒有這些貴人的無私相助,他能絕處逢生,成為世人所知的藝術家嗎?
高中畢業後,賽伊迫不急待向舊金山出發,那是母親珍愛,卻再也回不去的出生地。從藝術設計學院畢業後,賽伊曾返回日本,還發誓再也不回美國,但日本已不同往昔,再度回到美國後,他當一名看板畫家的助手,後又進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修習建築。2000年出版的《The Sign Painter》,就是當年賽伊在現實和理想之間擺盪的寫照。他在這本書中援引了美國當代藝術家喬治亞.歐姬芙(Georgia Totto O'Keeffe)、諾曼.洛克威爾(Norman Rockwell)和愛德華.霍普(Edward Hopper)的圖像和風格,顯示出他對美國文化的認同。
1962年賽伊被徵召入伍,到德國服兵役。兩年役期間,他對攝影產生了莫大的興趣,退伍回到加州後,從事商業攝影的工作。朋友們一直鼓勵他畫插畫,於是在1972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圖畫書《Dr. Smith’s Safari》。1974年出版的《Under the Cherry Blossom Tree》是一則日本民間故事,插圖充滿了日本文化的元素,受限於當時的印刷條件,賽伊只用墨色作畫,但生動的線條非常引人入勝。
賽伊曾說,他常常分不清楚事實和夢境,記憶中每件事似乎都是真的,但沒有一件事是準確的。最精彩的例子就是:1982年他出版《The Bicycle Man》時,帶著新書回日本參加小學同學會,當他提起書中寫到的那兩個美國士兵,曾向校長借腳踏車,在學校的運動會場表演特技的往事時,竟然沒有一個人記得這件事。同學們笑他好似去龍宮復返的浦島太郎,記不清前塵往事。只有賽伊心裡明白,身處於一個已經失去過往的世界,他的童年只存在他的腦海裡。
在賽伊的記憶寶庫裡,儲存著各種知覺的影像,藉著放大、縮小和拼貼各種手法,加以改變之後,將它們穩妥地安置在他的作品中。於是賽伊不斷挖掘深層的內在,享受反覆述說它們的樂趣,那些帶有夢境及潛意識色彩的情節,混合了傳記元素和幻想,加上他對視覺精確的掌握和經營,呈現似真似幻的圖畫故事,創造了一個介於虛實之間的閱讀世界。
1984年由Ina R. Friedman執筆,賽伊負責插畫的《How My Parents Learned to Eat》出版,談的是東西文化的交融。這是他首部全彩的作品,卻因為不滿意印刷出來的顏色效果,讓他失望挫折到決定要放棄插畫,繼續從事商業攝影工作。
若沒有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Houghton Mifflin)的編輯羅倫(Walter Lorraine)慧眼識英才,就沒有賽伊以圖畫書展開的第二人生。羅倫鼓勵賽伊重拾畫筆,由Dianne Snydere改寫日本鄉土傳說,1988年出版的《The Boy of the Three-Year Nap》得到了凱迪克銀牌獎和波士頓環球號角書獎的肯定,這時賽伊已經51歲了。在這份殊榮的鼓舞下,賽伊完全退出攝影界,全心投入兒童圖畫書的創作。
除了探索自己的生活和記憶之外,賽伊還寫繪過廣泛的主題,《A River Dream》和《失落之湖》(The Lost Lake)尋找失落的天堂;《中國鬥牛士王邦維》(El Chino)藉著華裔鬥牛士王邦維的自傳,探觸如何克服文化和身體的刻板印象;《Stranger in the Mirror》關心年齡歧視和老齡化的議題;《艾瑪的毯子》(Emma’s Rug)探索藝術創造的源頭;《艾莉森的家》(Allison)是一個跨文化家庭收養的故事,傳遞了賽伊對「家」何以組成的信念;《紙戲人》(Kamishibai Man)則是他對已然消逝的傳統文化,無限的緬懷和敬重。
洛杉磯日裔美國人國家博物館(Japanese American National Museum)曾於2000年為賽伊舉辦插畫展,當時館內正展出二戰期間日裔集中營的照片。自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對日本人有深深的敵意,即使已經是美籍的日人,也被視為敵方,許多日本移民都被送進愛達荷州、奧瑞岡州的集中營。同樣身為離鄉背井的移民,賽伊被這段歷史深深撼動,因此創作了《Home of the Brave》和《Music for Alice》二書,他對往事的回顧不再侷限於小我,更擴及國族的集體記憶。
《追憶似水年華》作者普魯斯特認爲:人的生活只有在回憶中才形成「真實的生活」,回顧是和遺忘的抗爭。賽伊為了力抗記憶的如煙消逝,將自己的經驗化為故事,並從中梳理出脈絡,組合進自己的世界觀,因此他稱自己的作品為「真人實境的虛構故事」。這些故事連結了他的想像力和夢想,激發了他追求生存的力量,讓他漂流在異文化中不致滅頂,在反覆提問「我是誰?」時,尋得自己的主體認同。
賽伊在創作一本新作品時,並非事先安排故事大綱,而是不停地塗鴉,先畫上百張草圖,再從其中產生構想。他早年的畫風常運用漫畫手法,在接受學院的訓練後,他純熟掌握西洋畫的技巧,但無論在構圖或設色上,都仍可見到來自日本畫的傳統。1994年他獲得凱迪克獎的殊榮,他是唯一得到這個獎項的日本人,並不是因為他的作品帶有異國風,而是他創作的圖畫書,真正搭起了文化溝通的橋樑。
導演費里尼曾說:「一切藝術都是自傳,珍珠,是牡蠣的自傳。」牡蠣因為傷口的刺激,拚盡全部的力量療傷,成就了晶瑩璀璨的珍珠,對賽伊而言,他用畫畫寫日記,他的書是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經由創作的淬鍊,這個曾經受傷的靈魂,得到了療癒和昇華。他創作的每一本圖畫書都是他的自傳,都是生命中無價的珍珠。●
【2/6國際書展講座】書寫、行動與反思:和島嶼互動的幾種方式
閱讀通信 vol.366》為什麼要叫勇者,不叫英雄?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