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短評》#542傾聽失去與收穫的極品好書懶人包
●採莓人
The Berry Pickers
亞曼達.彼得斯(Amanda Peters)著,祁怡瑋譯,木馬文化,480元
推薦原因: 議 文 樂
小說以一位莓果園女孩的失蹤為引,帶出家族記憶、原住民文化、世代繼承、階級矛盾、文化歸屬的失落課題。作者以最直白的敘事展現說故事的能力,不讓上述社會議題凌駕人物的塑造、情感關係的幽微深刻、以及字裡行間透露出的酸甜香氣。【內容簡介➤】
●大凍卵時代
一場關於選擇、控制與生育自由的真實故事
The Big Freeze: A Reporter’s Personal Journey into the World of Egg Freezing and the Quest to Control Our Fertility
娜塔莉・蘭珀特 (Natalie Lampert)著,蔡丹婷譯,感電出版,520元
推薦原因: 知 議 樂
這種昂貴的生殖技術,雖然還不算是一般選項,卻已然是種選項。作者以身試凍,痛並觀察著:生殖焦慮、身體自主、醫療話術、資本操弄⋯⋯各路議題盤根錯節,纏繞出一部美麗新世界的紀錄片,《你的卵子不是你的卵子》。【內容簡介➤】
●莉莉安娜的夏天
Liliana’s Invincible Summer: A Sister’s Search for Justice
克莉絲蒂娜.里維拉.加爾薩(Cristina Rivera Garza)著,賴懷宇譯,二十張出版,480元
推薦原因: 議 文 樂
這部姐妹長情的悼念文,如詩如咒,繾綣召喚出莉莉安娜的亡魂與短暫的一生。所有的憤怒與不解,交纏成漩渦般的連環詰問,以注定的無解,直戳墨西哥令人髮指的厭女謀殺——而這並非墨西哥的專利。【內容簡介➤】
●不乖乖
林巧棠著,時報出版,400元
推薦原因: 文 樂
女子成長的異類感,補不完的習,霸不完的凌,抗不完的議,再怎麼想融入,也還是格格不入。寫作太容易憂鬱,而憂鬱又是文學既有的迷魂配方。直視深淵,躍入深淵,以至於成為深淵,多美好的有病呻吟!文明向來是種病。【內容簡介➤】
●洪箱與土地正義
朱淑娟著,巨流文化,460元
推薦原因: 批 議 益
熱愛種田卻無田可種,洪箱之走上街頭,動機單純,語言直接,格外有力。不僅暴露了土地政策的急功近利,也為沉默的農民道出積壓既久的怨怒。本書記錄她生前十餘年間的抗爭歷程,一頁頁揭穿官商如何巧立名目,蠶食鯨吞我們腳下這片已然破碎瘡痍的家園。【內容簡介➤】
●以為無人傾聽的她們
台灣首部人工流產文集
吳曉樂編,游擊文化,520元
推薦原因: 思 議 益
這部文集結合短篇小說、詩、獨幕劇、訪談口述、法律分析、「墮胎」史研究、醫療經驗,為「人工流產」與女性身體發出史無前例的重要聲音,也為這一複雜經驗留下細緻的討論。虛構創作與法律醫療並置或許突兀,但卻是擴充敘事的重要安排,能讓子宮、生育離開被規訓的場域與論述,回到人生經驗與感受中被安放。【內容簡介➤】
●她們的選擇
關於人工流產,作家們想說
Choice Words: Writers on Abortion
安妮.芬奇(Annie Finch)編,聞若婷、夏菉泓譯,游擊文化,560元
推薦原因: 批 思 議 文 益
這部文集的可貴之處難以言喻。文學善於處理各種傷痛與失去,然而在古今中外的文學史中卻僅有這一部處理人工流產這個重要主題。此書帶有豐富的跨文化、跨文類書寫,將世界各地的女人在成為母親之前的身體經驗、生命體驗相互連結、並打開想像。這部文集同時指向生與死,並給予兩者一樣的重要性,善待在生死間掙扎的人們。【內容簡介➤】
●樹說時間的故事
一部跨越千年的生命史詩,述說自然共生、氣候變遷與人類未來的啟示
Twelve Trees:The Deep Roots of Our Future
丹尼爾.路易斯(Daniel Lewis)著,嚴麗娟譯,商周出版,480元
推薦原因: 知 議 樂 益
作者以12種樹木為時光機,穿越地球悠遠的歷史長河。融合植物學、歷史、人類學、地球科學……等諸多領域,以多重視角探查樹木與人類錯綜的關係。說明樹木在人類世界所扮演的角色,銜接自然造化與人類文明,呈現出視野壯闊的「看樹」方式。這一場爬上樹梢,踏上落葉的踏查,除了是自然與知識交織而成的探險,也引領我們重新思考時間的尺度,以及我們與這個星球的連結。【內容簡介➤】
●小廖與阿美的沖印歲月,還有攝影家三叔公
廖瞇著,遠流出版,400元
推薦原因: 議 樂
沖印藥水的氣味,燈下修片的側影,快速沖印的繽紛未來感,作者透過小廖阿美的照片人生,重述那個溫厚勤懇的時代,順道也拉出背景中的攝影沖印史。樸實直白的撒嬌文,深埋著對父母家族的感念,讓人也想把抽屜裡的家庭相簿拿出來重溫一下。【內容簡介➤】
●怪城少女
劉思坊著,時報出版,480元
推薦原因: 文 樂
台灣文學中不乏以1980-90年代、台北時空情境為背景的作品,對於都市精英、政治核心、消費文化,乃至社運能量的捕捉有一定的累積。《怪城少女》橫空出世,寫蛋黃區的前世、房市的復興、階層的流動,寫托爾斯泰式尋常人家的幸福與不幸。小說以迷人怪少女為主述者,雖然在每個故事段落唱著時代當紅流行歌,但以靈異奇想重新編曲,或在勵志向上的心靈雞湯中,滴了一滴紅藥水,讓台北這座城市的局部景觀,成為小說的華麗舞台。【內容簡介➤】
知識性.設計感.批判性.思想性.議題性.實用性.文學性. 閱讀樂趣.獨特性.公益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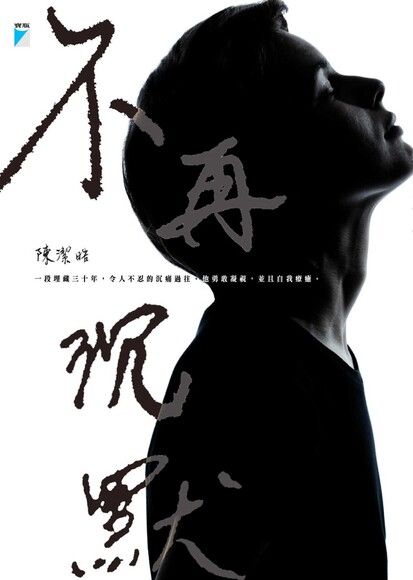 陳潔晧:那就是成長。創傷發生在成人身上跟發生在小孩身上,有一種絕對性的差異在於,他們的韌性不一樣。譬如說,成人的身體、心智已經長成,受到傷害或打擊時,有相對足夠的資源去處理它。
陳潔晧:那就是成長。創傷發生在成人身上跟發生在小孩身上,有一種絕對性的差異在於,他們的韌性不一樣。譬如說,成人的身體、心智已經長成,受到傷害或打擊時,有相對足夠的資源去處理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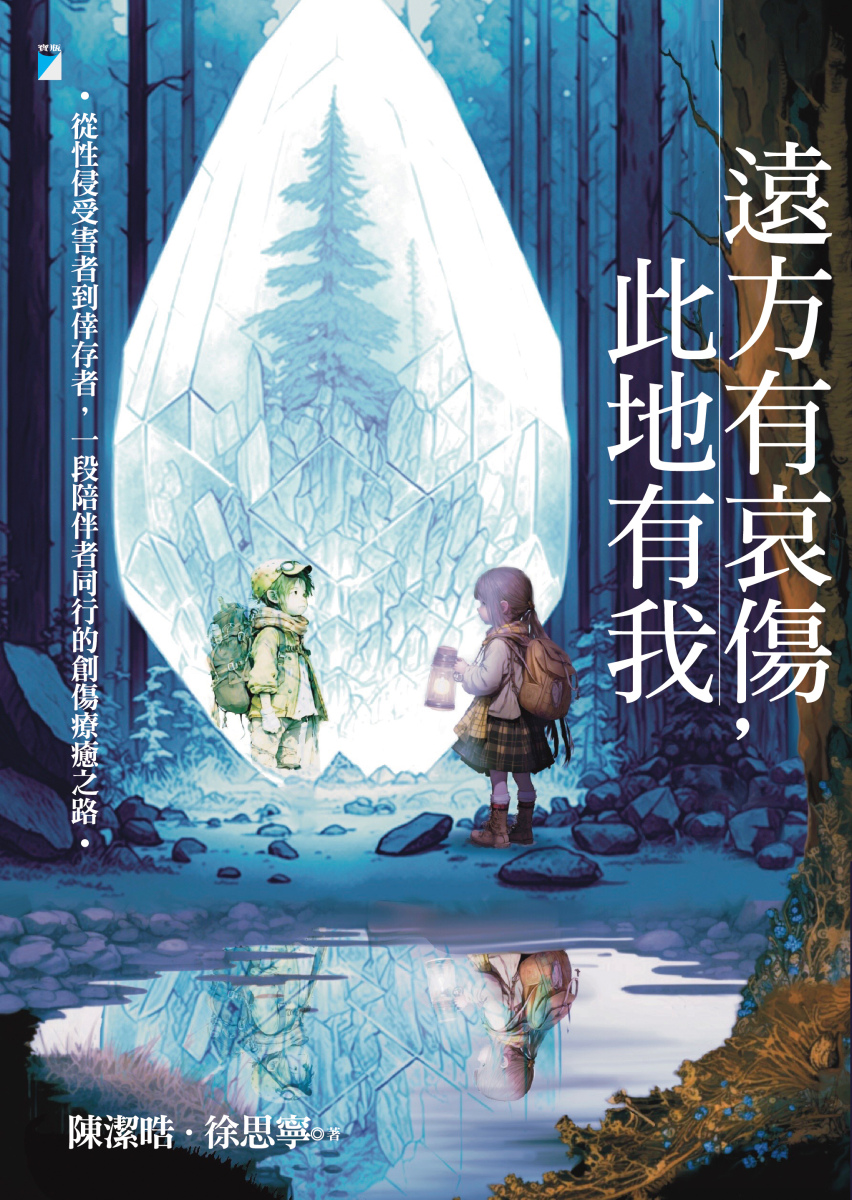 主持人:那麼在復原的過程裡,文字書寫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主持人:那麼在復原的過程裡,文字書寫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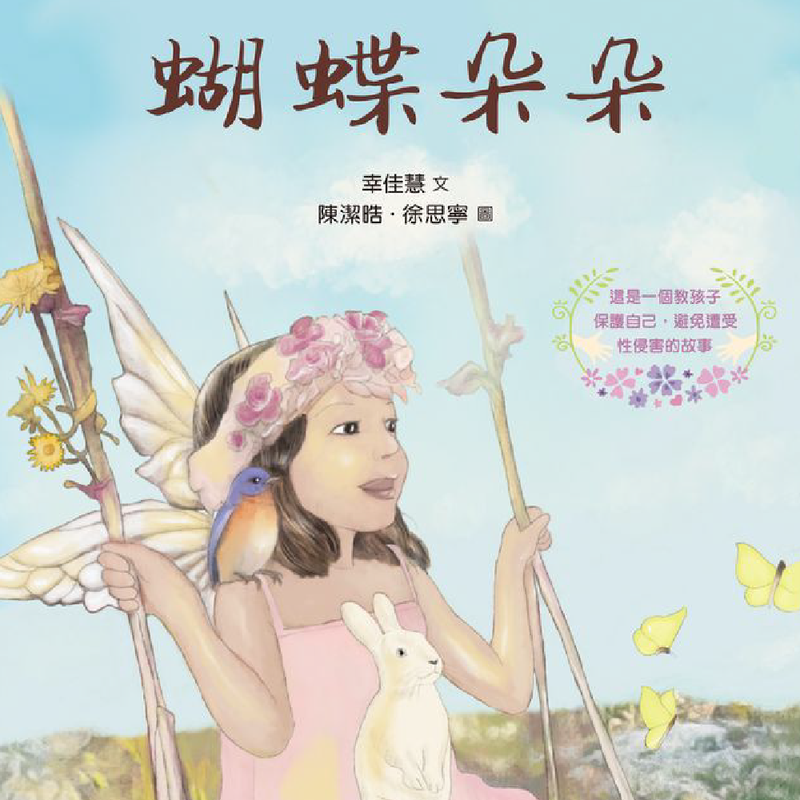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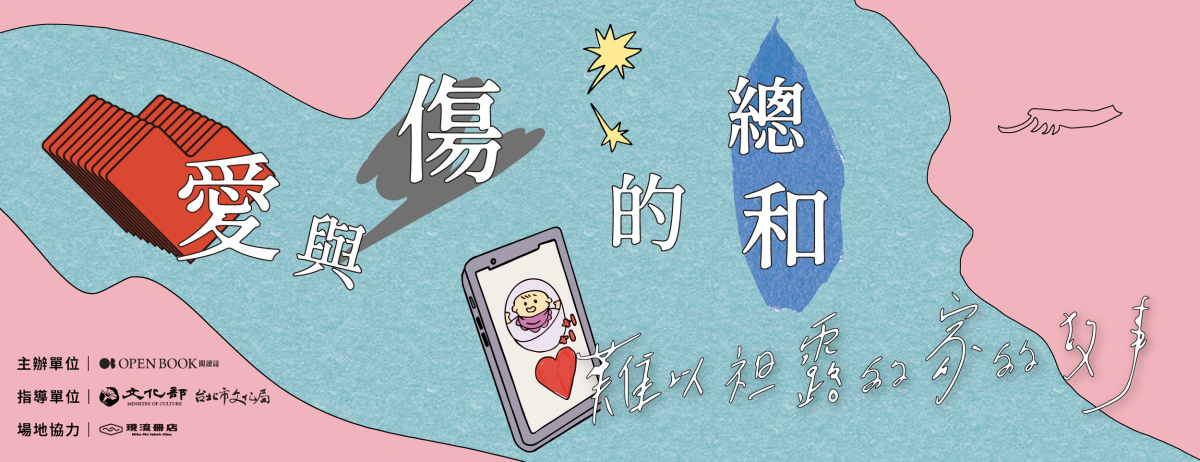

話題》有那麼多Vlog還讀旅行文學幹嘛?馬可孛羅旅行文學講座行前精華 ft.阿潑、山女孩kit、曹馥年、林玉菁
➤阿潑:在旅行的角落遇見國家黑暗歷史
許多關注文化與認同議題的讀者,書架上都有一本《憂鬱的邊界:一個菜鳥人類學家的行與思》,阿潑以人類學的視角走訪東亞各國,從台灣人的身分,探詢人們在各種「跨境」的情境中,呈現的複雜連結,反思我們看待自身與世界的方式。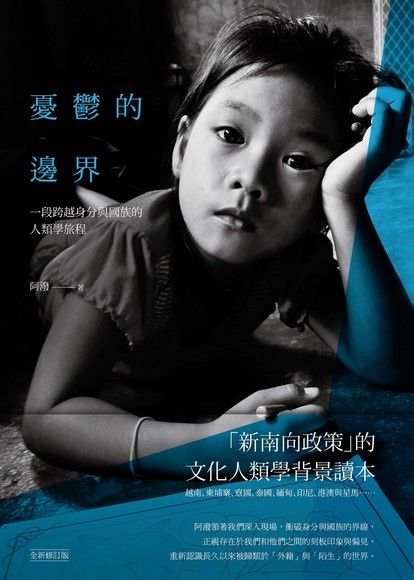
阿潑表示,其實在開始旅行的那幾年,看到的都是光明、榮耀的面向,直到她在柬埔寨金邊探訪,一個不起眼的普通小學,卻是知名的虐殺之地「S-21集中營」,而她遇到的當地人,對此竟一無所知。阿潑沒想過「一個國家的人對於自己國家曾發生的事可以這麼陌生跟訝異」,後來想想,台灣人其實也對自己的土地歷史感到陌生,反倒是有資本離開家鄉的外國旅人,透過探索陌生之地,比當地人更清楚國家的黑暗歷史。「這種奢侈感,可能就是促使我一直書寫旅行過的國家的歷史災厄、黑暗悲劇的原因吧。」
「作為一個記者,我看重的是現場經驗與口述,這反映的是此時此刻此地,與此人此事相遇的狀態。」這是阿潑對於自己與採訪、田野及旅行地的關係描述。然而,僅憑「此時此地」,並不能說清事情的脈絡經緯,因此文獻資料的補充,就像架設舞台,讓「現場經驗」發揮得當,使記述產生意義與深度。
無論旅行文學或者阿潑鍾情的亞洲議題,也都奠基於不分男女、各有特色的前行書寫者及作品之中,例如:《幽暗國度》、《一切未曾逝去:越南與戰爭記憶》、《世界的盡頭:從西非到近東,從伊朗到柬埔寨,一場種族與文化衝突的見證之旅》,與《普丁的國家:揭露俄羅斯真實面紗的採訪實錄》……等,都是她的推薦書單。
阿潑將以「一切未曾逝去:亞洲的黑暗歷史記憶」為講座主題,談談那些「承載歷史皺褶、人民悲喜的土地:這些人可能被迫旅行,但也可能終生都無法離開。」她表示,連結彼此、互相了解、進一步對話與關懷,或許正是旅行文學在這個時代可扮演的角色。
➤山女孩Kit:從旅遊書寫長出的小說創作
山女孩Kit的登山起點,最初來自療癒喪親之痛的起心動念,從家鄉北投的山,到走入世界各地的山徑,至今已11年。她總是從機場直奔登山步道口,旅行主題幾乎圍繞著「山脈」,反倒不一定會在城市停留。她形容自己是「崇拜親臨現場的體驗者」,只有抵達現場,才有辦法描述土地。因此,她習慣在移動中書寫,「飛機上、背包客房的上鋪、巴士的等候區、轉機的深夜。說穿了,就是在各種移動中,仔細地紀錄以獵人的眼睛捕捉到的微小差異,而那算不算文學,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其實,Kit的小說作品《腹語山》場景靈感,就來自於她2023年在安納普納大環線攀登時,經歷的雪崩。當時她聽見由遠而近、尖銳如笛的風聲,遠方有大片灰霧迎面而來,如不閉上眼睛,角膜很可能被夾帶冰晶與塵土的風雪刮傷而失明。她當晚細細記錄的情景,成為後來書中女主角翻越喜馬拉雅山的重要情節。這也是他她常推薦《山稜上的無名英雄》的原因,更可以理解這段艱辛而偉大的歷史。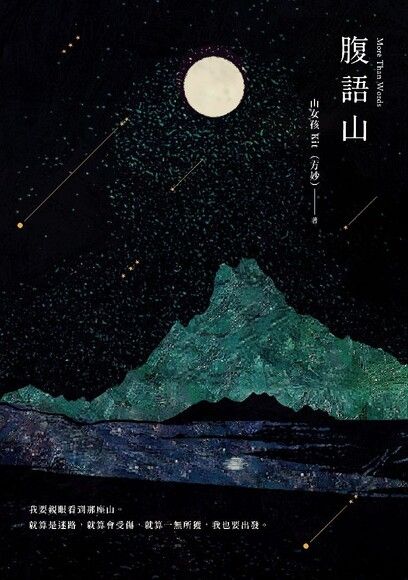
無論旅遊或攀登,女性在體力或心理上,都承擔更多無形壓力,也因此,Kit格外珍惜途中遇見的各種女性。她認為,男性創作者通常更著重戶外活動的異地冒險、陌生探索,而女性創作者的作品中,則更多描述人與人的互動情感,像是旅途中或步道中所遇之人的對話。
Kit過去的分享,大多圍繞在實務型的主題,例如:女生獨旅的裝備、如何藏好現金……等。有趣的是,她發現自己有一群不從事戶外活動的讀者,但他們卻能從自己的作品中有所共感,或許正是因為寫出了自我追尋過程的迷惘與矛盾,產生了共鳴。她的講座場次,將以「難以抵達的地方:出發是為了與自己相遇」為題,分享自己每次出發所聆聽到的「遠方鼓聲」,以及旅程中影響她的那些作品。
➤曹馥年:從世界盡頭出發抵達家鄉
曹馥年是一位調查記者。在追逐他人故事多年,她留職停薪一年,開啟了一場她稱之為「奢侈的逃避」的環球旅行。然而她發現,即使到了世界盡頭,亟欲逃離的事物並不會因為一趟遠行而消失。她在西班牙的青年旅館內,聽到其他背包客分享,曾在宜蘭外澳度過的長居夏日,而對方心目中這個「亞洲最美的浪點」,對她而言,心理距離似乎比日本還遙遠……
在旅途中,曹馥年意識到自己對台灣不夠熟悉,因此在寫下自己的旅行故事,出版《出發!到世界討生活》之後,她接著啟動「環島讀冊」計畫,藉由描寫全台各地的獨立書店,重新認識自己生長的土地。對曹馥年而言,跑新聞或者旅行,都能滿足她與生俱來的好奇心,新聞報導關注的是「人」,旅遊文學亦是,傳達的是作者體驗與感受,「將過往的經驗、記憶,融合當下所見,用主觀筆法詮釋與表達,書寫時需要大量放入自己,能抒情、能夾敘夾議,比新聞寫作來得自由。」
曹馥年觀察,比起過往,當代的女性旅行者能更自由地探索世界,以記者、登山家、人類學家、母親……等角色,走進長期由男性掌握話語權的場域,甚至深入男性未必能企及的地方,採集到女性能共鳴的聲音。
「女性不再是在家等待的伴侶、被觀看的客體、旅途中的點綴,而是說故事的人。」這些不受時間與空間約束,與作者同遊的「再現」,也是文字所賦予旅行文學的魔法,雖然不即時,卻能涵容更長的時間跨度,帶來無遠弗屆的想像。20世紀初少數由女性書寫的《拉薩之旅》,最能體現這段具有啟發與靈性的過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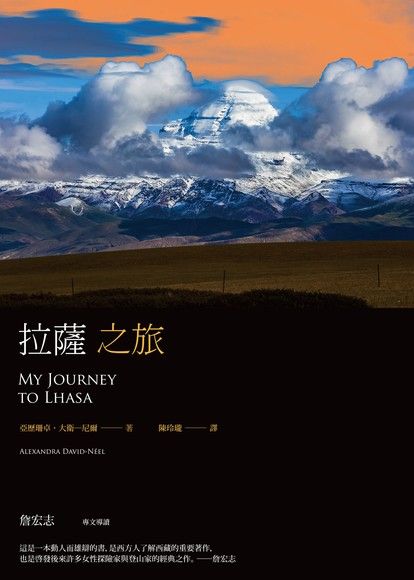
因此,即便社群媒體、短影音資訊大行其道,曹馥年仍偏好以「老派」方式規劃旅程,盡可能藉由遊記與旅行文學認識目的地,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我喜歡藉閱讀建構我對一個地方的第一印象,為自己保留一些初來乍到的驚喜,並將旅途中的見聞與書相互映照。」這也是她將在此次講座中,以「一年環球,一年環島:從旅行到旅行書寫之路」分享的心境與歷程。
➤林玉菁:與多元遊園地呼應的人生作品
攤開林玉菁的翻譯作品,同樣也發現濃厚的亞洲色彩,包括:黎智英傳記、亞洲毒梟集團、東印度公司的帝國侵略、中國海疆的殖民擴張、中國在印度洋的野心、美國在菲律賓等領地的擴張……都是扎實厚重的國際歷史與政治視野。對南亞議題有興趣的朋友,她也推薦《朝聖者的印度》、《拉達克之旅:一場照見內心探索性靈的旅程》、《九樣人生:九個人物,九種生命故事,在現代印度的蛻變風暴中守護著信仰的尊嚴》、《直擊緬甸內戰現場》等書籍。
林玉菁喜歡混亂多元完全不統一的南亞跟東南亞文化遊園地,並且「相信知識、眼光跟腳印得縫在一起。」因此在寫作、翻譯以外的人生,她也是多重身分的國際事務工作者、策展人、研究者。她在劍橋做印度研究,在紐約做政治學研究,也在藝術研究中心、國際與在地的NGO之間,尋找認識世界的多重方式,因為「專注發掘無法發出的聲音,藉以擾動既定的視野與思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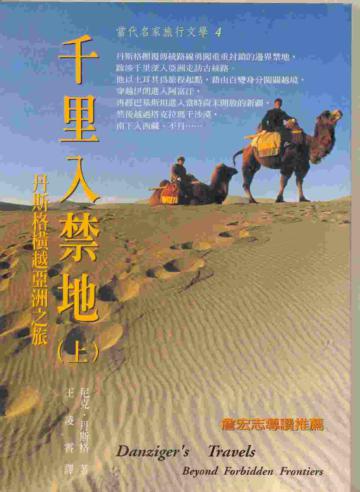
林玉菁以自己人生第一本閱讀的旅行文學書《千里入禁地》為例,這本馬可孛羅創社時期的作品,彷彿回應了她之後多年的人生路徑。今(2025)年6月,她在台灣作家吳明益與印度小說家舒班吉(Shubhangi Swarup)的對談會擔任口譯。二人之中,一位只當過老師與作家,一位則為了寫書曾化身各種身分。林玉菁由此獲得靈感,這次講座,她將以「禁地.聖地:迎向那不容你坐、不容你站,只容你走的每一根刺」為題,分享她多年來,以不同職業身分,進入南亞各國各地,透過寫作與策展,「迎向前方似無路的髮夾彎」的顛簸與風景。
常見的旅行選擇不乏資本主義式的消費,然而攸關人生的旅行,林玉菁以「只容你走」作為註解。無論是旅行、工作或人生,林玉菁都喜歡選擇「長的、慢的、顛簸的、難走的、找不到的、被拒絕的、不知名的路」,並在只容行走的過程中,享受迎風的滋味。●
閱讀通信 vol.369》出烤箱的好日子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