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短評》#281 幽默化解意義重負的極品好書懶人包
●兩個夏天
二つの夏
佐野洋子、谷川俊太郎著,邱香凝譯,木馬文化,360元
推薦原因: 樂
佐野洋子、谷川俊太郎以獨特的畫作、詩文,讓夏天的意象承載記憶,展開時間向度、拉出空間景深。兩個夏天分屬於少女與男人、指向過去與現在,又疊合為女子與少年,開啟的一方同時也等待回應,最後化成死亡的與未出世的、結束的並未開始。兩個靈魂與兩段記憶,在時光流淌過程中的交會,只有一瞬,卻恆久炙熱。【內容簡介➤】
●最美的日本文化名詞學習圖鑑
六大主題、千項名詞,從文化著手,升等素養,擺脫死背,立刻融入日本!
英訳付き ニッポンの名前図鑑:和食.年中行事、和服.伝統芸能、日本建築.生活道具
服部幸應、市田ひろみ、山本成一郎著,周若珍譯,末吉詠子繪,遠足文化,680元
推薦原因: 知 實 樂
本書雖然是靜態的詞條與圖鑑,一眼看去也像是精美的日文單字書,但圍繞飲食、服飾、建築、節慶、傳統藝能、生活用品等6個主題、近千筆的名詞解釋,呈現了「日本文化」4個字內涵的龐大物質細節。對於台灣讀者來說,日常生活已隨處可見的日本文化物件與元素,皆可在書中找到清楚易讀的說明,搭配的日文原文,也發揮語言才能傳遞的符號訊息功能。【內容簡介➤】
●永井荷風江戶藝術論
江戸芸術論
永井荷風(ながい かふう)著,侯詠馨譯,紅通通文化,380元
推薦原因: 知 樂 益
永井以耽美風格的小說為世所知,1952年獲頒國家文化勳章,授勳理由即基於他對江戶文學的研究與西方文學引進之貢獻。台灣讀者可透過這部關於浮世繪、錦繪(版畫)、狂歌、戲劇等江戶時期藝術的評論集,認識永井在江戶文學的足跡。對日本傳統藝術有興趣的讀者,亦可藉由永井溫雅的筆觸與明晰的洞察步入此一世界,下回再看到採用浮世繪圖樣的T-Shirt或參與影視演出的歌舞伎明星,也就能稍知其所以然了。【內容簡介➤】
●論幽默
Humour
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著,方慈安譯,商周出版,320元
推薦原因: 知 思 樂 獨
英國文學評論及文化理論巨擘泰瑞.伊格頓,以自身豐富的學養論說「幽默」的各種元素,從笑做為人這種動物的獨特舉動,到嘲弄、諷刺、雙關語的修辭,脫口秀表演,幽默的歷史變遷、笑的作用等,闡述笑做為社會符碼的表現與意義。英式散文的風格,及行文中對幽默的實踐,時而令讀者會心一笑。
本書不是要告訴你怎麼樣才好笑,而是從各種思考路徑觸探「笑」的符號學與「幽默」的歷史。過往許多討論已經點出:幽默來自期望或規範的悖反。伊格頓試圖解釋為什麼規範被違反後,本來應該帶來不安不悅不協調,卻讓人有愉悅的感覺?而我們(特別是喜劇相聲演員)怎麼知道哪些悖反是有趣的?伊格頓在書裡提供了這些問題的解答,也帶來閱讀的愉悅。【內容簡介➤】
●山林癒
沐浴山林擁抱樹木,借助大自然力量自我療癒
Un bain de forêt - Edition illustrée
艾力克.布里斯巴赫(Eric Brisbare)著,馬向陽譯,奇光出版,460元
推薦原因: 益
姑且不論樹療能有什麼樣的效果、是否真如作者眼中的那樣具性情,本書的確提供了人們一種面對樹木的溫柔,提醒大家,樹不只是林業資源或材料,更是生養於天地間厚實的生命體。【內容簡介➤】
●二次大戰後的野蠻歐陸
充滿復仇、內戰與種族清洗的血腥之地
Savage Continent: Europe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I
齊斯.洛韋(Keith Lowe)著,鄭煥昇譯,馬可孛羅出版,680元
推薦原因: 知
經過一場牽連廣大的戰事,體系與秩序崩解,人和人心也變了。本書談論二戰甫結束的歐洲,但罕見地將焦點置於重建、復員計畫尚未啟動的空窗期,讓讀者直視一個曚昧渾沌令人眩暈的世界。提醒我們,戰爭並未在一方宣告投降的下一刻就消失,生活也沒有在隔天就回到尋常。傷害沒有停止,正邪亦非一刀兩斷、涇渭分明。戰事所帶來的毁滅損害,與隨之而來的復仇,失控且扭曲,讀來慨然心碎,亦發人深省。【內容簡介➤】
●歷史學柑仔店1
歷史學柑仔店作者群著,左岸出版,500元
推薦原因: 知 樂
由學院歷史學者經營的虛擬學術雜貨店,開業6年來首次推出實體精華套餐。將學術語彙與最新研究成果轉換為扼要明晰的述說。讀者服用起來輕鬆,又能攝取豐富的養分,從中體悟到:歷史的確是現在與過去的對話。【內容簡介➤】
●AI之書
圖解人工智慧發展史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 Illustrated History: From Medieval Robots to Neural Networks
柯利弗德.皮寇弗(Clifford A. Pickover)著,林柏宏譯,時報出版,680元
推薦原因: 知 議 樂 獨
AI發展史圖文書。AI竟然能從西元前1300年的井字棋說起!這讓我們意識到,自動機械其來有自,並非人類文明史的空中樓閣。一頁圖搭一頁文,閱讀起來很容易掌握核心內容,但也不免遺憾於這種近似名詞解釋的寫法,可能使得作者欲傳達的脈絡與內涵,消溶於讀者自身的理解中。從西元前125年到1206年之間的歷史紀錄斷裂,也讓人不免感到疑惑,這或許與作者視野侷限於西方不無關係。【內容簡介➤】
知識性.設計感.批判性.思想性.議題性.實用性.文學性. 閱讀樂趣.獨特性.公益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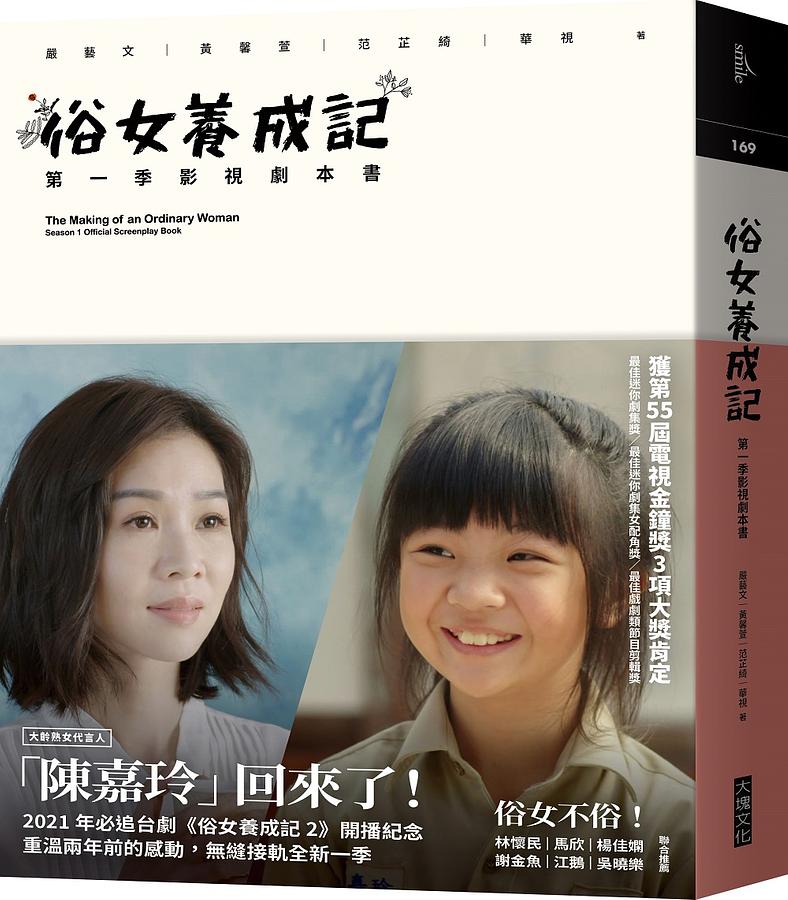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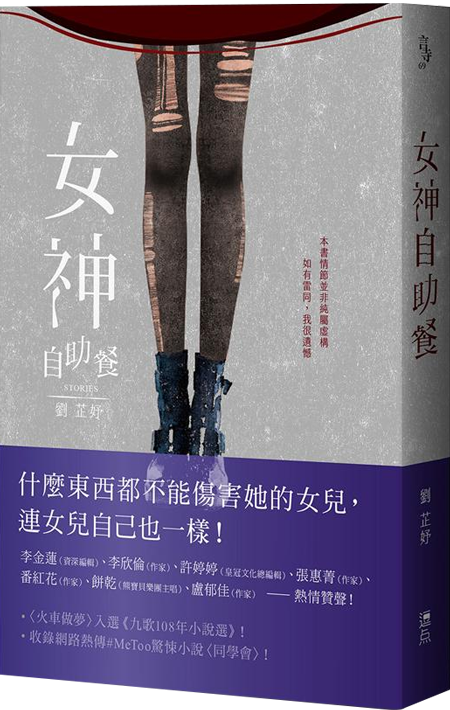
書.人生.何榮幸》「王子書城」裡的魔術師
吳明益以《天橋上的魔術師》重構了台北中華商場的集體記憶,我童年時期的魔術師則住在永康街「王子書城」。只要魔術師揮舞指揮棒,我就會義無反顧踏上冒險之旅,一路隨著文字的魔力起舞,至今仍深深著迷。
如果不是幼稚園時全家搬到台北,對我影響深遠的魔術師,很可能躲在南投埔里的甘蔗田裡,以不同方式牽動我的人生。但來到台北之後,我很快加入都市小孩潮流,成為《王子》雜誌的忠實讀者,這本在1966年與我同年誕生的日式風格雜誌,為我這一代青少年開啟了一扇閱讀的重要窗口。
在母親的鼓勵下,小學五、六年級時我開始投稿到《國語日報》及《王子》雜誌,後者尤其具有神聖地位,因為投稿若在《王子》刊出就能獲得「小記者證」,並享有到「王子書城」買書半價的優惠。
當年記者仍是受到社會肯定與尊敬的行業,儘管不知道記者的實際工作方式,「小記者證」對我仍具有巨大吸引力,召喚我大量閱讀與練筆。碰到星期天以及整個寒暑假,母親都會帶我到永吉路救總(原名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後改名中華救助總會)圖書館借書。我看完一本本文學名著、偵探小說、歷史故事後,就天馬行空自由創作,寫出一篇篇現在很懷疑當時腦袋裡究竟裝了什麼東西的怪文。
我還記得當時在《王子》刊出的第一篇文章名為「孫悟空大戰關公」,詳細內容早已忘光,總之就是一篇穿越時空的小學生版偽魔幻寫實,能夠刊出來應該算是奇蹟。另一篇我早已忘了曾經寫過,但收錄在《王子小記者文選2》書中的文章〈衛星的自述〉,則以第一人稱自剖衛星在天空中的孤單心情。無論如何,我就這樣得到了生平第一張小記者證,充分感受某種飄飄然的喜悅。
有了小記者證,下一步就要展開從永吉路到永康街王子書城的朝聖之旅。對於平常走路上學、很少坐公車的我和弟弟而言,兄弟倆坐公車到永康街是項陌生而特殊的嶄新經驗,但當時我們被喜悅沖昏了頭,根本沒有料到,前往王子書城的遙遠長征,竟然會留下此生永難忘懷的困窘記憶。
那一天,我和弟弟帶著辛苦存下來的零用錢,搭著公車感覺上繞過了半個台北,下車後又摸索走了一段路,終於來到嚮往已久的王子書城。出發之前我已盤算,此行可憑小記者證買下我和弟弟各自渴望的幾本新書,難得大老遠跑一趟,自然每分錢都要用在刀口上。
結果如我所願,我和弟弟在王子書城待了一個下午,把王子出版社幾本新書當場看完,再依計畫把想要珍藏的書單買齊。然而,當我和弟弟心滿意足走向公車站時,發生了一場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劇:我竟然花完了身上每一塊錢,再也沒有餘錢可以坐車回家了。
在無計可施之下,我只好厚著臉皮,像是當年曾經流行的詐騙集團一樣,在公車站牌前逢人就伸手哀求說「沒錢回家」。因為買書而用盡盤纏這件事實在太瞎,我只能臉紅低頭小聲乞討,長征買書壯舉一秒變成黑色笑話,心想我和弟弟大概會跟被看穿的詐騙集團相同下場,一毛錢都要不到而在黑夜走很長很長的路回家。
所幸老天還是眷顧因為買書而回不了家的傻子,在一兩個大人白眼及別過頭去之後,就有一位婦人從皮包拿出銅板,足夠我和弟弟在夜色降臨前上車離開永康街。這次經驗讓我開始相信人性的善良與美好,但也更加印證我的數學是從小時候就很糟糕。
無論如何,「小記者證」就像是已經得到霍格華茲魔法學校分類帽的認證一樣,持續發揮自我感覺良好的催眠效果,讓我深信自己已經跨過記者的門檻。直到多年之後,我才了解喜歡看書寫作跟成為專業記者完全是兩回事,但小記者證在我腦中植入的記者DNA卻伴隨至今。
不僅如此,王子書城、小記者證散發出的閱讀與寫作樂趣,也讓我童年時期的偶像與眾不同。當時常在《王子》刊登文章的幾個熟悉名字,在我心中的地位足以與凱旋歸國的三級棒球隊國手們並駕齊驅。但我從未想過,我和這些童年偶像們勤奮投稿之處,竟然是由「匪諜」所創辦的雜誌。
很久之後我才知道,《王子》創辦人蔡焜霖年輕時因加入讀書會被扣上「參加叛亂組織」罪名,判刑10年後坐監綠島。他出獄後待過多家出版社及廣告公司,然後與多位漫畫家及白色恐怖政治犯「同學」們創辦了圖文並茂的《王子》,還曾義助台東紅葉少棒隊到台北參加比賽。
此刻回首童年往事才發現,我生命中的魔術師其實不住在王子書城,而是只有小學畢業、卻懂得閱讀這件事如此重要的母親。在那個文憑至上、文組學生被認為不容易找到好工作的年代,母親不但帶我到圖書館大量閱讀她自己看不懂的課外雜書,在我收到王子小記者證時更是鼓勵有加,此後一路支持我走上記者之路,我才可能以記者做為一生的志業。
是因為有母親這位魔術師,王子書城才會成為我的童年聖地,王子小記者證才會預示我的未來工作,閱讀與寫作才會伴隨我一輩子。今生今世,我都會在母親編織的魔法裡繼續體驗閱讀與寫作的美好。●
何榮幸
1966年生,台大社會系畢業,記者資歷將滿30年,現任《報導者》創辦人兼執行長。
曾任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第一屆會長、台大新聞研究所第一屆傑出記者駐所講座、台大社會系兼任副教授。多次榮獲卓越新聞獎、曾虛白新聞獎、吳舜文新聞獎、金鼎獎、亞洲SOPA新聞獎等國內外重要獎項。
著有《學運世代》、《媒體突圍》、《彳亍躓頓七十年》、合著《煙囪之島》、《我的小革命》、策劃《黑夜中尋找星星─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等書。
【Openbook國際書展參戰(;・`д・´)】
2/6(五)歡迎加入玩耍!•̀.̫•́✧書寫、行動與反思:和島嶼互動的幾種方式
閱讀通信 vol.367》如果我在晚上九點敲響你的房門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