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射計畫》如果平行時空有漫天火雨:思索以現實材料為基礎的臺漫,對創作的啟發
➤戰爭從不在遠方
終戰80年的現在,生下來就在和平時期的我們,對戰爭其實一無所知。但面對臺海危機逐漸升高,俄烏戰事未息,每天我們都能多多少少感受到,彷彿難以計數的強力炸彈就在身邊倒數計時,讓人忍不住想問朋友:防災包準備好了嗎?
但更多時候,我又會沒什麼理由地樂觀想著,也許這些可怕的念頭都不會成真──就算過去發生過,不容抹煞,難道今天的我們都無法預防,為「最壞情況」按下停止鍵?
作為鍾愛歷史題材的閱讀者與書寫者,戰爭逼使人類在絕境展現本性和求生意志力,以及如何維持人的尊嚴,一直都是最吸引我的題材。但我也非常清楚,礙於有限的經歷(包括生理性別限制),我可能永遠也沒有辦法真正體會將所有人都捲入的戰爭,會有多麼複雜,人在其中想好好活下來,有多麼艱難。
這樣的題材還有很多具體的事物可以描繪,且須一再斟酌:例如逃難的人潮與疏導方案,濺血的駁火衝突,爾虞我詐的情報攻防,輿論的操弄運作,社會經濟秩序倫理崩潰,乃至握有決策權的高層勾心鬥角彷彿永不停歇的表演等等。要處理的材料極多,且彼此拉扯,要擔心露餡的地方也就愈多。
➤虛構盡頭的真實
看到梁紹先《燃燒的西太平洋》滿滿的臺美中各種軍情、武器與政治情勢推演細節,我只有佩服:竟然能這樣呈現距離如此迫近,升斗小民不希望發生(卻非常可能隨時降臨)、更無從設想怎麼展開的戰事脈絡。
漫畫中,有不少當代國際政治人物輪番登場,突顯的是各自政治目的、文化與歷史的立場、觀點。執著或不可能驅散的權力幽魂,透過敘事裡的西太平洋戰場,展現了猙獰與自私的面貌。但書中也閃爍著信念與憂國感的光輝,還傳達了謀略與情報戰的敘事魅力:料敵機先、欺敵、將計就計、追蹤、誤判、逆轉等等。甚至邀請讀者一起鬥智──很可能一個錯誤的或自以為是的判斷,就可能賠上眾人乃至整個國家的命運。
就臺漫的題材來說,這部作品不只是軍武,在政治或者推理類型來說,都是相當少見的創作。以自身專業知識入畫,梁紹先可說是相當具代表性的例子。他過去的職業軍官經歷,以及對國際情勢、軍武科技發展的長期關注,都讓漫畫中的所有虛構情節、戰況的刻畫,擁有令人讚嘆的真實說服力(解放軍的戰情指揮部長這樣喔!?)。我們也得以看到,除了對於當下臺灣處境的擔憂,一位漫畫創作者對於知識材料與現實訊息的解析、化用,能推敲得多深刻,多有趣。前傳《星條旗下:燃燒的西太平洋起始篇》也值得合併閱讀。
我們還看見,漫畫家投入最大的心力做研究功課,最終也成了其他創作者的功課和收藏。

➤史實為體,虛構為用
戰爭題材或許是個比較極端的例子,畢竟有許多可能隨時失控──譬如《燃燒的西太平洋》的關鍵設定之一:無所不在的失控和控制(搶占主導權),或者各種欲望、立場互相傾軋、隨時翻轉的狀況。
然而,即使真實的歷史也未必是循著時間軸不分岔跑野馬的,更何況如今人們更容易懷疑,歷史材料也可能說謊,或者為特定的人或價值服務。但若從不同的角度思考,這是否正是敘事戲劇性的寶庫?
我常常在讀與寫時思考,歷史題材為什麼愈來愈常成為創作者的優先選擇?是因為經過一段漫長的時光距離,能更全面從容地理解?還是那些才幾十年便已太遙遠的人事物,反而有種類似異國的迷人情調?又或者是,那不得不消逝、失去的什麼,擾動了我們心底的缺憾?還是,我們在那些歷史材料中認出什麼,判斷絕對不該從記憶裡拋棄……
或許都是。同時我也感覺幸運,不論是小說或是漫畫,近年有愈來愈多「史實為體,虛構為用」的用心好作品陸續出版,從不同路徑,去思索那些「看不見並不代表不存在」的時代遺痕,曾經對於人們個人史的擾動。這些作品或幽默或嚴肅,不論是重新詮釋或蹈襲既定印象,它們觸及的,卻不約而同:發動戰爭、創造或毀棄歷史的是人;使用武器、被武器傷害和奪去所有的也是人。終究創作者希望完成的,仍是人的故事。

人並不僅是時代或命運的被動棋子。我聯想到另外兩部以「人」或角色的自我覺醒作為主要關注,也做了大量扎實史料功課與講究呈現的臺漫作品:阿獰《蕉兵戰時記》和尚未完結的左萱《芭蕉的芽》。這兩部作品都是「臺北高校創校一百週年(2022)紀念作品」,臺北高校即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位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今址。兩部作品分別呈現不同時空下臺北高校學生的人生片段,《蕉兵戰時記》主要呈現個人面對戰爭時期的無力感與徬徨(其實當時的臺北都不能算是嚴格意義的直接戰場);《芭蕉的芽》則把時間往前推了十多年,著眼於1930年代高校生活的自由多彩,與追求文藝興趣的熱烈浪漫情懷。
在閱讀《蕉兵戰時記》時,我還想到一部相當特殊的日漫《cocoon繭》,可以一起看。許多作品中戰場主角或敘事觀點的男性面對的戰爭殘酷,不外乎死亡、傷殘或前途的毀滅;但對女性來說,殘酷有各種不同形式:肉體傷害,性的暴力,人際信任的動搖,或是對於「純潔」的信念挑戰等等。《cocoon繭》中出現的士兵(男性)全是模糊的白色影子──因為到了戰場上,男性就喪失了個體性;但纖細易感的女性面對的,卻是更加難以承受的世界。
《芭蕉的芽》的敘事主線始終放在「編出一本夢想中的文藝刊物」這樣浪漫的目標,充滿青春光輝,笑點層出不窮,並帶出那些身影一閃而逝的赫赫有名歷史人物彩蛋(教育家三澤糾、作家西川滿、張文環、呂赫若……)。表面上如常運作的校園,其實早已悄悄扭曲,幾乎每個人都必須經歷彼此或自我的審查、壓抑。
雖然這部作品的敘事時空距離戰爭降臨尚早(?),但我在閱讀時卻無法不後見之明地時感憂慮,那些充滿魅力的明朗有趣角色們,果真那麼遲鈍於終將到來的滿天火雨嗎?到時他們該怎麼辦?這似乎又連結回2025年我輩的無遠慮庸碌日常了嗎?但漫畫中那麼鮮烈的青春與自由,還是多少刺激著我反思:不論戰爭會不會來,我有沒有輕率蹉跎呢?


➤創作者的功課
要對歷史題材作品產生足夠的認同感,關鍵始終在「放對位置」──不該為了遷就劇情而刻意扭曲史實(再想辦法,多絞一些腦汁出來,讓兩邊都合理?),「大方向不出錯」(請自行玩味),還可以適當運用一些有趣的史實小細節,來突顯作品的背景時代,以及人物的性格特質。
有些對現代人來說可能有點奇怪的部分,反而很適合放進情節中。比方說《芭蕉的芽》開場時的「寮雨」(學生之間居高臨下對人灑尿的惡作劇),這類現代人覺得很怪異或骯髒的情節,反而很可以突出高校生放蕩不羈的個性。
漫畫的強項,是可以視覺化呈現,並由讀者自行決定暫留或前進的節奏──比影視化成本低、比文字更容易進入作品──但也因為如此,有時候會被讀者忽略其考證的強度之高。但所有的努力都不會白費,我知道有些優秀的創作者,他們極嚴謹地做了超級多研究,卻追求「不著痕跡」地呈現時代氛圍,認真的讀者反而會意外獲得近似解謎的樂趣,這讓我相當嚮往。
另一方面,不論是讀或寫歷史相關題材的作品,我自己會特別在意語言是不是能盡量還原當時的用法──這是我自己在進行創作,或日後與漫畫家合作時,比較會留意的地方。因為除了連續畫面,大家看漫畫時的視線移動就是跟著臺詞走的,好的臺詞相當重要。
藉由作品提供的各種設想,從真實材料中萃取驅動情節與人物行動的元素,是漫畫家,也是其他各類創作者的永恆挑戰。為了讓更多讀者在乎那些記憶與技藝,那麼等待著我們的真實未來,未必盡是如80年前晦澀暗沉的「未知」,而是可能種下某種新生的希望。至少我期待如此。●


![]()
《漫射報+》
國家漫畫博物館自籌備期起,過去以《漫射報》為名出版主題刊物,共發刊6期,編輯視角各有不同。國家漫畫博物館於2023年底正式落腳臺中,收穫著珍貴的回饋與善意,現在《漫射報+》重回舞臺.ᐟ .ᐟ 記錄籌備過程的多彩回憶,並將研究調查成果與圖像視野,持續與大家共享。
- 第5期封面繪製:布里斯
- 全台索取地點詳情:請點我
- 了解更多:歡迎上「國家漫畫博物館籌備處」官方網站
本文轉載自國家漫畫博物館籌備處同意刊登,原標題與連結為「漫言堂》如果平行時空有漫天火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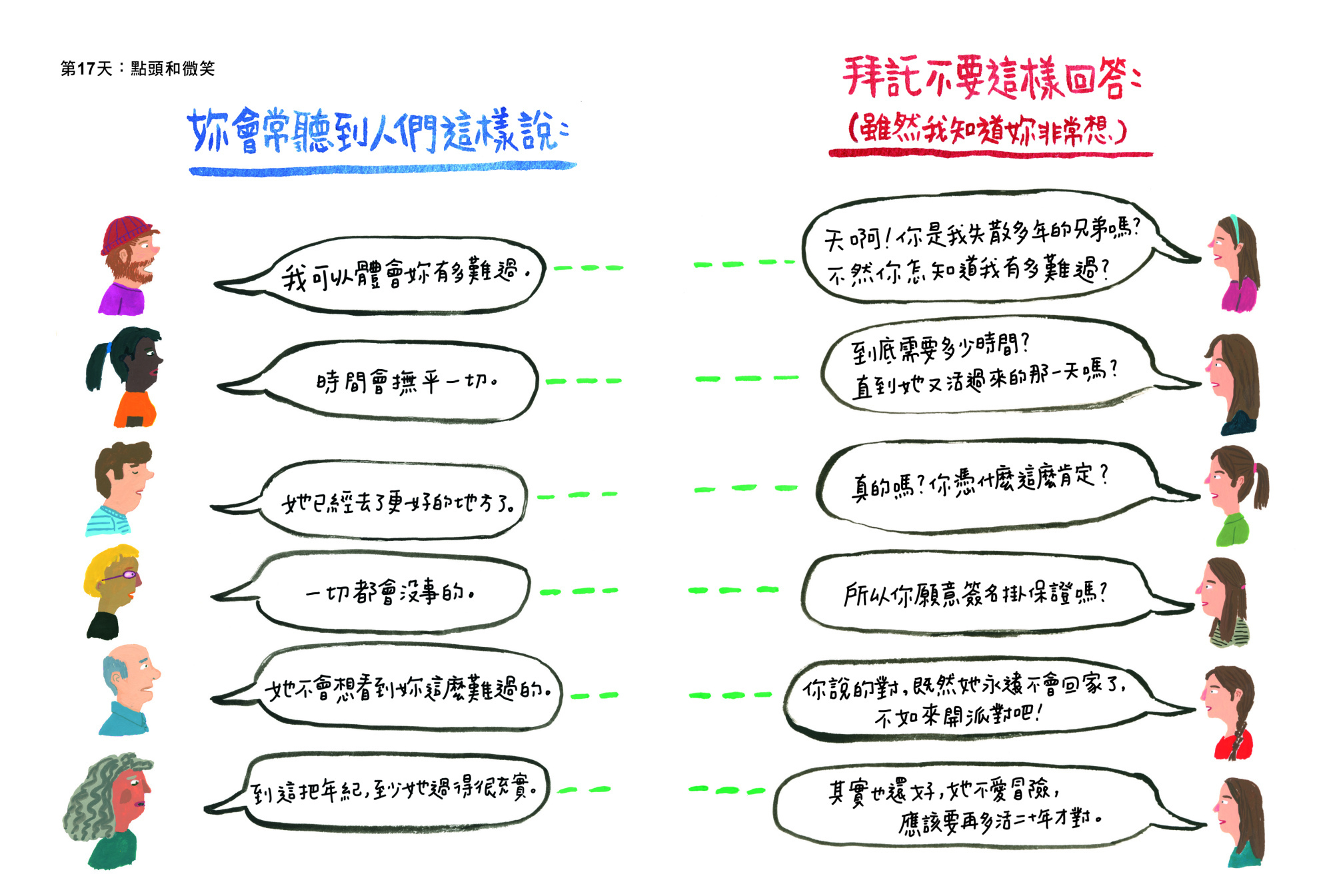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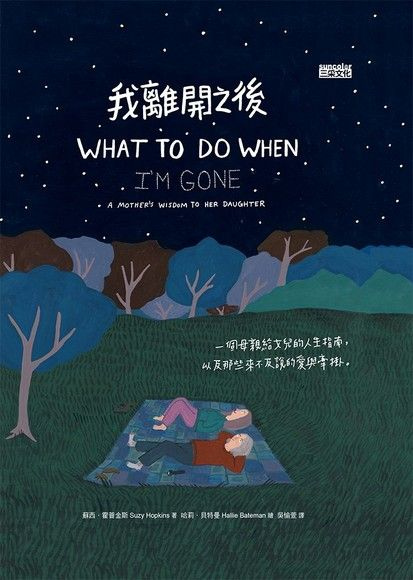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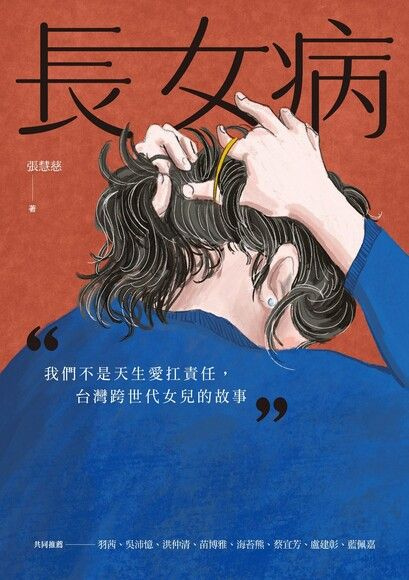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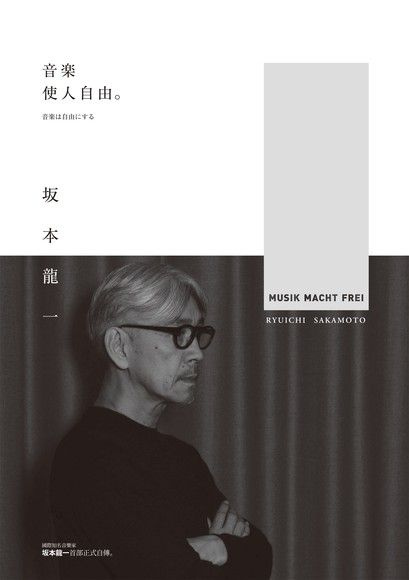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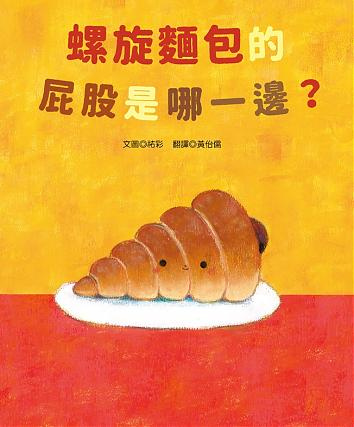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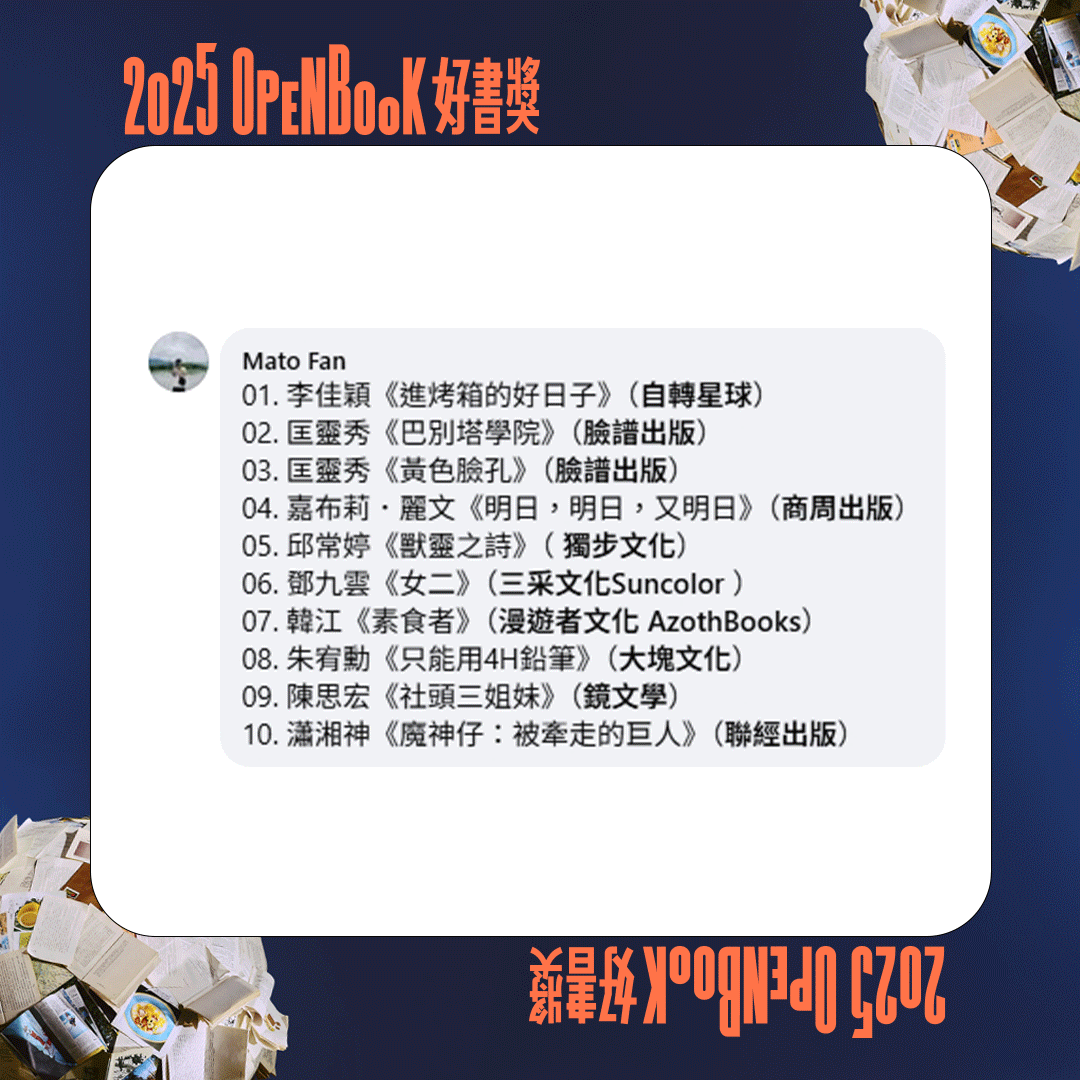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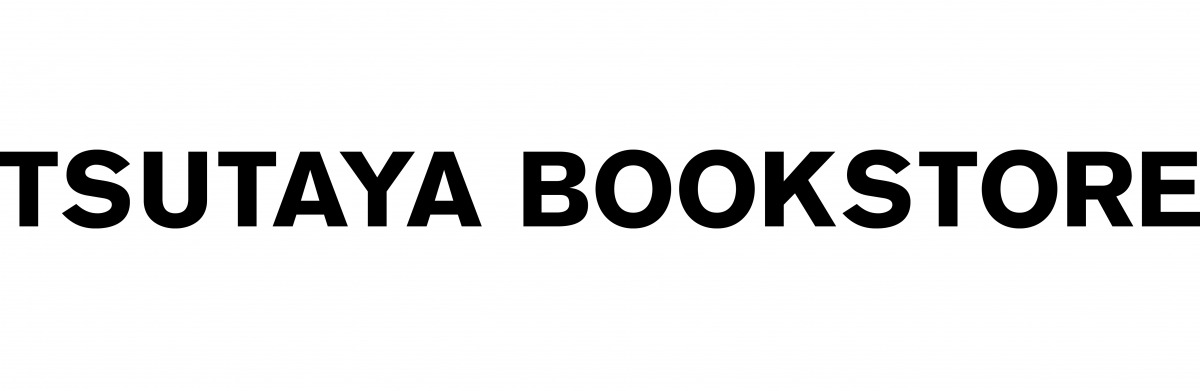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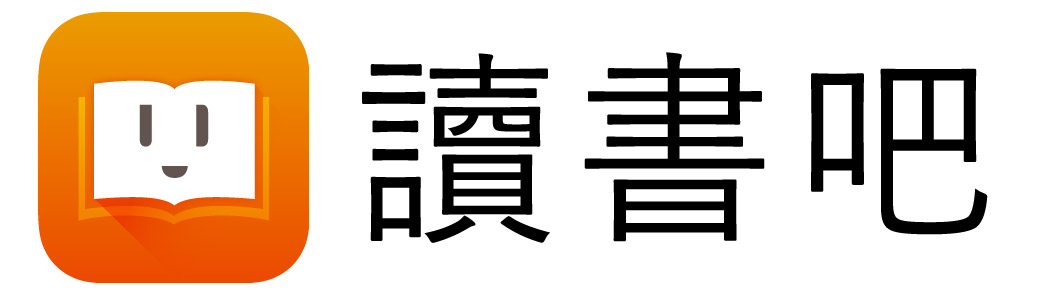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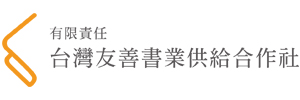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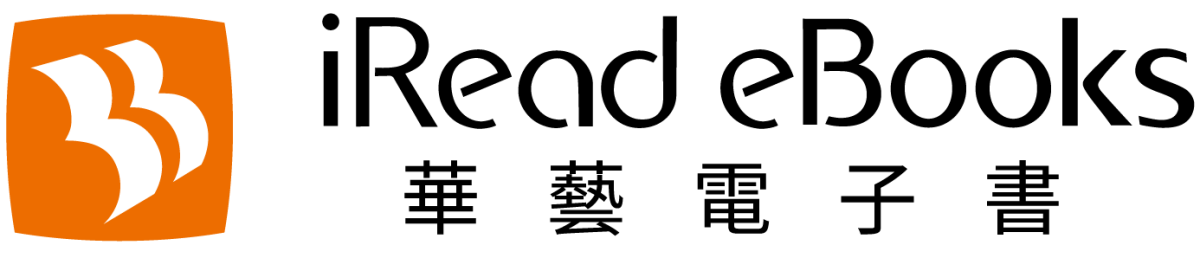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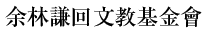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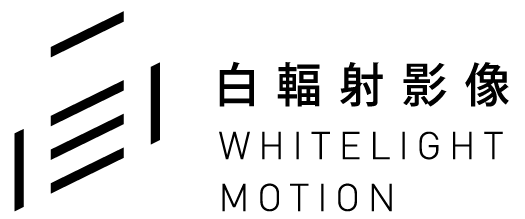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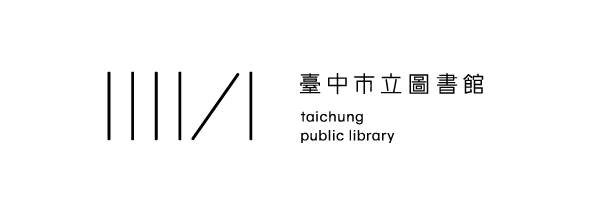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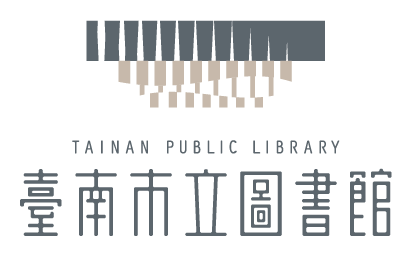
OB短評》#553探索世界規則的極品好書懶人包
●Size決定世界
Size:How It Explains the World
瓦茲拉夫.史密爾(Vaclav Smil)著,徐仕美譯,麥田出版,480元
推薦原因: 知 思 樂
將「尺寸」做為解讀世界的核心線索,探討人類對大小的感知,以及「大」與「小」的界定如何形塑今日世界的樣貌。透過跨領域的剖析,揭示尺寸背後的原理與規律,並透過數值間的關係,說明自然界與人造系統的運作機制。精巧有趣的思辨也提醒了我們,衡量世界的尺度所具有的相對性,它所依循的標準與詮釋方式,往往隱含著價值判斷與世界觀的偏向。【內容簡介➤】
●火新世
人類如何鑄成烈焰時代,未來將燃向何方
The Pyrocene:How We Created an Age of Fire, and What Happens Next
史帝芬.派恩(Stephen J. Pyne)著,林朝欽譯,野人文化,460元
推薦原因: 知 思 議 樂 益
以時間軸中的環境、科學、人類作為與思維,建構出關於自然相處、能源開發與氣候變遷的人火關係史,也梳理出火如何在文明中扮演重要角色。作者提出「火新世」一詞,統攝普羅米修斯以降,人類的命運發展與隨之震盪的自然劇變,揭示「火」——及其諸多熱能源子孫,既是進步的推手,也是失控的引信。這些火苗延燒的軌跡,點明了文明的輪廓,也燃起了反思的星火。【內容簡介➤】
●尼安德塔樂園的嘆息
郭品潔著,二十張出版,380元
推薦原因: 文 樂
這本詩集考肉身的古,也考肉身的現:一旦有恙,肉身立即化為超完美黑洞,把所有的心思、感覺、視線、氣力通通無差別吸進來,令無所逃。直白的文字,不哀不樂,別有怨艾,然而這卻是現代智人最需要的健康——承受存在的健康。【內容簡介➤】
●問題是,我大概會活很久
百歲傳奇女總編暢談活著不道歉,走時盡興如願
Somewhere Towards the End: A Memoir
黛安娜.阿西爾(Diana Athill)著,謝靜雯譯,大家出版,350元
推薦原因: 議 文 樂
看這位2019年謝世的人瑞編輯大姐大,回首自己的愛情、人生和老去,有點嘮叨,不時金句,口不嫌,體正直,坦白得近乎粗魯,實在爽氣。老也可以老得如此跋扈飛揚,有姿有態,讓人也想跟著高呼:婆婆奶奶站起來!【內容簡介➤】
●只是快撐不下去了
給不敢讓人失望的「高功能內向者」日常救援手冊
邱淳孝著,寶瓶文化,380元
推薦原因: 議 實 樂 益
從心理師自體化出的機智內向生活指南,為內向者在現代生活的迷宮中遞出一條身心安頓的指引繩,也可能讓非內向者得以理解那股時而襲來、難以名狀的疲憊從何而生。在今天這個推崇外放、競逐被看見的世界,引導無以自處的內向者們、累累的我們,做一個接納自我、安全無虞的確保。【內容簡介➤】
●野獸派調香師
潔曼.塞利耶的香水革命
Germaine Cellier - L’audace d’une parfumeuse
貝亞提絲.艾杰瑪(Béatrice Egémar) 著,陳文瑤譯,積木文化,680元
推薦原因: 知 樂
這本繪本的大功德,是把塞里耶這位傳奇女調香師重新召喚出來:早從40年代開始,她就以皮革調、綠香調、動物香等一系列革命性氣味,在二元對立的香氛市場殺出一條中性香賽道,也就是你在捷運上聞到的大部分香氣。如果你還在找一支欠缺的香水,請務必試試塞奶奶的作品。是的,還沒有絕版。【內容簡介➤】
●我會記住你愛我的樣子
春花媽著,一葦文思,480元
推薦原因: 知 議 樂
這本動物溝通錄別開生面,面對生老病死,牠們往往有驚人之語,頗有一休的架勢。野生動物的傳訊也令人莞爾,甚且教人羞愧,人類真的做了好些不好的事呢。漫畫的詮釋有點太規矩,稍微可惜了。【內容簡介➤】
●統治世界的貓咪
Gatos. Los felinos que dominan el mundo
艾絲特.佩卓薩(Esther Pedraza),阿穆德納.迪亞茲-米蓋爾(Almudena Díaz-Miguel)著,謝琬湞譯,創意市集,380元
推薦原因: 議 樂
這是一部喵的全球史,各篇章藏著各種意想不到的、貓與政治交織的冷知識。從知名的英國首相府邸喵、史詩戰役中的喵,到當代網紅喵,這部作品以翔實的考據、簡明輕鬆的文字,透過貓的足跡穿針引線,重新詮釋典故與軼事,也讓既有的歷史生動浮現。【內容簡介➤】
●水鬼事變
湖南蟲著,時報出版,380元
推薦原因: 文 樂
在形式與語言中更新既有的形式與語言,是這本詩集透過「人」、「鬼」與「殊途」不段復返的路徑。從人形肉身感官愛慾,過渡到水鬼與言靈等無形的詩身,最後繞回媒介的殊途,讓印刷、包裝媒材等文字肉身回到人世,各輯詩作讀來既魅惑又除魅,適合把生活放冷一點、再重新讀看看。【內容簡介➤】
●波霸雞與翹臀豬
肉食色情論
The Pornography of Meat: New and Updated Edition
卡蘿・J・亞當斯(Carol J. Adams)著,羅嵐、林若瑄譯,社團法人台灣動物平權促進會,600元
推薦原因: 批 思 議 樂
這本出版超過20年的經典作品,讓動物平權與父權批判匯流,橫向交織出一幅眼花撩亂的權力系統。書中收錄上個世紀公開流傳的數百張肉品廣告圖像,以敏銳的視角帶著讀者進行識讀,辨析「食物」的情色語言中夾雜的厭女、白人至上、人類中心、恐同與健全主義等壓迫語言,其批判精神別具洞見,歷久不衰。【內容簡介➤】
知識性.設計感.批判性.思想性.議題性.實用性.文學性. 閱讀樂趣.獨特性.公益性
閱讀通信 vol.370》當我在書裡讀到你的時候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