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家屋之內與之外:李欣倫讀平路《蒙妮卡日記》
平路的《蒙妮卡日記》收錄了15篇短篇小說,分為3輯,第一輯的敘事者多為女性,幽幽述說心事與情事;第二輯中,多數的敘事者為男性,以其角度見證世界史和科技史,包括了臺灣經濟奇蹟、複製人;最後一輯則廣幅了命運、改寫、夢境、創造等命題。即使小說描繪不同時代、不同性別的世界和視界,這些故事背後皆浮現了一個共同的輪廓:家屋。
展讀《蒙妮卡日記》,彷彿走進了城市中的公寓和辦公室,跨入他們(也是我們)的房間和空間。譬如〈蒙妮卡日記〉裡佈置溫馨的妮妮的房間;〈微雨魂魄〉中望著天花板水漬後,上樓進入陌生女子的房間;〈婚期〉裡對婚姻充滿憧憬的中文系女子,則寫過一篇〈愛情屋〉的短篇小說,無論單身、已婚、婚外情或寡婦,平路以細膩的文字架構家屋的同時,也帶讀者穿越了家庭史中無數個歡愉與沉默片刻,檢視生機與殺機的線索。

女性如此,男性亦然,除了三房兩廳的格局,家鄉的召喚總如鬼魅出沒,〈玉米田之死〉裡,死在玉米田的陳溪山是一則隱喻,藉由溯返童年時期的臺灣甘蔗田,身在美國而在婚姻(或職場)中動彈不得的男性,盼來了歸家的可能。
在平路筆下,對幸福、溫暖家庭的渴盼,甚至不是人類獨有的情感。〈猜猜,他想換些什麼?〉寫複製人的悲涼心境,即使身體淪為器官替換的農場,也隱隱透露對伴侶、穩定的家懷有終極渴望,因此在〈人工智慧記事〉中,被創造出來的機器人最終也想要創造生命,延續自我。
那麼,被創造出來的小說人物呢?〈歧路家園〉的題目不僅揭示了寫作是面對歧路的過程,從「家園」的命題和文中以「家:Yes?No?」的小標題來看,小說中的女主角對情愛抉擇的困惑,以及小說家對於命運的屢次改寫,都提供了不同版本的情愛與家屋想像。

但是,家到底是個什麼地方?熟知心理術並擅於拆解心靈密碼的平路,藉由文字帶領讀者反思:無論男女、成年、中年或老年,我們的情感地圖皆可回溯到童年時代,於是作者以精準的文字道出母親、女人與女孩間的幽微連結,如:「每個女人心裡頭都有一個小女孩。」探索自我的內在小孩,也是近年來心理諮商書常見的議題。
從這個角度看《蒙妮卡日記》,可以發現無論是對婚姻懷抱憧憬的女子、介入婚姻的小三,還是想像有個不存在的女兒,她們的愛與傷幾乎皆延續自原生家庭的創痛,那是受傷的第一現場,例如:女子的婚外情可能與父親當年的外遇相關;女主角對母親或繼母的畏懼及恨意,也影響了她對婚姻和家庭的想望(或妄想);又為了滿足內在那個無法被善待的小女孩,從想像中生出一個隱形女兒;甚至連機器人都需要被輸入活生生的童年經驗,使其更接近「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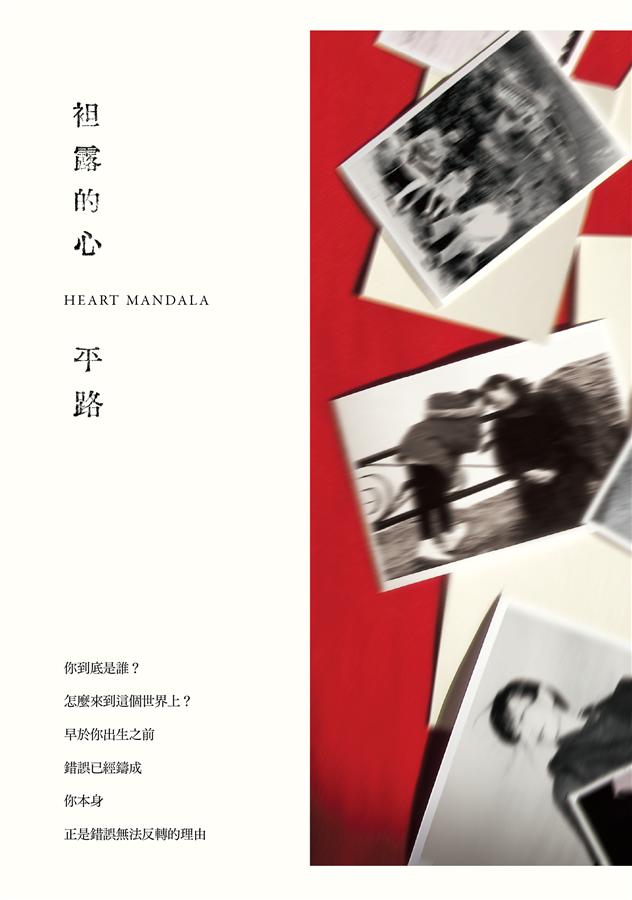 可見往事並不如煙,反而始終鬼魅般地纏祟著浮世男女,若對照於書寫身世之謎的散文《袒露的心》,即可讀出鉤沉童年經驗,進而對「我是誰」永不停歇的探尋,彷彿是平路念茲在茲的課題。
可見往事並不如煙,反而始終鬼魅般地纏祟著浮世男女,若對照於書寫身世之謎的散文《袒露的心》,即可讀出鉤沉童年經驗,進而對「我是誰」永不停歇的探尋,彷彿是平路念茲在茲的課題。
那麼,平路又如何發揮說故事的高超技藝,讓讀者一步步走入愛/情屋?此書的幾篇小說裡都有個待解謎團,不少故事縈繞著懸疑的氛圍,無論是從天花板逐漸擴大的水漬、最終死在玉米田的男人,死去的生命遺下諸多線索,既吸引讀者進入追索的過程,又能滿足讀者拼湊故事全貌的渴望。
不僅死亡,老、病描述也具力道,〈婚期〉裡被照顧的母親隨著年歲卻越活越年輕,相較於母親斑點的淡化,女兒臉上卻莫名長出黑斑,奇詭的細節強化母女衝突,隱約挑戰著老與少的邊界和定義。〈血色鄉關〉中重複述說當年勇、卻回不去了的忠貞黨員,耐心陪伴晚年罹患阿茲海默症的老七/老妻,然而比起患者的痴呆和遺忘,老男人的猜疑和脆弱是否也反顯了時代創傷?於是讀者雖從一個水漬般的細瑣細節走入主角的愛/情屋,最終卻翻出了壓在箱底的婚姻實錄,目睹一刀未剪的家屋劇場。更驚悚的是,這些片段彷彿似曾相識,即使《蒙妮卡日記》是舊作結集,但卻那麼真實地貼近了你我的家,目睹新鮮的傷口持續冒出血液。
家屋內外的愛與不愛是個問題,吸引眾男女透過卜算(〈紅塵五注〉)、時間的推論與辯證(〈愛情二重奏〉),試圖將惶惶然的自心,安放在一個距離死亡最遙遠的、歲月靜好的假設與假象中。
家屋之內如此,家屋之外亦如是,始終關照細節的平路細膩描繪了發生在家庭的愛、痛和殺機,進而以同樣的目光聚焦社會,放眼世界。具豐富媒體經驗的平路,以老夫人的口吻,敘寫媒體如何略過她的智慧機伶,放大無關緊要的時尚花邊,而老夫人也深諳於此,了解民眾需求的她知道「全國人民沒有比現在更需要一張照片」(〈百齡箋〉);又「臺灣化」一詞從堅強賭性、經濟力到流行病的多義性,最終指向眾人對歷史記憶的遺忘(〈臺灣奇蹟〉),即使走出家屋,平路以一篇又一篇精彩的短篇小說,帶讀者回看銘記在歷史中的步履,而每一步的選擇皆面向並決定未來。由此來看小說最後一輯中關於創造、運算、宿命之議題便饒富興味,這些關鍵詞共同構成了一個深刻提問:你所想像或創造的,會是什麼樣的未來?
於是,讀《蒙妮卡日記》,彷彿走進一個又一個眾生的愛/情(樣品)屋,裝載了所有你能想到與想不到的情感靜物和情緒活物,在家屋之內,又在家屋之外。●
|
|
|
作者簡介:平路 出⽣於臺灣⾼雄,臺⼤⼼理系畢業,美國愛荷華⼤學碩⼠。曾從事數理統計專業、於媒體界服務、任香港光華⽂化新聞中⼼主任,並曾在臺⼤新聞研究所與北藝⼤藝術管理研究所任教。曾獲金典獎、金鼎獎、吳三連獎;第22屆國家⽂藝獎;⾦⽯堂2021年度「風雲作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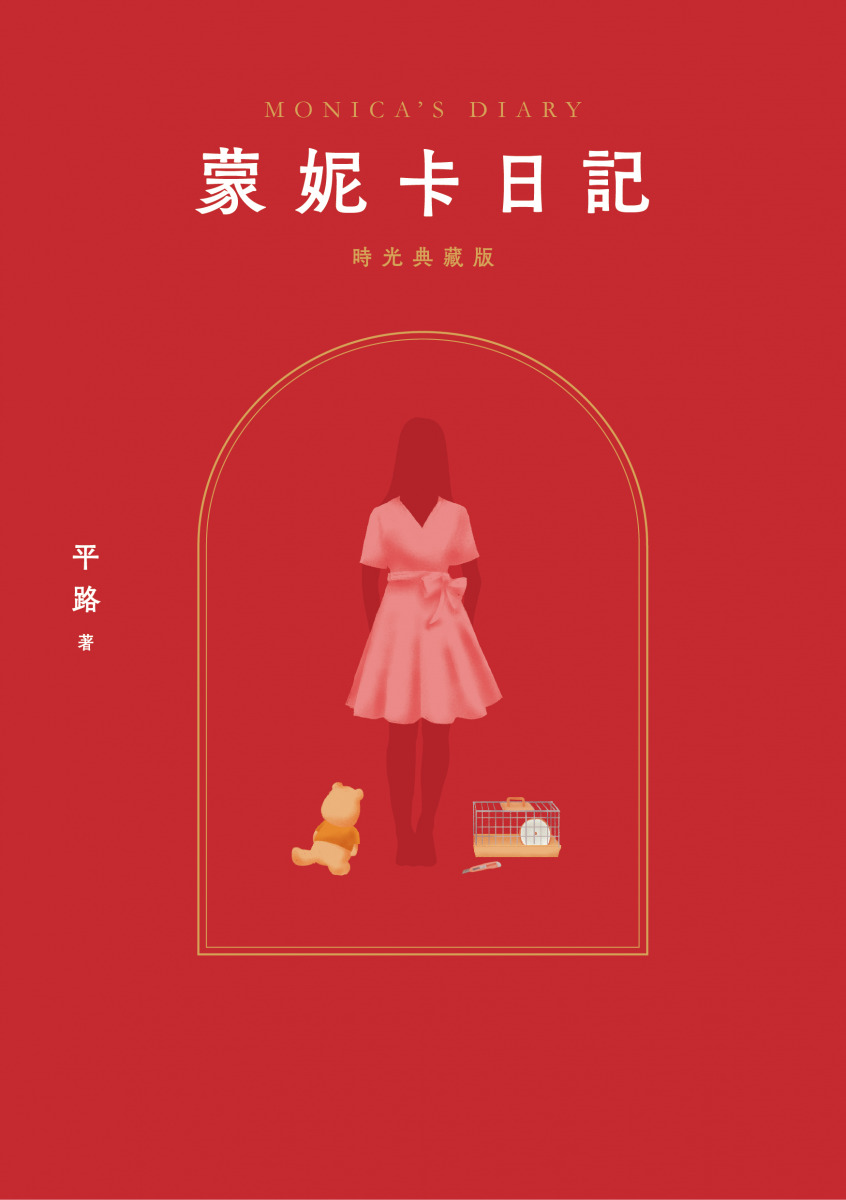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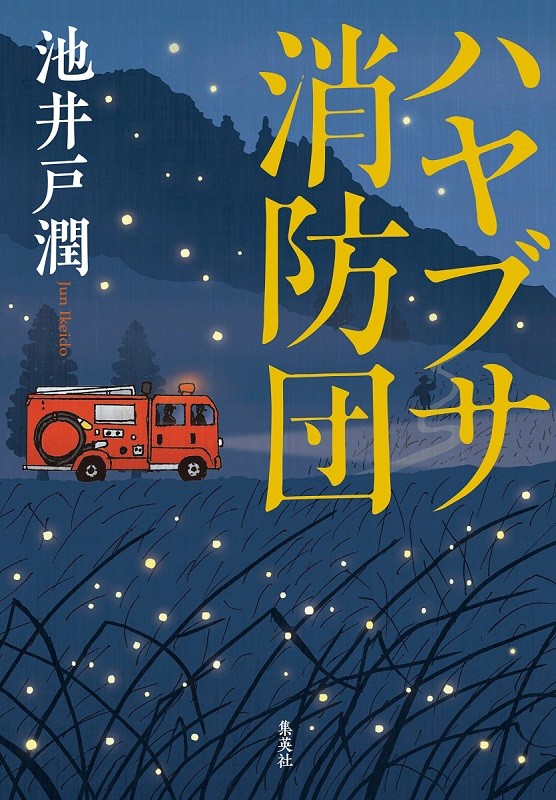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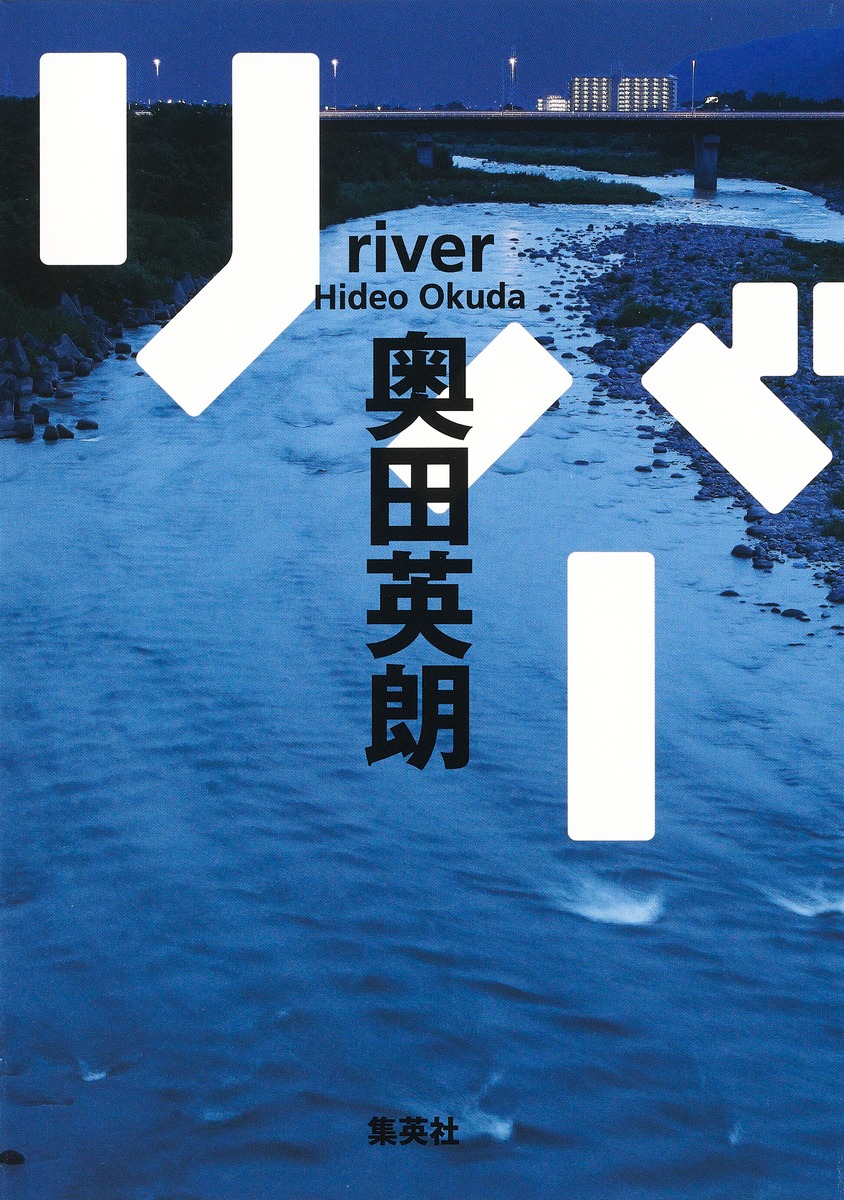 ■《邪魔》、《空中鞦韆》、《家日和》、《新冠肺炎與潛水服》作者奥田英朗,於本月底推出全新長篇犯罪小說《
■《邪魔》、《空中鞦韆》、《家日和》、《新冠肺炎與潛水服》作者奥田英朗,於本月底推出全新長篇犯罪小說《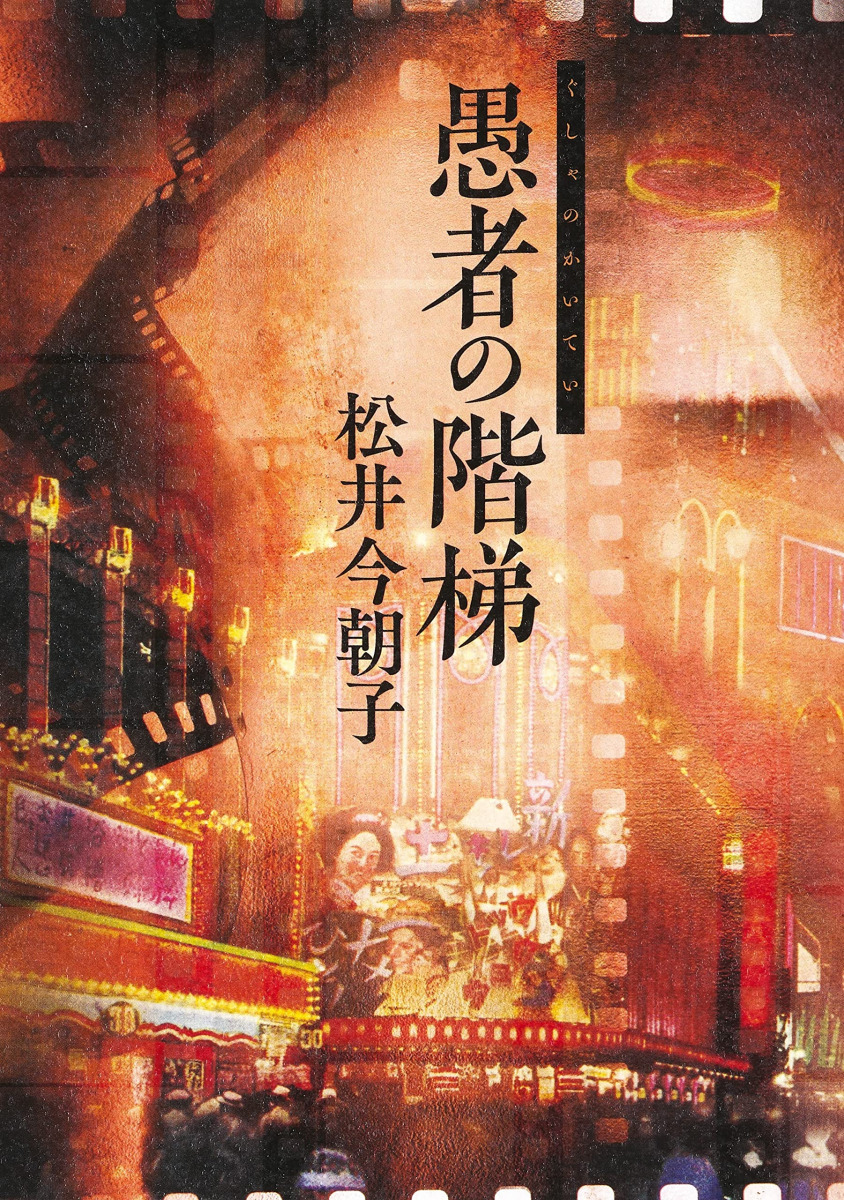 ■曾出版《仲藏狂亂》、《吉原手引草》等文學獎得獎作,在戲劇、評論、寫作等領域成就斐然的松井今朝子,繼《壺中的回廊》與獲得渡邊淳一文學獎的《芙蓉的干城》後,終於在本月初發行昭和三部曲完結篇《愚者的階梯》(集英社)。
■曾出版《仲藏狂亂》、《吉原手引草》等文學獎得獎作,在戲劇、評論、寫作等領域成就斐然的松井今朝子,繼《壺中的回廊》與獲得渡邊淳一文學獎的《芙蓉的干城》後,終於在本月初發行昭和三部曲完結篇《愚者的階梯》(集英社)。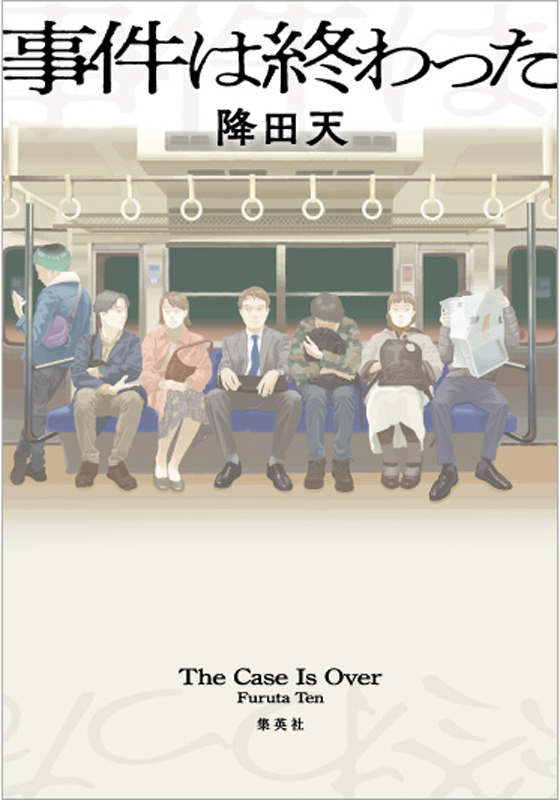 ■著有《女王不歸來》、《虛假之春》、《紫羅蘭之家的罪人》等暢銷作品的推理小說家降田天,在上個月底推出連作短篇集《事件終結》(集英社),訴說悲劇的後日談。某年歲末,在地下鐵S線內,一名男子突然手持利刃向孕婦揮砍,最後將一旁介入協助的老人刺殺。這場震撼社會的無差別殺傷事件後,被捲入意外的群眾,理應回歸日常生活。然而,對一部分的人而言,這卻不是終結。
■著有《女王不歸來》、《虛假之春》、《紫羅蘭之家的罪人》等暢銷作品的推理小說家降田天,在上個月底推出連作短篇集《事件終結》(集英社),訴說悲劇的後日談。某年歲末,在地下鐵S線內,一名男子突然手持利刃向孕婦揮砍,最後將一旁介入協助的老人刺殺。這場震撼社會的無差別殺傷事件後,被捲入意外的群眾,理應回歸日常生活。然而,對一部分的人而言,這卻不是終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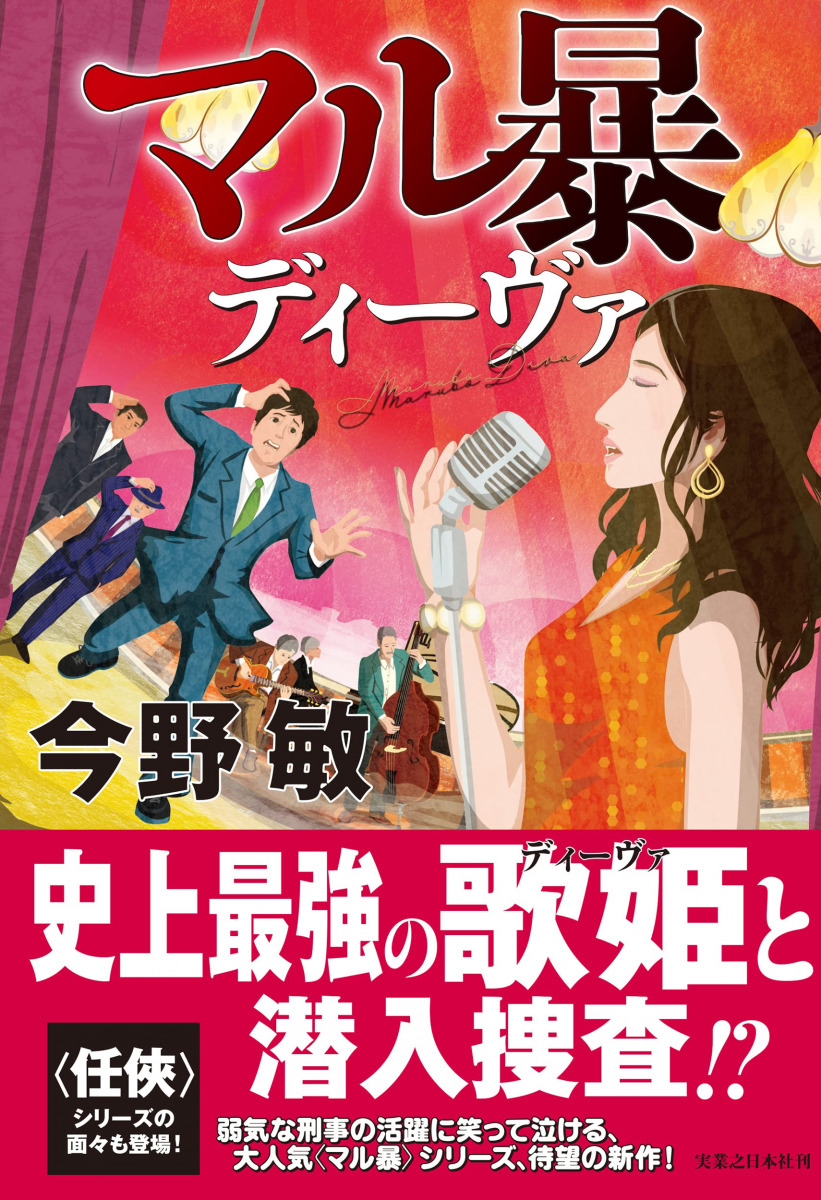 ■曾出版《隱蔽搜查》、《ST警視廳科學特搜班》系列,名下超過上百部著作的日本暢銷作家今野敏,本月初發行黑道系列第3部:《黑道歌姬》(實業之日本社)。《超弱刑警暴甘糟》的主角甘糟達夫,這次將和一臉兇樣宛若黑道的前輩郡原虎藏,一同潛入疑似偷偷兜售禁藥的爵士樂俱樂部。到了會場的兩人,不知不覺被舞台上的歌手星野愛吸引了注意。這個具有美妙歌聲的歌姬,是否有著不為人知的身分呢?而生性膽小的刑警甘糟,這次又將帶來什麼樣啼笑皆非的故事?
■曾出版《隱蔽搜查》、《ST警視廳科學特搜班》系列,名下超過上百部著作的日本暢銷作家今野敏,本月初發行黑道系列第3部:《黑道歌姬》(實業之日本社)。《超弱刑警暴甘糟》的主角甘糟達夫,這次將和一臉兇樣宛若黑道的前輩郡原虎藏,一同潛入疑似偷偷兜售禁藥的爵士樂俱樂部。到了會場的兩人,不知不覺被舞台上的歌手星野愛吸引了注意。這個具有美妙歌聲的歌姬,是否有著不為人知的身分呢?而生性膽小的刑警甘糟,這次又將帶來什麼樣啼笑皆非的故事? ■今年初在「小學生的童書總選舉」奪得冠軍、累積銷售突破400萬冊的《神奇柑仔店》(偕成社),本月中發行系列作第18卷。《神奇柑仔店》講述經營柑仔店「錢天堂」的詭異老闆紅子,透過前所未見的神奇零食,解決顧客人生煩惱的故事。
■今年初在「小學生的童書總選舉」奪得冠軍、累積銷售突破400萬冊的《神奇柑仔店》(偕成社),本月中發行系列作第18卷。《神奇柑仔店》講述經營柑仔店「錢天堂」的詭異老闆紅子,透過前所未見的神奇零食,解決顧客人生煩惱的故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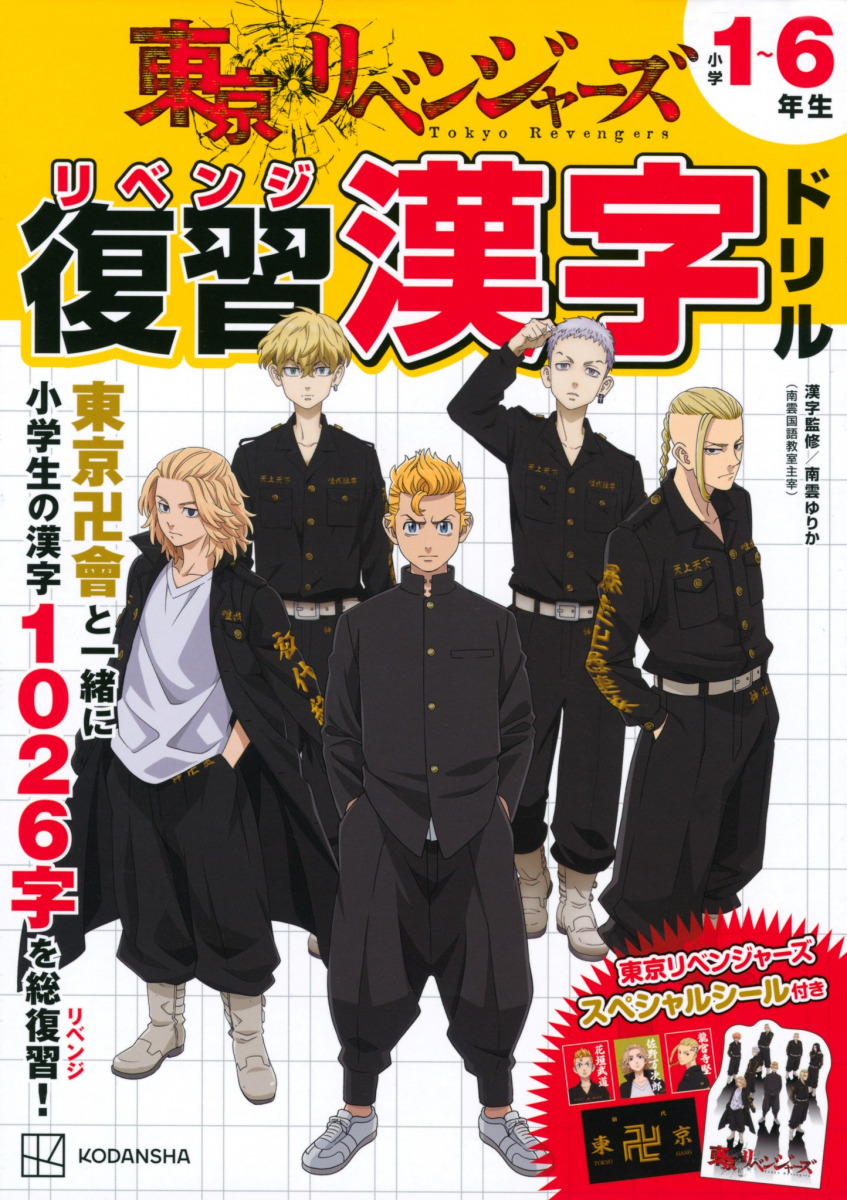 ■看《東京卍復仇者》居然也可以學漢字?原作單行本累計超過6500萬冊的動畫《東京卍復仇者》,8個月中推出漢字學習手冊《東京卍復仇者:複習(ㄔㄡˊ)漢字學習帖》(講談社),在日本社群網站引發話題。這本教材結合了《東京卍復仇者》的故事劇情,讓學生在閱讀故事文章的同時,學習當中使用的漢字,並熟悉其書寫方式,輕鬆回顧小學階段的1026個必學字彙。
■看《東京卍復仇者》居然也可以學漢字?原作單行本累計超過6500萬冊的動畫《東京卍復仇者》,8個月中推出漢字學習手冊《東京卍復仇者:複習(ㄔㄡˊ)漢字學習帖》(講談社),在日本社群網站引發話題。這本教材結合了《東京卍復仇者》的故事劇情,讓學生在閱讀故事文章的同時,學習當中使用的漢字,並熟悉其書寫方式,輕鬆回顧小學階段的1026個必學字彙。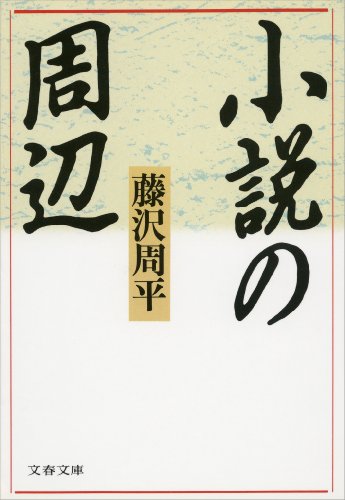 ■今年8月25日,中國文學界最高榮譽之一、每3年評選1次的鲁迅文學獎,公佈第8屆評選結果,日本作家藤澤周平創作、資深譯者竺祖慈翻譯的散文集《小說周邊》,榮獲該獎項中的文學翻譯獎。這是繼2007年大江健三郎的小說《別了,我的書!》以來,第二次有日本作家在魯迅文學獎榜上留名。藤澤透過 《小說周邊》這部作品,訴說關於家鄉山形縣鶴岡市的幼年回憶,以及自身對創作的思考。據《天津日報》記者仇宇浩報導,評審委員以「娓娓道來,充滿沉靜和智慧」評述藤澤的作品,並稱竺祖慈的翻譯「老到傳神,可謂達到了與作者相同的心境」。
■今年8月25日,中國文學界最高榮譽之一、每3年評選1次的鲁迅文學獎,公佈第8屆評選結果,日本作家藤澤周平創作、資深譯者竺祖慈翻譯的散文集《小說周邊》,榮獲該獎項中的文學翻譯獎。這是繼2007年大江健三郎的小說《別了,我的書!》以來,第二次有日本作家在魯迅文學獎榜上留名。藤澤透過 《小說周邊》這部作品,訴說關於家鄉山形縣鶴岡市的幼年回憶,以及自身對創作的思考。據《天津日報》記者仇宇浩報導,評審委員以「娓娓道來,充滿沉靜和智慧」評述藤澤的作品,並稱竺祖慈的翻譯「老到傳神,可謂達到了與作者相同的心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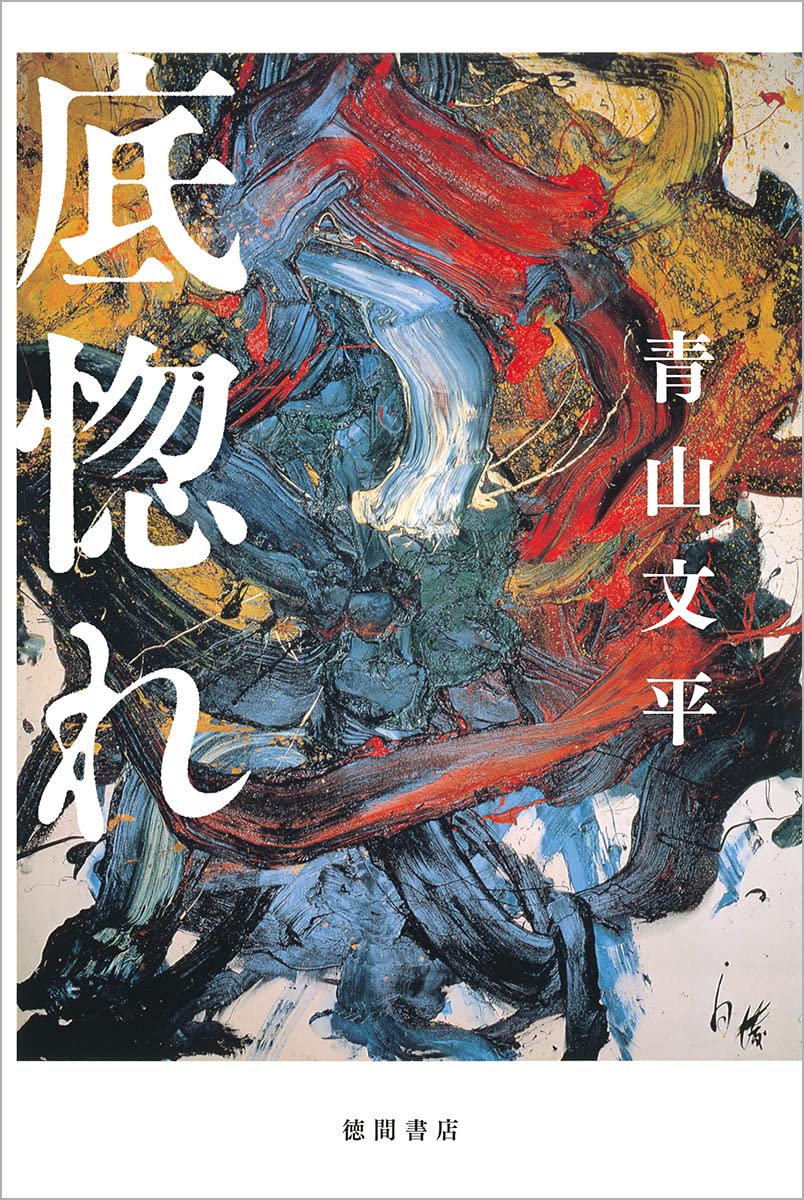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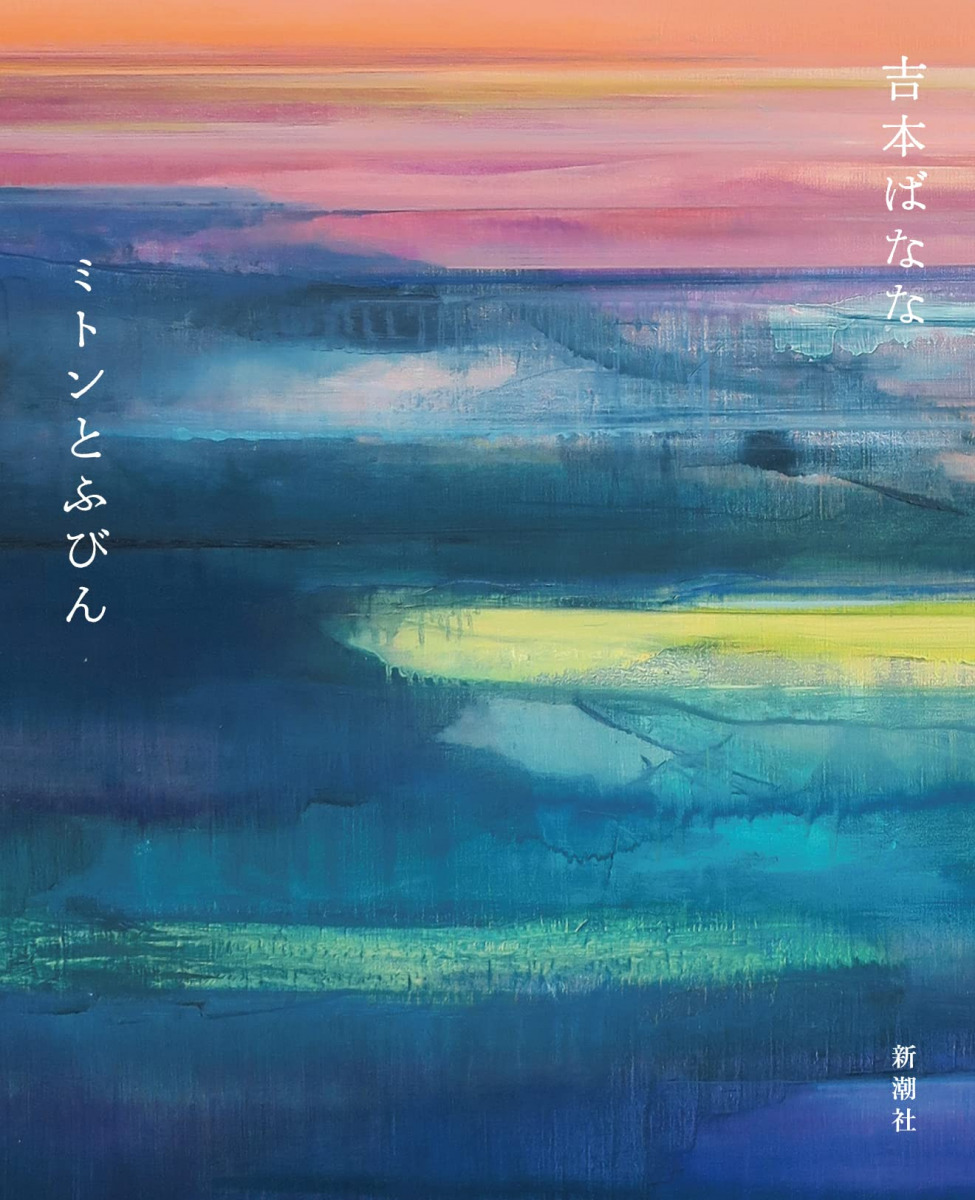 ■第58屆谷崎潤一郎獎亦於8月底公布評選結果,小說家吉本芭娜娜憑藉去年底推出的短篇集《厚手套與哀憐》(新潮社),成為本屆獎項得主。即便歷經重要之人的死亡、懷抱無法痊癒的喪失感,人依然會活下去。冷冽冰寒的赫爾辛基,由歷史的重量層層堆砌的羅馬,吹著南國香甜的風、植物終年翠青的台北,在不斷運轉的地球上,無數的邂逅持續發生。吉本以細膩的筆觸,描摹微光照拂、溫柔滿溢的6個短篇。她寫道:「這是如今的我能寫出來的最好的一本書。」
■第58屆谷崎潤一郎獎亦於8月底公布評選結果,小說家吉本芭娜娜憑藉去年底推出的短篇集《厚手套與哀憐》(新潮社),成為本屆獎項得主。即便歷經重要之人的死亡、懷抱無法痊癒的喪失感,人依然會活下去。冷冽冰寒的赫爾辛基,由歷史的重量層層堆砌的羅馬,吹著南國香甜的風、植物終年翠青的台北,在不斷運轉的地球上,無數的邂逅持續發生。吉本以細膩的筆觸,描摹微光照拂、溫柔滿溢的6個短篇。她寫道:「這是如今的我能寫出來的最好的一本書。」
國外愛這味.版權》漫畫、繪本國際版權銷售的關鍵推力
在國際版權交易的舞台上,競爭對手往往是來自世界各國的優秀創作,臺灣圖像作品必須具備哪些特質,才能吸引國外出版社的目光?國際版權交易的策略和眉角又有哪些?本文分別訪問了資深漫畫編輯、繪本企畫編輯以及專業版權人員,探究國際版權銷售背後的關鍵推力。
➤漫畫、繪本圖文結合,易打動國外讀者
近年來,臺灣越來越多人投入漫畫創作,新生代漫畫家不斷出現,2022年安古蘭國際漫畫節臺灣館執行策展人、大塊文化第二編輯部總編林怡君,擁有多年海外參展經驗,她認為,創作者們對漫畫的想法及表現風格都很不一樣,各具特色,為臺灣漫畫增添多元面貌,因此,每年如有新作不斷推出,國外出版社將有更多機會從中挑選出適合當地讀者喜愛的作品,進一步購買版權和推廣。
2022年義大利波隆那書展駐館版權人員、愛米粒出版社總編輯莊靜君表示,繪本創作相當不容易,需要兼備故事與圖畫的品質,也須用最簡潔的故事文字和精采的圖像打動國外讀者。歐洲出版的圖像小說通常都能深入挖掘主題,圖文結合的說故事能力和技巧都不容小覷,然而,國際上版權的競爭對象是各國傑出的作品,莊靜君認為可透過廣泛的閱讀,幫助提升創作的故事力。
➤現場觀察、主動出擊,了解國際出版市場趨勢
莊靜君於1998年首次參加德國法蘭克福書展,見識到全世界重要的出版人聚會,至今,她還是會年年參展,透過在現場的近身觀察,掌握更多國際版權市場的趨勢。
她以2018年參與倫敦書展的經驗為例,當時特別留意亞洲翻譯小說區,發現日本小說《在咖啡冷掉之前》、《如果這世界貓消失了》、《旅貓日記》和《稻妻小路的貓》在歐美十分暢銷,因此推測許多外國編輯除了喜歡貓,對於「日本文化」、「日式庭園」等元素也相當喜愛。
其中夏川草介的《守護書的貓》目前已有38種翻譯語言,是村上春樹的作品之外,近年來亞洲賣到最多國家的作品。根據英國雜誌Bookseller當時的報導,英國翻譯書Top 10有3本來自日本,其中之一就是《守護書的貓》。由此可見,國際出版市場中的暢銷書趨勢,也會成為版權銷售時特別被關注的指標。
莊靜君過去在皇冠出版社任職時,也曾將瓊瑤、侯文詠的作品帶到印尼、越南和泰國,獲得東南亞書市不錯的迴響。她指出,泰國讀者偏好奇幻、言情小說,當地預付金雖不高,但泰國對臺灣書籍的接受度很高。
顯見除了全球性的出版趨勢,能掌握單一國家出版市場的口味,也是能否順利賣出版權的關鍵。
➤翻譯好、國際獲獎,都是助力
近年來,文化部的翻譯出版補助,也讓臺灣好作品更有機會被全球市場看見。莊靜君以臺灣小說家張渝歌2018年的作品《荒聞》為例,她說,因獲得翻譯補助,《荒聞》有足夠經費請到非常好的譯者,翻譯品質相當好,又因具臺灣特色,也有恐怖推理元素,且文字易讀,獲選為臺灣主力推到國際市場的 「Books From Taiwan」(BFT)選書,因而受到國外編輯的關注,不僅全球英文版賣給英國出版社Honford Star,日文版賣給日本出版社文藝春秋,越南文版權、希臘文版權等,也紛紛由當地的主流出版社買下。
莊靜君強調,BFT平台和翻譯補助,這兩個由政府提供資源做的事,對臺灣書籍及作者來說非常重要。但政府補助的方式可再細分,例如小說需要翻譯補助、圖文書需要印刷補助,至於臺灣作家的書籍出版外語版後,能有國際宣傳活動補助等等。
得到國際獎項也能增加作者的曝光,為前進國際市場再推一把。林怡君舉例,插畫家阿尼默的漫畫作品《小輓》與繪本《情批》,分別獲得2020年波隆那拉加茲青少年漫畫類首獎,以及2021年詩類別評審優選獎,阿尼默也因此獲邀前往演講。在現場,他的演講誠懇而精采,打動許多現場民眾,吸引了許多讀者及出版社,會後有不少人詢問,有無推出外語譯本。
➤題材選擇有助引起共鳴
《騎著恐龍去圖書館》是由劉思源與林小杯共同創作的繪本,簡單出版公司執行副總經理蘇欣指出,林小杯在畫面上,展現出故事想表達的童趣、歡樂與自由,書裡充滿創意的「恐龍校車」抓住了兒童普遍的喜好,作品的主題、故事和畫風都具備跨國界、跨文化的普遍童年生活體驗,至今已售出全球英、日、法、俄、韓、泰與斯洛伐克等語文的版權。
有普遍性、具共鳴的題材,有助於全球不同語系的版權銷售之外,也能透過不同的活動,觸及更多元的讀者。 林廉恩的繪本創作《Home》曾獲2021年波隆那拉加茲獎故事類首獎,以拼貼畫面描述一對父女和一隻紅色小鳥的所見所聞。出版社巴巴文化當時收到麥當勞「麥麥親子共讀日」限量贈書的邀請,凸顯出「家」這個主題獲得了共鳴,甚至還有媽媽讀者分享「自己比孩子更喜歡這本書」,全臺兩萬本繪本,更在單日內被換購一空。任職於巴巴文化的企畫編輯林珈如說,這是異業合作的成功案例。
此外,題材特殊的作品,也是吸引起外國出版社注意的因素。林怡君指出,擅長以女性視角結合日常情慾來創作的新生代漫畫家穀子,其作品《T子%%走》寫實地描繪了一位女子去日本嘗試用社交軟體約炮的酸甜苦辣,題材獨特、明確、有趣,容易引起不同文化讀者的共鳴,也獲得日本市場的關注,目前已有日文版本。
➤版權推廣的挑戰與自我精進
要能成功把好作品推到國外,版權人的工作也不容小覷。「要進入英美和日本的圖像市場非常不容易」,林怡君指出,國外出版社的分工細膩,買方(編輯)跟賣方(版權)窗口經常是不同的負責人,寄出書訊後,還要持續發信詢問、追蹤國外的購買意願,她認為,版權推廣是長期的經營累積,創作者認真面對自己的創作、盡力將作品做到最好,編輯和版權也需做好自己的工作,持續將好作品推廣給國外出版社。
林珈如則表示,臺灣繪本偏教育導向,國外繪本較無限制,她會與國外編輯分享最感動的畫面以及作品背後的故事,另外也會採購國外的繪本來參考書籍的設計、印刷、裝幀,研究其特色,掌握外國讀者的視覺口味。蘇欣補充,經過她對國際媒合會及說書活動的長年觀察,發現臺灣出版人較為害羞,她建議,可強化相關人員的中英文說書訓練,使版權推廣過程更為順暢。
蘇欣認為,臺灣版權在國外的成績愈來愈亮眼,不管是日本、英國文學獎,義大利波隆那,甚至是美國插畫獎等,都有臺灣創作者的身影,這是建立產業信心的重要因素。
臺灣除了擁有豐沛的創作能量,出版社的推廣也相當重要。國際上每一次的版權銷售,都在不斷累積臺灣圖像的能量與優勢,相信在創作者、出版社與政府的共同努力之下,臺灣的出版產業能一步步往前突破。●
【Openbook國際書展參戰(;・`д・´)】
2/6(五)歡迎加入玩耍!•̀.̫•́✧書寫、行動與反思:和島嶼互動的幾種方式
閱讀通信 vol.368》台北國際書展,來襲!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