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書店如跳火坑嗎? 「我先生林齊晧跟我說他有個前同事要開書店時,我心裡想:『怎麼會有人要做這種事,有什麼我們可以幫得上忙的?』那時候覺得開書店這件事很辛苦,而且又很難賺錢,他們竟然要開書店!」兒童教育工作者鍾欣穎伸手捂著嘴,微微皺眉,「那時我們剛好在搬家,有一些傢俱,就想說可以送給他們書店用。」
說話的此刻,鍾欣穎就坐在這位「前同事」林潔珊開設的獨立書店「現流冊店」舊址,只是外頭的招牌已改名為「書房有光」。
去(2024)年底,鍾欣穎和林齊晧攜手跳入經營獨立書店的火坑,接下這處舊址,用半年時光籌備,今年7月開始試營運。曾經覺得開一家書店簡直是可憐的事情,如今兩人對望一眼,「結果小丑是我自己啦。」林齊晧一陣大笑。
「說起來是我們推坑他們的。」現流冊店店長林潔珊噗哧一聲。她曾在《鳴人堂》擔任編輯,林齊晧則是隔壁《轉角國際》的編輯,兩人因此熟識。2021年林潔珊離職,2022年末,現流冊店在大橋頭一處巷弄裡開張。
(圖源:現流冊店粉專 )
現流冊店開張後,林齊晧經常出沒在書店裡,有時乾脆和專欄作者約在這裡談事情,還會帶媽媽到現流吃潔珊特製的馬來西亞風咖哩飯。除了擔任編輯,林齊晧同時也是podcast「轉角國際.重磅廣播」和廣播節目「寶島少年兄」的主持人,以「七號」之名為網友熟知。他主持的幾場live podcast和作者座談會,都曾選擇在現流冊店舉行。
不少七號的聽友也會循聲來訪現流冊店,「書店裡有個留言小本本,裡面都是他們的聽友來現流後留下的文字。」林潔珊手指比劃出2、3公分的厚度。留言本是聽友共同體存在的證明,如今已幾乎被寫滿,2024年隨著現流冊店搬家,一同帶去了朝陽公園附近的新店址。
社群媒體時代的媒體與文字工作者,面對幾乎面目模糊的讀者,且經常接收到網路留言謾罵等負面回饋,林齊晧感覺到不少作者似乎因此深陷自我懷疑,「他們常會想:『寫這些有用嗎?』,尤其下面都是仇恨言論,看久了會很迷惘。」
但幾次實體座談中,作者與讀者面對面談話,或是live podcast時,到場的聽友分享那些空中的音頻如何改變了自己的人生或觀念。真實的人際互動,給了內容生產者更多能量,「很多作者辦完實體活動都法喜充滿。」林齊晧笑了笑。
➤喜歡看書,還喜歡推薦別人看書 實體的相遇充滿魔力,讓兩人考慮起是否該經營一處空間。林齊晧也觀察到,「疫情後,媒體流量下降,AI出現影響了資訊傳播與獲取方式。這些都讓實體互動變得更重要。」
人間相遇的魔幻時刻需要有場所才能實現。現流冊店打算搬家時,舊址的租約還有一年半,林潔珊想找熟人接手,便慫恿起身邊朋友,「來啦,來開書店啦!」林潔珊問了林齊晧,當時他有些躊躇,空間也很快被其他人租下。本以為無緣,沒想到後來再次輾轉釋出,「我覺得這是個徵兆。」於是他下定決心,打算斜槓經營書店,並邀請妻子擔任顧問。
「反正我們本來在家裡就很常跟朋友分享書籍,有時聊天聊到一半,會轉身找出一本書推薦給朋友。還有之前擔任Openbook好書獎評審,就更讓我們確信自己喜歡分享和推薦書籍,願意投入心力做這件事。」林齊晧笑言,反正自己平日買書數量簡直和書店進貨差不多,經營書店或許不過是把平日的購書行為,換一個形式進行罷了。
但是,簽下租約之後,魔鬼的考驗也正式開始,「先是實體書店的補助申請沒有通過。」鍾欣穎苦笑,原本盤算若能拿到補助,經營上相對比較沒有成本壓力,可惜碰上政府預算縮減,許多獨立書店都沒能獲得補助。
再來是裝潢時發現樑柱結構有毀損,接著又冒出白蟻危機。「我以前參與過公辦民營親子館的營運,大概有心理準備,籌備期就是可能會有各種不順。」專業是兒童發展領域的鍾欣穎,已體驗過一個空間在籌備時期的禍不單行,面對各種突發狀況波瀾不驚。林齊晧則是用失控的正向思考來應對,「為了滅蟲,我那陣子聽滅蟲的師傅講解一堆白蟻的知識,都覺得可以來辦一場白蟻防治的座談了。」
無獨有偶,7月新掛上的「書房有光」招牌,竟然被行經巷弄的卡車撞壞。「我們當時就坐在店裡,眼睜睜看著本來應該跟落地窗垂直的招牌,竟然慢慢轉過來面向我們…… 」林齊晧無奈苦笑。接二連三的麻煩事,感覺像是冥冥中有股力量在整自己,導致他現在看到卡車路過,都死死盯著窗外。
➤有店主精選好書,還有熟客分享藏書 招牌緊急重製後掛上,鍾欣穎轉頭看著窗外安好的店招說,空間規劃不難,但想店名的過程有點頭痛。她想起在國外時曾造訪一家小小的獨立書店,推開門那一瞬間,店裡的明亮環境與溫暖氛圍讓她留下的深刻印象,「不只是下課後書店落地窗透出的光吸引著我,店員分享書的時候,她眼睛也在發光!」夫妻倆於是從「光」開始發想。光是個有趣的存在,代表著希望、信念,不同的宗教信仰與動漫都提過光。「一本書或一家書店,能讓人感受到那是有光的所在。我也希望這個空間能接納不同的光,想靜靜地照顧自己,或者成為別人的光都可以。」於是兩人將店名拍板定為「書房有光」。
招牌上的圖案是由林齊晧的妹妹設計,小小的三角形一端連著一道窄窄的長方形,「是門或書頁打開時,出現的那個空間意象。」鍾欣穎說道。
有光的所在,也是兩人合力打造的所在。書店裡有滿滿一排與兒童、性別有關的書籍,以及鍾欣穎四處搜集來的各國繪本。再往店內走,則是整櫃國際議題、歷史和台灣主題的著作。選書風格正反映了兩人各自的專業領域。
另一面書架上擺滿非賣品,是「限定閱覽圖書」,提供特別收藏的書籍讓讀者在店內閱讀。其中有全套《進擊的巨人》漫畫,那是一位住在附近的常客拿來分享的。林齊晧指著另一排書架說:「後來另一個「寶島少年兄」聽友看到,就說那他也分享《迷宮飯》好了,就拿來擺了。」還有聽友貢獻了動畫《暮然回首》的電影原聲帶。
這處留下許多空白的書櫃,反映了店主對於空間的期待——這裡不只是兩人風格與品味的延伸,也是和聽友、書友、過路客一起打造的場所,讓進來的人都能留下痕跡,為空間添上一抹顏色。
非賣品書架上還有許多兩人收藏的雜誌、復刻版日文漫畫週刊。林齊晧拿起一本以漫畫《凡爾賽玫瑰》為封面故事的日文雜誌,說起7月14日是法國國慶,也是《凡爾賽玫瑰》主角奧斯卡的忌日,碰巧串流平台幾個月前上架了《凡爾賽玫瑰》電影版,「我們就在奧斯卡忌日前一天辦了一場共讀會,還有人做了投影片來分享。」
林潔珊曾說,這個時代開書店很苦,「但肯定是有想做的事,才會來開書店。」林齊晧分享他對書店空間的規劃,能感受到擁有一個可恣意發揮的空間所帶來的興奮,「我還想到地下室可以改造成日本那種『沒截稿不准走出去』的咖啡店,把我們的作者關在裡面,交稿了才放他們出來。」
林齊晧笑著描繪他對空間的想像,鍾欣穎則是希望打造親子友善的場所。店裡的座椅高低錯落,有3、4歲的小朋友也能爬上去坐的沙發,她也準備了鋪在地上的巧拼軟墊,在廁所備有兒童馬桶坐墊,還一邊找尋合適的尿布檯。
在書店籌備期間,鍾欣穎走訪附近社區,探索周邊的發展歷史與人文議題,期待未來有機會讓書店作為社區工作的據點。性別議題書籍和奧斯卡共讀會;沒截稿不能出去的咖啡店和社區工作的據點,最嚴肅的議題與最詼諧的活動設計同處一室。
➤線上社群專屬的線下凝聚 奧斯卡共讀會後,迎來了7月26日第一階段大罷免。當天「書房有光」舉辦開票之夜,「大家看著開票數字,越來越沉默,沒人有心情開口。」開票之夜馬上變身療癒活動,「大家帶食物一起在店裡分享晚餐,聊一聊這個結果,聊到晚上11、12點,聊完覺得好多了。」林齊晧說道。那天參與的聽友,在留言本裡寫下當天相互取暖後,「體溫直接上升5度」。
幾天後,有個聽友安靜地來到店裡,「大罷免投票後,我們聽友的臉書社群裡有人發文說,因為罷免議題和家人政治立場相左,心情很沮喪。」同樣是聽友的小菜(他真的叫小菜不是打錯)說,社群裡的發文下,許多人安慰他,「還有人跟他約定,說自己隔天會去『書房有光』,如果有需要,可以一起來現場聊聊。」
隔天小菜正好到大橋頭附近,便也繞去「書房有光」。小菜選了個位子便處理起手邊的工作,「感覺很自在,七號和欣穎都在店裡,但他們不會過度招呼我,我就像待在朋友家客廳一樣。」那天越晚越多人來到書店裡,一人一句,氣氛熱絡。鍾欣穎提到:「有人說覺得大家能聚到一起很不現實,齊晧說:『我開書店也很不現實』。」也有心情沮喪的聽友安靜地窩在一角,聽著周圍的熱鬧,直到最後才害羞地現身自我介紹。
林齊晧指著另外一面書牆中間的古董寫字檯——那是鍾欣穎從一間結束營業的咖啡店裡撿回來的寶貝——拉開寫字檯的掀蓋,裡頭是新的「寶島少年兄」留言本,內頁已有不少聽友趁著試營運時來書店裡逛逛,留下文字。下方抽屜裡則有聽友做的貼紙、大罷免文宣。「我希望聽友來這裡可以有一些互動,所以放很多東西在裡面讓他們尋寶。」
➤分享書,分享點心,分享光 成為新手獨立書店經營者,各種雜事和待辦事項暴增,加上兩人都還各自有工作,當初推坑的林潔珊最怕兩人過勞。試營運一個月後,林潔珊到「書房有光」探班,「還好,他們氣色看起來不錯。」
不過,過去一直從事非營利與教育工作的鍾欣穎,如今經營書店,最不習慣的是要跟人「收錢」。非營利空間多是免費的,「突然要收錢,好像有點心理障礙。」鍾欣穎輕嘆一口氣,她曾遇到客人翻閱她精選的繪本後,拿了幾本來結帳,「結果我愣住,因為我不知道要定價多少錢。」林齊晧趕緊叮嚀:「這樣不行、這樣不行。」
相較於鍾欣穎,林齊晧則是想著各種旁門左道。「之前欣穎生日,我們買了蛋糕在書店裡慶祝,我想說這蛋糕切一切好像也可以拿出來賣給客人。」林齊晧眼角含笑打趣說著,鍾欣穎聽了則是隨即皺眉瞪他一眼。
9月的「書房有光」仍在試營運,林齊晧還在思索什麼時候要「正式營運」。一邊談著書店經營的想法,兩人一邊輪流接待一組又一組走進門的客人或熟人,來客一時多了起來,鍾欣穎忙著調製飲料,翻出聽友送的點心分享給在場每個人。
或許就一直維持彈性的試營運模式也無不可,就像這個空間裡主客邊界的彈性,線上聽友與線下共同體邊界的彈性,讓走進書店的客人更像是來到書房拜訪的友人,或閒聊或聆聽或閱讀,或只是靜靜地被光圍繞。●
營業時間: 13:00~20:00(每月開店日期請見粉專公告)請點此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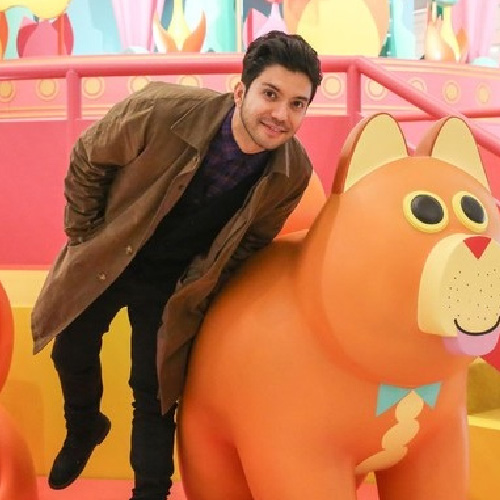

報導》像是待在朋友家般自在的書店:訪「書房有光」林齊晧與鍾欣穎
➤開書店如跳火坑嗎?
「我先生林齊晧跟我說他有個前同事要開書店時,我心裡想:『怎麼會有人要做這種事,有什麼我們可以幫得上忙的?』那時候覺得開書店這件事很辛苦,而且又很難賺錢,他們竟然要開書店!」兒童教育工作者鍾欣穎伸手捂著嘴,微微皺眉,「那時我們剛好在搬家,有一些傢俱,就想說可以送給他們書店用。」
說話的此刻,鍾欣穎就坐在這位「前同事」林潔珊開設的獨立書店「現流冊店」舊址,只是外頭的招牌已改名為「書房有光」。
去(2024)年底,鍾欣穎和林齊晧攜手跳入經營獨立書店的火坑,接下這處舊址,用半年時光籌備,今年7月開始試營運。曾經覺得開一家書店簡直是可憐的事情,如今兩人對望一眼,「結果小丑是我自己啦。」林齊晧一陣大笑。
「說起來是我們推坑他們的。」現流冊店店長林潔珊噗哧一聲。她曾在《鳴人堂》擔任編輯,林齊晧則是隔壁《轉角國際》的編輯,兩人因此熟識。2021年林潔珊離職,2022年末,現流冊店在大橋頭一處巷弄裡開張。
現流冊店開張後,林齊晧經常出沒在書店裡,有時乾脆和專欄作者約在這裡談事情,還會帶媽媽到現流吃潔珊特製的馬來西亞風咖哩飯。除了擔任編輯,林齊晧同時也是podcast「轉角國際.重磅廣播」和廣播節目「寶島少年兄」的主持人,以「七號」之名為網友熟知。他主持的幾場live podcast和作者座談會,都曾選擇在現流冊店舉行。
不少七號的聽友也會循聲來訪現流冊店,「書店裡有個留言小本本,裡面都是他們的聽友來現流後留下的文字。」林潔珊手指比劃出2、3公分的厚度。留言本是聽友共同體存在的證明,如今已幾乎被寫滿,2024年隨著現流冊店搬家,一同帶去了朝陽公園附近的新店址。
社群媒體時代的媒體與文字工作者,面對幾乎面目模糊的讀者,且經常接收到網路留言謾罵等負面回饋,林齊晧感覺到不少作者似乎因此深陷自我懷疑,「他們常會想:『寫這些有用嗎?』,尤其下面都是仇恨言論,看久了會很迷惘。」
但幾次實體座談中,作者與讀者面對面談話,或是live podcast時,到場的聽友分享那些空中的音頻如何改變了自己的人生或觀念。真實的人際互動,給了內容生產者更多能量,「很多作者辦完實體活動都法喜充滿。」林齊晧笑了笑。
➤喜歡看書,還喜歡推薦別人看書
實體的相遇充滿魔力,讓兩人考慮起是否該經營一處空間。林齊晧也觀察到,「疫情後,媒體流量下降,AI出現影響了資訊傳播與獲取方式。這些都讓實體互動變得更重要。」
人間相遇的魔幻時刻需要有場所才能實現。現流冊店打算搬家時,舊址的租約還有一年半,林潔珊想找熟人接手,便慫恿起身邊朋友,「來啦,來開書店啦!」林潔珊問了林齊晧,當時他有些躊躇,空間也很快被其他人租下。本以為無緣,沒想到後來再次輾轉釋出,「我覺得這是個徵兆。」於是他下定決心,打算斜槓經營書店,並邀請妻子擔任顧問。
「反正我們本來在家裡就很常跟朋友分享書籍,有時聊天聊到一半,會轉身找出一本書推薦給朋友。還有之前擔任Openbook好書獎評審,就更讓我們確信自己喜歡分享和推薦書籍,願意投入心力做這件事。」林齊晧笑言,反正自己平日買書數量簡直和書店進貨差不多,經營書店或許不過是把平日的購書行為,換一個形式進行罷了。
但是,簽下租約之後,魔鬼的考驗也正式開始,「先是實體書店的補助申請沒有通過。」鍾欣穎苦笑,原本盤算若能拿到補助,經營上相對比較沒有成本壓力,可惜碰上政府預算縮減,許多獨立書店都沒能獲得補助。
再來是裝潢時發現樑柱結構有毀損,接著又冒出白蟻危機。「我以前參與過公辦民營親子館的營運,大概有心理準備,籌備期就是可能會有各種不順。」專業是兒童發展領域的鍾欣穎,已體驗過一個空間在籌備時期的禍不單行,面對各種突發狀況波瀾不驚。林齊晧則是用失控的正向思考來應對,「為了滅蟲,我那陣子聽滅蟲的師傅講解一堆白蟻的知識,都覺得可以來辦一場白蟻防治的座談了。」
無獨有偶,7月新掛上的「書房有光」招牌,竟然被行經巷弄的卡車撞壞。「我們當時就坐在店裡,眼睜睜看著本來應該跟落地窗垂直的招牌,竟然慢慢轉過來面向我們……」林齊晧無奈苦笑。接二連三的麻煩事,感覺像是冥冥中有股力量在整自己,導致他現在看到卡車路過,都死死盯著窗外。
➤有店主精選好書,還有熟客分享藏書
招牌緊急重製後掛上,鍾欣穎轉頭看著窗外安好的店招說,空間規劃不難,但想店名的過程有點頭痛。她想起在國外時曾造訪一家小小的獨立書店,推開門那一瞬間,店裡的明亮環境與溫暖氛圍讓她留下的深刻印象,「不只是下課後書店落地窗透出的光吸引著我,店員分享書的時候,她眼睛也在發光!」夫妻倆於是從「光」開始發想。光是個有趣的存在,代表著希望、信念,不同的宗教信仰與動漫都提過光。「一本書或一家書店,能讓人感受到那是有光的所在。我也希望這個空間能接納不同的光,想靜靜地照顧自己,或者成為別人的光都可以。」於是兩人將店名拍板定為「書房有光」。
招牌上的圖案是由林齊晧的妹妹設計,小小的三角形一端連著一道窄窄的長方形,「是門或書頁打開時,出現的那個空間意象。」鍾欣穎說道。
有光的所在,也是兩人合力打造的所在。書店裡有滿滿一排與兒童、性別有關的書籍,以及鍾欣穎四處搜集來的各國繪本。再往店內走,則是整櫃國際議題、歷史和台灣主題的著作。選書風格正反映了兩人各自的專業領域。
另一面書架上擺滿非賣品,是「限定閱覽圖書」,提供特別收藏的書籍讓讀者在店內閱讀。其中有全套《進擊的巨人》漫畫,那是一位住在附近的常客拿來分享的。林齊晧指著另一排書架說:「後來另一個「寶島少年兄」聽友看到,就說那他也分享《迷宮飯》好了,就拿來擺了。」還有聽友貢獻了動畫《暮然回首》的電影原聲帶。
這處留下許多空白的書櫃,反映了店主對於空間的期待——這裡不只是兩人風格與品味的延伸,也是和聽友、書友、過路客一起打造的場所,讓進來的人都能留下痕跡,為空間添上一抹顏色。
非賣品書架上還有許多兩人收藏的雜誌、復刻版日文漫畫週刊。林齊晧拿起一本以漫畫《凡爾賽玫瑰》為封面故事的日文雜誌,說起7月14日是法國國慶,也是《凡爾賽玫瑰》主角奧斯卡的忌日,碰巧串流平台幾個月前上架了《凡爾賽玫瑰》電影版,「我們就在奧斯卡忌日前一天辦了一場共讀會,還有人做了投影片來分享。」
林潔珊曾說,這個時代開書店很苦,「但肯定是有想做的事,才會來開書店。」林齊晧分享他對書店空間的規劃,能感受到擁有一個可恣意發揮的空間所帶來的興奮,「我還想到地下室可以改造成日本那種『沒截稿不准走出去』的咖啡店,把我們的作者關在裡面,交稿了才放他們出來。」
林齊晧笑著描繪他對空間的想像,鍾欣穎則是希望打造親子友善的場所。店裡的座椅高低錯落,有3、4歲的小朋友也能爬上去坐的沙發,她也準備了鋪在地上的巧拼軟墊,在廁所備有兒童馬桶坐墊,還一邊找尋合適的尿布檯。
在書店籌備期間,鍾欣穎走訪附近社區,探索周邊的發展歷史與人文議題,期待未來有機會讓書店作為社區工作的據點。性別議題書籍和奧斯卡共讀會;沒截稿不能出去的咖啡店和社區工作的據點,最嚴肅的議題與最詼諧的活動設計同處一室。
➤線上社群專屬的線下凝聚
奧斯卡共讀會後,迎來了7月26日第一階段大罷免。當天「書房有光」舉辦開票之夜,「大家看著開票數字,越來越沉默,沒人有心情開口。」開票之夜馬上變身療癒活動,「大家帶食物一起在店裡分享晚餐,聊一聊這個結果,聊到晚上11、12點,聊完覺得好多了。」林齊晧說道。那天參與的聽友,在留言本裡寫下當天相互取暖後,「體溫直接上升5度」。
幾天後,有個聽友安靜地來到店裡,「大罷免投票後,我們聽友的臉書社群裡有人發文說,因為罷免議題和家人政治立場相左,心情很沮喪。」同樣是聽友的小菜(他真的叫小菜不是打錯)說,社群裡的發文下,許多人安慰他,「還有人跟他約定,說自己隔天會去『書房有光』,如果有需要,可以一起來現場聊聊。」
隔天小菜正好到大橋頭附近,便也繞去「書房有光」。小菜選了個位子便處理起手邊的工作,「感覺很自在,七號和欣穎都在店裡,但他們不會過度招呼我,我就像待在朋友家客廳一樣。」那天越晚越多人來到書店裡,一人一句,氣氛熱絡。鍾欣穎提到:「有人說覺得大家能聚到一起很不現實,齊晧說:『我開書店也很不現實』。」也有心情沮喪的聽友安靜地窩在一角,聽著周圍的熱鬧,直到最後才害羞地現身自我介紹。
林齊晧指著另外一面書牆中間的古董寫字檯——那是鍾欣穎從一間結束營業的咖啡店裡撿回來的寶貝——拉開寫字檯的掀蓋,裡頭是新的「寶島少年兄」留言本,內頁已有不少聽友趁著試營運時來書店裡逛逛,留下文字。下方抽屜裡則有聽友做的貼紙、大罷免文宣。「我希望聽友來這裡可以有一些互動,所以放很多東西在裡面讓他們尋寶。」
➤分享書,分享點心,分享光
成為新手獨立書店經營者,各種雜事和待辦事項暴增,加上兩人都還各自有工作,當初推坑的林潔珊最怕兩人過勞。試營運一個月後,林潔珊到「書房有光」探班,「還好,他們氣色看起來不錯。」
不過,過去一直從事非營利與教育工作的鍾欣穎,如今經營書店,最不習慣的是要跟人「收錢」。非營利空間多是免費的,「突然要收錢,好像有點心理障礙。」鍾欣穎輕嘆一口氣,她曾遇到客人翻閱她精選的繪本後,拿了幾本來結帳,「結果我愣住,因為我不知道要定價多少錢。」林齊晧趕緊叮嚀:「這樣不行、這樣不行。」
相較於鍾欣穎,林齊晧則是想著各種旁門左道。「之前欣穎生日,我們買了蛋糕在書店裡慶祝,我想說這蛋糕切一切好像也可以拿出來賣給客人。」林齊晧眼角含笑打趣說著,鍾欣穎聽了則是隨即皺眉瞪他一眼。
9月的「書房有光」仍在試營運,林齊晧還在思索什麼時候要「正式營運」。一邊談著書店經營的想法,兩人一邊輪流接待一組又一組走進門的客人或熟人,來客一時多了起來,鍾欣穎忙著調製飲料,翻出聽友送的點心分享給在場每個人。
或許就一直維持彈性的試營運模式也無不可,就像這個空間裡主客邊界的彈性,線上聽友與線下共同體邊界的彈性,讓走進書店的客人更像是來到書房拜訪的友人,或閒聊或聆聽或閱讀,或只是靜靜地被光圍繞。●
營業時間: 13:00~20:00(每月開店日期請見粉專公告)
地址: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25巷26號
粉專連結:請點此。
閱讀通信 vol.369》出烤箱的好日子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