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題》少女暴行之死的根源,乃名為「母性」的重重業障:讀《八月之母》
「我也要勉強自己照顧母親,就像母親勉強自己把我養大那樣嗎?」美佐子這種想法就顯示出,母女關係的困難,有一部分是來自環境,亦即社會或一般大眾強加在她身上的。
──齋藤環《弒母情結:互相控制與依存的母女戰爭》
2014年8月15日凌晨,日本愛媛縣伊予市警方接獲報案,在一棟廉價集合住宅(俗稱團地)的三樓房間日式壁櫥內,尋獲一具被毯子緊緊包住的屍體。搜查人員隨後透露,死者的狀態不堪入目,臉孔腫脹發紫、口腔內僅存一顆牙齒,甚至被傷害到看不出性別,死因是蜘蛛網膜下腔出血及內臟破裂。「肯定每天都遭受私刑暴力對待!」
警方逮捕了36歲的女子,屋主窪田惠和幾名青少年,其中包含女子16歲的兒子。經過周邊調查,17歲的死者大野裕香與窪田一家同住,起初關係融洽,最後卻被暴力凌虐致死。起訴後法官對8名加害者中唯一的成年人窪田惠判下11年的有期徒刑,並強調沒有任何酌情減刑的餘地。其餘未成年則分處3至8年的不定期刑,「伊予市少女暴行殺人事件」在2015年的審判後迅速落幕。
➤你所不知的愛媛
愛媛是日本觀光勝地,有氣勢雄壯的松山城、古色古香的道後溫泉、安藤忠雄設計的坂上之雲博物館等景點。因為得天獨厚的自然絕景,許多經典動漫作品,巧妙將故事背景置入於此。宮崎駿《神隱少女》的油屋澡堂取景自道後溫泉本館、京阿尼《境界的彼方》與足球名作《青之蘆葦》出現具鄉愁存在感的下灘車站,今年上映的新海城大作《鈴芽之旅》,也幾乎原汁原味重現八幡濱港口、大洲城。

2016年移居愛媛縣的小說家早見和真,在松山市的居所度過了難忘的6年。他積極觀察、參與城市的活動,並結合進創作。他與繪本畫家合作,在《愛媛新聞報》連載的「悲傷的胖貓」圖文童話廣受歡迎,還改編成動畫版。故事藉由胖貓在愛媛的旅遊過程,呈現濃厚的在地人文風情。但是,前幾年遭遇新冠肺炎的疫情封城,早見陷入前所未見的寫作瓶頸。
「出道12年,這是我第一次無法寫出東西。世界改變了,我很想知道是否能夠找回以前寫作的感覺。」2019推出長篇小說《皇室》後,因疫情影響不再能好好寫出文字的早見,隔年夏天進行了採訪高中棒球員的記錄片工作。
努力打球,卻因為疫情停賽而喪失打進甲子園的夢想,但小球員並沒有因而頹喪,反而認為「就算沒有甲子園,打棒球還是很有趣!」這個回應也化解了早見的心魔,他決心趕快面對寫小說這件事,於是接下《野性時代》的邀請,開啟了《八月之母》的連載。這部作品採取與《悲傷的胖貓》截然不同的角度,揭開早見親眼所見所聞的,愛媛的陰暗面。
➤惡鬼藏身何處
日本的犯罪率很低,2020年法務省公布的《犯罪白皮書》統計顯示,近5年兇殺案發生率(以每10萬人為單位)僅有0.2件,比起歐美先進國家要少得多。若更進一步觀察47都道府縣的重大犯罪數據,愛媛縣在四國中更一向是治安良好的模範生。正因如此,「那起事件」格外銘刻於愛媛人記憶中。以描述女性犯罪的《無罪之日》榮獲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的早見搬到松山後,常被當地人問起的問題便是:「喔喔,你知道那個事件嗎?」
「伊予市少女暴行殺人事件」悲劇的發生早有徵兆,原來窪田家被鄰里視為麻煩的無法地帶。許多不良少年少女進出,半夜大聲喧嘩酗酒放音樂,甚至在陽台上放煙火,行徑囂張脫序。團地居民有人因害怕搬走,也有人多次向市府與警方報案,並反映看過(日後的事件受害者)大野裕香被毆打得鼻青臉腫。然而市府與警方相互推託、警方甚至回應「沒有發生案件就無法出動」,事後受到輿論嚴厲批判。因為這起無可挽回的悲劇,伊予市成立了市府、警局和兒福中心的跨部門聯絡組織,革新了防治少年、老人受虐的安全網。
日本青少年集團犯罪在20世紀末連續爆發:1989年女高中生水泥埋屍案、1999年栃木私刑殺人事件的殘酷性,酒鬼薔薇聖斗事件導致民怨,促使原先寬鬆的少年法修法。

相較之下,伊予市少女暴行事件並沒有受到太多關注,除了地點偏遠,世人的心證更因加害少年們的供述而有顯著差異。據說,窪田惠在家中是絕對的權力中心。她從不自己動手,而是側面以話語煽動男孩們行使暴力。有少年說,「我想透過暴行取得惠的稱讚與認可。」法官與媒體也將猛烈的砲火集中在窪田惠身上,批判她如同尼崎事件的「鬼女」角田美代子、或福岡二手店連環殺人的「惡魔妻」中尾知佐的惡女再現。比起青少年犯罪,本案性質更被視為大人「教唆」無知小孩。
然而,幕後真相就是這麼一回事嗎?同為加害者,難道沒有人為了推卸責任而說謊?韓劇《少年法庭》曾出現青少女聯手謊稱收容中心虐待她們,只是為了教訓主事者,讓自己過得更輕鬆的案例。報導中的窪田惠確實外貌「不良」,領取生活保護金度日,不配合社區規範,法庭上也沒有多做辯解。她的人設很容易讓讀者聯想到《無罪之日》的死刑犯田中幸乃,是輕易為世人唾棄的對象。
早見因此做出了一個大膽的「假設」,並親自造訪20名認識窪田惠的愛媛人,徵詢他們的反應,也取得廣泛認可的回應。這讓他確定了《八月之母》的方向:挑戰一個敏感的議題。
➤母之前是女
《八月之母》小說分為二部曲,並從序章開始,不斷穿插一位懷胎母親的第一人稱敘事。她在東京過著美滿家庭生活,心中卻懷抱著「沉入瀨戶內海的夕陽令人鬱悶」的無窮黑暗。她是誰?為什麼狼狽逃離故鄉愛媛、與母親斷絕聯繫?開頭就讓讀者好奇不已的懸念,直到小說中段才會被驚愕地揭開。
第一部「於伊予市」講述自1977年8月至2000年8月這24年間的漫長時間。家庭關係緊繃窒息的越智美智子,在小學六年級時隨著母親離家,兩度投靠不同的男人,最後落腳伊予市。年輕力壯的繼父一郎,肆意地在房內與母親交合,更對未成年的美智子露出虎視眈眈的笑容……對美智子來說,這間房子彷彿由沙子堆成,隨時都會崩塌毀滅。

歷經一連串事件,25歲的美智子經營著小酒店,活得行屍走肉。孤獨感作祟與某次的心血來潮,她決定不再打掉孩子,把父親不詳的女嬰生下,以觸動自己心弦的花名「Erica」為她命名惠梨香。追求幸福,卻屢被男人、家人背叛的美智子,想要再活過來一次,和惠梨香一起幸福開心。
惠梨香在小學五年級、國中三年級和23歲時,接連發生不同的故事。沒有父親、母親也在特種行業中逐漸墮落,惠梨香得不到家庭之愛,一直都很寂寞。三名男性在這三個時間點,對不快樂的惠梨香展露了關心與協助。然而,男人們的關心總是伴隨著慾望,所有付出都期待女性肉體的等價交換,甚至在不可得時行諸暴力。男人們不約而同在面臨「非典型母親」美智子的壓力時選擇逃跑,留存在惠梨香心中的只有無奈與放棄。
第二部「於公宅」,時間點跳躍至2012年6月至2013年8月之間。女主角是16歲少女清家紘子,她偶然造訪男友越智麗央的公宅住處,被屋主惠梨香及她的小女兒所吸引。兩房兩廳的狹窄住家時常人滿為患,擠進一堆青少年。惠梨香是個熱情洋溢的大姊姊,總是一視同仁地慷慨供餐與照顧他們,公宅是個溫馨和樂的大家庭。紘子越來越喜歡與依賴這個安身處,然而事態卻逐漸失控……
➤狹窄、迂腐,所以恐怖
《八月之母》是一部深刻描寫母性,探索親子之愛、家族之愛及「人類的業障」的長篇史詩。惠梨香是貫穿全書的核心人物,也是早見試圖針對窪田惠描繪的假設形象。
惠梨香的背影,其實與踏上旅途的《悲傷的胖貓》重疊。然而胖貓走向寬廣的世界,惠梨香與美智子卻被禁錮在伊予市內,想逃離鄉下,卻沒有足夠的生活能力與金錢。兩部作品充分映照出愛媛的光與影,女兒繼承了母親的怨恨,仇恨她卻又無法割捨掉她——哪有人能輕易地拋棄說出「不要丟下我」的親生媽媽呢?
早見和真指出,搬到愛媛生活最初帶給他的文化衝擊,便是驚訝於此地民風是多麼地保守、男尊女卑的傾向又是多麼鮮明。每個人都是傳統家庭的「俘虜」,「因為我是父親,所以我就是這樣」、「因為我是母親,所以我就得這樣」……小說中藉由紘子離鄉的哥哥之口,犀利地描寫出作者的觀察:
久久一次回到這裡來,不論是好的地方或不好的地方,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好的地方就是這裡在石鎚山的庇護下,極少受到災害。還保留著古老文化的地方也很不錯,都是愛媛的獨特景色。不好的地方也是因為長久以來一直被守護下來,才會變成那樣。以負面的角度來說,這裡非常傳統。有時候真的會被嚇到,想說為什麼男人可以一副自己很了不起的態度對待女人?

這種根深柢固的陳腐價值觀,其中一個面向就是「母性」的假象。早見認為,根據經驗,不只在愛媛,日本各地有太多熱衷於「當個好媽媽」的女性。她們被母性規則所束縛,大多認真安分,卻因此受苦。扭曲的母性,正是「伊予市少女暴行殺人事件」的根源。而悲劇的催化劑,更來自於整個社會,惠梨香(窪田惠)本身也是受害者,被錯誤的母性觀點所擺布。
所以早見需要以厚重的篇幅,寫下越智三代母女的人生。他所刻劃的是瀰漫於日本這個國家,尤其是盤據在伊予等鄉間的「沉悶空氣」。男性主掌的世界要求女人的母性,甚至老師認為自己做出任何事,小女孩都會原諒他,「因為女人從出生時即擁有母性」,以此來合理化戀童癖行為。
➤從母性逃離
倘若母親並不存在母性,該怎麼辦呢?就像美智子以「我自己也是啊,我的母親什麼也沒有教過我,我以前也幾乎沒有去學校上課」的說詞來肯定自我,惠梨香自小遭遇情感忽視(Emotional neglect)虐待,導致她長大後變得極端渴求母性,想要成為好媽媽。她把自己沒有得到的愛,加倍地灌注給孩子,也因此打造公宅這座堡壘。
問題在於,為什麼保護與教養孩子的責任都落到女性頭上?因為她們被賦予了無條件為孩子付出的「母性」神話。美智子母女的男人運差,不是她們不想「正常」過活,而是嘴上說著好聽話、床上肆意發洩慾望的男人們,終究把她們棄若敝屣,丟下應盡的責任,把她們逼入獨力撫養孩子的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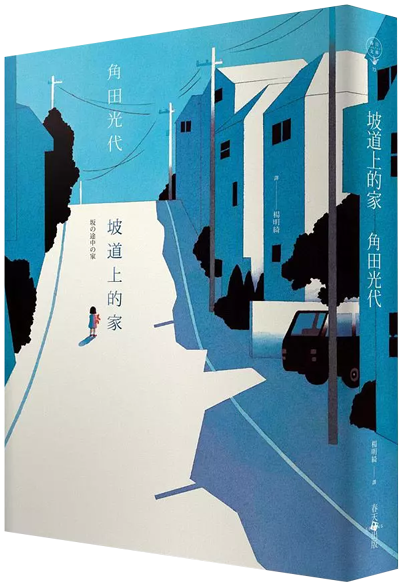 筆者認為最驚悚之處在於,鄉下女性的悲哀已經不僅僅是出嫁從夫,而是連想要「組成家庭」的基本尊嚴,都被踐踏與歧視。
筆者認為最驚悚之處在於,鄉下女性的悲哀已經不僅僅是出嫁從夫,而是連想要「組成家庭」的基本尊嚴,都被踐踏與歧視。
至於成為母親的鄉下女性,往往將沉重的鎖鏈繼續綑綁住下一代,因為她們只懂得這種生活方式。同樣處理母性議題的角田光代《坡道上的家》提到:「鄉下地方有著不可動搖的信念與原則。縱使再怎麼說明這是多麼偏頗的觀念,也無法改變當地人的想法。」出身類似的作家辻村深月也表達認同,鄉下的團結排外意識強,在地人一旦離開就被劃為異己,而造就出一種「年輕人嘴上說著要離開,卻沒有人是認真的」常態。居於男權家庭中最弱勢的「母女關係」,也跟著仰賴彼此為重重的「業障」。
惠梨香在家庭與愛情中絕望,所剩的選項就是拚命追求自己的樂園,只是人越來越多、群體消極「空氣」漸漸膨脹失序的公宅已日益失控。她的出發點是純然的善,結局卻落入絕對的惡。
早見想說的是,犯罪是層層社會結構失能破洞所引發的連鎖效應,只是人們太過輕易盲信與攻擊著自以為是的「罪魁禍首」。紘子無數次想返校學習,卻被學校的冷漠氛圍逼得走投無路,只能一直逃回公宅取暖。故事中沒有惡人,事件的所有加害者與受害者想要的,只是一處歸屬。沒有提供歸屬的我們,怎能事不關己地指責她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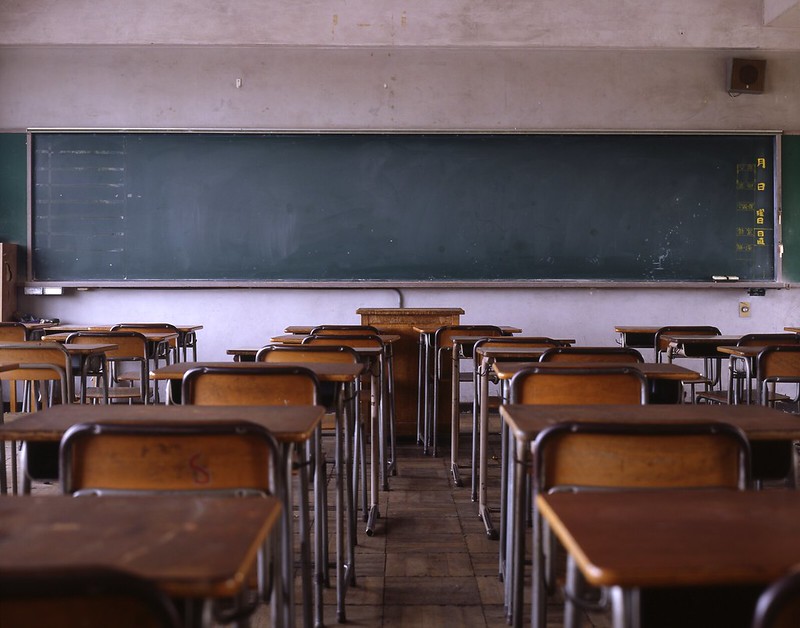
現實中的大野裕香「學壞」了,那促使她退學逃家的理由是什麼?原生家庭沒有責任嗎?她的父親在隔年受訪時艱難地透露:「這意味著那裡(團地)更舒服,無論她做了什麼事都不會被罵。我們是一個普通的家庭,所以我們會對她有要求。她在那裡感覺更舒服,就只是這樣。」
或許真相不只如此,窪田家二女兒在偵訊中回答了她的論點:為何裕香死命忍耐著被毆打的生活也不離開團地?因為她內心一直夢想著回到之前那段「幸福」的日子,原生家庭無法給予的日子。
《八月之母》尖銳地質疑了過時的家庭觀和鄉下縣市的陋習,看似探討一個舉世皆然的主題,但鎖定於愛媛真實事件後,卻又非常接日本地氣,精采至極。演員池松壯亮深深折服於本作的「筆壓」(氣場),辻村深月在體悟到結局關於神祕女主角的抉擇涵義後,以「渾身起了雞皮疙瘩」的震憾從頭再次閱讀一遍這部致鬱系傑作。
早見希望這本書能讓為母性所困的女人們活得更為自由,放下那份虛妄,並勇於相信與母性「訣別」後的希望。●
|
|
|
作者簡介:早見和真 1977年生於日本神奈川縣。定居於愛媛縣。2008年以《108》一書踏入文壇。2015年以《無罪之日》榮獲第68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賞(長篇暨連作短篇集部門)、以《ザ・ロイヤルファミリー》一書榮獲2019年度JRA賞馬事文化賞以及第三十三屆山本周五郎賞。而後,以《雖然店長少根筋》一書榮獲2020年本屋大賞第九名、《あの夏の正解》一書獲得「2021年Yahoo!新聞|本屋大賞紀實書籍大賞」提名。其他著作包括《スリーピング・ブッダ》、《95》、《ぼくたちの家族》、《笑うマトリョーシカ》、《かなしきデブ猫ちゃん》(插畫:加納果林)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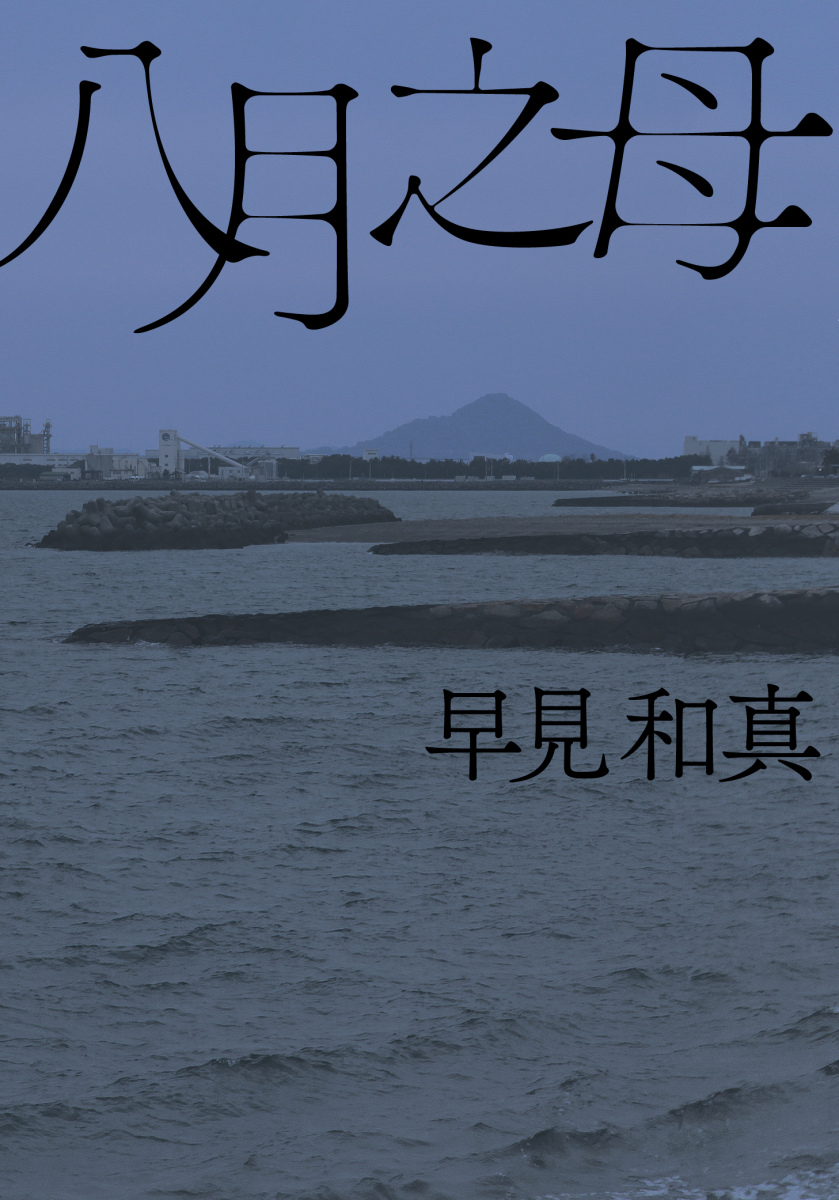 八月之母
八月之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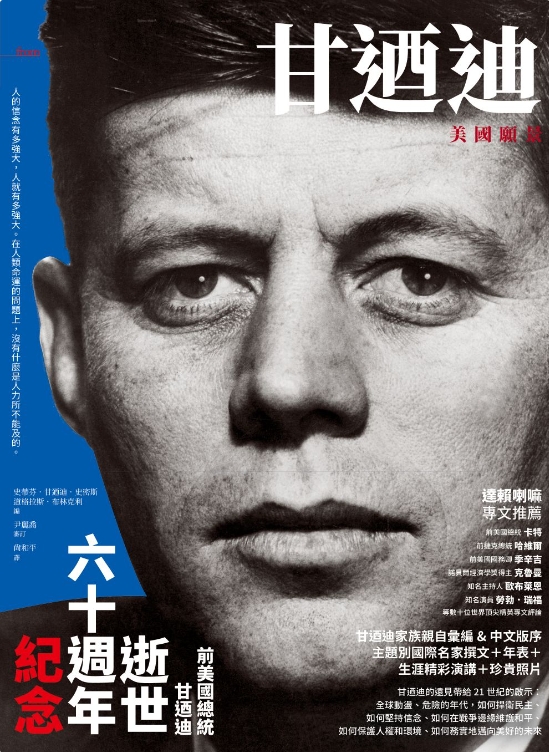
漫評》在青春的漩渦中:讀淺野一二O《錯位的青春》
畫風無害、內容卻超乎想像寫實震撼的《晚安,布布》系列漫畫,2008年在台灣翻譯出版後,淺野一二O的獨特的風格便逐漸被讀者認識。《錯位的青春》改編電影去(2022)年底在台灣上映,讓讀者能用另一種觀看角度感受十多年前原作帶來的震撼,漫畫新裝版也在近日重版出來。
這十幾年來,只要是會播放另類搖滾、日本老city pop與lo-fi hiphop beats的文青咖啡店,總會有不小的機率在書架看到一、兩套淺野一二O的單行本。
淺野一二O,有人會把他的名字讀成「一二零」,其實數字後面那個O,是大寫英文字母O。對淺野作品如數家珍的讀者,就會知道這個筆名源自他的保險證編號。
淺野從高中開始玩樂團,漫畫分格具有音樂韻律感,是他的作品特色之一。印象中,淺野的漫畫總是把瞪鞋搖滾的吉他音浪視覺化,以細密的筆觸呈現在框格內。漫畫角色多以沾水筆繪製,背景、網點與效果則仰賴電腦,得以在作品中呈現栩栩如生又不突兀的構圖。
自從用電腦完稿以來,漫畫背景大多來自他親手拍攝的照片,後來導入3D造型與人工智慧算圖,更呈現出壯觀場面。淺野持續發表不同視覺風格的作品,例如:《Solanin/樂與路》(ソラニン,2005-2006,英譯版入圍2009年美國艾斯納獎最佳外國漫畫)或《晚安,布布》(おやすみプンプン,2007-2013)等。後來他以故事引人入勝的《Dead Dead Demon's Dededede Destruction惡魔的破壞》榮獲2021年小學館漫畫獎一般部門獎,以及2022年文化廳媒體藝術祭漫畫類優秀獎等榮譽。
本文要介紹的《錯位的青春》(うみべの女の子,2011)是他創作生涯進入第二個十年的中篇作品,篇幅約400頁。故事發生在閑散的漁村,角色不以漂亮可愛為號召,從手機款式變化可看出,背景時空約從2000年代到2010年左右。敘事主線是女主角小梅與同學磯邊發生性關係後的心境轉折。
縱使性描寫在本作品中佔去一定篇幅、也出現幾個打鬥場面,我們仍然很難像衛道人士一樣,為這部作品直接扣上「色情」、「暴力」的帽子。色情與暴力顯然不是《錯位的青春》敘事重心,最後兩人是否順利交往,並不是這部作品想要交代的主題。然而,故事設定在那個號稱「海邊到了夏天也人煙稀少」的破舊漁港,青春漫畫的場面彷彿也蒙上一層陰影。
➤破舊漁村裡,苦悶青少年的性探索
男主角磯邊父親從事遊戲產業,母親經常往返日本與台灣。他小學時代跟著父親從東京一起搬到這個漁村,算是外地人,哥哥在學校受到欺負而自殺,卻被警察以意外死亡處理。他心底不時浮現死去哥哥的身影,想為哥哥做些什麼事情以告慰其在天之靈,往往事與願違。
在父母經常不在家的情形下,磯邊接手哥哥生前管理的動漫懶人包部落格,並且與匿名網友、女主角小梅在網上對話。與磯邊一樣瘦瘦小小的、留著平頭的弟弟鹿島,與小梅從小學就認識,對小梅有點好感,結果小梅先跑去跟學長三崎告白,失敗被甩,又跑去跟磯邊摸來摸去。兩人在稀疏平常的漁村生活中偷偷地破處。
限制級描寫後的一連串對話,讓前面發生的畫面顯得「無足輕重」。小梅可以大方出入磯邊房裡打炮,但始終介意他用來當作電腦桌布的不明少女照片。
淺野在作品一開頭,安排磯邊在帶小梅回家路上撿到SD卡,記憶卡裡面有穿著泳裝的少女留下的許多照片,而這正是原日文書名「海邊的女孩」由來。但淺野並不解釋海邊少女「本尊」與作品意義的關聯性,而是讓陳悶的背景氣氛向讀者說話。
磯邊處在思春期,除了嘗試性行為與手排,還嘗試後庭開發。看似可笑的畫面,作者卻不以成年人的道德高度進行批判。作品中的阿飛角色三崎,在上集先是對小梅始亂終棄,到了下集被磯邊報「殺兄之仇」後,在警察面前整個跩樣都不見了,變回鄉下苦悶青少年的樣子。
前面框格埋藏的伏筆,容易在細緻的畫工下被忽略,但到了後面一說明白,讀者就不得不佩服作者的安排。台版書名的「錯位」也取得恰到好處:即使兩人肉體糾纏在一起並且說了真心話,最後青春仍然錯位。
➤視解轉換及重複背景:超越電影動態的漫畫手法
本作品令讀者印象最深刻的場面,莫過於單行本下集,學校文化祭當天突然颳起颱風,小梅冒著狂風暴雨去海邊找磯邊的過程,同時學校文化祭的學生電台播放日本搖滾樂團Happy End的名曲〈收集群風〉(風をあつめて,1971)。
淺野不僅從曲中汲取靈感聯想畫面,讀者好奇從網路上找到這首曲子以後,順著頁面順序一直看下去,還會得到一種不同於音樂影帶與「蒙太奇理論」的節奏感。
默片從娛樂變成嚴肅藝術以來,強調無機符號有機組合的「愛森斯坦蒙太奇」(例如愛森斯坦的《波坦金戰艦》Battleship "Potemkin",1925)與用不同攝影機同時拍攝一場戲,透過視角轉換產生動態感的「格里菲斯蒙太奇」(例如黑澤明的《七武士》,1954),不僅用於電影與電視上,也回過頭來被應用在漫畫分格上。
不論漫畫之神手塚治虫的〈COM〉、《GARO》雜誌白土三平等「劇畫」志向的漫畫家,乃至於同一時期少女漫畫所謂「花之二十四年組」(青池保子、萩尾望都、竹宮惠子、山岸涼子、大島弓子……等,於1949〔昭和24〕年前後出生的新人),都致力於推翻既有連環圖畫書思維的分格方式與敘事節奏。不僅在故事、畫面表現上跳脫舊有漫畫的窠臼,也反映出對電影與音樂的愛好,其中包括電影語法的引用。
早年直接由暢銷漫畫改編的電影,常常直接以漫畫書的分格指示演員「站在這裡、站在那裡」; 漫畫呈現許多攝影機鏡頭很難擺出的角度與構圖,並且讓角色呈現真人也很難表現的動作。即使是靜止畫面,都能形成獨有的動態感。
劇情以外,另一值得觀察的元素,是框格內背景的重複。
這種手法相當於電影電視的長鏡頭,但未必用於角色的較長台詞。除了角色在畫面角落的動作,每一格看起來幾乎一模一樣。這種手法早在40餘年前,就曾經被大友克洋的短篇漫畫〈睡美人〉(眠れる森の美女,收錄於短篇集《糖果屋ヘンゼルとグレーテル》,1980)運用過:密林深處的城堡中,有位公主一直睡,讀者在看了連續幾格相同畫面後,公主突然在其中一格翻身。
以老太婆、排泄物等各種直球低級笑點見長的漫☆畫太郎(目前台北「唐吉訶德」賣場可以找得到由他繪製包裝的零嘴),只要遇到故事畫不下去,也會大量使用影印機複製單一原稿混稿費,讀者再怎麼喊罵也拿他沒轍,只能迎向最後的毀滅結局。淺野的重複背景,不再需要影印機,因為他意識到鏡頭擺位能營造更強烈的電影感。
以電腦檔案格式出稿的另一個好處,就是動態影像可以直接使用漫畫底稿的共通資料,節省轉換手續。他於2016年為日本Mynavi房屋租賃服務繪製動畫短片,雖以格數少的2D動畫與動態美工(motion graphics)的圖層移動變形為主,15秒動畫完全就是他的漫畫風格。
➤青春的窘境與淡淡餘韻
用文青喜歡的畫風,去描繪讀者即使身為大人,也難免會遇到的苦境窘境,是圖像文學值得經營的重點。同樣描寫少女複雜心境的日本成年漫畫作品,則首推《今日的貓村小姐》(きょうの猫村さん,2005─)作者星余里子的圖像小說《逢澤理玖》(逢沢りく,2014)。
同樣具有兩本單行本篇幅的《逢澤理玖》,完全以鉛筆與手寫字構成,背景也走極簡路線。描述嬌生慣養的都市少女,舉家搬遷至日本關西。如何在陌生鄉土卸除層層心房,真正為了內在心情──而非引人注意──而哭的歷程。儘管鉛筆與水彩繪製的頁面,通常簡潔到僅剩角色、話框與桌椅窗等線條,卻以獨到敘事手法贏得讀者與評論的肯定,並且榮獲2015年手塚治虫文化獎的漫畫大獎。
大概沒人會想到要把同樣以14歲少女為主角的《錯位的青春》與《逢澤理玖》放在一起看,但是經過社會洗禮的讀者,必能從這兩部作品中感受到青春淡淡的餘韻。
➤淺野代表作與改編
淺野代表作之一、搖滾樂漫畫《Solanin/樂與路》已經先於2010年被改編成電影,原作裡的同名曲也被Asian Kung-fu Generation改編成電影主題曲。台灣上映時的片名取作《手拉你》,電影海報也曾經出現在許多咖啡館裡。
在電影拍攝時期連載的《錯位的青春》,10餘年後也被音樂錄影帶導演上田篤司忠實地改編成電影版,淺野大方提供繪製本作背景素材的拍攝地點,需要大膽場面的主要角色,均由已成年演員飾演,配樂上又找來World's End Girlfriend製作與詮釋,淺野本人對於拍出來的成品也頗為滿意。
強調硬派懸疑元素的《零落》(2017)後來被演而優則導的竹中直人相中搬上大銀幕,由日活與Happinet Phantom Studios聯合發行,3月於日本上映。在本片的首映記者會上,竹中盛讚淺野是「現代版的芥川龍之介」。在淺野創作走向多元類型與國際化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將舞台集約在漁村少年少女身上,並且高度結合數位漫畫技術完成的《錯位的青春》,視為淺野前期的創作縮影。●
作者:淺野一二O
譯者:涂博惟
出版:台灣東販
定價:250元
【內容簡介➤】
作者:淺野一二O
譯者:涂博惟
出版:台灣東販
定價:25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淺野一二O
1980年生,1997年在小學館的雜誌增刊號上刊載《普通の日》後出道,2001年在《SUNDY GENE-X》月刊,以《宇宙からコンニチハ》得到第一屆GX新人獎。2005年發表超越性別與世代,喚起真確共鳴的超話題作品《SOLANIN》(ソラニン),曾經被改編成電影《手拉你》(2010),表現出新世代的人們的愛情觀、人生觀。2007年開始於《YOUNG SUNDAY》上連載《晚安,布布》。《錯位的青春》亦改編成同名電影,由《櫻之雨》導演上田篤司忠實呈現作品世界觀,由石川瑠華、青木柚共同主演,2021在日本上映、2022年臺灣上映。
作品包括:《光之城》、《SOLANIN》、《多美好的人生》、《虹之原》、《世界末日與黎明前》、《Ctrl+T淺野一二O的漫畫世界》、《錯位的青春》、《晚安,布布》、《零落》、《淺野一二O短篇集》、《DEAD DEAD DEMON'S DEDEDEDE DESTRUCTION惡魔的破壞》等。
閱讀通信 vol.368》台北國際書展,來襲!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